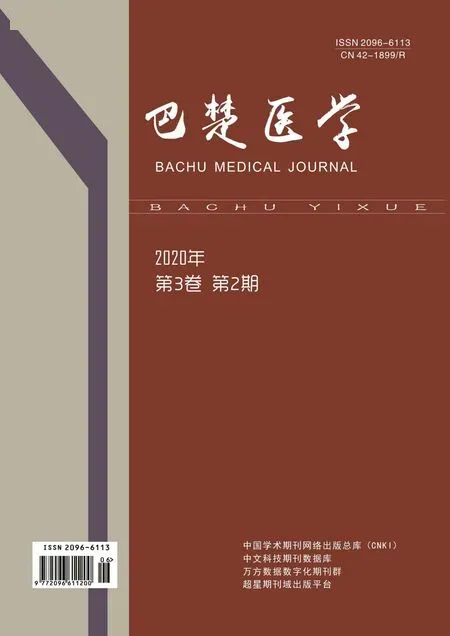黏蛋白在结直肠黏液腺癌中的研究进展
李中胜 陈爱军
(三峡大学 第一临床医学院[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胃肠外科, 湖北 宜昌 443003)
结直肠恶性肿瘤是一类具有高发病率和高死亡率的消化道恶性肿瘤。据国家肿瘤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2015年我国结直肠恶性肿瘤的发病率、死亡率在所有肿瘤性疾病中分别排在第3位和第5位,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1]。结直肠黏液腺癌的发病率占全部结直肠恶性肿瘤的4%~19%,是一种少见的结直肠癌病理类型,有着与非黏液性结直肠癌不同的临床病理特征、遗传概况及组织发生途径[2]。同时,与非黏液性结直肠肿瘤相比,结直肠黏液腺癌患者往往预后极差,并对化疗等辅助治疗反应不佳。因此,结直肠黏液腺癌往往被视为影响结直肠恶性肿瘤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在结直肠黏液腺癌的发生及发展过程中,黏蛋白(mucoprotein, MUC)起到“润滑剂”及“保护膜”的作用。本文围绕MUC对结直肠黏液腺癌发生、发展及对耐受辅助治疗的作用进行综述。
1 黏液腺癌与黏蛋白概况
黏液腺癌是一类黏液性细胞外基质超过肿瘤灶50%的恶性肿瘤。在结直肠黏液腺癌中存在两种预后截然不同的亚型,根据其错配修复基因突变程度差异,可分为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of a high level,MSI-H)亚型与微卫星稳定(microsatellite stable,MSS)亚型[3]。有研究表明,黏液腺癌MSI-H亚型的预后比MSS亚型及非黏液性结直肠恶性肿瘤更好,且发病率比MSS黏液性肿瘤低[4]。造成这种差异的具体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MSI-H黏液腺癌MUC5AC表达活跃使肿瘤细胞转移能力下降有关。而在MSS结直肠肿瘤中,MUC5AC可因启动子甲基化而表达受抑[5]。结直肠黏液腺癌MSS亚型(下文称黏液腺癌),主要发生于右半结肠,继发于结直肠无柄锯齿状息肉(sessile serrated adenoma,SSA)瘤变。与染色体不稳定导致的大多数结直肠肿瘤不同,黏液腺癌起源于MAPK信号传导通路的BRAF突变[6]。MAPK通路是细胞信号传导的关键部分,介导细胞外信号对细胞生长、分化和凋亡的反应。BRAF突变时启动子高水平胞嘧啶-鸟嘌呤二核苷酸(cytosine-guanine pairs,CPGs)甲基化,造成抑癌基因P16及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O6-methylguanine-DNA-methyltransferase, MGTM)表达缺失,导致了黏液腺癌的发生与发展[7]。
构成黏液腺癌细胞内外黏液成分的主要物质是MUC,它是一种由超过总分子量50%的O型寡聚糖链与含有大量脯氨酸、苏氨酸和丝氨酸的蛋白核心组成的糖蛋白,可分为分泌性MUC(MUC2、MUC5AC、 MUC5B、 MUC6、 MUC7、MUC8与MUC19等)与跨膜MUC(MUC1、MUC3A、MUC3B、MUC4、MUC11-13、MUC15-17、MUC20、MUC21和MUC22等)两类。在正常肠道组织中,MUC由肠上皮杯状细胞产生并分泌于肠腔表面,在保护肠粘膜、免疫传递、维持肠道菌群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8]。而在SSA的瘤变过程中,位于11p15.5染色体上的MUC基因失控,以MUC1、MUC2及MUC4为主的MUC表达上调并大量分泌至细胞膜上或细胞外,水化并形成黏液,是黏液腺癌的主要病理学特征,并对肿瘤的发展产生影响[9]。
2 黏蛋白与肿瘤免疫
肠道中有丰富的淋巴管网及完备的免疫防御机制。分布在肠道组织中的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是肠道免疫系统中的主要抗原提呈细胞,主要发挥免疫监视作用。当树突细胞伪足上的组织相容性受体识别到肿瘤细胞表面的肿瘤特异性抗原时,可吞噬肿瘤细胞活体或碎片并处理相关抗原,形成抗原-MHCII类分子复合物并向T细胞提呈,迅速而强烈的激活细胞免疫反应,对肿瘤细胞产生杀伤作用[10]。有研究表明,黏液腺癌具有较强的免疫逃避能力。在结直肠黏液腺癌的免疫逃避过程中,MUC介导的免疫抑制和MUC屏蔽肿瘤相关表位导致的免疫识别障碍起到关键性的作用[11]。
2.1 黏蛋白的免疫抑制作用
MUC O型寡聚糖链因其多变的空间结构可以形成众多抗原表位[12]。尽管其具体的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现有研究证明了MUC上某些抗原表位在黏液腺癌免疫逃避中发挥了一定作用。Krantz等[13]在一项体外T细胞模型实验中发现,肿瘤细胞表达的MUC-1上某些抗原表位可与T细胞表面的细胞间黏附分子-1(intercellular adhesion molecule-1,ICAM-1)等多种抑制性受体相互作用,导致T细胞失活,抑制细胞免疫。另外,Hiltbold等[14]研究显示,未成熟的树突细胞吞噬MUC1后,由于糖基对MUC N-端的保护,树突细胞溶酶体无法对MUC进行分解及进一步处理,从而影响树突细胞表面抗原-MHC复合物的形成与细胞免疫的激活,进一步诱导免疫耐受的产生。
2.2 黏蛋白的免疫屏蔽作用
黏液腺癌肿瘤细胞表面聚集的MUC-2可以通过其核心蛋白的N-端相互连接,在肿瘤细胞表面形成致密的网状结构[8]。这种网状结构可以在免疫细胞与肿瘤细胞之间形成空间阻位效应[15],有效的屏蔽肿瘤细胞表面的特异性抗原,使淋巴细胞对肿瘤的识别过程受阻,从而使肿瘤细胞免受自然杀伤细胞、细胞毒性T细胞的识别与杀伤。在上述协同作用下,黏液腺癌表现出了更强的免疫逃避能力,使肿瘤迅速地增殖、扩张。
3 黏蛋白与肿瘤的种植/转移
结直肠黏液腺癌与非黏液腺癌相比,在转移趋向性上有着显著的不同。Hugen等[16]研究显示,结直肠非黏液腺癌的远处转移以单纯肝转移多见,而在结直肠黏液腺癌患者中更常见的是广泛腹膜转移。MUC在黏液腺癌的转移过程中起关键性的作用。
3.1 黏蛋白与黏液解剖
黏液腺癌中MUC的合成与分泌旺盛,使肿瘤灶可以更加迅速的膨胀,同时对肿瘤周围组织施加压力,分离组织间隙,也就是黏液解剖,使得肿瘤细胞能够轻易的穿透肠道组织达到腹膜腔或者进入淋巴系统,成为黏液腺癌腹腔转移趋向性的基础。
3.2 黏蛋白与肿瘤微环境
癌变造成MUC上寡糖链异常表达,大量的表位为选择素提供了充足的结合位点。在黏液介导的黏液腺癌肿瘤微环境中,白细胞表面的选择素与MUC上的配体结合,形成聚集体[17]。同时,由于细胞表面抗原被MUC屏蔽,肿瘤细胞可以有效的避免被吞噬杀伤[15]。这种细胞聚集体的存在,为黏液腺癌的转移和种植提供了条件。Rowson-Hodel 等[17]相关研究证实,MUC4在形成细胞聚集体的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当肿瘤细胞突破肠道组织并散落入腹腔时,由于细胞聚集体的存在,使肿瘤细胞获得了更强的游走能力,短时间内便可进入乳斑等网膜中的淋巴组织结构,并在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免疫细胞的促肿瘤微环境作用下,快速形成肿瘤滋养血管并定植[18]。
黏液腺癌的腹膜转移往往可以形成大量的隐匿性转移灶,在以肿瘤细胞减灭术为主的结直肠黏液腺癌外科治疗中,这些潜在的肿瘤病灶往往无法彻底的清扫[19]。因此,黏液腺癌患者术后常需辅以腹腔热灌注、全身化疗等进一步治疗。
4 黏蛋白与肿瘤耐受辅助治疗
现有研究表明,与结直肠非黏液腺癌相比,全身化疗、腹腔热灌注等辅助治疗对结直肠黏液腺癌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Mccawley等[20]荟萃分析显示,与非黏液腺癌患者相比,在接受相同术前辅助化疗方案后,黏液性直肠癌患者的手术切缘阳性率明显升高。同样,Negri等[21]数据统计显示,黏液腺癌患者在接受以氟尿嘧啶为核心的一线化疗方案后,其中位生存期远低于非黏液腺癌患者(黏液 Vs非黏液:11.8月 Vs 17.9月)。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在结直肠黏液性肿瘤中,胸腺合成酶(thymidylate synthase,TS)和GSTP1基因过表达,导致黏液腺癌对以氟尿嘧啶、奥沙利铂为核心的一线化疗方案敏感程度较低[22]。其次,黏液性肿瘤的一些物理特性也影响化疗效果[23]。黏液的产生使肿瘤细胞得以漂浮在黏液湖中,使得血管中的化疗药物需要渗透大量的黏液成分后才能到达肿瘤细胞表面,进一步降低了化疗药物的浓度。此外,由于黏液腺癌病灶的高压力,肿瘤周围的滋养血管受到压迫,使局部血管阻力增加,血流供应减少,化疗药物不能有效的到达肿瘤病灶。多种因素导致黏液腺癌病灶处的化疗药物浓度难以达到理想水平,进而影响化疗效果[24]。
近年来,随着腹腔热灌注化疗技术的发展,术后早期腹腔热灌注已成为肿瘤腹膜转移的高危患者术后辅助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腹腔热灌注化疗,旨在利用热(43℃)和高浓度的化疗药物对腹腔内进行持续灌注冲洗,以达到消灭腹腔内潜在肿瘤灶的目的。现有研究虽证明了腹腔热灌注化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25],但其对伴有腹膜转移的黏液腺癌患者治疗效果尚存争议。Fujishima等[26]体外实验发现,将肿瘤细胞置于43℃的高温环境下持续24 h后,伴有黏液分泌的结肠肿瘤细胞具有更高的存活率(黏液 Vs 非黏液:63% Vs 20%)。这项研究证明,黏液腺癌细胞表面的黏液成分可以显著减轻肿瘤细胞所受的热杀伤,从而很大程度上影响腹腔热灌注化疗的治疗效果。
综上,MUC在黏液腺癌的发生发展、耐受热灌注、化疗等辅助治疗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因MUC的多样性与分子结构的复杂性,不同MUC分子在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具体影响尚需进一步研究。在目前的临床诊疗工作中,术前病理诊断、利用分子检测技术或基因检测技术对黏液腺癌进一步分型尤为重要,可有效避免对部分预后良好的MSI黏液腺癌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治疗。对于预后不佳的MSS黏液腺癌患者,一方面需进一步推广肠镜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另一方面,随着靶向药物的发展,以MUC为靶点的靶向放疗可成为黏液腺癌临床治疗的突破口。利用黏液腺癌大量分泌MUC的特点,使药物富集于肿瘤灶,且不受MUC空间阻位效应的影响,可能有效杀灭肿瘤细胞并改善患者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