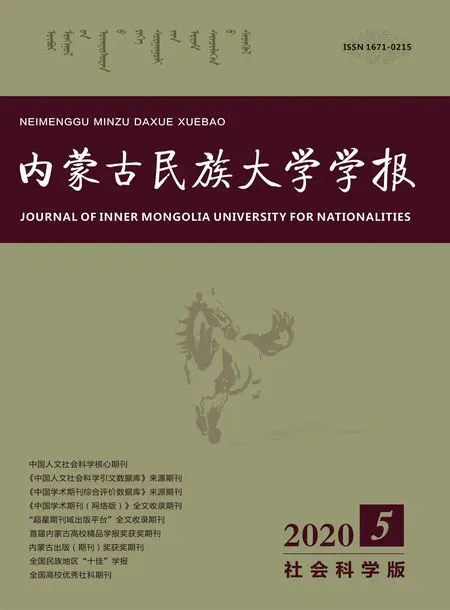蒙古族作家汉语纪实性散文的“小说化”倾向
白叶茹
(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
文体是发展中的事物,事物的发展都基于运动,而运动平衡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事物的运动平衡不是指绝对的静止平衡,而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平衡性,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不存在绝对的平衡。事物在运动的一个方向上是不平衡的,而在另一个方向上是平衡的,这就是事物的运动规律。与一切事物的运动平衡一样,散文文体的发展也不存在“绝对的平衡”,它也在力争摆脱“静止”,在“运动”和“变化”中谋求其自身的发展。这样,在散文创作的实践中就引发了散文应该“写实”还是“虚构”的争论,即使散文文体的特征是非虚构性的。在争论中,出现了摈弃“写实”与“虚构”偏见的一种“中庸”的观点,而这种观点逐渐得到作家以及理论界的认可。陈敢在其《散文题材纪实性刍议》中,科学地梳理前人的不同观点后提出了“当前文学界、学术界对散文题材纪实性所持的三种看法都是失之偏颇的。我认为,散文既可以写实,也可以虚构。可以写实为主,也可以虚构为主。而以虚实结合并富有诗一样意境的散文为上品”[1]的观点。散文“可以虚构”,陈敢的这种观点给蒙古族作家汉语纪实性散文的虚构现象带来了理论依据。
蒙古族作家汉语纪实性散文的虚构现象,主要体现在散文的“小说化”方面。我们从汉语纪实性散文的文本中不难发现人物性格的“典型化”、叙述结构的情节化、题材内容的细节化等小说文本的因素。“小说化”倾向,是蒙古族作家汉语纪实性散文在其发展中摆脱“静止”,用“运动”“变化”来谋求其自身发展的结果。“在散文创作实践中,‘小说化’已经成为散文文体自身发展的一种必然流变。实际上,散文‘小说化’流变并没有否定纪实性特征,只是赋予了散文以更丰富的表现能力、审美效应和阅读张力。”[2]蒙古族作家汉语纪实性散文,在其创作实践“小说化”的过程中被赋予了审美效应和阅读张力。
小说家对散文创作的涉足、环境与人物的典型化和抒情语言向叙述语言的移动,这些内在和外在的因素都给蒙古族作家汉语纪实性散文的“小说化”倾向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一、小说家对散文创作的涉足
在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上,有不少在小说创作领域获得卓越成就、又在散文创作领域笔耕收获的作家,如李凖、舒湮、敖德斯尔、玛拉沁夫、扎拉嘎胡、安柯钦夫、朋斯克、特·赛音巴雅尔、韩汝城、苏尔塔拉图、张志成、哈斯乌拉、郭雪波、满都麦、乌雅泰、白音达赉等都是蜗居于小说和散文创作领域的两栖作家。他们用汉语笔耕,在蒙古族汉语散文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佳绩。
李凖著有小说名篇《不能走那条路》(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中篇小说)、《黄河东流去》(长篇小说)等,也写有散文力作《相会在洛杉矶》《华盛顿漫步》《红叶如醉送嫩寒》等。他的散文很少涉及蒙古题材,但也留下了《内蒙古散记》等游览内蒙古的散文;敖德斯尔是蒙古族著名小说家,是蒙古族当代文学奠基人之一,《阿力玛斯之歌》(短篇小说)、《草原之子》(中篇小说)、《骑兵之歌》(长篇小说)等是敖德斯尔代表性的小说作品。20世纪60年代,敖德斯尔涉足散文创作领域,用母语创作《慈母湖》《马驹湖》《牧马人之歌》《金庄稼》等散文,逐步形成了“景物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感情,景中有情,情景交融,如水乳交融,合成一体,自然和谐”[3]119的散文风格。新时期,敖德斯尔又用汉语创作《故乡》《故乡行》《急托蒂》等散文,展现了其人生阅历、艺术修养和审美层次;玛拉沁夫是以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走上文坛、用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奠基了其雄阔的艺术风格的知名作家。玛拉沁夫著有散文集《想念青春》,其中收集了《故乡的路,消失在远方》《新春寄语》《虎坊艺谭》等蒙古题材散文,从这些带有乡土习气的散文篇章里我们能够领略到“他洒脱而多思的心灵,对生活对草原的炽热情感”[4];扎拉嘎胡著有短篇小说《一朵花》、中篇小说《春到草原》和长篇小说《嘎达梅林传奇》,此外,他还创作了《蒙古马》《蒙古松》《圣水的诱惑》《童年的自白》《故乡风云录》等散文作品。评论家张锦怡读完《童年的自白》之后,给扎拉嘎胡的散文“很平常的记叙中却呈现出特定情境中一个蒙古族少年的心理状态”[5]的评价;安柯钦夫1953年创作短篇小说《在冬天的牧场上》,1959年出版小说散文集《家乡新貌》,晚年又发表了《荞麦礼赞》《奶茶赋》《故乡塔影》《达赉湖漫兴》等散文作品。“安柯钦夫的散文多写观感,取材真实,忌讳雕琢杜撰,因为它扎根在生活的沃土上,具有自然朴实的美”[3]288;苏尔塔拉图著有《枣骝马》《哦,寻找我童年的足迹》《库伦旗的传说与现实》《博格达湖》等散文,他的散文“写人,写得真切感人;写景,描得委婉细致。”[3]294
在蒙古族汉语散文中,以小说创作为主同时在散文领域中大放异彩的作家,就不得不提郭雪波。郭雪波从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锡林河的女神》《火宅》《沦丧》《大漠狼孩》《狐啸》、中篇小说《沙狐》《大漠魂》、短篇小说《沙狼》《红色温柔》《暖岸》等。这些小说多以沙漠生活为题材,因此郭雪波的小说被称为“生态文学”。同样,郭雪波将“生态文学”的理念也贯彻到其散文创作中。郭雪波在其作品《我在跋涉》中告白:“我要感谢‘天’——大自然,就是在那沙坨子里,在那不枯不竭不灭的生命群体中间,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含意、生命的哲学以及生命的伟大。”[6]118从沙漠里感受生命,这也是郭雪波为什么要向往故乡热土、独尊沙漠题材的理由之一吧。2016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郭雪波的散文集《大漠笔记》,收录了《阿拉坦·根娜》《嘎达梅林小路》《荒漠魂》《大漠落日》《一只大蝈蝈》《父亲的故事》《儿子小名叫八斤》《乡间趣事》《白狗》等散文。其中,散文《父亲的故事》曾获“长江文艺”奖。郭雪波的散文有着返归朴野、智性追问、赋而不涩、去伪存真、语如家常、余味缭绕的艺术风格。在题材和主题方面,郭雪波的小说和散文是一脉相承的。孟凡珍评论郭雪波作品时说道:“当代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的作品以科尔沁沙地的生活为题材,表达了他关注生命生存状态,即以尊重生命、和谐共存为主旨的生命理念。永无休止的欲望和肆无忌惮的攫取带来现代人性的搁浅,因而在敬畏自然中走向对自然荒野的回归和融入,成为人性回归的必然选择。尊重自然、尊重非人类,构建和谐环境是其生命哲学的意蕴。”[7]郭雪波以小说家的身份介入散文创造,不仅开拓散文的题材,还深化了散文的主题。更重要的是他对散文体裁“小说化”的把握,给散文内容的丰富性与结构的多元化带来了质的变化。
小说家似乎拥有贴近现实和人心的天然的优势,这种优势使他们的散文脱离了梦呓般的凌空高蹈,重新贴近现实和人心。在写作手法上,他们改变了以往散文中“卒章显志”的写法,有意深化主题,使散文的思想有了必然的张力;在表现手法上,尽量节制情感的抒发,克服了以往散文中“过度抒情”的毛病。用丰富的表现力处理人和事,小说家深厚的文学素养、自由多元借鉴的写作姿态改变了散文的边界和疆域,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散文的审美品格。
二、环境与人物的“典型化”倾向
散文的“小说化”和小说的“散文化”是文学体裁发展的自然规律。散文的“小说化”是两种文体多种笔法相交融的结果。小说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散文则以人和事、景和物、情和意为表达对象,抒写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真切的体验和感受。在特定环境中塑造人物、抒写人物的命运和个性方面,小说和散文有着他们的共同点。比如,有的小说作品用意境化的形象来达到反映现实的目的;有的散文作品,则在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里铺展人和事,达到环境与人物“典型化”的效果。正因如此,小说和散文在审美的交叉点相遇,散文也找到了其“小说化”的途径。
小说家对散文领域的介入,散文家有意模仿小说笔法等加速了散文“小说化”的进程。“新时期以来,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恢复和弘扬,文体意识的自觉,创新探索的活跃,不少作家率先打破各文体间的清规戒律,大大拓宽了形象思维的艺术空间。”[8]22散文和小说互相借鉴,相映成趣,散文的“小说化”也由自在逐渐走向自觉。
散文是一种“真实”的艺术,它在描写真人真事、真情真景方面还是与小说略显不同。纪实性散文,在不失“真实”的前提下,营造“典型化”的环境,抒写“典型化”的人物,渐渐显露了其“小说化”的特征。
(一)环境的“典型化”倾向
乡土是纪实性散文人之生存、事之发生的环境。蒙古族汉语散文的环境“典型化”倾向体现在回忆语境下的乡土环境、还乡语境下的乡土环境和文化语境下的乡土环境中。
1.回忆语境下的乡土环境
纪实性散文的回忆语境在历史描写中形成,是历史赋予人物生存的具体环境。回忆语境主要出现在兼有纪实性和回忆性散文的文本里,如巴彦布的《忆童年》、扎拉嘎胡的《故乡风云录》、敖德斯尔的《托蒂祭》、王雄斌的《二姐》等,这些散文在回忆语境下完成了对某种环境中发生的某种人和事的写作。
巴彦布的《忆童年》用纪实的方式回忆了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嘎尔奇村野童部落的“裸史”。“嘎尔奇——这个农牧渔业并举的小村,北面与松花江北岸的肇源县相望;向南系郭尔罗斯草原;向西则于内蒙古兴安盟接壤;它是吉林省扶余县的鱼米之乡的代表,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清朝时期的嘎尔奇,成为向朝廷进贡的‘鳇鱼圈’之一。”[9]抗日战争时期,就是这样一个富足殷实的蒙古村,不到几年工夫,被日本鬼子折腾成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在搜刮和侵略中嘎尔奇的大人和野童部落用“以牙还牙”的手段进行抵抗,最终看到了“狗日子的倒台子”。散文中,嘎尔奇既是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又是野童部落活动的自然环境,纪实性的环境描写证实了环境语境的真实性。
扎拉嘎胡的《故乡风云录》由“白城印象”“梦中的葛根庙”“风雨红城岁月深”“重返出生地”“谒祖坟”等组成,散文中,反复出现“斯力很”这样一个典型环境。斯力很是“我”的故乡,是童年的记忆。“我刚懂事时,斯力很并不大。我只要翻过房后墙院的墙,便来到了触膝的大片深草中了。这里灌木丛生,马莲花和萨拉仁花遍地都是。到了冬天一下雪,满地是野雀、沙半鸡,它们为觅食落在房前屋后,刹时那里变成了黑压压蠕动着的土地。乘雪后下套子打猎的人挺多。这些人一出动,个个都有收获,此时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野味飘香。端午节后,我们在长满芍药花的草丛中跑起来后,从我们脚下不时飞起鹌鹑、野鸡;到了冬天,村里的人们带上铁锹、鱼叉、渔网,来到洮儿河的冰面上,乘夜凿开窟窿,只要旁边点上火,便能把成群结队的鱼引诱过来,于是鱼叉渔网一下去,便能大获鱼利而归。”[10]“我”的祖父和另两家蒙古人开拓了斯力很村。在散文里,斯力很被描绘成“莺飞燕舞的草地”“水草丰美的牧场”“野狼和狐狸的乐园”。童年的生活虽然艰难苦涩,但斯力很的自然环境给苦涩的童年染上了五彩斑斓的色彩,“大自然的美,构架了‘我’童年心灵的空间。”[11]
敖德斯尔的《托蒂祭》以夏营地为背景,追忆了已经死去五十多年、当时年龄不到二十岁的贫苦牧民的女儿——托蒂。托蒂的死因竟是因为无医救治,“在那个岁月,草原上找不到一个医生。人得了病,实在没办法时人们把求生的欲望寄托在请喇嘛念经上”。散文《托蒂祭》中的环境描写再现了那个黑暗年代蒙古地区的愚昧和落后。“如今,草原儿女永远摆脱了贫苦落后和愚昧无知的黑暗的年代,迎来了灿烂的春天,祝愿我家乡的人民在新世纪里更加安康、幸福。”[12]在新旧环境的比较中,作者对家乡的人民送去了由衷的祝福。
《二姐其其格》是乌力吉系列散文《草原亲人》之一。与《忆童年》《故乡风云录》《托蒂祭》相比,《二姐》的环境描写的历史感稍微逊色。从“听母亲说,二姐出生在一个青黄不接的季节,但二姐却在饥饿和灾难中犹如一棵小草坚强地挺了过来”[13]的叙述语境中,我们仍然能够揣摩到一个灰色时代的信息。二姐放过羊,挖过甘草,卖过羊皮,渴望过读书,结过两次婚,最终在异乡兼做三份保姆的工作,像个旋转的陀螺……散文中有这么一段场景描写:“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我去荒野找二姐。远远地看见在空旷和沉寂的原野上,瘦小的二姐正背负着硕大的粪筐从余晖中走来。一种悲凉弥漫了我的整个世界”。凄凉的背景、明丽的语言、质朴的情感,使一个小人物瘦小的身影跃然纸上,引起人们的同情、叹惋乃至强烈的共鸣。
2.还乡语境下的乡土环境
还乡是乡土情结的具体表现。还乡使“离乡”的人对乡土产生了“在家”的感受。“‘在家’是散文家‘还乡’动机的终极实现,……也是散文家通过抒情和叙事行为在散文里显示的艺术特质。”[14]61“在家”给纪实者提供了“在场”的叙述视角,散文家们运用“在场”的视角,认识乡土一隅的现实,领略乡土风物的自然美,体验家园文化与乡土秩序,从而描绘出了真实风貌的还乡语境下的乡土环境。我们从刘川的《风吹草底》、包玉英的《土默川一日》、云珍的系列散文《故乡年关记事》、郭雪波的系列散文《遥远的故乡》、鲍尔吉·原野的系列散文《老家的人》中能够感受到这种身临其境的还乡语境下的乡土环境。
云珍的系列散文《故乡年关记事》由《腊月二十九》《年夜饭》《跑年》《接神》《与乡友大麻将》《顺子来访》《九叔、改花以及……》《返程》等组成。散文从作者腊月二十九回故乡“站在近村岔路口,不敢举步”写起,到提前返程“走到岔路口,车子停下,由不得再望故土”结束。散文中,作者以“在场”的视角设置了“平原”“村庄”“屋子”“供桌”“锅台”“炕席”等由远及近的场景,为“九叔”“姐姐”“春旺”“王嫂”“顺子”“改花”“三儿”等人的出场做了铺垫。
郭雪波的系列散文《遥远的故乡》由《父亲的故事》《儿子小名叫八斤》《乡间趣事》《白狗》组成。郭雪波是一位怀有浓厚沙漠情结的作家,拜读他的散文我们总能目睹或一粒“沙子”或一片“沙漠”的影子。沙漠唤起了他的乡恋,也为他的散文铺设了背景。郭雪波沙漠情结的抒发与他每次回到故乡所看到的景观有关,2007年他回到故乡所写的《一篇发自沙村小学的报告》中这样叙述了他自己故乡的沙漠景色:“我就出生在这曾经是美丽的养息牧河岸。现在这片能设百里金帐的美丽草滩,已不复存在了。村北横亘着一条几十里宽几百里长的大沙漠,村前那条清澈的小河也被两岸黄沙侵吞后已浑黄不清,也快窒息了。”[6]74正因如此,他所写的《遥远的故乡》中的人和事总是与“大漠”相伴,接受着“风沙”的吹打和“沙漠”的润色。回乡后,“我”每天早晨都要到“水面上蒸腾着晨雾的沙漠河”边上散步(《白驹》);父亲为了教训儿子好好读书,“离开贫瘠的沙村”,用鞭子狠狠地抽打了他(《父亲的故事·父亲的鞭子》);“我”记得小时候,天黑后屋里点着小油灯,“外边刮着风沙”,父亲就靠炕上被摞坐着,缓缓吟唱哀婉的民歌(《父亲的故事·父亲的四胡》);还记得小时候,与父亲“走在一条漫漫的沙路上”,替父亲背胡琴或酒壶,到邻村人家去吟唱或说书(《父亲的故事·父亲的四胡》);父亲伺候瘫儿时,“拿个特制的小板掺和着细沙给其揩擦屎尿,再把变脏的细沙和垫布拿出去扔掉,重新换上干净细沙和垫布”(《父亲的故事·父亲和瘫儿》);弟弟白沙主持祭祖仪式时,在“平坦的养息牧河沙滩上”,拿一根树枝画出了象征是座房子的挺大的一个方形框子(《乡间趣事·那些漂游在乡间的“鬼”魂们》)。
鲍尔吉·原野的系列散文《老家的人》由《继母》《格日勒》《萨茹拉》《大姑老爷》《宁丁舅舅》等组成。“老家的人”生活于“我”的老家——胡斯台,地处科尔沁沙地的胡斯台是作者在散文里着力打造的“世外桃源”。这里虽然贫瘠,但人们的脸上全有笑容,过着无忧无虑的世俗生活。
胡斯台的白天和夜晚像两个地方。这么说,早晨、中午、下午都不一样。八月的太阳像卸车一样把热量倾斜在科尔沁沙地,周遭白花花的,人被晒得睁不开眼睛。最热的时候,空气里如有声音:“嗡——”这是太阳照在沙漠上的音波,传自太阳。在白天,胡斯台的房子和沙漠颜色相似,燥白,树和庄稼发灰。一切静悄悄的。到了傍晚,村庄开始一点点蠕动。我是说,炊烟和小孩游动时,狗和毛驴在动,房子也走动起来,像从冰块里活过来的鱼。玉米恢复黑肥之绿,饮马的石槽淡青。我哥朝克的房上有瓦,明黄色。鸭子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竟有一群,蛋囊岌岌乎坠地。人们出现在家门口,全有笑容,世俗生活又回来了。在《阳光碎片》中,作者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对胡斯台的早晨、中午、下午等不同时段进行了“在场”的观察。作为还乡语境下的乡土环境——胡斯台村的景色既是“静态”,又是“动态”的。白天它的“一切是静悄悄”的,到了傍晚村子便有了活力,连“房子也走动起来”,这是一个典型的半农半牧的乡土环境。这个偏僻、宁静、朴实的乡村环境滋养了像格日勒、萨茹拉、大姑老爷、宁丁舅舅……等一批安于现状、“全有笑容”的形象。
——鲍尔吉·原野:《阳光碎片》[15]
3.文化语境下的乡土环境
以纪实性的叙述话语将读者带入文化语境,这便是汉语纪实性散文产生文化语境下乡土环境的主要原因。特·达木林的《被猎场勾起的童心》用《打野鸡》《打野兔》《打狐狸》等系列散文叙述了“位于北大荒以西,平齐线铁路和嫩江、洮儿河之间的平坦而广阔地带”,“蒙汉杂居”,“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村落的打猎活动。散文专设《好传统》一篇来阐明“蒙古族人们非常喜欢打猎”的“好传统”,为文本文化语境的产生作了穿针引线的伏笔。“这里的打猎,不同于兴安岭上的鄂伦春和鄂温克族猎民那样以枪打为主,而是以快马猎狗加布鲁追拿。因为这里只有狐狼兔,而无獐狍猂鹿。打猎多在冬季,尤其利用雪天进行。打法多种,诸如下夹子、下套子、放签子、扣筐子和码脚印追拿等等。”[16]打猎季节和打猎方法的具体交代,凸显了其“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的乡村环境,给散文带来了以“地区”和“民族”为特征的文化氛围。胡素的《鄂伦春婚礼》描写了安布伦和欧妮诺的婚礼场面。新郎新娘的婚装、迎亲队伍的组成、精心安排的“老考台”仪式、表示吉祥的互送礼物、新郎新娘安歇的“斜仁柱”洞房……在全景式的叙述中,“具有狩猎民族传统习惯和独特民族风格”[17]的鄂伦春婚礼便跃然纸上,每个场景都留给人们一种文化旅行的感受。白涛的《山西蒙古人》中乡土环境的描写是在汉人蒙化的跨文化语境中完成的。山西“蒙古人”生活于汾河与黄河的浑水,吕梁与阴山的绵连。扁食、取灯、马哈……山西蒙古人都能说几句蒙古话;炒米、奶茶、手把肉……山西蒙古人都会享用这些草原美食。山西“蒙古人”喜欢唱漫翰调,“漫翰调的旋律一半儿是山西味儿的晋陕调儿,另一半又加上了草原大漠的长调抒情。”[18]山西“蒙古人”,其实是明朝末年就开始陆陆续续卷着铺盖、来到大青山下扎下营子的走西口的后人。他们受到蒙古文化影响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文化影响了蒙古文化,“山西蒙古人拿手的羊肉汤汤莜面窝窝和荞面圪团儿蒙古人爱吃”。汉文化和蒙古文化的双向传播,造就了文化语境下的乡土环境,也造就了《山西蒙古人》。
(二)人物的“典型化”倾向
小说中,环境与人物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小说化”的散文也如此。说起环境与人物的关系,人们不由得想起恩格斯在其《致敏·考茨基》中下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著名论断。典型环境指环绕在典型人物周围并促使其行动“典型化”的环境。典型人物指在典型环境中形成个性和共性的人物,按恩格斯的话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19]
小说的典型人物与散文的“典型人物”不能相提并论,但纪实性散文在其创作实践中借鉴小说的肖像描写、人物对话、人物个性化等表现手法,在很大程度上使散文的人物趋向于“典型化”。
“车站有两间房。候车室,另一间应该是站长室,但窗台挡蚊的纱布里探出一只狗的脑袋,如雕像似的一动不动,等着风来吹发亮的黑鼻子头。
候车室的两张长椅,对着放,挨得很紧,身后是墙壁。我坐下以后,面对的是一位老人。两个陌生人,就这样鼻尖对着鼻尖坐着,没办法。
老汉两撇黑胡子向上翘起,能看出他常常用手捻,有尖。是一种晚年的游戏。老汉眼睛望着屋顶,目光痴滞,隔一会儿,飞撇我一眼,接着连眨几下。显然他不习惯我像傻子一样盯他胡子看,距离太近。
这种式样的胡子,即使到了戴高乐时代也落伍了,如今在一个乡村的蒙古老汉的唇边出现。我不小心笑了出来。这使老汉猝不及防,也笑了,眼光灵活而明亮。他仿佛早就想笑,没敢。他是一个谦恭的乡下人,牙齿没几颗了,一笑,他的嘴像藏在柴草里的缺渣的旧碗,而红软的舌头蠕动在牙洞间。
交谈,老汉是图力古尔人,去甘旗卡的外甥家做客,膝上的麻袋里装了一些杏,还有一包红茶和茶缸子。他说第一次去甘旗卡。甘旗卡是一个镇。他用粗黑裂口的指头,轻轻捻着浅粉色的车票。
话语结束,候车室又静下来,老汉向门外望闪闪发亮的铁轨。他用力抬眉毛,扛起前额一堆皱纹,这位老人与科尔沁草原的其他人一样,过着简朴的生活,心智单纯。假如你一笑,他会立刻报之一笑,胡子尖升达颧骨。他们的笑,一生浮在脸上,没间断过。像孩子一样,他们笑起来很容易,蹦着脸却困难。这样的脸如果不笑,看上去反而不对劲,仿佛带着忧愁。”
——鲍尔吉·原野《伊胡塔的候车室》[20]
鲍尔吉·原野在其散文《伊胡塔的候车室》中,以肖像描写的手法塑造了“老汉”这个“典型化”的人物。从故乡返城时,在伊胡塔候车室“我”与“老汉”相遇,“老汉”是一个涉世不深、不善交际、腼腆谦恭的乡下人。在散文中,作者以肖像特写、心理描写的手法使人物形象渐渐接近了“典型化”。“两撇黑胡子向上翘起”“眼睛望着屋顶,目光痴滞”“牙齿没几颗”“嘴像藏在柴草里的缺渣的旧碗”“红软的舌头蠕动在牙洞间”“用力抬眉毛,扛起前额一堆皱纹”——一系列的、捕捉式的追逐特写,使一个久经风霜、历经艰辛的“老汉”的肖像悄然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为了堤防涂墨单调而导致形象的痴呆,作者有意让“我”与“老汉”互动,通过眼神的变化,使“老汉”微妙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出来。老汉一开始“目光痴滞”,接着“连眨几下”,最后“灵活而明亮”起来。从眼神里流露出的心理活动,是“老汉”的简朴生活和单纯心智的写照和展现。散文的表现手法,虽源于小说,但胜似小说。
敖力布皋是个方方正正大屯子,周围夯实土墙,四角高垒炮台,邹家正好在西南角炮台底下。姑娘我没印象,对她弟弟却不陌生,他叫灵子,年岁与我相仿,是个看似老实、实则蔫淘的男孩。我前去,邹家已知消息,早派灵子在门口。我一露脸,灵子便朝院里大喊:“爹,客(音qiě)来啦!”
大概特意为迎候贵客,一家人都在黄瓜架下纳凉,一张炕八仙桌旁坐着灵子他爹他妈还有他姐。见我进院,姑娘站起来,大大方方笑着道声:“来啦?”转身进屋去了。她爹拿蒲扇指指一只小凳子说:“坐下,孩子。”然后便细细端详我,像打量什么心爱的物件,看得我浑身发毛,怪不自在。半天,才见老汉点头嗯了一声:“像,真像你爸。”
我忙问:“你老认识我爸?”
在早敖力布皋没几户人家,就像你跟灵子,我跟你爸常一块儿玩,他还比我小几岁呢,心眼够用,人也仁义。可没想到……”轻轻叹了口气,接着又说:“你大伯当家那咱儿,我也是你家的耪青户,后来才自个儿置了几垧荒。你爸离家也就你这么大,打那以后再没见着。”
灵子妈也插话,问我属啥的,念几年书了,家里还有啥人。其实,这些问题他们早该打听清楚,也许是没话找话。也许是有意考察,我不得不一一作答。大概因为我口齿还算伶俐,看老太太那神色,似乎表示满意。韩汝城的《乞丐相亲》叙述了“我”在堂兄和众人的建议下,到邹家登门相亲的经历。散文,通过人物对话完成了“我”在邹家相亲的经过。《乞丐相亲》的人物对话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场景的设置突出了地区特征。由“大屯子”“土墙”“黄瓜架”“八仙桌”等组成的描写因素,把人引进了具有半农半牧特征的科尔沁式乡土环境。“老实则蔫淘”“客(音qiě)来啦”“耪青户”“几垧荒”等方言的巧妙介入,为对话语境的形成制造了积极的效果;其次,采用了说话人在引语前的对话形式。运用“大喊”“道声”“说”“忙问”“又说”等提示语引出对话,让相亲的场面弥漫了“自然”的气氛。“朝院里(大喊)”“笑着(道声)”“指指一只小凳子(说)”“点头(嗯了一声)”等动词的点缀,又微妙地暴露了对话者的复杂心理;再次,设计了多层次的对话结构。第一,语气对话层面。由“她爹”发起的“嗯了一声”“叹了口气”等语气对话,在对话语境中产生了活跃对话场面的效果;第二,直接对话层面。在“我”与灵子、“我”与姑娘、“我”与“她爹”之间发生,作为对话语境的主导,直接对话层面对相亲过程的完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三,间接对话层面。指简化对话过程的一种对话语境。在散文中,“我”与“灵子妈”之间的对话完全被省略,只用“灵子妈也插话,问我属啥的,念几年书了,家里还有啥人”等,以“我代叙”的方式避免了对话拖长的问题。通过对话,《乞丐相亲》描写了“我”“她爹”“姑娘”“灵子”“灵子妈”等人物的形象,用简笔的手法勾勒出每个人物自有的鲜明个性。
——韩汝城:《乞丐相亲》[21]
纪实性散文,通过对“小说化”的“生态”打造,汇聚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其中也不乏“典型化”的人物。如,以凌乱的影子摇晃在被灯火熏染的黄麻纸上,总是受人嘲笑和欺负的小人物锁子哥(云珍《锁子哥,魂兮归来》);披着一件又破又脏的大棉袄,身边离不开一杆黑烟袋,扯起那苍老的歌喉喊蒙古长调的七十三岁的瘸老头(刘川《风吹草低》);在开着小窗的房子里眯着眼吧吧地吸旱烟,和人聊天眼睛总是笑眯眯,留给“我”那么少又是多么深刻影响的阿公(丁晓《阿公印象》);披头散发,傻笑狂语,老往沙坨子上胡乱插条子种树,站在那些老树中间,远远看去活像是钉进沙漠里的铁桩子式的巴亚尔爸爸(郭雪波《不屈的树》);赶着毛驴车来,坐在炕头,用不断的“拷问”打听大城市的事情,有一点怪行为的满达老人(鲍尔吉·原野《阳光碎片》)等等。这些形象的塑造,不是依靠宏大叙述语境,而是依靠或一处场景描写,或一段事件的记叙,或一缕情感的表达来成就的。以《阳光碎片》的满达老人的形象塑造为例,我们能够略悟纪实性散文人物“个性”的孕育、人物形象的“典型化”过程。
满达老人一早就到了。他的毛驴车上铺着红花绿叶图案的棉被,还有旧军用水壶。进屋上炕,敬茶,朝克卷烟双手递给老人。老汉喝一口茶,烟雾从鼻孔漾出,海狮胡子花白。
“沈阳的庄稼怎么样啊?”
“沈阳郊县的庄稼很好。”
“嗯。”老汉喝茶,问,“沈阳的天气怎么样啊?”
“越来越热了。”
“可以种西瓜。”他说。过一会儿又问,“沈阳还有卖丝线的吗?”
半天,我想起马秋芬写的《老沈阳》提到中街吉顺丝房的事,说,“已经不卖了。”
老汉拉过我的手,捏一捏,放下,说,“沈阳有多少蒙古人?”
“有七万人。”我回答,“大学里也有蒙古孩子,聚会的时候唱蒙古歌。”
“是吗?”老汉似乎感动了。
“是的。”
老汉看我,仿佛从我的面孔中看到遥远的沈阳,而后微笑着扳腿下地,划拉鞋,说,“我走了,到那什罕村的孙女家。”
上驴车时他转回身说,“沈阳好啊!我十八岁去过,过去七十年了。沈阳多好。”白嘴的毛驴,耳朵立而不平,像告别。《阳光碎片》由三个段落组成。第一段落,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对乡土小村早晨、中午、下午等不同时段进行了“在场”的观察;第二段落,以场景描写的手段,对进夜后在“我”住的东屋里发生的众人有趣的交谈进行了叙述;第三段落,则是对满达老汉形象的“塑造”。七十年前满达老人曾去过沈阳。这天,老人赶着毛驴车来专访从沈阳来的小老乡。时光荏苒,岁迁景变,带有鸿沟的两代人之间已经话不投机。满达老汉是个有个性的人。散文里,虽没有用浓涂厚抹来描摹满达老汉,但他那“古董”式的身着打扮、“拷问”式的对话方式、“陀螺”式的行动风格,使一个乡村倔老人的形象奕奕如生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鲍尔吉·原野:《阳光碎片》[22]
三、抒情语言向叙述语言的游移
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散文是一种抒情的艺术,它以描写真人真事、真情真景而与小说区分开来,其主要的审美特征是一种‘我’的文学,表现自我和个性。”[8]23散文强调“写‘我’的自得之见,抒‘我’的自然之情,用‘我’的自由之笔,显‘我’的自在之趣”[23],但我们不要忘记“散文处于再现性小说与表现性诗歌的中间开阔地带。兼有再现和表现的双重特点”[24],表现的文体重抒情,再现的文体重叙述。作为散文文体的一种,散文同样也“处于再现性小说与表现性诗歌的中间开阔地带”,这就为什么纪实性散文的语言由抒情游移叙述的理由了。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20世纪以来散文的发展经历了现代、当代、新时期等三个时期。现代是告别的身影,已成传统。当代是人们曾经经历的,被酿成经验。新时期正与我们同步,需要我们在不断探索中寻找到更适于表现现代人审美趋向的散文路径。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加快了市场经济的步伐,大众文化的流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散文创作,散文不断趋于世俗化。散文的这种大环境决定了纪实性散文的语言由典雅的抒情向通俗的叙述游移的态势。颜水生在其评论《新时期散文试论》中,对新时期散文创作群体进行考察,敏锐地看到了在散文中所形成的叙述风格。他说:“积淀了深厚的艺术功底,历练了丰富的人情世故,以一种平实委婉的叙述风格,蕴藏着真挚深厚的乡土情感,为散文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5]73
20世纪90年代,蒙古族作家汉语散文迎来了其成熟时期。这个时期萧乾、牛汉、敖德斯尔、李準、安柯钦夫、扎拉嘎胡等老一辈作家继续发挥其余热,为汉语散文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席慕蓉、鲍尔吉·原野、郭雪波、包国晨、白涛、删丹、额·巴雅尔等新一代散文作家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托举了汉语散文的一片蓝天。在蒙古族新老散文作家的共同努力下,蒙古族汉语散文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大好局面。散文家们,在纪实性散文领域大胆运用叙述语境,以别样的笔调拓展题材,追求主题的多样化,开掘了迎合读者阅读兴趣的审美时空。
蒙古族作家汉语散文的成熟得益于全国散文体裁的繁荣。“新时期散文创作形成了三个主要的创作群体,以汪曾祺和陆文夫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作家的散文继承了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风格;以贾平凹和韩少功等人为代表的中年作家的散文表现了明显的反思现代性的意识;以刘亮程、谢宗玉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的散文表现了‘大地悲歌’的美学风格。”[25]72全国散文领域的强大阵容,以及他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构成的“乡土抒情、乡土反思两种叙事倾向”和“家族叙事与归乡叙事两种模式”[26]深深地影响了蒙古族作家汉语散文的叙述走向。由于在捷径中行走,所以蒙古族作家在其汉语创作实践中很是得心应手,他们用开放的姿态投入写实和纪实,准确地把握了散文语言从抒情向叙述游移的特质。
在散文的品类中相对而言,纪实性散文更享有叙述话语的权力。在创作实践中,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安柯钦夫、朋斯克、韩汝城、苏尔塔拉图、张志成、鲍尔吉·原野、郭雪波、满都麦等纪实性散文的写作者们,“自觉地把‘抒情小品’的体式扩展,”[14]132把叙述语言有效地运用于民族题材上,通过个人体验委婉曲折地记叙了散文环境和人物,为散文文体的延伸起到了嫁枝接节的作用。
综上所述,散文的“小说化”倾向是“散文文体变异的一种轨迹,这种变异呈现出散文文体的伸展性和延拓性,对题材的容纳、主题的多样、审美的开掘都是有益的尝试,并进一步演化成散文自身发展的动力。”[27]小说家对散文创作的涉足、环境与人物的“典型化”、抒情语言向叙述语言的游移,使纪实性散文的创作景观更显姹紫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