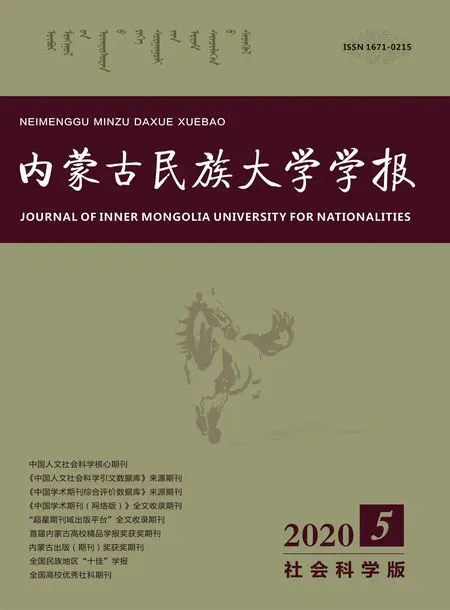20世纪20至30年代赎地纠纷的审判
——基于河北省高等法院档案的考察
邵 琪
(西南石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成都610500)
中国传统乡村的农民,通常因陷入贫困而典卖土地。所谓“典卖土地”,即附有回赎条件的土地转让。具体来说,就是卖主(出典人)在保留土地回赎权的前提下,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一部分转让权让渡给买主(典主),从而获得钱财。卖方并未斩断与典卖土地的关系,卖方(与其后代)和买方(与其后代)会围绕土地回赎发生诸多纠纷。岸本美绪在关于明清时期找价回赎问题的研究中指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土地买卖秩序“由以前历次所有者连锁式的认证和中人等证人这种人际关系网予以保证。”[1]433岸本美绪认为,只要缺乏非人格的官方登记制度的保证,找价回赎纠纷就难以避免[1]455。黄宗智认为,土地回赎纠纷的核心在于前商业逻辑和市场经济逻辑二者之间的矛盾。黄宗智所说的“前商业逻辑”,是指出典人认为土地可以无限期回赎,而一个长期持有典权的人理所当然地将土地视为己有,这体现了“市场经济逻辑”[2]67—91。上述研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裁判是国家对于人民显示自身权力的象征之一,面对难以避免的赎地纠纷,执法者依据哪些依据作出裁决。透过赎地纠纷审判这一特定媒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国家与乡村基层社会之间呈现出什么样的关系。
本文在岸本美绪、黄宗智等学者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赎地纠纷的审判依据,探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限于资料,本文主要以20世纪20至30年代河北赎地纠纷的审判为中心,所用资料大多来自河北省档案馆所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中藏有一大批赎地纠纷档案,内容涉及20世纪20至30年代河北乡村发生赎地纠纷的来龙去脉。本文以此为基础,结合这一时期农村经济调查资料,系统分析赎地纠纷的审判情形。
一、依据国家法的裁判
岸本美绪的研究显示,清代找价纠纷和诉讼数量的增加让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颇为忧虑[1]425。为此,清廷在雍正八年(1730年)修改了《大清律例》,试图厘清“典卖”和“绝卖”之间的区别,规定以绝卖名义而转移的土地不可回赎,买方付清买价后即不欠卖方一丝一毫;以典卖名义出卖的土地,在契约规定的时限内可以回赎,若卖方无力回赎,买方须支付找贴的价格,即土地典价与目前市价的差额,将典卖变为绝卖。买方只要不支付找价,卖方就有权将土地赎回。清廷在乾隆十八年(1753年)进一步规定,土地回赎的期限为三十年[3]。黄宗智认为,发生赎地纠纷诉讼时,清代的地方官依据上述国家法律保护当事者的权利[4]。1912年以后,相关法律进一步规范了乡村土地的买卖秩序。
(一)回赎期限
土地回赎期限方面,1915年10月16日颁布的《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规定自典卖契约成立十年内,卖主可以随时回赎;典卖契约成立一旦超过六十年,典卖自然变为绝卖①。1929年5月23日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规定,卖方须在典卖契约规定的典期届满后两年之内回赎土地,否则丧失回赎权[5]79。黄宗智认为,与民间无限期回赎土地的习惯相比,这一回赎期限的限制反映了立法者力图“寻找一条调和前商业逻辑与市场逻辑”的思路[2]84—88。
面对民间习惯与国家法律之间的背离,司法者如何处理涉及土地回赎期限纠纷案件?有的赎地纠纷诉讼发生于《中华民国民法》颁行之后,但是涉讼双方订立典契的时间在《中华民国民法》颁行之前,这种情况适用什么法律条文呢?
“刘继儒等与刘玉峰地亩”一案,安次县小北尹的刘玉峰在1936年试图赎回祖父刘宪廷于1926年出典的土地,被承典人刘继儒拒绝,为此,双方涉讼。安次县政府在1937年4月30日作出一审判决,准许刘玉峰备价赎地。刘继儒对这一判决表示不服,上诉到河北高等法院。刘继儒持有的理由包括:第一,刘玉峰在1928年找价时曾经约定以后不准回赎;第二,典期届满后已经超过八年,根据《中华民国民法》第九百二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承典人已经取得典地的所有权。在该案中,刘继儒一方面指出对方曾经作出“放弃回赎”的声明,另一方面援引《中华民国民法》关于回赎期限的规定,维护自己的正当性权利。
法院针对刘继儒对民法相关规定的援引,指出:
再查两造之典当契约,固经订定典当期限三年,但其典契之成立为民国十五年十月,当时现行民法尚未施行。依民法物权编施行法第十五条规定,依旧法规得回赎者,仍适用旧法规。再查民法施行前所适用之《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第八条规定,凡典产自立约之日起,十年期限之内,唯业主随时告赎②。
法院指出,涉讼双方订立典契的时间在《中华民国民法》颁布施行之前,不能适用《中华民国民法》的相关规定;订立契约时通行的《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规定土地回赎期限为十年。法院据此认为,出典人回赎土地的时间距离立契时间并未超过十年,刘玉峰可以备价赎地。这一民事判决,从国家法律规定方面论证了讼争地亩的地权归属,可谓依据国家法的判决。
“王墨林与王文生赎地”一案,法院也援引了国家相关法律论证地权归属。王墨林的祖父王怀智生前在1916 年将座落在通县第四区应寺村之地八亩二分出典给王文生的先父王玉芬,约定“不拘年限,钱到回赎”。面对王墨林请求回赎该地的主张,法院援引《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的相关规定,指出讼争地出典时间已经超过十年,王墨林无权回赎③。
上述两个案例的判决表明,法院审理涉及回赎期限这类案件时,并未考虑无限期回赎的民间习惯,而是援引国家在土地回赎期限的相关条文作出判决,在采用哪一法律条文这一问题上,法院选择的是典契成立时而非诉讼时通行的法律。寺田浩明认为,清代民事审判以“互让共存伦理”为中心,本质是惩罚只强调自身利益的正当性而忘记互让的“逾分”之人,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存[6]。艾仁民在对清代东北地区的土地买卖制度和实际运作的研究中指出,面对国家法律与地方习惯之间的冲突,县官采取了策略性的方式进行裁决:或遵循法律条文,或选择向习俗靠拢[7],这一研究表明了清代民事审判具有的实用色彩。河北高等法院在回赎期限这一问题上严格适用国家相关法律,反映出时至民国,保护弱者、互助共存这一伦理因素在民事审判中的式微,司法审判的实用模式开始向近代司法转化。
(二)共有土地的回赎
中国向近代转型之前,家族生活实行家族共产制。滋贺秀三通俗地解释了家族共产制,即“家族靠一个钱袋来生活,各个人的勤劳所得全部凑集到这个钱袋里,每个人的生计也全部由这个共同的钱袋供给,从而财产作为共同的家产得到保持。”[8]12家族的每个人对作为共有之物而被保持的家产拥有什么样的权利,滋贺秀三指出:家族中的每个人在家产未分割之前,无权处分实际为自己所有的东西,家产的处分需要通过全体成员的共同许可,这是唯一的处分家产之道[8]253。时至民国,家族共产制仍然在乡村社会延续。
如果有人私自将家族共有土地出典而引发家族中其他人的回赎诉讼,法院如何裁断,我们以“董赵氏与董福祥等请求回赎茔地及确认管理权”一案为例。1928年,董赵氏的先夫董存桂生前将祖遗茔地四十二亩中的三十亩零五分出典给他人,董福祥以董存桂之叔的身份诉请董赵氏赎回地亩。法院依据《中华民国民法》第八百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指出共有物应当由共有人共同管理,并作出判决:
本件讼争茔地两造既无特约订定由某一共有人管理,则董福祥等确认对于该地有共同管理权,即非无据。其次,公同共有物非经公同共有人全体之同意,不得处分。本件讼争茔地内三十亩零五分,既系董赵氏故夫董存桂以一人名义于民国十七年出典于传钱二姓而未取得董福祥等之同意,依法自属无效。兹董福祥诉请董赵氏赎回该地,亦无不当④。
以上情况表明,法院认为,董存桂将共有茔地出典时并未取得共有人董福祥的同意,这一做法“依法自属无效”(此处之“法”指的是《中华民国民法》)。因此,法院认为董福祥的诉讼请求具有正当性。
(三)债权和典权的分辨
《中华民国民法》对典权作了这样的定义:“称典权者,谓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之不动产而为使用及收益之权”[5]79,这一定义并未考虑到乡村社会中的典权有时由债权转化而来。例如,山西省祁县人在借贷时,以土地作为抵押品,书写借贷契约。倘若到期无法清偿债务,债务人再改写典约,抽回原立借贷契约[9]389。
若发生赎地诉讼,其中的典权由债权转化而来,在判断是债权还是典权这一问题上,法院如何裁断呢?
“魏朝卿与张万勤地亩”一案,魏朝卿声称,张万勤的先父张兆维生前向魏朝卿借款,因欠债未还,将讼争地亩出典,张万勤不应将该地亩再出典给第三方,要求将讼争地亩返还给魏朝卿。面对这一请求,法院检视魏朝卿提出的指地借款字据,认为这是债权契约而非典权契约,根据“民法第七百六十条不动产物权之移转或设定应以书面为之规定”,驳回了魏朝卿的请求⑤。可见,法院并未考究双方是否已经由债权关系转成典权关系,而是参考《中华民国民法》的规定,以缺乏书面典权契约、无法证明物权移转为由,判决魏朝卿的请求不具备正当性。
(四)典权人的先买权
在清末民初进行的习惯调查报告中,“典权人具有先买权”被认为是很多地方的“习惯”。例如,河南省开封县人出卖土地时,典主具有先买之权[9]100—101。山西省潞城县的出典人如果绝卖典卖土地,必须让典主先买,典主不愿买时,才能卖与他人[9]123。山西省定襄县“买不压典”的习惯,即指典权人具有先买权[9]388。
上述记载说明,民间社会承认典权人的先买权。在“张进善等与时韩氏赎地”一案中,1920年,时韩氏将讼争地亩典与张进善,双方并未约定回赎期限。1936 年,时韩氏欲将该地亩赎回另卖,被张进善拒绝。张进善认为,自己作为典权人,享有讼争地亩的先买权。法院并未针对是否存在典权人具有先买权这样的民间习惯以及是否承认这样的民间习惯具有法律效力作出判断,而是认为双方订立契约时通行的《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中“并无典产应由典主先买之定例”,所以时韩氏将土地卖与第三方而未让典权人张进善先买,不能成为张进善拒绝时韩氏回赎地亩请求的正当理由⑥。我们通过该案发现,法院对典权人的先买权这类案件作出判决时,依据的是国家法律而非民间习惯。
总之,在涉及回赎期限、共有土地的回赎、债权还是典权、典权人的先买权问题的纠纷审判中,河北高等法院依据国家法律进行明确裁定。
二、超越国家法的裁判
著名法学家齐佩利乌斯指出,适用国家法律有助于实现公正,但是忽略个案的特殊性则极有可能造成个案的非正义处置[10]。齐佩利乌斯认为,在司法个案中,如果适用国家法律会带来有失公平的现象,法院应该选择超越国家法的裁判。
河北高等法院档案中的赎地纠纷案例显示,情理、私人契约、民间习惯、先例这些超越国家法的因素同样是法院审判的依据。这一司法实践并非单纯追求个案的公正处理,更多的是司法官员面对既有的社会现实做出的无奈退让和妥协。
(一)情理
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清代民事审判带有强烈的调解色彩,是一种“教谕式的调解”[11]21,他将国家法律比喻为“情理的大海上时而可见的漂浮的冰山”[11]36,地方官做出的判断是“准情酌理”即习惯上妥当的判断,这里的习惯并不具有“在西洋法学传统影响下我们理解‘习惯’一词所具有的‘虽然不成文却能够得到实定化的具体规范’这种含义”[11]73。可见,滋贺秀三认为,清代民事审判的主要依据是“情理”。法官在民国时期的赎地纠纷审判中,“情理”也是裁断的重要考量因素。
“杨之秀与王振抚请求赎地”一案,密云县羊山庄的王振抚试图回赎在宣统三年(1911年)出典的地亩,被承典人杨之秀拒绝。密云县政府裁定王振抚按照东钱二十四吊折合银元的比率回赎地亩。杨之秀对这一判决表示不服,上诉到河北高等法院。在法庭上,杨之秀指出:第一,双方订立契约时,言明回赎期限为十年,现在距离出典日期已经二十余年,根据立契时的约定,讼争地亩理应归自己所有;第二,王振抚已经将讼争地亩卖与果廷萃而未卖与作为典权人的杨之秀,这一行为不符合“典权人具有先买权”之习俗;第三,即使允许王振抚赎地,亦应按照典契成立和找价时东钱折合银元的比率来核算。王振抚针对“典权人具有先买权”这一问题作了说明,声称在杨之秀表明不愿购买讼争地亩之后,才将该地亩卖与第三方果廷萃。可见,双方当事者皆依据“典权人具有先买权”这一民间习惯来陈述自身权利的正当性。
与前述“张进善等与时韩氏赎地一案”对照来看,这一案件中的一方同样依据“典权人具有先买权”这一民间习惯来声称自身的正当利益。在这一案件中,河北高等法院一方面依据国家法,说明“典权人具有先买权”这一民间习惯的非法性;另一方面,采取了“情理”的论证方式,力图证明王振抚将讼争地亩卖与第三方之前让杨深秀先买这一情况属实⑦。从人之常情出发,法院认为典权人杨之秀并非真正想要购买讼争地亩,从而驳回了杨之秀的请求。
当然,所谓“情理”,有时指的是实情,法官需要仔细辨析事实以取得实情,人证和物证得到了法院的重视。我们以“王秀芳与王秀兰赎地”一案为例。在该案中,王秀兰声称杨家楼的八亩土地为王秀兰和胞弟王秀惠分得的共有之产,此地在1928年由胞弟王秀惠出典给王秀芳的先父王守谦。王秀兰已经同胞弟分家析产,故向王秀芳请求回赎其中的四亩。王秀兰拿出分家析产簿,请证人证明自己的权利。经过核阅析产簿内的记载,法院指出,该簿并未记明具体亩数,无法确定讼争地亩由王秀兰分得;所谓的证人在“典价若干,何时出典”这些问题上表达含混。综合这些情况,法院裁定王秀兰的赎地请求无理⑧。这一案例从反面说明了司法裁判对事实的重视,包括对物证和人证的重视。
(二)私人契约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土地买卖秩序的维持,依赖的是交易双方订立的私人契约。清代官府通过征收契税的形式,得以介入民间土地交易,私人契约和官方契税文书共同构成产权凭证。有学者发现,人们并不愿意通过承担缴纳契税的责任换取政府对产权的保护:“个人权利最可靠的保证或许仍是得到地方社群的承认”[12]146。有学者发现:“契约如此有用,以致没有契约的人会通过欺诈和伪造契约来支撑他们的主张。他们把死去的人作为中人用他的名字伪造契约。他们会让家族中的一个文盲递交伪造的文件,利用他的不识字来减轻怀疑。”[12]130时至民国,政府推广新的产权证明,例如验契执照、不动产登记证书等[13],但是这些官方产权凭证并未在民间社会得到彻底推行。
在“刘承阴与李芝兰请求赎地”一案中,刘承阴声称讼争地亩于1928年出典给李芝兰,其间找价一次,但是并未绝卖,因而请求回赎。李芝兰声称在土地已经典出的情况下,刘承阴于1931年又将讼争地亩绝卖与他的弟弟刘承恩,李芝兰在1934年从刘承恩处购买了讼争地亩,因而拒绝回赎。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李芝兰提供了两份土地绝卖契约:一份是1931年刘承阴所立,另一契约是1934年刘承恩所立。面对这种情况,刘承阴否认上述两份契约的真实性。
我们同过上述案件发现,李芝兰除了提供两份土地契约之外,并未提供任何官方产权凭证。法院没有利用纳税登记来辨识契约的真伪,而是通过中人的证词以及核对笔迹等方式,确认了两份契约确实为刘承阴与刘承恩亲立。法院最终裁定李芝兰拥有讼争地亩的地权,驳回了刘承阴的赎地请求⑨。可见,在厘清纠纷事实中,私人契约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朱玉泉与朱玉樵回赎地亩”一案中,朱玉泉主张,祖父朱廷绍生前将二十五亩讼争土地典与徐光武,后由朱廷绍的长子朱镜代为赎回。朱镜已经出继,依照地方习惯,朱镜没有继承朱廷绍财产的权利,因而朱镜代为赎回的土地应归朱玉泉的先父朱镰。鉴于朱镜已经去世,因而向朱镜之子朱玉樵请求赎地。朱玉樵提交了光绪二十五年卖契,以此证明讼争土地并非出典而是绝卖,因此即使讼争土地分归朱玉泉,朱玉泉也无权回赎讼争地亩。通过核阅朱玉樵提供的地契,法院认为“纸张墨色均极陈旧”,并非“临讼捏造”,真实性自属无疑⑩。从这一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到法院非常重视双方订立的契约。
试图赎回先祖已卖之地的纠纷案件并不少见,这是人们视土地为神圣祖产这一观念的反映。在回赎过程中,有无契约关系重大。例如,杨俊山试图赎回父亲在世时出典给丁氏的土地。然而,丁氏已经将土地转卖给杨明显之父。在杨俊山无法提供相应契约证明权利主张正当性的情况下,河北高等法院裁断杨俊山不可赎回土地⑪。在这一案例中,法院将契约视为审判的重要依据,从反面证明了契约在诉讼中的地位。
上述案例表明,当事人订立的契约在日后发生纠纷时具有作为解决纠纷依据的效力。借用寺田浩明研究清代赎地纠纷的结论,官方面对土地回赎纠纷进行的土地裁决是以民间私契为依据的[14],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面对官方产权凭证并未在乡村社会得到彻底推行这一社会现实,司法官员从而做出退让和妥协。
(三)民间习惯
日本法律人类学学者千叶正士提出“法律多元”的概念,认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另外的法律体系”和国家法律共同发挥作用[15]。千叶正士谈到的“另外的法律体系”即民间习惯,民间习惯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正像昂格尔所指出的“即使是最冷酷的官僚法规则体制也只能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许多社会活动仍然受到习惯性行为模式的支配,这些规则被认为是自然规则的延伸。”[16]既然民间习惯的基础存在于当事人所在的社会中,法院在审判中就需要参照民间习惯达到解决纠纷的目的。
1913年大理院判决明确宣布:“判断民事案件,应先依法律所规定。法律无明文者,依习惯法。无习惯法者,依条理。”[17]1929年颁行的《中华民国民法》第一条规定:“民事法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5]41,在立法的角度表示了对民间习惯的尊重,填补了法律规定的漏洞。在土地的回赎时间上,大部分地区以“不违背农时”为基本原则。河北高等法院审判涉及回赎时间的赎地纠纷案时,采用了这一民间习惯。
我们以“崔永福与张永泉请求赎地”一案为例。1939年,崔永福承典张永泉所有地四亩。张永泉在典期届满请求回赎地亩时,崔永福以赎地时间不符“腊月不赎麦”“四月不赎秋”这一民间习惯为由,拒绝了张永泉的赎地请求。法院在判决时也指出了“回赎耕作地应于收益季节后,次期作业开始前为之”这一民间习惯的合理性⑫,这一判决依据表明了对民间赎地时间这一习惯的尊重。
(四)先例
先例,简单来说,即历史上曾经实行过的规则或者具体做法。
我们以“杨士昆等与张文彬赎地”案为例。在该案中,1923年,杨士昆典与张文彬十亩土地,典价东钱贰千吊。回赎土地时,双方在按照1920年还是1923年的东钱折合银元的比率支付典价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法院以“应就契载钱数比照当时市价计算”这一最高法院判决先例作出判决,认为杨士昆应当按照立契时间即1923年的比率赎地,故应支付张文彬典价一百六十七元⑬。我们从这一案例可知,最高法院的判决先例成为法院裁判本案是非曲直的重要依据。
三、裁断依据的多元化
综上所述,本文从国家法、情理、私人契约、民间习惯、先例五个方面分别就民国时期赎地纠纷的司法裁判依据进行了阐述。清末民初的法制改革和西方法制的引进,开启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建立了许多近代型的司法制度。刘昕杰认为,中国近代基层民事审判仍然延续了清代以纠纷解决而非法律适用为目标的实用型司法模式[18]。笔者与刘昕杰观点的不同在于,西方法制大规模引入背景下,在涉及回赎期限、典权人的先买权问题这些国家法律与民间习惯严重冲突的问题上,河北高等法院严格适用国家法律而非实用主义式的适用民间习惯进行裁决。“私人契约”“情理”“民间习惯”“先例”等因素在裁断中的适用,反映了民国司法体系功能的不足以及地方控制的薄弱,表明了这一阶段的审判实践中传统与革新交错的独特状况,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整合。
[注释]
①见《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载《东方杂志》,1915年第11期,第28页。
②河北省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 刘继儒等与刘玉峰地亩》,卷宗号:634—1—1103。
③河北省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 王墨林与王文生赎地》,卷宗号:634—1—915。
④河北省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董赵氏与董福祥等请求回赎茔地及确认管理权》,卷宗号:634—1—14。
⑤河北省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 魏朝卿与张万勤地亩》,卷宗号:634—1—806。
⑥河北省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 张进善等与时韩氏赎地》,卷宗号:634—1—273。
⑦河北省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 杨之秀与王振抚请求赎地》,卷宗号:634—1—1123。
⑧河北省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 王秀芳与王秀兰赎地》,卷宗号:634—1—1000。
⑨河北省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 刘承阴与李芝兰请求赎地》,卷宗号:634—1—299。
⑩河北省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 朱玉泉与朱玉樵回赎地亩》,卷宗号:634—1—1049。
⑪河北省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 杨俊山与杨明显请求回赎地亩》,卷宗号:634—2—402。
⑫河北省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 崔永福与张永泉请求赎地》,卷宗号:634—4—196。
⑬河北省档案馆藏《河北高等法院档案 杨士昆等与张文彬赎地》,卷宗号:634—1—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