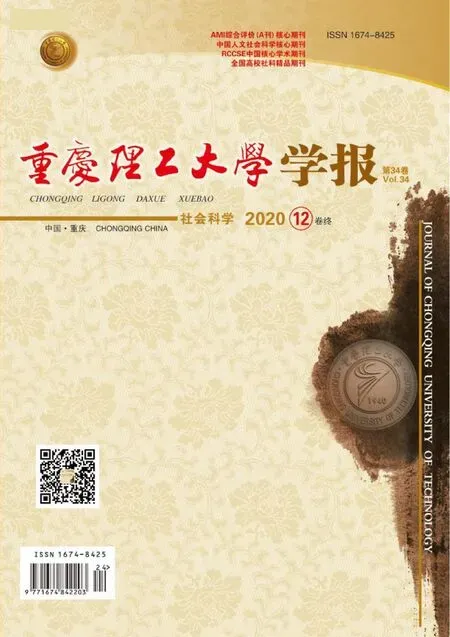拉康的欲望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陈蓉蓉
(常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
“欲望”是拉康精神分析哲学中的核心话语之一,它区别于弗洛伊德那里由无意识和性本能所驱使的欲望层面,也不同于黑格尔“自我意识”中主奴辩证法的欲望关系,而是在超越二者的基础上又援引了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能指链”理论,彻底颠覆了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的传统。在拉康的欲望理论的宣示下,主体作为一个“无”从出生甚至未出生就被命名的那一刻起旋即丧失了自我,而后又在他者的欲望牵引下陷进无尽的深渊,再无反抗及翻身的可能。
一、拉康欲望理论的逻辑起点
从笛卡尔的人类可以用理性掌控自我的“我思”开始,经由德国古典哲学的康德、黑格尔的系统阐述后,主体理论逐渐成为西方近代哲学的核心范畴。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作为自觉自明并且拥有自我意识的主体逐渐被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哲学家所质疑,结构主义、解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精神分析学等哲学流派纷纷加入了颠覆或改造主体的行列。其中,拉康用具有“先验的否定性”改造的“伪主体”理论更是冲击了传统的主体理论,令人深思。
“伪主体”理论是拉康全部哲学的逻辑基础。拉康对传统主体理论的解构是通过阐述主体的“两次异化”来实现的,而每次异化过程又可分为两个层面。也就是说,在拉康的笔下,真正的主体是经由4次蜕变逐步沦为“伪主体”的,而每一次的异变都是主体被打入痛苦的无尽“黑夜”的暴力之举。然而,更为恐怖的是,早已被掏空的自我被套上伪自我的面具却浑然不知。也因为此,拉康才写下了“在我思之玩物之处我不在,我在我不思之处”,以及人的存在“总是在别处”等一系列令人绝望的话语。
展开来说,第一次主体的异化是发生在想象域。在婴儿6~18个月的镜像阶段中,他还无法感知自己的身体以及协调自己的行为,比如排泄和进食。而当他第一次看到镜子中的自己,他就完全“被自己镜中的形象迷住了!”他会做各种动作来观察镜中的影像,慢慢地,婴儿认为镜中的像就是自己。婴儿异常兴奋,因为他通过镜子发现了自己“破碎的身体”的同一性和整体性,终于辨识出了“自我”。如此,婴儿将“自我”误认为是镜子中的影像,但事实上镜中的影像却是虚构的。婴儿放弃了真实存在的“自我”而将这个虚构的影像想象性地认同为“自我”,这是“伪主体”被建构的起点,也正是主体被扼杀的时刻。换句话说,主体在确认“自我”的那一刻起就丧失了真正的自我,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这也是贯穿整个想象域中“误认”的基点。拉康称这种最初的“理性—自我”为主体的视觉格式塔建构,也是拉康笔下主体首次异化的第一个层面。在这里要注意,“照镜子”一说是一种本体逻辑上的哲学隐喻,它并非实指实际中的照镜子行为,而是代指主体与小他者之间的一种关系性介质。第二层异化是从他人的形象认同中发生的想象性误认。婴儿逐渐长大,开始将父母、其他亲人的面容以及身边玩伴的行为和游戏等小他者的形象对象化为自己的欲望。这实际上就是一场隐性的暴力,因为当婴儿可以认清表情的背后所隐含的特定涵义时,原先那个“镜像之我”就会再一次强化和重构。主体占据着他者的位置,通过对面容的认同返回式地规范自身,在他者的凝视中抛弃自我,这实际上是一种以他者形象自居的自恋式、虚假式的想象性关系。这种以他人的面部表情、行为等产生的倒错式的意象投射到自我的想象性关系中的过程,再次印证了真实自我构建的不可能性。
想象域中的“理想自我”已被证伪,那象征域是否有生还的机遇?进入语言教化的象征域之后,已在镜像阶段失却自我的主体在大他者的关系性询唤中再次遭受异化,被迫接受大他者对自我的奴役,完成了由“理想自我”向“自我理想” 的转化。在本文的开头就提到,婴儿未出生就被命名的时刻是主体在象征域的第一层异化,这一层异化虽然发生在象征域,其实际上甚至是比想象域更早的一次异化。拉康说:“从他出生之时开始,即使那时只是以他的姓名的形式,他已经加入了话语的广泛活动之中去了。”[1]429主体自出生就被迫接受这个充满着先验期许的符号,并且无时无刻地被反复询唤着。“你叫A”“A很聪明”“A以后是个钢琴家”“A要好好学习”……殊不知你早已不是你,你只是一个替代品,一个符号。在强迫性认同之后,接踵而至的是更彻底的语言询唤中的异化。在拉康看来,整个社会就是一张由语言能指构建起来的象征性符号之网,人的本质就是一切语言能指询唤关系的总和。在现实的语言文化系统中,所有的交往都是一场场缺失的主体与另一个缺失的主体通过语言符号实现的交互式的象征性游戏。主体接受了大他者对自己的指认与引导,反过来主体也承担着大他者的角色重复着对他人的预设。基于此,拉康篡改了弗洛伊德引以为傲的“无意识”概念,将无意识与象征性语言链接起来,发出了“无意识是大写他者的话语”的最强音,宣告了本能原欲的不可能。“我不是我”,主体逐渐接受自己的符号与他者的询唤,成为空无之上的异化之再异化。
二、拉康欲望理论的逻辑展开
依据拉康的观点,个人主体在经过重重异化之后丧失了本真的自我,沦为“伪主体”,那么由“伪主体”内发出来的欲望自然也是虚假的。拉康在其独特的“需要—要求—欲望”三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欲望理论的核心观点——欲望就是他者的欲望。
(一)“需要—要求—欲望”三元说
弗洛伊德将本我之欲望视为主体生存的真正内驱力,认为欲望之我才是最具有本真性的。因为它是性本能冲动的延伸,尽管它会受到本我和超我的监督和阻碍,但总会想方设法挣脱出来实现自身的满足。然而,拉康改写了这种认知,他明目张胆地打着“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但却釜底抽薪瓦解了弗洛伊德的学理基础:之前是他的无意识理论,这次未能幸免的是作为无意识基础的本能原欲。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的“需要—欲望”观纯属于生物主义的本能说,拉低了人与动物的区别,因而给予了坚决的贬斥。拉康总是比他人复杂得多,他在自己“三界”理论的基础上区分出了“需要”与“要求”两个概念,继而抛出了“需要—要求—欲望”的三元说。
拉康认为,要求是异化了的需要。在镜像阶段以前,主体的需要来源于生理方面的匮乏,比如婴儿饿了会哭,而一旦得到了食物,婴儿就会停止哭啼。主体只要获得对象,具体的需要得到满足,需要就会终止。但是,在镜像阶段后期,这种需要开始发生某种转变。随着个人的身心发展,当主体可以区分出他人面容时,他已经开始通过认同他人的意象来重塑自己的内在要求了,欲望浮出水面。特别是在进入象征界以后,象征性语言的出现使得纯粹的生理需要不复存在,主体的要求被彻底异化,欲望开始兴风作浪,需要与要求最终分道扬镳。那么,这种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拉康告诉我们,从本体论意义上来说,自婴儿出生、离开母体之后,主体即面对着一种不可逆转的决定性的失去,因为婴儿再也不能回归母体。降生打破了主体与母体的一体性,主体有了生命,但这种存在却是以失去为代价的,这也变成了人类永远的“乡愁”。难怪拉康会说:“存在是作为缺乏的一种功能而开始存在的。”[1]223人自出生就意味着失去,缺失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缺失与生存相互统一。
然而,面对这种基始性的失去,主体虽无可奈何却还得不依不饶地寻求满足,以期填补这不可能的空缺。此时,要求开始登场。主体不断地向外界“要”,但在得到具体对象后仍无法得到满足。究其原因,拉康犀利地指出:“要求本身涉及到的是它所要满足的以外的别的事。它要求的是一个在场和一个不在场的东西。”[1]593在场的东西是需要的对象,不在场的东西才是主体真正欲求的——大写他者的爱。主体通过这种要求性的“要”表面上索要着具体的对象,但真正能使欲望得到满足的却是需要以外的东西。欲望=要求—需要。由此可以看出,在满足欲望的道路上,占据需要位置的具体对象是无足轻重的。主体要A,得到的可能是BCD,甚至绕过ABCD什么也没有得到,主体的欲望都有可能得以满足,因为主体真正的目的是得到大写他者的爱。换句话说,从需求到要求的过渡舍弃了特定的需求客体的特殊性,直接以对大他者的爱的表象形式发挥作用[2]。
主体缺乏的是大他者的爱,得到爱即可满足。可是,拉康的笔锋再次一转,他告诉我们欲望从始至终都是他者的欲望。
(二)欲望是他者的欲望
1.欲望是对他者欲望的回应。这点可以通过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加以说明。黑格尔指出:“自我意识是从感性的和知觉的世界存在反思而来的,并且,本质上是从他物的回归。”[3]116也就是说,自我意识是通过对自身以外的其他某物的反思性关系映照和确立的,自我意识不能自我存在,它只有通过镜像式地认同他物,通过对他物的确立才能返回自身、印证自身。我们知道,黑格尔笔下的自我意识问题的本质是对人类个体主体的确立,但我们可以挪用这一理论思维方式去理解拉康的欲望。欲望存在于与他人欲望的间性之中,反映了一种主体际间的交互关系。欲望总是发生在主体之外:一方面,主体的欲望与他者的欲望相对立,主体通过放弃自我的欲望,又在发现他者的欲望后映射式地确立了自我欲望;另一方面,主体在他者欲望中看到的是自己的欲望,实现了与他者身份的互换,因而也就扬弃了他者的欲望。这种“先否定自我—后肯定他者—再否定他者—最终肯定自我”的欲望的确立过程深刻说明了自我欲望与他者欲望的共在共存、对立统一。黑格尔早在《精神现象学》中就曾提出:“自我意识就是欲望。”[3]120这说明欲望是无法自身独立存在的自足实体,它必须在扬弃他者欲望的过程中才能确信自己的存在。对此,萨特也说过类似的话:“我是一个由于别人才是自为的存在。”[4]伊波利特也曾说:“只有两个自我意识相遇才可能存在自我意识,才可能存在人的存在。‘我’在另一个我中自知,而另一个仍然是它自己。”[5]
2.欲望是对缺失的欲求。拉康的“需要—要求—欲望”三元说之间的逻辑关系表明,伴随着个体进入象征域,需要开始转变为要求,要求又必须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语言不过是一系列漂浮的能指所组成的,意义总在他处。此处,拉康引入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透彻分析了欲望归根结底是对无的欲求。在由人类的语言交往构成的象征域中,任何事物都用符号来指称,没有符号的事物是不存在的。符号代替了具体事物的存在,但这种替代却是在符号挖空自身存在之后才实现的永恒。符号杀死了存在,反过来又通过这种象征关系重构了存在,但是,在空无之上建构的任何事物终究也只能是空。拉康又改写了索绪尔符号结构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强调能指的至上性,认为能指并不依赖于所指,能指可以脱离所指。在拉康看来,语言取代对象或者主体的本质就是能指取代它们真实存在的过程,能指才是本体论上真正的统治者。然而,能指本身只是一种关系,它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只有通过转喻或换喻的方式,在对其他能指的不断的迁移和替换中才能描述自己。由此我们得出结论,唯有通过能指才能表达出来的欲望也终究无法完全被表征,欲望就是缺失。因而,无论主体欲望什么,始终也只是一个能指滑向另一个能指的符号游戏罢了。欲望本身的空无恰恰就是主体永远欲望的无尽的内驱力量,然而欲望本身的空无将欲望演变成一个巨大的漩涡,主体不断地对他者产生欲望以寻求满足,其结果只能是越陷越深。
3.欲望是成为他人欲望对象的欲望。科耶夫说:“所有人类的人性的欲望,即产生自我意识和个性现实的欲望,最终都是为了获得‘承认’的欲望的一个功能。”[6]人的欲望就是被承认的欲望,就是成为他人欲望对象的欲望。在黑格尔著名的主奴辩证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主人和奴仆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一场承认的斗争。主人和奴仆最初都是同等的,但在二者相互映证的过程中并非都能够达到平衡,在还未达到完全统一状态时,二者就不得不以两个相互对立的“自我意识”形态存在。在这场殊死的斗争中,“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一场的个人”即输的一方“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3]126,因而沦为具有依赖意识的奴隶,变成了被承认者;而赢的一方则成为了承认者,即具有独立的意识的主人。后来,奴隶在劳动过程中获得了自己自为的存在,主奴关系开始颠倒,继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承认与被承认的较量。再比如精神分析学话语中的独特的“俄狄浦斯情结”,幼儿知道母亲的欲望是菲勒斯,因而为了博得母亲的爱不惜做出各种努力,他要把自己变成菲勒斯,即欲成为母亲的欲望对象。主体始终追求着另一个欲望对自己的对象性承认,换句话说,主体欲望的本质其实就是成为他人的欲望对象。
三、拉康欲望理论的逻辑深化
要想更深层次地读懂拉康的欲望理论,还必须区分出“欲望对象”和“欲望的对象—成因”两个概念。“欲望对象”就是主体想得到的那个具体的东西,而“欲望的对象—成因”则是指为何主体想要那个东西,驱使主体渴望那个东西的动因是什么,拉康称之为“对象a”。在拉康的哲学视域中,对象a可谓是一个最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概念,而它又被拉康自己视为最大的理论成就。笔者试图在拉康的欲望理论语境下,尝试解读对象a是如何实现欲望运作的。
(一)欲望的动因:对象a
对象a从何而来?我们知道,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哲学中,主体是被异化、被划去本真存在的伪主体。主体要想进入社会文化体系,就必须经过象征域中语言符号的洗礼,压抑或摒弃那些不为社会秩序所容的主体欲望。然而,象征界对主体的这种阉割往往都是不完全的,总会留有些剩余、残渣,这就形成了一种创伤性的因素,从而构成了实在界。也就是说,实在界或者这些创伤是象征域对主体符号化失败的剩余、产物,这就是对象a。可见,对象a就是不能被符号化的东西,它是一种抽象的快感剩余物。这与前文所阐述的欲望是要求减去需要所得到的以外的东西相一致的。拉康告诉我们,对象a从一开始就与幼儿的自我身份认同相关。它是幼儿回溯性认同和寻找能够提供身份定位的东西,是与幼儿与母亲的关系中被赋予特殊意义的东西——乳房、粪便、男根等[3]126。欲望正是围绕着对象a来旋转和运作的。不仅如此,对象a还会随同主体一起进入象征界,这就会导致能指秩序的不一致性和空缺。为了阻止实在界对象征界的侵入,隐藏社会的不一致性,就需要幻象(MYM◇a)修饰和填补能指秩序的空缺,赋予社会以整合意义。
(二)欲望的运作:幻象
幻象的公式$◇a表明伪主体在追逐对象a的过程中形成了幻象。拉康的门徒齐泽克告诉我们,由对象a产生了幻象,幻象又建构了欲望。幻象为伪主体的欲望提供了一个框架,伪主体在这一框架中拥抱了欲望和现实。换言之,幻象塑造了伪主体的欲望,因为幻象的形成,伪主体才能够产生欲望,幻象正是伪主体与对象a成功架构主体之现实的存在方式。在幻象的帷幕下,主体追逐着他者的欲望,渴望着具体的欲望对象,但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幻觉,主体真正的欲望实际上是对对象a的欲望。再换种说法就是,对象a并不是直接的欲望对象,而是欲望中的对象。如此一来,每个主体都根据自己的对象a构建出了独特的幻象,在这一幻象框架中追求着各自的欲望对象。幻象还有一个功能,就是维持欲望,阻止主体过于接近实在界之原质即对象a。幻象的这两个功能恰恰又形成了幻象的悖论:幻象通过对象a构建了主体的欲望,却又要始终保持着欲望与对象a的分裂,如此欲望才能延续。齐泽克说:“将幻象的悖论加深到极致,将其变成了一个重言句,欲望本身就是对欲望的抵制。”[7]这也正是齐泽克的“欲望是对欲望的防御”一说的理论来源。
(三)欲望的毁灭(这里特指被幻象建构起来的欲望):穿越幻象
对象a是形成欲望对象的成因,但要维持主体欲望的正常运行就必须要保持对象a与欲望对象之间存在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欲望不能通过直接获得对象a寻求满足,否则过于接近实在界的原质的结果就是失去欲望本身。我们可以通过希区柯克的经典影片《迷魂记》来阐述欲望的毁灭。患有恐高症的侦探斯考蒂在爱人玛德琳死后,回溯性地将本是普通客体的玛德琳提升至崇高客体的位置。在和玛德琳的长相一模一样的朱蒂出现后,斯考蒂的对象a就显现出来了,那就是在斯考蒂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玛德琳的金色的卷发和银灰色的套裙。此时,幻象形成,并开始组织起斯科特的欲望。在这一幻象架构中,斯考蒂的欲望对象是玛德琳。斯考蒂在朱蒂身上疯狂追求着玛德琳的痕迹,他把朱蒂打扮成玛德琳的模样——一样的金色卷发和银灰色的套裙。然而,故事出现转折。当朱蒂把属于玛德琳的项链佩戴在胸前时,斯考蒂终于明白朱蒂就是玛德琳。玛德琳没有死,斯考蒂找回了一直追求的欲望对象。但是,斯考蒂对玛德琳(即眼前的朱蒂)的所有欲望却烟消云散,最终还企图杀死朱蒂。剧情竟如此发展,原因就在于死亡后的玛德琳是借助于对象a在斯考蒂的幻象中重生的,她本该仅仅存在于实在界,却意外被斯考蒂撞破,换言之,对象a不幸遭到了斯考蒂的正面凝视而立即消失,幻象破灭,欲望自然也不复存在。
拉康的欲望理论为我们重新认识人的存在、人的追求等问题提供了别样的思路,虽然它有些消极,总是在一种悲情主义的语调中解读着“人生而死亡”的论断,但每一种理论的诞生都是在帮助人类更加清楚自己的处境。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拉康的欲望理论可以说是当头一棒,使我们有一丝清醒,要我们学会“向死而生”。
四、拉康欲望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欲望理论作为拉康精神分析学派的核心范畴之一,它与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之间有何区别,对指导我国当代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是否具有现实意义,这些都需要作进一步的解读。
(一)拉康的欲望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之间的区别
拉康的欲望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看似相同,都是在探讨人的能动性等问题,但实际上二者存在质的差别。稍不注意,人们就会倾向于把二者相互混淆以致走向唯心论。因此,必须正面解读拉康的欲望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之间的区别。
1.二者的哲学基础不同。如前所述,拉康的欲望理论是在根本否定人之存在的关系本体论又颠覆性地吸收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能指链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拉康信奉的是一种“能指决定论”。在他看来,整个社会都是由能指构成的,人类在构建自我的同时异化成一串符号,沦为能指统治世界的工具。如此,拉康的欲望理论也就失去了任何客观性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生产,生产的目的是需要,而需要及其满足又是人类生存及历史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说:“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如果不是为了人的需要,人们就什么也不能做。”[8]“没有需要,就没有发展。”[9]9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需要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本身。由于生存和发展从来都不是随心所欲,而是依据一定的客观条件的,所以条件也自然衍化成需要的题中之义。这些都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客观性基础。
2.二者的价值目标不同。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以人的发展为最高命题,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其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它包涵3个层面: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乐需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抨击也可以说是从这3个层面出发的,他尖锐地指出了阶级地位对满足需要的影响。马克思描绘了当时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指出被剥削阶级只有生存的需要,而这个最基本的需要都被资本家降到低于动物需要的水平,以致被剥削阶级失去了任何可能发展的机会。因而,要实现人的解放就必须肯定人的需要。拉康的欲望理论从想象之镜到他人之镜再到语言的域场,最终引出了“对象a”的概念。拉康告诉人们“对象a”才是欲望追求的真正对象。正如前文所阐述的,对象a也仅仅只是存在于实在界的缺失。换句话说,拉康的欲望理论来自空无,走向空无,那么其价值目标也只有空无。
3.二者的历史性不同。马克思说:“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9]218需要及其满足是一切人类历史的前提,社会的发展推动需要的不断变迁,吃、喝、住、穿等需要的满足又会引起新的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在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之后,劳动又会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也将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可见,马克思主义一直都非常重视需要的历史性,可以说,需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共同主题。与之相比,拉康的欲望理论严重忽视了历史性,甚至可以说,拉康的欲望理论中根本不存在历史维度。拉康仅仅关注欲望对象的共时态变化,缺乏对历时态的研究。在拉康的笔下,欲望是他者的欲望,欲望永远是变动不居、捉摸不定的,而欲望越是在形式上纷繁复杂、变化万千,越是说明欲望的无规律性、无发展性,因而也就暴露了欲望理论的无历史性。这也是拉康整个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的致命缺陷所在。
(二)拉康欲望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当代价值
对拉康欲望理论的解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思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形成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蒸蒸日上,究其原因,离不开党和国家在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满足人民的需要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并逐渐成为尖锐的社会矛盾。无良人士对利益的追逐开始掩盖其道德诉求,欲望在当代对人的压迫开始变本加厉,社会开始成为欲望的道场。失去理性的欲望与需要渐行渐远,欲望与需要分离的直接结果就是主体变成欲望的奴隶。这里,我们可以援引鲍德里亚对消费时代的批判加以说明。他说:“浪费性消费已经成为一种日常义务。”[10]浪费性消费的存在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密切相关,特别是现代社会中的媒介文化已经达到了“神”一般的境界:电视、电影、广告等通过日新月异的技术手段激起人的消费欲望并逐渐开始支配人的生活。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从来都不是去真正地消费媒介文化所宣传的产品本身,而仅仅是消费它们所制造出来的欲望。换句话说,人们在媒介文化的驱使下一遍遍地将所拥有的产品更新换代却从不满足,无所不在的欲望大肆侵淫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永远为眼前光怪陆离的色彩而亢奋。反思当下国内对某品牌手机的疯狂追求就能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大众对无限膨胀的欲望追逐的现象。因此,拉康的欲望理论虽有其缺陷,但对深入分析当代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中人的欲望与人的需要的关系问题有一定的启示。
欲望作为一种驱动力,它应该是实现需要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背叛自我的迷药。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要特别重视引导人们厘清欲望与需要的关系,通过宣传教育倡导满足正当需要,避免欲望的泛滥,达到大众对欲望和需要理性认识的统一,从而让人们对欲望进行自我约束,实现自我解放;另一方面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同时,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以人民的需要为准绳,保持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之间的平衡,合理调控社会大众的欲望追求,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建设,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