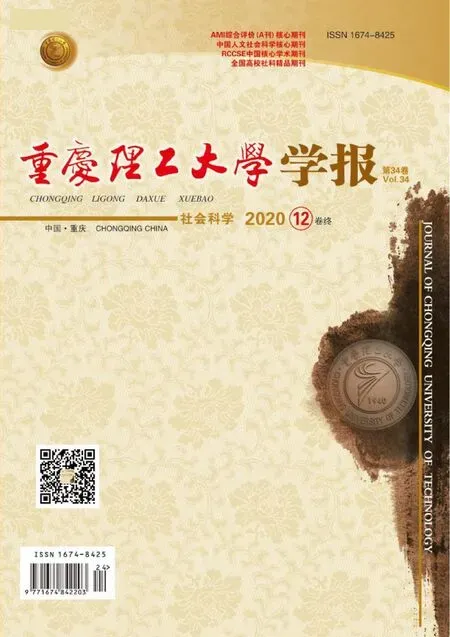和三个“逻辑悖论”相关的几个分类—命名问题
胡义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悖论”这个名称是有歧义的。在逻辑和哲学之外,“悖论”的意义宽泛得多,那些满足“有悖于常理”这一古希腊要求的概念、陈述、论证甚至图形都可以看作“悖论”。但是,在逻辑和哲学之内,我们对于“悖论”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一般只会把那些从看起来可接受的前提经过看起来可接受的推理却得出不可接受的结论(1)这是对于笔者2018年对英国哲学家塞恩斯伯里(Richard M.Sainsbury)的悖论定义的修正的一个再修正[2],差不多算是又回到了塞恩斯伯里的说法,除了“看起来不可接受的结论”和“不可接受的结论”之间的差异而外。只不过我们不必太纠结于这个差异,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迄今为止都不太关注那些包含初看起来不可接受而细看之后却是可接受的结论的“悖论”。的论证看作“悖论”。这种严格一些的“悖论”,在逻辑和哲学之外看来,基本上就是“悖论”加上“逻辑”限制得到的“逻辑悖论”想要指向的东西。那么,回到逻辑和哲学之内,“逻辑悖论”因为加了“逻辑”的限制又该指向何处呢?
令人诧异的是,恰恰是在逻辑和哲学之内的现代讨论当中,关于“逻辑悖论”呈现出了一种混乱的理论景观:“逻辑悖论”在国内外先后至少以三种不同命名方式出现过,而围绕着这些方式出现了一些本不该出现的分类—命名问题。我们从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弗兰克·兰姆赛(2)对于Ramsey,国内已经有“莱姆塞”(张建军)、“拉姆赛”(陈波)这两种译法。考虑到更接近英文发音而且不太偏离已有译法,本文采取“兰姆塞”的译法。本文中引文的翻译均系笔者所为。(Frank P.Ramsey)将《数学原理》第一卷引论当中的7个“自我指称”悖论加上格雷灵悖论分成“A”“B”两类这个现代开端以来开始算起,主要关注的是其中的三种命名方式,而没有把更早些时候,譬如英国作家、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刘易斯·卡洛尔(Lewis Caroll)1894年在Mind杂志上对于“逻辑悖论”的用法考虑在内,也没有把美国哲学家罗伊·库克(Roy A.Cook)最近在《逻辑哲学词典》当中等同于“语义悖论”的孤立用法考虑在内:
语义悖论(或者逻辑悖论)是关于真、满足、指称或相关语义概念的基本直觉引起的悖论。语义悖论的例子包括说谎者悖论,雅布罗悖论以及指称悖论。[1]255-256
第一种方式把兰姆赛的A类悖论称为“逻辑悖论”,而兰姆赛当时只是暗示而没有明确表述出这一方式。第二种是美国哲学家霍华德·卡哈尼(Howard Kahane)的方式,按照“使用逻辑产生或者澄清的悖论”的定义方式来使用“逻辑悖论”。第三种是张建军教授的方式,将“逻辑悖论”定义为满足“三要素”的一种特殊理论状况。
从“悖论”到“逻辑悖论”,即便正如本文急切期盼的那样只是在逻辑和哲学之内讨论,都还是摆脱不了某种程度的模糊性。这原本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更紧要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已经获得“悖论”称号却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的理论,譬如说谎者悖论,我们如何从理解跨越到将其解决。因而当我们发现在关于“逻辑悖论”的定义或者命名方式当中出现了某种混乱的时候,把其他的紧要事项暂时放在一边,认真考虑一下其中的问题实质是什么,应该也是有一些重要意义的。
“逻辑悖论”应该是在“悖论”当中按照某种意义上的“逻辑”特征划分出来的一个名称,因此要追究有关“逻辑悖论”的定义或者命名方式当中涉及到的问题,我们就有必要把它们放在分类—命名这个连贯机制当中来观察。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采用“分类—命名”这一连贯表达,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只是考虑到把“分类—命名”看作一个连贯过程,以便从整体视角观察“逻辑悖论”中的问题更方便而已。
一、分类—命名过程及其可能问题
在构建人类知识秩序的活动当中,分类和命名都是基础和平常的事情,而且分类几乎总是伴随着命名。把它们连贯起来称为“分类—命名”就是,在一类东西当中按照某个恰当的原则分类并为由此划分出来的子类命名这样一种过程。详细来说,一个分类—命名过程大致是这样的:首先确定一个能在这类东西当中造成有效划分的分类原则,然后根据这个分类原则划分出不同的子类,最后根据这些子类相对于这个分类原则表现出来的特征,用代表这些特征的词项和原来的类名结合来为这些子类命名。以奇偶数的数学分类为例,能否被2整除就是类别特征,能被2整除的归为“偶数”一类,不能被2整除的归为“奇数”一类。
一个分类—命名过程,往往是可以轻松实施的,只要我们稍加留意以确保分类原则和命名机制的恰当性。不过,我们也可能在分类—命名的事情上出错。在分类的这一环节上主要有两种出错方式,有时候是因为分类原则的有效性欠佳,造成某些个体同时出现在一个以上的子类当中,而更多的时候是错误划分,也就是把那些不具备某个类别特征的个体误认为具有这个类别特征从而划入错误的子类当中。但是另一方面,在有一个恰当(或者哪怕权且看作恰当)的分类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几乎很难想象会在为已经恰当划分出来的子类命名时出错,事实上我们也很少会在命名这个更轻松的环节上出错。
在悖论的分类—命名上,我们有可能因为在分类原则的选择上超前于某些悖论的研究现状或者涉及到如何才算恰当解决一个悖论这样的争议,带来更多的错误划分。除开这种可能出现在分类环节上的特殊困难而外,悖论的分类—命名大体上也是同样可以轻松实施的。我们不必像波兰逻辑学家皮奥特·库科夫斯基(Piotrukowski)那样过分忧虑:
悖论分类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不清楚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分类。[3]2
而更应该像美国哲学家尼古拉斯·雷彻尔(Nicholas Rescher)那样坦然面对分类原则的可能性:
几乎跟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悖论可以按照各种不同的原则来分类。主要的一些原则包括:主题内容,从是什么东西出错而导致悖论这个角度来说的病理学,消解模式,跟谈论悖论对于精细分析机制的需求程度相关的复杂度。[4]70
雷彻尔在他的书当中选择了主题内容这一个分类原则,可能因为它是“我们最熟悉的”[4]70也是最安全的。但是,即便选择了像病理学或者消解模式这样“危险”的分类原则,我们也不必恐惧,大可以抱着试错的心态照常执行分类—命名的过程。然后,对于我们感兴趣的单个悖论照常努力尝试理解和消解,直到对它的深入理解带来它在划分方式上的变化时再回过头来修正原来的划分方式。事实上,那位波兰逻辑学家也是这么做的,他冒险选择了“将一个悖论的实质作为分类的根本原则”[3]2,并且据此从悖论当中划分出“错误直觉的悖论”“歧义的悖论”“自我指称的悖论”以及“本体论悖论”,写完了整本书。
这么说来,我们为悖论的分类—命名不管是选择安全还是危险的分类原则,接下来的事情跟在其他分类—命名过程当中一样,也是简单明了的,按理不会出现命名上的问题。但是,在下面三个“逻辑悖论”当中看到出现在命名环节上的分类—命名错误时,我们多少还是会感到几分错愕。
二、兰姆赛的“逻辑悖论”
准确地说,兰姆塞的“逻辑悖论”不是他自己命名的,而是后来的学者追加给他的。在1925年发表并且在1931年重印在他的纪念论文集当中的《数学的逻辑基础》那篇文章中,兰姆赛追随弗雷格(Gottlob Frege)、怀特海(Alfred N.Whitehead)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等人试图用逻辑为数学奠定基础的逻辑主义路线,来尝试对于怀特海和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提出一些改进。他对于《数学原理》当中对于那7个“自我指称”悖论的处理方式不满意,建议按照“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分类原则将那7个悖论和格雷灵悖论一起分成“A”“B”两类或者两组(3)尽管“组”是更符合原文“group”的译法,但是因为它和“类”在这里并无实质差异,我们仅在引用兰姆赛时采用这一译法。:
A.(1)所有不属于自己的类组成的类。(罗素悖论)(4)这些括号连同其中的通用悖论名称都是本文添加的标注。
(2)其中一个关系对于另一个关系没有前一个关系的两个关系之间的关系。(理发师悖论)
(3)最大基数的布拉里-弗蒂悖论。
B.(4)“我正在说谎。”(说谎者悖论)
(5)不可用少于十九个音节命名的最小整数。(贝里悖论)
(6)最小的不可定义序数。
(7)理查德悖论。
(8)魏尔关于“异质性 ”的悖论(格雷灵悖论(5)兰姆赛当时将这个悖论的发现权错误地归功给了德国数学家赫尔曼·魏尔。)。[5]20
在将这个分类方法看作悖论分类的现代开端的同时,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它跟现在对于悖论的分类—命名的一般理解有几个不同之处。首先,兰姆赛的这个悖论分类并不是在逻辑和哲学当中的悖论的一般范围内执行的,而只是局限在数学的逻辑主义兴趣所及的那几个悖论当中。其次,兰姆赛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具有根本重要性的”的分类原则是什么。好在我们可以推断出来,相比主题内容和可表述方式,兰姆塞更重视的是悖论的错误根源:
A组悖论由那些在没有对它们做好防范的情况下出现在一个逻辑或者数学系统本身当中的悖论构成。它们仅仅涉及诸如类和数这样的逻辑或者数学用语,并且表明是我们的逻辑或者数学出了毛病。但是B组的悖论不是纯逻辑的,也不能仅仅使用逻辑用语陈述;因为它们都涉及到了不是形式用语而是经验用语的思想、语言或者符号系统。因此,它们的悖论根源也许不是错误的逻辑或者数学,而是关于思想或者语言的错误观念。如果这样,它们就不会和数学或者逻辑相关(如果我们的“逻辑”指的是一个符号系统的话),尽管它们也会在思想分析的意义上跟逻辑相关。[5]20-21
最后一点,更有意思的是,也是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是,兰姆赛居然没有为划分出来的两类悖论分别取一个有意义的子类名称,而只是给了“A”和“B”这两个仅仅有区分意义的标签。这个略显尴尬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在探讨数学的逻辑基础的情景当中,兰姆塞没有为悖论分类起漂亮名字的修辞功力,也可能是因为兰姆塞在为A类悖论快速找到“逻辑或者数学”的类别特征的同时,为B类悖论初步提炼出来的“经验”“思想或者语言”“认识论”这些特征都不够准确甚至很不准确,而要从中挑选一个概念作为B类悖论的类别特征难免有点牵强。
兰姆赛的分类—命名没有走完的最后一步,其实也就是最后的轻轻一跃。后来的学者继续遵循逻辑主义的路线,就将A类悖论称为“逻辑悖论”,但是随着逻辑主义的式微,“逻辑悖论”的这个用法逐渐被“集合论悖论”甚至“数学悖论”代替。即便如此,“逻辑悖论”这个名称迄今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被看成是一个还有生命力或者值得格雷汉姆·普列斯特(Graham Priest)[6]25挑战的正统名称。另外,对B类悖论的“思想或者语言”“认识论”根源的进一步认识最终让我们抵达“语义悖论”这个争议更小的名称。然而,正是在“B类悖论”和“语义悖论”之间出现的一段插曲,容纳了“语形悖论”这个现在看来非常奇特的命名形式。
◆卡尔纳普的“语形悖论”
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是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他的《语言的逻辑语形学》先是以德文版的形式在1934年出版,稍后以齐柏林公爵夫人翻译并且经由他本人修改而成的英文版形式在1937年出版。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现代逻辑在经过近一百年的形式化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情况下,“语形主义”思潮在主要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学术圈子内汹涌澎拜的时候。卡尔纳普在这本书中试图构建一种他称之为“语形-语言”(syntax-language)的语言,来实现仅仅通过语形上的计算与推理来解决人类在经验事实之外的所有思想争端这一伟大的语形主义构想。
卡尔纳普有可能就是第一个帮兰姆赛走完那最后一步的学者。他考虑在语形-语言当中如何避免悖论时,“遵循兰姆塞将悖论分为两类的先例”,接着又说那两类悖论“可以分别称之为逻辑的(在比较狭隘的意义上)和语形的(后者也被称之为语言的、认识论的,或者语义的)”[7]211-12。将兰姆塞的A类悖论称为“逻辑悖论”,这好理解,但是他将兰姆塞的B类悖论称为“语形悖论”,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初看起来,卡尔纳普以格雷灵悖论作为“语形悖论”的例子,其中一个谓词的语形形式不具有这个谓词本身指称的性质(譬如“圆”这个字本身不是圆的)这个异质性而起,倒是包含了语形因素这一个独特之处。但是,其他B类悖论中却没有类似于格雷灵悖论当中的这个语形因素,那么在遵循兰姆塞的分类原则的情况下,卡尔纳普又是怎么在既包括格雷灵悖论又包括说谎者悖论的B类悖论中提取出“语形”这个类别特征的呢?
现在看来,他的“语形悖论”更有可能来自他对于兰姆赛的两类悖论在语言层次上的数量差别的观察。兰姆赛的A类悖论只涉及一个语言层次,在数学或者逻辑的对象语言当中就可以被描述出来,而B类悖论则涉及两个语言层次,一个是“是真的”“可定义的”这些语义概念词所在的元语言层次,另一个是被它们谈论的对象语言层次。在已有“元语言”和“对象语言”这种对比用法的情况下,卡尔纳普却因为被语形主义驱使才另外设计了一个“语形-语言”的名称来代替“元语言”。这样一来,当A类悖论的悖论根源在于“逻辑-语言”而被称为“逻辑悖论”,而B类悖论的根源在于“语形-语言”而被称为“语形悖论”也就可以得到解释了。但是,这个“语形-语言”的用法,从语言的分类—命名的角度来看,至少现在看来,是不恰当的。还有个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个恰当的分类—命名过程当中,“语形悖论”怎么能同时又可以被称为“语义悖论”呢?
或许,卡尔纳普对于“语形”的用法不那么纯粹,还杂糅了对于语义因素的考虑,惟其如此,我们才可以勉强解释关于“语形悖论”的这些问题。纯粹的语形主义构想注定要失败。事实上,没过多久,卡尔纳普在塔尔斯基的启发和建议之下放弃了这个语形主义构想,转向语义学,并相继于1942年和1943年在“语义学研究”系列下分别出版了《语义学导论》和《逻辑的形式化》两本书。另外,除了随后几年有几个学者(包括罗素和格雷灵在内)在赞同他对于悖论分类的观点时顺带沿用了他的“语形悖论”以外,卡尔纳普的“语形悖论”很快被人遗忘了,他本人从此以后也再没有提起过这个奇怪的名字(主要的原因是他的研究路径的变化没有给他再次讨论相关议题的机会)。
三、卡哈尼的“逻辑悖论”
作为推动非形式逻辑发展的一个重要人物,霍华德·卡哈尼也擅长以“以清晰、简洁和相对容易理解的方式”[8]前言给学生提供现代逻辑基础的全面介绍。他的《逻辑和哲学》第1版在1969年发行,随后多次再版,从第7版开始有合作者加入,而最近的版本是2012年的第12版。谈论逻辑和哲学,就很容易谈到悖论。从这本书跨越近30年的第4版和第11版这两个版本来看,始终都有名为“逻辑悖论”的一个章节(在第4版是一章,在第11版是一节)在谈论悖论,而卡哈尼基本上就只是在“逻辑悖论”的名称下谈论悖论。
一方面,他把“逻辑悖论”理解为“使用逻辑生成或者澄清的悖论”[8]318,[9]310,期望涵盖的还是兰姆赛那两类悖论。显然,这种理解对于兰姆赛的分类传统既有遵循的一面,又有偏离的一面。但是,遵循的一面,反映的却是对于1969年以来超出兰姆赛的逻辑主义视野关注更大的悖论范围这一主流立场的一种偏离。而在偏离的一面,“使用逻辑生成或者澄清”的表述并不够清楚,如何算是“使用逻辑生成”和如何算是“使用逻辑澄清”都是问题,那么以它作为分类原则进而得出“逻辑悖论”这一名称可能就是不太适合的。反过来看,那些不是借着“使用逻辑生成或者澄清”的悖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是像第4版当中在“逻辑悖论”之外出现而在第11版当中消失的乌鸦悖论那样的么?正如他曾经承认乌鸦悖论“有希望通过使用谓词逻辑来阐明”[8]313的那样,在“逻辑悖论”之外的乌鸦悖论和其他悖论都可以归入“逻辑悖论”,那么卡哈尼的“逻辑悖论”也就轻易超出了原来设定的兰姆赛范围,因此丧失了他试图用“逻辑”从悖论当中刻画某种“逻辑”特征的分类—命名作用。另一方面,在“逻辑悖论”之内,卡哈尼依据一个危险的分类原则将兰姆赛的两类悖论分别称为“语形悖论”和“语义悖论”,由此展现出来的是更为严重的分类—命名问题。
◆“语形悖论”和“语义悖论”
卡哈尼把悖论的解决方案区分为“语形的”和“语义的”,以此为基础确立分类原则,进而把“逻辑悖论”划分为“语形悖论”和“语义悖论”:
语形悖论:一个大多数哲学家仅仅接受其语形解决方案的悖论。比如,不可谓述悖论是一个语形悖论。[8]323
语义悖论:一个大多数哲学家仅仅接受其语义解决方案的悖论。例如,说谎者悖论是一个语义悖论。大多数哲学家接受一个语义理论,那个所谓的语言层级理论,作为这个悖论的一个解决方案。[9]318
这正好与逻辑系统分为语形学和语义学的二分法对应,从形式上来看非常新颖和优雅,但是形式上的美感并不一定对应着实质上的合理性。事实上,大多数哲学家仅仅接受其语形还是语义解决方案这样的分类原则是错乱无效的。首先,其中的“大多数”蕴含着的模糊性,势必削弱这个分类原则造成清晰划分的能力。其次,一个基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悖论解决方案应当被称为“语形的”,什么样的应当被称为“语义的”呢?卡哈尼大概觉得“语形”和“语义”之间的区分如此清晰,用来区分悖论的解决方案时也无需辨析,以致我们只能在他对于两类悖论的解决方案评述当中推测他的相关理解。基于大多数哲学家接受类型论方案作为不可谓述悖论的解决方案这一当时已经不太可靠的假定,他将不可谓述悖论(罗素悖论的一个变体)看成“语形悖论”,是勉强可以理解的,因为执行类型论方案最方便的方法就是为相关表达式增加不同的语形标记来表征不同的类型。但是,他将说谎者悖论看成是语义悖论的代表时,依据的分类—命名理由却是,说谎者悖论的语言层次论方案应该看成语义解决方案,这就完全忽视了语言层级和类型在语形处理上的相同之处:表征语言层级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通过在相关的语言设施上添加语形标记,譬如“真1”“真2”那样,由此表现出跟类型论的处理方案相同的语形意味。如果卡哈尼的理解是前后一致的,那么说谎者悖论也应该照此被理解为“语形悖论”,甚至更进一步,所有其他语义悖论也有可能被改称为“语形悖论”。然而,悖论研究的现实情况正好与之相反。随着对悖论理解的不断深入,卡哈尼的“语形悖论”的分类—命名基础逐渐消失殆尽,因为不仅是罗素悖论的类型论方案早在卡哈尼这本书之前就已经失去主流支持,让位于对于原来不受限制的概括原则的修正,而且说谎者悖论的语言层次论方案也因为对于语言设施的过度整修逐渐成为明日黄花。其实,卡哈尼在评述这两种方案的末尾都说已经发现它们有严重的缺陷,那么它们就更不应该被理解为“大多数哲学家仅仅接受的方案”而作为悖论划分的基础事实。可见,卡哈尼对于悖论解决方案在“语形”和“语义”之间的理解是既不清晰也不可靠的。最后,也更重要的一点是,在悖论解决方案当中寻找“语形的”和“语义的”之间的界限即便是可行的,也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因为悖论本质上是语义的病症,而对于悖论病症的解决方案本质上是语义的。如果非要在悖论解决方案中找出语形方案的踪迹不可,那只不过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悖论解决方案中对于语义上的实质调整必须通过语形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主张,既然任何语义上的调整都可以通过语形上的调整来表现,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语义方案不复存在而只剩下语形方案。
总的来说,卡哈尼的分类方法有点理论魔法的味道,但是他的这个魔法玩得并不成功。面对未来再遐想一下,如果他注意到语用学可能和悖论有一点关系,是不是也会据此再增加一条“语用解决方案”的标准来将“语用悖论”解释为“一个大多数哲学家仅仅接受其语用解决方案的悖论”呢?
四、张建军的“逻辑悖论”
张建军教授的悖论“三要素”定义凝聚了他对于悖论的基本理解,不仅在他自己的悖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国内其他一些研究悖论的学者也有重要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这个定义时,他还是基本遵照“悖论”在逻辑和哲学之内的一般用法的,尽管“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以及“可以建立矛盾等价式”这三个要素的过强刚性跟我们对于“悖论”的一般理解始终有一些偏差[2]24-27。他说:
悖论是指这样一种理论事实或状况,在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之下,可以合乎逻辑地建立两个矛盾命题相互推出的矛盾等价式。[10]51
在提出这个定义之后几年的时间里,最迟不过在1994年,张建军教授就开始把之前惯用的“悖论”改写为“逻辑悖论”[11]13。他在2002年直接通过《逻辑悖论研究引论》的书名标示了这个变化,也在书中跟兰姆赛的“逻辑悖论”做对比的情况下明确地解释了“逻辑悖论”:
莱姆塞意义上的“逻辑悖论”是该词的最狭义用法,这种用法与本书所使用的“逻辑悖论”一词的根本差异在于:莱姆塞命名中的“逻辑”主要指谓悖论所据以推导的背景知识的“逻辑性”,即集合论语言可以转化为纯粹的逻辑语形语言;而本书命名中的“逻辑”主要指谓悖论推导过稈的“逻辑性”,这是该词的广义用法。[12]17
和卡哈尼一样,其说法造成了在“逻辑悖论”与“悖论”之间可能需要分类—命名解释的理论负担。不过,好在这种理论负担很快就被表明是不必要的,因为张建军教授也感觉到有必要在这两者之间做一个大约等价的变通:
为简便起见,在本书以下的论述中,除非有特别说明,“悖论”一词均指谓上述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悖论。[12]27
但是,这样的变通并不是“为了简便起见”就能完全解释的。事实上,张建军教授后来在既保持悖论“三要素”定义的经典形态和引入“逻辑”限定之间做了一个微妙的平衡,更进一步表明了他的“逻辑悖论”当中的“逻辑”,从分类—命名的视角来看,并没有实质的必要:
虽然在学术讨论中受到不少批评,我仍然坚持从1991年开始使用的如下定义:“(逻辑)悖论指谓这样一种理论事实或状况,在某些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之下,可以合乎逻辑地建立两个矛盾语句相互推出的矛盾等价式。”[13]47
◆作为分类原则的“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
张建军教授基于悖论“三要素”定义,为“逻辑悖论”的类型划分明确地提出了分类原则:
若以本书的“逻辑悖论”定义为据,则必以“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之不同,作为划分逻辑悖论不同类型的标准。[12]13
用“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来代替塞恩斯伯里的“看起来可接受的前提”作为悖论定义的一个要素并不可取[2]24-25,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把它径直看成“看起来可接受的前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即便在对“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做了这样的重新诠释之后,要把它用作悖论的分类原则的基础也是不恰当的,甚至是无效的。因为对于一个悖论的“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可以从许多方面来观察,而每一个方面的观察有可能涉及到许多因素,因此当我们比较两个悖论在“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上的不同时,我们应该在哪一方面或者某一方面的哪一个因素上比较,就成了超出这个原则的判断能力的尴尬问题。要继续勉强利用“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来划分悖论,也就很有可能造成一些奇奇怪怪的分类—命名问题。
当然,张建军教授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又紧接着用“本质地包含”或者“本质地涉及”这样的“本质”追加来挽救“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
由于这两个悖论在其背景知识所指层面本质地使用了“可定义”、“描述”这样的语义词项,因而它们均被归入语义悖论。[12]18
但是,知道者悖论与说谎者悖论之间有一个重要差别,即“知道”是所谓表达“态度”的谓词,本质地涉及认知主体与语句意义之间的关系。[12]20
他既没有回去修订原来的分类原则,也没有进一步解释这里所谓“本质地”的详细含义,反而以包含某种关系、涉及某种因素等多种形态来利用“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结果只会让我们在分类—命名的审视当中更清晰地看到其中更多的混乱。如果张建军教授期待的是利用这种挽救方法把我们带回到悖论出错的根源这样的分类原则当中,那么他为什么不明确表示出来呢?恐怕只是因为“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作为三要素定义的一大要素在他看来坚如磐石,是不可轻易抛弃的。但是,当他将“逻辑悖论”划分成三个大类时,在“狭义逻辑悖论”的命名上,他不仅抛弃了“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甚至也摆脱了分类—命名机制的桎梏。他说:
总之,狭义逻辑悖论、哲学悖论、具体理论悖论,是统摄于逻辑悖论之语用学界说的三种既互相区别又密切相关的基本类型。[12]27
◆“狭义逻辑悖论”
张建军教授先后使用过“语形悖论”“语义悖论”和“语用悖论”这三个名称。可能受符号学(或者语言学)可以三分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一事实的反向启示,他为它们的聚合特别设立了一个名称:
为讨论方便,我们将语形、语义、语用悖论统称“狭义逻辑悖论”。[12]81
“讨论方便”并不是分类—命名当中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正是由于有了这个理由,“狭义逻辑悖论”这个名称既可以避开被追问“狭义逻辑”的确切含义的麻烦,又可以避开被质疑更应该按照“莱姆塞意义上的‘逻辑悖论’是该词的最狭义用法”[12]17的主张指向兰姆赛的A类悖论的尴尬。不过,张建军教授在接受了“讨论方便”的这两个好处之余,不太甘心为它所限,还是希望在和哲学悖论、具体科学悖论对比的框架当中,为“狭义逻辑悖论”找一点超出“讨论方便”的解释:
哲学悖论的构造与狭义逻辑悖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所由以导出的背景知识及其推导过程,均未能得到如后者那样的逻辑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严格塑述,其逻辑的无误性只是在认知共同体未找到其推导过程中的逻辑错误的意义上成立。[12]26
具体理论悖论构造的严格性要求高于哲学悖论而低于狭义逻辑悖论。[12]26
但是,张建军教授似乎没有注意到可以区分这三种悖论的“悖论构造的严格性”和可以统一它们的“严密无误的逻辑推导”之间的冲突。还有一点可能超出他的想象的是,有了“狭义逻辑悖论”这个用法,以及符号学三分法的不断提示,其他人很容易落入“狭义逻辑悖论”覆盖了所有悖论这一思想陷阱。如:
许多书籍一般将悖论分为语形悖论和语义悖论。但笔者认为,将悖论分为语形悖论、语义悖论和语用悖论三部分比较合理。[14]
悖论有语形悖论、语义悖论、语用悖论等几种。[15]
张建军教授的“逻辑悖论”被一清二楚地一分为三,他自然不会犯这种错误,但是其他人犯的这种错误的背后其实是跟他对于“语形悖论”和“语用悖论”的分类—命名错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正是这样的错误为“语形悖论”“语义悖论”和“语用悖论”的三分法类比提供了联想的基础。
◆“语形悖论”
张建军教授主要是受卡哈尼的影响,开始采用“语形悖论”这一名称来指向兰姆赛的A类悖论(6)根据笔者和张建军教授的个人通信交流。。在这之前,他一直遵照一般的习惯把这类悖论称为“集合论悖论”。对于卡哈尼的影响,他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试图通过从“集合论悖论”到“集合论-语形悖论”最后到“语形悖论”的过渡,跟自己的过去保持妥协共存的联系:
由于集合论语言可以转化为高阶逻辑语言,故莱姆塞意义上的逻辑悖论时常被明确指认为高阶逻辑悖论,更多地则称为“集合论-语形悖论”或“语形悖论”。[16]80
但是,这种过渡并不平滑,因为在“集合论悖论”和“语形悖论”之间的差异不只是字面上的差异,而是更应该是从分类—命名机制的角度观察的分类原则差异。像张建军教授那样用一个连字符把它们串联起来形成“集合论-语形悖论”这么一个中间体试图消弭这种差异,不但不会成功,反而只会带来新的混乱。问题的根源在于,张建军教授对卡哈尼的“语形悖论”的接受缺乏足够的辨析,尤其是从分类—命名的视角。他因为有自己那一个哪怕不太恰当的分类原则,也就没有遵循卡哈尼的那个新颖奇特的分类原则,但是为了接受卡哈尼的“语形悖论”,他不得不丢弃自己原来的分类原则,而在偶尔需要解释这个名称的时候换用另外一个更不合格的原则:
“语形悖论”之“语形”不能作纯粹的无释义的“语形”理解,而需作“逻辑语形语言”的理解,其前提之释义(比本书所谓背景知识之“所指层面”)只需涉及“个体”、“性质”、“关系”等逻辑本体范畴,而不含有语义学范畴。——修订本注[17]15
在这种新的理解之下,“语形悖论”可以看成是“逻辑语形悖论”或者“集合论语形悖论”的紧缩。本来“逻辑”“集合论”是这些悖论的特征词项,而“语形”反而是可以普遍使用的非特征词项,譬如既可以出现“物理学语形”“认识论语形”,也可以出现在“博弈论语形”当中,但是这样的紧缩居然把“逻辑”“集合论”丢掉,保留“语形”,实在有点不可思议。再回过头来观察“集合论-语形悖论”用来表示并列的连字符“-”,它除了为这种不合理的紧缩做好随时待命的准备之外,并不会为“语形悖论”的分类—命名合法性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辩护。
◆“语用悖论”
英国哲学家丹尼尔·奥康纳(D.J.O’Connor)第一次把对于意外考试悖论的讨论正式带到了学术刊物当中的文章就叫《语用悖论》[18]358-35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语用悖论”并没有指向一个完整的悖论,而是仅仅指向一个悖论的部分,指的是那些在形式上并不自我矛盾,但是通过一个语用行为就表现出自我反驳特征的陈述,由此表现出来的对于“悖论”的理解跟我们现在对于“悖论”的一般理解颇不相同。进一步看,他不是在悖论如何分类的语境下,而是以“语用”的通常使用方式和“悖论”的不通常使用方式相结合,为满足一定条件的陈述树立了“语用悖论”这个名称而已,也更不是用来和“语义悖论”还有“语形悖论”一起构造一个统一的分类—命名景观的。也就难怪奥康纳的“语用悖论”并没有流行开来,很快就被更恰当的“认知悖论”给取代了。
起初,张建军教授也不主张使用“语用悖论”这个名称:
但有鉴于命题态度概念本质地引入了“认知主体”因素,有人早在MIND讨论知道疑难时就建议称之为“语用悖论”。或许由于在语用学与语义学相互关系上存在一些针锋相对的争议,这个称谓没有流传开来。“认知悖论” 的称谓是伯奇提出来,现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笔者亦曾撰文认为:“把关于命题态度的悖论统称为认知悖论是恰当的,它不仅有利于与(本质上不涉及认知主体的)语义概念相区别,而且可以体现其与认知逻辑的密切关联。”[19]30
但是,随着悖论的情境语义学解决方案的一度兴起,张建军教授在“逻辑悖论”的理解当中发现了语用学概念:
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悖论”既不是纯语形学概念,也不只是语义学概念,而是一个包容语形、语义因素的语用学概念。[16]77
接着,他又重新发现了“语用悖论”,不过这次是以不同于50多年前奥康纳的方式:
和语义悖论相应,我们可把认知悖论和合理选择或合理行为悖论,以及所有在背景知识所指层面本质地涉及语用因素的悖论统称为“语用悖论”(请注意,不能把“语用悖论”与悖论的语用学概念混为一谈,正如不能把“语用预设”与预设的语用学概念混为一谈)。[16]81
尽管张建军教授在括号中加了注意区别“语用悖论”和悖论的语用学概念的提示,但是它们在共同反映了他对于语用学概念的过度泛化的理解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这种泛化理解的背后是对于语用学的一种误读,也就是误认为凡是跟语言使用相关的问题就是语用学的问题。因为任何符号,不管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只是因为有人(或者一般的使用者)使用才被称之为符号的。对于语用学概念的泛化理解,很自然地导致我们走向一个极端,就是凡是语言的,就是语用的,那么整个语言学甚至符号学就都成了语用学,反过来就取消了语用学作为符号学和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的实际价值。放到理解悖论的情景当中来看,这种语用学的泛化理解除了带来一些用字面上的“语用学”写出来的口号而外,并不会带来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洞见。张建军教授说:
悖论的语用学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从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相互关系角度,把握“集合”这种使一般属性个体化、离散化的抽象客体的本性,从而对集合论的不同公理化系统及其等价性以及它们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给予新的理解。[16]82
逻辑悖论语用学性质的确认,亦可帮助我们在国内外学界歧见颇多的悖论分型问题上获得新的认识。[12]13
其实,这反而有时候会带来一些严重的认知混乱,譬如因为每个悖论当中都有无处不在的语用因素,每一个悖论都该被称为“语用悖论”。张建军教授还说:
语用学概念的外延划分,必诉诸其中所包含的语用学因素,若以本书的“逻辑悖论”定义为据,则必以“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之不同,作为划分逻辑悖论不同类型的标准。[12]13
张建军教授将“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的分类原则改写为“在背景知识所指层面本质地涉及语用因素”,只是又一次揭示了“公认正确的背景知识”的多方面多角度破坏了它可以用作一个恰当的分类原则的可能性,并不能把“语用悖论”从悖论的语用学概念当中单独挽救出来。他说:
符合三要素标准的任何严格意义的逻辑悖论的出现都是一种语用现象,而语用悖论则只是逻辑悖论的一个子类。[12]21
我们始终没有看到,也无法猜测包括意外考试悖论在内的那些认知悖论和合理选择(行为)悖论是如何本质地涉及到语用因素,而其他悖论则只是非本质地涉及到语用因素的。
为了澄清“语用悖论”当中的迷雾,我们既有必要回顾在分类—命名过程当中一个恰当的分类原则的重要性,也有必要去追溯张建军教授对于语用学概念的过度泛化的起因是什么。张建军教授认为:
其实,西方学界逻辑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早已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只是与预设研究不同,这种转向是在没有“悖论”之明确的语用学概念的情况下,由解决语义悖论的语用学方案肇始,其显著标志是一系列语境敏感方案的提出及其相对于语境迟钝方案之优势地位的确立。[16]79
然而,所谓“逻辑悖论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其实是一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因为这种转向指向的不过是20世纪下半叶乔恩·巴怀思(Jon Barwise)和约翰·爱切门迪(John Etchemendy)为解决说谎者悖论开辟的情境语义学这条一直不太成功的路径而已。
五、结语
《荀子·正名》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到了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对于命名的理解就不只是“约定俗成”这么简单了。单独来看,一个命名行为可以是任意的,也就是说,对于任意一个对象可以分配任意一个符号来作为它的名称。但是,绝大多数时候,一个命名行为并不是独立发生的,而是在一个已有的语言系统中发生的,因此它就需要遵循某些用以确保语言系统有效运行的约束条件,而不能随意。反过来说,一个命名行为就可能因为违反那些本应该遵守的约束条件而被认为是不恰当的。在分类—命名这种认知活动当中,首先确保分类原则是明确有效的,其次确保命名机制得以恰当执行,则是我们需要遵守的基本规则。
回到悖论的分类—命名问题,我们不要为了着急落实“悖论的一般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的研究纲领,在没有充分理解分类—命名机制的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就将未加批判的一些学术遗产杂糅起来,推出一个一揽子处理方案,而要首先确保我们找到一个合理的分类原则,然后将某些悖论聚合在按这个原则区分出来的一个类当中,把对于它们的理解和消解的成熟方案综合起来考察是否能够从中得出一般性的教训。否则,我们就该认认真真去逐一尝试理解和消解那些还没有达到理解和消解的成熟状态的悖论。
如果我们之前还不懂得悖论的分类—命名当中可能会潜藏着一些什么理论陷阱或者困难的话,在充分理解与这三种“逻辑悖论”相关的分类—命名问题的几个故事以后,或许我们就会像兰姆赛一样谨慎,甚至像库科夫斯基一样忧虑了,因为我们可能发现我们曾经或者现在对于一个悖论的实质理解可能随着我们对于这个悖论的理解深度和角度的变化而显得不再那么明确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