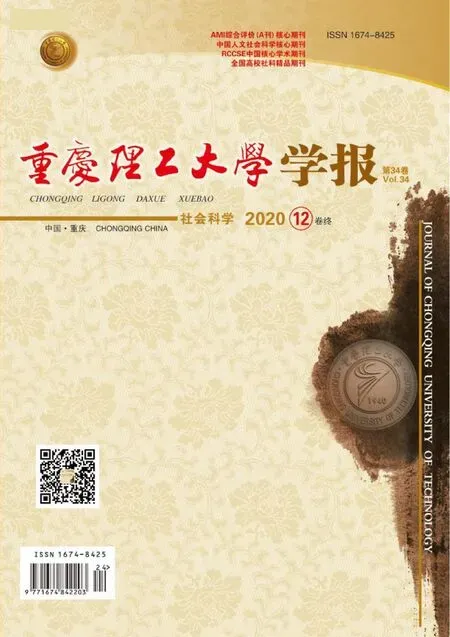“名转动词+宾语”结构语义合成研究
董 涛
(济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名转动词+宾语”结构是名词转用的动词与其后的名词合成的一种论元结构,其中名转动词是临时用法。国内外对名转动词的研究有:Clark[1]、徐盛桓[2]、宋作艳[3]对其进行的语义和语用分析;王冬梅[4]、高航[5]对该结构生成机制的认知语言学探讨;Dirven[6]、刘正光[7]、魏在江[8]在转喻框架内的认知分析。除此之外,胡波分析了名转动词的句法特征及其生成机制[9],Hilpert用构式语法探讨了名转动词义的生成[10]。以上研究深化了学界对名转动词的理解和认识。
尽管名转动词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将名转动词与其后的宾语作为整体的研究尚不多见,“名转动词+宾语”结构的合成问题更是鲜有涉及。例如:
(1)hammer the nail(1)本文所用例子大都出自参考文献[1],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例(1)中,按照Langacker对名词合成关系的相关论述[11]236,[12]162-167,hammer和the nail的合成结构hammer the nail是hammer进一步阐释the nail的实体结构(entity),即名词表达式。但是,hammer和the nail的合成结构却是表时间关系的事件结构(event),即动词表达式。
“名转动词+宾语”论元结构蕴含着丰富的人类经验,体现了人类与客观世界的认知互动关系,揭示了人类对意义的认知加工方式。于是,笔者以Goldberg提出的场景编码假设理论及Langacker提出的射体界标理论为框架,探寻“名转动词+宾语”论元结构的概念基础、允准和限制机制,希冀对该结构有更深入的认识。
一、构式图式及其合成性
构式是从众多示例抽象出来的图式,构式图式是图式化的构式。具体地讲,语法是由约定俗成的、业已形成的构式组成的网络。该网络依靠一套节点和一套弧线把节点两两连接起来。构式占据节点,节点间的弧线代表范畴化。范畴化依靠阐释(elaboration)和引申(extension)实现。这样看来,构式图式是抽象程度更高的构式。
构式图式描述了由较简单的表达式合成较复杂的表达式的方式。这就是说,构式图式具有合成性(compositionality)。在认知语法看来,构式图式不仅体现了多个合成成分之间的合成关系,而且体现了其合成路径。一方面,子构式起到垫脚石(stepping-stone)的作用被后置,合成构式被前置,示例构式图式。另一方面,子构式并非随意堆砌,而是具有一定的合成路径。例如:
(2)jar lid
例(2)中,一方面,jar lid既不是阐释的jar的概念内容,也不是lid的概念内容,而是jar和lid合成结构的概念内容;jar和lid对合成结构的语义贡献不尽相同,合成结构jar lid承继了lid的侧显,jar对lid进一步引申。另一方面,jar lid不是jar和lid垒积木似的随意堆砌,而是严格地体现了名词短语构式图式的建构关系。jar lid语义合成路径体现在合成成分jar和lid、与合成结构jar lid及名词短语构式的对应关系和范畴化关系上,具体如图1所示。
图1描述了射体(tr)和界标(lm)与jar(J)和lid(L)的对应关系(虚线)和范畴化关系(实线箭头和虚线箭头)。对应关系和范畴化关系是语义合成操作机制的两个方面,前者表示两个或者多个合成成分的概念重合程度,是两个概念合成的认知基础;后者表示概念化者(conceptualizer)根据业已存在的结构对体验的阐释,是实现构式图式的有效途径。对应关系分为横向对应关系和纵向对应关系。横向对应是合成成分侧显与构式中界标和射体的对应;纵向对应是合成结构与构式的对应。具体地,图1中,jar(左侧黑色圆圈中的J)和lid(右侧黑色圆圈中的L)侧显分别与名词短语构式图式的界标(黑色阴影圆圈)和射体(黑色阴影圆圈)、jar lid合成结构中jar(上面黑色圆圈中的J)与 lid(上面黑色圆圈中的L)概念重合,产生横向对应;合成结构jar lid侧显与名词构式概念重合,构成纵向对应。jar和lid与jar lid构式图式的横向和纵向对应关系使jar和lid的概念合成具备了认知基础。范畴化方面,jar(左侧黑色圆圈中的J)和lid(右侧黑色圆圈中的L)与界标(黑色阴影圆圈)和射体(黑色阴影圆圈)是阐释关系(实线箭头),合成结构jar lid(上面黑色长方形方框)与名词短语构式(下面黑色长方形方框)是阐释关系(实线箭头),造成范畴化。范畴化的结果是jar lid成为名词短语构式的一个示例,也就是说jar lid概念合成完成,合成就是范畴化[13]164。
但是,Langacker的相关论述[11-16]仅涉及到了名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的合成,鲜有对动词表达式的合成关系及其路径的论述。笔者认为,Goldberg提出的场景编码假设理论(Scene-encoding hypothesis)[17]可以弥补Langacker这方面的不足,Langacker的射体界标理论可以进一步阐释情景编码假设理论。场景编码假设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构式把与人类经验有关的事件类型编码为其典型意义。Goldberg进一步总结出几类与人类经验有关的事件类型对应的构式:及物构式、双宾语构式、致使移动构式、致使结果构式、领属构式[18]。这些构式对应着与人类经验有关的事件类型,其表征为基本句子类型。这样看来,动词表达式的识解和合成机制应该依赖构式的典型意义,才能阐释与动词表达式对应的事件类型。上述构式中,及物构式是事件原型,是最基本的,能产性强的构式,其构式图式如图2所示。图2表示的是射体(tr)对界标(lm)实施一个行为的及物构式图式。该及物构式涉及两个成分和一个关系,即射体和界标及其他们之间的引申关系。及物构式图式中,射体是主要凸显的事件参与者,起着激活及物构式的作用;界标是次要凸显的事件参与者,其作用是为射体激活及物构式提供详细的描述。
二、“名转动词+宾语”结构家族及其多义性
“名转动词+宾语”结构是以及物构式为语法原型的多义性构式,其语义可以阐释及物构式、双宾语构式、致使结果构式、致使移动构式和领属构式等构式义。及物构式原型包括两个事件参与者:施事(射体)和受事(界标),施事对受事做出某种行为,受事完全受到该行为的影响。例如:
(3)Taylorhammers the nail.
(4)Smithbutchered me a cow.
(5)Edwardpowdered the aspirin.
(6)Maryspooned the soup into the bowl.
(7)Bobnetted a fish.
例(3)表达了及物构式义,表示施事Taylor对受事the nail实施了一个行为,影响到了受事,其中hammer是工具名词临时转用做动词;例(4)是双宾语构式义,表示Smith给予了直接受事me一个间接受事a cow,其中butcher临时用作动词;例(5)是致使结果构式义,表示Edward对aspirin实施了一个行为,使aspirin变成了powder,其中powder临时转用做动词;例(6)是致使移动构式义,表示Mary用勺子把the soup盛入碗中,其中spoon是临时动词;例(7)中,netted a fish是领属构式义,表示Bob用网捕并且拥有了一条鱼,netted是临时动词。以上分析表明,“名转动词+宾语”结构是一个能产性强、涵盖意义广的构式。另外,受到及物构式、双宾语构式、致使结果构式、致使移动构式和领属构式阐释的“名转动词+宾语”结构也再次佐证了及物构式原型的地位。
构式都具有及物性,只不过及物性程度不同[19]。笔者认为,双宾语构式、致使结果构式、致使移动构式和领属构式能够阐释“名转动词+宾语”结构的原因是及物构式与其它构式的引申关系(extension),这主要体现在双宾语构式等构式对于及物构式描述的详细化程度,即施事对受事实施一个行为,受事受到影响的不同程度。例如:
(8)Taylorhammers the nail into the hole.
例(8)表达了致使移动义,即Taylor把钉子砸进了洞里。显而易见,例(8)是例(3)及物构式Taylor hammers the nail的详细化描述,即语义引申。同理可知,例(4)~例(8)也是对及物构式义的引申。例(4)中,Smith实施屠宰a cow这一行为的影响到me,即给予me,其中me是对Smith屠宰牛及物构式义的详细化描述;例(5)阐释了及物构式的结果,即Edward对the aspirin实施一个行为的影响,使之变成了powder,;例(6)中,Mary对the soup实施了移动的行为,使the soup进入了the bowl里,其中into the bowl是对Mary实施行为的详细化描述;例(7)阐释了及物构式的领属的结果,也就是Bob对a fish实施了一个行为,使a fish变成了Bob的物品。
三、“名转动词+宾语”结构的语义合成
(一)“名转动词+宾语”结构语义合成的概念基础
认知语法和认知构式语法都采纳百科知识语义观,认为词义包括一系列与该实体或者事件有关系的开放知识,即概念。基于这种认识,词义是概念化者对与该词义有关系的概念的突显。例如,儿子突显了父子关系中“子”的概念。句法同样如此。“名转动词+宾语”结构突显的是与临时动词和宾语有关系的事件。那么“名转动词+宾语”构式图式合成的认知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概念重合(conceptual overlap)是“名转动词+宾语”结构合成的概念基础。构式就像拼图,其组成成分在概念上会产生重合,该重合部分激活构式义[14]260。就“名转动词+宾语”结构而言,名转动词和其后对宾语好像两块拼图,分散状态的时候,名转动词和宾语都保持各自名词词性,合成在一起时,名转动词及其宾语的侧显好像两块拼图的拼接处,会与某个事件类型产生概念重合,即概念重合部分激活与事件类型对应的构式。
(二)“名转动词+宾语”结构的允准
如上所述,及物构式、双宾语构式、致使结果构式、致使移动构式和领属构式等构式义有助于识解“名转动词+宾语”结构,也就是说,“名转动词+宾语”结构的语义建构体现了其组成成分承载的合成关系,即不同的构式图式。Goldberg将构式对识解新奇结构所起的作用称为压制(coersion)[17],Langacker称之为强制(superimposition)[13]10。实际上,Goldberg的压制说和langacker的强制说都是强调结果,不是构式图式对于新奇结构合成机制的认知操作过程的阐释。正如第二部分所述,“名转动词+宾语”结构主要阐释了及物构式义、双宾语构式义、致使结果构式义、致使移动构式义和领属构式义。由于及物构式是最基本事件类型,也是典型构式,因此我们以 “名转动词+宾语”及物构式义为例阐释其允准机制,即合成关系。
“名转动词+宾语”及物构式义的合成过程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对应关系和范畴化关系。对应关系中、“名转动词+宾语”合成成分(名转动词和名词)分别与其合成结构、及物构式的界标和射体构成横向对应和纵向对应关系。横向对应中,“名转动词+宾语”结构主语凸显施事,即动作的发出者,宾语凸显受事,即行为的接受者,这与合成结构和及物构式图式的射体和界标侧面概念重合,构成横向对应关系。纵向对应中,“名转动词+宾语”及物构式中作为施事和作为受事与及物构式的射体和界标产生概念重合,构成纵向对应。“名转动词+宾语”及物构式施事和受事的横向和纵向的对应关系是Goldberg所说的压制和Langacker所说的强制的概念基础。范畴化关系中,“名转动词+宾语”及物构式范畴化关系体现在两个层面:“名转动词+宾语”及物构式的合成成分对于及物构式的界标和射体的阐释以及合成结构“名转动词+宾语”对及物构式图式的阐释。值得注意的是,与典型的及物构式不同,“名转动词+宾语”及物构式的动词由名词担任,所以“名转动词+宾语”结构范畴化过程具有强制的特点。在构式语法看来,一个表达式的概念义不是由动词决定,而是由该表达式的构式义决定。如第一部分所述,及物构式图式中,表示事件过程的动词是侧面决定成分,继承及物构式义。那么,“名转动词+宾语”合成结构被强制范畴化为及物构式义,动词位置上的名词继承及物构式义,使该名词具有了标志时间性,动态性的临时动词义。
下面,我们以(3)为例对“名转动词+宾语”及物构式义合成机制进行阐释,如图3所示。
图3中,合成成分Taylor(左侧黑色圆圈T)和nail(右侧黑色圆圈N)侧显与合成结构中Taylor(上面黑色圆圈T)和nail(上面黑色圆圈N)、及物构式中射体(黑色阴影圆圈tr)和界标(黑色阴影圆圈lm)分别概念重合,构成横向对应关系(虚线)。合成结构中Taylor(上面黑色圆圈T)和nail(上面黑色圆圈N)与及物构式图式中射体(黑色阴影圆圈tr)和界标(黑色阴影圆圈lm)分别概念重合,构成横向对应关系。基于此,合成成分Taylor(左侧黑色圆圈T)和nail(右侧黑色圆圈N)的侧显阐释及物构式中射体(黑色阴影圆圈tr)和界标(黑色阴影圆圈lm),合成结构(上方黑色长方形)阐释及物构式(下方黑色长方形)。综上所述,Taylor hammers the nail被范畴化为及物构式的一个示例。范畴化过程中,由于Taylor hammers the nail被识解为及物构式的示例,所以处在动词位置上的名词hammer继承了及物构式义,被临时强制转化成动词。
(三)“名转动词+宾语”结构的限制
正如例(1)所述,hammer(the)nail本应该被识解为实体(名词表达式),而不是事件(动词表达式)。那么,“名转动词+宾语”结构为什么不能被识解为实体呢?我们认为,及物构式不但具有允准特征,还有限制的特性,这与hammer(the)nail事件性识解有关。
1.界标和射体的不同位置对“名转动词+宾语”结构实体性识解的限制
在认知语法看来,语义结构包括概念内容及其加在其上的识解方式,界标和射体组合是识解方式之一,其中射体是侧显关系中主要凸显事件参与者,界标是次要凸显事件参与者。“名转动词+宾语”构式的实体性识解或者事件性识解同样适用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名词短语构式的界标和射体位置与及物构式界标和射体位置的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凸显成分的不同与“名转动词+宾语”结构实体识解限制有一定关系。
具体地,图1中lid是射体,jar是界标,也就是说lid是主要事件参与者,jar是次要事件参与者。与之相反,图3中Taylor是射体,也是主要事件参与者,nail是界标,也是次要事件参与者。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图1和图3射体和界标的位置相反,这说明语言表达式的实体性识解或者实体性识解是由界标和射体的不同位置决定的,也就是说语言表达式中,射体在前,界标在后,该语言表达式易被识解为事件;界标在前,射体在后,语言表达式易被识解为实体。显而易见,“名转动词+宾语”结构的事件性识解取决于概念化者对于界标和射体位置的安排以及由此带来了凸显了不同的事件参与者。我们仍以(3)为例。为了方便讨论,暂不讨论情景植入成分(grounding element)单数第三人称s和定冠词the。如图3所示,Taylor是射体,nail是界标,这说明在这个及物构式义识解中,Taylor是事件凸显的主要参与者,nail是次要参与者。这与及物构式中施动者是动作的发出方,为事件的主要参与者,受动者是动作的接受方,为事件的次要参与者的表述吻合。随着例(3)被识解为及物构式义,hammer的临时动词义应运而生。
2.阐释距离对“名转动词+宾语”结构实体性识解的限制
Taylor提出图式竞争理论(schema competition)[20]301-302,其主要意思是范畴化语言表达式时,若存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候选图式,这时图式竞争出现;哪个图式胜出取决于图式与示例间的阐释距离(elaborative distance):阐释距离越小,该图式范畴化该示例可能性越大,阐释距离越大,该图式范畴化该示例可能性越小。Langacker更加具体地表达了同样的看法[12]229-230,并进一步指出规约化程度、与目标表达式的重合度、语境影响是影响阐释距离的3个因素。下面我们从规约化程度、与目标表达式的重合度、语境影响3个方面说明阐释距离对“名转动词+宾语”构式的实体性识解的限制。
首先,规约化程度体现的是图式被激活的难易程度,一般来说规约化程度越大,图式越容易被激活,反之亦然。就“名转动词+宾语”及物构式而言,例(3)被识解为及物构式义或者实体性由实体性构式图式和事件性构式图式之间哪个构式更容易被激活造成的。司显柱基于BNC语料库收集了740个名转动词示例,发现有722个示例阐释及物构式[21]。这说明及物构式规约化程度高,容易被激活,从侧面验证了及物构式是原型构式的假设。基于此,hammer(the)nail的事件性阐释距离比实体性阐释距离大,事件性识解概率大,限制了其实体性识解。
其次,与目标表达式的重合程度主要指语言表达式与某一构式的重合度程度。一般来讲,目标表达式与某构式形式上重合程度越高,该表达式越容易被激活。例(3)中,Taylor和nail与及物构式施动者和受动者位置重合度高,所以该结构容易被及物构式激活,示例及物构式。值得一提的是,尽管hammer与及物构式动词重合度小,但是,由于例(3)示例及物构式义,hammer的侧面随之继承了及物构式义,变成了临时动词,因此hammer与及物构式动词的重合度变大。这样看来,例(3)的事件性识解比实体性识解概率大,限制了其实体性识解。
最后,语境影响是指语言表达式的阐释离不开语境的影响。“名转动词+宾语”结构的阐释亦是如此。例如:
(9)They will ensure that there will be crime.It is possible for us toimage a societyof saints in which no one committed what we see as crimes.
例(9)中,image的位置(不定式结构to后面)构成了识解image a society的语境。根据语法规则,我们不难把image a society识解为事件。
四、结语
本文从认知语义合成的角度研究了“名转动词+宾语”多义结构及其合成路径、允准和限制机制。研究发现:“名转动词+宾语”结构以概念重合为认知基础,在场景编码理论假设的框架内,射体和界标与及物构式、双宾语构式、致使移动构式、致使结果构式、领属构式等构式意义的对应关系和范畴化关系两个层面进行认知操作。与此同时,“名转动词+宾语”结构的实体性识解亦受到射体和界标的所处的位置和目标表达式与候选构式间阐释距离大小的双重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