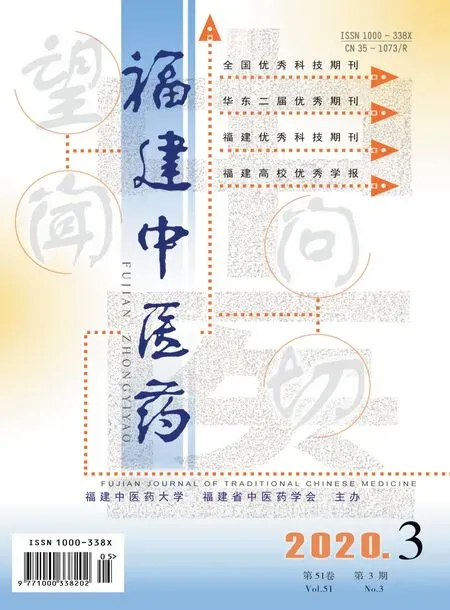福建名医刘亚农学术见解初探
李君君,肖诏玮
(福州市中医院,福建 福州 350001)
刘亚农(1884—?),字幼雪,福建侯官人(今福州市),幼习儒,为末代帝师陈宝琛及门弟子,陈氏赞其“年少治经,有声里党”[1]。后因患咯血症卧床多年,广求中西医名医治疗,未见起色,遂于病中刻苦学习岐黄之术,遍尝百草,衷中参西,自起沉疴,遂笃志学医。拜福州名医邱肖川为师,医术更进。继之宦游燕、冀、皖、赣、宁、湘、沪、津等地,边从政边行医,济世活人,中年弃政专事医业。民国二十二年(1923年)游北平,悬壶于西单武功卫口外小秤钩胡同8号,并执教于华北国医学院,乐育英才。晚年南归返里,悬壶于福州市鼓西路[2]。
刘亚农乃近代卓有成就的内科名医、教育家,堪称“闽医学泰斗”,且声达省外,名动北平,惜闽省对其生平学术研究不多。吾师肖诏玮主任早于1980年从事福州中医流派研究时关注过刘氏,拜访过刘氏在榕传人刘任航先生,限于种种原因,整理其材料甚简,深以为憾。《刘亚农生平与著作考》[3]一文对其生平、著作、贡献等方面进行详实的考证和中肯的评价,笔者阅读后深有同感,并于近年在编撰《榕医翰墨》时,目睹数纸刘亚农方笺,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嗣后有幸拜读其代表性著作《二十世纪伤寒论》《古今药物别名考》等,卒读之下,获益良多,现对刘氏学术见解初探如下。
1 经方新病,不尽相能
1.1 取法仲师,切忌顺旧 刘亚农枕籍岐黄,服膺张仲景。他在《二十世纪伤寒论》序中云:“汉张机著《伤寒杂病论》为中医有方案之鼻祖”,在导言中又首肯《伤寒论》固为医宗之基础,乃仲景积数十年之精力学识经验,发为至理明言。刘氏积平生之学,深知《伤寒论》为方书之祖,使医学始有系统可言,书以惠人,厥功甚伟。其书虽名为伤寒,然其记载之诊候、治法,以至一切药方,殆用之于万病,无不适当,可作为“中医内科全书”。但刘氏认为做为医者,不可崇古心坚,视为圣经贤传,以致食古不化,铸为大错。张仲景在《伤寒论》自序中言,其撰写是书系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针砭时医“各承家技,始终顺旧”之谬误。刘氏认为倘不观察气运之变,陵谷之迁,气禀之厚薄,犹泥守仲景一百十三方之成法,使仲景复生,亦必诋今医为顺旧省疾,所以墨守古方者“是直仲景之罪人也”。仲景之法,可循其规、蹈其矩,刘氏强调惟其所列之汤液,与今人体质每不合宜。故今日之汤液,有变通取舍之必要。
1.2 五方之人,惊人异判 刘氏尝宦游北京、河北、安徽、江西、湖南、南京、武汉等地,观察其风土气候,还特地去过南阳,测验仲景所处之乡,气候与水土不同。他生长于闽中,遍历闽省南北,留意考察各地天时、地气与人之体质,得出结论“知易地有惊人之判异焉”。五方之民,病之不同,治法因之而各异,《黄帝内经》郑重言之,他再特别阐明。即使一州之内,有山居者,为居积阴之所。崇山峻岭,山有泉,其气寒,能寒中,其有病者,多中风中寒之疾。通都大市,空气氤氲,郁浊化热,风邪从口鼻而入,辄发温病,山居野处之人,与通都大市之人,气禀不同。膏粱文绣之人,与手足胼胝之人,亦有区别。膏粱文绣之人,身逸心劳,饱暖出其淫欲,精神耗损,脏腑失调,平日心散气浮,相火上炽,一旦风邪外袭,内热交侵,寒病易于热化。所以刘氏主张“其气禀羸弱者,用药取其轻清平淡。素体阴虚者,用药勿过辛烈温燥,欲去其病,先防其偏”。
1.3 二十世纪,与时俱进 刘氏在其代表作《二十世纪伤寒论》中引用《素问·异法方宜论》:“黄帝问曰:医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对曰:地势使然也。”刘氏详尽引述了岐黄关于东西北南中央之人,证治有异,他遵从《黄帝内经》五方气候、饮食居处和生活习惯不同导致所患之病有异,此认为秦汉即有认识,垂有方法,立有津梁,而仲景去今二千年,书中所列证候汤方,“虽辄举病立方,然病之变化无常,须就其人、其地、其时,而参酌损益之,读者万勿视为呆板图案”,他主张“惟其所列之汤液,与今人体质每不合直,是图案虽同,而材料不能不变更”。易言之,用仲景之辨证,而遣方用药要有变通取舍之必要。所以刘氏著作冠以“二十世纪”四字,即体现他的鲜明观点,当因人、因时、因地治疗。
1.4 峻猛轻清,遣药变通 刘氏以桂枝汤为例,阐明己见。“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他认为西北地区及虚寒之人照方服之,轻者代以荆防饮(荆芥、防风、枳壳、竹茹、桔梗、苦杏、黄芩、淡竹叶等味)出入为治。近温带或热带之人,如闽粤、香港、汕头、台湾等地及吕宋南泽群岛之人,桂枝、麻黄、羌活、细辛等药,不宜轻易使用,荆防亦慎与之。因其地气热,禀质薄,一投辛烈,轻则鼻衄、咳血,重则烦热、神昏等症立见。所以太阳伤风桂枝汤证,宜改为三叶饮(桑叶、枇杷叶、薄荷、杏仁、连翘、竹茹、枳壳、甘草),可加淡竹叶、菊花,则为五叶饮。如夹湿加佩兰、半夏、陈皮,胸痞加郁金、桔梗、石菖蒲,伤食加麦芽、厚朴,夹燥加川贝母、芦根、牛蒡子、天花粉等,可见刘氏代以时方,以轻、清、舒达之,以防导泄真气。但是刘氏并非一味主张用轻描淡写之法,对于东南之人,若体质雄厚,或居水滨卑湿之地者,临证也用防风冲和汤(防风、羌活、白术、川芎、白芷、生地黄、黄芩、细辛、甘草)或九味羌活汤(南人及虚弱者,改细辛为川椒)。又如,“太阳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西北人、崇山峻岭人可用桂枝加葛根汤主之;东南人,可用葛根汤加桑枝、忍冬藤、钩藤主之。“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可予桂枝汤,若不上冲者,不可予之”。刘氏认为气上冲,当辨其虚实,虚者调其气血,桂枝汤可与之,实者仍下之,东南人或以温胆汤加柴胡,或以郁金汤加减(郁金、川贝母、杏仁、枇杷叶、淡竹叶、竹茹、茯苓等)。
1.5 闽中名医,异彩纷呈 刘氏乃地道闽中人(侯官县,属福州府),又游历多省,深知中国地域广阔,南北异禀,腊月寒冬,北国冰封雪飘,风刀霜剑,而福州闽江两岸,万木郁郁葱葱,花果飘香,证治必然有异,唐代诗人韩偓宦游福州,抒写福州有“四序有花常带雨,一冬无雪却闻雷”诗句。无独有偶,近代福州伤寒名家刘少山(1902—1988年),字必鼎,世居福州市洪山西河村,出生中医世家,行医五十余载,学验俱丰,1976年经福建省卫生厅确定为重点继承的老中医,著有《刘少山医疗经验选》一书。少山认为榕垣地处东南,闽江泱泱水流,外感风寒易夹湿邪,三拗汤有疏风散寒、宣肺止咳之功,却无化湿之效,故仿其意,以藿香易麻黄,防风易甘草,去麻黄发汗太过之弊,须增强化湿透邪之力,故以藿香、防风、杏仁三味组成,命曰“假三拗汤”,有芳香透邪、祛风散寒、化湿定痛、宣肺止咳的作用[4]。少山认为三拗汤仅能宣肺,而假三拗汤功效较三拗汤更全面,经刘氏三世应用颇为得心。若表邪重加苏叶、佩兰、白豆蔻;如湿困于脾,运化失调,加苍术、川厚朴等;若风邪与湿相抟,郁阻经络,致四肢痹,加海桐皮、金毛狗脊等;若咳嗽痰多,加姜半夏、蜜紫菀、远志等。刘少山运用此方得心应手,乃因福州气候,且其家住闽江江畔,地卑多湿故也。
再如王德藩(1878—1960年),福州市人,三世行医,善用经方,特别擅长治疗少阴病,每起沉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出任福州第一届中医公会常务十二人理事之一。1929年,创办福州中医学社,出任社长,该社办十届,毕业生249人,摇木铎而作金声,遣经方而称巨擘[5]。新中国成立后,榕垣中医主任多为王氏门弟子,王曾任福建省人民医院顾问,福州市人民医院(中医院)名誉院长,福州市政协常委,福州市人民代表。著有《少阴病辨治经验》一书,他居城内,师仲景法,但不拘泥于伤寒方,如少阴兼太阳病,若证由房劳后感寒而引起者,其宗《伤寒论》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汤之法,但又不拘泥于其法,自拟荆防桂枝汤加附子,不用麻黄、细辛等辛散之品,恐有迫汗伤津、重虚肾气之弊,改用荆防桂枝汤以解太阳之邪,用附子温肾壮阳,以补少阴之虚[4]。以上两位名家,王德藩较刘亚农年龄稍长,刘少山年庚稍后,三人未审是否谋面,但学术见解异曲同工。
2 药分猛次,量体裁衣
外感病有伤寒、伤风的区别,何哉?刘氏认为“六经有经有络,伤于络者轻,为伤风,伤于经者重,为伤寒”。刘氏举例说明,太阳经脉,上连风府,病在经者,恶寒或发热,头项必强,腰背必痛,此为病在太阳经的表现;若仅头痛恶寒脉浮而项不强者,此病在太阳络,以伤风治之,经药非所宜。阳明、少阳也有经和络之分,因此药也应分经与络之别。伤寒之方,经药居多,举隅如麻黄、细辛、柴胡、附子等;生姜、桂枝则为络药。陶弘景之后,盛用荆芥、羌活、独活、葱白、薄荷等络药;明清以降,又增桑叶、青蒿、菊花、淡竹叶、枇杷叶等络药,缘由近代生民气禀较薄,不宜予峻剂辛温,且络病易传热的缘故。
刘氏将中药分成十七门:精门、气门、血门、心门、肺门、胃门、肝门、肾门、外表门、攻下门、镇涩门、痰门、火门、水门、湿门、痛门、毒门[1]。每门又分类,每类又别其猛次,如气门分补气和伐气两类。补气类,凡二十三味。补气猛将有附子、人参、高丽参、黄芪、黄精、白术、蛤蚧尾、鹿茸等;补气次将有枸杞、白术、五味子、龙眼、荔枝、西洋参、高丽须等。伐气类,凡四十三味,分猛、次、轻三类。伐气猛将有麻黄、细辛、旋覆花、青皮、柴胡、紫苏、乌药;伐气次将有吴茱萸、香附、延胡索、半夏、麝香、槟榔、陈皮、木香、沉香、香橼、五加皮、苏子、前胡、厚朴、鳖血柴胡、郁金、大腹皮、薤白、白豆蔻、神曲、川楝子;伐气轻将有陈皮、木瓜、绿萼梅、厚朴花等。
刘氏分药物为十七门,具体划分或有可商之处。但刘氏在临证遣药时,必根据病情、体质、邪正盛衰区别应用,救急拯危,药性要猛,补偏救弊。长期服药者,药性宜轻;病重药轻,隔靴搔痒,贻误病情;病轻药重,药过病所,亦属失误,令病家既伤于病,再伤于药,脏腑无语,生命堪虞。尤其小儿用药,稍呆则滞,稍重则伤,稍不对证,则莫知其乡。遣药的最高境界是丝丝入扣,刘氏药物分类法,用药如用兵,示人以规矩、准绳,足见其良苦用心、裨益后学。
3 衷中参西,不分畛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福州、厦门是五口通商口岸,欧风东渐,早期传教士来闽传入泰西医学,继之创办西医院。刘亚农在福州耳濡目染西洋医学,他年少曾“患咯血,偃卧床蓐,数载中西名医束手”,他由中而西涉猎殆尽,体会“所谓菌(细菌)并非西医所捏造,亦确有其见证,确有其物”。西医以“爱克司光”(X光)胸透,服“杀菌、滋补肺部药品数十种”,但均无效果,且精神颓废,自汗失眠,气散欲脱。后他寝馈岐黄,探究本草,急投峻补肝肾之剂百余服,血止肺强,百病渐瘳。从此他拜师学医,且手不释卷,攻读《黄帝内经》《伤寒论》,笃志从医,但他亦不排斥西学,认为西医检查细菌、胸部透视、肌肉注射等亦有可取之处。但中医病因、病理,尤其是气化学说十分高明。“西医倒果为因,究实质而抛气化,外治之法治内病,是其所短”。故中医、西医互有短长,与其分立门户,杆格不通,不如取彼所长,补我所短,交换学识,俱臻完全,其乐何如哉。刘氏援例说明,如例1,某友高热,西医断为肺炎,针药并进无效。肺炎者,炎者重火也,刘氏不惑于炎症,断为虚寒,虚阳倂于上,进桂附数服愈之。例2,方某患“肠炎症”,二便壅闭,西医予泻下药而膈食作,进食困难75 d,只饮牛奶,刘氏予半夏泻心汤,服药五剂,能进米饭2碗。方中无消化之品而能开胃,人疑有神助,盖苦辛合化之功也。例3,贫血症,中药以阿胶、干地黄、川芎、当归等味治疗,然芎归还暖动肝,阿胶、地黄近滞伤脾,功效亦缓,而改为西药补铁剂,价廉功倍,有鉴于此,刘氏主张召集中、西名医,互相研讨,取长补短,实质于气化并论,宜互究而勿偏;实验与学理相衡,当兼收并蓄。所以他倡议福建医学总会改为医药联合会(应为“全闽医药学会”),民国三年(1914年)全国医药联合会厦门分会成立,他致祝词,据长者(收藏家)提供材料,全闽医药学会(福州)会章,福州于民国元年(1912年)成立,会长方澍桐,下设理事部、评议部、编辑部(聘西医张友琴两人)、研究部(聘西医王彰彩等人),此得力于刘氏所倡议也。
4 不拘门户,熔汇寒温
刘氏著《二十世纪伤寒论》,是书分六卷。第一卷导言、病理篇;第二卷六经诊断篇;第三卷平脉篇;第四卷温病篇等;第五卷药物学分类;第六卷静坐疗病法。可见刘氏推崇伤寒,但亦重视温病。他认为温病与伤寒不同,治法亦异,凡温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肺经;伤寒自下而上,始于膀胱经,故温病不能依伤寒成例。“伤寒论附于各种温病,多未议及。吴鞠通温病条辨,却能羽翼前贤。”即《伤寒论》是辨证论治的基础,是方书之祖,是温病之先河,但温病羽翼伤寒,两者并不矛盾,伤寒六经和温病三焦、卫气营血的理法方药统一起来,从而构成一套完整的外感辨证论治体系,故该书第四卷列温病篇、湿温篇、脑膜炎治疗篇、痧痘麻疹斑、猩红热之鉴别及治法篇。如治疗太阴风温初起,恶风寒者,桂枝汤主之。刘氏认为既病属温,则不宜用桂枝汤,初病之证,形寒发热,头痛肢痛,无汗不解,咳嗽口渴,舌苔薄白,脉息或弦或紧或滑或数,皮肤炽热者,应以银翘散、五味饮等加减治之。风温之病,宜辛凉解表;温病之病,宜辛凉透邪;温毒之病,宜清热解毒;湿温之病,宜分化湿热,兼疏外邪,予湿热两解法。以上辨证选方遣药均迥异于伤寒。至于“脑膜炎”“麻疹”等病多与热毒有关,当按温病治疗,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伤寒与温病虽是不同的体系,但温病是在伤寒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伤寒是温病的基础,温病是伤寒的发展。刘氏不排斥温病,将其列为单独章节,互为补充,一统寒温,临床因时因地因人不同,不可拘执。
刘亚农系近现代福建杏林泰斗,执医重教,深耕伤寒。著述颇丰,声动八闽,名达京畿。吾追随肖师多年,今笔者从其著作、方笺、医案等方面初探其学术见解。刘氏其学深邃,其理湛深,笔者虽努力探索,自知陋质,不能烛幽,然旨在做问路之石,望同仁鉴之,共同推动中医学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