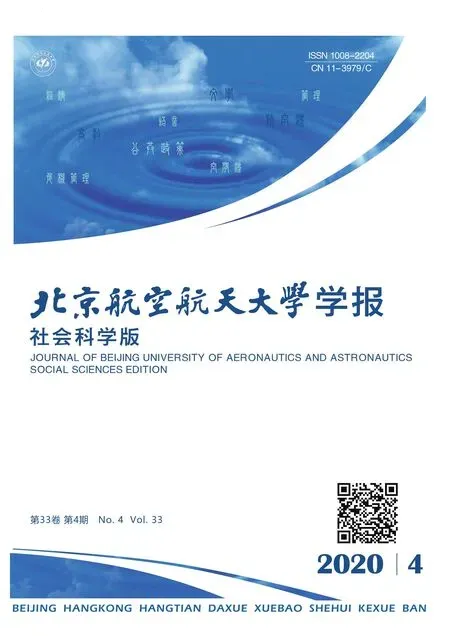记忆、遗忘与宽容:《被掩埋的巨人》中的人文思考
唐晓芹, 石云龙
(1.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WPP视觉艺术学院, 上海 200231;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6)
一、引言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秉持国际化的文创理念,书写了多部题材鲜明、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作品。2007年英国利物浦召开“石黑一雄与国际化小说”会议,使其国际主义写作享誉世界。石黑一雄国际主义书写力作《被掩埋的巨人》,“包含了对于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重要意义的生活景象”[1]。小说以记忆为依托,关注全球背景下国际战争与和平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身份、生命和人类生存等主题,在迷雾的遗忘中揭露个体身份的困境;以碎片化记忆为工具,重新审视历史事件,重构个体和民族身份;放眼人类生存状况从伦理层面去思考人类终极目标,在记忆、遗忘与宽恕中体悟生命意义,体现出石黑一雄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切的人文关怀。
二、迷雾下的失忆:自我身份的困境
记忆始终是石黑一雄小说的重要主题和特色之一,《被掩埋的巨人》更是将记忆书写极致化。小说通过全民族集体失忆描写将人类常态记忆与个体及民族身份编织成网,在迷雾的失忆中“扫描过去,探寻自身身份、失落及背弃的线索”[2],剖析和思考失忆背后隐藏的个体及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小说开篇就营造出一种迷雾笼罩下的荒凉气氛,为刻画人物的内心焦虑与身份失落预设基调。“冰冷的雾气弥漫着整片河流沼泽”[3]3,还有可怕的食人兽不时出没。年迈的埃克索(Axl)夫妇就住在附近“嶙峋的山峦”之下的“阴影”中,“孤独的生活着”[3]4。在这种阴森的环境中,埃克索时常会觉得“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噬咬着他的心”[3]5。读者在小说碎片化的叙述中逐渐发现埃克索失落感的根源正是这片由母龙魁瑞格(Querig)喷出的会让人们陷入失忆的迷雾。迷雾不仅让埃克索夫妇失忆,甚至使得整个民族都“不会回想过去,哪怕是刚发生的事情”[3]7。这种全民族范围的失忆使“《被掩埋的巨人》的主人公们对自己的身份一无所知”[4],碧特丽丝(Beatrice)绝望地哭诉着“这片被诅咒了的土地被遗忘的迷雾笼罩”“我们都不记得那些日子,后来多年的事情也不记得……我们甚至也不记得我们的儿子,也不曾记得为什么他会离开我们”[3]51。在某种程度上,埃克索夫妇失忆使得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错乱,难以抵制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就像精神的牢笼一样将其困顿其中,也成为他们迫切开启寻子之旅,摆脱迷雾的控制,找回记忆和身份的根本原因。
石黑一雄敏锐地察觉到迷雾笼罩下的巨大身份危机,通过小说《被掩埋的巨人》多声部叙述揭露主人公埃克索身份的不确定性和碎片化,以小人物的微视角展现被掩埋的记忆创伤对身份认同的深远影响,亦借此表达出对当今社会人类身份危机的关注和思考。小说首先以全知视角叙述方式将主人公埃克索介绍给读者,并明确表示“可能这不是他们准确的名字,也不是全名”[3]4。作者有意以含糊不清的叙述为解读埃克索身份危机提供些许信息和线索,让读者凭借这些叙述碎片拼凑出埃克索夫妇的生存状态:他们生活在村子的边缘,被禁止使用蜡烛,与其他村民也很少来往,甚至因有一次与村子里的一名陌生人吵架而被赶出村子。然而,读者也不由自主地对埃克索夫妇的生存困境提出一连串的疑问,他们的他者化身份依然像个谜一样尚未破解,直到作者将另外两个叙述声部引入,即威斯坦武士(Master Wistan)和高文爵士(Sir Gawain)的声音。一方面,威斯坦武士认为埃克索的身份会唤醒过去的某个重要记忆,在其不断逼问下埃克索感到“一些记忆的片段浮现脑海”[3]126,甚至有一种焦虑和不安;另一方面,当高文爵士仔细地观察埃克索的容貌时,他立刻露出了“震惊”的表情,而埃克索自己也“本能地转过脸”[3]123。高文爵士随后的浮想叙述犹如电影的最后一个镜头,将掩埋在迷雾下的创伤记忆全部揭开,埃克索一直迷惑甚至不敢面对的真正身份也随之拼接完成。埃克索实际上是亚瑟王(Arthur)的一名骑士,因无法承受后者违背“无辜者保护法”[3]244,下令屠杀撒克逊人的悲惨场面而逃离。当统治者滥用民族历史记忆,将“官方版本民族历史”强加于人们的时候,人们往往就已经成为被迫失忆群体,丧失“重新叙述他们自身行动的原始动力”[5]。迷雾的笼罩下,埃克索的被动失忆使其沦为生活中的悲剧式人物,饱受身份错乱的煎熬,陷入自我身份认同的无限困境中。在当今世界格局演变过程中,战争暴力冲突时有发生,石黑一雄笔下的埃克索宛如当今社会种种战乱后无数幸存者的代表之一:他们生活在某种被迫的和平迷雾下,虽然暂时忘记战争创伤记忆,但始终承受着身份认同危机带来的巨大精神创伤。
三、碎片化的记忆:直面身份的重构
石黑一雄继续深入个人集体失忆的背后,旨在探讨个体、民族乃至全世界究竟应该如何面对过去,在黑暗记忆中重构自我身份以继续生存。在一次访谈中,他曾坦言:《被掩埋的巨人》中“不仅仅是书写个人的记忆和身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探索人们“如何面对过去的黑暗记忆”[6]。迷雾使埃克索陷入自我身份的困顿期,甚至无法正常生活,其寻子之旅中的记忆碎片犹如微弱的希望之光,照亮其重建身份的艰难路程。“记忆,包括创伤记忆在个体和集体身份构建过程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7]。一方面, 通过碎片化的创伤记忆书写,石黑一雄描绘出埃克索的心灵景观,帮助个体寻找和重构自我身份,在无法安慰的现实世界中找回一份慰藉;另一方 面,石黑一雄将个体的回忆与民族的历史融合交织在一起,集合埃克索个体记忆碎片和身份重建架构起亚瑟王时代的民族历史和身份,并以此映射当今英国乃至其他国家民族面对过去的黑暗记忆时的民族身份问题。
随着迷雾真相的揭露,埃克索通过记忆碎片克服其自我身份的失落,渐渐找回勇气回忆和面对被掩埋的创伤记忆,进而破解现在的身份困境以重构自己完整的身份。然而,在埃克索重建过去身份的过程中,他始终有一种既担忧又期望的矛盾心理。在回忆过程中,埃克索总有一种担忧,不愿意完全记起过去的事情。一方面,埃克索十分不确定消除迷雾“会带来什么样的好处”[3]68,即使有些许的愉快记忆碎片重现脑海中,但内心的喜悦总是“夹杂着一丝的悲伤”[3]79;另一方面,威斯坦武士和高文爵士的记忆叙述又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埃克索放下担忧,不断揭开过去的创伤记忆,重新思考自我身份归属。在《被掩埋的巨人》中,多声部的碎片化叙述取代传统的线性叙述,这种断裂和拼接恰如其分地表现出那些饱受战乱创伤记忆之苦的幸存者们的生存状态。当威斯坦撒克逊武士身份被揭露,高文爵士坦白地下掩埋着“过去屠杀留下的遗骸”[3]195的时候,埃克索意识到“个人过去经历和民族记忆之间无法避免地联系在一起”[4],终于勇敢地承认其亚瑟王骑士身份,执行着推广亚瑟王的伟大法律的重要任务。随着更多记忆碎片的拼接,埃克索揭开高文爵士的伪装,指出其母龙守护者身份,直言法律和迷雾是“一个阴险的办法”[3]326,承认自己过去“像是个做着梦的傻瓜”,亲眼目睹“庄重的誓言毁于残酷的屠杀”[3]335。至此,埃克索已不再恐惧过去的黑暗记忆,为自我身份的重建过程画上完满的句号。石黑一雄追寻人物记忆碎片,探寻其身份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呼吁人们能够勇敢地挖掘和面对掩埋的创伤记忆,在悲伤世界中重构新的身份继续生存。
《被掩埋的巨人》中碎片化记忆不仅是主人公重建个体身份的工具,也是作者站在客观角度再次审视民族历史,反思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的工具。石黑一雄曾表示想在其作品中“一方面关注历经重大社会变革的国家,另一方面关注个体记忆。但我从未能够将两者放在一起”[8]。实际上,小说《被掩埋的巨人》已将这两个主题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并完美呈现出来。高文爵士亚瑟王骑士的特殊身份使其成为那段历史的代言人,借助其个体记忆书写,石黑一雄回顾民族历史,再现民族创伤记忆,重新定义民族身份。在高文爵士的记忆碎片中,撒克逊人和不列颠人之间长期的民族战争的历史真相得以揭露,不列颠人在所谓伟大法律的谎言掩盖下大规模屠杀撒克逊人,随之又施以魔法,借助母龙的气息剥夺整个民族的记忆,换取“强制性和平”[6]时代。然而,以威斯坦武士为代表的撒克逊人从未放弃过复仇的决心,被掩埋的创伤记忆还是慢慢觉醒,将高文爵士所代表的亚瑟王统治者们的面具撕得粉碎。在现实面前,高文爵士不得不承认不列颠人对撒克逊民族所犯下的罪证。可悲的是,高文爵士像亚瑟王殖民般统治者的傀儡一样不肯面对帝国历史的瓦解,始终幻想着只要即使已奄奄一息的母龙再维持一段时间,被掩埋的巨人不被唤醒就可以给人们足够时间“让伤口永远愈合”[3]327。然而,“和平建立在屠杀与魔法师的骗术之上,怎么能够持久呢?”[3]327威斯坦武士毫不留情的质问犹如一把尖刀给了高文爵士最后的致命一击,使其不得不重新正视两个民族历史和身份。石黑一雄曾坦言自己因受到南斯拉夫战争、卢旺达大屠杀等现代冲突和战争的启发而创作《被掩埋的巨人》,他借助文学化的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的战争历史书写现代社会历史,“不止是那些近期从冲突中恢复的社会,还有那些拥有长期被掩埋记忆的社会”,比如“二战后的法国、被日本完全忘记的对中国的大屠杀历史等”[6]。战争过后满是创伤记忆的民族身份认同该何去何从?从某种意义上讲,石黑一雄的《被掩埋的巨人》为探索该如何对待创伤记忆背后隐藏的民族历史,如何面对创伤后的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提供了人文思考平台。
四、浴火重生的宽恕:人类生存的伦理思考
石黑一雄并未止于对记忆与遗忘、个体与国家民族身份等主题的书写与思考,他赋予作品以开放性、包容性和延展性的力量,“挖掘隐藏在我们与世界联为一体的幻觉下的深渊”[9],旨在探讨记忆背后更深层的人性和人类生存共同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被掩埋的巨人》堪称石黑一雄这一创作理念的最佳代表。小说以英国亚瑟王时期为历史背景,通过记忆书写讲述一对不列颠老夫妇寻子之旅的故事,揭露出创伤记忆给主人公们所带来的身份失落、他者生存困境及精神危机等问题。作为“一位伟大的人性守护者、优秀的情绪管理者和技术高超的故事讲述者”,石黑一雄在小说《被掩埋的巨人》中继续以某种看似“难以避免的悲伤”[10]的精神力量对人类生存展开深层次的伦理思考,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现代社会中深受各种精神创伤痛苦困扰之下的人类生存困境、情感困境和人性伦理困境等现实问题的思考,期望让“我们关心这个世界,关心他人,关心我们自己”[11]2,彰显出其作品的文学伦理关怀属性。
首先,石黑一雄以英国撒克逊与不列颠人的历史战争为背景讨论当今社会战争与和平的矛盾问题,通过寓言式记忆书写将小说《被掩埋的巨人》转化成对战争与和平的文学伦理反思,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全局发展角度上探索国家和民族与过去战争创伤的和解,表达其对全人类和平的文学伦理呼吁。小说《被掩埋的巨人》中,人们似乎生活在一种稳定的和平环境下,因为人们的记忆总是在几个星期或几天甚至几小时后就消失在迷雾中。然而,这种和平生活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它看似保持着和平,但事实上不过是由于某种军事上的胜利而维持了表面的和平而已”[12]。过去残酷的、血腥的行径因亚瑟王的特殊战争策略而被掩埋,撒克逊民族和不列颠民族的幸存者们获得了短暂的和平。然而,记忆的碎片又不时地苏醒,种族之间的仇恨一次次被唤醒,战争与和平再次成为难以调和的矛盾。当威斯坦武士终于打败高文爵士,杀死母龙之后,却“显得很沮丧,没有一点凯旋而归的样子”[3]338。虽然完成了“公平与复仇”的重大使命,威斯坦武士仍然无法逃避地陷入一种纠结的矛盾心理。他既“鄙视不列颠人中的懦弱者,又尊敬和热爱那些优秀者”[3]338,心中总有一种声音“厌恶这仇恨的火焰”[3]340,久久无法狠下心为获得所谓的和平和公平开启新一轮的屠杀。然而,母龙一旦被杀,被掩埋的记忆巨人便会迅速觉醒,两个民族间的屠杀与战乱将再次爆发。在事实面前,埃克索无奈地感慨“我们只好希望上帝能找到办法,维系两个民族之间的纽带”,否则“当巧舌之辈点燃古老的怨恨,挑起对土地和征服的新欲望之时,谁知道会带来什么灾祸呢?”[3]340石黑一雄精巧的情节冲突设计将人们面对战争与和平陷入两难困境时的“遗忘、记忆和宽容”的复杂心理过程刻画得淋漓尽致,深刻地诠释出人们对“正义和宽恕的伦理思考,为获得和平从过去的负担中释怀的需求”[13]。石黑一雄在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中亦提到战争与和平问题,他反思“难道真的有时候只有遗忘才是停止暴力循环或阻止一个社会陷入混乱和战争的唯一途径?另一方面,难道稳定自由的民族真的建立在人为的遗忘和令人沮丧的公平之上?”[14]当小说中埃克索夫妇祈求战后新生代代表埃德温(Edwin)“记住他们以及他们之间的友谊”[3]344的时候,或许作者对战争与和平的古老辩题给予了某种文学伦理启示。石黑一雄“不仅从哲学、历史以及心理学等各种层面对处在动荡时代的个人与国家进行了生动的描绘,而且还对道德问题有着很深刻的剖析”[15]。小说中作为新生代力量的埃德温,与“战争的关系已有所不同”,尽管“可能也有复仇的愿望”[16],但当他意识到自己所仇恨的不列颠人中不包括善良的埃克索夫妇的时候,或许就已经学会了在记忆与遗忘中释怀。“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 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17]。石黑一雄借助埃德温之口表达出对全球和平的期望,呼吁当代人类对生存和生活的热爱和不懈追求。
石黑一雄的伦理关怀理念还体现在小说《被掩埋的巨人》中对个体情感生活的独特观察和描述,以“沉着而精明的叙述方式更加贴近伦理问题和困境”[11]6,探讨生活中的伦理选择问题:人们“如何对待人记忆中那些你想要掩埋的巨人?”“如果婚姻或家庭中的爱建立在错误或不完整的记忆之上那还是爱吗?”[18]小说《被掩埋的巨人》开篇伊始就提出关于爱的话题,并以埃克索夫妇的情感生活为主要叙述情节之一贯穿全文。船夫告诉埃克索夫妇只有“两人之间拥有异常强大的爱情纽带的夫妻”[3]45才能一起踏上温暖美丽的天堂般小岛。对于埃克索夫妇来说,爱的纽带就是彼此共同的记忆,因此他们的寻子之旅亦是重拾共同记忆的旅行。然而,当遗忘的迷雾就要褪去之时,总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些许的恐惧时不时地萦绕彼此心头,碧特丽丝担忧地询问丈夫“迷雾散了,你可曾害怕接下来会有什么揭露在我们面前?”[3]283同样,埃克索也担心妻子若回忆起自己曾多次让其失望而感到恐惧。因此他恳请妻子迷雾散去之后无论怎样 “请永远记着这一刻你心里对我的感情”[3]294。正如他们所担心的那样,随着记忆的再次浮现,埃克索的不负责任、碧特丽丝的背叛等不愉快的往事也随之重新摆在他们面前,迫使他们不得不面对新的伦理选择困境:如果没有迷雾他们的爱情会一直牢固吗?面对残酷的被掩埋已久的真相,到底该如何选择?埃克索坦白尽管自己“言行都主张宽恕,但尘封多年的内心深处某个角落却渴望复仇”[3]357,也因此伤害了自己的妻儿。庆幸的是,在新的伦理选择困境面前,埃克索坚定地告诉船夫“伤口愈合很慢,但终究还是愈合了”[3]357。石黑一雄曾表示其小说涉及“生活中在一定程度上走错路的人、迷失方向的人……面临的挑战是首先拥有正确的价值观,同时拥有勇气以某种方式坚持下去”[19]。小说最后,面对创伤记忆埃克索夫妇相互宽恕,选择在记忆与遗忘中从容释怀,将当下的爱铭刻于心,带着希望期待明天。石黑一雄以埃克索夫妇的个体情感伦理困境触及现代人的内心,引导人们思考在经历过某些难以避免的创伤之后该如何在情感困境中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事实上,对于个体情感和家庭而言,埃克索夫妇就像现代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尽管被掩埋的创伤记忆会以各种形式再现,尽管这种再现或许会让人们陷入更多的伦理选择困境,但石黑一雄用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无论记忆与遗忘的经历有多痛苦,宽恕也许是人类生存的最佳伦理选择。
五、 结语
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化问题为文学写作提供了更多创作主题。石黑一雄着眼当今国际战争与和平问题再次实践国际主义文学创新,其新作《被掩埋的巨人》便是在这种多维度的影响下对身份、生命和人类生存等国际主题更深层次的书写和探讨。战争带来的创伤记忆不仅使得整个国家民族及个体身份陷入失落迷茫的尴尬境地,也对个体情感和家庭产生极大的影响。如何面对创伤记忆和遗忘以维持某种程度上的世界和平及个体情感和家庭的和谐成为人们亟需面对的艰难抉择。作为一名 “高质量的、以人性为本的作家”,石黑一雄用寓言式的写作向人们“展示如何去做这件事,并在行动中返以一定程度的力量、希望和安慰”[20]。小说《被掩埋的巨人》将人类生存的宏大命题聚焦在记忆的书写中,展现主人公们在记忆与遗忘中学会宽恕,实现伦理意义上的自我超越,也启示读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思考国际问题,体现出文学作品的实践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