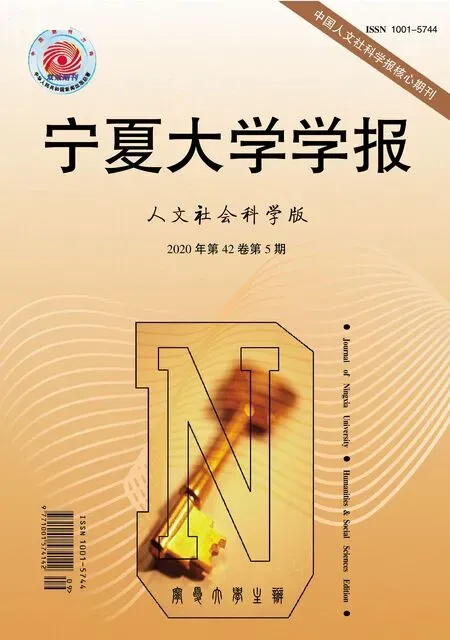消解文本叙事中心,重构平等话语空间
——《一个好人在非洲》中的后现代伦理叙事
常智勇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872;唐山学院 外语系,河北 唐山 063000)
威廉·博伊德(William Boyd)是英国当代文坛一位后现代作家。他的小说《一个好人在非洲》出版之后即被评为当年最佳长篇小说,荣获惠特布雷德文学奖(Whitbread First Novel Award),第二年又获得了毛姆奖(Somerset Maugham Award)。小说讲述了派往一个西非国家金占扎的外交官摩根·利非的曲折经历,他被卷入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和难以启齿的桃色事件,陷入尴尬境地,成了一个反英雄形象。传统作品中英国列强盛气凌人的帝国形象被解构,英国殖民者精明能干、高高在上的身份地位被消解,欧洲中心、自我中心和种族优越论被无情地讽刺和抨击。作者在其小说中将狂欢化与互文等后现代叙事手法与社会批评相结合,使他者之声与权威之声组成社会话语的交响之音,展现了英国与非洲国家之间以及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种族歧视等不公平现象。小说凸显了承认差异、尊重他者、对他者负有绝对责任的后现代伦理思想。正如作者在采访中谈道:“当一个人写作出了名,有了自己的读者,同时也有了他应尽的责任。这是应当认真考虑的。”[1]因此,作者也是一位具有后现代伦理思想的作家。
一 后现代文学伦理叙事的主要关切
自20 世纪末,在西方各种后现代文化理论激烈争鸣之时,“后现代伦理学”“后现代道德”等概念术语应运而生。英国利兹大学社会学教授齐格蒙特·鲍曼是较早公开使用“后现代伦理”“后现代道德”这两个概念的影响较大的学者之一。鲍曼认为,现代性排斥、拒绝和否定差异使一切“他者”成为不合法,通过不可能的真理、纯艺术、人性的普遍性,本来不存在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在场,把它强加给人们,从而使自己成为可能。后现代性试图通过弘扬革新的思想观念,改变和超越现代性或现代精神,建立承认差异、尊重他者,主张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合理的后现代社会秩序和后现代精神[2]。以后现代性为其核心观念的后现代西方伦理学是对现代性和现代西方伦理学的解构和批判,同时建构了一种能重建后现代西方道德价值体系的伦理学理论。雅克·德里达质疑各种知识定论赖以形成的基础,表现了从前人知识实践的限制和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思想意识,批判和瓦解启蒙思想的基础,提醒人们从逻各斯所不能认同的立场来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即呼吁人们以别样的语言来重新书写逻各斯,从而解构了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以后的著述中,德里达提出了弥赛亚意识、正义和友爱精神等恒久的终极价值,以此构建后现代西方文化伦理。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多次讨论了一种“没有救世主的弥赛亚”精神。按德里达的说法,弥赛亚是“绝对差异的他者”,他永远存在于异域,不息地恳请和呼唤,要求对他做出应答,也就是负起责任,这是一种“没有救世主的弥赛亚精神”,是德里达对即将到来的“他者”保持一种期待[3]。在此基础上,德里达在其《友爱的政治学》一书中提出了人类美好的价值理想——期许的友爱和未来的民主。在马内利·列维纳斯看来,伦理是“与他者的始源关系”[4]。“他者”是独一无二的,是绝对相异的。列维纳斯的后现代伦理学呼唤责任、呼唤友善,在经过“他者”而确证无条件的责任时,其思想就展开了对集权、暴力的反思和批判。后现代主义消解权威和中心、承认并尊重差异、主张彻底多元化的基本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后现代伦理诉求,是后现代西方伦理学的思想基础。后现代伦理叙事是后现代伦理学的体现,它尊重差异和他者,消除作者的叙事权威和文本的叙事中心,采用以多角度观察、多样的叙述者、多种声音叙述(复调)、杂糅结构、多种变量的表达技巧等狂欢化叙事,用平行结构、戏仿和直接引用等构成互文叙事。这种去中心、多样化的伦理叙事形式与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尊重差异和他者具有一致性[5]。后现代伦理叙事的消除文本叙事中心和巴赫金提出的复调小说具有一致性,是一种全面对话和多声部的小说,多角度观察的多叙述者、多声音(或复调)的对话的叙述机制。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基础上,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概念:“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拼凑,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改编。因此,互文性的概念应该取代主体间性的概念。”[6]关于“互文性”,罗兰·巴尔特这样解释说:“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并以多少能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文本,例如,先前文化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7]“互文性”是解构主义的一个基本概念,它的提出旨在打破结构主义文本的孤立性与封闭性。解构主义认为,任何文本的互文性都是由词语引发该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对话,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在差异中形成自身的价值[8]。这种消解作者与叙述者权威的狂欢化叙事和互文叙事与其所表现的后现代伦理思想相得益彰。
二 用狂欢化叙事建构权威声音与他者声音平等对话
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小说具有对话性质,“任何一个表述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对话”[9],一部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容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10]。巴赫金的复调小说是一种全面对话和多声部的小说。正如“愤怒青年”主题小说和“垮掉一代”主题小说将传统小说塑造人物和反映现实的文本观双重解构,体现了世界经验狂欢化的要义。博伊德以戏仿、黑色幽默、真实与虚构并置等写作方式解构了文本的稳定性,并使意义上没有得到确证的可能,从而实现了文本的狂欢化。他通过戏仿、黑色幽默等艺术手法,力求解放现代文明和权力机制的压抑,改变死寂世界中荒诞的现实,并对命运、无常和死亡等形而上学的哲学命题进行了深刻阐释和重构。他的笔下展示的是一个破碎、不稳定、怪诞的小说世界,小说中的人物变成了狂欢节上的“小丑”,上演着加冕和脱冕的狂欢节仪式,实现了世界的狂欢化。这种后现代伦理叙事形式消解了传统叙事的整体性和同一性。博伊德主要对“欧洲来客”利非进行了“脱冕”,同时对非洲政客山姆进行了“加冕”,打破权力等级关系、消除种族界限,实现了小说中人物关系的狂欢。另外,小说的开放性结局增加了小说情节的不确定性,消解了作者中心的特权,使作者与读者平等对话,实现了小说作者与读者的狂欢。这种消解作者与叙述者权威的狂欢化叙事与其所表现的后现代伦理思想相得益彰。
首先,小说对“欧洲来客”权威声音进行了颠覆,作者描写了英国特派专员的第一秘书摩根·利非在贪墨成风、腐败盛行的刚赞巴滑稽而又曲折的经历。当时刚赞巴市政治腐败、社会混乱,英国在那里的外交官员们生活奢靡,这样复杂的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摩根。在小说的开端,摩根被描绘成一个身体和心理上滑稽可笑的英国外交官形象、一个很单纯和对生活没有抱负的反英雄形象、一个被“脱冕”的滑稽的小丑。“摩根喝光了他那瓶啤酒。他愉悦地自言自语道:生活在非洲有两件好事情:只有两件。啤酒和性交;性交和啤酒。他不确定以什么顺序给他们排列———他真的是漠不关心——但是他们是他生活中始终没有让他失望的事情。”[11]作者在塑造摩根这个反英雄形象的时候,性在他的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由于他的放荡,他感染了性病,这不仅造成了他身体的不适,而且还影响了他和专员女儿普莉希拉·范肖的恋人关系。后来体检结果暂时让他中止了在非洲仅有的两个“享乐”资源。默里医生警告他在传染期不要喝酒或发生任何性关系。虽然医生夸大了摩根疾病的严重性,但他幼稚的反应暴露了他缺乏理性和自控能力。当默里医生告知摩根他得了性病的时候,博伊德仍把这种很严肃的情况描写得滑稽可笑:“‘对’,他很麻利地说,‘让我看看。’‘你的意思是?’摩根清了清他的嗓子。‘脱掉裤子?’‘是的。脱掉短裤,全部脱掉。’摩根认为他很可能会晕倒。他用颤抖的手指解开裤子并把裤子脱到脚踝。结果忘记了他的宽松的、破旧的短裤,当他解开别在内裤上的别针时由于尴尬他感到脸上在冒火。”[12]摩根感染性病是一件比较严肃、难以启齿的事情,而在作者笔下,以后现代黑色幽默的方式来刻画摩根愚蠢、滑稽可笑的行为,使作品产生一种怪诞的感觉,讥讽了愚昧无知的英国殖民者形象。摩根的反英雄形象还表现在金占扎总统大选结果公布之后,当时在高级委员会门前爆发了一场暴力游行示威,抗议英国殖民者暗中干预金占扎总统大选,抗议者把摩根和他的长官阿瑟·范肖与其妻子包围在委员会的大楼,摩根当时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表现了“英雄主义”,他决定把自己伪装成阿瑟·范肖作为诱饵,很无畏地对他的长官说:“‘不是你,阿瑟,’他说,一股自信的力量在他的身体里涌动,‘我,我将坐在你的位置上作为诱饵。我会迫使人群让开路,你们其他人随后逃脱。’”[13]摩根为了一个他憎恨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他逃脱,即使表现了英雄主义,也显得荒唐可笑。虽然摩根和范肖的妻子设法逃了出来,但是他们在一个十字路口迷路了,最后又回到了暴乱的地方,这位“英雄”没有完成任务,摩根的“光荣时刻”是短暂的,其愚蠢、无能又一次被暴露,打消了读者想看到摩根完成英雄考验的期望,再次强化了他的反英雄本质。这里既有对摩根“英雄主义”的“加冕”,又有对他愚蠢无能、胆小怕事、哗众取宠的小丑形象的“脱冕”,作者再一次颠覆了以往英帝国殖民者在殖民地耀武扬威的形象。小说中作者丑化了英帝国殖民者本应有的外交官的威严形象,其目的是通过颠覆英国殖民者形象来说明英帝国在世界的中心地位已被颠覆,打破了传统小说中英国殖民者的英雄形象,同时打破了英帝国殖民者的霸权话语。作者的这种书写,消解了西方中心和权威,体现了后现代伦理叙事策略。博伊德作为一名英国后现代作家,对英国殖民者的反思与批判,体现了他承认差异、尊重他者的后现代伦理思想。后现代西方伦理学反对主体主义(即中心主义),因为它不断加剧“自我”与“他者”在现实生活中的对立。这是作者对以前英国殖民者在殖民地高高在上、耀武扬威形象的“脱冕”,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作品中对殖民者的书写,没有了昔日作品中在殖民地精于算计、征服、盘剥和掠夺,而是滑稽、无能、愚蠢的形象,作者打破了白人至上的书写模式,体现了追求多元性的后现代伦理叙事模式。
其次,博伊德对殖民霸权下“他者”声音的“加冕”。《一个好人在非洲》中的山姆·阿德库诺是金占扎国家党(KNP)的领导人,一位野心勃勃和肆无忌惮的非洲政客,他利用和英国殖民者的利益关系,帮助他自己在大选中获胜。同时,英国殖民者想通过满足新兴中产阶层参政要求的办法,将他们改变为殖民政府的“合法者”,逐步使政治上愿意与英国政府合作的非洲民族主义温和派进入中央立法会议和政府,从而改善和延长其殖民统治,保全它在非洲的殖民帝国。因此,英国殖民者不顾民众的反对默许了山姆的一些做法,山姆表面上在刚赞巴施行了一系列受欢迎的政策,其实他是为自己以后的政治道路捞资本。有一次在范肖家举办的舞会上,暴露了他双面性的人格。“现在,俯视那群忠心的臣民,摩根看到了山姆和一个白人妇女正站在酒吧旁,他确定她为这位政客的妻子。阿德库诺穿着本民族的衣服,拿着一个雕刻的乌木手杖”[14]。阿德库诺穿着本民族的服装,大力宣传他对祖先的忠诚、对本民族文化的忠诚,但是作者在小说中暗示英国殖民者举办的这次舞会是为了拉拢金占扎亲英的中产阶级。舞会上应当穿西装表示对舞会举办方的尊敬,而山姆的穿着具有一定的反讽作用。他没有低三下四地投靠英国殖民者,在舞会上还是“俯视臣民”,手里拿着象征权力的“乌木手杖”,他借助英国殖民者竞选总统的职位只是想通往一个和英国直接联系的政治世界。在后殖民小说中,被殖民的人物一般描写得很卑微、愚蠢、无能,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他刻画成被殖民者低三下四的形象,却把山姆描写成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人物,他能够在英国驻金占扎高级委员会中游刃有余地利用英国殖民者之间的特殊关系与英国殖民者的心理。作者打破了后殖民小说中对非洲被殖民者形象的固定写作模式,把山姆描写成一个狡猾、精于盘算的、贪婪的、野心勃勃的政客,为了实现目的而不择手段。比如,山姆·阿德库诺抓住了摩根的把柄,利用他为自己在英国殖民者那里牟取更大的利益。山姆充分利用了摩根愚昧、无能的弱点,当他发现摩根和他的妻子西莉亚有不正当关系时,他一反常态,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反应很冷淡:“阿德库诺表现得更像是质疑一个预定的停车位的人,而不是面对妻子情人生气的丈夫,摩根发现这个合理性、这个缺乏可辩解的愤怒更令人不安。”[15]这里山姆的表现消解了沉默的非洲“他者”下贱、愚蠢、卑微、任人宰割的书写模式,而冠之以狡猾、算计、贪婪、野心勃勃的特点,让“他者”有了言说的权力,体现了作者尊重差异和他者,采用以多角度观察、多种声音叙述(复调)的狂欢化叙事。作者用狂欢化叙事展现了金占扎新兴资产阶级要与英国殖民者平等对话,批判了原来殖民小说中欧洲中心主义、自我中心主义、种族歧视等不公平现象,打破了英帝国殖民者的“白色神话”。
另外,狂欢化叙事还体现在小说情节发展的不确定性上。后现代主义文学受解构主义思潮对“逻各斯中心”进行解构的影响,认为文本世界是作家的“虚构物”,因而作家已不再坚持文本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对应与模仿,而转向以话语言说的方式来表达作家对世界的见解。小说结尾的环境描写暗示了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金占扎国内政局不稳定,武装暴力频发,摩根对英国未来还能否继续保持其在非洲的殖民帝国位置感到很迷茫。小说结尾写道:“在黑暗中外面的雨轻轻地下着,蟾蜍和蟋蟀发出它们的声音,各种昆虫开始探测并展开它们的翅膀期待雨停下来。暴动结束了,广场荒凉了下来,烟从烧焦的汽车上一缕缕地飘动。国内其他地方的金占扎部队也包围了政府大楼,控制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开始逮捕重要的政治领袖们。名叫无辜的女佣躺在泥泞的佣人的生活区院子里,默里躺在Ademola 的停尸房里。雷声传到了海岸,在那里,Shango———神秘而费解的神,在这个寂静、湿淋淋的丛林上空闪现、雀跃。”[16]这样的结尾所传递的意象可能有些凄凉和失望,但是开放式的结尾说明未来世界怎么样不得而知。这种不确定性的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没有给出主人公最后的出路是什么,也没有告诉读者故事的最后结局怎样,让故事中的人物和读者共同参与进去,去思考英国殖民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这种不确定性让作者、小说中的人物、读者平等对话,消解了作者的权威。
三 用戏仿的叙事重构文本之间平等的互文话语空间
互文性是后现代主义文学书写的一种新的建构方式,打破了以作者为中心的孤立的、封闭的叙事空间,建构了该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对话模式,在平等的对话中形成自身的文学价值,在文学的狂欢化中建构一种开放的、异质的、破碎的、众声喧哗的后现代主义文本。互文性作为后现代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类。它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17]。因此,戏仿是互文的一种叙事形式。戏仿是后现代小说家们经常用到的一种叙事手法,他们在作品中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现象,对古典文学名著的题材、内容、形式和风格进行夸张的、扭曲变形的、嘲弄的模仿,使其变得荒唐和滑稽可笑,从而达到对传统、历史和现实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过去的文学范式进行批判、讽刺和否定的目的[18]。后现代戏仿是在滑稽模仿的同时将历史、社会现实问题化,从而对其进行社会政治批判,形成反讽效果。博伊德的这部小说《一个好人在非洲》运用了戏仿叙事手法,分别对象征欧洲文明的古罗马城、对基督教文化的经典《圣经》,以及对英国经典作品《鲁滨孙漂流记》进行了戏仿,表现了后现代主义对权威的嘲弄和颠覆、对元叙事的消解、对知识神秘性和神圣性的取消,对权力语言、欲望语言和欺诈语言的解构。
首先,博伊德对象征欧洲文明的古罗马城进行戏仿。在小说中,作者描写了一个充斥着腐败、股票投机商、政治流氓的地方,在那里非洲政客们不惜牺牲他们的尊严,其目标就是获得最高的经济利益或政治资本。作者把刚赞巴城的建筑描写得单一、沉闷、没有生机、让人感到恶心:“如同罗马城,刚赞巴城建在了七座山上,但是两者没有相似点。它建在了波状的热带雨林里,从空中看去,好像在谁家宽阔的没有割的草坪上,因喝酒过量而吐的一大摊呕吐物。每个建筑物都是波状钢的屋顶。从委员会的窗户望去——委员会大楼建在城镇的山上,在眼前摩根可以看到绵延的屋顶,一个赭石色的铁皮跳棋棋盘,一片恶心的金属海洋,一个疯子城市设计者的偏执狂想象。”[19]众所周知,罗马古城包括帕拉蒂诺、卡皮托利、埃斯奎利诺等七个山丘,史称七丘之城。公元前1 世纪,罗马城成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这是一座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古城,还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世界文化名城,一座令人感到十分神秘的城市,古罗马城代表了古代欧洲先进的文化。余秋雨先生在《行者无疆》中也有过对罗马城的赞美:“只有一个词,它们不会争,争到了也不受用,它静静安踞在并不明亮的位置上,留给那唯一的城市。这个词叫伟大,这个城市叫‘罗马’。”小说中作者把刚赞巴城与古罗马城进行了滑稽的模仿,虽然说它也建在七座山丘上,但是城市的建筑风格单一,没有城市规划,城市环境恶劣,作者把它讽刺为“一大摊呕吐物”“一个赭石色的铁皮跳棋棋盘”“一片恶心的金属海洋”,城市建筑风格、城市环境让人感到恶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纷纷独立,英国对非洲政策开始演变为所谓的“非殖民化”方式,进一步干涉金占扎国家内政,扶植亲英派政客掌握国家政权,企图控制整个国家,从而实现其在非洲的政治和战略目的,英国殖民者的行径让人感到恶心。作者表面上讽刺刚赞巴城,实则讽刺象征西方历史文化辉煌的罗马古城,也就是嘲讽了西方文明,从而消解了欧洲中心论,颠覆了欧洲的优越性,同时也讽刺了英帝国卑劣的殖民行径。
其次,博伊德对西方基督教经典《圣经》进行戏仿。《圣经》对西方社会的精神信仰和行为方式影响至深至巨,与希腊神话同为打开西方精神世界的钥匙。书中的神话、宗教、历史和伦理故事,以及哲理箴言,多蕴含意味深长的玄思,读来有一种耐人寻味的魅力。这部书对于世界历史,尤其是西方文明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把摩根和一位非洲官员夫人西莉亚的私通与《圣经》中的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进行了戏仿,摩根滑稽地模仿着亚当的样子:“‘并且他们看着他们光着身子,并且十分害羞。’他用响亮的声音说‘夏娃过来,用柚木树叶给你自己做个裙子。’”[20]很明显,这里作者戏仿了《圣经》的开篇,里面亚当和夏娃原罪的场景出现在这里,对摩根和西莉亚所采用的亚当与夏娃式的滑稽可笑的偷情进行了无情讽刺。在西方社会基督教信仰的背景下,没有什么比原罪更具威胁性,小说中,摩根的鲁莽行为也预言了他后来的灾难:西莉亚的丈夫山姆·阿德库诺,最后发现了摩根与西莉亚偷情的事,他威胁摩根,如果想保留工作的话,要弥补自己所做的一切。从那时起,来自山姆的压力始终缠绕着他,摩根成了山姆手中被利用的工具。摩根本来是一个殖民者,反而成了被殖民者手里的工具。《圣经》是西方社会的精神支柱,基督教是西方人的神圣信仰,作者把摩根与西莉亚的偷情与《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进行滑稽模仿,从而贬低了西方的神圣经典,同时批判了英国殖民者的卑劣行径,颠覆了英帝国在殖民地的崇高形象。
再次,博伊德对英国经典作品《鲁滨孙漂流记》进行了戏仿。小说《一个好人在非洲》中殖民者摩根和他的仆人星期五戏谑模仿了《鲁滨孙漂流记》中的鲁滨孙和他的奴隶星期五。摩根对仆人星期五说话时盛气凌人,由于星期五来自法属殖民地,英语不熟练,摩根经常责骂他是“蠢货”,但摩根不再像鲁滨孙一样,对星期五进行教育和驯化,不再教星期五英语。作者笔下英帝国殖民者代表摩根失去了西方殖民者最初的开拓者、探险者的英雄形象,成为懒惰、愚蠢、懦弱的代表。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等作品的出版在当时间接参与了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和帝国意识的建构,其小说与英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而博伊德的《一个好人在非洲》最显著的特点是后殖民书写,他摆脱了对土著人他者形象的固定思维模式,而是逆写了“高贵的”白人形象,挑战了欧洲和英国的形而上基础。作者这里戏仿鲁滨孙与星期五的主仆关系,改写了英国的传统经典作品,在后殖民话语中重构英国殖民者懒惰、愚蠢的“现实”,从他者的角度质疑了所谓的英帝国的先进文明以及英国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形象,其目的是去除英国殖民主义者在非洲殖民的合法化。另外,小说中,作者批判了一个好吃懒做的年轻的英国行政官达尔米,作为一个在非洲的殖民者,他整天游手好闲,工作懒散、懈怠,颠覆了殖民者的开拓精神,斥责了打上烙印的观念:赞扬殖民者热心工作,被殖民者天生被动、懒惰。作者描绘出一个绝对滑稽的在非洲的英国殖民者画像。殖民者不再是神话式的探险者,而是相当粗心和懒惰的只对权力感兴趣的管理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非洲殖民地推行所谓“非殖民化”政策,这些政策表面上给了非洲国家自治权,其实是从精神和意识形态上进一步殖民,英帝国的殖民者不仅要征服土地,而且还要征服道德、伦理、意识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英国逐渐走向没落,有力地讽刺了新的殖民者的懒惰、愚蠢,揭露了英国在当今世界霸权地位的衰落。
四 结语
后现代伦理叙事是后现代伦理学承认差异、尊重他者、敢于担当思想的文学表征,是后现代叙事策略与深刻思想的辩证统一。当代英国作家威廉·博伊德的长篇小说《一个好人在非洲》中的后现代伦理叙事主要建立在狂欢化叙事和互文叙事策略之上,其别具一格的叙事伦理彰显的是作者对国家之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深度剖析。小说打破了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学中“欧洲中心主义”“白人至上”“边缘化被殖民地人民”的传统叙事模式。一方面,作者运用了后现代主义伦理叙事的狂欢化叙事手法,打破了白人优越论,用滑稽幽默的语言讽刺了英国的殖民者,消解了欧洲殖民者高高在上的形象。另一方面,作者运用了后现代伦理叙事互文叙事手法,通过戏仿手法,对象征西方神圣、崇高的《圣经》、古罗马城进行了解构,消解了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形象。小说的结尾是开放的,是不确定的,也体现了后现代伦理叙事的思想,消解作者的权威。博伊德的《一个好人在非洲》一书是对英国殖民历史的后现代伦理深刻剖析,消解“白色神话”,逆写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