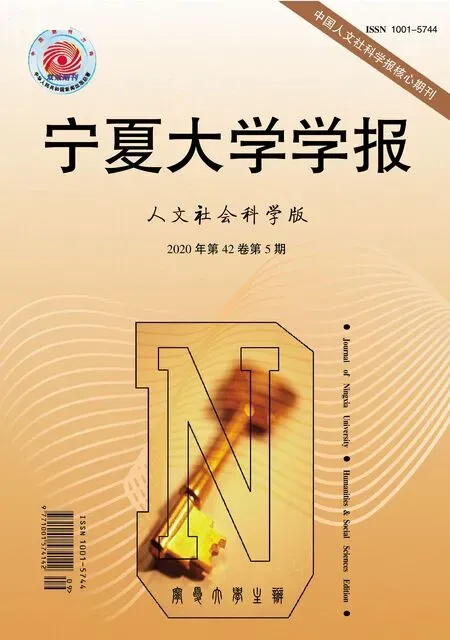宋代诗学“才性”论
于帅帅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宋人极为重视诗人主体的诗学素养,因此,诗人的“才性”问题被推到了诗学探讨的重要位置。“才性”是宋代诗学的一个时代性话题,是宋人着重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宋代儒学哲学化,理学兴起,不仅影响了宋人的思维方式,也使他们开始从哲学的高度思考诗学问题。程朱理学的“理本论”、张载的“气本论”和南宋陆九渊的“心本论”思想都深刻影响了宋代诗学的发展。诗人“才性”问题在宋代得以广泛讨论,受到哲学“理”“气”“心”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张载“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提出,对宋代诗学“才性”说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宋人的“才性”说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需要我们下一番细密的梳理功夫,才能将宋代诗学中的“才性”观念分辨清楚。由于“才性”问题自先秦就已提出,在魏晋时期加以哲学化,至南朝隋唐时期又进入文论领域,流衍至宋代,很多问题都得以解决,如“才”“性”之辨、政治才性与文学才性的区分等都已基本厘清,所以我们不打算溯源,而是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宋人诗学“才性”观念的梳理上,即诗人的诗学天赋与气质问题,同时这里的“才性”取广义的概念,着眼于诗人的所有诗学素养。我们从以下四个层面讨论宋诗学的“才性”观,一是天性、天赋;二是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改变的气质;三是气质改变和才性涵养的重要途径是学习;四是作为风格论的“文气”说,讨论宋人对才性与风格关系的思考。
一 天赋:天与诗性,自然绝人
宋人论诗,几乎必谈“才性”,“才性”论不仅在两宋时期的数量较前代为多,且纷纭复杂的“才性”说在宋人诗学中得以厘清,相关论述丰富多样。如周密《浩然斋雅谈》引周必大之说:“文章有天分,有人力,而诗为甚。才高者语新,气和者韵胜,此天分也”[1]。文章的生成有两种内在动力,一靠天分,一靠人力,这种现象在诗歌创作中更为明显,相对应的便有两种类型的诗,即天分之诗与人力之诗,有天分的诗人才高气和,所作的诗天趣流洽,自然生成,语新韵胜。这里所说的“天分”主要指天之禀赋层面的“才性”。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则讨论了才与学的关系,“人才高下,固有分限,然亦在所习,不可不谨”[2]。诗人之才,有有无和高下之分,但涵养才性,必须要重视后天的学习。
这里就涉及一个问题,即“才”“性”之辨的话题。“才”与“性”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才性”一词广泛应用于诗文理论中,于是“才”“性”的界限渐趋模糊,甚至出现了混用的倾向。苏轼《扬雄论》对“才”“性”的区别有精到辨析:
昔之为性论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为善,而荀子以为恶,扬子以为善恶混。而韩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说,而折之以孔子之论,离性以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以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遗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说为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谓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与才相近而不同,其别不啻若白黑之异也。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也。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后生,雨露风气之所养,畅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坚者为毂,柔者为轮,大者为楹,小者为桷。桷之不可以为楹,轮之不可以为毂,是岂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3]
古今论“性”者众多,但他们对“性”的本质都持有不同见解,孟子是性善论者,同为儒家宗师的荀子则认为性本恶,汉代扬雄持中立态度,认为性善恶相混,到了中唐的韩愈,则总结孟、荀、韩三人的观点,又结合孔子的观点将“性”区分为上、中、下三品,且认为“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孔、孟、荀等提出了“人之本性”和“性之本然”的问题,但囿于认识的局限性,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性”的形成和先天的关系,可见,“性”是天之禀赋,后天很难改变,而“才”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通过阅历和知识来提高涵养的。其本质的区别,一为先天赋予,一为后天培养。
宋代理学家张载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他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都是由‘气’聚合而成。人之生,都禀有‘天地之性’,天地之性纯善,因而人之本性无不善。人性之所以千差万别,是因为人又有‘气质之性’。当人禀气而生时,所禀之气清浊各异,其性就有开蔽通塞之别,人就有贤愚刚柔之不同。人之气禀千差万别,发而为文也就如万花千木”[4]。人的本性纯善,后来之所以千差万别是由于所禀之气不同,而且气质是可以变化的,通过学来涵养气质德性是宋人的重要观念。
王禹偁称赞北宋诗人潘阆说:“处士总角之岁,天与诗性,故亲族骇其语焉;弱冠之年,世有诗名,故贤英服其才焉”[5]。“天与诗性”就是天赋,诗学才能与生俱来,非后天锻造而成。富有天性的人,其本身就潇洒不拘,自然而然,诗作飘逸灵动。黄静称赏潘阆:“潘阆,谪仙人也,放怀湖山,随意吟咏,词翰飘洒,非俗子所可仰望”,潘阆可谓富有“天与诗性”的典型诗人,他这种飘洒不羁的人生态度和自然灵动的诗学禀赋类似于盛唐诗人李白。李白是公认的天才型诗人,他的才性与生俱来,行为潇洒放旷,诗作飘逸灵动。宋人论李杜诗优劣就是从诗学“才性”的角度切入,欧阳修《李白杜甫诗优劣说》:
“落日欲没岘山西,倒著接篱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大家争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其横放,其所以警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也。杜甫于白,得其一节,而精强过之。至于天才自放,非甫可到也。[6]
诗之“常言”易得,而“警动千古”之言非“天与诗性”之人不可道出。李、杜虽同为诗歌巨擘,而二人的诗风和气质截然不同,杜甫学习李白,虽得其一节,但精强过之,从“天才自放”的层面看,杜甫显然不及李白,欧阳修之言可谓中肯客观。白诗以天才自放取胜,杜诗则以功力法度扬名,天才自放不可易得,而法度功力则有因袭模仿的路径与可能性,所以后世诗人多师法杜甫,在宋代就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盛况,江西诗派极为推崇杜甫,将其视为诗社之祖,黄庭坚认为:“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7]。江西诗派的推崇,是杜诗经典化的重要一环,于是“文物皇唐盛,诗家老杜豪”[8],这样的称赏之声在整个中国诗史上不绝如缕。但李白的“天才自放”却成了后人仰望的高标,因为李白的“诗性”禀于天,不可易得,后天很难涵养此种气质,所以诗史上师法白诗者微乎其微。
“天与诗性”是诗人先天的诗歌禀赋,有“诗性”的诗人所作之诗就是天才之诗,与天才之诗相对的就是靠人力雕琢的诗。谢尧仁在《张于湖先生集序》中论述了天才之文章与人力之文章:
文章有以天才胜,有以人力胜,出于人者可勉也,出于天者不可强也。今观贾谊、司马迁、李太白、韩文公、苏东坡,此数人皆以天才胜,如神龙之夭矫,天马之奔轶,得蹑其踪而追其驾。惟其才力难局于小用,是以亦时有疏略简易之处,然善观其文者,举其大而遗其细可也。若乃柳子厚专下刻深工夫,黄山谷、陈后山专寓深远趣味,以至唐末诸诗人,雕肝琢肺,求工于一言一字间,在于人力,固可以无恨,而概之前数公纵横驰骋之才,则又有间矣。故曰人可勉也,天不可强也[9]。
就文章而言,可以概括为“以天才取胜的文章”和“以人力取胜的文章”。就诗人和文学家来说,有“以天才胜”者,如贾谊、司马迁、李太白、韩文公、苏东坡诸人,他们才力大,难局于小用,所作诗文如“神龙之夭矫,天马之奔轶”,虽然因为才气贯通,行文有粗疏之处,但文章细节之处大可不必留意,所以朱熹评苏东坡文章说:“坡文只是大势好,不可逐一字去点检”[10]。有“以人力胜”者,如柳子厚、贾岛等,他们或专下深功夫,或专寓深远趣味,发展至晚唐,雕琢的功夫走向了极端化,工于一言一字间,气度窘促,诗失去了自然灵动的气质,后世诗人及诗论家对此种做法多有异议,如梅尧臣就在表明自己诗学立场的同时表达了自己不赞赏雕琢为诗的态度:“宁从陶令野,(公曰:彭泽多野逸田舍之语。)不取孟郊新。(公曰:郊诗有五言一句,全用新字)”[11]。谢尧仁对此显然也是持否定态度,同时他强调“出于人者可勉也,出于天者不可强也”,也认为“天与诗性”是天之禀赋的诗歌才能,非是后天模仿学习可达到的。
宋人不仅在诗学中论述“天性”,在书学中也强调“天性”,王禹偁说:“大篆小篆八分体,楷隶章草何纷纭。因兹八分各有要,遂使六艺区以分。其中最难惟草圣,玄妙功夫自天性”[12],“玄妙功夫自天性”是书学中的最高境界,一般书家难以模仿,更难以达到。可见“天性”论是宋代诗学中的重要论题,也是宋代文艺理论中的基本话题。
二 涵养:修身养才,真味发溢
诗人才性中有禀于天的层面,也包括品格、志趣、德性、修养、境界等后天可以涵养改变的一面,也即张载所说的“气质之性”。詹福瑞先生认为,作家的个性包括了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即先天的情性和后天的陶染两种类型。同时,先天的才情、气质与后天的学识、习染,虽然都是影响作品风格的因素,但是,先天的因素和后天的因素,在刘勰看来,是有内外之别和主次之分的。刘勰认为“‘才力居中’,对于创作与风格来说,才情气质属于作家主体的内在资质,在影响创作与风格的因素中,起着‘盟主’的作用,即主要的作用。而学识和习染则属于外在功力,在影响创作与风格的因素中,起着‘辅佐’的作用”[13]。而关于“天与诗性”与后天涵养孰轻孰重的问题,宋人似乎普遍持有与刘勰相反的观点,在宋人那里,他们认为诗人作家的品格、德性、志趣、艺术修养等相对于“天与诗性”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陆游《中丞蒋公墓志铭》说:
公天资警迈,七岁赋《牧童》诗,有奇思,遂精词赋。十四弃其业,习戴氏《礼》,期年辄通贯,诸老先生自谓莫及。一日,先生有欲勉成之者,期以间处,曰:“吾将有以发子。”公先时往,俟之甚谨,先生喜曰:“子诚可教。士当务学,才不足恃也。子于书,能博观而得要,则善;如其未也,当勉之。毋以才自足,蹈吾所悔。”公再拜谢。自是穷日之力,无所不读,人罕见其面。[14]
陆游所论显然是将后天的读书学习看作第一要务,不能自恃才华,而轻视了读书,应“博观而得要”。宋代诗人和诗论家对诗歌本质的认识决定了他们的诗学取向,诗歌天赋是诗人的重要素质,但宋人认为诗为“心之声”“天之义”和“文之精”,这就决定了诗人必须要重视品格的熏染、性情的陶冶和诗文品鉴能力的提升,这些才性的获得靠的都是后天习染,所以宋人更为重视诗人后天才性的涵养,这是宋代诗学中的普遍认识。
宋人论诗文书画都强调言为心声,将文艺与人的才性品格紧密联系在一起,如徐铉说:“睹其诗如所闻,接其人如其诗”[15]。欧阳修论书画也持有此种观点,“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16]。这也是古人所说的“文如其人”,吴承学先生认为“文如其人”说“其实包含了两个命题:一个是‘体’与‘性’即风格与创作个性的关系;一个是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前者探讨作家的气质、禀性、性格等个性因素对于文学风格的影响;后者则主要探讨作家的人格、情操、思想、品行等道德因素对于艺术品格的制约”[17]。其实在宋人那里,这两个命题都是综合而论的,都是诗人创作“才性”的表现,且诗人后天之才性还包括艺术鉴赏能力的熏染等层面。
宋代诗学“才性”论重视诗人的品格、胸襟、德性、修养、志趣等层面,它们是宋代诗学重视内省、人文、书卷和知识的主流倾向的直接表现。宋人论诗常强调诗人的品格胸次,如黄庭坚评苏东坡黄州诗云:“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18]杨万里也曾论及诗人胸次:“胸中磊块有余地,语下飘萧无俗气”[19]。胸襟旷达,胸次脱俗,笔下自然无尘埃,所作诗句自然飘逸不俗,耐人寻味。心境淡泊,超越功利,也是宋人养才的一种表现,刘克庄说:
和陶自二苏公始,然士之生世,鲜不以荣辱得丧挠败其天真者。渊明一生,惟在彭泽八十余日涉世故,余皆高枕北窗之日,无荣恶乎辱?无得恶乎丧?此其所以为绝倡而寡和也。二苏公则不然,方其得意也,为执政,为侍从,及其失意也,至下狱过岭,晚更忧患,始有和陶之作。二公虽惓惓于渊明,未知渊明果印可否?[20]
陶诗自然真淳,陶渊明本人也天真,陶诗的天真无关乎其人生仕途的荣辱得失,是其心境的真实流露。而二苏之类的和陶者,皆是在人生失意时才有和陶之作,他们的天真在一定程度上被世俗的荣辱得失影响。
诗人后天才性涵养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艺术品鉴能力的提升,宋人对待前人诗歌的态度是豁达的,而且善于通过熟读前辈诗家的诗作领悟其艺术精神,并获得艺术修养:
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之为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21]
择取唐前优秀的诗人诗作进行熟读,然后再反复含玩李、杜诗,最后博取盛唐诸名家诗作,熟读酝酿,在心中反复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于诗之精神气韵自然能深刻悟入。诗人的德性修养也是诗人才性的一方面,关于诗人德性与创作的关系是宋代诗学中集中关注的问题,且涉及宋代理学家的诗学观问题,这一点前人多有论述,在此没有必要再着笔墨详述。
诗人的才性、气质不仅可以通过涵养学习而改变,而且还会随着年龄的变化逐年而异,宋人对此问题开始广泛关注,且多有精金美玉之论。如吴曾《著述须待老》说:
前辈未尝敢自夸大。宋景文公尝谓:“予于为文,似蘧瑗。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之非。其庶几至道乎?”又曰:“予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梅尧臣曰:“公之文进矣,仆之为诗亦然。”故公晚年修《唐书》,始悟文章之难,且叹曰:“若天假吾年,犹冀老而后成。”南城李泰伯叙其文,亦曰:“天将寿我乎,所为固未足也。”类皆不自满如此,故其文卓然自成一家。善乎欧阳公之言曰:“著述须待老,积勤宜少时。”岂公亦有所悔耶?[22]
吴曾在此提出了“著述须待老,积勤宜少时”的理论命题,他认为随着年龄的变化,人的积累逐年增加,阅历逐渐丰富,气质涵养逐年提升,著述须等到老年才能有所作为。周紫芝《竹坡诗话》引苏东坡语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23]。为文渐老渐熟,随着人年龄的增长,才性涵养的功夫更加深厚,诗文创作才趋于平淡自然,这种平淡是豪华落尽后的真淳。当然也有诗论家认为诗人的才性逐年减退,如刘克庄就是这种言论的代表,他在《刘圻父诗序》中论述了这一现象:“文以气为主。少锐老惰,人莫不然。世谓鲍照、江淹,晚节才尽,予独以气为有惰而才无尽。子美夔州,介甫钟山以后所作,岂以老而惰哉?”[24]刘克庄认为文章灌注文人的才气,文人在年少时才性丰赡,气质锋锐,而随着年岁的增长,至老年则老懒颓惰,诗情减弱。这些都是宋人关于诗学才性、气质、修养功夫的独到思考。
三 书本:才有天资,学慎始习
诗人才性涵养的方法与途径是宋人广为讨论的话题,也是宋代诗学中极有价值的论题。他们认为诗思、诗情和诗才的获得需要丰富的阅历,自然和生活都能给诗人以诗材和诗才。陆游:“造物有意娱诗人,供与诗材次第新”[25]。杨万里:“红尘不解送诗来,身在烟波句自佳”[26]。都是指自然和生活供与诗人诗材,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诗人的诗思。文天祥也论述了这一问题,但他所说的从生活与自然中获得诗才的状态却不像陆游、杨万里那般悠然自得,放翁、诚斋所言是环境激发了诗人诗性,这种环境既包括自然的,也包括人文的,而文天祥所言则是类似于杜甫的“国破山河在”所激发的诗人的诗性:
自丧乱后,友人挈其家避地,游官岭海,而全家毁于盗。孤穷流落,困顿万状。然后崖山除礼部侍郎中,且权直学士矣。会南风不竞,御舟漂散。友人仓卒蹈海者再。为北军所钩致,遂不获死,以至于今。凡十数年间,可惊、可愕、可悲、可愤、可痛、可闷之事,友人备尝,无所不至。其惨戚感慨之气,结而不信,皆于诗乎发之。盖至是动乎情性,自不能不诗。[27]
国家丧乱,诗人的命运也随着国家的命运升降沉浮,数十年间,友人邓光荐经历了种种磨难坎坷,幸不获死,但国破家亡的痛楚和生活的磨砺充实了诗人的性情,所谓“可惊、可愕、可悲、可愤、可痛、可闷之事”都激发了诗人的诗才,不得不作诗以吐露感慨之气。
人生阅历和自然环境涵养了诗人的诗才,这些诗学观念也受到理学“气本论”的影响,但在宋代诗学中最受宋人推崇的还是书本。宋人推崇书本,以学养才,以知识写诗,以知识论诗蔚然成风,可以说宋代诗学和诗歌的知识化转向是宋人的主流意识。前面部分我们论述了天赋之诗性与后天涵养之诗才,宋前的诗学多重视诗人天赋,而到宋人这里出现了转向,亦即更重视后天涵养的诗才。这里我们要说的就是宋人不仅重视后天涵养的诗才,而且在后天涵养诗才的途径中,他们更重视以书本涵养诗才。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篇曾说:
夫才有天资,学慎始习。斫梓染丝,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难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沿根讨叶,思转自圆。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28]
刘勰认为文才一部分自天赋中来,但也要重视后天的学习,学习的途径就包括经典的阅读。而且他强调作家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性格特征培养适合自己的风格和诗才,这才是正确的学习道路。宋人的知识诗学的逻辑起点可以追溯至刘勰。
诗人阅读经典,储备知识为创作打下基础,诗人有无知识,在其诗作的语言和风貌上就可窥见:“僧祖可作诗多佳句。如‘怀人更作梦千里,归思欲迷云一滩’。‘窗间一塌篆烟碧,门外四山秋叶红。’等句,皆清新可喜。然读书不多,故变态少。观其体格,亦不过烟云、草树、山川、鸥鸟而已”[29]。诗僧祖可诗作佳句虽多,然变化却少,视野狭窄,诗材局限,诗思不展,这些都是因为其读书不多。诗人有无读书,读书多少,直接影响诗歌的艺术水准。
诗人通过读书培养诗才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涵养,一是诗歌艺术能力的培养,一是品格性情的陶冶。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艺术品鉴能力的培养需要遍览历代典籍,尤其是集部文献,宋前诗歌尤其是唐诗为宋人的诗歌阅读提供了大量范本,宋诗人可以从前代诗人的作品中汲取大量知识和艺术营养。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述及熟参前人诗以悟诗之做法的具体途径:
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独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尽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30]
阅读前人经典诗作,通过知识的摄入和艺术的熏陶,培养诗人“辨是非”的能力,这种辨别诗作品格的能力就是诗才的表现,这种才性获得的方法就是知识的涵养。而且严羽在此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步骤,方法是“熟参”,步骤就是循序渐进地学习汉、魏至本朝苏、黄以下诸家诗。读书涵养了诗人的艺术品鉴能力,成就诗人“下笔如有神”的艺术境界。但读书是为作诗而不是以书为诗,虽然江西诗派在这方面有所偏颇,但宋人在以书本为诗的问题上有所警醒和批评。范晞文《对床夜语》引萧德藻的观点云:“诗不读书不可为,然以书为诗,不可也。老杜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读书而至破万卷,则抑扬上下,何施不可,非谓以万卷之书为诗也”[31]。读书的目的不是以书为诗,而是培养诗人的才性和诗性,读破万卷书的过程就是涵养诗人艺术能力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诗人培养了自己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诗歌创作能力,这些能力的获得使诗人“抑扬上下,何施不可”。
读书不仅能提升诗人的诗歌创作水准,更能陶冶诗人的性情,涵养诗人的气质,这些都是诗人诗才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文人极为重视自己的知识素养,他们身上有着浓重的书卷气息和人文气质,读书是他们涵养气质的重要途径。唐代文人有着强烈的事功意识,他们读书的目的极为明确,那就是科举仕途,而且读书不是他们入仕的唯一途径,由此我们看到唐代文人壮游、隐居、出塞等各种复杂的人生经历。宋代文人地位崇高,他们读书心无旁骛,而且功利意识没有唐人那样强烈,这就造就了宋代文人的学者气和书卷气,从宋人身上我们能真切感知到“腹有诗书气自华”。晁补之《石远叔集序》说:“文章视其一时风声气俗所为,而巧拙则存乎人。亦其所养有薄厚,故激扬沉抑,或侈或廉,秾纤不同,各有态度,常随其人性情”[32]。诗人通过读书涵养学问和气质,学养深厚各异,故人的气质性情和诗歌风格也各异。关于读书与诗人气质的话题,黄庭坚有云:
予友生王观复作诗,有古人态度,虽气格已超俗,但未能从容中玉佩之音,左准绳、右规矩尔。意者读书未破万卷,观古人之文章,未能尽得其规摹及所总览笼络,但知玩其山龙黼黻成章耶?[33]
这里的“气格超俗”虽是指王观复所作诗的品格,实际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其人的“气格”。他从古人那里汲取营养,涵养出了古人的态度和气质,但是仍然为规矩所束缚,主要原因就是读书不够,气质的修养未到达一定的境界。
关于书本与才性的关系问题,宋人普遍认为才性能通过知识的摄入而得以涵养,宋诗学整体上呈现出知识化的倾向。知识和书本是才性获得的重要途径,它能提升诗人的艺术水准,更能陶冶诗人的性情气质,这是宋人诗学中的主流话语。关于知识与才性的话题,我们以黄庭坚的一段论述结束本节。
天难于生才,而才者须学问琢磨,以就晚成之器,其不能者则不得归怨于天也。世实须才,而才者未必用。君子未尝以世不用而废学问,其自废惰欤,则不得归怨于世也。凡为足下道者,皆在中朝时闻天下长者之言也。足下以为然,当继此有进于左右。[34]
天才不易得,更不易改变,有才能的人也须以学问和知识涵养才性,只有不断学习,以学问养才,以知识琢磨才性,才能成就一番文学事业,诗才才能通透无碍,才会达到“老夫不是寻诗句,诗句自来寻老夫”[35]的自由境界。
四 体性:宋人对风格与才性关系的思考
文学风格学是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它源远流长,理论精微,且富有特色,极具体系性。它既研究中国古代文学风格的类型,也探讨推动风格生成的诸种要素。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诗歌的风格类型,前人有精到的概括,如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将诗之风格概括为雄浑、冲淡、纤秾、沈着、高古、典雅、洗练、绮丽、自然等风格,且用形象的比喻对这些风格进行阐述,他在解释“冲淡”这一风格概念时说:“素处以默,妙机其微。饮之太和,独鹤与飞。犹之惠风,荏苒在衣。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36],这种阐发完全是自然的、诗性的。关于风格生成的问题,其因素繁多且复杂,从创作主体看,诗人的气质、才思、性情、品行,以及外在的阅历、见识、书本、修养、学识都是影响风格的重要因素;从外在层面看,历史背景、时代、地域、自然环境、迁谪、社会风俗、语言形式、思维传统都对风格的形成造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诗是诗人作出来的,不管是诗人的自然流露,还是其刻意雕琢,都是其心灵的反映,所以诗人的才性是影响诗歌风格的重要因素。曹丕以“气”论文,他在《典论·论文》中云:“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37]。他又论述了建安七子不同的“文气”,亦即文学风格,曹丕“文气”论实质是由论作家才性进而论文章风格的风格论。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专门讨论风格与作家个性的关系,关于《体性》篇之“体”“性”的具体含义,历来说法不一,但“体性”是风格论,已无异议。詹福瑞先生在总结了“体”“性”的不同解释后指出:“‘体性’是论述风格与个性关系的理论”[38],个性中包括作家之才性,所以我们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宋人对风格与才性关系问题的思考和论述上,通过材料的梳理归纳出宋人的独特观点。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虑周而藻密;仲宣躁竞,故颖出而才果;公幹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俶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39]
“才力居中,肇自血气”,詹锳先生对此条疏证云:“《事类》篇:‘才自内发,学以外成’。风格变化的出发点是人的才力和气质。而各人才力的不同,又源于不同的气质。‘血气’,即先天的气质。‘居中’是说居于内心。《朱子全书·性理》中解释道:气一也,主于心者,则为志气;主于形体者,则为血气”[40]。诗人的才性、气质促进了风格的形成和变化,作家才性、气质不同,其风格自然各异,所以詹福瑞先生说:“文学作品既然是作家情志的表现形态,那么作家个人先天的资质与后天的修养,必然会影响到他的创作,造成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貌风格”[41]。这就揭示了作家“才性”与风格的密切关系。
才性影响诗人的体裁选择,才性各异,诗人所擅长的体制不同,体制不同的诗歌所具备的艺术质素和风格也不同,这是宋代诗学中时常论述的一种现象,“老杜之诗,备于众体,是为诗史。近世所论,东坡长于古韵,豪逸大度;鲁直长于律诗,老健超迈;荆公长于绝句,闲暇清癯,其各一家也。然则荆公之诗,覃深精思,是亦今时之所尚者”[42]。杜甫才性宏赡,兼备众体,是诗史上集大成的诗人,而对大多数诗人来说,兼备众体并不容易,他们多根据自己的才性和才力选择最为擅长的体裁来表达自己的情志,如东坡于古韵为胜,豪逸大度,潇洒出尘;鲁直长于律诗,学问精微,事理深刻;荆公心仪绝句,自然灵动,清癯绝俗,他们都特点鲜明,自成一家。这样的诗学观念在宋代并非孤立特出,杨万里由“文难”说,引出“诗文难兼善”的话题,进而论述文人才性与体裁选择及诗歌风格的关系。他在《石湖先生大资参政范公文集序》中说:
甚矣,文之难也。长于台阁之体者,或短于山林之味;谐于时世之嗜者,或漓于古雅之风。笺奏与记序异曲,五七与百千不同调。非文之难,兼之者难也。至于公训诰具西汉之尔雅,赋篇有杜牧之之刻深,《骚》词得楚人之幽婉,序山水则柳子厚,传任侠则太史迁。至于大篇决流,短章敛芒;缛而不酿,缩而不窘。清新妩丽,奄有鲍、谢;奔逸隽伟,穷追太白。求其只字之陈陈,一唱之呜呜,而不可得也。[43]
文之难,在于文各有体,体裁不同,其要求具备的才性也不同,台阁之体与山林之味,嗜于时事与古雅之风,所要求的文人素养不同,偏重于一种文体较为简易,但兼备众体很难做到,只有杜甫这样的大家才能达到集大成的境界。进而他又称赞范成大能兼备众体,风格多样,训诰、赋、骚体、序、传、诗等文体都渊源有自,诗也能兼善大篇和短章,且风格清新妩丽如鲍谢,奔逸隽伟追太白。
才思敏捷也是才性富赡的一大表现形态,诗人的才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才思,有的诗人援笔成章,下笔千言,有人则含笔腐毫,闭门觅句,才思敏捷之人所作的诗自有一种风神形态。严羽论李白之才思云:“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卒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44]。李白才思敏捷,诗句脱口而出,率然而成,率然既是一种作诗状态,也可视为一种诗歌风格,于李白而言率然而成的诗必定是潇洒飘逸、自然圆融的,观李白诗要识得此种特点。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专论作文迟速的问题:
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二公盖亦互相讥嘲,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雕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缜密也。昌黎志孟东野云:“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言其得之艰难。赠崔立之云:“朝为百赋犹郁怒,暮作千诗转遒紧。摇毫掷简自不供,顷刻青红浮海蜃。”言其得之容易。余谓文章要在理意深长,辞语明粹,足以传世觉后,岂但夸多斗速于一时哉!山谷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世传无己每有诗兴,拥被卧床,呻吟累日,乃能成章。少游则杯觞流行,篇咏错出,略不经意。然少游特流连光景之词,而无己意高词古,直欲追踪《骚》《雅》,正自不可同年语也。[45]
李白援笔成章,一斗百篇,杜子美则“新诗改罢自长吟”,才思敏捷状态下所作的诗会率然而欠缜密,以一丝不苟的态度作诗则会陷入雕镌的窠臼,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两种状态下所成的诗歌也会有风格上的差异。这种作文迟速异分的现象在诗人中极为普遍,孟东野的苦吟、崔立之的率意,秦少游的对客挥毫、陈无己的呻吟累日,都是这两种创作状态的典型。对于才思的迟速问题,罗大经显然持客观的态度,他并没有将两种创作状态加以优劣之分,而是认为这两种创作状态下所成的诗歌各有特点,甚至认为才思迟钝的诗人经过反复苦吟雕琢反倒能成佳篇,风格也能近于古人,如秦少游才思敏捷,多流连光景之词,陈无己虽才思迟钝,却意高词古。评价诗作高下的标准不是作文之迟速,而是要着眼于诗作本身的风格、风貌,“理意深长,辞语明粹”之作才足以传世。
诗歌风格与诗人的才性关系密切,才性不同,诗人的体裁选择就不同,每种体裁本身就具有固定的风格,所以在这一层面上才性对风格会加以影响,同时诗人的才性、气质也会灌注于诗作,并直接呈现在诗歌风格上,如“阮嗣宗诗,专以意胜;陶渊明诗,专以味胜;曹子建诗,专以韵胜;杜子美诗,专以气胜”[46]。才思作为才性的一大表现形态,其迟速也对诗歌风格产生影响,才思敏捷的人诗作多率意自然,才思迟缓的人诗作多雕镌缜密,这些都是宋代诗学中所反复论及的问题。
“才性”论发展至宋代,概念逐渐厘清,其诗学意义也逐步被发现,成为宋代诗学中的一个时代性话题,更成为中国诗学中的一个核心论题。宋代理学“理”“气”“心”的探讨影响了诗人和诗论家的思维,且有了从哲学高度创建文学本体论、作家论和风格论的萌芽,宋代诗学广泛探讨诗人“才性”,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张载“气本论”哲学的影响。虽然前代诗论家也关注了“才性”,但宋代自有其特点,一是宋前的“才性”观杂糅了政治才性与诗学才性,二者界限不明,甚至在唐代这两种“才性”还难以分辨,但宋人却极为明确地将文学“才性”分辨清晰。二是宋人诗学中开始广泛讨论“才性”,这是前代所不可比拟的,这一现象是宋代诗学史值得关注的。到元明清时期,尤其是明清诗学,“才性”论的话题更成为核心话题,这些都是宋代诗学“才性”论在元明清诗学中的展开和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