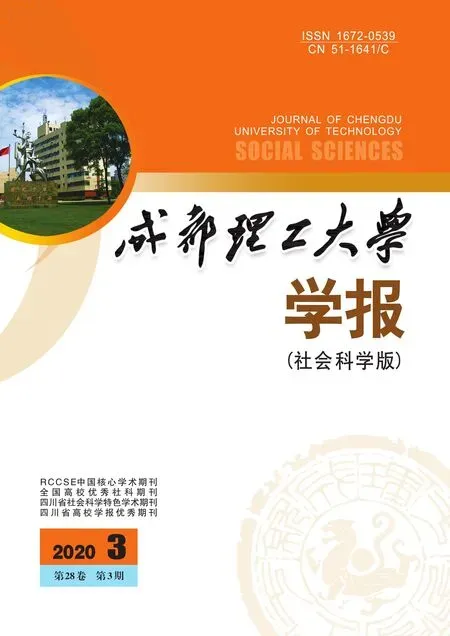论海德格尔对康德想象力概念的解释
冯 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191)
一、康德的想象力概念与海德格尔的解释
康德认为,想象力是一种综合能力。他在第一版《纯粹理性批判》中说:“想象力是一种先天综合的能力,为此缘故,我们赋予它生产的想象力的名称;就它在显象的一切杂多方面无非是以显象的综合中的必然统一性为自己的目的而言,这种必然的统一性可以被称为想象力的先验功能。”[1]140接着又说:“我们有一种纯粹的想象力,它是人类灵魂的一种先天地作为一切知识之基础的基本能力。”[1]141《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共提出了两种想象力:一是再生性想象力;二是生产性想象力。再生性想象力属于经验性想象力,对感觉杂多进行综观;生产性想象力属于先验想象力或超越论想象力,对知识进行综合。生产性想象力是再生性想象力何以可能的根据。
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感性结构、知性结构之根据是先验想象力结构,感性能力、知性能力之根据是先验想象力。康德说:“人类知识有两个主干,它们也许出自一个共同的、但不为我们所知的根源,这两个主干就是感性和知性。”[1]47“从我们的认识能力的总根分杈并长出两个主干的那个点开始,这两个主干的一个就是理性。”[1]542海德格尔援引康德的这两句话,认为康德已经意识到感性和知性有一个共同的来源,即想象力。
康德哲学要解决一个形式与质料结合的问题,也就是概念何以能和直观结合,或统摄直观。康德提出,要由先验图型作为中介才可以实现结合。先验图型既有概念形式的一面,又有图像质料的一面。概念经过图型的过渡或规定获得与直观的同质性、相近性,从而合法地统摄直观。由先验想象力构造先验图型以便将概念和直观结合,从而解决了形式—质料二分的问题。“必须有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同类,另一方面必须与显象同类,并使前者运用于后者成为可能。这个中介性的表象必须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经验性的东西),并且毕竟一方面是理智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这样一个表象就是先验的图型。”[1]148在第二版《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改变了想象力的职能。他将想象力归属到知性能力。康德这种做法会产生一个问题,即中介的合法性何在。想象力不仅具有知性的特点,还具有感性的特点。归属于感性、知性二者任何一方都无法说明其具有的兼容特点。同时,如果想象力属于知性,先验图型作为想象力的产物,也要归属于知性。按照这里中介的特点,它不能属于两方的任何一方,而且还要跟两方都有联系。所以,中介只能来源于第三方,这样才有资格作中介。假如图型来自知性,图型就不是第三者了,也就失去了作为中介的合法性。因此,形式和质料二分的问题就会重新出现,继续追问知性概念何以应用到感性直观?它的合法性在哪里?
海德格尔认为,康德将想象力作为直观和知性的共同来源,不仅是对二元论的否定,也是对泛逻辑主义的否定。想象力作为共同根,“这样做本身就大大动摇了理性和知性的统治。‘逻辑’被除去了自古以来就在形而上学中形成的优先地位。”[2]264但是,当想象力被归属于知性之后,知性、逻辑得以继续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在德国唯心论中开始的反对‘物自体’的争斗,除去意味着对康德所为之奋争的事业的越来越多的遗忘之外,还能意味什么呢?”[2]265
二、想象力何以作为直观、思维的共同根
海德格尔将康德的想象力解释成直观和思维的共同根,这种说法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模型。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和质料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较低级的形式会成为较高级形式的质料,依此层层递进。通常认为,康德将直观和思维严格划分,认为直观是接受性的,思维是自发性的。直观和思维结合构成了知识,所以康德是二元论的认识论。当把康德解释为严格的二元论时,就等于严格划分了形式和质料,而不是相对地划分形式和质料。海德格尔解释下的康德想象力概念一定程度上回到了亚里士多德将形式、质料看成相对地这种说法。形式也是质料,质料也是形式,是不可分的。因此,时间空间相对于感觉杂多是形式,而相对于范畴就是质料,范畴就是更高一级的形式。形式和质料是有层级性的,没有一个东西孤立的就是形式或质料,而是看相对于谁。当对形式和质料不做严格划分而是在相对的意义上来看时,形式和质料就是同一物的不同表现。在这里,思维和直观就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形式和质料关系,其各自内部又是层级性的形式和质料关系。海德格尔在这个意义上,将直观和思维看作想象力共同根生出的两个枝。“思维和直观,尽管有所区别,但绝非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那样分别开来。相反,两者都作为表象类的东西属于表—像之一般的种。”[2]162
三、想象力与综合、统觉的关系
根据康德的定义,想象力首先是一种先验的综合能力。对先验想象力的根基地位进行解释,需要说明想象力与综合的关系。康德说:“我们的思维的自发性要求这种杂多首先以某种方式被审视、接受和结合,以便用它构成一种知识。这种行动我称为综合。但是,我在最普遍的意义上把综合理解为把各种不同的表象相互加在一起并在一个认识中把握它们的杂多性的行动。如果杂多不是经验性地、而是先天性地被给予的(就像空间和时间中的杂多那样),那么,这样一种综合就是纯粹的。”[1]91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要解决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因此,综合是关键。“如果我们想对我们的知识的最初起源作出判断,综合是我们首先应当予以注意的东西。”[1]92所以综合本身的来源问题,就是全书的一把钥匙。海德格尔援引康德给出的答案,“一般的综合纯然是想象力亦即灵魂的一种盲目的、尽管不可或缺的功能的结果,没有这种功能,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根本不会有知识,但我们却很少哪怕有一次意识到它。”[1]92所以,综合来源于想象力,先天综合判断以想象力为根据。
海德格尔以统觉与纯粹综合的关系,给出了想象力与统觉的关系。他认为,统觉是纯粹综合的一种自身同一性表象或原则,其来源于纯粹综合,也意味着其来源于想象力。“纯粹综合,就其在纯粹综合中表象出来的统一性而言,将自己带到了给予它自身统一性的概念那里。”“在康德那里就表现为:他在直观与知性的粘—合中,明确出纯粹综合的自身同一性。”[2]74“纯粹统觉提供了一切可能的直观中杂多的综合统一性的原则。但是,这种综合的统一性以一种综合为前提条件”“想象力的纯粹的(生产的)综合之必然统一性的原则先于统觉而是一切知识的可能性的根据”[1]137-138。在海德格尔看来,统觉是综合表现出来的统一性原则,而综合又来源于想象力。因此,想象力始终是优先于统觉的。
四、想象力与智性直观的关系
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海德格尔反复提到源始性直观,即智性直观。康德的这个特殊的概念让海德格尔的想象力解释陷入了困境。根据康德的定义,智性直观是“一种本身就使得直观的客体的存在被给予的方式”[1]73。康德认为,智性直观是源始性直观,是不依赖于客体的直观,这种能力属于神。也就是说,不需要外界提供杂多质料,自己就能产出杂多质料,天然就有直观形式和直观杂多。这种智性直观是不需要物自体的,因为不需要物自体去提供刺激。人的直观是派生性直观,是只有在受到客体刺激时才能为主体所表象的形式。海德格尔也认为,智性直观属于神的认识。他指出,神的认识活动是无限的直观,人的认识活动是有限的直观。因为人本身有思维,他的直观是有思维的直观,而思维就意味着要受到限制。相反,神是不需要思维的,直观就是全部的认识本身,“神的认知就是这样的表像活动,此表像在直观中首先创造出可被直观的存在物自身。但是,因为现在此表像活动完全先行地、通透地、直接地在整体上直观存在物,就不需要思维。”[2]33
但是,当海德格尔将想象力作为直观和思维的共同根之后,想象力就被提升到了智性直观的地位。
海德格尔虽然认为人是有限性的直观,无限性直观只能属于神。但是,当他为有限直观做出可能性演绎时却出现了矛盾,“有一有限性的本然存在者,它本身受制于存在物并依赖存在物的领受状态;它也并非存在物的‘创生者’,但它如何能够在所有的领受状态之先,就可以认知,即直观存在物呢?”[2]48“作为认知,超越论的综合必须是一种直观,而且作为先天的认知,它必须是一种纯粹的直观。作为隶属于人之有限性的纯粹认知,纯粹直观必然通过某种纯粹思维来规定自身。”[2]53那么,这种直观到底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是不是意味着,人的有限直观可以来自于人自身的自由因素、无限性因素。因此,无限性直观不仅仅是属于神呢?最后,海德格尔只能得出与自己之前不同的结论,“纯粹直观必然在某种意义上是‘创生性’的。”[2]54“出于其本己的可能性,关于存在物的有限性认知就要求有某种尚未—领受的(似乎非—有限的)认知,就像是某种‘创生性的’直观一样。”[2]48这种非有限的、创生性的直观就是想象力。
想象力具有感性、知性的双重特点。它非但不从属于二者,二者反而要以想象力为根据。当认为想象力可以直观,并且可以不需要物的在场就可以创造性的直观时,想象力事实上已经成为智性直观了。因此,可以说康德的智性直观不是神才具备,人也同样拥有。智性直观就来源于先验想象力。从字面上分析智性直观可以看到,智性直观一说来源于知性形式和感性质料的结合,直观不仅有感性的接收性一面,还可以有知性的自发性的一面。这种自发是创造性的,可以自己创造质料,无需外界的给予。因此,在想象力这一点上,人的自由是与神比肩的。神想要有光,便有了光。人的自由体现在想象力上,就可以是人想象有光,便有了光。
因此,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康德想象力概念就是一种源始性直观,即智性直观。
五、海德格尔重新解释康德想象力的目的
海德格尔将康德的想象力作为直观和知性的共同根,对康德的二元论进行了一元论解释。“康德的形而上学奠基活动引导走向超越论的想象力。而超越论的想象力是两大枝干——感性和知性——的根柢。超越论想象力本身使得存在论综合的源初性统一得以可能。”[2]219-220他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主题是为形而上学进行存在论奠基,而想象力是这种奠基活动的根据。并且,以往对康德的认识论解释,即由认识符合对象转变为对象符合认识的“哥白尼式转向”,是对康德的误读。所以,海德格尔提出了“哥白尼式转向”的存在论解释。
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一书中,海德格尔试图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解释成一种为形而上学奠基的活动。他认为,康德的这种奠基是基础存在论意义上的奠基,而基础存在论是一种对人的有限本质的分析,是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他认为,只有建立这种人的此在的形而上学才会为形而上学的可能提供根据。海德格尔反对对《纯粹理性批判》做认识论的解释。他认为,应该将康德“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追问回溯到存在论的本质上。并且,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有自己的定义。他认为,形而上学是对一般存在物和对存在物整体的认知,其研究对象是普遍的存在物和最高存在物。海德格尔关注的不是经验意义上的特殊存在物,而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存在本身。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海德格尔对这个问题本身也进行了存在论的改造。他认为,“在存在论认知中,这一被知晓的存在物的‘是什么’,在所有存在物的经验之前——虽然正是为了这些存在物的经验——就已被先天地提供了出来。康德将某种提供出存在物的‘实质内容’的认知以及那显明存在物自身的认知,称为是‘综合的’。这样,对存在论认知的可能性的发问就变成了去疑问先天综合判断的本质。”“形而上学奠基作为存在论之本质的暴露,就是‘纯粹理性批判’。存在论的认知,即先天的‘综合’,也就成为‘那整个批判所真正要达到的’东西。”[2]22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哥白尼式转向”不是对“认识—对象”符合论认识论的颠倒,而是将形而上学的研究从着重于经验的存在物转变为存在本身。他认为,对存在物的认识并不重要,因为这是经验层面的表象;重要的是存在物何以作为存在物而被认识,即存在物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存在论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存在论的认知提供了存在物层面上的认知的可能性。并且,从存在物到存在的这种转向才是康德“哥白尼式转向”的真正含义。“存在物层面上的真理势必要依循存在论的真理来调整方向。这是重新对‘哥白尼转向’的意义所做的一个正确解释。”[2]26
海德格尔的解释说,康德以此项工作,即从对存在物的认识转变为存在物何以作为存在物的存在论认识,为形而上学进行了奠基活动。海德格尔这样解释的目的是想要建立此在的形而上学一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