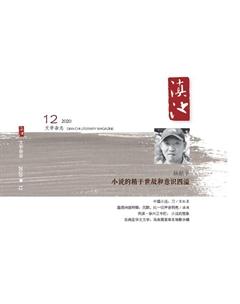大飞机
洪放
车罱子站在桥边上,他离桥大概三米。对面,是柏延,比他大一岁,上柏庄人。车罱子是下柏庄人。虽然都是柏庄,但一上一下,隔了有三里地。连接他们是伊洛河。伊洛河四季有水。上柏庄与下柏庄一左一右错落在河的两岸。上下柏庄人几乎都姓柏,因此,也几乎都连亲带故,关系大致出不了五服。上下柏庄的孩子都在柏庄小学读书。柏庄小学坐落在下柏庄的最下端。所以,整个上下柏庄的孩子们,上學放学,都得经过下柏庄。下柏庄的孩子自然直接回家。上柏庄的孩子再过柏庄桥回家。柏庄桥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伊洛河流到柏庄桥这会儿,大概河面宽有五十米。而且产生了上下两米左右的落差。地势突然向下,令河水猝不及防。早些年,这说的早些年,不是一般的早,而是很早很早了。上下柏庄的人都没见过的早。早些年,庄子里的先人们发狠,在河里筑坝,两边同时开筑,往中间合拢。到了中间,留下一丈五左右的空档,上面架桥,底下流水。这桥也同样早,一长块白条石,最宽的地方两尺,最窄的地方一尺二寸。要是赶上现在,说不定这桥早就被拆了。太窄,不安全。但那时候,上下柏庄的人竟然都没意识到。他们天天打桥上过,连上学的孩子也从桥上过。而且过的速度,一点不比在平地上走时慢。大家眼睛里,似乎没有桥。桥成了路的一部分,虽然那么窄,但打从它建成起,也没听见说有人从桥上跌下来过。要是真跌下来,那可是天大的危险。桥下河面也是铺着青石条,长年被水冲洗,光滑滑的,生满青苔。再下面是河潭,据说有三丈深。这里倒是真的淹死过三个人。一个是摸鱼淹死的,另外两个是妇女,跟家里人置了气,寻死的。农村里,只要有塘水的地方,哪有不淹死人的理?所以,死了三个人,也不见得这河潭上就有鬼气。日头白晃晃的,大家照样你来我往,潭里也偶尔有人摸鱼。一个猛子钻下去,好一会儿才出来,手里提着摆着尾子的鲢胡子。这情景也只有夏天才有,到了秋天,更别说冬天和春天,潭水古怪地冷,扎骨。没有人再敢下潭,虽然经常大清晨的,潭面上升起白雾。但那是冰雾,有些是冰溜子融化了的。反正那气也是极寒。过桥的人倘若走慢了,被那气给缠上,回家少不得大病一场。庄子里大人小孩,于是过桥总是迅速。仿佛后面被什么追着一样,过了桥,便松了口气。过了桥,是下柏庄的老樟树,三百年了,冠盖比小学校的操场还大。树上时不时有人缠上红布,还偶尔有香油,纸灰。这都是封建迷信,可在上下柏庄,大家都信这个。孩子丢了魂,到树下来喊;哪家大人要出远门了,到树下来许个愿儿。还有那些眼看着就要上山(老死)的人,也会撑着来树下坐会儿,用枯瘦的手摸摸树身,流两行浊得不能再浊的老泪。桥首的上柏庄,桥边上早些年是座茶亭。解放后拆了。现在是大队部。大队部三间房子,中间房子门前安着个喇叭,主要是传达指示,安排农活。有时,也兼作寻找孩子。大喇叭里,如果是村支书的声音出来,就一定是指示;村主任声音出来,大半是安排活计;如果换了上下柏庄哪家女人的声音,多半是孩子没归家,找不见,便通过大喇叭来找。这喇叭声音覆盖着方圆四五里,就连伊洛山上洞里的岩石也都能听得见。猫着没归的熊孩子,自然也能听见。听见了,就忙跑着归家。归了家,大喇叭便没了声音。
现在还没到归家的时候。正是正午。又是周日。车罱子问柏延:柏皮怎么还没来?这拖鼻涕的,做事磨蹭。
柏延说:他得看弟弟。过一会儿就会来的。
柏皮跟柏延都是上柏庄人,堂兄弟。车罱子也不姓车,同样姓柏。他爷是大队书记,他出生后,他爷骑着自行车,把他放在车罱子里带回了柏庄。于是,他就落了个车罱子的小号。上下柏庄的人都这么称呼,也没觉得跟大名有什么区别。在学校里,他叫柏为民。大名字,总得有点意义。不过很少有人喊他柏为民,就像庄子里很少有人喊香樟树叫香樟,而是喊神树。
我总觉得有事。车罱子抓着头发咕哝着。
啥事?大白天,见了鬼?
不是见了鬼。我总觉得有事。
车罱子和柏延在等柏皮,他们商量好了,三个人待会儿要做件想了很久的事情——骑着车子过桥。
这可是个大胆的想法。不过,在上下柏庄,有这想法的人还真不少。当然,付诸实施的人也还真不多。一来是上下柏庄自行车也就两部,一部是车罱子的爷——大队支书的。那是公家的东西,一般的人摸不得。另一部是下柏庄柏翠花男人的。她男人是邮递员,自行车被刷成绿色的,连着三个袋子。这人面色漆黑,一大早出门,掌灯时才归家。所以,骑着自行车过桥的想法,上下柏庄肯定会有。但真的能骑上自行车过桥的人,到现在为止,也没见一个。当然,柏翠花说她见过。她见过她的男人,也就是邮递员骑着车子过了伊洛河桥。那是他们相亲的日子,柏翠花一开始没相中这个漆黑的男人。男人也没磨蹭,出了下柏庄就往上柏庄走。他得去给村支书也就是车罱子的爷送报纸。大概是心里窝着气,或者有些羞恼,他骑着绿色的自行车经过神树,直接上了连接桥的河坝。一般情况下,上了河坝再踩几圈,就得下来推着车子过桥。但那天,这个漆黑面孔的邮递员,没有下车,呼啦一下骑着车子过了桥。
那个快!我还没眨完眼睛,他就过去了,就到了大队部。柏翠花说她当时正站在神树下,准备将邮递员带给她的雪花膏还给他。她就看见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过了桥。就那一骑,一过,她改了心,回家说:我得嫁他。娘骂她,说这多丢面子,刚才才回了人家的。她说:那我不管。我就得嫁他。这桩婚事就这么定了下来,如今儿子都打酱油了。不过,庄子里有很多人都怀疑,说柏翠花是找借口,关键是想追回邮递员。他们的理由也很充足:这以后,再也没有人看过邮递员骑车过桥。庄子里有人撺掇邮递员,这漆黑的男人死也不肯,还说骑车上桥一生只能有一次,那是给他老婆看的。这理由很堂皇。庄里几个年轻人,曾专门到桥头上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又通过初中数学和物理原理,一再证明骑着自行车过伊洛河桥,不亚于上天。桥太窄,车子摇摆之中,掉入桥下的概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九。他们不相信漆黑的邮递员会那么幸运,而且,如果他真的能骑车过桥,那么,他就该在上下柏庄人面前大方地骑一回。好在这些计较也都是玩玩而已。没有自行车,谁就无法实验。有自行车的人,拿准了不会干这要命的事情。
柏皮却突然有了这想法。柏皮十三岁,比车罱子大两岁。柏皮也是听柏翠花说她男人骑着车子过了桥以后,突然就产生了要骑车过桥的想法。有些想法,说怪就是怪。早不来,晚不来,天晴不来,下雨不来,偏偏就在这三个愣头少年躺在草皮毯上时到来了。头天是星期六,三个人边放牛边在草皮毯上说话。说着,说着,就说到这想法。车罱子说我爷到县里开会去了,车在家里。明天中午吃了饭,我将车子推过来,大家骑着过桥。柏延说这过桥的事,上下柏庄就邮递员骑过,我们来骑,怕不会……柏皮推了他一把,说:不骑哪知道?先推着车子过桥,推两遍,不就熟了?车罱子觉得有理,说:我一个人在院子骑过车子,简单得很。那车子自己会跑,只要手把住方向,就不会变道。邮递员能骑过去,我就能行。
自行车放在队部的办公室里。中午,队部没人。车罱子昨天晚上已经从爷爷抽屉里找出了办公室钥匙和车子钥匙。此刻,只要柏皮过来了。三个人就会开始实施他们的想法。
正午。风是热的。下柏庄的神树,竟然冒出了一缕青烟。柏延指着青烟,说:庄子里又要死人了。这是伊洛河两岸古老的说法,神树冒烟,人要升天。车罱子皱着眉头,想了想,说:想着没有看上去要死的人。哪是谁呢?估计他自己也看不到这烟。亚先生都说:要死的人,是看不见神树的青烟的。不过,亚先生也早死了。前年冬天,他喝酒过后,冻死在神树下面。第二天早晨庄子里的人发现时,亚先生已經成了冰砣子。
不说这些了。柏皮来了,车罱子喊道:柏皮,怎么磨蹭到现在?
我妈让我看弟弟。柏皮说。柏皮有三个弟弟。都是混蛋。柏皮是他们家孩子中唯一一个明白的孩子。三个弟弟整天哭哭啼啼,脸红得像灯笼。柏皮有一次狠着心对车罱子说:真想捏死他们。连笑都不会笑的三砣肉,一吃一大碗。我不知道我妈为什么要留着他们,现在好人都吃不饱,还留着傻子……唉!
话是这么说。柏皮也没真的去下手。他走过桥头,下到坡里。问车罱子:都弄好了?
弄好了。
那就干吧。
我有点怕了。
怕?车罱子,昨天不是你说的一点也不怕。不就是这丈把长的桥?你推车来,我来骑!
你骑个啥?都跨不到车上。
我天生会。不就两个轱辘,脚一踩,它就跑。有什么难的?
柏延出来打圆场,说:别斗嘴了。车罱子,你到底还弄不弄?
这……还是弄吧。车罱子捏着裤腰里的钥匙,手有些出汗。他说:我先去队部。推了车,踩几圈,再过来。
车罱子上了坡,沿着坝顶,往队部走。走了一半,他回头看了看桥。桥如同一条蛇,突然翻滚了下。这让车罱子吓出一身汗。他停住脚步,再看。桥又不动了。桥还是桥,青灰色的,两尺宽,架在伊洛河上。河水不大,因此就没有初夏时节轰隆隆的声音。车罱子往前走。队部门关着。其实是虚掩的。这车罱子清楚。大队部是伊洛河上下柏庄的中心,爷说这队部就是伊洛河的中南海。中南海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换句话就是:队部就是上下柏庄的政治中心。亚先生在世时,曾说这是皇宫。老先生因此被批斗了三天。新社会哪还能提那些封建的东西?这
理连车罱子、柏延他们都知道。可偏偏上下庄子读书最多的亚先生犯了这个忌。亚先生被批斗时,脖了上挂了块大匾,上面红笔写着:封建残余。亚先生驮着这匾,从桥上走过去。他走得慢。据说走这桥,他足足走了一袋烟的功夫。后来庄子里有人说:桥上从此没了蚂蚁,都被亚先生给踩死光了。
不管是皇宫也好,还是中心,或者爷所说的柏庄的中南海,此时,门是虚掩的。队干部也都回家吃饭去了。车罱子贴近队部,他像电影里侦察员一样,机警地朝门缝里看了看。果然没人。他“吱呀”一声推开门,往左首,就是办公室。他一眼就看见爷的自行车。红绸子布还系在车把子上,车子被爷擦得锃亮。他上前像爷一样先是拍了拍坐凳,再拿出钥匙开锁。“啪哒”一声,清脆,明亮,利落。甚至有些动人。车罱子并没有立即推车,而是又用坐凳下面的抹布将坐凳细细地擦了遍。这一切的程序,都来自于爷爷。他不能避免,也不能偷工减料。这毕竟是爷爷的自行车,爷爷是柏庄的书记,那么,爷爷不也就相当于……车罱子被自己这想法又吓了一跳,赶紧回过神来,推着车子,就往门外走。门坎有半尺高,他得先是跟爷爷一样,用手托起车把,车前轮就过去了。然后再用手拉着车后杠,后轮上了门坎,再一用力,滑哧,后轮就出了门。一出门,正是个斜坡。车子立马像被三头猪拉着,往前奔走。车罱子的手有些把握不住了,他跟着车子,往前飞跑。终于,在到达大坝时,车子被一块石头给挡翻。车罱子也随着车子摔倒地上。那边,柏皮和柏延正站在桥头上,一见这阵势,赶紧过来,扶起车罱子,问:没事吧?没摔坏吧?
没事。就是那该死的石头。车罱子脸通红,左腿有些痛。他也不好说出来。他起身,柏延和柏皮已经将车子给支起来了。柏延又拍拍车罱子身上的灰土,说:要不行,就算了。咱不过桥了。
谁说不行了?我爷以前骑过的。我爷行,我就行!可是,庄子里没人说你爷骑过。倒是邮递员……别提他黑鬼!车罱子问柏皮:你把那
件事先说了,我就骑。啥事?柏延凑上来。没你的事。车罱子靠近柏皮,说:你
不说,我就不骑。
柏皮用衣袖擦了下鼻子,那衣袖已变得硬邦邦的灰亮着。他说:我想了想,还是不能说。
怎么就不能说了?刚才神树都冒烟
了,是不是说了就要死人?那倒不至于。那怎么不说?说吧,说了,我就骑车
过桥。保证一次成功!那……说吧!那好,我可说了。前儿天中午,我牵
牛回家,路过队部。队部门掩着。我就走过去,朝里看了看。你说:我怎么那么背气,就看见了……
看见什么了?看见你爷……我爷?就是。就是书记,正压在柏翠花的身
上。柏翠花躺在地上,两只脚乱蹬,嘴里还在哇哇啦啦地叫唤。你怎么这么胡说呢?车罱子气红了
脸,上前就打了柏皮一拳。
柏皮先是定定地看着车罱子,忽然就“哇”地一声哭了,说:我说不讲,你非要我讲。讲了,你又打我。我看的都是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反正不是好事。我回去给我妈说,我妈说那是配种。
配你妈的种!车罱子再次打了柏皮一拳,柏延过来拉住,说:都别扯了。我们还得骑车过桥。车罱子,柏皮可是说了,走,过桥去!
柏皮收了哭。车罱子掌着车把,柏延扶着车后杠,柏皮跟着,三个人下了坝,走到桥前。桥下流水声音不大,正午的上下柏庄,有些静。人声都被热回了屋里,而蝉声却使这静,更静了。
骑吧!柏延望着车罱子。
这……我得推车回到那边,要借点势子。
有道理。
车罱子又推着车子回到队部门前,这回他掌握了技巧,带着刹车,脚踮起来,踩起脚踏,自行车速度加快,往坝子上冲来。眼看着就到了桥边,柏皮和柏延早分开站在两边上。车罱子突然刹了车,刹车的尖叫声,让人生疼。车子離桥半米,车罱子手心都是汗水。柏延问:又怎么了?
我想着柏皮刚才说我爷,我就生气。车罱子说:柏皮,你怎么能说我爷呢?他是大队书记。书记,你知道吧?
知道。书记。全大队的人都得听他的。可是,他真的把柏翠花压在身子下的。我看得清楚,柏翠花还朝我笑了笑。
你……车罱子又想上前打一拳,可是车子正好隔住了他和柏皮。他说:我爷怎么会压人?再说那地上,也都是灰土。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柏皮不说了。
柏延道:快骑吧,待会大队部里要来人了。
车罱子又把车推回到大队部门口,手握着车把,带着刹车,用右脚伸过斜杠踩着脚踏,车子像小姑娘的头,摆个不停,但一直向前。又像柏皮写在本子上的字,歪歪扭扭,直冲到桥边上。柏皮和柏延正盯着车子看,突然,轰隆隆地声音从天空下倾泻而下。他们的眼睛几乎是同时离开了车罱子和他的自行车,而望向天空。天空碧蓝,一架硕大的飞机,从南往北,银光四射。柏皮喊道:飞机!飞机!
上下柏庄的人看飞机并不是多么意外的事情。据说在离柏庄三十里的山里,有个空军基地,一般每两三天,就会有飞机从柏庄飞过。但像这么大,这么低,这么银亮的飞机,还是第一次见。飞机上红色的五角星,依稀都能看到。柏延也跟着喊:大飞机,大飞机!
飞机!飞机!大飞机!车罱子的声音接着就来了。
车罱子这一喊,飞机就像着了魔似的,一下子爬高了,然后变成了越来越小的亮点子,一直往北,往北,再也看不见了。
那飞机真大!从来没见过。柏皮有些依依不舍。
真从来没见过。那上面一定坐了大干部。车罱子,不会是你爷吧?
直到这会儿,柏皮和柏延才发现车罱子和自行车都已经过了桥。柏皮问:真的骑过去的?怎么没看见?
当然是骑过来的。你们正看飞机。
不像是。这么快就过了桥?柏延疑惑着。这么短的桥,一眨眼就骑过来了。我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你们!车罱子涨红着脸,说:你们只顾着看飞机,我车子刹不住,就一溜儿骑过来了。真的,骑过来的。反正我们没看见。要不,再骑一回?我可不干了。你们爱信不信。我反正骑过了桥。车罱子推着车子,小心翼翼地过了桥。然后,上了坝,到了队部。又用手抬着车把,进了门坎;接着又托着后杠,进了门。他将车子放在老地方锁好,然后出门。这时,他看见:爷正过桥。老远,就听爷喊道:你们三个在干啥呢?
我们玩儿。柏延说。车罱子见了爷,说:刚才我们看见大飞机了。柏皮说:刚才车罱子骑车过了桥。啥?骑车?骑什么车?爷问。自行车。哈哈,怎么可能?人还没车高。你们说刚才看见大飞机了?我也看见了,那肯定是执行重大任务。都不说了,快回家吧!爷从包里拿出三颗牛沙糖,一人一颗,说:快回家吧!车罱子,告诉你奶奶,我晚上到邮递员家吃饭!
哼!车罱子转身就走。
柏皮和柏延也走了。爷回了队部。伊洛河上的桥同这个正午一样,又静了下来。
多年后,《柏庄村志》居然记载了这件事:1971年 9月 13日,柏庄少年柏为民骑自行车通过柏庄桥。同时,天空中出现由南向北大飞机。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