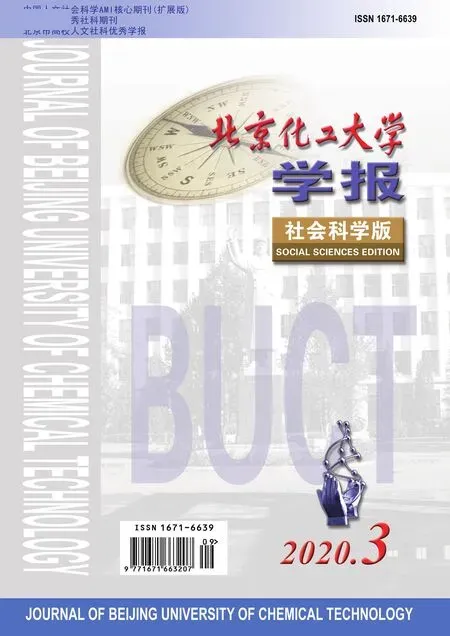公正效率两相衡:清代众证规则的演变及其动因
(清华大学法学院,北京100084)
习法之人都明白,案件的客观真实永远都无法被完全复现,审判所确认的事实是通过一系列证据构造的。故而,证据规则之良窳实关系审判效果之优劣。古代中国的法官对罪犯的口供颇为重视,沈家本就曾指出:“有证无供,即难论决。”[1]不过,假如法官无法取得输服供词,那么又当如何结案?许受衡在《清史稿·刑法志》中写到:“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律虽有‘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文,然非共犯有逃亡,并罪在军、流以下,不轻用也。”[2]按此说法,在无法取得输服供词的情况下,法官可以依据众证来判案,但有三个限制条件:其一,该犯罪是共同犯罪;其二,该罪犯是共同犯罪人中的在逃者;其三,所犯之罪的刑罚应在军、流以下。
许氏所引的律文,出自清律《名例律》中的“犯罪事发在逃”一条。《大清律集解附例》规定:“凡二人共犯罪,而有一人在逃,见获者称在逃者为首,更无人证佐,则但据其所称,决其从罪。后获逃者称前获之人为首,鞫问是实,还将前人依首论,通计前决之罪,以充后问之数。若犯罪事发而在逃者,众证明白,或係为首,或係为从,即同狱成,将来照提到官,止以原招决之。不须对问。仍加逃罪二等。”[3]至乾隆五年律文定型之时,此条律文变化无多,只在末尾添入小字注解“逃在未经到官者,不坐”。这条律文包括了许氏所言的前两个限制条件,但却没有表达出第三个限制条件,那么该条件从何而来?
此外,结合当时的审判实践来看,许氏的描述也未尽确切。比如在光绪二十七年,江苏巡抚以案犯朱永璜狡辩不服,在其并无共犯同伙,也并非在逃的情况下,决定按众证判决,并“照例奏请定夺”。刑部同意了江苏巡抚的意见[4]。再如在光绪三十一年,刑部在一桩现审案件中写明,依据“奏定新章”,按众证定拟[5]。这些例子说明,清代众证规则应该有律有例,晚清修律时还新定了章程。
学界对清代众证规则探讨不多,铃木秀光教授就此进行了梳理,发现在嘉庆十九年和道光十四年,清代众证规则先后增设并改定了条例①参见:李交发.中国诉讼法史[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6:113.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06-107.杨晓秋.明清刑事证据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50.郭成伟.中国证据制度的传统与近代化[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188-19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祖伟对“据众证定案”的考察仅限于唐代,认为其是承认特权及恤刑原则的具体化,没有关注到清代众证规则。参见:祖伟.中国古代证据制度及其理据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12-113,188-189.祖伟.中国古代“据众证定罪”证据规则论[J].当代法学,2012(1):71-77.[日]铃木秀光.“狱成”之现场——清代后期刑事审判上的认罪口供和众证[J].法制史研究(台湾),2009(16):253.。此外,滋贺秀三教授在论述清代听讼时,认为当事人不肯输服的案件是无法结案的,清代的听讼缺乏使判决获得终局性的判定程序②滋贺先生的观点及本文对其的讨论,详见本文第四部分,在此暂不详引。。
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清代众证规则完整的演变过程、演变动因及其反映出的清人对公正与效率的思考进行分析。
一、嘉庆纂例:众证规则适用范围的扩大
细绎律文,前引《名例律》中“犯罪事发在逃”一律包含两层内容。
第一层言,共同犯罪成立,由于一名共犯在逃,又没有其他的“证佐”③据清人解释,“证佐”指“亲见、亲闻之人,及现获赃物可以为证者”。参见大臣在雍正三年为此律所做的按语。参见:郭成伟.大清律例根原[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188.,因此无法确定被获之共犯是主是从,可犯罪业已成立,案件便不能久拖不决。如沈之奇所言:“狱贵初情,若因在逃之人停囚对质,则事久迁延,奸人得以漏网。”[6]但目前毕竟只有被获之犯的一面之词,不能为了迅速结案而不顾公正,故而立法者采取了“罪疑惟轻”的策略,对被获之共犯,先以从犯定其罪,待在逃之共犯被缉到案后,向其审明情由,若前犯实为从犯,则前判公正,若前犯实为首犯,则通计前罪一并定拟。律注进一步说明,此处可以适用“二罪俱发条内,余罪后发,重者更论之”之例[7]。
与第一层言“更无证佐”不同的是,第二层言“众证明白”,即亲供之外的其他证据已经形成了逻辑严密的证据链,足以证明被获和在逃二犯各自的犯罪事实。在此情况下,则不必继续令犯待质,可以迳行判决,以免节外生枝。如时臣所议:“因众证业已明白,若不即成狱,恐久或避脱,故不嫌果决。”④[清]吉纶.奏为审明巨野县民人姚文珂呈控其堂伯姚鸣庭侵占房墙一案按律定拟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全宗朱批奏折”,档案编号:04-01-01-0521-021.
综合两层内容来看,在犯罪已成,但“更无证佐”的情况下,立法者通过“罪疑惟轻”的策略试图兼顾审判的效率和公正;在“众证明白”的情况下,法律推定公正可得保障,故依据众证断案,进一步提高审判效率。可以说,“犯罪事发在逃”律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公正和效率所作的调和,而众证规则正是作为一种调和的方式,被引入到审理过程中来。
不过此时的众证规则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如果审判的公平性需要“众证明白”来保障,那么“众证明白”由谁来判断?其二,若法律规定了“众证明白”的最终判定者,那么为了提高审判效率,众证规则的适用范围还有必要局限于“二人共犯,一人在逃”么?
这些潜在的问题在嘉庆十五年被明确提出。山东巡抚吉纶为巨野县民人姚文珂赴京呈控其堂伯姚鸣庭等私拆入官房墙、侵占地基一案,上奏朝廷。吉纶奏称:“此案屡经质讯,姚鸣庭并无拆毁姚学瑛入官房墙之处,房屋间数有原抄册底可查,地址界限现经两次委员逐次勘明,又据众供确凿,其为姚文珂挟嫌诬告无疑。该犯明知罪应坐诬,尚狡展不服,总图延案拖累,实属刁健。今案已经审明,未便因犯供狡执,久悬不结,自应以勘丈并众供定断,将姚文珂依诬告律拟徒等因。”[8]本案并非共同犯罪,罪犯姚文珂也非事发在逃,故地方官理应取其输服供词,不应适用众证规则,但吉纶仍然凭众证定了案。查其原因,乃是姚文珂狡展刁健,坚不承招,而案件未便久拖不决,故吉纶认为有必要适用众证规则来迅速结案。
刑部不完全认同吉纶的意见。刑部首先强调了律文所规定的适用范围,“经臣部查: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律,係专指本犯事发在逃,各供俱已吻合,案情毫无疑窦者而言。若本犯业已到案,即应摘奸雪枉,取具输服供词,俾成信谳,不得滥引此律”[9]。继而批评了地方官员为求速结而任意节删律文的行为,指出“近来各省问刑衙门审办案件,往往因本犯未肯输服,辄删犯罪事发在逃律文,牵引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条。”在刑部看来,当官员草率论证或罗织证据时,众证规则便无法保障判决公正,此时所谓提高结案效率也就失去了意义。如其所言:“诚以狱期明决,固不可任黠辩以长刁风,而讼贵得情,尤不可藉武断以成文。”为使官员能够慎重刑章,刑部重申律义,对于未逃之犯不得适用众证规则。
不过,现实情况迫使这条律文退居为原则性规定。刑部对坚不承招之案犯作出了变通,“设遇实在刁健之徒,知罪犯重大,坚不承招,妄冀拖延,亦应奏请定夺,不得率行咨部完结。”刑部不再强调“二人共犯”这一前提,而是把一人犯罪的情况也纳入到众证规则的适用范围。在案犯狡展刁健之时,即可依众证定案,以防审讯迁延日久,节外生枝。当然,为防止法官们走回“节删牵引”的老路,刑部又补充到官员需奏请皇帝定夺,而不能仅仅行咨刑部即告完案。
嘉庆十九年,刑部的意见被纂辑入例,条例曰:“内外问刑衙门审办案件,除本犯事发在逃,众证明白,仍照律即同狱成外,如犯未逃走,鞫狱官详别讯问,务得输服供词,毋得节引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律,遽请定案。其有实在刁健、坚不承招者,即据众证情状,奏请定夺,不得率行咨结。”[10]
二、道光改定:在覆核与奏咨上的琢磨
法典中之任何一条法律通常都不是孤立的,一条法律规范被修改,与其相关联的其他法律规范往往会随之变动。清代众证规则的第一次演变也产生了这个效果。嘉庆十九年条例对据众证审决的案件,规定必须“奏请定夺,不得率行咨结”,即无论案情重大与否,只要适用众证规则定案,地方官就必须奏请皇帝裁决,而不能仅以咨文的形式向刑部汇报。这一规定触及了关于清代审判程序的两项内容:一是案件须层层上报覆核,二是奏与咨的运作。
简要来讲,在清代,倘若案情仅涉户婚、田土、钱债等民间细故,且对应刑罚为笞杖刑罚的,则州县官员可自行审理结案。倘若案涉命盗,且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则州县官员在审理之后不能自行结案,无论被告是否服判,都必须上报覆核,经府、道、按察司、督抚、刑部或三法司甚至皇帝层层覆核后才能了结。如此做法,一来由于国家对细故案件可能存在着主观上的轻视;二来也由于多如牛毛的细故案件若均行复审,则整个司法系统将不堪其累。
与此相配合的是奏与咨的运作。清律规定,州县自理的案件不必上奏或咨部,而各省徒罪以上案件则均须咨部或上奏皇帝。所谓咨部,即地方督抚以咨文的方式向刑部汇报审判意见,咨文是中央六部与地方督抚间的一种平行文书。所谓上奏,是指官员通过上行文书来向皇帝陈述意见,以获取皇帝本人的指示,具体到本节所讨论的时期,这种上行文书主要是题本和奏折①关于清代题本、奏本和奏折演进过程的大致轮廓,学者们已多有论述。简要来说,清初承袭明制,以奏本和题本为主。至康熙朝中叶,奏折逐渐得到普遍运用。至雍正朝,奏折的运用越发制度化,其地位也日渐升高,呈现出与奏本、题本并列的态势。乾隆朝早期亦是如此。迨至乾隆十三年,乾隆以“同一入告,何必分别名色”为由,正式废除奏本,而保持题本与奏折并行的制度。本文对众证规则嘉庆十九年条例的讨论,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关于题本、奏本和奏折演进过程更详细的论述,参见:庄吉发.清朝奏折制度[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6:41-86,109-121,235-241.杨启樵.雍正帝及其奏折制度[M].长沙:岳麓书社,2014:159-192.冯尔康.雍正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23-240.。其中,题本沿袭自明朝,自清初起便是官员们例陈公事的重要文书。题本的运作大体须经上陈、翻译、贴黄、票签、上呈皇帝、批红、发抄等多个环节,程序复杂繁琐,往往导致案件积压。相比之下,奏折的呈交速度相对较快,由上奏人经邮驿直达宫内,经奏事处或者少数亲信之人径直交由皇帝批阅。但由于奏折所载的内容往往是重情大案,故朝廷对奏折的处理慎之又慎,多由皇帝发交军机处拟写谕旨,钦定后再发军机处抄录奏折,再交内阁中书领出传抄给各部院。
由此可见,无论题本还是奏折,都因其关涉圣裁而具有一套复杂的运行程序,这套程序面对多如牛毛的细故案件时颇为低效。即便奏折的运行相对简单,可若地方官事无巨细地皆以奏折上陈,则朝廷仍会疲于应对。对此,在乾隆六十年,怡亲王永琅会同六部提出的“改奏为咨”议案恰可证明。面对奏折积压的情况,该议案以列举式的方法规定了只有某些重大情形才可以奏折入奏,其余情况除循例入题外,皆应以咨文报部即可。而本次改革的宗旨,便是“以归简要”[11]。
反观众证规则的嘉庆十九年条例,我们不妨设想,若是一起罪在笞杖的细故案件,经由地方官依据众证判决之后,那么它是否需由督抚向皇帝奏报呢?若否,则所谓“奏请定夺”之例几成具文;若然,则一部分细故案件便也须听候圣断,或题或奏都需履行繁琐的程序,如此牺牲审判效率是否值得?
道光十年八月,江苏巡抚陶澍在覆审顾怀瑾京控案时便谈到了这个问题。在本案中,顾怀瑾先向地方官控告顾鸣扬等人包娼诱妹戏谑,并纠抢田菜。地方官审理后认为顾怀瑾所言仅部分属实,故依据相关证据作出了判决。可顾怀瑾及其母顾吴氏并不满意,遂顾吴氏令顾怀瑾代其抱告,屡次赴京翻控。至陶澍覆审此案时,陶澍以众证明确,不应再任其狡辩不休以致拖累为由,将顾怀瑾依不应重律拟杖八十结案。
同时,陶澍向刑部建议:“若寻常细故无关罪名轻重出入,众证已明,仅一原告逞刁狡执,不肯输服,此等案情一皆纷纷入告,未免繁琐,似可就案咨结,以归简便。”刑部基本接受了陶澍的意见,将前例未加明确的轻重犯罪做了区别对待,规定依据众证结案的笞杖罪案件,除例应上奏的,其余案件均毋庸上奏,以此来减轻司法系统的负担,提升审判效率。不过这些案件也不同于寻常的州县自理案件,而须经督抚亲自提审,确认无误后咨报刑部,方可最终结案[12]。此处仍是通过延长审判程序,而为公正补充了一个安全阀。
参酌刑部的意见,朝廷于道光十四年修改了例文。改定后的例文曰:“内外问刑衙门审办案件,除本犯事发在逃,众证明白,仍照律即同狱成外,如犯未逃走,鞫狱官详别讯问,务得输服供词,毋得节引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之律,遽请定案。其有实在刁健、坚不承招者,如该犯徒罪以上,仍据众证情状,奏请定夺,不得率行咨结。杖、笞以下,係本应具奏之案,照例奏请。其寻常咨行事件,如果讯无屈抑,经该督抚亲提审究,实係逞刁狡执,意存拖累者,即据众证情状,咨部完结。”[13]
薛允升对此条例文颇不以为然,其在《读例存疑》中提出了三点批评:其一,对于犯未逃者,“若必取其输服供词方成信谳,则众证明白之语几成虚设。”其二,“律言不须对问,此处云务得输服供词,亦属与律不合。”其三,既然已经规定实在刁健者可依众证定案,那么又何必对笞杖案件作单独规定[14]。
结合前文的论述来看,薛允升的评价未必妥当。其一,律文“众证明白”“不须对问”之语的适用条件是共犯在逃,而例文“必取输服供词”之语的适用条件,则不限于共犯,且该犯已被捕获,此时法官有机会获得罪犯的亲供,为防止法官罗织众证使判决有失公正,故作此规定,二者间并不矛盾。这是在提高审判效率的情况下兼顾公正。其二,“必取输服供词”也只是原则性规定,对于坚不承招的特殊情况,法官仍可变通行事,凭众证定案。这是在保障公正的情况下兼顾效率。其三,法官的变通亦不可率性而为,故法律通过延长审判程序来保障公正,同时依照案件轻重将其区分为奏请定夺和咨部完结,通过“分流”式处理来提高效率。
三、光绪新章:不再受理笞杖案件的翻控
通过国初设律、嘉庆十九年纂修新例以及道光十四年改定例文,清代众证规则逐渐细致起来。不过,众证规则在审判实践中的运用情况,恐怕并不尽如人意。张之洞曾言:“查例载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不须对问。然照此断拟者往往翻控,非诬问官受贿,即诋证人得赃,以故非有确供不敢详办。”[15]可见,当事人翻控往往令官员不愿适用众证来定案。
虽然翻控有别于一般的诉讼程序,但其并非不法之举,即便是京控,“也是朝廷开辟给小民的唯一的申诉渠道,是允许他们去利用的”[16]。尽管律例中规定了对京控不实的处罚,但实际上“京控得实,甚至是怀疑控告,都有可能不用被判刑。这样的情形,无疑是间接促使百姓京控。长此下来京控正式成为一条民间上控的渠道”[17]。而朝廷之所以允许翻控,是想在一般的诉讼程序之外设立一种特殊的程序,使民意得以直达天听,这在理论上自然是为加大对个案公正的保障力度。
不过翻控之人非尽含冤待雪,如张之洞所言,其中多有诬告诋毁之举①当然,清代官员为了息事宁人、保全官声,往往先入为主地判断京控的原告为诬告,这很可能也是一种污蔑诋毁。相关研究可参看李典蓉的论述:李典蓉.清朝京控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在此情况下,翻控这一特殊的渠道不仅无助于保障公正,反而给刁健之徒留下了逞刁图赖的机会。尤其在依据众证所定之案中,当事人本来就没有输服供词,故而翻控之机愈多,流弊亦愈甚。
如两江总督孙玉庭在道光二年处理的一桩京控案,该案的原始案情係民人徐华与吴鹤庆因买卖坟地发生了纠纷,本属州县自理的细故案件。可在本县官吏审决之后,吴鹤庆的族亲吴恕恒等人抗断藐详,坚不输服,随即开始上控。上级法官仍以原案众证明白维持原判,而吴恕恒等依然狡展不服,继续上控,直至赴京,以致本案提省三年,案悬六载,仍未能完结。甚至在长年的京控过程中,被迫应诉一方的代表人徐行,因长期滞留京城,盘缠无着,又多有族人谴责其办事不力,遂郁闷自杀。直到孙玉庭审理之时,仍依据前述众证定案,并因徐行之死,将吴恕恒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此案始得彻底了结[18]。
一件原本众证明白的细故案件,却因一方当事人屡屡翻控而久拖不决,至酿人命,足见众证规则在翻控面前的弱势。难怪道光年间江苏巡抚李星沅在清厘京控积案时,要强调“不准稍涉迁就,其狡供险健、坚不承招,而众证明白、毫无疑义者,声明请旨定夺。庶法立令行,颓风渐挽”②[清]李星沅.奏为勒限清厘京控案件并东台县知县葛起元等提解逾限请先行交部议处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全宗朱批奏折”,档案编号:04-01-08-0042-001.。
翻控长期干预着常规审判程序的运行,众证规则也概莫能外。翻控为含冤者开辟了昭雪之路,也为刁健者留下了起衅之机。前者使公正得以保全,后者则使公正和效率两失。两相权衡,立法者应该何去何从?再者,前述众证规则的道光十四年定例规定,徒刑以上案件要上奏皇帝,以求圣裁;即如笞杖案件,也要经督抚亲自提审并行咨刑部,待查核无误后才能最终结案。相较于同类依据输服供词结案的情况,如此规定已经颇为审慎了。那么是否可以对翻控加以限制,以平衡公正和效率呢?晚清的立法者们作出了决断。
张之洞向朝廷指出:“夫既非死罪,又有众证,兼有覆勘,即是本犯不肯输服,不过意有不足,断不能全然颠倒。据此定案,则全案应讯之人等可以省释谋生。夫为一人之军、流而致妨废多家之生业,拖毙无数之人命,孰得孰失,仁人良吏必有能辨之者矣。”进而建议:“拟请以后断案,除死罪必须有鞫服供词外,其军、流以下罪名,若本犯狡供拖延至半年以外者,果係众证确凿,其证人皆係公正可信,上司层递亲提覆讯皆无疑义者,即按律定拟,奏咨立案。如再京控、上控,均不准理。”[19]
刑部同意了张之洞的建议,伍廷芳等议覆曰:“夫既非死罪,又有众证,兼有覆勘,案情断不至于全行颠倒。倘再翻控,希图拖累,实为刁健之尤,诚不可不杜其渐。臣等公同酌议,应如该督等所奏,嗣后断案除死罪必须取具输服供词外,其徒、流以下罪名若本犯狡供不认,果系众证确凿,其证人皆系公正可信,上司层递亲提覆讯皆无疑义者,即按律定拟,奏咨立案。如再京控、上控均不准理。”[20]
张之洞和伍廷芳等人均认同不应以一人之刁健而拖累全案之大局,故在排除死刑并对众证加以限制的情况下,规定徒、流罪以下众证明白的案件,不允许两造再行上控或京控,在法律上赋予一部分众证定案以终局性效力。这便是本文开篇所提的“奏定新章”。
四、演变的动因:公正与效率的权衡
纵观清代众证规则的演变过程,可以说这是一场公正与效率的拉锯战,其设立和演变的各个环节,都包含了清人对公正和效率的权衡。
(一)公正、效率与程序
对于清代的诉讼,滋贺秀三先生曾有过细致的分析,但其中仍有可以进一步探讨之处。在分析州县自理案件的审判①在滋贺先生的论述中,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审判也被称为“听讼”或“民事诉讼”。时,滋贺先生指出:“在民事方面同样不存在这样一种制度:即把坚持争议、不肯承服的当事人置于判定程序中去,宣告通过这种程序达到的裁决就是当事人之间的法,而无论当事人是否愿意,程序到此即告终结。”[21]这与本文所探讨的“众证明白,即同狱成”和“其(笞、杖以下)寻常咨行事件,如果讯无屈抑,经该督抚亲提审究,实係逞刁狡执,意存拖累者,即据众证情状,咨部完结”等规定显有出入。
细察其详,滋贺先生从欧陆法系截至当时的诉讼史中获得经验,认为审判程序本身应该具有“判定”的意味,即由享有权威的第三者来对相互争议的主张作判断,且判断一经作出,便无法被当事人或裁判人更改或撤回[22]。以此反观清代的听讼,其更像一场“教谕式调解”[23]。审判程序的展开,“表现出理念上是法官居高临下地说服劝导以至威吓当事人,实质上却也是法官与当事人之间讨价还价的交涉过程”[24]。
这种描述在一定范围内是准确的,但并非清代司法样态之全貌。众证规则显示出,在众证明白可当事人坚不承招的情况下,法官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证人的核查,仅意味着法官慎重的态度,并不决然意味着法官要向当事人或其他相关人员作出让步,二者间的交流可以被理解为法官通过众证所作的确认,即坚不承招之案犯已经不值得再被劝教。此时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即使案犯仍有话可说,在法官看来其也是无言可辩。从制度设计的初衷来讲,众证规则无疑是要为缺乏被告输服的听讼提供一种结案方式,而非为当事人日后翻控留下话柄。从众证规则的演变过程来讲,民事案件从奏请定夺到咨部完案再到不许翻控,地方官员审判的自主性和判决的确定性都越来越强。如果我们聚焦个案,自然会发现法官如何倾尽所能来获得当事人的“认可”,可当我们从司法系统之整体来观察,则会发现在众证明白的情况下,法官们并不总如父母般耐心地劝教,法律也不会一直容忍案件因缺乏亲供而久拖不决。
进一步探讨“程序”,西方的法学理论称,我们之所以会需要程序,是因为程序能够营造一个“法的空间”,而营造“法的空间”之价值在于维护“法的安定性”,即如果不赋予确定判决以终局性质,不仅永远都难以把该具体案件中的“什么是法”固定下来,而且还可能导致此后产生的一系列法律关系总是处于基础未稳的不安定状态。而之所以要维持“法的安定性”,则可从维持市场交易连锁的安全这一效率性角度来说明[25]。至于程序与实质公正则显示出一种不对等的关系,诚如滋贺先生所论:“诉讼关系到人的生命、身体和财产而直接左右人的命运,因而不能设想被搁置起来留待将来解决,不得不在现在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得出结论。于是,通过一定的程序——在文明各个阶段的当时条件下不可能考虑有比此更加完善的那种程序——并以通过完成这种程序而得来的结论代替真实本身。”[26]
可见人们创造程序的主要理由并非实现实质公正,而是人们必须通过某种机制来生产出一种普遍认可的公正,以满足对于迅速结案的迫切需求,使得整个社会能够更有效率地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讲,程序是人们用来调和公正和效率的一种方式,暗含了实质公正向效率的妥协。
尽管这些关于“程序”的论述是学者们基于西方法律传统所总结的,但实际上生活在清代中国的人们也思考着同样的问题。在清代,词讼案件之多达到了令地方官疲于应付的地步。包世臣言:“至于词讼,三八放告,繁剧之邑常有一期收呈词至百数十纸者。”[27]可以想见,众证明白而当事人坚不承招的情况更令法官难以忍受。诉讼的紧迫性逼迫官员们提高审判效率,而仅靠劝诫官员们要“爱民如子”多是不能奏效的,因此清代的法律不得不在制度上设立一种裁判程序来保障效率。这种程序不再以获取被告的输服供词为首要目的,而在以其强制力来迅速终止审讯。众证规则便是此意的一种表达,他们将个案的裁判与整个司法系统之运作相关联,在假定众证可以确保实质公正的情况下,以强制力来终止审讯,不顾及当事人一味的坚持是否真有隐情,从而提高审判效率。就此而言,清代的听讼并非全然没有“程序”的意味。
(二)对效率的承认与审慎
当然,这种意味不够浓厚也是实情,但是一个制度在立法层面被时人思考、设立和调整,与其在司法实践中是否被广泛地适用,应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这一现象绝不简单地表示该制度是无意义的,反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思考中国古代司法文化的切口。
一方面,古人对判决的终局性以及程序的效率性价值的思考并非肇始于清代,而是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
比如早在北魏时期,朝廷就正式讨论过此类问题。《魏书·刑罚志》载,延昌三年六月,兼廷尉卿元志、监王靖等上言,认为:“其家人陈述,信其专辞,而阻成断,便是曲遂于私,有乖公体。何者?五诈既穷,六备已立,侥幸之辈,更起异端,进求延罪于刻漏,退希不测之恩宥,辩以惑正,曲以乱直,长民奸于下,隳国法于上。”大理正崔纂、评杨机、丞甲休、律博士刘安元则认为应当给罪犯覆审的机会,但不能没有限度,故上奏曰:“刑宪不轻,理须讯鞫。既为公正,岂疑于私。如谓规不测之泽,抑绝讼端,则枉滞之徒,终无申理。若从其案成,便乖复治之律……愚谓经奏遇赦,及已复治,得为狱成。”[28]
元志等人的意见即是当各种审讯和论证的方法都适用完毕后,如果犯人及其家属仍然狡辩,朝廷就不应当准理。崔纂等人则意在表明,应该允许罪犯提起覆审,但案件不能久拖不决,故皇帝特赦或者已经经过覆审的案件则为结案。概而言之,这次讨论的核心内容就是,当罪犯不服意图上诉之时,案件审理到什么程度就应该作出终局判决了。皇帝最终肯定了崔纂等人的意见。
后来,唐律中也有据众证定案的规则。《唐律疏议》中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疏议曰:若赃状露验,谓计赃者见获真赃,杀人者检得实状,赃状明白,理不可疑,问虽不承,听具状科断。”[29]至宋代,《宋刑统》径直将此规定纳入“不合考讯者取众证为定”[30]条。至明代,明律在《名例律》中设“犯罪事发在逃”[31]条,是为清初定律中“犯罪是发在逃”条之所承。薛允升评价道:“添纂犯罪事发在逃者,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不须对问之语,明律指犯逃走而言,唐律指犯不承引而言,虽不无稍有参差,而‘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与‘理不可疑,即据状断之’之义彼此相符。”[32]可见,在难以取得输服供词的情况下依据众证定案,超脱罪犯口供所代表的公正而接受由众证规则所建立的公正,从而保障起码的审判效率,这是历代立法者共同的选择。
另一方面,清代的听讼也确如滋贺先生的描述,法官会对那些看起来陈述不实的当事人、证人指出其陈述的矛盾,把相反的证据摆在他面前,以迫使他陷入无言以对的境地[33]。滋贺先生指出,这是因为听讼的主要依据是“情理”[34]。上述观察虽然准确,但滋贺先生仍未指出“所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整体”与西方法律中的“权利”究竟是什么关系,清代的听讼不判断权利的有无,那么它所保护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对此,苏亦工教授指出,西方的诉讼所保护的权利实际上就是财产利益或物质利益,而明清听讼所保护的核心目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伦理,特别是家庭伦理,两种诉讼模式所保护的核心目标不同,应是两种诉讼模式的根本差别所在[35]。此系的论。这意味着,清代听讼的目的至少不以解决财产纠纷为主,而是修复已经出现裂缝的伦理关系。不同于财产利益可以通过数量多寡来显示是非曲直,伦理关系不能采用这种标准,故而听讼的最终结果只能是使当事人间重归相安无事,用古人的话说即“息讼”,而用今天的表达即“案结事了”。
在这种情况下,清代的法官便无法保持“被动”,不能仅通过当事人各自的陈述和举证,简单地对财产利益在数量上进行划分即告结案,且不允许当事人再有任何申辩的机会。百姓期待法官们能够深入到个案的具体案情之中,细细体察当事人间的伦常关系及其背后的天理人情。而要做好这一点,法官就不能不和当事人充分地交流,因为在这一点上,法官的判断力并不当然地优于当事人。这对诉讼程序产生的影响便是,在当事人间的伦理关系还没有被修复时,法官便可依据众证规则结案,这样的程序很难被认可,尽管它可以提高审判效率,但个案中的伦理关系尚未重归和谐,故而这种效率性价值也不值得被推崇。这就是众证规则没有被普遍适用的原因。
五、结语
古代中国的证据规则既重视输服供词,也讲求众证。清代的众证规则历经三次演变而越发合理,从设置和修改规则的动因来看,众证规则是一种调和公正与效率的方式,立法者对这一组关系的权衡,是其演变的动力。这说明清代司法并非只看重个案公正,而轻视审判效率,清代的听讼也并非如滋贺秀三教授所论,全然缺乏对终局性裁判程序的思考和制度设计。诉讼的紧迫性迫使人们经由程序来生产正义,以满足对高效解纷的需求,这一思路并非西方人所独有,也是中国古代立法经验的一部分,清人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也作出了类似的制度回应。不过由于清代的听讼以修复伦理关系为首要目的,故而侧重效率的众证定案程序也就难获推崇。古人在权衡公正与效率之时,既在追求实质公正之外意识到了效率的必要性,同时也尤为审慎地对待由于盲目追逐效率以致公正受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