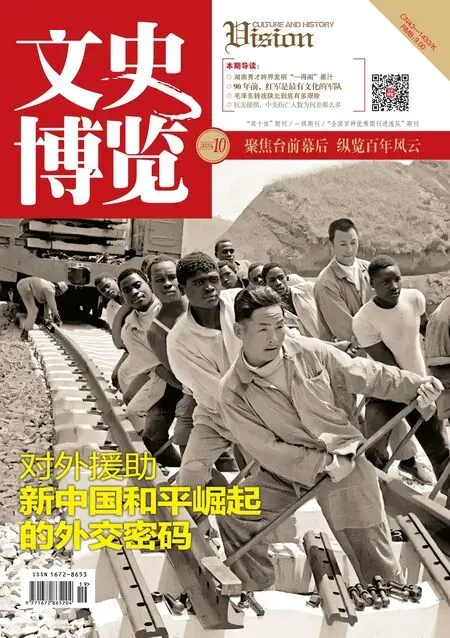否认“尧舜”,民国教科书被查禁
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1923年,历史学家、民俗学家顾颉刚(1893—1980)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伴随着文化环境的革故鼎新,一大批疑古言论如雨后春笋涌现,顾颉刚把这类探讨争议的文章汇集成书,书名为《古史辨》,竟达洋洋7大册,数百万字。
1926年,北京朴社印行第1册后,疑古思潮更为高涨,该册一年之内再版了10次。钱玄同、胡适、吕思勉、罗根泽等人亦置身其间,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古史辨学派。
“自从地面上初有人类以后,一直到所谓黄帝时,都是鸿荒之世,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只要看这黄帝的称号,便可与再前一点的炎帝一类同样看待,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便用什么五行里的土德来表示他。”顾颉刚撰文写道。作为古史辨学派当仁不让的创始者、奠基人,在甚嚣尘上的诸多疑古言论中,顾颉刚表现得最为尖锐,引发的争议也最大,是“公认的妄人”。

顾颉刚
所谓“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包含三层意思: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譬如,周代时,人们心目中最古老的王是禹,到春秋时开始认为有尧舜,至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再往后到秦代时出现了“三皇”,汉代以后才有了“盘古开天辟地”的说法。二,时代愈后,记述中的中心元素愈被放大。三,在考证古史时,我们即使无法知道某一件事的真实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记述中的最早的状况。简而言之,顾颉刚认为:我们的古代历史,是在转述的过程中逐渐地一层一层地被累加上去的,是不可信的。
正是根据“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顾颉刚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论断:国人津津乐道的“三皇五帝”或许子虚乌有,也不存在所谓的尧让位于舜,舜又让位于禹的禅让传说,因为大禹很可能是一个动物的化身。“禹是动物,出自九鼎”“尧、舜的传说,为后世所崇信;我们看惯了,遂以为古代真有一个圣明的尧、舜时代了。其实,尧、舜的故事一部分属于神话,一部分出于周末学者‘托古改制’的捏造;他们‘言必称尧舜’,你造一段,他又造一段,越造就越像真有其人其事了”……当然,诸如此类的观点若放在今天,可权且算作但说无妨的“方家之言”,但在当时,则由此引起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公案。
1922年春,经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代理文科学长的胡适推荐,顾颉刚、王钟麒等人参与了初中用历史教科书《本国史》(上、中、下三册)的编撰。其中,由“总说”和上古史、中古史构成的《本国史》上册,完全由顾颉刚编写。在编写前,顾颉刚想把自己对“三皇五帝”的看法写入书中。考虑到在教科书中公开否定“三皇五帝”的存在可能会“平地起波澜”,所以,顾颉刚踌躇再三。征询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主任朱经农的意见时,朱经农说:“此刻,当局大略还管不到这些事吧,你只要写得隐晦些就是了。”果然,其后的《本国史》样稿在走马灯般的人事更迭中通过了北洋政府的审定,准许付梓,全国发行。
1929年,发行量已达25万册的《本国史》(上册)突然被南京国民政府查禁。教科书的受众该有多广?学生、教员、文化界、政界……事情东窗事发:开始是山东曹州重华学院院董丛涟珠、院长陈亚三等呈请禁止,紧接着山东省参议员王鸿一提出专案,弹劾该书“非圣无法”。尔后,南京国民政府第十七次国务会议作出决定,通令全国查禁。当时的北平《新晨报》还以《国府严禁反动教材发行》为题作了报道。
不仅书被禁,顾颉刚本人也受到了有关方面的严厉训诫。南京国民政府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认定这部历史教科书是惑世诬民的邪说,足以动摇国本。戴季陶表示:“三皇五帝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中国之所以一直能成为一个整体,就是因为在精神上、文化上,大家都相信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尤其是黄帝,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珍贵信仰和崇拜,成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如今顾颉刚竟然说三皇、五帝是不存在的,这等于把作为一个整体的全国人民给解散了,这还了得!”
祸起萧墙,商务印书馆自然也难脱干系。戴季陶这位一贯以思想卫道士自居的国民党早期“教父”继而“高屋建瓴”批评:“民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商榷是可以的,至于书店出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话说到如此高度,出版该书的肇事方——商务印书馆也战战兢兢了。于是,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慌忙从上海赶到南京,转弯抹角,谒见“党国元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寻求解决办法。
后来,通过背后往来穿梭的斡旋,有人提出了一个方案:“这部教科书前后总共印刷了160万册,那就罚商务印书馆160万元。”结果,商务印书馆交不起这笔大额罚款,又去请吴稚晖出面具名转圜求情。最后总算减免了罚款,以禁止发行终结此案。
遭此当头棒喝的顾颉刚很是委屈地说:“这是我为讨论古史在商务印书馆所撞出的祸,也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文字狱。”
对顾颉刚的观点和做法,认同者有之,反对者亦不鲜见。毛泽东算得上是一位疑古思想的同情者,所以,在后来的《贺新郎·读史》中,他写了“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的句子。而鲁迅则是著名的反对派之一,他曾在小说《理水》中写道:“‘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胀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的,‘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影射顾颉刚是“口吃的鸟头先生”,其嘲讽、揶揄意味显而易见。
转眼间,当年这桩轰动一时的公案已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今天回看,顾颉刚的做法或许的确值得商榷。站在国家的角度上,学术研究与国民所需的基本教育是有很大区别的两个层面,不宜等同。毕竟教科书是国民普遍认知历史的来源,影响深远,尤其对青少年学生极为关键——他们历史观的形成由此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