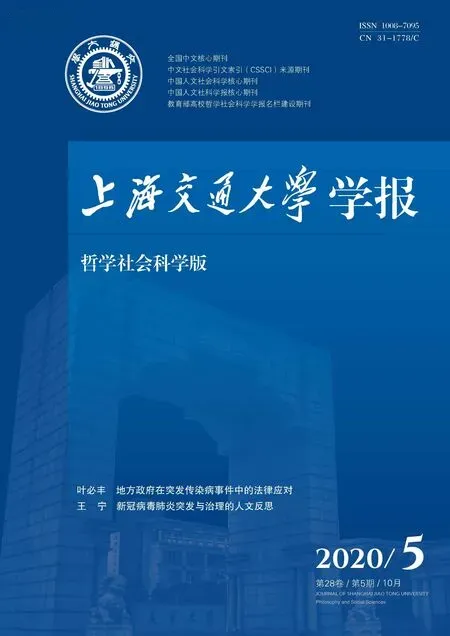新冠病毒肺炎突发与治理的人文反思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240)
今年年初,正当我们度过2020年新年,准备于1月下旬和家人欢度春节之际,一种致命的新型病毒降临中国大地,这就是我们近来经常谈虎色变的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这场病毒的蔓延导致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不同程度地受到感染。但是经过中国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的众志成城和严阵以待,这场强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终于率先在中国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西方一些国家的媒体和官员指责中国违反人权强令人们居家隔离时,疫情却先后在欧美国家暴发,并有一发不可收之势。欧美国家不得不效法中国的做法,相继也采取这种“违反人权”的措施对疑似病毒患者实行封闭式隔离。尽管现在病毒仍在全球数十个国家蔓延,但是中国有效控制病毒的经验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领导人和医务工作者所认可,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而求助于中国。同时,经过努力他们也开始采取果断的措施逐步有效地控制疫情在本国的蔓延。我们在悼念死者之际,不得不对人类突然遭遇到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进行反思。作为地球上的物种之一,我们人类也要追问自己这些问题: 面对自然界的突发事件,人类应该采取何种对策?人与自然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历时数月的疫情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何种影响?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应该如何迎接新型教学模式的调整?如此等等。除了医务工作者应当努力工作尽快研发出预防病毒的疫苗外;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则应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反思,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
一、 从全球蔓延到全球治理
面对新冠病毒的侵袭,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病毒是无国界的,任何国家不管多么强大,在病毒的侵袭面前都会变得十分脆弱;一个国家出现的病毒绝不是孤立的,如不及时管控治理就会迅速地波及周边的国家,甚至蔓延到全球更多的国家。新冠病毒在欧洲的蔓延就证明了这一点。既然整个地球上的人类都生活在一个硕大无垠的“地球村”里,那么我们便可以进一步推论,我们彼此都相互依赖、休戚与共,因为我们都是一个拥有共同的命运并分享着共同利益的“共同体”(community)的成员。因此,一方有难,应该八方支援。我们绝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出现在某一个国家的孤立事件而对之袖手旁观,更不能对之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已经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全球化联结为一体了,所以新冠病毒肺炎的突发也给我们的全球化研究增添了一个新的课题——病毒的全球蔓延和全球治理。
全球化自20世纪末进入中国以来,早已不只是一个经济上和金融界的现象,它已经逐步渗透至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今天离开全球化恐怕难以在地球上生存。因此,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现象,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黑死病、鼠疫、非典、埃博拉等跨越国界和民族界限的流行病就是疾病全球性蔓延的案例。此次的新冠病毒肺炎更是一个全球性的突发现象。它没有一个单一的源头,而是先后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暴发。既然新冠病毒肺炎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那么要控制它单靠一个国家显然是不可能的。对于波及全球的病毒我们就要采取全球治理的手法来遏制病毒的蔓延。此外,我们也应该从全球化这个根本来究其原因。
首先,我们要重新思考全球化对中国而言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早在中国是否应该加入世贸组织时就进行得十分激烈。最后,在权衡了各种利弊后并着眼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考虑,中央领导果断地下定决心: 中国一定要加入世贸组织,而且要在其中发挥领军的作用。如果从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成为其第143个成员算起,全球化在中国的登陆已接近二十年,而全球化作为一个经济学和金融学界的现象则在那之前就已经忽隐忽现地在中国出现,并逐步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几年前,曾经一度鼓吹“历史终结论”的美国日裔学者福山在与中国学者俞可平的对话中曾毫不隐讳地指出,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赢家,(1)俞可平.福山对话中国发展模式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N].北京日报,2011-03-28(019).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发展和GDP排名的飙升,更体现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而对于这后一点,我们相当一部分人文知识分子却视而不见。众所周知,当北京奥运会于2008年成功地举办之后,西方媒体曾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昔日的“东亚病夫”已经不复存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东方大国的出现已成为不争之实。显然,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而在这之后先后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和进博会的巨大成功则更是向全世界展现了上海这颗“东方明珠”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作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得到进一步确立,而且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这些无疑都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红利和积极的方面,我们作为直接的受益者,自然要珍惜这一来之不易的成绩。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全球化在带给人类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 贫富等级的加剧、地球资源的耗竭、民族/国家疆界的模糊以及文化上的趋同倾向等等,不一而足。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被甩进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再者,全球化的到来也为疾病的全球性传播和蔓延埋下了伏笔。(2)比利时学者西奥·德汉在5月23日的视频讲座《剧变: 文明是如何变化的,它和流行病有何关系?》(Swerves: How Civilizations Change and What Pandemics Have to Do with It?)中指出,欧洲国家疆界的模糊和出行的过于便利也为疫情的大规模蔓延埋下了祸根,因此当疫情在一个欧盟成员国暴发时,其他国家纷纷采取关闭边界和机场、减少旅行和家庭聚会,甚至隔离等手段来遏制疫情在欧洲大陆的蔓延。现在经过各国政府的努力和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协调,疫情已经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显然,他们从中国的抗疫斗争中得到了一定的启示和教益。因此,从全球化的视角来进一步考察新冠病毒的全球性传播和蔓延也应该成为我们全方位地研究全球化问题的一个新课题。在这方面,中国在遏制新冠病毒肺炎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展现出的中国智慧将对当下以及今后全球性的疾病防控和遏制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
新冠病毒肺炎带来的蝴蝶效应目前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彰显出来,它使得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受到严重的干扰和阻碍,同时也使得经济停滞甚至衰退。但即便如此,西方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仍然认为当地政府以“流行病的发明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借口,借以扩大他们超越任何限制的权力。”(3)例如,意大利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哲学家吉奥吉·阿甘本(Giorgio Agemben)就在一篇题为《流行病的发明》(L’invenzion di un’epidemia, Quodlibet, 26 febbraio 2020)的文章中表达了这一观点,他的意大利文原文是: Giorgio Agemben. l’invenzione di un’epidemia possa offrire il pretesto ideale per ampliarli oltre ogni limite[EB/OL].(2020-02-26)[2020-06-21].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l-invenzione-di-un-epidemia.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大利左翼知识分子吉奥吉·阿甘本(Giorgio Agemben)素来以反对专制集权著称,但是面对新冠病毒的侵袭,他却没有实事求是地支持政府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因此,他的这种不切实际的看法自然受到了很多知识分子的批驳,同时也被后来新冠病毒在意大利的大规模暴发证明是失当的。这就说明,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或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关心人民的疾苦,当普通的人畏缩在毫无遮掩的斗室里遭受病毒的侵袭时,侈谈所谓的“人权”还有什么意义?当一个人的生存都受到危及之时,人权还能得到保障吗?因此,面对疫情的侵袭,我们首先应果断地将患者送往医院或居家隔离,以免更多的人受到病魔的侵袭。好在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政府所采取的果断措施十分理解,并积极地予以配合。因而在中国,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共同努力,采取全国各省市联手治理的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疫情的发展和蔓延。至少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这些超级国际大都市中,疫情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本地居民中大规模蔓延,而更多出现的是境外输入的病毒携带者。但是这些境外来客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受到全球治理的限制: 他们不得进入人口稠密的市区,也不得与当地的居民进行直接的交流,首先要自觉地隔离14天后才能自由地活动。在非常的时期也只有采取这样一种果断的措施医务工作者才能将境外输入的病毒扼杀在萌芽状态中,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行为,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人权的必要保证。现在我们从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这些中国最大的城市的病毒现存数据中不难看出这一举措初步的成效。当然,6月上旬北京地区出现本土病例也提醒人们不能放松警惕。所有这些都说明,新冠病毒肺炎作为一个波及全球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它的出现并非是在一个国家,而是在不断地通过人们的接触波及世界各地。因此,单靠某一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去努力是无法有效地遏制疫情的。这样看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取一种全球治理的手段来全方位地控制疫情的传播和蔓延。既然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那么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说就同属于一个有着共同命运并分享共同利益的“社群”,或曰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我们彼此都分享着共同的利益,同时也应该分担共同的灾难,绝不应当一方有难,他方幸灾乐祸。更不能将本国疫情的突发和蔓延甩锅到别的国家,动辄就要向别国提出不切实际的索赔诉求,这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缺乏基本的科学数据作为支撑。作为深受新冠病毒侵袭的中国,只能理所当然地予以拒绝,同时也并不排除继续向别国的受害人民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二、 人与自然的关系再认识
如果说,对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和蔓延采取一种全球治理的方法加以遏制确实有效的话,那么这也只是一种应急的治标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做到防患于未然。因此我们就需要从更深的层次上来寻找其根源,从而达到治本的目的。人们通过进一步追根寻源发现,新冠病毒的天然宿主可能是蝙蝠,最近人们又从北京突发的多个本土病例发现了三文鱼也可能是病毒的携带者。但是,对于究竟是蝙蝠体内的哪种病毒通过何种途径进化出新冠病毒并迅速地感染人类,或者说三文鱼究竟以何种方式滋生并携带病毒以及通过何种途径使之迅速传播和蔓延,至今仍然未得到科学实验数据的证明。所以,就此而言,进一步深入调查是颇有必要的,同时这应该是具有全球治理功能的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研项目。作为人文学者,我们要考虑的是,既然我们可以确定新冠病毒来自自然界,那么我们就要重新思考并调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这方面,笔者曾作过一些研究,并发表过一些著述,(4)这方面可参阅拙作: 王宁.后现代生态语境下的环境伦理学建构[J].理论与现代化,2008(6): 63-66;王宁.生态批评与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建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5-12;王宁.生态文明与生态批评: 现状与未来前景[J].东方丛刊,2010(2): 1-16;王宁.生态文明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J].跨文化对话,2010(26)等。以及英文论文: Wang Ning. On the Man-Nature Relationship Represented in Chinese and Western Literary Works[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2000, 1(1): 80-93; Wang Ning. Toward a Literary Environmental Ethics: A Reflection on Ecocriticism[J]. Neohelicon, 2009, 32(2): 289-298; Wang Ning. Global in the Local: Ecocriticism in China[J].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2014, 21(4): 739-748; Wang Ning. Introduction: Ecocriticism and Eco-civilization in the Confucian Cultural Environment[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2018, 55(4): 729-740.但在本文中,我仅就新冠病毒的起源和蔓延来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毋庸置疑,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致力探讨的永不衰竭的主题。诚然,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和不断的变化: 在远古时期,人与自然十分和谐,甚至达到了中国儒家哲学中所说的“天人合一”状态,实际上也就是人与自然的浑然一体。确实,人既然来自自然,是自然的一分子,那么人类就应该与自然呈一种和谐的关系,并且要善待自然,不仅要爱护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同时也要关爱自然界的其他物种。人的最后归宿也是回归自然。显然,这次新冠病毒肺炎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大自然对于人类大量耗竭其资源并长期以来未能善待它所施行的一种严厉的报复。确实,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每个国家都要谋求发展,争取早日实现现代化。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现代性大计在中国的实施使我们只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却忘记了中国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人口众多。人口众多就意味着要拥有足够的自然资源来支撑人们的生存和繁衍,但是毕竟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它迟早会被使用殆尽。尤其,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无度的消费和享乐,而忘记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因此我们在奢侈地使用各种自然资源时,还应当有着自觉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从而使得我们在致力于打造金山银山的同时,悉心地保护好自然界的绿水青山。
当我们在庆祝抗疫战斗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也应当严肃地反思,为什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自然灾害总是不断地侵袭人类,其根本的原因究竟何在?毫无疑问,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作为人类的成员,我们总是希望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来改造自然,让大自然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当然,在我们处于发展阶段时,这种“以人为本”的措施还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样,那些不善待自然的人也许现在还不明白,那种“以人为本”的愿望久而久之就会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因而在许多人看来,自然理应服务于人类,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只有牺牲自然的格局,宁愿“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也要满足人们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望。
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利用迟早会使人类受到无情的报复。确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类在对待自然方面犯了无数的错误,甚至不惜牺牲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而不遗余力地实施现代化大计,对此我们应该从环境伦理学的视角进行反思。不可否认,我们需要现代性,并欢迎它的早日到来,因为它毕竟给人们带来诸多福祉和发展的机会,使人们能够生活得更加幸福舒适。此外,现代性大计的实施也加快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在物质文化的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这种快速发展同时也刺激了人们的战斗精神,使他们不切实际地提出一些伤害大自然的口号: 人定胜天,以人类中心主义的意愿来重新规划自然环境,如此等等。
如果我们仅仅回顾一下最近几年来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就不得不正视这样几个事件: 地震、火山喷发、台风、洪涝灾害、酸雨以及海啸。所有这些自然灾害都使我们想到,地球的承受力已经被人类扩大到了极限。大自然正在无情地向人类进行报复,它不仅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秩序,而且夺去了成千上万的人们的生命。十多年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暴发的非典,就已经使得人类的持续繁衍罩上一层阴影,而海啸在印度洋的出现则更是向我们警示了自然界的这种报复。也许当前仍在蔓延的新冠病毒肺炎就是对人类实施的最厉害的一种惩罚。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员,我们不仅珍爱自己的生命,同时也更加珍惜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命。因此我们要负责任地善待自然和我们的生存环境,以便能够留给子孙后代一个美好舒适的环境。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有责任保护自然和我们的生存环境,并且建构一种人与自然得以双赢的环境伦理学。这种伦理学的主旨就是: 人与自然应该始终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因为人本来就来自自然,人类固然需要发展自己,但是人类的发展不应该以牺牲自然和改造自然环境作为代价。也许最为理想的方式就是找到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双赢方式。再者,在这种新的环境伦理学的指导下,人类应该平等地对待自然,将自然环境看作是自己的朋友和邻居,尊重它的发展规则和固有的格局。也就是说,人类应该既发展自己,同时又不破坏自然环境,这样才可以达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我想这应该是我们从新冠病毒侵袭和残害人类的过程中汲取的教训和得到的启示。
三、 人类的现状及未来: 从自然之神到“后人类”阶段
近十多年来,在国内外学界,关于“后人类”(posthuman)现象以及“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问题的讨论如火如荼,笔者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并发表了一些文字。(5)关于笔者这方面的著述,参阅: 王宁.“后理论时代”的后人文研究: 兼论文学与机器的关系[J].外国文学,2013(2): 119-127;王宁.后人文主义与文学理论的未来[J].文艺争鸣,2013(9): 27-29;王宁.“后理论时代”的理论风云: 走向后人文主义[J].文艺理论研究,2013,33(6): 4-11;王宁.科学与人文的冲突与共融: 兼论后人文主义语境下的数字人文[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70(4): 7-15;王宁.当代生态批评的“动物转向”[J].外国文学研究,2020,42(1): 34-41.以及英文论文: Wang Ning. Humanities Encounters Science: Confronting the Challenge of Post-humanism[J]. European Review, 2018,26(2): 344-353; Wang Ning. The Rise of Posthumanism: Challenge to and Prospect for Mankind[J].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12(1): 1-13.我的主要观点可以这样简略地加以概括: 面对自然的威力,个人的力量是十分渺小的,即使是一个经济实力强大、政治影响广泛的国家在自然的威力面前有时也显得微不足道。我的这些观点为新冠病毒在全球传播和蔓延所带来的后果所证实: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四月份不幸感染上新冠病毒,不得不住院治疗。当然在英国十分先进的医疗技术以及医护人员的精心护理下他很快就治愈出院,并继续行使自己的职权,这当然是个人的案例。至于强大的国家之案例我们则可根据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数据窥见其一斑: 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9月1日12时28分左右,美国累计确诊6 030 587例,累计死亡183 597人。(6)关于这一数据,参阅(国际疫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新冠死亡病例超85万例(2020-09-01)[2020-09-01]. https://www.360kuai.com/pc/985e99dcb585d0027?cota=3&kuai_so=1&sign=360_e39369d1&refer_scene=so_54.如果我们进一步提出两个问题就不难看出这两个案例的严重性: 首先,就约翰逊首相而言,如果他不是英国首相或内阁高官的话,他能够享受如此优越的医护条件并快速康复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其二,就美国这个当今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而言,美国的医疗技术和护理条件无疑是世界一流的,当然由于特朗普政府未及时采取严厉的遏制措施,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但是即使如此,为什么美国会出现那么多的新冠病例?再者,为什么在这些新冠病例中又会有如此之多的人丧生?排除其应对措施和治理手段的不力,这一事实至少证明了我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一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权力和多高的地位,在自然灾害和病毒面前都是十分渺小的,冷酷的自然依然会无情地对他进行伤害甚至夺去他的生命;同样,一个国家不管多么强大,不管其财富有多少,面对自然灾害和病毒的侵袭同样显得微不足道。这就使得人类曾经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发生了动摇,人类已经被自然拉下了神坛,又返回到初始状态——自然界万物之一种,与动物的差别仅在于其智力和情感的高低之差别。因此大写的“人”(Man)在当今时代便成了一种“后人类”。他与包括其他动物在内的自然界万物应该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的地位被贬低了,人又回复到其“前人类”的初始状态,即动物的阶段;而恰恰是动物及自然界万物的地位被提升了,也由于人类对动物之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程度也有了新的认识。自然界万物是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物链的重要一环,一旦这一生物链断裂,人类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动物也应该受到人类的平等对待和关爱,这样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才会得以实现。
如上所述,作为人类的成员,我们确实应该善待自然,视自然为我们的朋友和邻居。此外,作为自然界万物大家庭的成员,动物也应该受到人类的平等对待。目前在西方乃至国际学界,一些专事生态环境研究的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同样出自自然界的动物,他们从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的著作中找到了这种“动物转向”的思想。(7)关于这种“动物转向”的详细讨论,参阅拙作: 王宁.当代生态批评的“动物转向”[J].外国文学研究,2020,42(1): 34-41.确实,德里达不仅对任何主张“中心意识”的现象采取了批判和消解的态度,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注意到了长期存在的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并在自己的两部著作中聚焦动物,通过考察人与动物的关系来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 《所以我才是动物》(TheAnimalThatThereforeIAm, 2008)通过一只猫窥视他洗浴这一现象总结到,人也是一个具有动物性的物种,而动物作为地球上的万物之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通人性的,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与人进行交流和沟通;《野兽与君王》(TheBeastandtheSovereign, 2009, 2011)则探讨了动物与人类有着种种差别的原因。这两部著作在德里达逝世后迅速被译成英文,并推进了英语世界的“动物研究”(animal studies)。这无疑标志着德里达这位解构主义大师在进行了一系列解构尝试后最终将解构的笔触直接指向人自身。(8)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讨论,参阅Jane Goldman. Ecce Animot: Animal Turns[M]//Jean-Michel Rabaté (Eds.). After Derrida: Literature, Theory and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61-179.
滥食动物是破坏自然也危及人类本身。有些动物,例如老鼠、穿山甲、蝙蝠等,携带并传播病毒,给人类造成致命的伤害。因此,滥食动物不仅会使人染上疾病,而且也会导致地球上的生物链断裂。久而久之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恶性膨胀: 一切都为了满足人类的欲望,而不顾及自然的规律。从反人类中心主义伦理的视角着眼,我们则不应当食用野生动物,而应当把它们保护好,从而使得自然界的生物链得以维系。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本身也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而着想。如果我们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对待自然以及自然界的动物,我们就能够维持人与自然以及其他动物的和谐关系,而不至于经常受其伤害了。因为所有的自然界万物,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生活在一个硕大无垠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ary community)中,他们共同分享着彼此的切身利益,同时也彼此承受着共同的命运。这应该是我们从此次新冠病毒肺炎在全世界的传播和蔓延之后果中得出的教益。
四、 迎接“后疫情时代”的挑战
毫无疑问,新冠病毒的出现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蔓延给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导致了一些令人始料不及的后果。但是随着疫情的逐步缓和并渐趋结束,我们将步入一个“后疫情”时代(“post-epidemic” era),正如阿甘本在描述意大利所采取的抗疫措施所导致的后果时所概括的,这些措施包括:
(1) 禁止任何人离开受影响的市镇或地区;(2) 禁止任何人从外界进入受影响的市镇或地区;(3) 暂停在公共或私人场所举办任何性质的活动或举措,以及任何形式的集会,包括文化、娱乐、体育和宗教性质的活动或举措,包括向公众开放的密闭空间;(4) 关闭各级幼儿园、儿童保育服务机构和学校,关闭学校、高等教育活动和专业课程,但远程教育除外;(5) 根据2004年1月22日的法令,《文化和景观遗产法》第101条所列博物馆和其他文化机构和空间不对公众开放,关于自由进入这些机构和空间的所有规定也暂停执行;(6) 暂停在意大利和国外的所有教育旅行;(7) 暂停所有公共检查程序和公共机构的所有活动,但不妨碍提供必要的公用事业服务;(8) 执行检疫措施,并对与确诊感染病例有密切接触的个人进行积极监测。(9)Cf. Giorgio Agemben. L’invenzion di un’epidemia[EB/OL].(2020-02-26)[2020-06-21].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l-invenzione-di-un-epidemia.
这应该是意大利政府从中国的成功经验中获得启示并采取的积极的抗疫措施,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积极的措施却受到了阿甘本等左翼思想家的批评。但实践证明,正是上述果断措施的实施才有效地遏制了意大利的疫情,使其新的确诊病例归零。(10)这方面的疫情最新数据,可参见: 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EB/OL].https://voice.baidu.com/act/newpneumonia/newpneumonia/?from=osari_pc_1.毋庸置疑,疫情的到来迫使我们对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进行重新调整。面对各大餐馆的暂时关闭,热衷于享受美食文化的人们不得不在家自己做饭,或者订购外卖食品;面对旅游景点的关闭和社区的封闭式隔离,喜欢旅游观光的人们不得不自我封闭在家里,在电视或网络上欣赏情节动人的电影和精美绝伦的山水图片;对于那些喜欢交际的人们来说,面对实体互访和朋友聚会的暂时停止,他们不得不改为通过视频和微信进行频繁的交流;但在阿甘本看来,“比这些措施所暗示的对自由的限制更令人悲哀的是,这些措施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另一个人,无论他是谁,即使是他所爱的人,也不能被接近或触碰——事实上,我们和他之间必须保持距离。”(11)Cf. Giorgio Agamben. Contagio[EB/OL].(2020-03-11)[2020-06-21].https://www.quodlibet.it/giorgio-agamben-contagio.面对学校的关闭和实体教学的暂停,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也不得不掌握网络技术,实施在线教学,从而使得正常的教学工作得以不同的方式维持,如此等等。这一切都使我们既有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完全打乱了,我们不得不去努力适应一种新的战时形势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诚然,面对上述这些现象,一些反全球化的人们认为,既然全球化导致了疾病的传播,那就得实施“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或“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的战略。但我恰恰认为,上述这些应变措施的实施正是全球化的力量以另一种方式的体现: 全球联通性(global connectivity)和大数据的管理。在这方面,互联网再次发挥了强有力的全球联通作用,它使我们得以在云端进行交流。确实网络的普及解决了人们的许多生活和工作上出现的问题,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后果。诸如那些曾经极大地受益于全球化的旅游、餐饮和电影娱乐企业成了全球病毒传播的直接受害者,有些企业直接濒临倒闭,而大多数企业则通过裁员和削减行政开支等措施来维持生存。作为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我们的教学工作也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些新的教学和研究生指导模式应运而生,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一些效果。因此,面对这一情形,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措施迎接这些新的挑战呢?这正是我在结束本文前需要略加阐发的一个方面。
首先,新冠病毒的全球传播和蔓延使得我们不得不暂停实体教学,而改为在线教学,研究生的论文答辩也改为在线答辩。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将在“后疫情时代”继续实践。这就对我们的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那些恪守传统观念的人文学科教师,并不喜欢甚至抵制高科技的辅助教学手段,他们依然习惯于拿着一本教科书和一支粉笔走进教室,通过面对面的授课和现场的即兴发挥阐述自己对经典哲学和文学名著的阅读感受。确实,聆听这些学识渊博的教师授课,对学生不啻是一种享受,学生有时可以通过教师的面部表情和言语声调的抑扬顿挫得到直接的理论和审美教益,而这种效果在网络上是得不到的。面对疫情的冲击,教师们不得不学习电脑和网络操作技术,有时线路的卡顿直接使自己的思维中断,而与学生的互动也隔着一层冷漠的电脑屏幕。但是优秀的教师依然迅速地适应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我本人作为一位长期从事人文学科教学的教师也是这样: 从开始的不适应到逐步适应。通过视频教学,我们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备课,有时甚至将自己要讲授的内容写成文字,从而更加规范和精炼了我们的授课内容。在完成一次在线授课或网上公开讲座后,我不禁惊异地发现,正是由于自己的精心准备,一篇学术论文的雏形已经完成,只需稍加润色文字和核实引文数据,我就可以将自己基于授课或讲座写成的论文发给期刊编辑。而那些懒惰和不思进取的学者则颇不情愿地应付这种教学方式的改变,他们也许会在疫情过后惊异地发现,几个月的居家工作,自己竟然一事无成。这就再一次说明,成功在于勤奋学习,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来的。
其次,疫情的波及也使我们大规模地取消了学术会议和论坛,改为视频会议和在线讨论。这既节省了大量的学科建设经费和人力、物力,又使得更多的由于繁忙的教学工作和有限的科研经费所限不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青年学者有机会一睹学术大师之风采。同时对于我们人文学者来说,也可以省下旅途所耗费的时间,静下心来认真阅读那些由于往日工作的繁忙而无法阅读的书籍,把自己一拖再拖的科研项目认真完成并提交结项。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网络去在线阅读那些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最新论文,以便充实自己未来的教学和研究。而这一点在以往则是无法保证的: 冗繁重复的文山会海使学者们难以静下心来阅读并充实自己,同时也占据了他们本来可用于思考并写作的宝贵时间。
再者,由于疫情的波及,我们人文学者的研究生指导工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人文学科的研究生导师经常通过读书会和定期约见学生讨论等形式指导研究生,而疫情的波及则使这种传统的“耳提面命”式的指导不得不中断,而代之以互通电子邮件、微信和电话交流等方式来完成论文的指导。这无疑对我们的研究生导师提出了新的挑战。我自己虽然不用微信,但我总是要求学生将自己的论文初稿通过邮件的方式发给我,以便我在仔细阅读后直接进行修改,然后将修改过的论文连同自己的建议一并发给学生。这样不但没有耽误自己的论文指导工作,反而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导师的指导性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最后达到答辩或发表的水平。
也许有人会认为,疫情的暴发使得许多单位大规模裁员,一些不会操作电脑和网络教学的高校人文学者也面临着被淘汰的危机。而我则认为,疫情的暴发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秩序确实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但也为努力勤奋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时间,使我们能够潜心读书,勤奋著述,深入思考一些以往来不及或根本无暇去思考的学术理论问题。这样看来,我们完全可以将不利的因素变为有利的因素,为未来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做好必要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