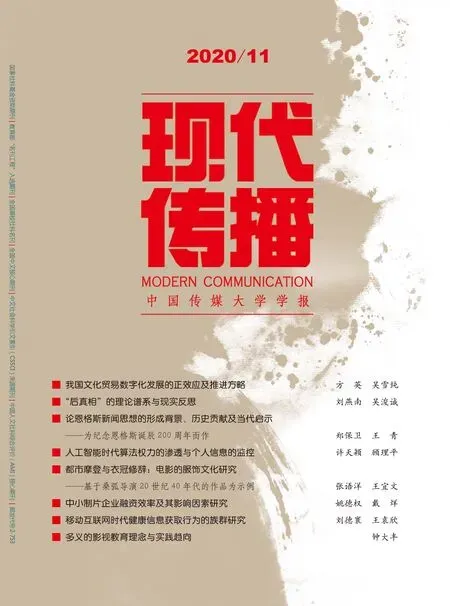纪实真实与艺术真实:奥斯卡获奖影片的非虚构元素研究
■ 潘 桦 孙 一
一、问题的提出
新媒介背景下,信息传播的便捷与迅速让镜头下个体的经历和命运被无限放大,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主角和时代的脚注。摄影机的特性在于揭示真实①,因而电影就成为了记录与诠释个体生命故事、为特定群体发声的重要媒介。在根据真实故事和纪实作品改编的影片中,如何对“非虚构元素”做电影化的处理,又如何寻求叙事与现实、艺术与纪实之间的平衡,是创作者绕不开的问题。
2020年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上,根据福克斯新闻网2016年的性侵丑闻改编的电影《爆炸新闻》(2019)获得了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奖。片中饰演梅根·凯利(Megyn Kelly)、格蕾琴·卡尔森(Gretchen Carlson)、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的几位主要演员通过精湛的化妆与造型设计,与真实事件中的原型人物十分神似。影片的出彩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真实人物的精心刻画,但片中直面职场潜规则的重场戏,并非现实还原,而是虚构而来——福克斯新闻董事长在办公室命令年轻漂亮的女制片凯拉为自己转圈并提起裙边供他欣赏。作为片中的主要角色之一,这名女制片凯拉虽然是“虚构”人物,但她却是福克斯性侵丑闻中许多当事人经历的集合,电影的创作人员还曾对当年指控福克斯新闻高管艾尔斯性侵的多名女性做了访谈。②创作者不仅在叙事和艺术上对虚构人物进行了加工,同样也利用了“非虚构元素”来为人物增色。
近年来,很多带有纪实色彩的电影作品摘得了奥斯卡的众多奖项,如改编自纪实小说并获得2020年最佳剪辑奖的《极速车王》、2019年的最佳影片《绿皮书》以及2018年获得最佳男主角奖的《至暗时刻》等。作为历史最悠久也最能体现大众审美的媒体奖项,奥斯卡“小金人”既象征着电影界的至高荣誉,也代表了媒体和观众的肯定与青睐。在揭露真相与还原历史的欢呼声中,这些涉及“非虚构”人物与事件的影片也引发了来自各方的质疑:其一,由于电影中往往会强调和省略诸多细节,有时也会对事件进行“再次编辑”和“演绎”,如此难免会遭到当事人的非议;其二,在“非虚构”背景下,源自真实的震撼力量才是电影的魅力所在,而过多戏剧化的虚构内容难以令观众信服。关于非虚构类题材,电影创作者面对一个重要困境,就是纪实呈现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取舍问题。
二、从新现实主义到非虚构
早在20世纪40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倡导把摄影机面向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抗争,最终成为二战后西方电影写实主义阵营最有代表性的创作理念。新现实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导演卢基诺·维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曾说:“新现实主义首先是个内容问题。”电影《大地在浮动》(1952)中纪实性的表现方式令影片具有了一种独特的魅力。反观当下创作者对于“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追捧,体现了对民众生存现状与社会问题的聚焦,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主张在内涵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在2019年的奥斯卡获奖名单中,电影《绿皮书》《黑色党徒》和《假如比尔街能够讲话》均改编自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分别反映了不同时期黑人在美国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种族问题在今天依然是美国社会的热点。
新现实主义运动发轫于二战结束之际,由于制片上受到战后经济条件的限制,在创作手法上较为平白,最终发展成了非情节化和非性格化的艺术主张。③苦守写实主义的传统而没有变通,必将在创作过程中固步自封。艺术源于生活,但对现实世界的机械复制反而会抑制创作的生命力;电影是关乎叙事的艺术,利用非虚构元素进行创作的电影也并不意味着全面忠诚地搬演和还原物质现实。叙事学专家们也承认叙事本质的虚构特性,如马克·柯里(Mark Currie)认为:“要想使自我意识以叙事的形式出现,它就得在叙事的那一刻放弃自我意识,这使得自我意识与撒谎处于同一逻辑地位。”④当非虚构的理念走进虚构领域,“叙事”与“非虚构”即形成了一对矛盾体,但这并不妨碍摄影的真实性与戏剧化的幻像性在一部现实题材的电影中并行不悖。
何谓“非虚构”?对于“非虚构”的理解,可以借用文学领域中的一些观点。作家王安忆认为,“非虚构就是真实地发生的事实”,是漫长的时间段中一种无序的自然状态。⑤非虚构作家梁鸿提出了“非虚构写作就是报告文学”的说法。报告文学是指介于新闻报道与小说之间,兼有新闻与文学特性的散文。同样,根据“非虚构”事件改编的影片也普遍兼具纪实性与叙事性。
无论是《极速车王》这样的传记影片,还是像《爆炸新闻》一类的剧情片,要彻底以“非虚构”的方式呈现是不可能的。根据真实人物或事件改编的电影既不是纪录片,也不能被简单地划归为“非虚构电影”。目前在媒体报道和各类学术研究中,关于“非虚构电影”的说法五花八门,并未有统一的界定。“非虚构电影”的源头要追溯到电影产生之初,如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和《婴儿午餐》等作品,这类“电影”的共同特征是从根本上排斥叙事性的存在。在诺埃尔·卡罗尔(Noel Carroll)的电影理论中:非虚构电影,包括故事性的非虚构电影,不需要按照它们的叙事结构,并以之为必要的虚构,也不需要把它们当作是对历史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强加或歪曲。⑥由此可见,在电影艺术的推动下,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严密界限已经被逐渐侵蚀了。
“非虚构”与“现实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但无论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宗旨与否,电影只能以现实一定的再现形式为出发点。⑦在以“非虚构”原型为创作基础的影片中,叙事素材来源于自然和真实生活,影像通过对直接和具体现实的观察去描述“存在”;叙事结构同样是必备的虚构成分,因为电影需要以一定程式的、或多或少的虚构存在去揭示本质。⑧电影只有对 “非虚构元素”进行叙事化的处理,才有可能找到呈现内容的最佳形式,进而从记录层面走向更深层意义上的真实。
三、奥斯卡获奖影片中的“非虚构元素”
在近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中,“非虚构元素”的出现总能让人眼前一亮,电影中对于“非虚构元素”的呈现,主要集中在人物、事件和细节三个方面。
第一,电影中的“非虚构”人物,首先是历史和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物,通常会由外形与之相似的演员扮演。相比于非虚构文学,电影具有图解式的视觉表达手段,凭借化妆、造型以及视觉特效等手段,可以让片中人物与真实原型达到形神皆似,这是影像表达的优势所在。电影《爆炸新闻》中,梅根·凯利的扮演者查理兹·塞隆(Charlize Theron)从造型到神态、举止,都再现了干练的电视新闻主播气质。影片《极速车王》中肯·迈尔斯(Ken Miles)的扮演者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在外形上与真实人物有很高的相似度。在2013年的影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中,扮演主角罗恩·伍德罗夫(Ronald Woodroof)的马修·麦康纳(Matthew McConaughey)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为了演好这个病入膏肓的艾滋病病人,他在开拍前减掉了近三分之一的体重,罗恩的家人在看到马修在剧中的造型时说:“他看起来和罗恩生病后每况愈下的状态太像了。他的眼睛,眼睛里的神情,是最重要的。”⑨
有很多带有传记性质的剧情片中的主人公是家喻户晓的政治家、科学家等公众人物,扮演者的形似既体现了对历史史实的尊重,也有利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如电影《林肯》(2012)中的美国总统,《至暗时刻》(2017)中的丘吉尔和《万物理论》(2014)中的霍金,这些人物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一方面扮演者形神兼备地演绎这些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符合观众的心理期待,另一方面对于人物的高超还原即是传记题材影片的亮点所在。
另一类“非虚构”人物是“文献综述”式的形象,这一类往往是根据众多真实人物集结而成的“虚构”角色。例如《爆炸新闻》中的性侵受害者凯拉。影片的末尾展示了多名在福克斯性侵案中勇敢站出来作证的女性的照片,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受到保密条款限制无法公开发声的当事人,她们共同的遭遇,汇集成了凯拉在办公室的“潜规则”经历。该片的导演如是形容这场戏的拍摄:“我从未拍摄过如此令人痛苦的场景。”⑩片中的凯拉从遭遇性侵、被同事冷落到奋起反抗的历程,完全是以现实中的人物经历为基础,富有创造性地呈现了在特定环境中可能发生的事实。这一场戏既是艺术创造的产物,也是对现实本身的反映。与凯拉形成对照的是片中的真实人物梅根·凯利,作为一位全球顶尖新闻平台的女主播,一面不断发出种族歧视言论,另一面也有过遭受上级骚扰的辛酸过往,从“硬核”沉默到坦然发声,她的人物弧光本应是点睛之笔,但影片却过于简化了凯利这一形象的复杂性与暧昧性。在这一对角色的对照中,“文献综述”式的人物在表现力上更具有“杀伤力”。
第二,电影对“非虚构”事件的呈现必须具有合理性,“合理”与“真实”可以相得益彰。电影的时长和画框内只是一个临时性的界限,不会是对某一事件的实录。媒体总会不厌其烦地寻找影片背后的真实故事,从而与片中的呈现进行对比或提出质疑。奥斯卡近年的获奖影片虽然在呈现的方式和选取的角度各异,但在改编过程中都体现了对基本事实的尊重。
对待“非虚构”事件中的争议话题,电影可以做出适当的省略。关于电影《极速车王》中的赛车手原型肯·迈尔斯之死曾引发巨大的争议,媒体也曾报道过多种猜测和说法。在电影中,迈尔斯在赛车场上的疯狂与执着表现得淋漓尽致,最终,他在一次常规试车过程中不幸遇难。影片略过了最有争议的部分,并未对此作过多的解释,如此“省略”增加了传奇人物的神秘色彩,同时也保证了影片叙事的完整性与合理性。
对于“非虚构”事件中的无序性,电影可以在尊重历史背景的情况下对时空进行适当地改写。在电影《绿皮书》中,非裔美籍音乐家“唐博士”雇佣意大利裔美籍司机托尼·利普穿越美国南部腹地巡演的故事是真实存在的。但为了保证叙事的效率和节奏,电影对两人的公路旅行作了“缩放”处理。电影中两位主人公的“公路之行”仅仅用了两个月,而现实中的这次南部巡演整整持续了一年半的时间。编剧之一尼克·瓦莱隆加(Nick Vallelonga)称这是对史实的“创造性修改”。根据皇后乐队真实经历改编的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也有类似的处理方法,影片的时间线横跨皇后乐队从成立到1985年“拯救生命演唱会”(Live Aid)的历程。在现实生活中,主唱Freddie于1987年被确诊患有艾滋病,而电影的讲述结束于1985年的演唱会。由于感染这种特殊疾病的经历是Freddie生前较为重要的一部分,为了全面展现主角的命运,电影在保证故事合理和真实反映人物形象的基础上,修改了叙事的时间线。
第三,在电影中巧妙运用现实中的“细节”,可以提高人物认同感与真实感。在电影《绿皮书》中,唐博士在路上多次帮助托尼给妻子写信的经历确有其事,编剧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也参考了原始信件。朗读信件的几个片段成为了影片中难能可贵的温情插曲,也为托尼家人与唐博士的和解埋下了伏笔。影片名中的“绿皮书”在历史上也“确有其书”,它是一部美国种族隔离时期黑人驾驶出行的指南,书中详细记载了全美对黑人较为友善的餐厅、旅社,以及哪些地区在夜晚禁止黑人出行。“绿皮书”的出现也让种族歧视背景下的紧张氛围更为真实可感。除了像“绿皮书”这种能够反映时代背景的细节,空间环境细节的刻画也十分重要。2016年上映的影片《萨利机长》根据2009年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迫降的事件改编,电影不仅在视觉效果上真实地还原了飞机在发动机失灵状况下的种种细节,其中飞机营救戏的拍摄地——哈德逊河面,即为现实中真实的营救地点。
在现实主义电影创作中,纪实与虚构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克拉考尔曾说:“哪怕是最有创造性的电影导演,他们跟未经加工的自然之间的关系,也要比画家或诗人密切得多。”但电影又是一种再现的艺术,它需要依靠搬演来展现复杂多样的外部现实,如果电影中没有了任何虚构的成分,表现“非虚构”的内容也将无法实现。只要搬演的世界能够使观众感到忠实地还原了真实世界,那便是合理与正当的。
四、关于电影中“非虚构”元素真实性的辨析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影评人彼得·莱纳(Peter Rainer)对奥斯卡曾有这样的评价:“奥斯卡奖很少直接反映国家的时代思潮或者社会气候。反过来,学院通常是奖励那些商业成功的,‘为产业增光’的电影……”在当下,这一评价显然是一种过时的刻板印象,那些演绎真实事件的现实题材影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创作者也将目光对准了“非虚构”的富矿,电影的真实性再次被提到了审美的高度。
第一,在对“非虚构”元素进行电影化的拆解和重构的过程中,感性真实高于理性真实。电影不同于新闻报道,其传播效果的实现,主要依靠影像叙事对观众产生作用,而电影独有的感染力往往使其具有比新闻更强大且更“润物于无声”的教化作用。影片《爆炸新闻》通过对几名性侵受害者的刻画,渲染了职场女性在工作中的无助与艰难,鼓励女性为维护自身权益勇敢发声,这既是对于女权意识的普及,也是对物化女性的社会风气的一种扶正。2019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罗马》也呼应了女性话题,影片中的人物和场景很多都来自导演儿时的真实经历,但电影在人物塑造和情节上都做了戏剧化的处理,影像在感性上营造出的真实感往往具有更强的震撼力。导演通过一个在中产家庭工作的保姆视角,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的社会动荡。影片对主仆两个女人之间感情的细微变化刻画得细腻真切,这种感性层面的心理真实是打动观众的关键。
在中外电影史上,不乏有追求理性真实的极端案例。新现实主义运动趋于衰落之后,欧美又兴起了“直接电影”的创作风潮。导演根据自己的敏锐观察,在现实中寻找戏剧性的事件,在事件即将开始时就着手拍摄,并随着事件的结束而结束,创作者们称之为“纪录式故事片”。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电影的拍摄也顺应时代的潮流,为了能够迅速反映生活中的新人新事,“纪录性艺术片”应运而生,当时很多影片中的主要角色都由生活中的原型人物扮演,例如电影《黄宝妹》中的主要角色就由劳动模范纺织女工黄宝妹本人扮演。纪录性艺术片过分追求拍摄速度,情节单一,旁白充满了宣教的意味,在纪录之余,少了艺术的味道。无论是“直接电影”,还是纪录性艺术片,都在不同程度上排斥“出演”的概念,并且过分强调影片的纪实性,这种对于理性真实的机械式追求一方面受到当时经济水平、社会思潮和电影技术的限制,另一方面则代表着影像创作思维的僵化和后退。
第二,在伦理问题面前,对真实的追求应有所妥协。如媒体评价,奥斯卡奖越来越注重“政治正确”,近年的获奖影片普遍涉及了较为敏感的题材,如女权、同性、种族歧视、艾滋病等问题。在利用非虚构的事件背景进行创作时,必然要做伦理层面的考量,否则就有可能对事件当事人造成负面影响。
电影《绿皮书》上映之后在获得赞誉的同时也受到了质疑,故事主体的建构主要来源于原型人物白人司机托尼对黑人钢琴家唐博士的回忆,因而影片对待种族问题的态度屡屡因“白人化视角”受到诟病。在现实生活中,唐博士在生前并未公开过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但影片中唐博士与陌生男子在公共浴室被捕的情节隐晦地指明了他的同志身份。片中唐博士与家人的关系十分淡漠,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也并不相符。这类涉及隐私和略带负面效应的信息在银幕上展露无疑,无论影片中的内容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人物经历,对于当事人及其后代来说,都可能造成情感上的伤害。虽然从艺术上讲,影片展现了极为高超的叙事水平;但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影片的处理有欠妥之处。
第三,电影的特效技术也能“模拟”真实。巴赞的现实主义真实美学观主张以长镜头和景深镜头来表现时间和空间的真实,只要影像与现实相通,只要虚构而来的内容符合事物的本质,对真实性的追求就并不妨碍在银幕上展现非实在的内容。随着CG和特效技术的不断成熟,很多从前看似无法表现的题材和场面也都出现在了电影画面上,影像的真实性也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在对“非虚构元素”的展现中,同样离不开特效技术。电影《萨利机长》中的飞机迫降段落在真实环境中是无法拍摄的,但视觉特效技术却逼真地展现了飞机降落的紧张过程。影片《绿皮书》中的唐博士在小酒馆即兴弹奏,演员的神态动作与弹琴指法全景镜头的呈现完全是依靠CG技术合成的。片中真正弹奏钢琴的人是该片的作曲者,但近乎完美的特效演绎令人真假难辨。电影技术的不断进步让“以虚为实”成为可能,视觉特效可以让虚构的画面成为真正的“现实的渐近线”。
从历史、伦理、技术多重维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以非虚构素材为蓝本的影片中,一味追求纪实的真实既不现实,也不符合电影的创作规律。电影的放映终究要受到画框、时间和空间这些非真实、非自然元素的影响,既然叙事化和虚构化的手段必不可少,那么追求艺术化的真实也将是电影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五、结语:纪实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博弈
在新媒介迅速成长的背景下,每个人都是信息的发布者,都是自己生命故事的记录者和讲述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大众媒介时代自上而下的信息传播模式。如福柯所言,话语是被建构的,只有将话语赋予社会的底层,才能还原历史本真。如今的新闻、电视和电影对个体生命经历给予了空前的关注,正体现了当下媒介话语的转向。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银幕上的发声者:一方面,是新的媒介环境提供了不竭的灵感和素材;另一方面,创作者尤其需要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辨别真伪、去伪存真。
“非虚构”与电影之间的互动是双向的。当非虚构走进电影领域,电影的叙事化特征也影响着现实生活。在五花八门的自媒体平台中,很多人不惜以断章取义、歪曲事实、夸大其词的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以博取关注与点击量。同样,严肃新闻经过类似的“加工”之后也改头换面变成供看客娱乐的工具。在“娱乐至死”的时代,优秀电影作品对于纪实真实的恪守与追求显得难能可贵。
自“非虚构”走进电影创作,纪实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博弈就一直存在。“非虚构”不应仅是电影宣传中的噱头,也该是忠于历史和现实的态度显现。要达到纪实真实,创作者需要广泛掌握关于非虚构人物、事件与相关细节的信息,并从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内容予以展现,电影可以立足于不同的视角,但在反映客观实在的过程中应警惕偏见。艺术创作需要通过自身的形式和表象去表现现实的“本质”而非“本体”,揭示现实的本原也并不单纯依靠物质现实的再现。电影创作者以视听语言为基本手段,需要对具体实在进行归纳和演绎,在表象中抽丝剥茧,力求探寻事物的深层内涵,方能达到艺术的真实。
在众多斩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中,“根据真实故事改编”一类为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创作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模式。在再现现实的过程中,这些影片在纪实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达到了一种较为理想的平衡状态。对于叙事艺术来说,偏执于纪实性和艺术性的任何一方都将过犹不及,但二者恰能巧妙地融合;自然与象征、具象与幻想、虚构与非虚构可以在同一部电影中兼容并蓄,使纪实真实与艺术真实自矛盾走向统一。
现实中的离奇与荒诞,感动与温情永远具有不可预知、独一无二的魔力。近年来,利用“非虚构元素”进行创作的影片在各类奖项中屡获殊荣,同时也展现了不俗的票房成绩,这表明市场对此类影片的接受度在不断提高,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类型片所带来的审美疲劳,也对形塑大众审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 [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崔君衍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3页。
②⑩ Megan Garber:《〈爆炸新闻〉中最震撼的一场戏》,《大西洋月刊》,https://movie.douban.com/awards/Oscar/89/nominees,2019年12月23日。
③ [美]路易斯·贾内梯:《认识电影》,胡尧之等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287页。
④ [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⑤ 材料来源:https://www.sohu.com/a/5598405_108102,2015年3月11日。
⑥ 曾耀农:《非虚构电影与新有声电影——卡罗尔电影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贵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21—23页。
⑦ [法]让·米特里:《电影美学与心理学》,崔君衍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449—452页。
⑧ 聂如欣:《非虚构影片中的元叙事》,《福建艺术》,2007年第4期,第55页。
⑨ 每日邮报记者:《现实中的艾滋病患者:罗恩·伍德罗夫 》,每日邮报网,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2244249/Pictured-Real-life-AIDs-victim-Ron-Woodroof-tragic-life-played-Matthew-McConaughey-movie-The-Dallas-Club.html,2012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