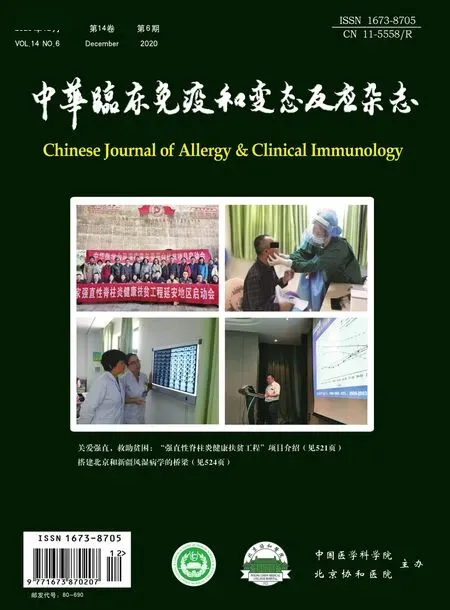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相关血管炎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临床特点
黄晓璐,李菁
抗中性粒细胞胞浆抗体(anti-neutrophil cytoplasmic antibodies,ANCA) 相关性血管炎(ANCA associated vasculitis,AAV)是一类毛细血管和小动脉、小静脉受累,导致全身多系统、多脏器损害的疾病,包括显微镜下多血管炎(microscopic polyan-giitis,MPA)、肉芽肿性多血管炎 (granulomatosis polyangiitis,GPA) 和嗜酸性肉芽肿性多血管炎(esoinophilic granulomatosis with polyangiltis, EGPA)[1]。AAV以血清中能检测到致病性ANCAs为突出特点,病理以小血管全层炎症、坏死,伴或不伴肉芽肿形成为特征,临床表现多样化,可累及皮肤、眼耳鼻、上下呼吸道、肾脏及神经等多个系统。 神经系统虽然经常被累及,但以周围神经损害较为常见,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包括颅神经损害则较为少见。已有临床研究发现,在不同类型的AAV中,神经系统受累的好发部位及发病率各不相同[2-6],临床上容易被忽视及误诊,因此提高对AAV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认识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主要对AAV相关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进行综述。
1 流行病学
尽管AAV相关神经系统损害并不少见,但CNS病变的发生率较低,目前尚缺乏大样本的流行病学数据,多为个案报告或小样本数据。André等[2]对88例EGPA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回顾性研究发现,EGPA患者周围神经病变最为常见、发生率高达51%,而CNS及颅神经损害在EGPA中分别只占5%和3%。另据Ceri等[7]报道,神经系统受累在GPA中发生率为22%~54%,主要病变类型是多发性单神经炎;而CNS损害在GPA中仅占7%~11%,主要表现为脑出血。日本学者Kato等[8]报道,脑出血在GPA相关CNS病变中发生率为6%。在MPA中,高达55%~79%的病例有神经系统受累表现[6],周围神经系统受累较为多见;CNS损害则相对少见,Decker等[3]报道其发生率为10%~30%。
2 发病机制
GPA累及中枢神经系统的报道较为多见,最常见到3个主要结构的受累:脑垂体、脑膜和脑脉管系统,相对应的致病机制有所不同,包括邻近结构侵袭浸润、CNS原位肉芽肿病变及全身血管炎的波及。具体表现为以下3种类型:首先,GPA具有侵袭邻近结构的特点,鼻咽腔等颅外肉芽肿性病变可扩展浸润眼眶、视神经、视交叉、颅神经、脑膜和垂体;其次,肉芽肿性炎性改变可以累及CNS中大脑、脑膜、颅神经和颅骨等结构;最后,GPA作为一种系统性疾病,中动脉及小动脉的血管炎可直接累及脑和脊髓的血管系统,表现为中枢神经系统节段性坏死性小血管炎,病理组织学上表现为淋巴细胞在血管壁各层的浸润[9]。
目前尚无MPA累及CNS发病机制研究的报道,基于MPA小血管节段性纤维素样坏死、无坏死性肉芽肿炎的病理特征,推测MPA累及CNS的发病机制与直接累及脑和脊髓中小血管以及血管壁各层的浸润性炎性改变有关,但炎症为何能穿透血脑屏障、是否存在对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的高度选择性尚未可知。
EGPA的临床表现比GPA和MPA更为复杂。嗜酸性粒细胞和小血管炎是EGPA诊断和发病机制的重要基础,因此EGPA中的组织损伤可能是坏死性血管炎和嗜酸性粒细胞增殖激活的共同结果,导致组织器官嗜酸性粒细胞浸润沉积和颗粒性细胞毒蛋白释放[2]。EGPA相关CNS损害可能源自血管炎和/或嗜酸性粒细胞介导的损伤,一些作者认为该损伤机制也与EGPA的周围神经病变有关[2]。
3 临床表现
中枢神经系统临床表现可在AAV初诊阶段被发现,也可以在复发后出现,甚至诊断前发现, Ma等[4]报道的一项29例单中心AAV中枢神经系统损害的回顾性研究分析中提到,从AAV初诊到出现CNS受累间隔的中位时间是12个月(9 ~31个月)。国外也有报道,从诊断EGPA到出现CNS病变间隔的中位时间为24个月,可能与EPGA易被漏诊、误诊相关[2]。
AAV患者的中枢神经系统表现多种多样。一般来说,当累及脑实质和颅神经时,常表现为单侧肢体无力和/或感觉障碍、偏盲、抽搐、持续性头痛、截瘫、癫痫发作等局灶性损害症状,也可出现精神症状、人格变化、意识障碍甚至昏迷等多灶性、弥散性损害的症状;当脑垂体受累时,可出现尿崩症的表现;颅神经损害时,常出现周围性面瘫、眼球运动障碍等;脊髓损伤则非常少见,时有病例报告肥厚性硬脑脊膜炎合并脊髓压迫症等较为罕见的表现[10-11]。此外,还有个例报道EGPA相关的可逆性后部白质脑病综合征(posterior reversible encephalopathy syndrome,PRES)[12],可见MRI T2加权像显示双侧枕、顶叶白质高信号的典型表现,应用降压治疗后,复查影像学异常信号消失,四肢无力症状好转。
3.1 不同类型AAV脑实质病变
GPA的主要CNS表现为:(1)脑膜炎:例如常表现为伴有头痛和颅神经病的肥厚性脑膜炎;(2)脑动脉血管炎(CNS血管炎):导致缺血性脑梗死、出血性脑病变(包括脑室出血、脑内或蛛网膜下腔出血)以及动静脉血栓形成[4,9,13-14];另有罕见报道在不同的血管区域同时出现多发性脑出血(SMICH)[8]。
MPA相关CNS病变非常少见,有限的病例报告多为脑卒中、脑实质内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SAH)、肥厚性脑膜炎等中枢神经系统病变,以缺血性脑病最多见[15]。
EGPA周围神经病变多见,CNS受累相对少见,文献报道最常见为脑梗死和蛛网膜下腔出血[2,5,16]。André等[2]报道了88例EGPA合并CNS损害的患者,52%表现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变(46/88),33%为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视神经炎和皮质盲区引起的视力减退(28/85),24%为脑内出血和/或蛛网膜下腔出血(21/88),21%为颅神经麻痹(18/88);其中有25例患者有一种以上的CNS表现;随访发现,在81例可评估神经系统治疗反应患者中,出现神经系统后遗症非常常见,约占43%。
3.2 颅神经病变
颅神经病变常见于EGPA,面神经受累最为多见,其次为动眼神经、三叉神经、前庭耳蜗神经,还有少见的舌咽神经及迷走神经受累[2,17]。
3.3 脊髓病变
AAV相关脊髓病变非常少见,文献报告GPA合并脊髓病变较多,其次为EGPA,MPA合并脊髓病变罕见。临床表现包括,出血后脊髓压迫或原位脊髓肿块、肥厚性脑膜炎、原发性硬脑膜血管炎及炎症性脊髓炎,多数同时伴有其他系统受累表现[10-11]。
绝大多数AAV相关CNS损害的病例,伴有非中枢神经系统受累表现[3,6,18],而且表现多样,例如GPA常见上呼吸道病变(鼻窦炎、鼻出血、鼻痂、鼻塞)和下呼吸病变(肺部浸润性结节),EGPA常见哮喘,MPA常见出血性肺泡炎、肾脏病变(镜下血尿、肾皮质梗死、肾小球肾炎、肾衰竭)等。
4 诊断
由于CNS病变需要与多种疾病进行鉴别,包括感染、肿瘤、药物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因此对AAV相关CNS受累的诊断具有挑战性。对于中枢神经系统受累的患者,脑组织活检虽然被认为是诊断AAV相关CNS血管炎的金标准,但敏感性有限,且获取组织相对困难,活检创伤及风险性大,临床操作性不高。其他辅助检查手段如影像学,特别是脑血管MRI(MRA)对中枢神经系统内的缺血性病变检测敏感度高,可同时显示大面积脑梗死和广泛的白质病变,与小血管缺血性疾病影像学一致,但由于分辨率有限,对颅内微小动脉狭窄显示不佳,因此在鉴别AAV相关CNS损害方面缺乏特异性。此外,CT、MRA和常规血管造影术,只能偶尔显示动脉瘤性和/或狭窄性病变,但是AAV累及的脑血管多为小血管,受累血管的大小往往低于这些成像技术的分辨率而显示不清[19]。因此,无创的影像学检查和有创的血管造影,对评价AAV合并CNS受累患者的血管炎都有局限性。Kato等[8]等分析24例GPA相关脑出血病例发现,14例(58%)为脑出血(其中6例为多发性脑出血),其余10例(42%)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其中有11例患者行脑血管造影检查,然而仅1例发现动脉瘤改变,其余脑血管造影没有显著发现[8],提示常规脑血管造影对显示血管炎病变的敏感性很低。其他检查,如脑脊液、脑电图等,对诊断AAV相关CNS损害也缺乏特异性。因此,大多数患者的诊断还是基于临床特征,特别是非中枢神经系统症状,血清检测出致病性ANCAs特别是PR3-ANCA、MPO-ANCA,以及组织病理(特别是肺、肾、鼻窦及结节性红斑的活检)结果。研究发现,PR3-ANCA和MPO-ANCA这两种血清致病性ANCAs在AAV相关CNS损害患者中检测阳性率相似[20],但它们影响CNS的模式和严重程度不同;来自日本的一项研究发现,RP3-ANCA阳性者往往有更严重的神经损伤和更广泛的脏器损害[21]。
5 治疗与预后
通常,中枢神经系统受累被认为是AAV患者的重要脏器损伤,因此其主要诱导治疗方案为高剂量糖皮质激素联合口服或静脉环磷酰胺的免疫抑制治疗,活动期或病情严重者,还可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或行血浆置换等,从长期来看血浆置换似乎不能降低死亡或终末肾病的发生率[22]。已有临床试验显示,常规治疗无效的患者改用利妥昔单抗进行诱导可能有效[23-25]。硫唑嘌呤、甲氨蝶呤、利妥昔单抗和霉酚酸酯等药物可作为诱导缓解后维持治疗的备选药物[26-28]。临床研究显示,常规免疫抑制剂对于复发风险高的患者的维持缓解可能疗效不足,而利妥昔单抗似乎更有效[29]。另外,近年发现补体激活的替代通路在AAV发病机制中有重要作用,其中C5aR阻滞剂小分子CCX168(商品名Avacopan)用于AAV诱导缓解治疗的Ш期临床试验已证实其可能替代泼尼松,而且副作用较少,基于此结果进一步开展的Ш期临床试验(ADVOCATE研究),用于AAV诱导缓解和维持缓解治疗阶段,初步结果已于2020年欧洲风湿病年会发布,未来可能成为替代糖皮质激素治疗AAV的药物选择[30]。
并发神经系统损害的AAV患者经积极治疗后,多数神经系统症状明显改善[4,13],但有文献报道有CNS受累的AAV患者往往整体病情较重,可能和CNS受累范围广、因误诊漏诊未及时加用免疫抑制剂和/或糖皮质激素可能有关,若同时合并弥漫性多器官受累,往往提示整体预后不良[31]。Ma等[4]发现,在中国AAV患者中,CNS受累主要表现为脑缺血性病变;与无CNS受累的AAV患者相比,有CNS患者表现出更高的疾病活动度,同时伴发外周神经系统受累的比例更高,但总生存率与未合并CNS损害者无明显差异。
中枢神经系统血管炎的发生可能与AAV其他器官受累的病情活动度有关,如弥漫性肺出血[7]。因此,除了严重器官受累和复发难治性患者应用利妥昔单抗等经典治疗方法外,还可以考虑新的治疗策略如C5a受体选择性抑制剂Avacopan等[32]。
另外,目前大量研究表明,影响AAV患者预后的主要因素还是肺受累和肾功能损害,而继发感染和心血管事件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33]。来自日本的一项单中心回顾性研究分析小样本数据后发现,心肌损害、中枢神经系统受累和年龄大于65岁是老年MPA死亡的独立预测因素[34]。究竟CNS病变是否对AAV生存有明显影响,尚待更大样本量及更长时间的随访研究进行探索。
综上所述,AAV相关中枢神经系统损害发生率低,起病可为急性或亚急性,临床易漏诊误诊,且临床表现多样;目前尚无特异性影像学表现,诊断仍主要依赖其他系统症状及血清学特异性抗体;积极控制原发病,有利于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合并其他重要脏器受累的患者可能预后较差。本文提示,当AAV患者出现CNS症状应警惕原发病累及CNS的可能;以CNS症状为首发表现的患者,在除外常见病因后,应当注意询问其他系统的症状、排查ANCA相关血管炎的可能;尽早明确诊断、给予精准治疗,有利于改善患者长期生存及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