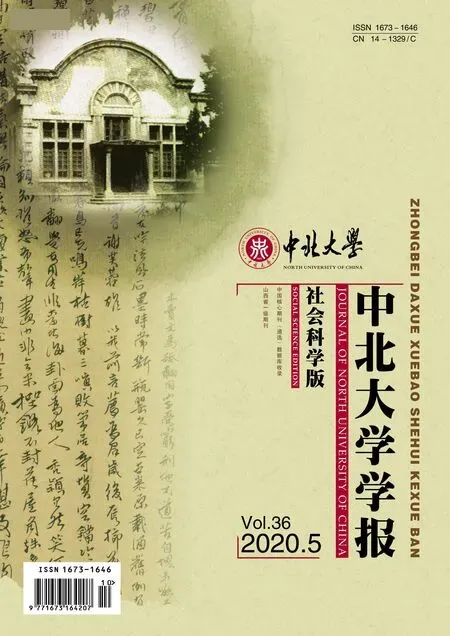“影像史学”探析:概念、 对象与操作*
刘金泉
(云南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00)
随着社会的发展, 历史的记录方式和传播途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世纪60、 70年代, 影像逐渐开始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 历史学者们对影像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诸多讨论。 1988年,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创造了“historiophoty”一词来研究影像如何书写历史。 中国最早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是台湾中兴大学周樑楷教授, 他将“historiophoty”翻译为“影视史学”, 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最早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大陆, 引起了大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 其中, 学者们争议较多的、 也是最基本的问题是关于影像史学的概念定义; 讨论较多的是影像史料的真实性、 影像史学与书写历史的关系、 影像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前景等问题。 这些问题亦是本文探讨的核心话题。
1 问题的提出
如果要追溯“影像史学”的源头, 大概可以从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拍摄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火车进站》谈起, 在电影诞生后第三年, 波雷斯拉特瓦·马绍斯基就先见地意识到了影像记录和传播的功能, 他认为影像具有巨大的史学价值, 并提议用影像记录人们的生活, 建立一个“影片博物馆或影片库”[1]77。 法国年鉴学派马克·费罗(Marc Ferro)在其《电影和历史》一书中展开了影像书写历史可能的讨论, 并将其视为一种“社会与历史角度的诠释方式”[2]23。 然而, 真正明确提出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登·怀特, 他在 1988 年发表的《HistoriographyandHistoriophoty》一文中, 发明了一个新术语即“historiophoty”来表述“影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3]。
国内最早从事这项研究的是台湾中兴大学周樑楷教授, 他将海登·怀特提出的“Historiophoty”翻译为“影视史学”, 他认为海登·怀特所说的“影视史学”主要是电影、 电视的研究, 是狭义的概念, “影视”应该是包括动态的和静态的视觉符号。 于是, 便提出了广义的“影视史学”概念, 一层含义是“以静态的或动态的图像、 符号, 传达人们对于过去事实的认知”; 另一层含义是指“探讨分析影视历史文本的思维方式或知识理论”[4]。 1996 年, 复旦大学历史系张广智教授, 将“影视史学”这一概念引入中国大陆, 并展开了一系列研究。(1)张广智教授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代表有:国内第一本探讨“影视史学”的学术专著《影视史学》, 1998 年在台北扬智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期刊文章主要有:《重现历史——再谈影视史学》, 《学术研究》2000 年第 8 期; 《影视史学与书写史学之异同——三论影视史学》, 《学习与探索》2002 年第 1 期; 张广智:《影视史学:历史学的新生代》, 《历史教学问题》2007 年第5期等。在张广智的研究中, 肯定了周樑楷对“影视史学”概念的定义及其扩展, 并从海登·怀特强调视觉影视即电影的角度出发, 以《鸦片战争》《红樱桃》《人约黄昏》等历史影视为例探讨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新景观。[5]
随着“影视史学”研究在国内不断发展, 学者们的讨论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吴紫阳认为, 周樑楷在《影视史学:理论基础及课程主旨的反思》一文中提出的“影像视觉的历史文本”[4]即广义的概念“可能还包括战场、 遗址、 文物、 雕塑、 建筑、 画册等等。”[6]陆旭认为周樑楷将海登·怀特对“影视史学”概念的扩展是画蛇添足之举, 海登·怀特原文中的“visual images”一词语已经包含了动静两种“视觉影像”, 故而他建议将“影像史学”理解为“以视觉构图和胶片话语表现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7]。 蒋保认为历史影视(历史题材电影或电视剧)是“影视史学”研究的误区, “historiophoty”翻译成“影视历史”或“影视史学”无法涵盖电脑、 收音机、 录音机等视听媒体, 所以“将‘historiophoty’译为‘音像历史’(‘音像史学’)或者‘视听历史’(‘视听史学’)较为适合 。”[8]。 孙逊则认为, “应该回归怀特的定义, 不追求将影视史学当成如同计量史学或口述史之类的研究方法, 而单纯当做一种历史叙事的表现手段。 从定义范围上将不适宜的静态视觉材料全部舍弃, 只保留电影等动态资料”[9]。
正是学者们不同声音的讨论引起了人们更多的关注, 笔者肯定以上学者对促进“影像史学”在中国发展做出的努力, 但并不完全认同上述学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 第一, “影像史学”比“影视史学”更为合适。 周樑楷将“historiophoty”一词翻译为“影视史学”已经取得国内学界大部分学者的认可, 但还未在学界达成统一认识, 如吴琼、 徐凡、 谢会敏、 周勇、 刘帆、 秦扬、 王灿、 王镇富等学者在文章中使用“影像史学”, 蒋保从其研究对象的范围考虑建议将其翻译为“音像史学”或“视听史学”。 从词意上来看, 影像是“人对视觉感知的物质再现, 从广义上来说, 它既包括由光学设备获取的照片、 影片和录像等, 也包括人为创作的绘画、 图像等。”[10]1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 “影视”是指“电影和电视的合称”[11]1563。 从这些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 “影像”包含静态的图像之意, 而“影视”则主要是指电影和电视剧作品等。 因此, 笔者有理由认为国内将“影视史学”等同于或侧重于历史题材电影、 电视剧的研究, 与对“影视”一词的理解不无关系, “因为从字面意思看, 容易让人误解成‘(电)影(电)视史学’, 而忽视了图像的作用”[12]。 因而, 笔者赞成将“historiophoty”翻译为“影像史学”而非“影视史学”。 第二, “影像史学”概念包含动静两种“视觉影像”的提法并没有界定清楚其概念范围, 反而使得“影像史学”概念的边界更加模糊, 容易陷入研究的困惑。 按照周樑楷等学者的观点, “影视史学”应该包括静态的视觉影像, 这样说来, 应该也包括发明电影之前已经存在的各种图画(绘画、 壁画)、 雕塑、 建筑等静态的视觉材料。 而困境之处就在于这些绘画、 雕塑等历史资料也是传统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换句话说, 按照这一界定, “影视史学”和历史学、 考古学等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有交叉, 并且模糊的边界还容易使“影像史学”的范围无限扩展, 难以把握和研究。 第三, “从定义范围上舍弃不适宜的静态视觉材料, 只保留电影等动态资料”完全不具备操作性。 孙逊的这一观点已经考虑到了周樑楷等学者上述观点的缺憾, 故而提出要剔除不适宜的静态视觉材料, 但是问题的关键也恰恰在这里, 什么是“不适宜”?“适宜”的标准又是什么?他未能做出解释说明, 未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界定。
基于以上考虑, 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界定一下“影像史学”的概念, 厘清一下研究对象的范围, 以便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2 “影像史学”概念界说
笔者认为, “影像史学”应该是一切电子视听设备产生的作品所传达的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 这一概念表述的“我们对历史的见解”与周樑楷、 张广智等学者的界定一样, 故不多赘言。 在此仅对不一样的地方做一点说明:电子视听设备包括摄像机、 录像机、 手机、 多媒体电脑、 录音(笔)机等, 以及现在发展迅速的能够利用各种数字化技术产生视听产品的各种软件或硬件。
第一, 电子视听设备产生的产品的记录和展示历史的方式有着相似的特征——利用声、 光、 色构成影像来记录历史, 而这些特征完全区别于传统的书写历史。 这里以摄影摄像作品为例来说明。 镜头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类”(2)本文借用王明珂对“文类”的定义, “文类是一种被沿用而产生许多文本之范式化书写、 编辑与阅读模式。”参见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第213-214页。, 有着属于自己独特的“书写”规则, 不同的镜头(焦距、 景深)、 景别(远景、 全景、 中景、 近景、 特写)、 拍摄角度(平视镜头、 仰视镜头、 俯视镜头、 倾斜镜头)、 镜头运动(镜头内部运动:横向、 垂直、 纵向; 镜头外部摄影机运动:推、 拉、 摇、 移、 跟)、 拍摄参数设置(升格、 降格)、 色彩、 光线传达出不同的含义, 如“不同的焦距镜头能够使观众产生不同的观影体验。 用广角镜头造成的物体或人物扭曲, 能够表达出某种特殊的意义或主体心理状态; 用长焦镜头把主体从背景中突出出来, 能够发挥镜头的强调作用”[13]48-49。 “平视镜头能够传达出旁观、 理性的色彩, 给人以客观、 公正、 真实的感觉, 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 仰视镜头一般可以造成某种优越感, 表示是一种赞颂、 敬仰和自豪等感情色彩, 这种镜头扩大了人物形象的内涵。 俯视镜头常用来表现人物境遇的凄惨或者品格的卑微, 带有压抑、 阴郁、 藐视的感情色彩, 也可以用来鸟瞰景物全貌, 介绍故事背景。 倾视镜头常被用于表现一些非常规的场面, 能够表现人物内心的焦虑、 紧张不安。”[13]59-60这些特征都是传统的书写历史所不具备的。
第二, 从视听产品的后期制作来看, 后期剪辑对事件顺序的改变、 特效的处理等有着许多特定规则。 电影发明之初, 就是几个简单的“长镜头”拼接在一起就算完成了一部作品, 但是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 不得不依靠后期剪辑来表现复杂且连续的情节, 于是出现了“蒙太奇”。 蒙太奇一词出自法语, 原意是“组接、 装配、 构成”之意, 是法国电影学家路易·德吕克(Louis Delluc)从建筑学中借用的概念。 郝朴宁、 李丽芳综合了学界对蒙太奇的各种观点, 认为“所谓蒙太奇, 即选择和组接诸镜头以构成影片意义整体的程序。 这一程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镜头内部各同质因素间的并列安排, 然后再选择合用的镜头单元; 二是诸镜头在临近关系或连续关系中的次序安排; 三是每个镜头长短以及各镜头间的‘过渡镜头’长短的时延确定。 而蒙太奇程序的根本旨意是在镜头内部的镜头之间分解电影元素并利用已分解的电影元素去构造新的艺术整体”[14]144。 此外, 后期剪辑对色彩和光线的处理也有特定规则, 色彩和光线不仅是画面内容的组成元素, 还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并传达出特定的情感。
第三, 这一概念界定强调的电子视听设备产生的产品, 排除了188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 录音机以前的那些绘画、 雕塑等视觉材料, 避免了“影像史学”研究对象无限扩大的困惑。 “科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是一门科学得以建立的前提。”[15]11研究对象范围的不确定是“影像史学”难以像历史学下其他分支学科如口述史学、 计量史学等快速发展并取得学界广泛认可的重要原因之一。 研究对象边界的模糊不仅造成了学者们对“影像史学”是研究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或纪实性纪录片的争议, 更严重阻碍了它的发展。 笔者提出的这一界定强调能够产生视听媒体产品的电子视听设备, 厘清了研究对象范围并且具有可操作性, 即为笔者提出这一想法的初衷。 此外, 电子视听设备产生的产品涵盖了所有视听媒体产品, 自然包括以声音为主的产品, 解决了相关学者提出的是否有必要理解为“音像史学”或“视听史学”的问题。 在此, 要强调绘画、 雕塑之类本身不是“影像史学”的研究范围, 如果经拍摄之后的作品, 就是“影像史学”的题中之义了。
3 研究对象的合理性
“影像史学”受到最多质疑的应该属研究对象的真实性问题。 笔者的这一界定虽然明确了研究对象的范围, 但是似乎也扩大了“影像史学”书写者的范围, 不仅涵盖了官方的组织、 社团、 科研机构, 更是包括了处于不同情境和意图中的个人, 并且还囊括了一些鲜有学者关注的题材, 如动漫、 游戏或者抖音、 快手等软件拍的短视频等。 因此, 对这些问题的阐释直接影响到了笔者界定的“影像史学”的理论可行性, 笔者认为:
其一, “影像史学”所研究的“影像”都有建构的成分, “真实性”不该是把动漫、 抖音短视频等题材排除在外的理由。 在上文已经说明, 影像是一种特别的“文类”, 用来表现该“文类”的视听语言有着自己独特的书写范式和规则, 在拍摄时视角的选取、 拍摄时的天气和光线都会影响结果的展现, 并且拍摄后期剪辑制作运用的蒙太奇手法、 配音、 调色等手段都可以使之与事物的本来面貌呈现巨大差异。 换句话说, 经现代化电子设备产生的视听媒体作品或多或少都有建构的成分, 不能因其建构成分的多少(并且不存在具体的衡量指标)就把个人拍摄的动漫或抖音短视频等题材排除在“影像史学”研究范围之外。 所以, 笔者不敢苟同王镇富所研究的狭义的影像“它的任何形象画面都必须直接采自现实生活,不能有任何虚构”[16]的做法以及张广智等学者以历史题材电影或纪实性纪录片等作为“影视史学”的研究路径。 此外, 在21世纪的今天, 人人都是历史的书写者, 用影像记录历史、 传播历史不该只是属于历史学家或影视专业人员的专利, 应该“把历史还给人民”[17]。 “中国历史上曾经创造了一个‘帝王本位’的‘国家史学’系统, 未来要建设一个‘公众本位’的‘公众史学’系统。 这是一个全新的民间史学系统, 书写对象、 参与人员、 书写方式、 使用方式, 均会不同于传统国家史学。”[18]因此,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历史方法的“影像史学”, 没有理由将民间的个人或其他形式拍摄的影视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其二, 传统的“书写史学”同样有想象建构的成分, “影像史学”所研究的“影像资料”的虚构问题不该是阻碍其发展的原因。 在以上的论述分析中, 展现给读者更多的是影像参杂了许多虚构和想象的成分, 影像所呈现的结果不等于真实的存在, 但书写历史中的正史和所谓的“信史”就是完全的“历史事实”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首先, 传统史学家在书写历史前所选用的“文类”, 已经确定了“文本结构”, 如正史多采用纪传体、 编年体等, 地方志只局限于一个地方风土物貌而难以展现与周边地区甚至更远地区存在的联系, 因而注定使得一些在当时处于边缘的史料难以入选史册, “过去我们的历史观念已经先在地设定了什么是应当叙述的, 什么是没有价值的, 所以, 那些被判定没有价值的东西, 在以某种价值来设计框架的历史章节中, 是找不到自己容身之处的, 就是有人想把他们写进去, 也不知道写在哪里为好”[19]。 史学家选择书写的“文类”就如同导演选择剧本一样, 在选择后书写就已经决定了该“文本”(3)此处借用王明珂定义的广义的文本, 指任何能被观察、 解读的社会文化表征, 如一个广告、 一张民俗图像、 一部电视剧或电影、 一个宗教仪式, 甚至一个社会行动、 运动或事件。 参见王明珂:《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文本与表征分析》,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 第148页。的主旨和整体走向。 第二, 史学家对“文本”章节的安排及遣词造句上的斟酌就如同导演对脚本在拍摄和剪辑方面的要求一样, 书写者要受到个人立场的束缚而带有主观感情色彩, 因而所呈现的结果也并非是完完全全的本来面貌。 例如, 欧阳修编纂的《新唐书》本纪部分鲜明地体现了“辨是非、 寓褒贬”的史观和“春秋笔法”的痕迹; 张艺谋导演“总是以一个‘反叛者’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他的作品既是对时代与传统的反叛, 更是向自我与过去的反叛; 在风格和性格上, 他偏于感觉和直觉的导演思维, 这种导演思维注重画面感, 通过强调构图、 色彩、 光线等造型要素, 以感性鲜明的影像风格, 映现或寄托主体情感”[20]。
其三, “书写史学”和“影像史学”同样需要想象力, 其作品都有想象建构的成分。 例如, 被称为“史家之绝唱”的《史记》中同样存在许多想象建构之处, 司马迁不在鸿门宴的现场, 而在《史记·项羽本纪》中却详细描绘了在场人员的言行举止。 李剑鸣也曾说过, “历史写作也需要想象力的参与。 研究者在史料的基础上, 再运用常识和见闻来想象事件的氛围以及人物处境, 写出的文章就可以引人入胜”[21]161。
4 “影像史学”的实际操作
上一部分论述了影像资料同文字资料一样存在想象建构的问题, 这一部分将借鉴史料学的知识从鉴别技术、 存档管理、 应用分析、 人才建设四个方面来探讨“影像史学”的实际操作, 即影像资料如何应用于历史研究。
第一, 追溯史源, 探究作者的生平背景和创作意图。 与传统史学对史料考据一样, “影像史学”同样需要考究史料(影像资料)的来源、 创作目的、 作者的史学观等。 随着科技的发展, “今天摄影的记录特质亦被新技术改变, 不再是光效、 构图、 影像, 而是‘raw.’格式将一切记录为数据——可以在后期重组、 再造的数据”[22]127。 所以, 影像资料的考据主要聚焦于拍摄(时间、 地点、 角度、 参数设置等)和后期制作(美化、 剪辑、 拼凑等)。 可以用来鉴别影像资料的方法主要有:一是EXIF信息分析法, “主要针对数码照片, 通过查看和检验数码照片的EXIF信息来对照片的真实性进行验证。 EXIF信息记录了数码照片的属性信息和拍摄数据, 主要包括拍摄相机型号、 日期和时间、 摄影参数、 数码相片参数、 作者标记等。 如果数码照片经过修改, 在EXIF信息中同样应有所体现, 包括修改时使用软件的名称、 版本以及具体修改日期和时间等”[23]。 二是图像盲取证研究, “在不依赖任何先验信息的情况下为鉴别图像真伪提供有力证据的技术, 其关键是找到充分、 可靠、 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证明图像是否发生篡改”[24]。 以上两种方法能够从技术层面鉴别一些图像的真伪, 但是“如果伪造者在篡改图像的同时利用反取证技术对篡改的痕迹进行消除或伪造, 那么已有的大量被动取证技术都将失效”[25]。 因此, 需要借助第三种方法, 即逻辑分析法。 逻辑分析法主要用于判断图像呈现的画面内容是否符合常理和逻辑, 主要聚焦于人或物能否出现在同一场景里以及人物的着装或话语是否符合所生活的时代背景, 例如番茄是明朝时期传入中国的, 而明朝以前的影像甚至是文字记载有番茄炒鸡蛋这一菜的均是后人的想象和建构。 此外, 我们也要像重视史料作者的史学观一样去重视分析影像创作者的生活背景及创作意图,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分析经过镜头记录和后期制作后所呈现的影像与事物本来面貌之间的差异。
第二, 孤例不证, 文字与影像资料的综合研究。 以影像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影像史学”并不以取代文字书写历史为目的, 而是丰富研究历史、 拓宽史料来源的一种方法。 一方面, 昨日相对于今日已经成为历史, 今日相对于明日也将成为历史, “今天出现的事物, 到了明天就成了史料”[26]13。 影像以其直观、 生动、 形象的记录优势, 可以与文字史料互证, “凡依据一切历史的、 现实的实物、 事象所拍摄的照片、 记录片及文艺表演影像, 均是视觉史料, 是理解、 阐释历史的史源之一种”[27]。 从历史上看, 随着史学的发展, 史料的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马克·费罗((Marc Ferro)曾说:“史学家会根据时代和使命的不同来选择采用这种或那种文献和研究方法, 对不合时宜的进行更换, 就像战士更换过时的武器战术一样。”[2]彼得·伯克(Peter Burke)也认为:“影像所提供的有关过去的证词有真正的价值, 可以与文字档案提供的证词相互补充和印证……在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领域中, 图像特别有价值的证词, 可以用它来证明街头贸易习俗, 而有关这一贸易的文字记载非常少见, 因为它们相对来说带有非正式的性质。”[28]293-294另一方面, 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事物本身都是客观的, 但使用影像对它们进行记录和展示却是主观的(文字书写同样如此)。 然而, 即使影像反映的不是事物的真相, 但虚构影像的这一过程本身, 也可以提供研究当时社会情境下国家意识形态、 社会文化取向、 创作者个人心态等方面的重要影像史料, 如大跃进时期的一些具有浓烈浮夸风的影像资料和文革时期的样板戏等, 再结合当时文字资料来进行文本分析, 才可能“更‘接近地’认识社会本相与历史事实”[29]258。
第三, 存用一体, “影像史料库”数字化平台建设构想。 影像既然可以作为一种史料应用在历史研究中, 那就必须要辨别影像的真伪, 从而判断史料价值的大小。 “影像史料库”可以分为官方账户和个人账户, 登陆后可自行上传影像, 经审核通过后可进入史料库。 鼓励个人拍摄上传, 入选史料库后可给予一定物质奖励, 这也是呼吁人人参与书写历史的一种手段, “当每个民众都有机会, 也有能力拿起影像工具来书写自己的历史时, 我们才能真正地、 无缝隙地对广袤的人类社会进程形成扎实、 均衡的影像记录”[30]。 “影像史料库”的前期筛选需要“建立一套考据的方法与标准”[30], 并且需要一批专业技术人员来严格把控, 只将那些相对真实客观、 具有研究历史价值的影像入选史料库, 入选史料库时需要进行分类编目处理, 并须注明拍摄和后期制作的一些必要信息。 在这里要强调, 这类经过考据入库的影像是可以直接作为史料使用, 不在史料库的影像并非没有史料价值, 而是在使用之前需要鉴别分析影像的真伪, 去研究制作虚假(伪造)影像的人所处的社会情境及其意图, 也可得到了解那段历史的有用信息。 当然, 这个构想不是一蹴可就的,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 以人为本, 培育“影像史学”专业人才。 人才是一个学科或者行业发展的必要前提, 也是上述三点设想可以顺利开展的保障, 笔者认为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中的历史学或电影学学科下培养“影像史学”方向的人才迫在眉睫。 首先, 要想做好“影像史学”研究, 必须要具备影视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影像“隐含了一套异于话语组织的代码, 一套光、 影、 颜色、 线条、 造型形成的表意符号, 一套特定的‘蒙太奇’式衔接, 这甚至将提供一套迥异的知识典范和‘真实’概念”[31]334。 如果一些不具备影视学知识和技能的历史学者来做“影像史学”研究, 恐怕是难以搞懂视听语言背后的含义和隐喻, 更容易被后期剪辑修改所迷惑, 那么这样的研究只能是局限于影像文本表面, 最终也逃不过“泛之于流, 失之于空”的命运。 其次, 必须具有历史学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掌握基本的历史学知识。 影像史学展现和传播方式更适合满足现代大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 因而在普及历史知识和历史教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 “影像工作者在从事历史节目的创作中, 则须禀承史量才所倡导‘史家精神’‘同人则以史自役’, 在史家思想和史学规范的指导下进行严谨的历史影像写作”[32]。 最后, 必须会分析阐释历史, 表达我们对历史的见解。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曾说:“全部历史就在于阐释。”[33]6在掌握影视学和历史学的知识技能基础上来分析影像文本, 具体分析时参考美国电影学家伊恩·贾维(Ian Jarvie)对影片分析的观点, “①谁制作影片, 为什么制作影片?②谁看电影, 怎样看电影, 为什么看电影?③什么让人看到了, 怎样让人看到的, 为什么让人看到?④影片是如何受人评价的, 被谁评价的, 为什么受到评价?”[34]201
5 结 语
展望未来, “影像史学”大有可为。 无论认可与否, 影像在今天都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在记录和传播历史, 影像向普通大众普及历史知识, 改变着普通大众对历史的认知, “用影片表达的形象能产生更大的力量”[28]264。 研究历史的学者要有一种美美与共、 和而不同的广阔胸怀, 要有一种合作开放、 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 要“用理性的思维和理智的态度去平等对待和接纳学术、 史学的多元化, 尤其是史学形式的多元化”[35]。 可喜的是,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影视界的部分影像工作者开始有意识地践行海登·怀特所倡导的“影像史学”, 并取得了如《百年中国》《见证·影像志》系列纪录片等反响良好的成果。 学术界对“影像史学”的关注度和认可度也与日俱增, 自1996年张广智表发第一篇介绍“影像史学”起至2002年止八年时间以“影像史学”或“影视史学”为主题词可查的学术论文有共有六篇, 其中三篇还是张广智一人所作, 而2016~2018年三年时间相关学述论文就有29篇, 由此可见, 近年来“影像史学”在国内的关注度之高。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影像实验室的成立则开启了大陆建立以研究、 创作历史影像为主的教学科研机构先河, 自2015年起每年举办一次的全国“影像史学”学术研讨会, 则促进了历史学、 影视学、 传播学等多学科对话, 并且中国人民大学史学理论研究所创办的《中国公共史学集刊》第2集就以影像为主题来专题探讨影像与历史学的关系, “影像史学”愈来愈显得生机勃勃。 所以, 笔者有理由相信“影像史学”的春天就要到来, 也相信“影视史学在21世纪势必形成崭新的史学理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