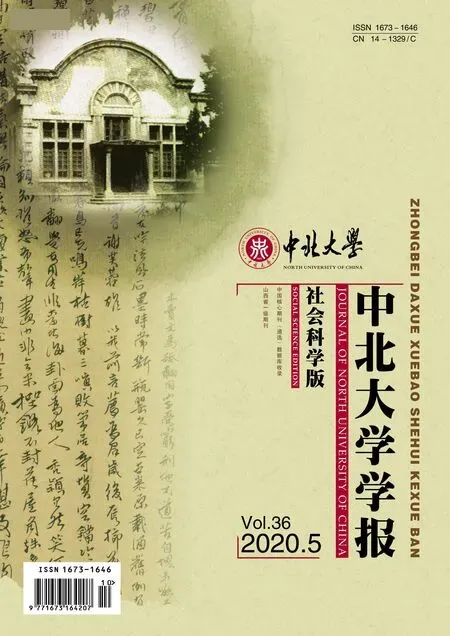从“同情者”到“同路人”
——论鲁迅的翻译活动及其革命文艺观的演变*
兰轲轲, 王静静
(1. 安徽财经大学 党政办公室, 安徽 蚌埠 233030; 2. 安徽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0 引 言
在鲁迅及其文艺思想演化的研究中, 其与左翼文学的相互关联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 鲁迅在20年代末与创造社和太阳社有过“革命文学”的论争, 但之后1930年却加入左联, 一时间成为左联宣扬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 鲁迅在面对新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时, 是纠结和复杂的, 在接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又被左联所孤立。 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遵循两种思路, 一种是直接把鲁迅塑造成左翼文学的先锋代表性人物, 两者之间其他的关系都略为不谈; 另一种是意在揭露鲁迅与左联的不和。 但无论是哪一种思路, 其实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这个问题的主体, 也即忽略了鲁迅贯穿始终的革命文艺观具体是怎样一种文艺观, 以及这种革命文艺观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抱持此种革命文艺观的鲁迅, 在30年代又是如何以左联的“领路人”, 但实际上却是“同路人”形象出现的等问题。 而这些问题都要回到鲁迅革命文艺观演变的过程中去考察。 在追溯这个问题的时候, 鲁迅在20、 30年代所翻译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理论、 作品, 及其为此做的序跋都为鲁迅革命文艺观的形成提供了材料来源和阐释空间。
1 同情弱者:鲁迅翻译苏联小说的缘起
鲁迅的译文序跋主要集中在其《译文序跋集》中, 其余散见于《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之中。 按照时序来看, 鲁迅所作译文序跋一开始是其为所翻译作品(主要是外国小说)写的序或者后记, 到1924年才开始为其翻译的理论译著作序跋。 鲁迅早期在留日期间就开始尝试翻译域外小说, 翻译的第一部作品是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 对应的是鲁迅早期“科学救国”的社会理想。 之后鲁迅翻译出《域外小说集》《工人绥惠略夫》《现代小说译丛》《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现代日本小说集》等各国文学作品, 主要还是集中于对小说的译介。 在这些译介的小说中, 并不是各国小说都包涵, 而是有所倚重, 主要倾向的是北欧以及苏联小说。 在1921年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的序中, 鲁迅对此做了解释:“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 有一种茫漠的希望: 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 改造社会的。 因此这意见, 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 于是……姑且尝试, 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1]161可以看出, 在译介初期, 鲁迅首先是希冀译介文学可以改造社会, 而译介偏重于北欧、 苏联小说则是“这30多篇短篇里, 所描写的事物, 在中国大半免不得很隔膜”, 因为这些国家的文学和中国当时处于类似的历史处境, 对疗治中国所遇到的问题是有参考作用的。
鲁迅在翻译苏联小说的过程中, 是有所取舍的。 当时苏联小说的主流是现实主义的写法, 鲁迅选取的大多是写革命、 写被侮辱和损害的一般民众的现实主义作品, 风格上偏向对革命有深入思考、 对社会和命运有反抗精神的作品。 正如他在《工人绥惠略夫》译本的后记中所说:“绥惠略夫却确乎显出尼采式的强者的色采来。 他用了力量和意志的全副。 终身战争, 就是用了炸弹和手枪, 反抗而且沦灭。”[2]169这是鲁迅1921年在其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后写的一篇后记, 关注的是苏联下层人民, 彰显的是作为无产者的工人对社会的不公进行宣战的精神意志。 在这个阶段, 鲁迅的译介符合其早期所推崇的尼采式强人精神, 认为凭借个人的力量, 确切地说是解放了的个人的力量(因为其译介的主人公都是接受革命思想或者被革命化了的带有鲁迅“立人”理想意味的人物, 这些人在鲁迅看来是可以作为个体彰显出生命的强力)和社会进行抗争的。 而这一时期他之所以倾向于译介苏联类似的带有社会反抗的小说, 也是为了中国能有如此的强力的文学创作, 而这种文学观又是和他初期就开始建设的“立人”以救国的文学观相契合的。 可以说, 鲁迅从1907年译介《域外小说集》开始, 到1928年接触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理论, 这段时间的译介是和其“弃医从文”的缘由一样, 就是“文艺救国”, 和其他“五四”文学的开创者认为救国的前提是“立人”一样, 鲁迅疗治这个病态社会的前奏是唤醒和救治病态社会里的人民。 他希冀外国文学能够给中国初创的新文学带来革命的强力和参照, 借苏联现实主义文学这块他山之石来攻中国文学这块玉。 因此, 这个阶段能够契合鲁迅这一观念的苏联小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其首选。
与此同时, 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 鲁迅在强调苏联小说中的“强者”形象可作为同时期中国新文学人物形象的参照时, 并不单单只推崇“强者”具有反抗意识这一面向, 也同时认可“强者”对于“弱者”的同情这一面向, “强者”对社会的“憎”是来源于对“弱者”的“爱”。 在另外一篇小说《医生》的译者附记中, 鲁迅认为《医生》并不能算作一篇杰作, 但他着重的价值是《医生》“对于他同胞的非人类行为的一个极猛烈的抗争”[3]176。 “无抵抗, 是作者所反抗的, 因为人在天性上不能没有憎, 而这憎, 又或许根于更广大的爱……人说, 俄国人有异常的残忍性和异常的慈悲性……我所想的, 只在自己这中国, 自从杀掉蚩尤以后, 兴高采烈自以为的制服异民族的时候也不少了, 不知道能否在《平定什么方略》等等之外, 寻出一篇这样为弱民族主张正义的文章来。”[3]177可以这么说, 鲁迅通过译介北欧、 苏联等国家的文学, 表现的是他对20、 30年代中国文学的想象, 也是他借译介完成自己对20、 30年代中国文学的移情。 在这幅想象的图景中, 既有可作为“反抗者”出现的“强者”, 也有作为“被救治者”出现的“弱者”。 但无论是对“强者”的推崇, 还是对“弱者”的救治, 其情感来源还是鲁迅对于20、 30年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受苦难的无产者以及为无产者发声的革命文学的同情。
总的来说, 从鲁迅1928年之前的译文序跋来看, 其实在译介外国小说的活动之初, 他就进行了苏联文学的译介, 而且不仅仅是翻译, 在翻译中他的倾向性是明显的, 那就是更重于对以下层受苦难的平民大众为对象, 主张反抗和生命之力的作品。 在序言和附记中, 他向中国读者介绍的除苏联革命作家的个人事迹之外, 更多地是他所认为的中国文学所或缺的, 而恰好是苏联小说所擅长的, 消融内在世界和外在表现的差别, 体现“严肃的现实性”和生活的“纤细”这种“灵肉一致的境地”[4]185。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鲁迅革命文艺观形成的准备阶段, 在译书的序或后记中, 他只是表述两国文学的不同, 中国“消闲” “帮佣”式的文学要向俄国“严肃” “写实”的人生文学这个方向走。 他对文学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文学“立人”、 同情弱者之上, 阶级论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些之后苏联文学以及左翼文学所强调的内容, 他并未过多关注。 如果按照王得后的看法, 鲁迅“立人”的文学观有三个部分:“一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 二是19世纪末‘掊物质而张灵明, 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潮。 鲁迅步入左翼文学阵营, 没有改变他的‘立人’思想, 而是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特别是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 这是他的‘立人’思想的第三块基石。”[5]那么, 这时候的鲁迅还并未进入第三部分。
2 鲁迅有关苏联文艺理论的翻译
1929年, 鲁迅开始着手翻译苏联文艺理论。 从1929年到1930年, 鲁迅集中翻译了三本苏联文艺理论专著、 论文集, 以及一本《文艺政策》。 按照译书的时间顺序分别是1929年4月译成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 同年译成, 出版于1929年10月的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 同年译成, 出版于1930年6月的《文艺政策》(内容为1924年到1925年间俄共(布)中央《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和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第一次大会的决议《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 以及1929年10月译成, 1930年7月出版的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论文集。 促使鲁迅翻译苏联文论的直接原因是1928年与后期创造社以及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 1927年正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上海蓬勃发展的时间, 也是鲁迅由广州到上海的时间。 一到上海, 创造社、 太阳社就“革命文学”和鲁迅展开了论争甚至是攻击, 在论争中, 鲁迅对创造社使用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来进行口号式的文学批评感到不满, 认为这样的文艺论争是无意义的, 更多夹杂的是个人恩怨。 在《三闲集·序》中, 鲁迅说过:“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 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 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 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 并且因此译了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 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6]6以及“超现实底的唯美主义, 在俄国的文坛上根柢原是如此之深, 所以革命底的批评家如卢那卡尔斯基等, 委实也不得不竭力加以排击。 又可以借此知道中国的创造社之流先前鼓吹‘为艺术的艺术’而现在大谈革命文学, 是怎样的永是看不见现实而本身又并无理想的空嚷嚷。”[7]426看似鲁迅是为受创造社所挤而着手翻译, 其实更多地也是为他自身。 1926年, 鲁迅离开北京, 南下厦门, 亲身感受到中国革命发生和发展着的事实, 此时的革命和他在北京的革命形势并不一样, 有新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出现。 面对这样一种新的形势, 再加上当时创造社以“无产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对鲁迅进行围攻, 这些不得不促使鲁迅产生新的思考, 中国的社会要向何处去?中国的文学要往何处去?而当时放在他面前的最直接的资源就是苏联的革命实践以及文学理论, 面对这些理论, 最为有效和有利的途径便是通过自己的翻译让国内的读者所知, 更重要的是为自己寻求答案。
那么, 鲁迅从苏联译介的文艺理论中看到了什么样的革命文学呢?集中在鲁迅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译序或者是后记中的首先是文艺是否有阶级性这个问题。 鲁迅首先选译的是卢那察尔斯基的两本理论集《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 在《文艺与批评》的译者附记中, 其实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的阶级论还是摇摆不定的, 力图找寻阶级论和人道主义之间的联系, 但并不主张文学阶级论在短时间内代替人道主义的文学观。 这一反复的举动主要体现在鲁迅在译文序跋中对卢那察尔斯基评价托尔斯泰的态度上, 卢那察尔斯基是处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研究者的立场, 而托尔斯泰是代表俄国经典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想。 鲁迅是从日本译本和杂志上选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六篇文艺评论文章, 转译编辑成《文艺与批评》, 译者附记中直接评价了这组关系, “卢那卡尔斯基并不以托尔斯泰主义为完全的正面之敌。 这是因为托尔斯泰主义在否定资本主义, 高唱同胞主义, 主张人类平等之点, 可以成为或一程度的同路人的缘故……作者以可怜的人道主义的侠客堂·吉诃德为革命的魔障, 然而并不想杀了他来祭革命的军旗。 我们在这里, 能够看见卢那卡尔斯基的很多的人性和宽大”[8]300-301。 在这里, 鲁迅肯定的是卢那卡尔斯基并没有以阶级论而否定托尔斯泰的价值, 人道主义是可以和无产阶级文学成为“同路人”的。 接着, 鲁迅在附记中又评价《文艺与批评》中的《艺术与革命》一文, 认为“其中于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之必得完全自由, 在阶级社会里之不能不暂有禁约, 尤其是于俄国那时艺术的衰微的情形, 指导者的保存, 启发, 鼓吹的劳作, 说得十分简明且要”[8]301。 鲁迅并未从一开始就完全接受文学是有阶级的这一观点, 而是有所质疑, 并认为某种程度上阶级对于文学来说是一种制约和束缚, 但也并未否认文学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必得自由这一论断, 只是还未把社会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视为一物。
在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译本小序中, 鲁迅对文学阶级论的态度就稍微明确了一些, 在序言里他认为卢那察尔斯基“所论艺术与产业之合一……现实底的理想之必要, 执着现实之必要……都是极为警辟的”[9]296。 《艺术论》是卢那察尔斯基《实证美学的基础》一书的新编本, 《实证美学的基础》主要涉及的内容是如何建设新兴无产阶级文学的问题, 鲁迅也在另外一篇后记中摘录了《实证美学的基础》中的一段话:“新的阶级或种族, 大抵是发达于对于以前的支配者的反抗之中的。 而且憎恶他们的文化, 是成了习惯。 所以文化发达的事实底的步调, 大概断断续续。 在种种处所, 在种种时代, 人类开手建设起来。”[10]355这里, 卢那察尔斯基论证的是文学在阶级社会中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新兴阶级的文学是在和旧阶级文学的斗争中才取得了新文学的资格的。 这也是直接承认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 同时间接支持了作为新兴文学势力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合理性。
在《文艺政策》的译后记中, 鲁迅摘录了《文艺政策》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版编后记中的一段话:“俄国的关于文艺的争执……约减起来, 也不过两派。 即对于阶级文艺, 一派偏重文艺, 如瓦浪斯基等, 一派偏重阶级, 是《那巴斯图》的人们, 布哈林们自然也主张支持无产阶级作家的, 但又以为最要紧的是要有创作。”[11]306“但到后来……瓦浪斯基承认了艺术的阶级性之重要, 烈烈威支的攻击也较先前稍微和缓了。”[11]307这里只是客观地呈现苏联无产阶级文艺中承认阶级文艺的事实, 但在这番介绍之后, 鲁迅在后记中又申明了一下他的意愿:“从这记录中, 可以看见在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 于现在的中国, 恐怕是不为无益的。”[11]307虽然在后记里他对文学是否有阶级性持有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态度, 但至少并没有反对, 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无产阶级文学的“经验”介绍到国内来; 换一个角度来看, 既然鲁迅已经承认俄国是“劳动阶级”文学的大本营, 那么也意味着他也承认了文学是有阶级性存在的这样一个事实。
鲁迅对蒲力汗诺夫《艺术论》的译介更为用心, 曾经参阅过联共(布党史)、 苏联革命史和文学史以及蒲力汉诺夫的生平来写《艺术论》译书的序言, 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主要是用唯物史观来解释艺术起源的问题。 序言中鲁迅评说蒲力汗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价值:“他的艺术论虽然还未能俨然成一个体系, 但所遗留的含有方法和成果的著作, 却不只作为后人研究的对象, 也不愧称为建立马克斯主义艺术理论, 社会学底美学的古典底文献的了。”[12]261那么, 是蒲力汗诺夫什么样的艺术观点让鲁迅觉得有留存的价值的呢?在序言的第四部分, 鲁迅概括了《艺术论》的主要观点, 首先他认为蒲力汗诺夫把美当作是艺术生产, 不同于唯美主义者把美神秘化的观点, 并以美的原始来源就是生产来解释马克思艺术论中艺术生产的问题, 其“第三篇《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以究明有用对象的生产(劳动), 先于艺术生产这一个唯物史观的根本底命题。 详言之, 即蒲力汗诺夫之所究明, 是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 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 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 继而推导出“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 就是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蒲力汗诺夫将唯心史观者所深恶痛绝的社会、 种族、 阶级的功利主义底见解, 引入艺术里去了”[12]262。 这里算是鲁迅对阶级论最为直接的表达了, 他基本上是同意并赞成蒲力汗诺夫关于文艺属于艺术生产这一说法的, 也就是允许把文艺放在社会阶级的范畴中去讨论。
3 由“同情”到“同路”
可以说, 鲁迅对苏联文艺理论的翻译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从理论上初步接受了文学是有阶级的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理论, 可是要回到中国具体的革命现实, 还有一个文学如何和革命结合的问题, 也就是要去考虑在中国左翼文学的实践中,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鲁迅除了1929年和1931年对苏联文艺理论的译介, 跟理论译介的同期持续或者是开始的是他一直持续到1936年的对小说、 杂文、 诗歌、 论文的译介。 如果说, 阶级论是他在理论上对苏联影响下的中国革命文学的思考, 那么, 在其对苏联具体文学创作的译文序跋里, 他表达出的则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
从鲁迅的《译文序跋集》来看, 其后期对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并不仅限于当时苏联无产阶级主流作家的作品, 还包括当时被称为“同路人”的苏联作家的创作。 “同路人”是一个相对比较概括的称呼, 主要是为了指称当时同情和拥护苏维埃政权但在政治立场和革命意识上持模糊态度, 更为关注文学本体意义的作家。 从鲁迅这一类的译文序跋来看, 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明显的叙述主要出现在为“同路人”作品作的译序或后记中, 但在为以无产阶级革命作家作的序跋中也有“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说, 只是这两者论述的侧重点并不一样, 也反映出鲁迅其实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是反复和不确定的。
一方面, 如果就鲁迅对其译介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评价来看, 他表达出来的态度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作家, 其自身应该了解革命形势, 并且认为有过革命经历的作家其作品更有现实性。 在这一点上, 鲁迅并未直接隔断作家与现实政治革命之间的关系, 甚至还认为投入革命现实的作家比起国内空嚷口号的革命文学家们更为了解革命的实质。 比如就法捷耶夫的《毁灭》来说, 鲁迅认为“因为文艺上和实践上的宝玉, 其中随在皆是, 不但泰茄的景色, 夜袭的情形, 非身历者不能描写, 即开枪和调马之术, 书中但以烘托美谛克的受窘者, 也都是得于实际的经验, 决非幻想的文人所能著笔的”[13]331。 随后在《毁灭》第二部一至三章的译者附记中又说:“当我译完这第二部的上半时, 还想写几句在翻译的进行中随时发生的感想。 这几章是很紧要的, 可以宝贵的文字, 是用生命的一部分, 或全部换来的东西, 非身经战斗的战士, 不能写出。”[14]335在表达了自己的感想后, 又在附记的最后再次强调:“倘要十分了解, 恐怕就非实际的革命者不可, 至少, 是懂些革命的意义, 于社会有广大的了解, 更至少, 则非研究唯物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不可了。”[14]337《毁灭》的价值在于法捷耶夫对革命的切身感受, 而《毁灭》能给中国读者带来的阅读价值也是因为这是一部用亲身革命经验写就的革命小说。 鲁迅显然深知这类革命小说的价值定位就是能够反映真实革命的种种, 他针对的是革命的空想乌托邦。 在这个意义上, 鲁迅是把文学和社会革命现实, 也就是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而且也认为文学是可以这样来写革命和社会现实的, 就是最好是作者的经历, 如若没有亲身经历, 对革命和社会具有相当的了解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 如若换一个说法, 当时的中国是可以反映政治以及革命现实的, 这个说法在鲁迅这里是成立的。
另一方面, 鲁迅着手苏联“同路人”作品的译介。 鲁迅摘录了托洛兹基的话来描述他眼中的“同路人”, “从党员的见地来看, 我是没有主义的人……我既不是共产主义者, 也不是社会革命党员, 又不是帝政主义者。 我只是俄罗斯人”[15]316。 接着鲁迅自己说:“‘同路人’各自有其不同的态度。 所以各人在那‘没有纲领’这一个纲领之下, 内容形式, 又各不同。”[15]316而“同路人”的作品在鲁迅看来:“表示了较有进步的观念形态的。 但其中的人物, 没有一个是铁底意志的革命家。”[15]317虽然“同路人”也写了有关革命的文学, 但他们是没有政治立场的, 比较倾向于自由博爱, 对革命抱有的是同情之意。 其实, 20年代苏联国内对“同路人”就有争议, “拉普”批评家基本持否定的态度, 认为“同路人”文学在根本上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 这种文学只会“歪曲革命” “诽谤革命”。 而托洛茨基以及《红色处女地》杂志则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苏联文学主要靠“同路人”作家。 最终俄共(布)中央在1925年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中规定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这种中间的思想形态, 并采取方法使他们尽可能迅速地转到共产主义思想方面来。 俄共(布)中央还主张让“同路人”走向共产主义文学创作方向, 1934年, 苏联作家协会成立, “同路人”许多作家加入了作协, 成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一份子。 但是, 在鲁迅这里来看, 他还是更为支持“同路人”的创作。 《一天的工作》前记中鲁迅摘录了《伟大的十年的文学》中的两段话来对比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和“同路人”的创作, 指出“无产者文学是从生活出发, 不是从文学性出发的”[16]357。 “所谓‘同路者’的文学, 是开拓了别一条路的。 他们从文学走到生活去。 他们从价值内在底技巧出发。 他们先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题材, 自说是对于一切倾向性的敌人, 梦想着无关于倾向的作家的自由的共和国。”[16]357这里鲁迅想要呈现的是文学与政治革命这两者谁更是革命文学创作前提的判定, 显然他更认同“从文学走到生活去” “将革命看作艺术底作品的题材”的“同路人”的文学态度, 既不远离政治, 也不认为文学就必是反映政治革命的工具, 因为革命现实在这里是艺术作品所反映的题材, 作者有选择何种革命现实进入作品, 以及在作品中如何表现革命现实的主动权, 而不是作者被作品的题材所选择。 这也正好印证了1927年12月鲁迅在暨南大学的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的观点, 文艺是不安于现状的, 而政治是要维持现状的, “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 那就不免被挤出去。 外国许多文学家, 在本国站不住脚, 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要是逃不掉, 那就被杀掉……俄国许多文学家, 受到这个结果, 还有许多充军到冰雪的西伯利亚去”[17]113。 这是鲁迅针对1927年国民政府的政治与文学的想法, 在转译了苏联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后, 与他开始对文学与政治的看法产生了重合。
4 结 语
鲁迅的文艺观从“五四”时期开始就是和社会、 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 可以说天然上是和左翼文学有共通点, 而20年代到30年代他渐渐接受左翼文学观, 其自身也从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及作品资源中去判断中国左翼文学的性质以及它发展的方向。 在这里, 鲁迅的革命文艺观一直处于吸收、 整合再变动的过程, 并不能将1930年鲁迅加入左联视为他对革命文艺探讨的终止, 在左联期间他仍然在译介苏联无产阶级论文和小说。 鲁迅的革命文艺观可以说是其对自身文艺观重建的过程,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在其译文序跋中对苏联文学的评析贯穿了他参与左联活动的始终, 而且还补上了其在左联之前对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认识。 同时, 鲁迅的革命文艺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的形成由最初的文艺要“立人”, 改变社会的功利主义, 到文艺是有阶级性的, 最后认为文学是要反映政治, 为革命呐喊, 但又质疑俄共(布)把文学完全划归到政治范畴中的观点, 也质疑中国左翼文学过于“口号化” “标语式”的革命文学创作, 一直在政治和文学之间做权衡, 并没有完全赞同或否定其中的任何一方, 既不认为应该“为艺术而艺术”, 也不主张为政治而变成口号的文学。 这两者在他看来都是带有“务虚”性质的文学, 他所寻找的是真实的, 能够真正表现出社会血与泪现实的文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 鲁迅选择了“同路人”的角色。 进而言之, 30年代从鲁迅的视角所见的左翼文学具体应该是何种形态, “同路人”的角色延续到50、 6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还是否有它的合理性, 这些又都是其他问题所讨论的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