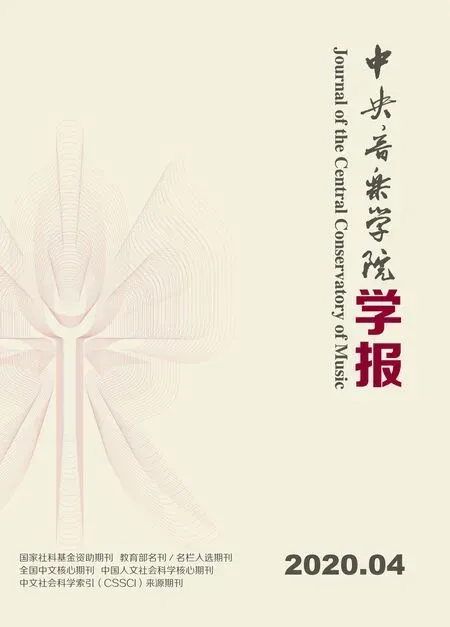从费尔莫到中国皇宫:德礼格,音乐家和使徒传教士
〔英〕彼得·奥索普、〔美〕乔伊斯·琳道芙黄 键 译余志刚 校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北堂馆藏中,有一套举世瞩目的《为小提琴和持续低音而作的奏鸣曲》(SonatasforViolinandBass)(Op.3)。该曲集包含12首作品,是18世纪前半叶以来西方音乐唯一留存在中国的手稿,作曲家是“内普里迪”(Nepridi)。这个显见的改变字母位置形成的单词指的是保罗·菲利普·德礼格·佩德里尼(Paolo Filippo Teodorico Pedrini,1671—1746),他于1671年6月30日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大区(Le Marche)的费尔莫(Fermo),1746年12月10日逝世于北京(1)两位勇敢的费尔莫人:法比奥·G.加勒弗(Fabio G.Galeffi)和加布里埃里·塔尔赛迪(Gabriele Tarsetti),收集了很多德礼格家族背景的信息。。1702年在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Clement XI,1700—1721年在位)的派遣下,德礼格被神圣的传信部总会(Congregation
of Propaganda Fide)选中,陪着命运多舛的多罗(迈拉德·德·图尔农,Maillard de Tournon,1668—1710)使团前往中国。现主要藏于罗马和巴黎一千余页他的信件,记录了他从那时起直到去世,作为三朝连任的宫廷音乐家的坎坷一生。虽然德礼格的名字因为他在中国重大的“礼仪之争”中所处的并不令人羡慕的地位,早已为历史学家和传教学家所熟知,但是直到上世纪,他的音乐才最终引起了在中国工作的两位神父的关注。20世纪30年代遣使会神父李蔚那(艾马尔-伯纳德·杜维尼奥,Aymard-Bernard Duvigneau,C.M.1879—?),作为《北京天主教公报》(BulletincatholiquedePékin)(2)参见Aymard-Bernard Duvigneau,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1935,p.88,note 3。亨利·伯纳德曾在一篇关于欧洲音乐在中国的文章中提到过德礼格的奏鸣曲。随后李蔚那神父的系列文章分别在1937年卷的第312—325、363—375、436—444、475—488、535—546页中可以看见。1951年,77岁的李蔚那和德礼格一样,在中国曾经入狱。的编者,写了一系列有关德礼格的文章,这些文献构成之后他写作德礼格传记的基础。卢华民(西奥多·鲁尔,Theodore Rühl)神父是位小提琴家,他曾在北京天主教堂举行的独奏音乐会上演奏了德礼格第三卷奏鸣曲中的第八首。他本打算让北京遣使会出版社将德礼格的这部作品集刊印,其中包含手稿摹本和现代译谱,并且已经将持续低音实现。(3)Eugen Feifel,“Book Reviews”,Monumenta Seric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2(1936-1937),p.259.但由于日本侵略中国的突发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乱,该作并未真正付梓。最近,这些奏鸣曲得以重新演出,并用激光唱片(4)五首奏鸣曲收录在《在紫禁城举行的巴洛克音乐会》激光唱片。参见Musique des Lumières,Concert Baroque à la Cité interdite,XVIII-21,Astrée E8609,1996。发行了部分曲目,现代版本的乐谱也即将出版。(5)Teodorico Pedrini,Sonatas for Violin and Bass,Op.3,ed.J.Lindorff,Madison,Wisconsin:A-R Editions.即将出版。之后更详细的德礼格传记研究也相继出现,但对他来自马尔凯大区的重要性依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6)参见Joyce Lindorff,“Teodorico Pedrini”,in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2nd.edn.,London,2001。
一
德礼格作为一名受人尊重的公证人的儿子,1692年在费尔莫大学民法与教会法(utroqueiure)专业毕业,原本打算从事法律职业。然而,是年他走出了决定人生的一步,进入了皮切诺学院(Collegio Piceno)。这个学院是在马尔凯地区兄弟会(Confraternit à della nazione marchigiana)或虔诚兄弟会(Pio Sodalizio)的赞助下,为来自马尔凯的学生提供进一步在罗马深造学习的机会(7)图书馆员玛利亚·安东涅塔·拉伽娜(Maria Antonietta Laganà),好心地允许我们阅读了她即将出版的传信部研究手稿。也可参见Maria Antonietta Laganà,Storia della biblioteca e catalogo delle sue cinquecentine,Rome:Pio Sodalizio dei Piceni,2000。皮切诺学院的历史档案目前我们无法访问。。现存的罗马“皮切诺学院的寄宿生名单”,确认了德礼格曾于1692年11月6日到1697年8月7日间在此学习。(8)这份名单刊登于Sandro Corradini,“La Comunità marchigiana in Roma vista da Pier Leone Ghezzi”,in Cultura e società nel settecento:3.Istruzione e istituzioni culturali nelle Marche.Atti del XII convegno del centro di studi avellaniti,Gubbio:Fonte Avellana,1988,pp.291-301。我们对科拉迪尼修士(Mons.Corradini)的慷慨相助表示感谢。当时,虔诚兄弟会已经收购了位于劳罗(Lauro)的圣·萨尔瓦托雷(San Salvatore)教堂,将其改名为“洛雷托圣母堂”(Santa Maria di Loreto),并为约40名学生在相邻的建筑里提供住宿。扩建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其赞助者红衣主教、费尔莫贵族、教皇克莱门特九世(Clement IX,1667—1669年在位)的国务卿迪奇奥·阿佐里尼(Decio Azzolini,1623—1689)自1668年到1689年去世的慷慨资助。今天,阿佐里尼最出名的可能是与前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Christina)的紧密联系,女王退位后在罗马居住,并皈依天主教。几年后,德礼格的姊妹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eresa)嫁给了学院院长朱塞佩·蒙蒂(Giuseppe Monti)。
皮切诺学院的创始人红衣主教贾巴蒂斯塔·帕罗塔(Giambattista Pallotta)规定的学院义务之一,是应承担所属教堂的音乐活动。这并非一纸空文,在乔瓦尼·安东尼奥·莱尼(Giovanni Antonio Leoni,ca.1590-ca.1650)的《小提琴独奏奏鸣曲》(SonatediViolinoaVoceSola,1652)前言中,说明了这一活动很快获得了相当高的赞誉。
谁人不晓,在这座城市中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建造了值得尊敬的洛雷托圣母堂。就像神圣的帕纳索斯山,那里一年中有无数次音乐家们的集会,他们虔诚地展现高贵的才华。有时是吟唱神圣赞美诗的甜美的音乐会,有时演奏和谐的辛弗尼亚,这些模仿天使的旋律,在神圣的教堂周围环绕,以闻所未闻的方式在海面上飘荡徘徊,这是通往天堂的路吗?(9)Giovanni Antonio Leoni,Sonate di Violino a Voce Sola,Op.III,Rome:Vitale Mascardi,1652.
罗马音乐赞助者们的一个喜好是,即使最负盛名的赞助机构也不倾向于供养一个领薪的管弦乐团,而是更乐于像赞助节庆这样的特定场合一样扩大乐团的音乐设施。这一点上,皮切诺学院尤为幸运,因为它可以依靠阿佐里尼和克里斯蒂娜女王之间的亲密关系来吸引音乐家为她的“室内乐团”(musico da camera)服务,这里说的音乐家不是别人,正是传说中的阿尔坎杰罗·科雷利(Arcangelo Corelli,1653—1713)。(10)关于科雷利和皮切诺学院的联系请参见Lepanto De Angelis,“Arcangelo Corelli nella direzione di un‘Concerto e Sinfonia’in S.Maria di Loreto dei Marchigiani di Roma”,Note d’archivio per la storia musicale,XVII,1940,pp.105-110。1689年为了感恩克里斯蒂娜大病痊愈,科雷利被任命指导洛雷托圣母堂的音乐。(11)“这篇简练的报告对这些在耶稣教堂和位于皮切诺的洛莱托圣所准备的事情做出了陈述,准备包括为感恩神圣的圣母吟唱《感恩赞》,还有1689年为神圣的瑞典女王大病初愈举办的庆祝活动。”参见Cod.Urb.lat 1689,Rome:Biblioteca Vaticana,fo.120。3月19日,在那里有一首由四个合唱团演唱的节日弥撒演出,“此外,圣母堂著名的科雷利大师创作了一首新的协竞风格的辛弗尼亚,其中有小号。这个城市的多数顶尖的专业人士都参与了演出,大大扩充了演出规模。”(12)Andreas Liess,“Neue Zeugnisse von Corellis Wirken in Rom”,Archiv für Musikwissenschaft,XIV,1957,p.136.1716年,科雷利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乔瓦尼·马里奥·克雷西姆贝尼(Giovanni Mario Crescimbeni,1663—1728)编辑完成了虔诚兄弟会最早和最全的记录之一。克雷西姆贝尼出生于马切拉塔(Macerata),是阿卡迪亚学会(Arcadian Society)唯一的总监护人,该协会的成立是为了延续女王克里斯蒂娜的学术影响力。(13)“感谢保存于罗马圣洁教堂中圣母玛利亚的相关神奇事迹的历史记录,即所说的劳罗的圣·萨尔瓦托雷圣母教堂,也就是今天的皮切诺学院的‘洛雷托圣母堂’,这由乔瓦尼·马里奥·克雷西姆贝尼收集。”参见Giovanni Mario Crescimbeni,S.de Rossi,Roma,1716。
科雷利与学院建立的联系在女王去世后依然持续了很久。1700年12月10日,这一年正是科雷利第五卷作品出版之时,它立即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小提琴奏鸣曲集。科雷利再次受雇于“阿尔奇兄弟会”(Arci confraternità),为洛雷托至圣所(Most Holy House of Loreto)指导音乐事宜,此事被罕有幸存的科雷利薪金全额支付单所证明。(14)Lepanto De Angelis,“Arcangelo Corelli nella direzione di un‘Concerto e Sinfonia’in S.Maria di Loreto dei Marchigiani di Roma”,Note d’archivio per la storia musicale,XVII,1940,pp.105-106.那时,科雷利得到红衣主教奥托博尼(Ottoboni)的赞助,住在坎塞勒里亚宫(Palazzo della Cancelleria),距离皮切诺学院咫尺之遥。德礼格在1719年9月15日的一封信中,顺带有趣地暗示了他可能是宫中常客。德礼格本人显然是一位技艺精湛、有能力的业余音乐家,因此理所当然地受到学院当局的热烈欢迎。他自己的作品非常强烈地反映出科雷利的影响,也就不足为奇。到达北京不久,他便立即请求传信部寄送“一些较好版本的科雷利作品”(15)Propaganda Fide,Scritture originali congregationi particulari dell’Indie Orientali e Cina,Rome,26,2 giugno 1711,26.293r-296r.(1711年3月4日),这封信也透露了在他抵达北京的第一个月里创作了十首三重奏鸣曲组成的三套作品,当时呈献给了皇帝,但现已遗失。
在皮切诺学院完成学业后,德礼格最终决定献身于神职。他早期一直在耶稣会(Jesuits)和奥拉托利会(Oratorians)的督导下学习,最后却选择了遣使会(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或Lazarists)。这种选择绝非偶然,因为遣使会在罗马蒙特·奇托利欧(Monte Citorio)的主会所的修士,常规性地要在皮切诺学院进行七或八天的灵修。来自蒙特·奇托利欧的一套当时的指导手册里,包含了一个部分,名为“皮切诺学院灵修指导者说明”(Instruzione per il Direttore degli esercizi spirituali del Collegio Piceno)(16)Archivio Collegio Leoniano,“Libro nel quale si contengono l’istruzioni per gli esercizij spirituali ad uso del Superiore della Casa di Monte Citorio di Roma”,Rome.。在此期间,指导者的职责似乎落在了乔瓦尼·安塞尔米(Giovanni Anselmi,?—1714)(或安塞尔莫,Anselmo)身上,他是德礼格未来职业走向的重大影响者。(17)“Relazione del Sigr.Giovanni Anselmi morto in Roma li 29 Gennajo del 1714”,in Relazioni de missionari Tomo XII,Archivio Collegio Leoniano,Rome,pp.319-347.1698年2月德礼格作为神职候选人加入修会一个月后,安塞尔米开始负责指导费尔莫的传教活动,这显然并非偶然。在修会账簿中的一个条目毫无疑问地表明两人是共同参与的:“8月26日。安塞尔米为德礼格先生支付给乔瓦尼·莫雷利(Giovanni Morelli)先生的四份付款订单,应由费尔莫的安塞尔米先生支付。”(18)Archivio Collegio Leoniano,Libro Maestro 1697-1705,Rome,p.394.也许这次任务的成功,使得费尔莫主教巴尔达萨雷·芩奇(Baldassare Cenci,1647—1709)准许该修会在城市设立会堂。它的第一任总监是乔瓦尼·阿皮亚尼(Giovanni Appiani),1698年他的兄弟毕天祥(罗德维克·安东尼奥·阿皮亚尼,Lodovico Antonio Appiani,1663—1733)成为第一个踏入中国的遣使会传教士。德礼格很可能在去中国之前就认识了兄弟俩,并与他们两人都有通信。
安塞尔米碰巧也是克莱门特十一世的密友,后者在升任之前,在蒙特·奇托利欧的灵修中受益巨大。前任教皇英诺森十二世(Innocent XII,1691—1700年在位)遗留未决的事业中,中国祭孔和祭祖的礼仪是个令人烦恼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一百年前的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时代便已出现,曾被耶稣会士当作民众仪式而非宗教仪式被宽容或“接纳”。克莱门特反对这种做法,委托传信部派遣使团采取果断行动以施加教皇权威,并且要求提前对此事做出裁决。可能在他与安塞尔米的每周磋商中,详细讨论了关于中国使团的章程。克莱门特首选的使节是费尔莫主教(19)这个声明在苏富比目录(1988)第22号出售的《菲利普·罗宾逊藏品》(Philip Robinson Collection)第二部分的描述中提出的,其中包括相关的中文文件。,主教以年老为由拒绝,但提议他的罗马审计员多罗担任,凑巧的是多罗是阿皮亚尼兄弟的堂兄。多罗也参加了蒙特·奇托利欧的灵修活动,并曾受安塞尔米的影响。多罗给岑奇的信中特意提到了安塞尔米主教给神职候选人所做的布道(1701年5月21日)(20)Archivio Storico Arcivescovile di Fermo,Fondo Arcivescovile,III-E-7,Lettere al Card.Cenci Arcivescovo di Carlo di Tournon suo Uditore e poi Cardinale,18 giugno 1698-1619 settembre 1702,Lettera del 21 maggio 1701.。5月26日,他在延迟了八到十天后进入了使团——这是他被任命为安提俄克主教(Patriarch of Antioch)和后来作为公使去中国之前的关键时期。克莱门特现在转向安塞尔米征集使团的代表,但是那些之前提名的人最终都没有加入使团。似乎德礼格并不是自愿的,而可能是属于应安塞尔米招募入团。命运在他的选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与岑奇、多罗、阿皮亚尼兄弟、尤其是安塞尔米的关系,再加上一个简单的事实,他和克莱门特十一世一样,都是马尔凯人。
从1702年离开罗马到1711年抵达北京,德礼格长达九年如奥德赛般的长途跋涉,可以说开局不利。由于在巴黎耽搁得太久,他错过了载着多罗和其他人经好望角到远东去的船。相反,他选择了一条令人震惊的途经美洲的路线,其所乘之船在绕过合恩角(Cape Horn)时被狂风刮偏航道。然后,他从智利出发,前往秘鲁、危地马拉,再从陆路到达墨西哥,最后乘船前往马尼拉。在那里他遇到了一队给澳门的多罗送红衣主教帽子的牧师。在西班牙总督的默许下,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他们终于可以登上中国大陆,他果敢地完成了一项壮举,这既显示了他的勇气和想象力,也暴露了他的鲁莽。德礼格剃掉了胡子,穿上了海军船长的制服,并征用了一艘船。然后他开始从马尼拉前往中国,由于没有什么航海技巧或经验,在途中几乎与灭顶之灾擦肩而过,使得船员和乘客们感到恐惧和惊慌。
德礼格早在1708年7月6日的一封信中告诉他的父亲,他已经了解到了这项任务的悲惨境遇。
如下是关于中国的一些新纪要:大主教颁布了一条法令,其中有罗马教廷1704年11月20日发布的决议,谴责了“中国礼仪”,而这却是耶稣会会士所维护的。几乎所有的世俗和正规传教士、特别是多明我会神父们皆被放逐,他们因服从罗马教廷及其使节而出名……一些人被放逐到了广东,另一些被放逐到澳门。在澳门他们住在主教家,最终所有那些服从于罗马教廷及其使节的人都遭受了痛苦。上帝没有狠狠地惩罚我,认为我不够坚强,事实上我亦如是,不能为了他受尽苦难,所以让我在旅途中停留了很长时间,他想让我远远地观望这些悲剧,却无法亲身体认。我坦然接受他那圣洁的心愿。(21)Archivio Collegio Leoniano,Rome,6 luglio,1708.
多罗认为,这场灾难完全是耶稣会士恶意策划的阴谋,他们没有准备接受强制执行教皇权威。另一方面,他认为这应该归因于康熙皇帝对教皇谴责“中国礼仪”的厌恶。事实上,多罗在澳门被监禁,并非奉康熙之命,而是受葡萄牙当局操控,他们认为该使团是对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1492—1503年在位)批准的所有远东任务主权的直接冒犯。(22)Paul Rule,“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Its History and Meaning,ed.D.E.Mungello,Nettetal:Steyler Verlag,1994,p.254.
康熙对传教士们胆大妄为地干涉中国事务感到非常愤怒,出于反击,他强制要求来华欧洲人办理居留许可或统称为“票”(piao)的居留证,这是对耶稣会“利玛窦规则”(la Confessione Ricciana)的直接承袭。德礼格不仅不会签署任何直接违反教皇谴责中国礼仪裁决的协议,而且作为传信部的使徒传教士,他相信自己被明确地派遣来是为了支持罗马教廷的事业,继而反对那些公然蔑视教皇权威的敌人。然而,皇帝对欧洲传教士之间教义争论的关心,远不及关心他们的实用能力,这与宗教信仰无关。他很快向多罗打听新来神父们的各自专长。作为一名音乐家,德礼格极其幸运地填补了1708年徐日升(托马斯·佩雷拉,Tomás Pereira,1645—1708)去世后留下的空缺,后者的去世不仅使皇帝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朋友,也失去了一位有着30年经历的宫廷西方音乐家。德礼格的同事穆天尺(约翰·米勒奈,Johann Mullener,1673—1742),自1698年定居中国,早在1708年就已经认识到新的事态变化的重要性:
如果他来了,不承认“利玛窦规则”或“儒家礼仪”将无法获准开始任务。可能的是,他的音乐帮助他作为皇帝的音乐家进入宫廷,这样的话可能会避开测试,否则开始这项任务是非常困难的。(23)Archivio Collegio Leoniano,Missioni Straniere:Pedrini,Rome,p.96.
在德礼格离开意大利的时候,尚未发现他将来可能成为宫廷音乐家的迹象。在1713年7月4日他写给母亲的信中,反而对宫廷音乐家表现出相当的不屑:
我已经写过很多次了,皇帝给了我七个学生,让我教他们音乐。最终皇帝对他们的学习成果感到非常高兴,以至于人们看到我最终居然成了宫廷乐师。多么伟大的职位啊!(24)Archivio Collegio Leoniano,Rome,4 luglio,1713.
德礼格离开罗马9年多后,1711年2月5日和他的传信部同事马国贤(马泰奥·里帕,Matteo Ripa,1682—1746)、古格列尔莫·法布里(Guglielmo Fabri)抵达清廷,成为第一批到达北京的非耶稣会传教士之一。在最近发现的一封他给传信部的信中(1711年3月4日),描述了他受到康熙皇帝异于寻常的接见:
皇帝问我是否带来一些新的动人的音乐;我说有自己创作的新作品。接着问我是否会一些学习音乐的新方法,或者能否运用音符ut、re、mi、fa、sol、la?我回答这些对我有用。他说如果在这些音符中,la后面加上si(这是法国人教音乐的新方法)或者没有si会怎样。他想说意大利的方法会通过升re和降la转调。我答道,对我而言这种或那种方法都无所谓,我解释了意大利转调的方法。他问我是否会唱ut、re、mi、fa、sol、la这些音符。我答道我的声音不适合唱歌,但了解一点音乐对位法的知识。尽管如此,他说让我试试,这时他自己已经开始唱起来了,我也跟上唱,他很高兴。接着他问我是否知道那些音符时值的划分,他想讲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和三十二分音符。翻译们解释这些术语有点困难,他们更多地用手势代替语言的讲解。我已意会,但他还是让他们解释。接着我回答说我不仅知道时值的划分,而且没有这些的话很难作好曲子。他问我是否懂“软型b”和“升号”。这些不用等翻译们解释了,他们貌似有很多事要做。我转向皇帝说,是不是这样的,继而我开始用升号唱这些音符。他很愉快地回答:是、是,好!好!好!他又问我有没有教授音乐的一些新方法,我答道有。他问是什么?我答道,是让一个人在短时间内学会演奏或演唱。我想具体说明一下。他转向太监,对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我没听明白他们的问答。据我揣测是,皇帝告诉他们必须要好好学习这些方法;我接着补充道,关于学习演奏和演唱,没有比经验更好的了。他笑着回答,但是人们都有耳朵;我也笑着答道如果没有耳朵呢?……他想知道我创作时的乐谱需要多少根线?我说五根。接着他问道,您是否了解乐器,能否教授这些乐器呢?我回答说,我不仅会这些,而且我也知道如何为欧洲乐器谱曲,通过练习,我也可以为特定的其他乐器作曲,但是他没有说明自己的意思。这就是我首次面圣的内容。(25)Propaganda Fide,Scritture originali congregationi particulari dell’Indie Orientali e Cina,26,Rome,4 marzo 1711,cc.293r-296r.
德礼格在这个陌生的新环境里,几乎不懂当地的语言,第一次见到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统治者,他对如此询问西方音乐理论的细节会有什么反应呢?
很快他便发现,自己已经开始从事将要度过余生的职位(1711年6月2日):
有时他(康熙)会让我演奏;他也会亲自拿起我的小提琴,和我一起演奏……。上帝赐予了他音乐的才能,他会亲自谱曲,把中国的旋律记写成乐谱……。他让我唱他写的一首歌曲,然后在羽管键琴上弹奏另外几首。先用中国的方式,再用欧洲的,再后来弹几首欧洲的奏鸣曲……。在这个宫殿里很少听到相同的协竞曲,正如陛下在演奏的时候向我说的那样:“你看,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曲子,徐日升神父(他是皇帝最喜爱的欧洲人之一)听到的时候喜极而泣,因为他在中国三十年了,之前我还没有给他听过。”那时我来中国还没满三个月,就获得了如此殊荣。(26)同注,cc.299r-304r。
从一开始,皇帝便表现出了对德礼格的特殊喜爱(1727年10月2日):
没有人比我受到皇帝更多的恩宠,虽然我是众人中最低下的。他从那时开始赞美我,多年来送给我各式各样的礼物,经常让我陪同他一起出席各类活动,敬我以繁多的礼节,使我区别于其他欧洲人。他对我如此亲切,他自己会创作音乐,让我给他校订。校订时他会亲自将笔递给我,让我和他在书桌上一起作曲。我们经常一人一手在同一架羽管键琴上演奏。值得注意的是,这么说吧,他不像我们的音乐家所学到的那样机械地欣赏音乐,而是研究音乐理论,就像对待数学一样,观察声部的配合、音程的度数,以及如何把中国的曲调转写成乐谱。(27)参见Ferdinand Combaluzier,“Theodoric Pedrini,lazariste,missionaire apostolique(Pékin 2 octobre 1727),Lettre inédite au cardinal Paolucci,Secrétaire d’Etat de Clément XI(1700-1721)et de Benoit XIII(1724-1726)”,Neue Zeitschrift fur Missionswissenschaft-Nouvelle Revue de science missionaire,XIII 1957,pp.139-147;142-147。提到的保存地点是皮亚琴察的阿尔贝罗尼学院(Collegio Alberoni)。
我们继续通过阅读以下资料可见,德礼格是少数被皇帝选中随行到热河夏宫(Manchurian estate in Jehol,现承德避暑山庄)的幸运的外籍人士之一(1713年8月22日)(28)《热河夏宫》,画家沈瑜(音名Shen Yu)之作,汪曾祺用精美的书法抄写了一首题献给康熙皇帝的诗。参见《避暑山庄七十二景》,北京: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93,图14。。
陛下每天都给我更多的殊荣和恩泽;他不满足于我每天和其他欧洲人一起来到宫廷。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了花园内部,那里没有允许过欧洲人进入。在那儿,他指定给了我一套房子和一个服侍我的太监……。陛下每天都从这附近经过,他常常怀着慈父般的感情,恩准我觐见,在他的皇子们和整个宫廷面前赞美我,这对我来说过于恩宠。(29)Propaganda Fide,Fondo Scritture Riferite nei Congressi:Indie orientali e Cina,12,Rome,22 agosto 1713,cc.397r-398v.
德礼格很快被委以重任维护皇帝收藏的大量乐器。此外,他还负责设计由中国工匠制作的新型键盘乐器,并被委托教授皇室成员(1714年12月9日):
他目前正在第三、第十五和第十六皇子的帮助下撰写一本书。他命令我在皇子们面前解释最基础的音乐知识和精微之处。(30)Fondo Albani,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Città del Vaticano,255,9 dicembre 1714,c.312v.
他提到的书即《续编》,是《律吕正义》(TheTrueDoctrineofMusic)(31)纪昀等:《四库全书》(文渊阁版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1987年,第215卷。的第五卷。此书的编撰始于徐日升、成于德礼格,是康熙皇帝对欧洲音乐充满兴趣的永久证明。这项中西音乐理论与乐器的研究是由康熙敕令进行的,受到1672年徐日升抵达北京后将西方音乐呈现给他后的启发。《律吕正义》收编在两套巨著中,即1723年的《律历渊源》和18世纪晚期、包含1500卷的百科全书《四库全书》中。至此,德礼格的理论著述收录在了中国皇家学术的两大文献集中。毫无疑问,不论德礼格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他对康熙皇帝授予他的荣誉深感自豪,他认为康熙是最伟大的统治者。在1714年10月20日写给教皇的密信中,他不仅颂扬了皇帝的伟大美德,而且间接地表扬了自己的功绩:
但是,等待我发觉的,还有他敏锐的理解力:他不仅以中国的、还以我们欧洲的方式,洞穿了一切科学中最晦涩的难点……在这里我只讲述关于音乐学科的事情。他在所有学科中最偏爱音乐这一科,尽管中国人有很多关于音乐的古书,但是尚未有人给皇帝详解过这如此高贵的艺术:他正在写作一本书,包含该学科最精微的规则,关于声部、调式、转调的不同;鞑靼、中国、欧洲的以气鸣发声或者振动发声的管弦乐器,其中有极其微小的不同,和极其精确的尺寸;他不以机械的,而以几何学的方式看待这门学科,并同时将其运用于实践。他已经做成了很多乐器,并且还在做极其大量、各式各样、比中国现有的更加完美的各类乐器。如果我把书中的内容全部介绍出来,那这信就变得太长了;我只说,书里的规则与我们欧洲音乐完美吻合,因此,我想它们在欧洲也会受人喜爱。宇宙中至高无上的君王,在整个世界伟大的建设中,使一切均衡的造物主启发了这两个相隔甚远的国度相同的灵感,这些灵感的种子塑造了同样的科学。(32)Fondo Albani,Archivio Segreto Vaticano,Città del Vaticano,255,20 ottobre 1714,cc.236r-237v.
几个因素可以解释康熙的多元文化态度。首先,因为他是满族后裔,在宫廷中对各种宗教都持独特的多元态度。(33)Evelyn Rawski,The Last Empero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264.自孩童时起,他曾受西方传教士的教导,所以教育背景是极为国际化的。其次,满族自北方入侵,培养了一种适应能力,并渴望从各种文化中博采众长,(34)Owen Lattimore,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Boston:Beacon Press,1951,p.123.这与中国汉族宫廷持续严格的传统形成对比。确实,满族人私下里保持着他们自己萨满教的宗教习俗,而在公开场合则奉行儒家礼仪。(35)Karl A.Wittfogel,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New York:MacMillan,1949,p.14.另外,道教和藏传佛教受到保护,以防止引发这些民众的不安。这种看法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反基督教情绪盛行时期,清廷仍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宗教容忍。而且,康熙时代,满族的神学观已经从多神论演变为一神观,朝廷的仪式不是儒家礼仪,也不再由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所限定。(36)Evelyn Rawski,The Last Emperor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pp.234-235.这两项原则都与基督教的上帝观念和各阶层人士的宗教实践相一致。
清代的多元文化主义延伸到音乐,音乐在宫廷礼仪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康熙对欧洲人带来的西方音乐表现出的热情,肯定与此相关。因此,德礼格对宫廷的音乐贡献可能直接或间接地贡献于包括祭孔在内的庆祝活动中——考虑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激进立场,这真是个讽刺。满族人在他们的仪式中融入了各种音乐的影响,包括中国汉族,蒙古、韩国、越南和尼泊尔等等。(37)Siu-Wah Yu,The Meaning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Non-Chinese Musics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Manchu Court,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96,p.42.考虑到这一国际语境,西方音乐的加入也并不显得不合时宜。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康熙对音乐理论的态度。他为了请德礼格教授第三、十五、十六皇子,1714年颁布的诏书中特别强调了理论基础的重要性。
关于请外国人德礼格教音乐,我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他们(皇子)学习演奏键盘乐器。我的目的是让他们研究律吕的起源(音乐理论)。如果我想要音乐家,我是缺哪种演奏者的吗?你可以明确地告知德礼格,让他要用心教。他应该教授的是音乐理论的基础。(38)方豪:《嘉庆前西洋音乐流传中国史略》,《大陆杂志》,1952年,第4卷,第10期,第7页。
也许德礼格在当时就明白了这一点,不然也就不会在前文引用的给母亲的信中,感叹作为宫廷音乐家的命运了。
二
德礼格的奏鸣曲由中国天主教会收藏,作为北堂图书馆丰富馆藏的一部分。这些资料大多原本是天主教会的财产,现在大部分保存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德礼格的手稿多年来一直受到严密保护。尽管北堂图书馆位于中国境内,但很大程度上并未对研究人员完全开放,所有权仍然存在争议。幸运的是手稿被李蔚那拍照后,存放在巴黎的赛扎尔·弗朗克学院(L’École César Franck)图书馆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们制作了微缩胶片可供参阅。最终,1996年12月北京国家图书馆首次准许笔者对手稿进行检查,2004年11月笔者再次获得访问许可。
笔者检阅德礼格的奏鸣曲手稿原件,在北堂图书馆目录编号为3397,其中提供了关于手稿的装订材料、构造、墨水和修正信息,以及其位置索引,但不幸的是没有创作日期。扉页标明“内普里迪为小提琴独奏和通奏低音而作的奏鸣曲,作品第三卷”(Sonate a Violino Solo col Basso del Nepridi,Opera Terza)。全卷共73页,丝绸封面,现已褪色且有墨水污迹。内页可见汉字。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标题页系手绘。出现的不是作曲家的名字,而是佩德里尼(Pedrini)的同字母异序词“内普里迪”(Nepridi)。所用纸张的厚度与质地不一致,大多数谱页由两张背对背胶合而成。唯一例外的是,第三奏鸣曲进入到第四奏鸣曲的第一部分,这几页纸是由一张米质纸、且两边粘着非常薄的纸组成的。墨水密度不一致,有些页面看起来比其他页面模糊得多。很多段落似乎仓促记写。五线谱大部分布局工整,有些是根据需要徒手随意添加的,使用了画交叉影线、擦除和黏贴纸片三种校正方法。装订非常精美,但封面内部撕裂,致使可观察到下层装订的织物——一根闪闪发光的金丝从中间穿过,还可以看到一些精心编织的丝绸锦缎。最有趣的是,几页纸上都出现了用胶水粘起来的页边空白,音乐记谱写在其中的一个上面,表明此卷在奏鸣曲正式完成之前就被装订起来了。
德礼格奏鸣曲的扉页模仿了科雷利《第五卷奏鸣曲》第二部分卷首插画的设计模式。后者的手稿誊抄版可能在出版之前就已经广为流传了,而德礼格对图案的借用,证实他已见过正式出版的乐谱。总的来说,德礼格的作品集更像是一部音乐笔记,由各种各样的纸张拼凑而成。封面的丝绸以及墨水的纹理都表明它更像是在中国组装的。纸张间不寻常的粘贴方式,以及频频出现的匆忙迹象,表明作曲者缺乏充足的材料和足够的闲暇。如此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份手稿即使不是1711年至1746年德礼格在中国生活期间创作的,也肯定是在中国誊抄的。虽然它们的创作时间无法确定,但一个有趣的推测是,这些奏鸣曲可能是德礼格在监禁期间创作的,兴许是想送给难以捉摸的皇帝的礼物。它们完全有可能在宫廷中由教士们表演,或者送给皇子们作为教学素材。尽管这些奏鸣曲认定为第三卷,颇具诱惑性,但并没有德礼格更早的作品流传下来。虽然他在前文中提到创作了十首三重奏鸣曲组成的三套作品,至少这个信息为进一步研究德礼格的创作提供了诱人的可能。
至少科雷利的一些作品当时已经在中国出现过。奏鸣曲第一至第四号为北堂书目的3251藏书号。这个编目完成于1949年,是图书馆员、遣使会神父惠泽霖(范哈伦,H.Verhaeren,C.M.)耗费十年完成的。在他的介绍中称这些藏品为“古老的遗产,在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历经沧桑、日积月累、持续不断地丰富起来。它始于1583年利玛窦抵达中国,止于1773年耶稣会士的镇压。”(39)H.Verhaerened,Catalogue of the Pei-T’ang Library,Beijing:Lazarist Mission Press,1949,p.v.图书馆的5133卷藏书来自耶稣会、遣使会和其他传教士图书馆。收藏的科雷利卷本是罗杰(Roger)的小提琴和大提琴分谱本,乐谱出版于1723年到1742年。这些乐谱可能是在德礼格生命的最后20年里到达中国的。(40)感谢鲁道夫·拉施(Rudolf Rasch)提供这些细节。
科雷利的第五号奏鸣曲在德礼格去中国前不久出版,并未出现在目录中,但从受其影响的谱页布局来判断,德礼格很有可能在创作自己的奏鸣曲时就已经接触到了这部作品。两套奏鸣曲的设计版式几乎一样,都包含12首奏鸣曲,尽管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划分不同。科雷利的奏鸣曲平均每部分为六首,而德礼格的第一部分有八首奏鸣曲,第二部分只有四首。科雷利奏鸣曲的第一部分每首都有五个乐章,他运用了庄板(Grave)、快板(Allegro)、柔版(Adagio)、活泼的(Vivace)和吉格-快板(Giga-Allegro)来标明。德礼格的第一部分有着相同的标题,但是额外加上了广板(Largo)、如歌的(Cantabile)和芭蕾-快板(Balletto-Allegro)。两位作曲家的第二部分都采用了舞曲:前奏曲、阿拉曼德、库朗特、萨拉班德、加沃特、吉格。像科雷利一样,德礼格常在舞曲后面加上速度标记,如前奏曲-活泼的、库朗特-快板,以及萨拉班德-活泼的。德礼格的一些乐章超出了科雷利的影响,而且事实上是采用了极端的衍伸手法。通常从引用一个动机开始,之后持续变化;而科雷利的技巧和音型都是自由挑选使用的。尽管德礼格的作品中有些明显的摘引,但自己的个性却自始至终闪耀着光芒。他的奏鸣曲包含了有趣和非比寻常的段落——一些明显的错误中存在着令人惊异的迷人的东西,最有价值的是,让我们能一窥其强大的精神世界之一隅。我们知道,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创作此类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在“仪式之争”中实现教皇议程的政治砝码;但同样有可能的是,它们也充当了德礼格自己的宗教砝码,是实现他对中国传教使命个人奉献的一种方式。
音阶的组织和音调系统对康熙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基音黄钟象征着皇帝本人。此外,中国音乐的记谱法将成为清朝的一个永久记录。
三
德礼格得到皇室恩宠的速度之快,并没有使他受到北京耶稣会士的喜爱。尽管他们对禁止礼仪的后果心存担忧,但德礼格甚至在皇帝本人面前公开支持这一禁令,似乎对他们之间亲切、乃至亲密的关系没有影响。1714年,康熙让他给教皇写了一封密信。这封信不可避免地被发现后,引起了耶稣会方面的强烈不满,他们坚决要求对信件进行修订。次年,在德礼格著名的奏贴中,最终决定以书面形式总呈教皇谴责法令,即1704年的《自登基之日》(Exilladie)通谕,同时以最强烈的措辞告诉皇帝他正在遭受的迫害(1715):
因为我将这些事告诉了尊贵的您,所以耶稣会士的怒气就向我发作,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迫害我、压迫我、迁怒于我,使我很难留在他们的会堂。他们唯一的愿望是,陛下把我赶出中国,除了耶稣会士,不允许我或其他任何人留在这里。这就是为什么去年他们完全改动了陛下您命令我写给教皇的信的原因。(41)Archivio Collegio Leoniano,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431,Rome,1715,pp.39-50.
德国耶稣会会士纪里安(基利安·斯通普夫,Kilian Stumpf,1655—1720),意识到肆意诽谤的重要性,决意在欧洲通过印刷名为《真理之讯》(InformatioproVeritas)的小宣传册来攻击在中国的遣使会徒。但是德礼格拒绝反击。“我手里没有这个小册子。耶稣会会士们不知我们是否看到了它。我们了解全部事实,我们也能让人们清楚地了解无可掩饰的谎言、污蔑、恶意及罪行。而这小册子正是这些东西滋生的土壤。他们不是还委托印刷发行了吗……轮不到我对它进行评价(1718年7月)。”(42)影印本藏于De Vincentiis,Documenti e titoli sul privato fondatore dell’attuale R.Istituto(antico Collegio dei cinesi in Napoli)Matteo Ripa sulle missioni in Cina nel secolo XVIII e sulla costituzione e consistenza patrimoniale della antica fondazione/R.Istituto orientale in Napoli;per Gherardo de Vincentiis,Napoli:G.Salvati,1904,p.315。
在德礼格这个传信部暴躁和倔强的主角身上,耶稣会士看到了对他们留在中国造成的致命威胁,于是在皇帝面前败坏他的名声,就像他们对多罗主教所做的那样。他们通过代理人官吏赵昌(Zhao Chang),让康熙确信德礼格篡改了他给教皇的密信,正是这些错误的信息导致克莱门特在1715年颁布了一个新的更强有力的诏令。如此一来,促使清廷用三种语言向欧洲发出了“红色通告”(Red Manifesto),并严厉地谴责了德礼格。如此残酷的迫害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1717年10月20日)。
谢主恩赐,我对自己的健康还算满意,觉得还算好,除了胃部和头部一贯虚弱外,有时会全身酸痛;双鬓全白,眼睛昏花;所有迹象都表明我行将就木。由于上帝的恩惠,我很快恢复了健康,但最坏的是精神上的伤害,那些无法接受由于我而让这位皇帝认识了教皇的规定、并让教皇认识了这位好皇帝的人,持续给我增添烦恼、迫害和忧愁。这就是在中国散布的一切谣传和诽谤的根源所在,毫无疑问,这些信息在欧洲的传播,使我成为两位君主的骗子和煽动者。上帝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骗子。(43)Archivio Collegio Leoniano,Rome,20 ottobre,1717.
到了1719年底,他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在没有任何人施以援手的情况下,我常不得不想起这些话来安慰自己:“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当作恶的仇敌来吃我肉的时候,当同样的他们召集全会来攻击我的时候,我将永远盼望、永远不会停止为神圣的律法而进行的上帝之战,罗马教廷已为此使命作出了指示。(44)1719年12月6日这封信的原件似乎是从莱奥尼亚诺学院(Collegio Leoniano)德礼格信件之卷中撕下来的。这可能是在它被翻译成法语之后发生的,参见A Launay ed.,Les Mémoir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Paris:Maison principale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1865-1866,volume V,pp.595-603.
《自登基之日》已经毫无疑问地确定了教皇反对中国的世俗礼仪,但在中国出版此通谕的努力一直受到耶稣会的阻挠。北京教区的牧师康和子(奥拉齐奥·达·卡斯托拉诺,Orazio da Castorano,1673—1755)首次尝试后,直接导致了使节们的被捕和监禁,康和子把这一切完全归罪于北京的耶稣会神父们。之后克莱门特决定第二次往中国派遣使节,选择了嘉乐主教(卡洛·安布罗吉奥·梅扎巴尔巴,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1685—1741)。这不仅是外交上再次的惨败,而且还导致了德礼格的入狱。1720年11月,德礼格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并寻求使节的介入:
尽管我应该去找这些教廷使节以反对在北京的耶稣会士,因为他们对我无休止的污蔑中伤,几乎置我于死地;但是我没有去,为了让他们不在皇帝面前指责我……。确信无疑的是,对于这些耶稣会士来说,在圣座面前如此污蔑我很重要,尤其是当遭到死亡威胁时。(45)1720年12月12日写给朱塞佩·切鲁(Giuseppe Cerù)的信件。原件已丢失。参见A Launay ed.,Les Mémoir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Paris:Maison principale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1865-1866,VolumeVI,p.38。转引自Viani,Istoria delle cose operate nella China da Monsignor Gio.Ambrogio Mezzabarba...Paris:Briasson,date unknown,pp.40-42。
然而,北京的耶稣会士凭借他们丰富的经验,已经为限制嘉乐的活动做了周密的准备,德礼格记录道:
莫劳,那位得到名叫“昌”(译者注:原文是Ciao,估计是听到的Chang,从而与赵昌吻合)的官员支持的神父,受“昌”先生口令让我们在每日每夜的大部分时间里受尽折磨,不仅得不到片刻的休息,还没有任何食物,我和马国贤也被禁止跟使节和其随从们有过多的交流。(1723年于狱中)(46)Archivio Collegio Leoniano,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469,Rome,1715,pp.551-570.
嘉乐已被说服采用妥协的八项许可来修改章程,这是必要的,修改后的章程作为在京传教士的一致决定要提交给罗马教廷。有鉴于此,莫劳神父和赵昌设计了一个颁布“使团要事摘要”[即所谓的《嘉乐来朝日记》(Mandarin’sDiary)]的诡计,并要求所有修士都在上面签字。但是德礼格拒绝了:
德礼格听了报告的拉丁文版本的一小部分,其中有几个结论被认为是使节作出的,使节说这些结论是在德礼格在场时提出的,但他实际上并不在场,因此有了这些事情。(47)Archivio Collegio Leoniano,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469,Rome,1715,pp.551-570.
莫劳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康熙,康熙勃然大怒,立即颁布了一项判决(1721年2月21日)。
德礼格不过是个卑鄙无耻的骗子之流。昨天他拒绝签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的冒犯。这种无赖在清廷鲜有见到。(48)这是安东尼奥·西斯托·罗索(Antonio Sisto Rosso)的第27号文件,参见Antonio Sisto Rosso,Apostolic Legations in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South Pasadena:P.D and Ione Perkins,1948,doc,n.27。
然后他命令,德礼格在赵昌的监督下接受惩罚。但赵昌对命令的执行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权限:
在宫廷的高额奖赏下,告密者层出不穷。皇帝下令把他关进监狱,带上新的镣铐,这是他无法写作的原因。就在向狱吏介绍之前,先把双手绑在身后,让太监将德礼格扔到地上,在他的头、脸、肩膀以及全身一阵脚踢、聒耳、击打,然后采用中国的方式来继续打他,之后是再次的拳打脚踢;继而将德礼格拖出大厅,后再拎回来,又是一顿踢打,最后被一名太监粗暴地拉了起来,带到囚禁其他欧洲人的地方。(49)同注。
十天之后,康熙稍微冷静了一点,他错误地将德礼格释放到了他的死敌——法国耶稣会士的手中(1723年10月16日):
陛下平息了愤怒,想要减轻我的牢狱之苦,但这反倒成了我的坏事。他让我从监狱中来到了教堂,这也得到了那些深谙此事的人的暗示。在所谓“好心”的关照下,我从未像在他们手中那样被严厉而紧密地监禁。(50)Archivio Collegio Leoniano,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469,Rome,1715,pp.571-601.
耶稣会士们“极端严苛和暴力”地监禁了德礼格,直到两年后在新皇帝雍正的命令下才不情愿地释放了他。
德礼格对在中国的这些年的描述与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大相径庭,而其中许多现有的观点都揭示了一种从耶稣会视角改写历史的倾向。这是一篇关于他的生活、但同样带有党派色彩的完整叙述,其许多完整的信件,实际上是在19世纪史诗般的《遣使会备忘录》(MémoiresdelaCongregationdelaMission)中就已经发表过。(51)A Launay ed.,Les Mémoires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Paris:Maison principale de la 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1865-1866,volume V,pp.595-603.我们非常感谢遣使会修士约翰·雷伯特(John Rybolt)提供给我们克劳德·劳蒂西耶(Claude Lautissier)扫描的相关卷的复印件。该书1865年出版后,由于被指对耶稣会进行了诽谤性的批评,一些人即刻付出不懈努力将其列入禁书名录,停止流通并予以销毁。最终,通过删除冗长的批评耶稣会士的段落,尤其是德礼格的那些批评言论(52)对《遣使会备忘录》的写作做了简要说明,参见L.Mezzadri and F.Onnis,Storia della Congregazione della Missione,II/1,Rome:CLV Edizioni Vincenziane,1992.pp.449-452。,由7卷缩减至3卷,1911年它以“政治正确”“新版、校订、更正并扩增”后重新发行。我们可以推测,1865年后正是这同一只手,开始枉顾事实地从前述德礼格的1708年7月6日的信中删去一些谴责耶稣会士的段落;同时也将现藏于莱奥尼亚诺学院(Collegio Leoniano)里的《遣使会备忘录》的装订撕毁,并把那些冗长且更具煽动性的书信从书中撕除。难道德礼格个人要为第一次基督教中国传教的最终失败负责吗?他始终坚称是因为耶稣会干涉国家事务而非教皇的任何裁决,才引发的致命的结果,并且他的行动一直是“为了神更大的荣耀”[A.M.D.G.(ad Maiorem Dei gloriam)],而非“通过耶稣会的方式”[A.M.D.G(al modo dei Gesuiti)]。直至他生命的尽头,德礼格在清廷担任了35年的乐师。当1724年基督教被禁止后,他的教堂——西堂,成为北京唯一被当时官方接纳的教堂。
译后记
彼得·奥索普(Peter Allsop),国际知名巴洛克音乐研究专家,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和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1973年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任教,曾多次在中央音乐学院担任访问教授。他是科雷利研究顶级专家,近二十年集中于巴洛克器乐和德礼格的研究,著作颇丰。代表作有:《意大利三重奏鸣曲,从起源到科雷利》(TheItalian“Trio”SonatafromitsOriginsuntilCorelli,Clarendon Press,1992年)、《阿坎杰罗·科雷利:“我们时代的新奥菲欧”》(ArcangeloCorelli:“TheOrpheusofOurTim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年)等。
乔伊斯·琳道芙(Joyce Lindorff),美国古钢琴演奏家,天普大学教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德礼格”词条撰写者,曾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访问教授。
这篇文章是彼得·奥索普教授2018年到西安讲学时,嘱托译者翻译成中文后发表,原文为英文。彼得说明该文为最新修改和校订的,并且尚未公开发表。此前,在2007年彼得和乔伊斯·琳道芙合作在《意大利音乐学杂志》上发表了意大利文的《从费尔莫到中国皇宫:德礼格,音乐家和使徒传教士》(DaFermoalcorteimperialediCina:TeodoricoPedrini,musicoemissionarioapostolico;参见:RivistaItalianadiMusicologia,vol.42,No.1,2007,pp.69-104)。
文章梳理了德礼格去中国之前的历史和曲折的旅途,以及到中国后在清廷中作为宫廷乐师的跌宕起伏:从受宠到因坚持教皇诏令、与耶稣会士之间的冲突以致锒铛下狱。彼得在研究中运用了大量德礼格信件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原始史料,具有很强的实证性。此文是目前学界研究德礼格史料最充足的文章之一。
译者经过和意大利文版同名文章对比后,发现在新的英文版文章中,作者对意大利文版的不确定信息予以校订,对引用信件的原文进行了审核,并对一些和文章主旨联系不紧密的背景信息予以删除和调整。尤其是删去了将近8页科雷利奏鸣曲的分析过程,整体上加强了文章逻辑推进的紧凑性。所以译者认为该文尽管与意大利文版同名,文章有近70%的相似性,但在研究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延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