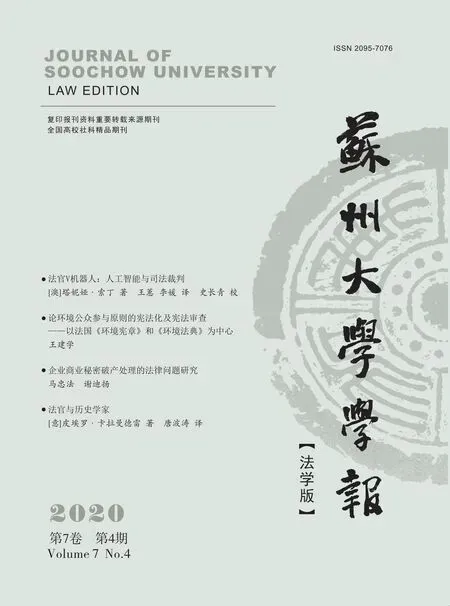论过失犯中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方法
蔡 仙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是德国刑法通说还是日本新旧过失论,都承认结果避免可能性是过失犯成立的必要条件。根据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即便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并造成损害结果,仍不足以成立过失犯,只有当行为人履行注意义务而能避免结果时,才能将不法结果归责于行为人。我国刑法语境下,接纳该理论不仅存在法理上的支撑,也具备实定法上的根据。但反观我国司法实务,法官们并未接受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例如,在多数过失犯案件中,简易的司法裁判居多,从而忽略了对过失犯成立的一般要素包括结果避免可能性展开论证。对于简单、明了的案件,简易裁判可能不存在多大问题,但若案情较为复杂时,判决缺乏充分论证便意味着裁判结论本身缺乏说服力而令人生疑,譬如“王某某、孙某某消防事故责任案”的判决。
基本案情:被告人王某某和孙某某于2002年4月租赁某商场人防工事东大厅并改建为酒吧。后二人因擅自改建施工而被责令停工整改。王某某报送整改报告后,在未取得市消防支队批准的情况下,再次施工,使用大量可燃材料对酒吧顶部、墙面进行装修,并多次将设置在酒吧与旁边休闲屋之间通道上的石膏挡板拆除,并于2002年12月28日21时将制作好的吧台搬入休闲屋过道中。当晚,休闲屋起火,蔓延到酒吧施工现场,致多人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经市公安消防支队认定,火灾原因不明;王某某和孙某某负间接责任。①(1)①参见《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52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0页。
该案中,法院经审理认为,二人在进行建筑内部装修工程中违反消防管理法规,经消防监督机构通知采取改正措施而拒绝执行,造成严重后果,构成消防责任事故罪。但消防责任事故罪属于特殊领域的过失犯,同样需要判断拒不执行改正措施与严重后果之间是否存在规范上的因果关联。因为,如果是他人故意放火的话,可能存在即便二人采取改正措施,结果仍然不可避免的情况,但法官并未考虑该要素。
诚然,上述现状与亟需满足被害人情感需要、当前技术鉴定水平有限以及提高办案效率等因素相关。但不可忽视的是,理论研究上的不充分亦会导致司法实践中理论供养不足,继而使得法官为了保险起见,不敢轻易引用刑法第16条来排除行为人的过失责任。而这种不充分主要体现在缺乏一套详尽的、可供借鉴的成体系性的判断结果避免可能性的方法和标准。
由于结果避免可能性的检验是在事实因果关系成立基础之上所进行的一个规范判断,它是一种假想因果流程的判断,因而,对它的检验采取的是一种假设性的调查。既然是一个假想的因果流程,那么,在理论上就有必要澄清以下问题:第一,该假设前提中,个案中遵守注意规范的行为是什么?尤其是在一人违反多个注意义务,或者合义务替代行为有多种选择时,该问题越发难以作答。第二,该假设条件所引起的结果中,“同一损害结果”如何界定?如果行为人履行注意义务仍然会引起法益损害(如轻伤),但其损害程度低于违反注意义务时所引起的(如重伤),此时,“损害结果”是指什么?结果的“同一性”如何判定?第三,学理上对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讨论多以“一过失单独正犯违反了一个注意义务”为原型而展开的,因此,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也相对简单。但在数人过失竞合的复杂情形下,又如何认定结果避免可能性?第四,如何对结果避免可能性予以证明?结果避免可能性要达到何种证明标准?
因德国司法实务很早承认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的正当性,在处理许多过失疑难案件时形成了系列重要判例。鉴于此,本文将围绕着结果避免可能性认定过程中的上述四个核心问题,立足于我国刑法规定,适当参考和吸收德国刑法理论及司法实务在判断结果避免可能性时所积累的经验,探讨一下过失犯中结果避免可能性要素的认定方法和具体规则。
二、对“合义务替代行为的实施”的正确假设
(一)注意义务遵守的主体限定
在只有一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的场合,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认定只会假设当行为人实施合义务替代行为时,结果能否避免。然而,有些案件会出现行为人与被害人同时违反注意规范的情况,以至于有的学者提出与通说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主张应假设“当被害人遵守注意规范时结果能否避免”;另一种观点主张应当假设“当行为人与被害人同时遵守注意规范时结果能否避免”。那么,这两种观点的内在逻辑是什么?能否在被害人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假定被害人遵守注意规范,以此来判断结果能否避免呢?以德国著名“卡车司机案”为例,对该问题加以澄清。
基本案情:行为人在笔直开阔、约6米宽的道路上驾驶着一辆载货卡车。在同一驾驶方向的右侧,被害人骑着一辆自行车。行为人以26~27km/h的速度超过骑自行车人。拖车车厢的边缘距离自行车驾驶者左边胳膊肘大约75cm。按照规定,要求的合法距离是1~1.5m。在超车过程中,骑车人的头部卷进拖车右边的后轮轮胎,接着被压过去,当场死亡。之后,从死者体内抽取血样,发现其血液内酒精含量为千分之1.96。事后查明,鉴于被害人当时的醉酒状态,即便卡车司机在超车时保持合法的距离,事故也很有可能仍然会发生。①(2)①BGHSt.11,1-7.
对于此案,作出判决的德国联邦法院假设的是“当行为人遵守注意规范时,事态会如何发生”。但学者Ranft认为,该案中重要的不是假定的符合注意义务的行为人举止,而是假定的无过错的被害人的一般情形。因为依规范保护目的理论,若行为人以外的其他起共同作用的风险因素参与了损害事件的发生,那么,是否成立过失犯要取决于转化为现实中的结果的危险是否落入了规范的合法保护领域。因此,重要的不是起共同作用的风险因素在假想行为人履行义务时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而是违反义务的举止在欠缺这个起共同作用的风险因素的情况下是否引发了某种结果类型的危险,而发生的具体结果就属于这种结果类型。②(3)②Vgl. Otfried Ranft, Berücksichtigung hypothetischer Bedingungen beim fahrlässigen Erfolgsdelikt? Zugleich eine Kritik der Formel vom, rechtmäßigen Alternativverhalten, NJW, 1984, S.1429.而学者Puppe则将那些由被害人和行为人共同过错引发结果的案件视为存在双重因果关系的情形,结果避免可能性也是一个因果关系判定的问题,即注意义务违反性是否是损害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中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此一来,多个分别足以造成结果发生的原因都是结果的原因。故“卡车司机案”的焦点在于判断交通参与双方是否足以单独引起结果,即该案是否属于双重因果关系。③(4)③Vgl. Ingeborg Puppe, Die Lehre von der objektiven Zurechnung und ihre Anwendung-Teil 1, ZJS 5/2008, S. 145.通常在双重因果关系的场合,可以想象一个参与者的注意义务违反不存在,因为另一个参与者对注意义务的违反足以单独解释事故。在判断被害人违反注意义务之外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是否是事故发生的一个充分的条件时,我们需要追问的不是“当行为人实施了合义务举止时会发生什么”,而是“当被害人履行注意义务时结果是否也会发生”。如果即便被害人履行了注意义务,结果仍然会发生,那么,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就是结果发生的充分条件,因此,可以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
但是,上述两种在认定过失犯时假设被害人履行注意义务的做法存在一定的疑问。首先,Ranft将“保持合法距离超车”这一规范目的界定为“防止一个清醒骑士受到惊吓而酿成事故”。然而,无论是毫无过错的骑车人,还是行为有瑕疵的骑车人,都应当受到“保持1~1.5米距离”该规范的平等保护。另外,Ranft对“卡车司机案”仅仅从注意规范保护目的视角认定卡车司机创设的风险是否属于注意规范要禁止的风险(风险创设的问题),却未考虑个案中注意规范到底能否发挥避免结果的实际效用(风险实现的问题)。再者,虽然在“卡车司机案”中,从自然因果关系视角来看,或许被害人的错误举止和行为人违规驾驶都是解释结果发生的原因。但正如前文所述,在刑法中被害人遵守注意规范后会引起什么样的结果并不重要,被害人的过错只是作为判断行为人的合义务行为能否避免结果时需要保留的、作为附随情境的事实要素。换言之,基于个人责任主义,刑法最终判断的是行为人本身是否具有结果避免能力。而至于行为人与被害人对结果产生所起到的作用力大小,则是评价行为人在民事损害赔偿上的份额问题。正如我国学者所言,Puppe的做法“明显混淆了与规范效力相关联的被害人因素,和与规范效力无关的被害人因素”。④(5)④参见陈璇:《论过失犯的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第695页,脚注37。
(二)“风险创设”的先行判断问题
依过失犯归责理论,结果避免可能性是在判断“创设了法所不被允许的风险”之后,对“不被允许的风险是否被实现”进行的一个鉴定。基于此,对“被违反的注意义务”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判断,将其界定为“创设了法所不被允许的并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风险”。因此,在判断结果避免可能性之前,需要排除以下两种情形:第一种,行为人违反的是完全与风险无关的行政规范。第二种,行为人违反行政法规上的义务虽然创设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但是该义务的设定不是为了避免具体案件中的法益损害结果,而是为了避免其他的损害结果。这也是过失犯中注意规范保护目的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基于思维经济性考虑,当行为人同时违反多个特别行政法规并造成人员伤亡时,对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没有必要将所有违反特殊规范的举止都以相应的合义务行为所替代。“查明过失犯的实行行为,将过失犯的内容限定在引起事故的主要原因上,不仅能够明确审查的对象,使被告人更加容易行使辩护权,而且,也可以减少很多无意义的证据审查,减少司法工作人员的办案负担”①(6)①参见黎宏:《过失犯研究》,载刘明祥、李立众主编:《过失犯研究——以交通过失和医疗过失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3页。。对此,可以下列案件为例,加以说明。
基本案情:某一货车司机超载超速行驶,路过某一地段时,路面突然垮塌,货车翻入路旁的农田之中,将正在田间劳动的一名农民当场压死。事后查明,该路段当时已到必然垮塌之时,即使货车司机既不超载也不超速行驶,当他驶过该路段时,路面也会发生垮塌。②(7)②参见刘志伟、左坚卫主编:《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页。
该案中,货车司机不论是违反超载规定还是超速规定,都创设了一个引起法益损害的具体危险。但是,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是由于路面坍塌所造成的,而防止路面坍塌正是禁止超载规定所要防止的结果,与违反超速规定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禁止超速的规定通常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减少制动时间,而非防止路面塌陷。因此,只能将过失实行行为界定为违反禁止超载规定的驾驶行为。不过,在有些案件中,多个违反行政规范都创设了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且这些规范都是为了防止具体个案中发生的法益损害后果。例如,司机A醉酒后在道路上超速行驶,突然遇到一路人B横穿绿化隔离带,A刹车不及撞到B,致B死亡。一般而言,司机醉酒会导致行为人反应迟钝,超速驾驶会导致刹车时间变长,从而都创设了法所不允许的具体风险,使得事故难以避免。当然,在排除极端的、仅由一种违规行为引起结果的情形后,我们可以将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界定为行为人超速且醉酒驾驶的行为。相应地,符合注意规范的行为是指行为人在清醒状态下在限定速度之内驾驶的行为。
(三)最低限度的合义务替代行为
在明确了未履行的注意义务之后,与之相对应合义务替代行为就相对容易确定了。不过,这种确定也只是初步性的,至于如何选择合义务替代行为,在司法实务中仍然可能出现问题。因为法官选择的替代行为仍然可能是违反注意义务的。例如在“幼儿中毒缺氧案”中,两个幼儿的母亲在家中招待客人之后,未检查客人吸烟所留下的点燃的或者有暗火的烟头,和客人一起离开自己的家,使得沙发上烟头留下的暗火蔓延,独自在家的两个幼儿因吸入暗火释放的一氧化碳和氰化物而死亡。③(8)③Vgl. Hans Kudlich, JuS 2005, S. 848. BGH, Urteil vom 1. 2. 2005-1 StR 422/04.一开始,地方法院从有利于母亲的角度出发指出,暗火不是五岁的儿子用打火机引起的,而是落在沙发上的、燃着的烟头或者烟灰火引起的。在这种情形下,母亲没有违反其照管义务。另外,也不能排除,当母亲实施合义务行为,也就是她回到家中后躺下睡觉,死亡结果也会发生。不过,联邦法院没有采纳地方法院的意见,因为在未检查火源后上床睡觉不是合义务的替代行为,合义务的行为应该是检查是否存在火源后休息的行为。
当然,有时候法官对合义务替代行为的错误认定是源于实定法上出现矛盾。在“醉酒驾驶案”中,醉酒司机以被允许的100km/h的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被另一辆摩托车在很狭窄的空间下抢道,以至于即便该司机全刹车,但还是撞上另一辆车。被告人提出,清醒状态下的司机也会发生事故。④(9)④Vgl. Ingeborg Puppe, Kausalität der Sorgfaltspflichtverletzung-BGH, NJW 1982, 292, Jus 1982, Heft 9, S.662.对此,德国联邦法院认为,此类案件的最终判断取决于实际事件发生过程以及“具体的交通状况”中行为人的失误。该案中,行为人的速度没有与当时行驶状况相适应。如果司机行驶得更加缓慢,那么就可能避免结果的发生。由此,联邦法院肯定了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存在。但德国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法院这种以另一个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醉酒缓慢行驶)替代原有违反谨慎义务的行为(醉酒行驶)的做法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形下,合义务替代行为应该是指“一个清醒的司机保持当时速度行驶”。⑤(10)⑤Vgl. Otto, Grundkurs Strafrecht, Allgemeine Strafrechtslehre, 2004, §10 I 4(a), S.194.因为依德国《道路交通法》(StVG)第24a.1规定,处于醉酒状态下的驾驶人根本不允许驾驶的。实际上,对此案的争论涉及德国两个规范之间适用上的位阶顺序。既然“凡是被禁止的,就是不被容许的”①(11)①参见[德]英格博格·普珀:《法学思维小学堂》,蔡圣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7页及其以下几页。,那么,保持适当速度的义务针对的是遵守一般规范如未饮酒的情形,而醉酒的情况下,无论如何不得驾驶。因此,醉酒状态下驾驶才是该案中重要的注意义务违反行为。在我国,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第2款规定了禁止饮酒后驾驶,而没有类似德国的“与其能力相适应的速度”的特别规定,但是,“驾驶过程中保持与其能力相适应的速度”是一个一般性的注意义务,因此,也会出现如何在两个注意规范之间进行抉择的难题。此时,就需要考虑规范之间的位阶关系。
另外,当可供法官选择的合义务替代行为有多个时,到底选择哪一个,有待明确一个标准。对此,我国有学者提出了限定合义务替代行为的两个原则:(1)合义务的替代行为必须与现实的违法行为同属一个行为类型。(2)若有多个与违法行为同属一种行为类型的合法举动可供选择,由于法秩序没有理由在此之外向公民提出更高的要求,则应将其中最低限度的合义务行为作为替代行为。②(12)②参见陈璇:《论过失犯的注意义务违反与结果之间的规范关联》,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第696页。本文看来,这两个限制原则是符合当今过失犯基本法理的。首先,合义务替代行为是避免义务以内的一般性的被允许的举止,而不是行为人义务以外的举止。不允许对那些行为人为了追寻其利益或特定情形下特定目的而选择的行为范围进行改变,虽然行为人的行为方式违反了特定义务,但是,其对特定行为利益的追求(如驾驶行为)并没有违反义务,相反,该行为是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衡量而被法律所允许的。基于此,合义务的替代行为必须与现实的违法行为同属一个行为类型。再者,对于“最低限度的合义务行为”的要求,也是基于既有的法律规定,国民能够享有的并且能够主张的利益。否则,对行为人过于苛刻,且与法律共同体所允许的内容相矛盾。
三、对“同一法益损害结果之引起”的合理考察
在确定了行为人所应当实施的合义务替代行为之后,紧接着就要判断当行为人实施该合义务替代行为后,同一结果是否发生。此时,又面临着以下问题:第一,该结果是谁引起时,才能肯定结果不可避免?如果后备的被害人、第三人行为或者自然事件也会引起结果发生时,行为人可否以此否定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存在而免除自己的责任?第二,结果的“同一性”到底如何界定?毕竟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假设的是另一种情况,因此,无论如何,假设因果流程中的结果与现实中发生的结果不可能完全重合。第三,如果行为人实施合义务行为会降低法益受损的程度,比如只造成被害人重伤而非现实中的死亡结果,又如何认定行为人的责任?为此,下文将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分析。
(一)对不重要后备原因的排除
在判断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假想因果流程中,侵害结果可能是由事实上引起结果的主体(如行为人、被害人、第三人或不可抗因素)引起,也可能是由后备的、事实上未引发结果的被害人举止(如自杀行为)、第三人违法举止(如故意杀人行为)或者自然事件(如地震)引起。如下列“连环追车案”中,即便被告人保持适当速度,M也会撞到被害人K。此时,行为人能否以存在那些也会引起结果的后备的、事实上未发生的被害人或第三人行为、自然事件来逃避责任呢?
基本案情:浓雾中,因不注意或者超速驾驶雪铁龙的K撞上了合规停放的B的卡车。K的汽车停在超速带上。K在B的帮助下毫无损伤地离开了他的汽车。被告人驾驶着福特,因为超速而撞上了K的车,将该车向前推出十米并撞伤了B和K。这时M驾驶着他的汽车将被告人的福特撞到绿化带中。B、K没有再次被撞到。③(13)③BGH, NJW 1982, 292.
对于此案,德国某州法院认为,尽管被告人保持与视野情况相符合的速度可能避免撞击到K驾驶的雪铁龙,但是,在本案中,M撞上了被告人的福特,如果撞上了雪铁龙的话,受伤的是K而不是B。州法院仅仅认定了被告人对B而不包括K所造成的身体伤害所要承担的责任,因为即便被告人没有超速行驶撞上K的车的话,K也会因之后M的撞击而受同样大小的伤。但是,联邦法院完全否定了被告人提出的因第三人的错误举止使得结果不可避免的辩护理由。其理由在于,根据先前的判例,当遵守注意义务时结果不可避免而免责的案件中,只有仍然会引起结果的假想的行为人或者被害人的行为才能让行为人免责。因此,本案不适用合义务的替代行为方案。但是,至于为什么只有被害人的过错才能免除被告人的责任,而第三人的过错不能免除被告人的责任,联邦法院似乎指明了原因,排除行为人责任的理由在于被害人自己而非第三人引起了一个危险,以至于即便没有行为人违反谨慎义务结果仍然会发生。①(14)①Vgl. Puppe, Kausalität der Sorgfaltspflichtverletzung-BGH, NJW 1982, 292, Jus 1982, Heft 9, S.664.可见,它是将被害人的过错看做了免除行为人责任的原因。但是,在有些场合,被害人只存在一个纯粹的潜在自损行为,如“卡车司机案”中被害人的醉酒行为。而被害人的这种过错难以成为刑法不去保护被害人的原因。这是因为,只有在被害人自我答责的场合,才能免除行为人的责任,而被害人的自我答责必须以被害人支配着法益侵害流程为前提的。
事实上,合义务替代行为免除行为人责任的基础在于“允许的风险”,而不是“被害人的过错”。根据允许的风险理论,基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容忍一定程度范围内的风险,因这一范围内风险引起结果的,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替代性的原因只能在允许的风险范围内加以考虑。而在“连环追车案”中,尽管行为人保持谨慎时,结果仍然会发生,但是,该结果却不是由行为人引起的。易言之,该案中结果不可避免并不是因为允许的风险,而是由于一个不重要的替代性原因造成的。另外,出于规范效力维护的考虑,不允许行为人以“他人在此之后也会引起结果”为由造成侵害结果。②(15)②Günter Jakobs, System der strafrechtlichen Zurechnung, 2012, S. 40.基于此,无关的、非现实的第三人、被害人以及自然事件等会成为引起结果的原因并不重要,也不能成为假设判断中“引起同一结果”的主体。只有当假想因果流程中引起侵害结果的主体与事实上引发结果的主体一致,亦即,都是被允许的风险所造成时,才能否定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存在,从而否定行为人的过失责任。
(二)具体时空内同一构成要件上的结果
假想因果流程中“结果的同一性”比对的是现实中发生的法益损害结果和假想的法益损害结果。因此,同一结果的认定需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必须事实上真正地发生了法益损害结果。在“器官捐献丑闻案”③(16)③OLG Braunschweig, Beschluss vom 20. 3. 2013-Ws 49/13, NStZ 2013, 593.中,作为器官移植医生的行为人操控了捐献器官的分配顺序,使得其他病人陷入不利状况。此时,并不能证明,本应排上序的病人在名单未被操控时会成为事实上的器官接收者,并且由于不存在器官特异性问题而存活下来。因而,被害人都只是抽象地被确定的病人,事实上到底是谁难以明确。因此,“其他病人会存活”这种想象的结果不足以成为刑法意义上的结果。
第二,假想因果流程中的“结果”必然是指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对于生命法益而言,由于它原则上只在生或者死这种本质的选择上才具有法律意义,因此,在行为人杀害了某个本已处于垂死状态之人的案件中,任何的假定因果流程都毫无意义。④(17)④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风险升高与风险降低》,陈璇译,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4期,第200页。但需注意的是,应当区分主动杀人行为与救助过程中导致病人死亡的情形。在医疗救助中,医生遵守注意规范的目的是为了拯救病人的生命,而不是延长一两天的生命。换言之,为了延长被害人一天的寿命,通过刑罚手段去迫使医生按时进行手术是没有必要的。
第三,关于“同一性”的认定。根据台湾学者许恒达教授的分类,“同一结果”至少可以分为以下三类①(18)①参见许恒达:《合法替代行为与过失犯的结果归责:假设容许风险实现理论的提出与应用》,载《台大法学论丛》2011年第2期,第726、727页。:(1)抽离具体时空的抽象结果。以“卡车司机案”为例,如“被害人的死亡”。(2)具体时空内的结果,即“在系争公路案发地点附近,于同一时点稍前或稍后所发生的乙死亡事件”。(3)具体时空内的结果再加入“法益受侵害方式”,那么,卡车司机案中是指“在系争公路上、系争时点前后,甲违反间距超车的风险实现的情境下,卷入车轮下而死亡”。
首先,第一种脱离具体时空的“结果”以及第三种加入结果发生方式的“结果”都难以承担其判断结果避免可能性的任务。第一种定义中的抽象结果在刑法上并无意义,在“刽子手案”中,如果允许“被害人终究会被执行死刑”的理由辩护,就必然会无限制地延伸出“从长远看,谁都难免一死”的辩护事由。②(19)②参见车浩:《假定因果关系、结果避免可能性与客观归责》,载《法学研究》2009年版第5期,第147页。第三种定义是高度具体化的、包括了具体行为方式的结果概念,它会使得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成为无效的理论,因为假定的合义务替代行为与事实上的义务违反行为必然是不同的。
其次,只有假想合义务替代行为与事实上违反注意义务行为同时发生,结果因而出现在具体时空内时,对于判断合义务替代行为能否避免结果才有意义。在“牙医案”③(20)③BGHSt 21 59.中,虽然牙医邀请内科医生会诊也无法诊断出该妇女所患的心脏疾病,但是至少可以推迟妇女死亡的时间,但正如联邦法院所言,义务违反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检验的应该是在拔牙时间都相同的时候,比较“请内科医生”和“没有请内科医生”所引起的结果是否一样。④(21)④BGHSt 21 61.同样地,在交通领域中,以“行为人保持合法速度行驶,那么,就不会在事故发生的时间抵达事故地点”为由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也是不当的。因为只有当采取预防措施适合避免违反(防止结果发生)举止规范,而不是适合推迟规范违反时间时,未采取措施才是原因。
因此,相较之下,第二种定义较为恰当。在“卡车司机案”中,违反注意义务地超车虽然改变了导致结果发生的伤害方式(例如轧过被害人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车轮),但事态发展仍然保持在已经被引起的风险(即超车行为)之中了。⑤(22)⑤Günter Jakobs, System der strafrechtlichen Zurechnung, 2012, S. 41.由此,可以认为两种结果是“同一”的。不过许恒达教授对第二种定义也提出了质疑。在下列案件中,甲为死刑犯,执行死刑前,应由乙医师打麻醉药剂,待甲昏迷再为枪决。未料乙医师不小心取用有毒药剂注射甲,甲在行刑前就因中毒而死亡。他认为,“若乙能稍加注意,注射正确的麻醉药,甲同样会因为行刑而于同一地点与差不多的时间死亡,同样侵害结果仍会出现,依回避可能性理论,结果不可归责于乙”。⑥(23)⑥参见许恒达:《合法替代行为与过失犯的结果归责:假设容许风险实现理论的提出与应用》,载《台大法学论丛》2011年第2期,第728页。但是,不可归责于乙这一结论是不当的,因为该案例真正涉及到的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后备因素”,与前文所提及的“连环追车案”一样,虽然行为人遵守注意义务,同一结果在相近时间和地点同样发生了,但却是由第三人引起的而非行为人引起的。
(三)作为对法益造成负面改变的“结果”
在过失犯认定过程中,若合义务替代行为防止了任何法益侵害结果,当然能肯定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存在;若合义务替代行为虽防止了更为严重的构成要件结果,如死亡,却引起了较为轻微的另一构成要件结果,如伤害,对于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认定,行为人仍然具备结果避免可能性。但是,除了上述两种情形外,合义务替代行为也可能引发了与事实上发生的结果属于同一构成要件的、但更轻微的结果。譬如,现实中发生了重伤害结果,合义务替代行为只会造成轻伤害结果;再或者,现实中发生的是重伤一级,合义务替代行为会引起重伤二级。那么,此时是应当认定合义务行为时(抽象的)结果不可避免,还是认定(具体的)结果可以避免呢?以德国曾发生争议的“儿童交通事故案”为例,进行说明。
基本案情:被告人以35km/h的速度且以过于狭窄的距离驶过一辆公共汽车。这辆公共汽车刚好从相反的方向驶过来并停了下来。一个五岁的儿童从汽车后面跑到车道上被被告人撞上且受伤。根据专家的鉴定意见,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所造成的结果是重伤害,如果行为人保持谨慎,虽然不会出现重伤害的结果,但仍会出现程度较轻的身体伤害。①(24)①OLG Oldenburg v. 1. 12. 1970.
在审理过程中,一审法官认为,虽然不能排除,行为人遵守交通规则的话,交通事故也会发生,但或许对被害人造成的伤害程度更小。因此,一审肯定了被告人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对于出现的具体的、更为严重的伤害结果的原因性。但在上诉审中,高等法院否定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指出:当行为人即便实施了合义务的行为,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仍然会发生,但会比违反义务时造成的结果更轻,据此要求行为人承担刑法上的责任是不符合构成要件的保障功能(即罪刑法定功能)。因为刑法中的过失伤害罪没有区分严重的和轻微的身体损害。但有学者认为,高等法院忽略了被害人原始的身体状况来认定伤害。每一个对身体的完整性造成的额外损害都是过失伤害罪意义上的伤害行为。只要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比遵守谨慎义务的行为造成的伤害更大,便足以认定过失伤害罪中的伤害结果。②(25)②Vgl. Schrönke-Schröder, Strafgeseztbuch, 2014, §229, Rn.2.构成要件的保证功能无论如何也不能为高等法院的观点提供依据,刑法条文并没有区分重伤和轻伤,因此,只要行为人在不可避免的轻伤的基础上,因过失违反义务又增加了一个更严重的损害,就可以归责。③(26)③Vgl. Günther Klussmann, Pflichtwidrigkeit und hypothetischer Kausalverkauf bei Fahrlässigkeitsdelikten, NJW 1973, 1098.
实质上,这场争论源于上诉审法官与一审法官及学者对构成要件之结果的理解不同。其中,高等法院将过失伤害罪中的“身体伤害”视为不法行为引起法益受损后所呈现的一个持续不变的状态。这样一来,无论是轻伤还是重伤都是伤害罪中的构成要件结果。因此,高等法院以合义务替代行为仍会造成同一构成要件结果为由,放弃了对行为人的追责。相反,反对者将过失伤害罪中的构成要件结果视为违法行为对法益引起的一个不利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对者的主张更为合理。因为即便是一个病人的健康也可以进一步被损害。在故意伤害中,没有人会质疑对一个身受重伤的人再次实施重伤害行为是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只规定了过失致人重伤罪,因此,在过失致人重伤的场合,即便是合义务替代行为也会引起重伤结果,也不能马上以不存在结果避免可能性为由否定行为人的责任。因为当认定了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在合义务替代行为造成的伤害结果基础上引起的是一个重伤程度的伤害时,就说明合义务替代行为可以避免这样一种重伤程度的不利变化,即重伤结果具有避免可能性。此时,仍有必要追究行为人的过失责任。
四、过失竞合时判定规则的特殊性
以往对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认定通常只论及过失单独犯,即一个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而造成损害的情形。此时,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较为简单,只需要进行一次性的判断。然而,伴随着社会分工的推进,在医疗、工程、食品等领域经常会发生多人同时违反注意义务而造成法益损害即过失竞合的情形。过失竞合类型多样,可细分为并列型过失竞合与直列型竞合。并列型过失竞合是指处于对等地位的行为人的过失同时地、并列地竞合在一起。从过失行为与所发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来看,并列型过失中包括了累积竞合以及并存竞合的情形,类似于累积因果关系和择一因果关系。直列型过失竞合是指在直接过失行为人之过失的背后还存在其他过失行为人的过失,如监督、管理过失的情形。
并列型过失竞合中的并存型竞合以及直列型竞合会面临这样的一种境况:即便是其中一个人遵守了注意义务,其他行为人的过失行为都足以单独导致结果发生。因此,按照过失单独犯中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认定方案,这些场合,行为人都可以“即便他履行了注意义务而结果仍会被其他人引发”为由排除自己的过失责任。在并存型竞合中,所有行为人都可以不具备事实上的结果避免可能性为借口逃避责任。在直列型竞合中,只有单方向依赖于另一方履行注意义务的行为人可以此为借口,如监督、管理者。
为了防止集体不负责现象的发生,学者们提出了以下三种解决方案:第一种方案,即参考多重因果关系时因果关系的认定方法,对条件公式进行修正。当存在两个(或者若干)条件时,若假设其中任意一个条件不存在,那么结果都不会消失;但若假设所有条件均不存在,那么结果就不会出现,则这两个条件(或所有条件)都与结果具有因果关系。过失竞合时,对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应该是假设“当所有行为人都采取合乎谨慎举止时,结果能否避免”。①(27)①Vgl. Urs Kindhäuser, Strafrecht, AT, 2015, S.289 f.第二种方案,即将结果避免可能性视作因果关系问题,然后根据“合法则的最小充分条件的必要组成要素”的标准来判断。②(28)②Vgl. Ingeborg Puppe, Wider die fahrlässige Mittäterschaft, GA 2004, S. 129-146.在所有过失竞合情形中,根据因果法则,任何一个行为人的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都是结果发生的最小充分条件的必要组成部分,因此,任一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都是原因,都应当加以归责。换言之,只要过失行为对结果发生具有促进作用,创设了法所不被允许的风险,便可以肯定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存在。该方案又被称为“风险升高方案”。第三种方案,即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以此实现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归责。在多个行为人共同违反注意义务并由这种共同创设的危险造成危害结果的场合,依“部分行为全部责任”基本原则追究这类案件中所有行为人的责任。③(29)③Luis Greco, Kausalitäts-und Zurechnungsfragen bei unechten Unterlassungsdelikten, ZIS 8-9, 2011, S. 686.
但以上三种方案都经不起推敲。首先,虽然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认定也采用了条件公式,然而,在过失竞合时为什么对规范归责意义上的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认定要参考事实归因上的多重因果关系的解决思路?第一种方案并没有从法理上加以说明。其次,运用“合法则的最小充分条件的必要组成部分”理论,将“注意义务违反性”视为结果发生的原因也是存在疑问。结果避免可能性考察的是具体案件中行为人应遵守的注意规范能否发挥避免结果的功效。但上述因果关系理论只是分析了逻辑上所有对结果发生起作用的要素,落脚点并不在对行为人的归责问题。再者,过失共同正犯的方案也行不通。其一,我国刑法并未承认过失共同犯罪,作为过失共同正犯成立前提的“共同注意义务”在法律中也不存在。其二,虽然事实上存在共同过失犯罪,即各行为人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而产生相互注意的协作、相互提醒的义务的情形,但依旧可采单独过失正犯形式,按照各行为人所违反的相关注意义务定罪处罚,无须承认过失共同犯罪。此时,应当将单个行为人的注意义务界定为:自己履行结果避免义务的同时,还要提醒、协助他人履行注意义务,防止结果发生。
虽然上述三个方案都行不通,但并不意味着过失竞合时应当放弃对各个行为人的追责。具体而言,在过失竞合时单独判断每个人的结果避免可能性,必须从“其他的行为人都履行了自己的注意义务”这一规范假定出发。因为过失竞合时结果避免义务的内容是指,通过履行其支配领域内可能的贡献,以便另一个人能够利用该贡献,并由此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努力来避免结果发生。简而言之,通过在支配可能性范围内给另一个人避免结果的机会,来避免他人死亡。至于另一人是否利用了这个机会,并不影响行为人法律义务的组成。如果另外一个人没有利用其提供的机会,那么,仅仅涉及另一个人自身的法律范围和其他的风险。
不过,在直列型过失竞合如监督管理过失中,如果要求监督管理者对他人直接造成的侵害结果承担责任,还需要进行多重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首先,其中监督管理者成立过失犯需要其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规范上的关联,即遵守注意义务时危害结果可以避免。而遵守注意义务能够避免危害结果却以被监督管理者履行注意义务时能够避免结果为前提。倘若直接引起结果的被监督管理者缺乏结果避免可能性,那么,即便监督管理者履行监督、管理义务,结果仍然会发生,也不可因为一个无效的注意义务被违反而追究行为人的责任。
五、证明方法与存疑原则的贯彻
(一)假设性调查作为证明方法
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认定属于一种假设性的调查,它与说明性调查不同。例如,在“山羊毛案”中,被害人所感染的炭疽杆菌是否来自该工厂这一事实,属于事实性调查,而法律规定的预防措施能否杀死这种杆菌则属于假设性调查,二者应当加以区分。①(30)①参见[美]H.L.A. 哈特、托尼·奥诺尔:《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张绍谦、孙战国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
假设性调查通常需要诸如医疗、交通、建筑工程等领域的事故鉴定专家通过模拟实验的方式来进行。譬如火灾事故中的结果避免可能性的判断,往往要综合考虑火烟流速的专家鉴定结论、避难所需时间的实验结果、证人证言等,并对比日常生活上的经验法则得出结论。以“川治王子饭店火灾事故案”为例,专家经鉴定认为,如果被告按规定设置防火门、防火区划就可以产生30分钟的防烟效果。30分钟对于被害人转移至安全场所是否足够呢?侦查机关通过实验得出结论,从火灾通报到最后一名客人逃生避难通常只需要7分多钟的时间,但是如果考虑“旅店的大多数客人都是老人,相比壮年人缺乏行动的敏捷性,作出避难行动的决断较慢、气力较弱,而且有的客人在面临火灾时,会由于恐惧或者狼狈而需要费工夫进行避难引导”,因此,若使所有客人都转移到安全场所将花费30分钟的时间。因此,法院认定如果被告事先设置防火门、防火区划并平日进行充分的火灾通报与避难引导训练,就可以使所有被害人免于伤亡,从而肯定了结果避免可能性。②(31)②参见吕英杰:《客观归责下的监督、管理过失》,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46页。在本文开篇提及的“王某某、孙某某消防责任事故案”中,在案件调查时就应当进行一个模拟侦查实验,模拟在当时的火势下,如果行为人保留了通道的石膏挡板以及停止使用易燃材料装潢,火势是否仍会继续蔓延并造成人员伤亡。在交通事故中,如果是两车相撞,那么就需要判断两车车速多少、两车相距多少时可以发现对方、被告反应时间多少、被害人死于何种伤害等等。如果是车辆撞上行人,就需要查明:在哪一个距离范围内可以发现行人;行人的行进的速度是多少;正常人反应能力如何;在哪一个距离范围内,被告人的预防性躲避是可能的;以多大减速度的刹车,才能避免事故;以什么样的减速度的刹车过程,事故不能避免,以及此时行人存活几率为多少等问题。
(二)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
既然结果避免可能性是过失犯成立的要素之一,那么,对于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证明而言,控方只有证明到如果行为人合乎义务地行动,结果就近乎肯定会避免时,才符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继而追求行为人的过失责任。德国法院一直将结果避免可能性作为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来认定的。虽然一开始德国帝国法院在有些案件中将举证责任转移给被告,要求被告证明在合义务行为时结果近乎确定也会发生来免除自己的责任,但后来德国联邦法院坚持“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并且指出,“只有在事实审法官确信行为人的行为与刑法上的结果之间有原因关系时,他才允许判决被告人有罪;在存有疑问的案件中则必须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决”③(32)③Vgl. BGHSt. 11, 1-7.。
然而,要求控方对结果避免可能性要素的证明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引发了学者们两个方面的忧虑。其一,依该标准,被告人可以轻易地以各种介入因素为由对“结果可以避免”提出怀疑,从而逃脱刑事责任追究。其二,依该标准,绝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在有复合因素共同导致结果发生时,过失犯几乎都会变得不可罚,以至于缺乏对被害人一方的有效保护。④(33)④Vgl. Puppe, NK, Rn. 202.基于此,一些学者要求降低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证明标准,并提出了风险升高的理论。根据该理论,只要当违反注意义务的行为相较于遵守注意义务的行为,升高了结果发生的风险,那么,足以将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但实际上,这两个忧虑是多余的。
针对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会被滥用,德国联邦法院早已形成了一个一般性主张。如果只存在一个纯粹思想上的可能性,即合义务行为仍然会引起侵害结果发生,并不能够马上肯定存在一个会对法秩序带来深远影响的重大的怀疑。因果关系——和行为人罪责一样——不需要通过排除最遥远的、相反的可能性来确定。因为,对于法官内心确信而言,只要求达至人类认识能力可及的确定性即可,不需要达到观念上无可辩驳的确定性。①(34)①Vgl. BGHSt 11,1.例如,在“精神病院案”中,两名被告人是精神病院的医生L和H,他们违反规定批准一名正接受保安处分的极度危险的精神病人S外出,结果S借外出机会实施了多项性侵并杀死了两名妇女。②(35)②Vgl. BGHSt 49,1.州法院判断两被告人无罪,因为即使没有被告人的批准,精神病人仍可通过折弯窗栅栏逃出。但是,联邦法院却改判为两被告有罪,因为无事实根据的假设(精神病人可能折弯窗栅栏)不能排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换言之,结果不会避免的可能性必须基于案件中被查明的事实,增加到能够合理地怀疑那个对于定罪而言必要的、达到几近确定的结论时,被告人才能以“不存在结果避免可能性”为由为自己进行合法抗辩。
至于第二个担忧首先存在定罪逻辑倒错的问题。对行为人定罪依据的是案件中过失犯成立要素是否得以全部满足,而非纯粹以是否有处罚必要、是否有利于保护被害人这些目的性因素来确定。如果个案中的被害人存在过错或者有其他因素介入,导致行为人缺乏结果避免能力的话,那么,只要不是行为人有意使自己陷入此种境地,就不追究行为人的过失责任。因为根据刑法中的责任主义,过失结果犯的成立必须以行为人具有避免结果的能力为前提。况且,从犯罪预防角度看,一般预防在有认识的过失中确实可以发挥其抑制力,但在无认识的过失中,由于被刑罚所威吓的行为并没有被意识到;再者,由于过失犯对于一般市民而言本质上是一种机会犯,因此,最多只是使惩罚带上刑罚的色彩而已,对于改变或培养谨慎的人格构造而言,惩罚并不是有效的手段。③(36)③[日]田宫裕:《刑事法的理论与现实》,岩波书店2000年日文版,第104页。转引自李世阳:《共同过失犯罪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2页。而处罚缺乏结果避免能力的行为人,刑罚更难以发挥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功能。另外,风险升高理论只是比较了违反注意义务行为与合义务行为在引起法益侵害结果发生概率上的大小问题,仍然围绕的是“不被允许的风险创设”,而非“不被允许的风险是否在法益侵害结果中实现”。
六、结论
法学不能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建构,而毋宁是一种实践之学,法学必须向社会实践开放并为后者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为了防止结果避免可能性理论沦为我国过失犯教义学上一个纯粹的理论形象而不能付诸司法实践,本文以德国刑事判例作为借镜,对结果避免可能性判断方法展开了研究,以期为我国过失犯司法实务提供有益的借鉴。经上文分析,本文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由于结果避免可能性考察的是行为人所违反的注意规范在具体案件中的效力,因此被害人履行注意义务时结果能否避免,对行为人的过失归责来说并不重要。在行为人违反多个行政规范的场合,对被违反的注意义务的认定需借助“不被允许的风险创设”以及“注意规范的保护目的”两个规则。在对诸多合义务替代行为进行筛选时,应当遵循“最低限度的合义务行为”标准。
第二,在比照现实与想象世界中的法益侵害结果是否“同一”时,需明确这两个结果是具体时空内的不包含具体发生方式的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另外,一个未发生的后备原因在行为人履行注意义务时也会引起结果,并不能否定结果避免可能性。因构成要件上的结果被界定为“对法益的一个负面改变”,所以在过失致人重伤案件中,即便合义务替代行为也会引发一个重伤结果,但如果违反注意义务行为与合义务替代行为引起的重伤之间还存在一个重伤程度之损害差的话,也应当追究行为人的过失责任。
第三,过失竞合时,基于规范效力的维护,行为人不能以“其他违法之人也会造成法益侵害结果”为由免除自己的责任。此时,单个行为人的注意义务在于,通过实施自己所支配的领域内可能的贡献,以便另一个人能够利用该贡献,并由此通过自己和他人的努力来避免结果发生。至于其他人是否遵守注意义务,利用了该贡献并不重要。因此,判断单个行为人履行注意义务时结果能否避免,还应假设其他人也履行了注意义务。
第四,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证明需要运用假设性调查法。必要之时,对其证明还需借助特殊领域的专家意见或鉴定。对结果避免可能性的证明也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任何假想的、无事实根据的“结果不可避免”不能免除行为人的过失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