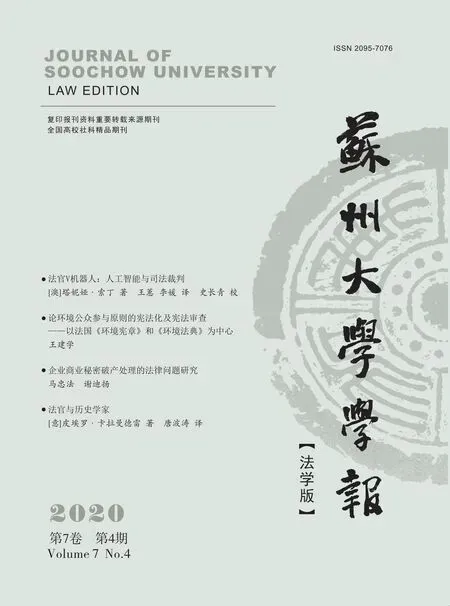论民事诉讼中事实的证明方式
曹志勋
一、问题的提出
《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民事诉讼法》第六章也以证据作为事实发现领域的核心对象。2019年底,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和扩展了约二十年前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以期通过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完善来实现民事审判中“事实认定符合客观真相”。从证据出发,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认定一般遵循“证据-间接事实-主要事实-要件事实-请求权基础”的递进过程,其中有时由于证据与主要事实之间存在直接关联,“间接事实”这一步骤可能被省略。反过来看,这就是由三段论中大前提中的找法与法律适用到小前提中的事实认定之间的涵摄过程。在裁判技术中,要件事实与请求权基础的关系原则上由实体法直接规定,以要件事实为中心的证明责任分配也相应地得到明确。①(1)①比如,参见胡学军:《证明责任制度本质重述》,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5期,第139-157页。在方法论上的检讨观点,参见吴英姿:《证明责任的程序法理》,载《南大法学》2020年第2期,第57-72页。就此而言,实体法上的法律适用与程序法上的事实认定紧密关联,无论是直接证明还是间接证明,其前提都是判断本案的要件事实以及其相应的主要事实为何,同时借此认定何者应当属于间接事实,进而需要通过一般的间接证明或者对经验法则的特别适用,得到最终的事实认定结果。
本文重点讨论的是事实认定技术中从证据到要件事实的过程,也就是事实得到证明的方式。对于法官发现相关事实的过程和结论的说明与论证,应当以大陆法系证明制度和理论上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为基础。依托于这些概念和原理,裁判中的事实说理也才获得了充实的方法论指引与得以证成的理论素材。①(2)①参见曹志勋:《对民事判决书结构与说理的重塑》,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4期,第243页。换个角度看,如果对上述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不够充分,也许法官本人仍然可以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并且因此成功调解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甚至不乏偶然地认定与客观事实一致的案件事实,但是却难以通过有效充分的说理,让当事人或者社会公众信服裁判结果。
二、直接证明与间接证明的差异性
(一)两大法系共享的分析框架
1.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理论区分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与之对应的即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②(3)②在德语中,证明和证据都对应Beweis一词,本文将区别语境加以使用。证明方式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事实证明过程的不同。直接证明即不需要通过任何中介就能证明某一要件事实存在或不存在,这可以由本证方或反证方完成,也可能分别适用证明或疏明标准;间接证明则涉及那些并不直接与法律构成要件相关的事实主张,但是可以结合其他事实,证成要件事实是否存在。在间接证明中还有证据辅助事实,涉及证据方法的合法性和证明力。相应地,直接证明对应的证明对象是案件事实中的主要事实(Haupttatsache,erhebliche Tatsache),而间接证明对应的是间接事实(Indiz,Indizientatsachen,Anzeichen)。③(4)③BGHZ 53, 245=NJW 1970, 946, 950 (不过其对辅助事实的定义已被学界通说改变);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Zivilprozessrecht, 18. Aufl., 2018, §§ 111 Rn. 15 f., 112 Rn. 7 ff. 日本法上的相同观点:新堂幸司『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9年),580頁;参见[日]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张卫平、许可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83页。类似介绍,参见许可:《民事审判方法:要件事实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0页。
举例而言,亲眼见证了甲砍伤乙过程的证人及其证言,属于直接证明;虽然证人没有完全见证,但是如果他看到了甲用刀威胁乙,而这把刀正是事后沾满乙的鲜血并留有甲手印的凶器,那么就属于能够推导出要件事实的间接证明;如果被告能够举证证人不可信并且事发时其实证人在他处,那么就属于辅助事实。④(5)④Baumgärtel/Laumen, Handbuch der Beweislast: Grundlagen, 4. Aufl., 2019, Kap. 2 Rn. 20 ff.
2.英美法系
从美国的情况看,理论和实践中也广泛承认直接证据(direct evidence)与间接证据/情势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的区分。⑤(6)⑤Christopher B. Mueller, Laird C. Kirkpatrick & Liesa L. Richter, Evidence, NY: Wolters Kluwer, 2018, pp. 161-162; Kenneth S. Broun et al., McCormick on Evidence, St. Paul, MN: Thomas/West, 2006, p. 308. 国内相关讨论,亦见陈瑞华:《比较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30页。美国民事诉讼领域的权威评注指出,直接证据是能够证明主要事实(consequential fact)、并且满足以下标准的证言,即证人对主要事实有准确的感知并且能够正确回忆,同时使用通常的语言诚实地表达出来。⑥(7)⑥22 Wright & Miller, Fed. Prac. & Proc. Evid., § 5162.1 (2020, westlaw).也有英美学者将大陆法系理论中的辅助证据称为间接相关证据(indirectly relevant evidence),而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则一同被概括为直接相关证据。⑦(8)⑦Terence Anderson, David Schum & William Twining, Analysis of Evid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62-63, 76-77.
在美国现行法上,判断证据是否具有相关性需要考虑实质性(materiality)和证明力(probative value, sufficiency, weight)两个因素(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1条),其中前者针对的是证据的证明主题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后者则指其对事实主张的成立所能起到的作用。⑧(9)⑧在英国也采取同样的思路。虽然在法官和陪审团的分工中,证明力属于事实问题而可采性属于法律问题,但是可采性/排除规则也要求证据必须具有最低限度的证明力(sufficient weight)。 Hodge M. Malek, Jonathan Auburn & Roderick Bagshaw, Phipson on Evidence, London: Sweet & Maxwell Ltd, 2010, para. 7.07, 7.17; Colin Tapper, Cross & Tapper on Evi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79.直接证据即被采信时能够直接证明主要事实的证据,而间接证据即使被采信,也必须配合其他证据才能证明主要事实。间接证据通常更为常见,而且证明与人相关的内部事实也只能依赖间接证据。①(10)①例如:U.S. v. Caraway, 534 F.3d 1290, 1301(10th Cir.2008)[书架上藏有制作爆炸物的恐怖活动书籍,可以推定他已经看过了,并且该证据不会导致不适当偏见(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403条)因而具有相关性].无论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都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②(11)②Holland v. U.S., 348 U.S. 121, 139-140 (1954).甚至间接证据链条能够更准确地满足说服责任的要求。③(12)③Desert Palace, Inc. v. Costa, 539 U.S. 90, 100 (2003).
与此相关但不同的是所谓可靠性或鉴真程序(authentication),④(13)④See Anderson, Schum & Twining, Analysis of Evidence, at 60, 63-64. 国内讨论,亦见陈瑞华:《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127-141页;牟绿叶:《论实物证据的鉴真与鉴定》,载《中国司法鉴定》2012年第3期,第25-30页(对要件事实和辅助事实采取了与本文不同的定义)。其针对的是证人证言是否可信、传闻证据和证据保存链条问题,比如监控录像记录的抢劫过程是否真实完整、证人在庭审之外做出的证言笔录或者被认为是凶器的刀是否就是法庭上作为证物出示的刀。上述内容不是相关性标准需要审查的对象,也不影响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
(二)区分不同证明方式的标准
判断某一案件事实对应主要事实还是间接事实的依据在于其所对应的法律构成要件,因此同一事实在不同的请求权基础下可能具有不同的属性。⑤(14)⑤相关讨论,参见曹志勋:《请求权基础对民事程序法适用的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8月5日,第4版。相应地,判断某一证据属于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也取决于证据与待证的主要事实的关系。比如,在确认合同法律关系存在时,对应要约与承诺的事实都属于主要事实;但在基于合同不履行请求损害赔偿时,合同成立且生效则成为主要事实,对应要约与承诺的事实则属于推论要件事实的间接事实。⑥(15)⑥Engisch, Einführung in das juristische Denken, 10. Aufl., 2005, S. 58 f. (以刑法上的投毒罪和买卖毒药的合同为例,后者为推导投毒行为的间接事实)对于同样的款项是否交付的事实,也可能存在多种不同认识。在买方请求卖方履行买卖合同项下移转所有权及交付义务时,金钱交付构成买方给付义务的完成,属于对待给付义务履行的要件之一,即在个案中表现为主要事实;在确认合同是否成立、当事人是否伪造若干年前签订的借款合同的纠纷中,声称借款人是否有能力及是否实际交付涉争金钱,则属于证明双方是否达成真实合意的间接事实;⑦(16)⑦这种情况的例示,参见赵某诉项某、何某民间借贷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12期。在确认借款合同是否成立时,金钱交付此时属于对应合同特别成立要件的主要事实(《民法典》第679条)。就此而言,程序法上的证明方式也直接受到实体法规则的影响。
三、不确定法律概念中的待证事实
(一)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法律定性
在涉及确定的法律概念(比如年龄)或者包含了法律概念和判断的事实主张(比如买卖)时,如上要件事实的确定相对明确。但是在涉及不确定法律概念⑧(17)⑧当然,法律概念的确定与不确定都是相对而言的,本文就此仅讨论思路和方法问题,而无力确定识别是否确定的标准。这方面的讨论,例见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第14-18页。德国法上概念定义的讨论,参见卢佩:《德国关于不确定法律概念之第三审级司法审查》,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6期,第147-149页。或一般条款时,比如欺诈、违反诚信原则、过错、善良风俗、可期待性、权利滥用以及重大事由等,由于其高度抽象性,答案似乎就不那么明确。除了这些显然的抽象法律概念之外,其他很多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确定。比如,在野生动物园里老虎咬人的事故中,暂且不考虑诉讼标的选择问题,动物园是否尽到管理职责(《民法典》第1248条后1分句)的认定就是法律与事实共同影响的结果,可能分别对应是否设置足够安全措施(比如防止逃票进场的围墙)、施救是否及时得当等不同角度的客观事实。易言之,法律概念的抽象与否更多是程度问题,法律要件与案件事实之间常常存在解释与具体化的空间。上述问题在其他部门法中也非常重要。民事实体法有必要经由个案中价值判断的具体化得以适用,①(18)①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案例研习: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2019年自版,第237-240页。刑法上对规范性和描述性法律概念涉及相似问题,也有相对充分的讨论。②(19)②参见张明楷:《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6期,第76-93页。
而在民事诉讼法学领域中,这里如果继续借鉴德国通行的法理和诉讼原理,则应当回到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区分上。③(20)③对这一区分的国内基础性研究,参见陈杭平:《论“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2期,第322-336页;张卫平:《民事诉讼法律审的功能及构造》,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5期,第43页;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第88-89页。在德国法上,作为第三审的审查对象的法律问题(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546条),不仅包括法律行为的解释、证明评价、思想法则和经验法则以及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当然也包括对法律规范中法律概念的理解和适用。在德国,争议主要存在于不确定法律概念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成为法律第三审的审查对象。通说认为,事实审法官在涵摄不确定法律概念及案件事实时享有评价的自由空间(Beurteilungsspielraum),第三审法院只能审查事实审法院对法律概念的理解是否正确,是否考虑了所有相关情况以及思想法则和经验法则。④(21)④比如:BGHZ 160, 354=NJW 2004, 3413, 3415.笔者的初步结论是,原则上三审法院能够审查上述问题,因为大多数法律概念在不确定性上只存在量的差异,不确定法律概念同样需要经过法规范解释和涵摄的过程,任何个案也都可以作为未来案例比较和区别的基础。限制三审审查权的原因不应在于控制上告审的许可条件(目的性上告限制说)(teleologische Revisionsmethode),而更应当是三审法院自身对事实发现的有限权限(基于权能的上告限制说)(Leistungsmethode)。⑤(22)⑤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 143 Rn. 27 ff.; Stein/Jonas/Jacobs, ZPO, 22. Aufl., 2013, § 546 Rn. 8, 27; Wieczorek/Schütze/Prütting, ZPO, 3. Aufl., 2005, § 546 Rn. 15, 37 f.; Prütting, Die Zulassung der Revision, 1977, S. 191 ff.; Gottwald, Die Revisionsinstanz als Tatsacheninstanz, 1975, S. 138 ff., 160 ff., 184. 国内详细介绍,参见卢佩:《德国第三审程序审查范围研究》,北京大学2013年博士论文,第139-153页(整体持与本文不同的目的性上告限制说的观点)。
(二)法律解释与要件事实的确定
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身属于法律问题⑥(23)⑥参见段文波:《规范出发型民事判决构造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71、91页。或者说评价性要件⑦(24)⑦参见许可:《民事审判方法:要件事实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9页。亦见纪格非:《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1期,第97页。,无法承担衔接抽象的请求权基础与具体的案件事实的重任,不宜直接成为要件事实。法学方法论上小前提中的案件事实与大前提的实体法律规范之间,需要比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程度更高的事实主张作为中介。比如就德国法上的过失而言,过失这一概念本身并不是要件事实,而只有足以认定过失存在的、构成注意义务违反的具体行为才是要件事实,并且原则上由主张权利方承担证明责任。⑧(25)⑧Baumgärtel/Repgen, Handbuch der Beweislast: §§ 1-811 BGB, 4. Aufl., 2019, § 276 Rn. 1, 5; Baumgärtel/Katzenmeier, Handbuch der Beweislast: §§ 812-2385 BGB, 4. Aufl., 2019, § 823 I Rn. 40 ff.; Balzer/Walther, Beweisaufnahme und Beweiswürdigung im Zivilprozess, 4. Aufl., 2018, Rn. 13.在确定要件事实之后,才存在通过表见证明减轻证明责任的问题,以便将内在的注意转换为外在的、对注意义务的违反。⑨(26)⑨Baumgärtel/Repgen, a.a.O. (§§ 1-811 BGB), § 276 Rn. 12 ff.再比如,在判定是否构成欺诈(德国《民法典》第123条第1款前一种情形)时,德国仍然以具体构成欺诈的积极行为和不披露必须披露事实的消极不作为作为(客观方面的)要件事实,⑩(27)⑩BGH NJW 2001, 64, 65; Baumgärtel/Kessen, a.a.O. (§§ 1-811 BGB), § 123 Rn. 3 ff. 国内研究,参见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52-253页。在涉及雇佣合同中的重大事由(德国《民法典》第626条第1款)时,重大事由本身同样属于法律概念,而那些满足重大事由的事实才是要件事实。(28)BGH NJW 1993, 463, 464 (本案中上诉法院错误地理解了重大事由的概念); Palandt/Weidenkaff, BGB, 79. Aufl., 2020, § 626 Rn. 38.与此相对,民法上的错误则不被视为不确定法律概念,本证方需要主张和证明的对象就是错误这个事实本身。(29)OLG Brandenburg NJW-RR 2002, 578, 580; Palandt/Ellenberger, a.a.O., § 119 Rn. 32; MüKoBGB/Armbrüster, 8. Aufl., 2018, § 119 Rn. 149; Baumgärtel/Kessen, a.a.O. (§§ 1-811 BGB), § 119 Rn. 1 f.在我国法上,除了前述同时也被我国法继受的民法概念外,也有许多典型示例可供参考。比如,作为离婚要件的“感情确已破裂”就属于上述抽象法律概念,而《民法典》第1079条第3款规定的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以及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诸事实,则属于辩论主义上的要件事实。
当然,将抽象法律概念具体化的新的要件事实,也只是降低了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抽象程度,本身仍然是相对抽象的。之所以要尽可能提高要件事实的具体化程度,是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学说上主要继受的是日本,日本就辩论主义的经典理论认为,只有当事人就要件事实作出的事实主张才具有约束法院的效果,而如后详述的间接证明的过程通常被认为属于法官的自由心证的范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86条第1款第1句),不在辩论主义下(如自认问题上)约束法官。①(30)①新堂幸司『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9年),472、587頁;伊藤眞『民事訴訟法』(有斐閣,2016年),305頁;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1-153页。对比来看,在德国法上,当事人就间接事实也可以自认;在主张责任与证明责任的问题中,主要事实和间接事实也都能够成为讨论证明的必要的对象。比如在德国法上,只有在个案中假设司机保持清醒时本来能避免事故发生的情况下,酒后驾车才能作为认定本案司机过错的表见证据,即满足高度盖然性的经验法则。②(31)②BGHZ 18, 311=NJW 1956, 21, 23; BGH NJW 1987, 1826, 1827 (扩展到自行车手); NJW 1976, 897 (酒后躺在马路上的行人); Stein/Jonas/Thole, ZPO, 23. Aufl., 2018, § 286 Rn. 232; Schneider, Beweis und Beweiswürdigung, 5. Aufl., 1994, Rn. 421 ff.此时,酒后驾车的因素被认定为间接事实,而非主要事实。但是,对于当事人仅就酒后驾车辩论、法官最后却以东张西望为理由认定满足过失的要求,从日本法出发,则可以认为这种转换将构成裁判突袭,并且有损当事人的程序保障。③(32)③参见许可:《民事审判方法:要件事实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3-34页。
笔者认为,直接将酒后驾车这样更为具体的事实直接上升到主要事实的层次,在前述经典理论的意义上,固然能够解决突袭性裁判的问题。但是,这并非就是说,“自古华山一条道”,而更可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除了将主要事实抑或间接事实的定性问题与对法院审判权的约束直接挂钩的做法之外,理论和技术上完全可以从法官是否行使释明权的角度加以判断。在前述酒后驾车还是东张西望的问题上,即便暂且不问其定性如何,法官也本就应当通过发问和解释引导当事人发表意见和辩论。特别是,酒后驾车并不当然等同于当事人有过失,仍有双方进一步解明案件事实的必要。如前所述,司机如果保持清醒也无法避免事故发生,比如受害人突然从树丛中窜出,就并不违反注意义务。就此而言,在日本也有观点试图挑战上述辩论主义中的经典理论。当不涉及前述抽象法律概念,而是关注在个案中具有关联性、构成当事人真正争点的间接事实时,如果将其扩大视为辩论主义的适用对象,确实有助于避免法官对当事人施加突袭性裁判。④(33)④三木浩一=笠井正俊=垣内秀介=菱田雄郷『民事訴訟法』(有斐閣,2018年),209-213頁;松本博之=上野泰男『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5年),50-51頁。不扩大辩论主义适用范围的观点同样注意到此时扩大释明权范围的必要性。伊藤眞『民事訴訟法』(有斐閣,2016年),306頁。就此而言,应当有意识区分传统以主要事实为核心的辩论主义下主要事实和间接事实的区分问题与应否将辩论主义的适用对象或者说界限扩大到重要的间接事实上的问题,前者仍然在日本法中原有的基本学理框架之下,后者则已经提出了对辩论主义原理本身的重新定义。⑤(34)⑤新堂幸司『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9年),472-480頁参照。王亚新教授已经对日本法的情况作了充分讨论,参见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6-91页。对日本学说的详细整理,亦见段文波:《我国民事自认的非约束性及其修正》,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110-113页。
四、直接证明方式的对象与必要
(一)直接证明对应主要事实
1.程序法上要件事实与主要事实概念
没有争议的是,待证事实应当是客观发生了的、具体的个案事实。但是,在民事诉讼学理中如何为其“贴标签”,如何理解几个相似的证据法概念,则存在一定争议。固然我们需要十分警惕“就概念论概念”的抽象论辩,但是如果概念使用可能妨碍对问题的准确说明,就至少有必要意识到差异的存在,进而发掘不同概念选择背后不同的(应然)考量。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一种有力观点认为,案件事实中的主要事实,就是“要件事实”,或者说要件事实被认为就是对应法律构成要件的案件事实。①(35)①参见王雷:《民法证据规范论》,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84页;王亚新:《诉讼程序中的实体形成》,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6期,第148页(但同时指出要件事实与主要事实、直接事实的含义相同:同上揭,第150页);段文波:《规范出发型民事判决构造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8-72页;许可:《民事审判方法:要件事实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3页。主张加以区分的观点,比如,参见包冰锋:《民事诉讼间接证明的机理证成与模型应用》,载《法律科学》2020年第5期,第179-180页。这种理解最主要的支持是,“要件事实”概念在词源上来自日本,而日本民事司法研修所就持前述理解,该机构由于负责培训法官,对于日本实务的影响非常大。针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解释》)中出现的“基本事实”,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也分别使用不同的术语,既可能是“要件事实”,②(36)②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17页。又可能是“主要事实”,③(37)③参见沈德咏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884页。折射出概念使用在我国讨论中的不确定性。
在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论述中,也同样出现这种概念使用上的不统一。既有学者将法律要件事实与主要事实等同的做法,④(38)④参见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中册,台北三民书局2014年版,第107-108页(“主要法律要件事实”)。亦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案例研习: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2019年自版,第106页。又有将两个概念混用的情况。后者比如邱联恭教授有时区分要件事实和主要事实,并且将前者理解为该当于权利的法律事实或实体法的内容(区别于具体事实⑤(39)⑤比如,参见邱联恭讲述、许士宦整理:《口述民事诉讼法讲义(一)》,2017年版,第24页。),而主要事实则为间接事实所推认的事实。⑥(40)⑥参见邱联恭:《司法之现代化与程序法》,台北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144和146页。在邱教授著作的具体行文中,又曾出现过将要件事实和主要事实等同作为具体事实的表述。⑦(41)⑦比如,参见邱联恭:《争点整理方法论》,台北三民书局2001年版,第400页。还有学者不同时采用要件事实和主要事实这两个概念,但是区分这两种不同含义,比如,直接称为“要件”(如买卖合意作为合同成立要件)和“直接相当于该要件之具体事实”(如买受土地所有权及支付价金的生活事实),⑧(42)⑧陈计男:《民事诉讼法论(上)》,台北三民书局2007年版,第463页脚注19。或者改称“构成要件事实”(实体法规范)和“以构成要件所指涉的事实”(社会事实)的一组概念。⑨(43)⑨吕太郎:《民事诉讼法》,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33页。在日本法上也可以看到这种分歧的痕迹。比如,虽然德国法上证明责任分配的对象应当被直译为“法律事实构成要件的特征”(Tatbestandsmerkmal),⑩(44)⑩MüKoZPO/Prütting, 5. Aufl., 2016, § 286 Rn. 110 ff.;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 116 Rn. 7 ff.但是日本学者理解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就可能分别被认为是对“法律要件要素”(45)松本博之=上野泰男『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5年),448-449頁。或者“要件事实”(46)新堂幸司『新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9年),473、605頁。新堂教授的著作中区分要件事实和主要事实概念。分配证明责任的学说。
笔者认为,有必要区分作为法律规范抽象内容的要件事实和属于具体案件事实的主要事实,即将要件事实概念与法律构成要件要素概念等量齐观,(47)类似做法,比如,参见〔德〕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并且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中区分使用要件事实与主要事实。从定义即可看出,要件事实和主要事实指向的内容不同,主要事实只是能够满足法律构成要件具体内容/要件事实的所有事实可能中的一个个例,因此在法学方法论上需要两个独立的概念来分别指代。在承认概念有区分必要的基础上,究竟用哪个名词来指代这一组概念,确实有讨论的空间。在德国法的一般理论上,法律事实构成要件(Tatbestand)(48)概念讨论,参见曹志勋:《论案件事实认定说理的不同维度——以彭宇案一审判决书为例》,载《北方法学》2020年第3期,第91-92页。是多个事实要件的集合,我们固然可以将这些事实要件直译为法律要件要素、①(49)①松本博之=上野泰男『民事訴訟法』(弘文堂,2015年),425頁。事实构成要素、②(50)②[德]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金振豹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3-51、140-141页。构成要件因素/要素(Element)③(51)③[奥]恩斯特·A·克莱默:《法律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6-37页。或者特征(Merkmal),④(52)④[德]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2-154页。也许也可以粗略称为“事实构成要件”⑤(53)⑤[德]罗森贝克、施瓦布、戈特瓦尔德:《德国民事诉讼法》,李大雪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850页。或者“要件”⑥(54)⑥邹碧华:《要件审判九步法》,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50-154页。,这当然也能够符合法学方法论上讨论的基本要求。
那么,应否认为,既然比如构成要件要素的译法已经能够完成直译的功能,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使用“要件事实”这一概念来翻译呢?⑦(55)⑦相关主张,参见胡学军:《在“生活事实”与“法律要件”之间:证明责任分配对象的误识与回归》,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2期,第248、251页及脚注33;曹云吉:《第一届紫荆民事诉讼青年沙龙实录》,载张卫平主编:《民事诉讼法研讨(一)》,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38-39页(任重教授的发言书面整理稿)。笔者认为,在准确的基础上,还要考虑概念本身能发挥的指向性功能。从追求实效的功能主义比较法研究和使用来看,还应该追问概念使用背后的原理和客观上更正确的答案。⑧(56)⑧参见傅郁林:《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6期,第1442页。构成要件要素这一类的翻译结果,只能突出其实体法规范的一面,而无法如“事实要件”这般,同时强调其与事实认定的相关性和作为法律适用要件的属性。“(事实)要件”与“要件事实”又只是语序不同,两者应当对应同一内容,否则极易引发误读。因此,要件事实概念更宜指代抽象规范对事实的要求。
同时,在民事诉讼法上,德国法和日本法上也都有主要事实(Haupttatsache)和与之类似的重要事实(erhebliche Tatsache)的概念,特别是由于日本民事诉讼法学教科书的翻译使用,主要事实概念在我国学界也已经得到了广泛使用,本身构成了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继受的一部分。⑨(57)⑨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40-241页。如果能够坚持要件事实与主要事实在术语中的区别使用,似乎也可以在民事诉讼法学中将法律适用三段论⑩(58)⑩囿于主题,这里并未讨论的是与本文相似、在法条理论下挑战传统三段论认识的观点,参见黄泽敏:《案件事实的归属论证》,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5期,第76-77页。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明确区分。易言之,在民事诉讼法学既有术语中,对于小前提也已经有主要事实这一对应表达,如果要件事实概念再指代相同内容,也令人有叠床架屋之感。
2.民法上民事法律事实概念的双重性
此外,民法上也有(民事)法律事实概念,即作为法律规范中法律后果的前提条件或者依法导致权利变动的事实。这一概念的作用在于建构民法概念体系并解释法律规范的具体构成,(59)Bork,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s, 3. Aufl., 2011, Rn. 273;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Das Rechtsgeschäft, 4. Aufl., 1992, S. 104 ff. 中文相关讨论,比如,参见常鹏翱:《法律事实的意义辨析》,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3-23页。其对应(本文认识中的)诉讼法上、抽象的要件事实,而区别于个案中的案件事实。(60)不同观点,参见许可:《民事审判方法:要件事实引论》,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0-31和38-43页。更常见的情况是,学者论述中使用的法律事实可能同时覆盖具体事实和法律事实构成(要件),比如,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 33-35页(魏振瀛执笔);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0-41页。比如,法律人就民法案例题说“甲乙之间的合同属于法律行为”、“丙先占无主物属于事实行为”,只不过是说甲乙之间的合同或丙事实上实施的先占行为是满足法律构成要件的一个事例。我们说法律行为是当事人之间私人自治以及具体意思的产物,强调的也只是其个例的特点。同样在这个意义上,说甲乙之间就土地所有权转让达成物权合意,也即主张甲乙之间达成的物权契约是所有权转让的构成要件要素的一个事例。在上述语境下的民法讨论中,我们通常不考虑诉讼法上的问题。至于其指向的具体行为是否确实存在,则仍需回到民事诉讼法的语境下,经由当事人自认或通过证据证明而得到答案。(61)就此从不同方向的理解,参见常鹏翱:《论现实存在与物权行为的无关联性》,载《法学》2015年第1期,第106-107页。
就这一概念的使用还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当前主流的民法教科书已经不再强调法律事实概念,但是从相关对法律行为以及其与准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区分仍然可以看出,他们均认为上述三者都可以导致权利变动,只不过原因和适用规则不同。①(62)①Larenz/Neuner,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11. Aufl., 2016, § 28 Rn. 1 ff.;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10. Aufl., 2010, Rn. 174 f., 184 ff.这种有意的无视可能与对抽象概念的扬弃有关,比如近年来,在欧洲法层面使用法律行为概念的做法都遭受广泛质疑。②(63)②Jansen/Zimmermann, Vertragsschluss und Irrtum im europäischen Vertragsrecht, AcP 210 (2010), 196, 202 ff.; Zweigert/Kötz,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vergleichung, 3. Aufl., 1996, S. 145. 但是这显然并不影响本文对概念本身的辨析,因为本文的目的在于寻求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在各个层面的联系。
(二)应当承认直接证明方式
1.证明理论上的争议
基于上述对主要事实的认识,笔者认为,民事诉讼法学③(64)③我国刑事诉讼法学中同样存在直接证明和间接证明的区分。比如,褚福民教授就将其称为验证模式和体系模式,参见褚福民:《刑事证明的两种模式》,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第93-103页。传统上对“直接证明/间接证明”的划分应当继续得到承认。从理论上看,无论前述外部事实还是内部事实都可能被直接证明。只不过,由于实践中反证方不太可能主动提供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如当事人陈述),通常也不存在能够直接证明欺诈目的的传来证据(如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对于主观意思的证明基本上只能依靠间接证据,④(65)④Baumgärtel/Laumen, a.a.O. (Grundlagen), Kap. 18 Rn. 5 ff.比如欺诈、恶意串通或者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要件。⑤(66)⑤基于解释论对我国法的有力讨论,参见吴泽勇:《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4期,第156-161页。而比如前述持刀伤人或者高空抛物的外部事实则完全可以得到直接证明,最典型的莫过于第三方提供的监控视频。对此,也有德国学者主张即使前述直接证明事发经过的证人证据也不属于直接证据,因为其认为此时也需要经过推论⑥(67)⑥Engisch, a.a.O., S. 59.或者甚至认为所有证据都是间接证据⑦(68)⑦Bender/Nack/Treuer, Tatsachenfeststellung vor Gericht, 3. Aufl., 2007, Rn. 577 f.,进而质疑传统上区分直接证明与间接证明的意义。
在我国,纪格非教授的观点具有代表性,她依托英美晚近的研究成果,认为所有证据都是间接证据,并试图论证直接证据在事实上并不存在。⑧(69)⑧参见纪格非:《“直接证据”真的存在吗?——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分类标准的再思考》,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第594-606页;纪格非:《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划分标准的反思与重构》,载《法学论坛》2013年第1期,第92-98页。不过除了下文的分析之外还需要明确的是,本文与纪格非教授在概念使用上有一些不同。比如,直接证据对应的待证事实只是某个要件事实而非全部法律构成要件,这样仅否定因果关系没有直接证据,并不能推出直接证据不存在。此外,对于纪格非教授提出的直接证据的证明体现的是演绎推理还是归纳推理的问题,笔者尚没有能力梳理英美法系不同学说的异同,特别是新证据学出现之后的诸多高深理论和新颖方法,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很难得到非黑即白式的答案。与此不同,李浩教授则旗帜鲜明地主张,判断、检验是否存在直接证据的标准和依据在于是否存在可以直接证明主要事实的证据,而不应采取纪格非教授提出的直接且单独的双重分类标准。⑨(70)⑨参见李浩:《“直接证据”真的不存在吗?》,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1期,第212-229页。
就此而言,笔者支持李浩教授的观点。纪格非教授的挑战观点虽然进一步明确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之间的界限,但是尚未能推翻大陆法系证据理论的通说。首先,法官可以通过勘验的方式直接查明比如损害是否发生(比如车辆的损毁情况),这时勘验对应的就是直接证据。当然勘验的结果本身也只是法官的事实判断,⑩(71)⑩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 112 Rn. 6.但是如果非要将其视为“间接”证据就只具有概念上的形式意义而已。其次,虽然如前所述,勘验以外的证明方法都属于事实判断而非法官直接感知的对象,(72)Stein/Jonas/Thole, a.a.O., § 284 Rn. 11; Baumgärtel/Laumen, a.a.O. (Grundlagen), Kap. 18 Rn. 1 & Fn. 5; Schneider, a.a.O., Rn. 373 f. 在美国则有观点认为此时该证据同时构成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比如证人作证证明当天下雨了,但严格来说他只是从听到打雷、看到闪电以及行人打伞做出了推断。22 Wright & Miller, Fed. Prac. & Proc. Evid., § 5162.1 (2020, westlaw). 张卫平教授同样强调证据的陈述/判断属性,参见张卫平:《事实探知:绝对化倾向及其消解》,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74页。但是在诉讼法的传统概念使用中,同时也与待证事实构成间接关系的证明方法才能称为间接证据(双重的间接关系)。相应地,主要事实也可以是需要法官推论的事实判断。再次,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反证方也可能提供不利于己的直接证据。比如在涉及责任保险时,由于实际侵权人与作为第三人的保险公司的利益不同,在侵权人作为当事人陈述案情时,可能直接承认原告受害人承担证明责任的主要事实(比如过错)。再比如,在实践中也可能出现侵权人自认侵权事实、但是对损害数额存在争议的情况,同样佐证了直接证据的可能性。总之,当我们看到北京大学未名湖平静的水面上飞来两只黑天鹅时,就足以推翻“天鹅都是白色的”的论断了。
2.直接证明的证明力
在仅需要考虑直接证明时,法律人面对的问题相对简单。由于直接证据对应案件的主要事实,本证方只需认定证据的证据能力/可采性,进一步是否完成主观证明责任的要求则取决于对直接证据证明力大小的判断。就此而言,2001年《证据规定》第77条第4项曾经指出,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认为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而2019年《证据规定》已经删除了该规则。虽然原有条文中使用了“一般大于”的谨慎表达,但是确实向司法实务传达了错误信号,认为在否定具体案件中直接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时,需要特别的理由与论证。这确实会妨碍法官基于个案情况形成心证的自由。
实际上,被定义为直接证据的证据仅仅表明其与待证事实有直接对应、无需中转的关系,但是并未包含这种关系的可能性大小。即使不是诸如记载了自然人的出生时间和死亡时间的出生证明和死亡证明(《民法典》第15条)①(73)①这是我国实体法上的特别规则,而通常而言,报道性公文书不应当被推定具有实质证明力。参见曹志勋:《论公文书实质证明力推定规则的限缩》,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第149-150页。和能够证明合同内容的公证合同书(《民事诉讼法》第69条)这样应当被推定内容为真的证据,比如能够提供诊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原因力大小的、法院指定的医疗损害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第2项)这样的证据,也确实具有较高的证明力。但是,直接证据中也包括比如证人证言这样需要具体审查的证据,很难泛泛地说其就具有较强的证明力。就此而言,2019年《证据规定》第96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审查证人的智力状况、品德、知识、经验、法律意识和专业技能等因素。其中,能够经由其他间接证据佐证的证人证言,可能的确更为可靠。②(74)②德国法的类似主张:Balzer/Walther, a.a.O., Rn. 341.
五、间接证明方式的类型与内容
(一)间接证明的三种类型
与前述直接证明不同,当事人在司法实践中提出的多属于间接事实主张和间接证据。于是,在证据到待证的主要事实之间就会存在一个或长或短的中间阶段,即间接证据-间接事实-主要事实。③(75)③反对观点,参见纪格非:《“直接证据”真的存在吗?——对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分类标准的再思考》,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第600页。在本文语境下,间接证明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运用具有较高盖然性经验法则的表见证明,适用的经验法则虽然盖然性达不到前述较高的程度、但是在适用同时能够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弱化表见证明,④(76)④详细讨论,参见曹志勋:《经验法则适用的两类模式》,载《法学家》2019年第5期,第33-44页。以及通过完善证据链条达到证明效果的、一般的间接证明。为了避免贸然使用源自外国法的“表见证明”概念可能造成的交流困扰,本文将前两种分别称为经验法则适用的常规模式和弱化模式,其证明的核心在于经验法则的运用以及对其他案件事实可能性的排除。而在第三类间接证明中,证明的焦点则在于如何通过间接证据链条的形成,使法官对主要事实形成临时心证,这当然也会造成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
(二)三种类型的区分原因
在笔者看来,承认经验法则适用的两种模式与一般的间接证明的区别,而不是将直接证明之外的所有证明过程笼统称为间接证明,主要考虑的是审理技术和裁判技术上的差异。至于在概念上究竟是强调表见证明与间接证明之间泾渭分明,还是认为表见证明只是间接证明的一种特殊类型,更多只是表达偏好问题,而并不会掩盖两者之间的差异。
1.审理技术
一方面,此时应当关注审理技术上的区别。首先,两种经验法则适用模式在诉讼过程中的攻防焦点之一在于经验法则盖然性的高低问题(另外两点则是直接攻击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的存在),而对于一般的间接证明来说,攻防焦点则在于是否形成了证据链条。前者其实是一个脱离个案案情、具有一般抽象性的判断(是否多数情况下均会出现推定事实),后者则是对个案案情的具体证明与认定。
其次,与此相对,法官在经验法则适用模式中,应当就可能适用的经验法则的盖然性程度,在释明之后给予当事人发表意见的机会,将经验法则作为案件的争点和庭审中心证开示的对象。而在一般的间接证明模式下,虽然此时也必然存在盖然性不高的经验法则,但是在此基础上的司法推断并不将具体的特定经验法则作为待证事实,而是关注其对法官心证的整体影响。
再次,在经验法则适用模式中,法官有必要根据经验法则盖然性的高低,确定究竟应当由反证方还是本证方承担排除其他可能性的负担,也即仅凭经验法则能否使本证方满足举证的必要,使法官形成事实存在的临时心证。这里具体的主观证明责任的转移与否,体现了两种经验法则对当事人举证策略的直接影响。在经典表见证明模式下,一个间接证据与高盖然性经验法则的组合,将直接使反证方承担举证的必要,至少要将法官就该事实主张形成的心证推回到真伪不明状态。如果本证方认为自己仅提出盖然性不够高的经验法则,则应当马上意识到,自己仍应进一步列举具有现实性的、不同于经验法则推论事实的可能性,进而说服法官认同这些可能性在本案中均不存在。而在一般的间接证明中,本证方从正面来看应当举出能够构成证据链条的多个间接证据,从反面来看也应当使证据链条达到排除其他可能性的效果。
由此可见,弱化模式的经验法则适用确实处于常规模式的经验法则适用与一般的间接证明之间,既体现出经验法则在诉讼过程中相对突出的地位,又强调与一般的间接证明相同的、排除其他可能性才能使法官确信的证明度要求。从这个角度看,笔者也能够理解仅区分强经验法则的适用与一般的间接证明的理论看法。德国主流观点就倾向于认为,弱化的经验法则适用模式应当直接作为间接证明来理解,经验法则适用仅有常规模式一种可能。①(77)①Baumgärtel/Laumen, a.a.O. (Grundlagen), Kap. 17 Rn. 27, 19 Rn. 57. 国内讨论,参见周翠:《从事实推定走向表见证明》,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6期,第111-113页。
2.裁判技术
另一方面,裁判技术需要与上述审理技术相配合,完成法律对裁判说理的要求。首先,在经验法则适用模式中,法官在裁判说理中应当明确提及自己适用的经验法则和其认为经验法则盖然性的大小,以便当事人、代理人、上级法院以及将来阅读裁判的公众与学者能够明确案件中事实说理的落脚点。而在一般的间接证明中,所适用的经验法则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存在间接证据链条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的问题,但是这一经验法则的盖然性则并非裁判说理的核心内容。
其次,经验法则的适用毕竟以脱离个案、抽象的盖然性为基础,即使某条经验法则的盖然性一般而言能够达到很有可能的高度,仍然令人心生不安,担心涉争个案恰恰属于少数的例外情形,从而在事实上导致错案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表见证明应该是穷尽其他证明方法之后、不得已采取的补充论证方式。②(78)②Baumgärtel/Laumen, a.a.O. (Grundlagen), Kap. 17 Rn. 1.于是,单纯依赖经验法则及其基础事实就形成了案件中满足证明标准所必要的心证,应当是司法实务中比较少见的情形,裁判者为此也可能担上不小的司法责任或者至少是说理负担。只有在法官基于当事人的主张或者从自己的认知出发,对适用经验法则的合理性充满信心,经验法则才可能成为裁判说理的基石。对比而言,一般的间接证明仍应当是实务中更可取、也更可靠的认定方式,尤其是在此前审理技术得到良好适用时,法官克服困难找到了每一块间接证据“拼图”。由此可见,也许“彭宇案”中主审法官最大的失误或者说遗憾不在于“错信”了经验法则,而在于未能尽力找到案件二审中才被提出的接警记录,其再现了双方于事故发生后分别电话报警时所作的事实陈述。这也许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复盘(巨大的社会关注也许在二审程序中成就了一审程序中难以想象的资源聚集),但是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国科研人员的持续努力相似,这种回顾性研究并非证明彼时彼刻主事人早已“铸成大错”,而恰恰是希望通过发现症结所在而避免“再度失足”。
再次,即使法官认为适用常规模式的经验法则即足以认定本案事实,但是仍然可能补充地排除其他可能性的存在。法官此时采取的是饱和论证的方式,在裁判说理中提供多个平行的补充论证。既然每个论证思路均能够独立完成充分的事实说理,那么在论证中使用“双保险”也不会影响裁判说理的质量。相反,这种做法可以使裁判更“安全”,只有在多种论证思路都被上级法院驳回时,才可能出现撤销原判的后果。法官当然可能在裁判说理中同时使用广义上间接证明的三种类型,只要其中任一种证明方式最终能够证成事实认定的结论,那么法官所作出的裁判就能经得起审视与推敲。从相对保守的角度看,饱和论证恰恰是法官规避裁判风险的“灵丹妙药”。但是从现实出发,个案法官将经验法则作为主要说理依据的原因恰恰就在于直接证据的缺失与不充分,此时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形成间接证据链条。事实论证的“饱和”,可能对多数法官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更多是法官在个案证明评价与说理中的愿景所在。
(三)间接证明的基本特征
在一般的间接证明中,由间接证据向间接事实的推导十分不稳定,这是大陆法系证明制度的基础框架决定的。在德国民事诉讼法理中有抽象规则与个案证明相分离的原则,当事人原则上只对实体法确定的要件事实承担客观证明责任,这被认为是具有普适性的法律问题,无论社会中是否发生以及发生什么纠纷,均储存在法官的知识库中;而间接事实及间接证据则指向具体个案中的证明评价问题,需要直接从案件事实中提取。①(79)①Baumgärtel/Laumen, a.a.O. (Grundlagen), Kap. 10 Rn. 2 f.可以说,评价间接证据时起关键作用的是推导出主要事实的思维过程,而不是间接事实本身。②(80)②BGHZ 53, 245=NJW 1970, 946, 950.不过由于例外情况下具体的主张责任/事案解明义务③(81)③较新讨论,参见吴泽勇:《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载《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第1360-1379页。的存在,间接事实本身在诉讼证明中同样有自己的作用,在作为证明主题时也必须被明确主张。④(82)④MüKoZPO/Prütting, a.a.O., § 284 Rn. 84. 国内类似主张,参见段文波:《一体化与集中化:口头审理方式的现状与未来》,载《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第142-143页。特别是如果证人试图证明的对象是他人的内在事实时,如前所述当然可以通过外部事实间接证明,此时申请调查证人的当事人也要说明其直接证明对象(间接事实)。⑤(83)⑤BGH NJW 2012, 2427, 2431 (本案涉及资本投资纠纷中对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 NJW 1983, 2034, 2035 (法官拒绝了调查证人的申请,因为原告并未陈述证人是如何得知原告的诉讼代理人最晚在何时知悉其错误的)。这样,我们并不必专门讨论间接证据与间接事实的关系,而只需集中精力关注间接证据是如何证明主要事实的。法官不需逐个认定间接事实(但是当然有权详细说明),间接事实原则上也没有主张责任、证明责任和证明度的问题。相反,法官应当从所有间接证据之间和其与案件事实的联系等方面评价证据(2019年《证据规定》第88条),这就意味着法官的审查需要以证据链条为核心。⑥(84)⑥部分由于不区分是否利用经验法则的间接证明产生的不同意见,参见段文波:《规范出发型民事判决构造论》,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50-153页。
参考德国法的经验具体可见,法官应当首先推定间接证据为真,然后审查全部间接证据链条是否足以说服自己认定主要事实存在,即所谓间接证据的充分性(Schlüssigkeit)。易言之,法官应判断能否排除其他可能性,认定根据间接证据形成的链条只可能推断出一种主要事实的可能。⑦(85)⑦BGHZ 53, 245=NJW 1970, 946, 950; Rosenberg/Schwab/Gottwald, a.a.O., § 111 Rn. 16; Baumgärtel/Laumen, a.a.O. (Grundlagen), Kap. 18 Rn. 22 f.如果申请人希望法官调查某位证人以证明内在的主要事实(如已知悉),那么必须要提前说明,证人是基于何种情形具有了就内在事实作证的能力。①(86)①Balzer/Walther, a.a.O., Rn. 55.如果申请方能够说服法官,那么就应当根据证据申请收集证据,否则构成程序违法,可以被三审法院撤销并发回;②(87)②BGH NJW 1989, 2947 (本案主要事实为与兽医大学中狗的接触是否导致了某犬类病毒感染)。如果不能达到说服的程度,法官则应当驳回证据申请。③(88)③Thomas/Putzo/Seiler, ZPO, 40. Aufl., 2019, Vorb § 284 Rn. 11.基于自由心证原则,事实审法官对于间接证据的证明评价原则上不受到任何法律限制,除非考虑的间接证据不全面④(89)④BGH NJW-RR 2007, 312, 313 ff. (在故意纵火以骗取保险金的案件中,法官必须充分全面地评价所有与该行为相关的间接证据,而不能笼统论之)。或者违反经验法则和思想法则。⑤(90)⑤BGH NJW 2004, 3423, 3424.当然,法官由于对其心证的形成负有说理义务(德国《民事诉讼法典》第286条第1款第2句;《民诉解释》第105条),也应当充分解释形成间接证据链条及其结论的依据。⑥(91)⑥BGH NJW 1994, 2289, 2291 f. (涉及违背善良风俗故意致人损害的请求权基础中被告对侵权行为知情的认定)。
(四)间接证据链与证据环
虽然一般的间接证明较难得到描述、更多取决于个案法官的经验活动,但是我国台湾地区姜世明教授还是尝试提炼出抽象的思维模式,这具体可以区分为证据链与证据环两种情形。其一,所谓单纯证据链条是指,主要事实需要经由间接事实和经验法则得到证明,而间接事实本身则需要单数或复数的间接证据证明。此时区别于前述经验法则适用的两种模式,应当重点关注数个间接证据才能证明间接事实的情形,比如检察官和法医出具的尸体证明书、继承系统表、户籍誊本、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和投保书,作为间接证据证明酒后呕吐和吸入窒息的间接事实,进而判定作为保险意外事故的主要事实是否发生。⑦(92)⑦参见姜世明:《证据评价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165页。该例中,多个间接证据均可以直接证明间接事实的发生,其实质证明机理与直接证明无异,只不过证据推导出的对象是间接事实而非直接事实而已,如前所述,这实际上取决于涉争实体法构成要件所确定的要件事实为何。随后,单一间接证据(及事实)结合经验法则推定待证事实的存在,则属于经验法则适用的两种模式之一。
其二,在单纯证据链条基础上,需要研究的是复杂证据链条,即在间接事实和经验法则的共同证明之下仍不能推导出直接事实的存在,而只是可能为多数的间接事实,随后需要重复这一推导过程,直至推出直接事实的存在。比如,当原告提出被告与其妻同床共枕以及出游分享同一行李箱的照片时,分别证明了这两个间接事实。此时再结合一个经验法则,可以认定被告与原告配偶过往甚密关系匪浅,并且经由第二个经验法则可以推出被告侵害原告基于配偶关系的人格身份法益的情节重大,最终能够支持原告诉请的、非财产上损害赔偿责任的成立。⑧(93)⑧参见姜世明:《证据评价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6-169页。与前述单纯证据链条相似,虽然在复杂证据链条中待证事实的证明过程较为复杂,但待证事实本身的证明仍然与单纯证据链条相同,即间接事实经经验法则的作用而证明推定事实的存在。其复杂性则体现在上述间接事实本身得到证明的过程,在个案中可能需要其他单一甚至多个间接事实与其他经验法则的协助,从而表现为多组经验法则适用的递进过程。
其三是所谓证据环,这更接近一般理解的证据链条,即无论其中各间接事实应当如何得到证明,法官都必须合并评价多个间接事实,才能证明直接事实的存在。在姜世明教授所举案例中,为了证明意外保险中意外事件的存在,二审法院共计考虑了四个间接事实,即原告被商用遮阳伞上掉落的铁架砸伤、原告左脚旧伤痊愈、本案所涉应属于新伤或者并发新伤、外伤性关节炎脚趾畸形与有截肢必要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大部分保单已多年缴纳保费,并且相应采纳了多项间接证据。⑨(94)⑨参见姜世明:《证据评价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0-174页。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最初原告采取证人证言的直接证明方式,被告则以间接反证方式否认意外事故的发生,一审法院根据相同一组证据也作出了与二审法院不同的事实认定结果。这种不同诉讼策略的选择与证明评价的理解本身,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凸显事实证明的疑难之处。甚至,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还可能出现证据链条与证据环综合适用的情形。①(95)①参见姜世明:《证据评价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6-181页。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在复杂案情下,对双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版本以及法院最终认定的事实结论和论证的描述,本身并未呈现区别于前述证据链或者证据环的特殊之处。
上述模式化讨论有助于发现案件争点与法官的实质论证,具有类似于其他法律问题讨论中使用树状图,甚至利用近年来流行的思维导图可能获得的好处。类似于经验法则的适用与一般的间接证明的区分,明确间接证明的具体模式,同样有助于审判技术中的释明权行使与裁判技术中的判决理由撰写。②(96)②相同观点,参见姜世明:《证据评价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2页。其中,一般间接证明也必然依赖一定程度的经验法则,甚至有时与前述弱化模式的经验法则适用难分彼此。但是,两种不同的经验法则的适用模式/表见证明类型作为描述性概念,仍应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