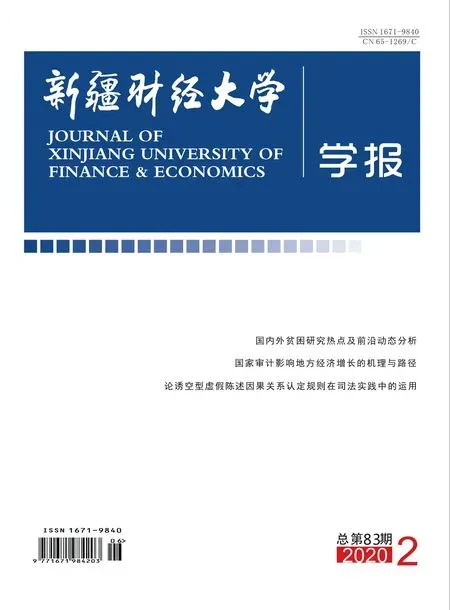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主体研究
左 晶,李 楠
(新疆财经大学,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宪法以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和限制公权力为己任,其对公权力的限制有两种模式:一是形式限制,即宪法只规定公权力的行使要件;二是实质限制,即宪法确立某些目标和对象,公权力必须围绕这些目标和对象行使而不能有所偏离。在实质限制中,基本权利条款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①详见Robert Alexy,"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基本权利条款为一国管辖内的每一个个体构筑了自由安全的私人领域和生活空间,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主体是谁决定了最终谁拥有这一自由安全的领域和空间,基本权利主体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基本权利体系和内容,也决定了宪法是否可以实现保障人权的最终目标。在世界各国宪法文本比较研究的马尔赛文经典著作②详见亨利·范·马尔赛文和格尔·范·德·唐著、陈云生译《成文宪法的比较研究》,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中并没有反映出基本权利的归属主体,而是以基本权利的研究取代了基本权利主体的研究。本文旨在通过对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主体立法体例和权利内容的分析,探讨宪法基本权利主体的特殊价值,并对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主体人和公民的权利空间及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续造。
一、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主体的立法体例
在193个国家的宪法文本③本文中的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主要参考孙谦和韩大元主编的《世界各国宪法》中的观点。中,基本权利主体的立法体例主要可以分为两类,即单一体例和多主体并存体例。单一体例的宪法文本以国籍为标志来确定“公民”“国民”“平民”“每个人”作为基本权利主体,采用这种体例的国家数量较少,只有10个。其中使用“公民”一词的国家是朝鲜、越南、老挝、也门和赤道几内亚,使用“国民”一词的是韩国,使用“平民”一词的是汤加,使用“每个人”或“任何人”一词的是英国、科摩罗和毛里求斯。多主体并存体例的宪法文本多采用“普遍主体+特殊主体”的范式,采用这种体例的一共有183个国家。普遍主体主要是使用“任何人”“每个人”“人人”“所有人”等词语,这里的“人”包括本国人、外国人及无国籍人;特殊主体主要以公民、儿童、妇女、老人等群体为保护对象。人和公民两分是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主体采用的主要范式,但也有“公民”和“人民”两种特殊基本权利主体并存的体例,如爱尔兰、捷克、利比亚、美国等均采用这种体例。在这类宪法文本中,“公民”“人民”强调拥有该国国籍的个体,部分宪法文本中使用了“居民”一词。因此,现代宪法基本权利主体不是仅以公民为保护对象,还有对于不区分国籍的任何人的关照。
最早体现人和公民基本权利主体两分的宪法文本是1789年的《人权宣言》,该文本在第一、二、四、五、七、八、九、十、十六、十七条中规定了人的基本权利,在第三、六、十一、十三、十四条中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成为权利主体之前,历史上的权利都是特权。主体的普遍性是人权区别于任何一种主体权利的最重要的特征,是权利发展中一次质的飞跃。宪法基本权利章节的名称主要以两种方式体现基本权利主体的这种变化:一种是以基本人权统领基本权利主体章节,将公民权利规定于其中;另一种是以人和公民的权利义务作为基本权利章节名称,将普遍主体的权利与公民权利在基本权利章节中分开规定,先规定人的基本权利,再规定公民权利。因此,现代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主体主要表现为两类,即作为普遍主体的人和作为特殊主体的公民。
二、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主体的权利框架
对于基本权利主体中普遍主体的人与特殊主体的公民的权利框架,各国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依照普遍主体享有该权利的百分比高低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框架。
第一框架主要包括生命权、刑事类权利、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财产权。大多数国家将此部分权利赋予了普遍主体,占比均在70%以上。在明确规定生命权的147个国家中,有133个将该权利规定为人的权利,占比为90%;在明确规定刑事类权利的128个国家中,有123个将该权利规定为人的权利,占比为96%;在明确规定思想自由的141个国家中,有125个将该权利规定为人的权利,占比为88.7%;在明确规定表达自由的118个国家中,有100个将该权利规定为人的权利,占比为84.7%;在明确规定财产权的82个国家中,有58个将该权利规定为人的权利,占比为70.7%。由此可见,多数国家将生命权、刑事类权利、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财产权赋予了普遍主体,这也意味着这些权利可以忽略国籍而被赋予任何主体。例如希腊宪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希腊领土内居住的所有人,不分国籍、种族或语言以及宗教或政治信仰,其生命、荣誉和自由均受全面保护,只有国际法规定的情形中,方可允许例外。”宪法文本所反映的趋势是生命权、刑事类权利、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财产权等已不能是公民的专属权利。在此框架内的基本权利,宪法文本多采用无法律保留的立法模式,因为这些权利具有“保障少数人”的特性,并不适宜由立法所代表的多数民主来决定①详见许育典著《宗教自由与宗教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9页。,以防因立法机构的恣意而使基本权利被掏空。
第二框架包括集会、游行、示威、平等权、社会权利。对于集会、游行是否是公民的专属权利,应将此部分权利赋予普遍主体的人还是特殊主体的公民,主流趋势并不明显,将其规定为普遍主体权利的占比在50%~60%。在明确规定和平集会权的136个国家中,有81个将该权利规定为人的权利,占比为59%;在明确规定除去组建政党的结社自由的126个国家中,有76个将该权利规定为人的权利,占比为60%;在139个明确规定教育自由的国家中,有84个将该权利规定为人的权利,占比为60.4%;在155个明确规定社会保障权利的国家中,有100个将该权利规定为人的权利,占比为64.5%。由于受教育权与社会保障权涉及国家财政成本的控制,因此,将这些权利作为人的权利还是公民专属权利,更多是根据一国控制财政成本的客观条件进行考量,是否将其作为公民专属权利,各国宪法态度并未呈现明显的主流趋势。
第三框架以选举权为主导,衍生出担任公职及公共事务参与权,这也是传统意义上公民权利的范围,在155个明确规定了选举权的国家中,有138个国家将该权利规定为公民专属权利,占比为89%,将选举权赋予本国公民是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普遍主体人的权利与特殊主体公民权利的区分突显了人与公民各自的价值,在差别中使人与公民的权利义务及其本质得以实现。
三、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主体的义务类型
在193个国家的宪法文本中,有108个国家规定了义务条款。义务是指个人应当遵从某种行为,也就是个人在对应的身份下应当完成的事务。个人只要身处社会生活中,与他人进行交往,就需承担各种义务,它不仅构成了对个人行为的各种不同形式的限制与选择,也意味着不同的惩罚方式。道德义务以个人心灵惩戒为主,政治义务意味着政治作为与政治问责,法律义务以违法为要件最终体现法律责任,宪法当中的义务以违宪体现最终责任。
据吴家麟教授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权利和义务统一论”,即宪法义务认为个体主张的权利必然意味着负有义务,这成为了宪法学界通说①详见中国宪法学研究会编《中国宪法学三十年(1985—2015)》,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80页。。黑格尔认为:“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存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②详见黑格尔著、张企泰和范扬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98页。。因此国家、社会福利和个人基本权利之间保持着辩证的、相互依存的一致性。依据宪法中基本权利主体的不同,可以将宪法义务分为人的义务和公民的义务,由此产生对社会的义务和对国家的义务,并形成不同的处罚措施。在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在公民的义务类型中占比最高的是服兵役的义务,共有78个国家将服兵役规定为公民专属义务,占比为40%。其余的公民义务所占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纳税的义务、保护公共财产的义务,但是对于这几项义务,各国宪法并未统一规定为公民的义务,而是呈现出以“每个人”或者“人人”等一般主体的义务与公民义务的两分。在明确规定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的60个国家中,将该义务规定为普遍主体人的义务与公民专属义务的比例为41∶19;在明确规定纳税义务的56个国家中,将该义务规定为普遍主体人的义务与公民专属义务的比例为22∶34;在明确规定保护公共财产义务的15个国家中,将该义务规定为普遍主体人的义务与公民专属义务的比例为5∶10。宪法中规定义务的国家,在对义务的设定中也呈现两分体例,义务的主体并不仅仅为公民,而是以公民义务为主,同时也规定了在本国境内的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人的义务。
对于同一项义务,有的国家规定为特殊主体公民的义务,有的国家规定为普遍主体人的义务。作出这种区分的依据是:首先,国家与社会建立的目的不同。最早确定宪法义务的1795年法国宪法第二节第一条规定“因为社会得以维持,需要社会成员承认并履行其义务”。在现代宪法文本中,有关纳税的义务,波兰宪法第八十三条将该义务规定为人人均应履行的责任和法律规定的公共义务;摩洛哥宪法第三十九条将其规定为一切人必须按其能力之比例承担的公共开支;而白俄罗斯宪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白俄罗斯公民有义务通过缴纳国税等费用的方式,为国家各种支出拨款”,此处将纳税义务视为对国家支出的负担。有关劳动的义务,坦桑尼亚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工作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是获得尊严的方式,人人有参与社会工作的义务”;而刚果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通过劳动促进国家建设和繁荣是每个刚果人的权利和义务”,此处将劳动的义务视为对国家的负担。因此,宪法文本中的公民义务是对国家的负担,人的义务是对社会的负担,国家与公民、社会与个人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普芬道夫认为“人的自然义务就是人的社会性”①详见塞缪尔·普芬道夫著、鞠成伟译《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7页。。宪法中的义务以个人主义观点的“基本权利”为前提,但却以共和主义、社会连带等观点为基础。宪法普遍主体人的基本义务的存在是以人的基本权利的存在为前提的,只有在保障人权的前提下,社会成员才能共同承担社会连带义务。
其次,履行义务的主体不同。普遍主体的义务意味着宪法义务履行主体的无差别性,例如普遍主体人作为纳税义务的主体,就意味着借助税收的普遍性原则和公平负担的基础让所有人根据其能力分担公共开支。理论上宪法义务条款就成为了法律设定义务的依据和限制,对于普遍主体义务的设定必须受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并且接受违宪审查。
最后,人的义务和公民义务的区分,也意味着不履行义务的处罚手段的不同。马克思·韦伯所认为的武力虽不是国家正常或唯一的手段,但确实是国家特有的手段②详见马克思·韦伯著、钱永祥译《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05页。。只有对国家的义务才能以强制措施予以保障,而对于受教育的义务或计划生育的义务等都应以行政强制措施为限度,只有准确划定人和公民的权利范围才能准确理解公民义务强制措施的类别。
四、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主体呈现的特点及其特殊价值
(一)基本权利主体两分导致人的权利与公民权利两分
在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对人身自由权、平等权、思想自由等权利均有半数以上的国家赋予了在本国地域的任何人;而对于社会权,不同国家基于经济能力的差异,有的仅赋予公民,有的则赋予了任何主体。宪法义务的类型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几乎所有国家都将服兵役的义务规定为公民义务,但是对于遵守宪法和法律、保护自然、劳动、纳税的义务,有的国家仅赋予公民,有的则赋予了任何主体。市民和公民的双重属性导致权利被最终分化为人权和公民权。人权是政治国家之上的权利,公民权则是政治国家之后的权利。
(二)政治权利是公民权利的核心,也是公民资格取得与暂停的重要标志
在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虽然公民权利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政治权利均是公民专属权利的核心内容,是公民资格取得与暂停的重要标志。例如,玻利维亚宪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政治权利包括参政、表决、选举、检察等权利,如果在战争中效力敌军或盗窃公共资源甚至叛国都将会被暂停政治权利。厄瓜多尔宪法第六十四条中的政治权利包含了选举与被选举权、参与涉及公共利益事务的权利及推翻普选政府的权利。被剥夺政治权利之时,也意味着公民资格的暂停。多数国家宪法中的公民权利除政治权利外还包括社会权利,当公民被剥夺或暂停政治权利后依然享有公民专属的社会权利。
(三)基本权利主体两分为人和公民的原因
1.国家目标决定了权利义务的两分及人的权利的价值。多数国家都将人的权利与自由的实现作为国家的最高价值和最终目标,例如白俄罗斯宪法第二条规定“人、人的权利和自由及其实现的保障,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价值和目标”。也有一些国家将人的尊严作为社会和国家的最高目标与价值,例如秘鲁宪法第一条规定“保护个人并维护其尊严是社会和国家的最高目标”。人类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制定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将“人的权利”统一于“人的尊严”之下,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一致认同。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的人的形象已不同于“近代私法中自私自利的、老谋深算的、机警灵活的人”③详见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著、舒国滢译《法律上的人》,原载于方流芳主编的《法大评论》第1卷第1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各国宪法文本中的人体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①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宪法文本中的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②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页。。詹姆斯·格里芬认为,人的这种能动性是人首先应该具有选择自己生活途径的自主性,其次是拥有某种基本教育与资源的最低限度供给,最后是拥有他人无法阻止个人追求设想生活的自由③详见詹姆斯·格里芬著、徐向东译《论人权》,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40页。,这也是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体现出的人的核心思想。
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人权的内涵都较为一致地体现出因为是人而具有的权利,但是对于人权的外延即具体权利内容的规定却不一致,因此人的权利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术语,各国宪法文本中对于人的权利的依据与人的权利的标准依然存在分歧。但能肯定的是,保障人的权利是基本权利的起点,也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前提。所有人一律平等享有宪法规定的人权,国家应当改善司法和行政条件以实现真正有效的所有人的平等,采取措施防止并消除歧视、边缘化弱势和排外主义。人权的发展历程证明,公民资格并不是一个人享有合法权利的必备条件,公民身份并不是一个人获得有尊严生活的前提条件,在此种情况之下,公民的价值可以说是在降低的。
2.人的权利与公民权利的界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权力恣意的空间。如果说任何具体的宪法规范目的在于规范政府的组成及权力的行使,建构一个有限政府以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那么宪法文本中人的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界限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宪法对公权力限制的强度。不同国家对人的权利与公民权利界限的划分不尽相同,如有的国家划定的公民权利内容较多,有的国家则将基本权利全部赋予了公民。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拥有的基本权利越多,公权力拥有的恣意空间就会越大。当宪法将基本权利较多地赋予为公民专属时,公权力就拥有了可以将国家内的任何人划出公民范围的恣意,任何个人都可能成为国家权力恣意的对象,因为如果普遍主体的人的权利没有获得宪法的根本保障,那么人的权利就只能依靠法律来实现,对于议会通过多数表决程序所制定的法律的理性,必须考虑其局限性的可能。此外,普遍主体中的非公民因缺乏政治权利,无法获得在法律制定中的民意参与,因此非公民的权利就无法在法律制定中得到充分考量,并且国家也没有保护非公民的动机,非公民的权利就无法获得保障,国家在决定谁是公民的权力中丝毫不受限制,最终损害的依然会是公民自身的权利。
这一观点在美国的移民政策中得到了印证,移民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于多数决策原则,多数决策原则下的移民政策经常出现的非法驱逐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因国家立法权力的毫无限制而导致的随意专断。美国对于衍生国籍的孩子和非法移民政策的专断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立法机关的恣意不仅“使移民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也将威胁美国长久的平等理念,并伤害每一个出生在美国国土的人”④详见Robert E,"Jurisdi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Meaning in the Citizenship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而移民政策恣意的一大根源也在于公民与非公民权利的界限不清,如果宪法中没有对人的权利和公民的权利予以区分与保障,那么国家公权力的恣意专断就会遁入法律的恣意或者缺失之中。
反之,公民的专属权利越小,那么普遍主体的人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范围就会越大,当非公民同样可以享有生命权、刑事类权利及宪法救济的权利时,才能保障其作为人的尊严而免于作为弱势群体的牺牲。因而可以说,人与公民权利的界限就是限制国家公权力恣意的界限,将公民的专属权利限缩在一定范围,才能实现对国家公权力的限制。这条界限不仅划分了公民与非公民的外部界限,也决定了公民与非公民的内部生活状态。
五、我国宪法文本中基本权利主体分析
我国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中对基本权利主体使用的是“臣民”的表述,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主体均采用单一立法体例,仅为“人民”,建国后沿袭苏联的立法范例,我国1954年、1975年、1978年宪法在主权归属者、基本权利主体方面的规定较为一致,均采用人民作为主权归属者、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单一立法体例。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有113个国家对主权归属者使用了“人民”,有6个国家使用了“公民”,还有少数国家使用了“国民”“居民”。对于“人民”的含义,多数宪法文本并没有作出解释,只有阿富汗宪法和索马里宪法规定人民由所有公民组成。“人民”在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主要是一个抽象概念和集合概念,人民通过民选权利机关行使权利,公民是人民的组成部分,公民通过选举代表和全民公决行使权利。国家的所有权力均来源于人民,对人民的治理应当经由人民的意志与同意,中央政府及其机构的权力和权威来自宪法,宪法的权威来自人民,人民同意按照宪法对其进行治理,人民通过定期选举或者公民投票的方式表达其对治理机构和治理方式的意志与同意。
我国2004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该条款对人权的解释既可以看作宪法原则意义上的人权,也可以看作国家价值观的人权,还可以看作转化基本权利内容的人权。作为国家价值观的人权很好地诠释了安全、人权与发展的关系,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更大的自由:为人人共享安全、发展和人权而奋斗》中强调了这三个目标和宗旨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没有安全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而没有对人权的尊重,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也无法享有安全”①详见UNDoc.A/59/2005,"In Large Freedom:Towards Department,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for All"。。据阿马蒂亚·森的论述,狭隘的发展观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工业化或社会现代化,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②详见阿马蒂亚·森著、任赜和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那么在两者之间尊重和保障人权必然是国家的第一要务,权利与自由才是发展的首要目标,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划分、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的权利的发展。“曾经被反映在以往许多宪法之中并且在冷战时期引发人权意识形态的冲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基本上失去了其对抗性的内容。与此相反,如今所有人权平等、不可分割和相互依赖性,这一点在国内和国际层次上都得到了承认”③详见曼弗雷德·诺瓦克著、孙世彦和毕小青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评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页。。“如果将权利保障只停留在国内法的水平上,那么非公民就得不到必不可少的人权保障”④详见杉原泰雄著、吕昶译《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90页。。因此,保障每一个境内个体的权利是我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展现的国家发展观。作为转化基本权利内容的人权,“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将“人”这一普遍主体纳入基本权利主体范围,成为人与公民基本权利主体并存的体例,这也符合世界各国宪法中将基本权利主体的人与公民两分的基本趋势。但是在我国宪法现有体例之下仍存在以下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人的权利空间不明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明确了基本权利主体是有人和公民之分的,但以第二章的题目和内容进行考察,我国宪法中具体权利均是以“公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且涵盖了各项权利,如果我们将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权利视作公民的专属权利,那么作为普遍主体的人的权利空间究竟是哪些呢?我国现有法律中关于人的权利的主要内容有:《民法通则》第八条、《继承法》第三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十二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和公民享有相同的权利;《民事诉讼法》第五条、《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行政复议法》第四十一条、《国家赔偿法》第四十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同我国公民享有同等的诉讼或复议的权利和义务;《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适用本法规定;《民用航空管理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外国人经营的外国民用航空器在我国从事民用航空活动适用本章规定。此外,对于难民地位的认定,主要依据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和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我国于1982年签署了这两个文件。我国并没有制定关于国际难民的专门法律,目前对难民的日常管理主要依据《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四十六条,除此之外并无相关详细规定。
以上法律适用的主体并没有一致规定为“外国人、无国籍人”,也有法律仅规定为“外国人”。这些零散的关于人的权利的条款并没有完整规划出第一框架和第二框架下的基本权利主体,人的权利的不完整从某种意义上说源于缺乏人的权利立法问责机制,根源则在于宪法中对于人的权利内容的规定不够明确。此外,我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对拘留审查、遣送出境等行政处罚措施仅规定了行政复议为最终救济措施,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无疑应给予更为充分的救济,对于应给予外国人、无国籍人、难民哪些权利,需依据宪法对此类主体的权益保障作出回应。如《世界人权宣言》所阐述的“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乃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人权正是强调没有例外的权利,对居住在我国的无国籍人、外国人以及难民给予人权保护,才能从根本上阻止忽视人权、践踏人权的暴行。
(二)以国籍确定公民缺少限制性规定
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肯定了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但对于国籍法所确定的公民,宪法既没有设置法律保留原则,也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条款。宪法必须规范国籍法确认的公民范围,才能保证最终通过宪法保障作为人民组成部分的公民的权益,否则国籍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拥有了将任何人划出公民范围的恣意。公民的范围是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中最重要的要素,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出生地主义与血统主义取向,以及衍生国籍和几代血亲后代可以获得国籍。
公民的历史从来不是一片静海,而是一片冲突的海洋,正如许多学者所论证的,公民的历史是一个排斥包容的过程,在美国“作为国籍的美国公民资格有着自己的排斥和接纳的历史,恐外症、种族歧视、宗教偏见、对外国阴谋的恐慌都曾经在历史中发挥过作用”①详见Judith N.Shklar,"American Citizenship:The Quest for Inclusion,Massachusetts"。。在政权更替的过程中,孤儿、私生子、单系血亲的人群以及移民等弱势群体都随着政权的更替或者国籍法的修改而重复着被排斥或者被吸纳的历史。例如美国公民条款的解释主要是围绕着第十四修正案公民条款展开的,自这一修正案诞生,人们对其中“all person born”“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和“in the United States”的解读便存有争议②详见 Garrett Epps,"Citizenship Clause:'A Legislative History'";Cristina M.Rodriguez,"Citizenship Clause,Original Meaning,and the Egalitarian Unity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Katherine Culliton-Gonzilez,"Born in the Americas: Birthright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Gayeski Dana,"Give Me Your Tired,Your Poor,Your Legal:Why Efforts to Repeal Birthright Citizenship Are Unconstitutional and Un-American";Robert E.Mensel,"Jurisdi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Meaning in the Citizenship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现已有十几种相互冲突的解释方案,随着不同问题的出现,联邦法院自身的解释也曾经出现过不一致,因此共和党人想要终止非法移民后代公民身份的争论一直没有消失。我国国籍法确认公民范围的宪法依据不够明确,宪法没有给予国籍法以明确的立法方向,对国籍法中公民资格的取得与丧失也没有作出法律保留或者授权限制,这些群体是易受侵害的对象,他们缺乏反映自身权利的表达渠道,应通过宪法中公民资格的标准和人的权利的规定严格对国家的问责机制,加强居民的私人亲属关系,减少移民政策的恣意,减少取得公民资格的武断。
六、我国宪法中人的权利与公民权利内涵的续造
为最大限度地避免立法机关的恣意,保障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对于人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内涵,本文以为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解决。一种是修改宪法,在宪法文本中直接作出规定,但该方案的施行将以牺牲宪法的稳定性为代价。韩国宪法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修宪方案①详见韩曹洪锡著、金玄卿译《韩国宪法的现在与未来——以有关宪法修正之讨论为中心》,原载于韩大元主编《比较宪法——宪法文本与宪法解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另一种是对“人权条款”结合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二条和具体的基本权利内容条款,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进行续造。
首先,制定现行宪法基本权利章节的指导思想是“扩大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范围”②详见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并且“总结几十年经验教训的结果……我们社会主义的宪法应充分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重要思想,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③详见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4页。,由此可以体味出,导致我国公民权利涵盖范围太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政治权利作为基本权利的起点,为了政治权利的实现,所以公民要享有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权利,因此我国宪法第二章主要体现的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卡尔·拉伦茨也认为法学都有一种价值导向的思考④详见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4页。,宪法第二章的价值导向无疑不再是公民的政治权利而是人权,但是第二章的内容并不适合作为人的权利的内容。
其次,在制定我国现行宪法的过程中,针对外国人的权益保护应放于哪一章节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将其放于第二章中,先规定公民权利,再规定外国人的受庇护权;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将其放于总纲中,因为第二章主要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加入一条外国人的权益似乎不太协调,最后采纳了后一种意见⑤详见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因此从文义解释和历史解释中可以得出,我国现行宪法中的非公民的权利与公民的权利采用的是并行的立法体例,并未采用合并的立法体例,因此非公民的权利主要应在第三十二条中,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第三十二条使用“外国人”一词的局限性,必须将“外国人”的内涵扩大至无国籍人、难民等主体,这也是“规范环境的演变可以导致迄今标准的规范意义之改变——或限缩之,或扩充之。除此之外,整个法秩序内部结构上的演变也可以造成法律解释的转变,例如明显的新的立法趋势”⑥详见卡尔·拉伦茨著、陈爱娥译《法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7页。。在人权条款作为宪法原则的基础上,第三十二条中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应主要包括人的权利第一框架和第二框架下的权利,对于第一框架下的生命权、刑事类权利、思想自由、表达自由、财产权应作无保留的宪法解释,对于第二框架下的权利可作条款的具体限制解释,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可设定基于和平方式的自由限制,社会权可参考南非宪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强调每个人有权获得紧急的医疗救助、在其不能照顾自己及亲属的情况下获得适当的社会救助以及接受基本教育。在中国外交部与公安部、教育部、民政部共同签订的协议中,难民儿童可在中国上公立学校的规定也印证了受教育权绝非公民专属权利。
对我国宪法基本权利主体的研究仍存在以对公民的研究代替基本权利主体的研究的现象,宪法文本的解释与人权价值转化仍需长期的实践,需从理念与实践角度建立人权宪法化的机制。另外,在宪法尚未进入诉讼领域的情况下,人权条款发挥功能的空间也受到了限制。只有充分发挥宪法解释的作用,不仅实现人和公民基本权利主体的两分之名,而且实现人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两分之实,才能真正实现以宪法保障人权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