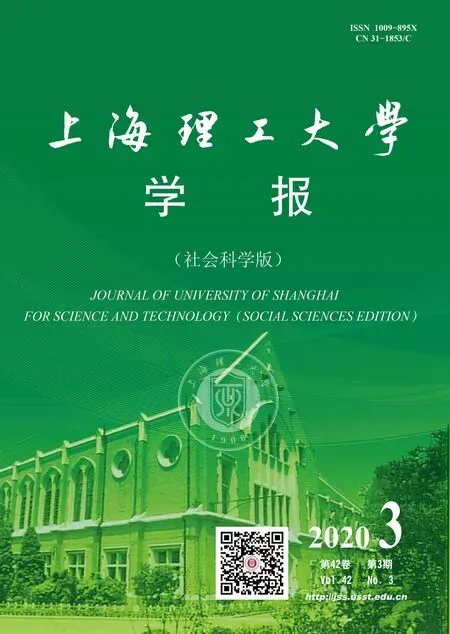刻板印象下的“白人性”书写
——《土生子》的后殖民主义解读
周奇林
(大连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44)
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1908—1960)最伟大的文学成就在于其开创了“赖特派”自然主义“抗议小说”(protest novel)之先河。从《汤姆叔叔的孩子们》(UncleTom’sChildren,1938)到《土生子》(NativeSon,1940),再到《黑小子》(BlackBoy,1945),赖特创造了各式各样的抗议形式,塑造了一个个风格迥异、个性鲜明的抗议人物。“一时间,赖特式的反映美国黑人困境的‘抗议小说’风靡一时,成了唯一应该效仿的文学范式,赖特也成了美国黑人文学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1]165其中,《土生子》的问世在美国文学评论界,乃至整个美国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西方评论家普遍认为,赖特的《土生子》出版后,非裔美国文学才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才真正在美国评论界占有一席之地。”[1]164《土生子》之所以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关键在于非裔美国文学作品中一以贯之的种族问题在该小说中被无限放大。黑人主人公别格·托马斯颠覆了昔日非裔美国文学作品中深入人心的黑人形象,凭借其暴力犯罪行径一改“汤姆叔叔”式的人物设定,将美洲大陆上沉寂了几个世纪之久的黑人民族置于显性的位置,迫使人们重新考虑黑人的民族特性与美国文明之间的关系。于赖特而言,黑人的民族特性与美国文明相互对立,共同构成“抗议”的实质,在此基础上,“黑人性”(blackness)与“白人性”(whiteness)实则是对这两者的具化。在“二元对立论”(binary opposition)下,“黑人性”与“白人性”朝着反方向发展,衍生出后殖民主义视阈下西方白种人至上的“种族意识形态”(ethnical ideology),“在这一种族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出现了西方国家的种族歧视、种族偏见和各种种族主义恶行”[2]。在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驱使下,黑与白之间的对抗性愈演愈烈,正如《土生子》中白人对黑人所持有的偏见将别格一步一步推向罪恶的边缘,别格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最终以悲剧收场。然而,刻板印象同样存在于黑人的意识形态之中。通过别格对白人社会的凝视,有助于观察其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深入了解其对白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即白人至上的印象,再由此深入探析小说中被忽略的“白人性”。
一、“黑人性”与“白人性”概念之界定
《土生子》是一部书写种族问题的“抗议小说”,尤其是文中对别格内心活动的描写,成为该部小说“抗议”精髓之所在,与此同时,外在的种族矛盾被内化为别格的心理活动,使得这部小说在“抗议”的同时不断趋向于心理小说之列。“四十年代,美国黑人作家以‘种族’问题为主题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心理小说’。这一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3]别格复杂的内心活动不仅是塑造人物形象的关键所在,而且还能带领读者透视其真实的内心世界。在这个复杂的内心世界中,一方面别格身上的“黑人性”被一览无遗,另一方面,透过别格对白人社会的凝视,与“黑人性”相对立而存在的“白人性”油然而生。
所谓的“黑人性”是基于肤色之上的一个身份概念,它是20世纪中叶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也是反对殖民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成为非洲政治文化运动口号的同时,还指涉40至50年代的非洲文学运动,“主张黑色人种精神来张扬民族自尊心,再现古老黑人文化艺术传统,并以此反对种族歧视,改变黑人受奴役、受压迫的悲惨境况”[4]。这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桑戈尔(Senghor)将“黑人性”一词定义为:“‘黑人性’是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正如这些价值在黑人的作品、制度、生活中表现的那样。”在非裔美国文学中,“黑人性”与种族问题息息相关,自非裔美国文学问世以来便开启了对“黑人性”的探讨,其中不乏宣扬黑人民族古老传统和灿烂文明的作品,如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映证了“‘黑人性’的最大特点是竭力维护和提高黑人民族的尊严……‘黑人性’文学在提高民族自尊的同时,也不时讥讽和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没落”[5]。这其中包括对美国社会绵延数百年的种族歧视的揭露与批判,相关作品不胜枚举,赖特的《土生子》便是其中一例。
作为“黑人性”研究的对立面,“白人性”研究的存在领域更为广阔。以往对“白人性”的探索多停留在“白人文学”的层面,例如,海明威笔下的“准则英雄”(Code Hero)坚守WASP(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品质,对WASP以外的“他者”持歧视态度,身上带有鲜明的美国主流社会“白人性”烙印[6];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所勾勒的穷白人以及南方没落贵族,他们固守一隅,坚守着仅有的一点来自肤色的自豪感,认为自己比黑人高一筹。由此可知,“白人性”研究与“白人文学”相关联,而将“白人性”研究的聚焦点切换至黑人文学,有助于了解“他者”视角下的白人主流社会,书写白人的民族特性。对于“白人性”而言,它是站在“黑人性”对立面的基于肤色之上的一个身份概念。“在美国的社会构成性结构中,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的‘白人性’相比,‘黑人性’是属于受支配的、边缘的范畴。”[7]因此,“白人性”较之“黑人性”,更加具备一种主体性与优越感,并且朝着与“黑人性”相反的方向发展。前者所呈现的主体性与优越感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层面,建立在对黑人形象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上。
对黑人形象的脸谱化再现不仅加深了白人社会对黑人的已有偏见,而且以文学经典的形式固化下来,形成对黑人歧视的制度化实践,隐藏在这一歧视背后的是一种本质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这种逻辑以话语、成规和符号的形式制造了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的“情感结构”,成为白人社会的普遍认知模式[8]。
显然,白人社会对黑人的固化认知模式是“种族意识形态”的衍生物,引导着种族问题探讨过程中的切入视角,使得研究视阈往“黑人性”方向倾斜。但是,在“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之下,不应紧扣白人的观察视角。黑人同样具备意识形态,在“黑人性”与“白人性”相互对抗的社会环境中,形成黑人对白人所持有的偏见。这层偏见在探析“白人性”的过程中同样具有参考价值,能让更多白人群体之外的族裔群体加深对美国主流文化群体的认识。
二、刻板印象的“双向性”原则
1978年,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问世,开启了以阶级、性别、种族为参照系,关系白种人和非白种人、宗主国和殖民地对立互动的“后殖民”(post-colonial)研究[9]。后殖民概念原指西方殖民者利用文化霸权和殖民话语,在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领域对非西方社会所施加的影响。刻板印象作为后殖民概念的产物,着重体现西方殖民者对非西方社会所持有的偏见,认为“他者”群体或是唯唯诺诺,或是愚昧无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优越感。但是,这种从主流文化群体的视角探析“他者”形象的做法,忽略了“他者”亦可反观主体形象,致使刻板印象不可避免地落入“单向性”原则之中。Tilman Cothran在WhiteStereotypesinFictionbyNegroes一文中指出,通常白人作家在其作品中会给文中的黑人贴上标签,但是他用黑人作家的作品反证黑人对白人持有相同的刻板印象[10]。由此可知,刻板印象并非仅限于主流文化群体对“他者”的印象,相反,“他者”对主流文化群体同样持有刻板印象。
在刻板印象的形成过程中,主体通过对客体的凝视(gaze),在意识形态层面对眼前的“景观”进行性别、阶级等方面的身份定位,顺应了“现代作家不像过去的作家那样强调合理的感受和专注直接、明朗的描写,而是侧重细腻隐晦的感受,着重感官知觉因素、印象和顿悟”[11]。然而,针对如何凝视这一问题,需综合考虑主体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因素,并且随着理论维度与身份政治维度的叠加,主体如何凝视以及在主观意识形态层面形成什么样的刻板印象,都会对潜意识产生深刻的影响。“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要义就是告诉我们东方永远处在西方的凝视下,黑人永远处在白人的凝视下。这种凝视使东方成为西方话语政治下的客体,黑人成为白人眼睛中的景观。”[12]若是消解这种颇具身份政治意味的凝视视角,给予“他者”凝视的权利,那么“他者”对主流文化群体的刻板印象将被赋予“颠覆”性质或“反抗”性质的意义。“因此,来自客体的“他者”的注视,也可以对已有的视界政体进行颠覆。发出自己的注视,就是将自己置于能动的位置,撇去种族、阶级、性别的影响而使自己占据主体的位置。”[12]在非裔美国文学中,凝视主体的变化极大地增强了黑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对白人社会的注视反思自身处境,同时,以小见大,透过个体影射整个黑人民族在美国社会的生存现状。而且从黑人的视角凝视白人社会,一方面为“黑人性”与“白人性”研究提供崭新的研究视阈,另一方面丰富了后殖民主义理论,映证了刻板印象的“双向性”原则。
三、《土生子》中“黑”与“白”之间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
白人从未真正注视过黑人,几百年来他们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黑人,把黑人定性为奴性十足、任人欺凌的“他者”。在刻板印象的驱使下,黑人常被白人剥夺获取公平正义的权利,对黑人滥用私刑,司法不公现象普遍存在。“如果白人能够理解白人的恐惧,他也应该同时理解黑人的恐惧,理解他们因恐惧而做出的极端行为。”[13]《土生子》中,别格所犯下的骇人罪行在芝加哥白人社会引起了恐惧的浪潮,加深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由来已久的隔阂,同时也加深了白人对黑人的仇视与敌对心理。谋杀案件一经发酵,芝加哥的黑人群体被视为一丘之貉,黑人狡猾、残忍的形象直击人性,以至于在搜捕别格的过程中,许多无辜的黑人被牵连其中。再者,别格卷入的杀人犯罪案件,将其推至风口浪尖,原本的杀人犯罪案件在未经调查的情况下被强制定性为强奸杀人案件,并且,以往未曾破获的强奸杀人案件皆归咎于别格,理由竟是在白人看来黑人男性常常觊觎白人女性。更为重要的是,“凡是想象得出来的偏见都已卷入了本案”[14]428。由此种种,白人主导下的刻板印象致使该群体对“黑人性”产生片面化的认识,用“罪恶”“堕落”“愚笨”等消极的字眼定义“黑人性”。而这一切归根结底是因为美国南北战争前的蓄奴制度与战争后“隔离但平等”的谎言遮蔽了白人的双眼,使他们与真正看不见东西的道尔顿太太一样,从未真正深入了解黑人这一族裔群体的民族性格。
同样地,黑人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压迫,也未曾真正注视过白人,继而,他们在刻板印象的驱使下对“白人性”的认识有所偏颇。“土生子”一词既是别格的代名词,也是别格身后一千两百万美国黑人的代名词。然而,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土生子”从未被当作真正的美国公民看待,他们极其缺乏社会归属感。究其原因,种族隔离制度筑起了一道以肤色为界限的“藩篱”,整个城市的等级秩序也因此而得以运作。为此,别格不由得发出感慨:“瞧!我们住在这儿,他们住在那儿。我们是黑人,他们是白人。他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干啥都成,我们干啥都不成。就像关在监牢里似的。有一半时间,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世界外边,巴着篱笆眼儿在往里瞧……”[14]21-22显然,种族隔离制度阻断了两个群体之间的正常交流,生活在“藩篱”这边的黑人唯有通过观看电影,或是通过那些受雇于白人家庭的黑人同胞,才能“窥视”到“藩篱”那边的白人世界,拼凑一幅不完整的白人社会图景。即便黑人跨越界限,与白人打交道,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遵守铁一般的社会等级秩序,无法真正注视白人。在与道尔顿先生的谈话过程中,别格“一次也不曾把他的眼睛抬得跟道尔顿先生的脸一般高。他站在那儿,稍稍弯着膝盖,微张着嘴,弯腰曲背;眼睛看东西也是浮光掠影的。他心里有数,在白人跟前,他们就喜欢你这副模样。倒不是有人真正教导过他,而是白人的态度使他感到他们喜欢你这样”[14]54。别格隶属于被“规训”(discipline)的黑人民族,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压迫。他与身后的一千两百万黑人早已习惯了对白人毕恭毕敬的生活,这种奴颜婢膝的生活姿态深深地刻在黑人民族的骨子里,致使他们觉得与白人对视是一种僭越行为。因此,无论是“窥视”,还是无法正视,别格对白人社会的理解趋于片面化,并在其意识形态层面烙上了印记,由此产生黑人对白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以别格为代表的黑人民众认为,所谓的“白人性”是一种凌驾于黑人之上的,能让黑人产生恐惧感与自卑感的社会气质,也正是这种社会气质构筑了一个民族的民族身份。
在别格和他的民族看来,白人不仅是人,而且是一种很大的自然力量,就像暴风雨前在头顶上出现的乌云,又像黑暗中突然伸展到你脚旁的又深又汹涌的河流。只要他和他的黑人民族不越过某些界限,就不必害怕这个白色力量。但不管他们是否害怕,都天天跟它一起过日子,即使嘴里不说它的名字,大家也都承认它的存在。他们只要住在城里这个被指定的角落里,就得默默地向它致敬[14]128。
于是,别格随身携带刀与枪,以便在会见道尔顿先生时能给予他勇气与自信,让他觉得自己与他们处于平等地位。然而,不管别格如何全副武装自己,他都无法堂堂正正地凝视白人,也无法摆脱潜在的“白人性”束缚。正是由于别格对“白人性”的片面化理解,使得内心深处的压抑感不断深化为暴力犯罪倾向,终酿成杀人惨案,别格本人也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四、《土生子》中“黑”与“白”之间刻板印象的消磨
别格对白人所持有的刻板印象早已在意识形态层面根深蒂固,然而,玛丽、简、麦克斯等白人的出现渐渐消磨了原有的偏见。原本在别格看来,“藩篱”另一头的白人世界中,除却穷白人,其余是一群能将意志强加给黑人民族的富白人,如道尔顿太太想努力说服别格上夜校,接受教育,“要他去做她认为他应该喜欢做的事”[14]71。玛丽的出现打破了别格内心的预设,让他越来越摸不透与之打交道的白人。在与玛丽的短暂相处过程中,别格意识到玛丽并非往常电影中所述的过着声色犬马生活的白人女性,她对待黑人的态度也让他无所适从。
她对他的反应是他也是人,跟她生活在同样的世界里。而过去,他在任何白人身上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可是为什么呢?这难道是一种花招?听她讲话时,一种隐隐约约的自由感是跟这样的严峻事实混淆在一起的:她是白人,有钱,属于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里的人告诉他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14]77。
的确,深受种族隔离制度影响的别格不知道该如何与这位有钱的白人女性相处,他不敢注视玛丽,小心翼翼地回答每一个问题,生怕出现纰漏。只要有白人的目光存在,别格便永远无法正视他们,也永远体察不到深埋内心的自由感。醉酒后的玛丽收起了白人的目光,于是,别格趁着这会儿真正凝视这位独特的白人女性。此刻,别格心中被压抑的自由感得以释放。也正是因为这片刻的自由感被突如其来的道尔顿太太打碎,恐惧感与自卑感重新涌入心头,促使他伸出了罪恶的双手,犯下了性质恶劣的罪行。
尽管玛丽没有彻底让别格突破刻板印象的界限,但是简与道尔顿则让他加深了对“白人性”的理解。因为玛丽虽然与别格平等相处,但是她的言辞不免会让别格落入恐惧感与自卑感之中。
“我去过英国、法国和墨西哥,可我不知道离我十条街的人们怎样生活。我们彼此是那么不了解。我光是想看看。我想要了解这些人。我这一辈子从来没到一个黑人家里去过。然而他们准是像我们一样生活。他们也是人……他们有一千两百万人口……他们生活在我们国家里……跟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里……”[14]79
玛丽十分想拉近黑人民族与本民族之间的距离,可是“他们”与“我们”形成了两个民族之间的距离感,这解释了为何别格会感受到隐隐约约的自由感与严峻的事实混淆在一起。但毋庸置疑,别格隐约中感受到原本存在于意识形态之内的根深蒂固的“白人性”出现了一丝变化。
相较于玛丽,在别格嫁祸简的阴谋被揭穿后,简非但没有怪罪他,相反,他还为别格提供了人道主义援助。这与满城之中想置别格于死地的白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至于麦克斯,他是别格能真正与之对视的白人,是给予别格生之希望的白人,也是唯一能让别格信任的白人,还是能帮助别格及其身后一千两百万黑人民众设身处地着想的白人。自别格被捕后,但凡他出现在公共场合,白人对他的憎恶感足以将他吞噬。在仇恨交织的城市空间中,任何辩解都会被视作狡辩,犹如困兽之斗。因此,他宁可保持缄默,承受着由刻板印象造成的恶果。在别格全然放弃活下去的意志之际,是麦克斯在为他尽力奔波。案件进入关键阶段时,别格瞧着麦克斯,只见“他的脸苍白憔悴。他的眼睛下面都是黑眼圈”[14]425。在法庭上,麦克斯滔滔不绝地为别格辩护,控诉白人对黑人的所作所为,将别格的暴力犯罪心理归咎于白人。即便别格的案件已尘埃落定,麦克斯仍未放弃希望,企图依靠自己微弱的力量让案件重现生机。至此,根深蒂固的“白人性”解说已瓦解,事实证明,“白人性”并非是完全站在“黑人性”对立面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种族问题的探讨过程中,“白人性”与“黑人性”也能相互交融,缓和了“黑人性”与“白人性”之间的对抗性,并进一步消除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
五、结束语
本文以后殖民主义为理论支撑,透过别格对白人社会的凝视,呈现“他者”眼中的主流社会,挑战传统的“黑人性”解说。别格步入的印象误区打破了刻板印象形成过程中的观察视角界限,体现了刻板印象的“双向性”原则。偏见并非主流文化群体之特权,即主流文化群体以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他者”,形成对“他者”的固化印象。同样地,“他者”对主流文化群体同样持有偏见,这种偏见建立在主流文化群体所持有的偏见的对立面。与此同时,刻板印象所具备的片面性使得凝视主体陷入主观臆断之中,尤其是在涉及种族或阶级问题的文本中,这种主观臆断不断趋于僵化状态,从而激化主流文化群体与“他者”之间的矛盾,产生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土生子》中,一方面,别格对“白人性”的片面化理解是其恐惧心理的内在源泉,助长了其暴力犯罪的倾向。另一方面,玛丽、简与麦克斯的出现让别格对“白人性”产生了新的认识。玛丽和简以平等的姿态与他相处,让他意识到自己对“白人性”的理解有所偏颇。对于麦克斯的倾力相助,别格的内心深处掀起了一阵波澜,让他意识到“白人性”与“黑人性”并非是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线,而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因此,认识到“白人性”的片面化指向,能够帮助黑人摆脱刻板印象的束缚,缓和“黑人性”与“白人性”之间的对抗性,进一步消除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