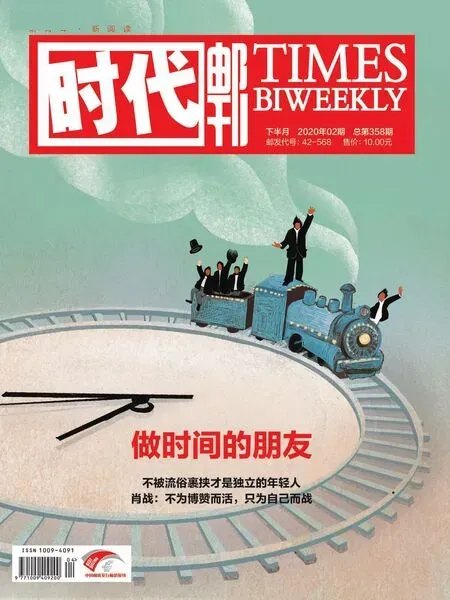打春
文 李成
在我家乡,“立春”一般是不说“立春”,而说“打春”的。“今年哪天打春?”“马上要打春了。”……在冬末春初,我总能听到这样的对话,我的母亲也常把这个词挂在嘴边上。一开始,我根本不知道“打春”是何意,母亲告诉我,“打春”就是“立春”,我便觉得“打春”这个词好。因为它比“立春”响亮。仿佛是铜锣一响,一场大戏拉开了帷幕,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即将降临大地。
确实,一个“打”意味着春天来得不同凡响,来得有声有色。它透着威武,又透着喜庆;春天的来临是如此不容置疑,如此彻底,让人感到震撼。
“打春”二字从小给了我很深的印象,长大后,我喜欢读把春天写得有声有色的诗。于坚的《春天咏叹调》,一开始就带来一声“巨响”:春天,你踢开我的窗子/一个跟头翻进我房间/你满身的阳光,鸟的羽毛和水/还有叶子/你撞翻了我那只穿着黑旗袍的花瓶……还有墨西哥诗人帕斯的《眼前的春天》:我触到的一切都在飞翔/白昼睁开眼,进入/提前到来的春天/鸟儿充满人间。春天就是这么声威十足,“冲”劲十足,这么有生气,甚至这么“莽撞”;冬天,山寒水瘦,草木枯槁凋零,大地死气沉沉,当然需要一声春雷把一切“打”醒!让“一切都在飞翔”……
后来,我从有关中国民俗的书中得知“打春”其实是指古人的一项活动——“鞭打春牛”。而“春牛”却是泥塑的牛,鞭打它,意味着要开始春耕生产了。这一风俗据说来自宫廷。立春这天,皇宫里张灯结彩,以示庆贺,而节庆的高潮是皇帝执鞭将立在宫门口的泥塑春牛打碎。史书有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京都风俗志》也有:宫前“东设芒神,西设春牛”。行礼如仪,散场之后,“众役打焚,故谓之打春”。
一打春,“土膏欲动雨频催,万草千花一晌开。”人间又是一番新气象,农人们就忙碌起来了,他们换上旧时裳,把犁耙、锄头、羊叉、铁锹、箩筐、扁担以及斗笠、雨衣(蓑衣)都找出来,擦洗擦洗,为一场浩大的春耕生产做好准备,牛栏里的牛当然也更受到重视,这一切都预示着一场春耕春播大戏真的就要开锣上演。
每当这时,我的母亲也要做些准备。除了检修些必要的农具,她还要把各种蔬菜的种子——不知她平日收藏在哪里,变戏法似地找出来,分门别类放到纸里瓶里包好装好,甚至一边包装,一边念念有词。我知道,我们家的那一小块菜地,很快就将花红叶绿,一片五彩缤纷。
早年间,在打春那天,母亲还要为我们烙几张荞麦饼吃。那饼是绿色的,有时还缠绕上几丝韭菜,点缀着几粒白葱,吃起来,略有点苦,稍一回味,却又是甜!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这也是一种古老风俗的延续:唐宋以后,立春之日有食春饼与生菜的习惯。东汉崔寔《四民月令》:“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春饼、生菜以盘承之,即名“春盘”。春盘里的“内容”当然因时而异,因人而异,但韭菜、葱、萝卜之类的总少不了的,这些吃上去脆生生的,新鲜可口(所以又有“咬春”一说)。原来,中国民间曾经是这么的有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