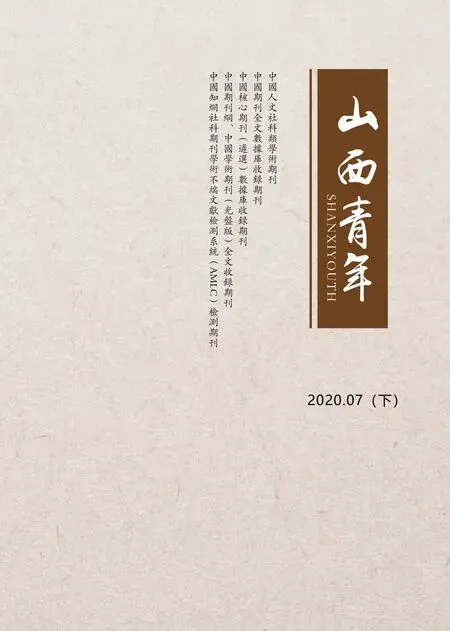试论康德崇高的形式
姜鹏越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崇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在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中对于青铜饕鬄文化的讲述,那时候人们要用神秘恐怖狞厉可畏的形象作为一种对自己部落的保护。这种沉淀着历史力量的形象是当时一种崇高的形式。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崇高的形式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但是无论是在哪一个时代,崇高都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显现。
人类的审美活动对人类的大脑中的思维是有一定要求的。审美活动是超功利的,审美主体要摆脱现实生活的束缚是前提条件。在这一点上崇高也是和其他审美范畴是一样的。当海啸要淹没的人的生命的时候人只会感受到威胁和恐惧,人自然是无法体会到崇高的美感的。恐惧和崇高之间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是否崇高都是由一定程度的恐惧转化而成的呢?这个问题会在后面进行探讨。
审美活动的主体是人,固定审美对象在不同的审美主体的心理产生的结果不同,审美对象在审美主体心里产生的感受也是不可估计的。那么崇高的审美对象一定是“力”的无限大和“数”的无限大是不是过于绝对呢?这两种一定会让人产生崇高吗?不是这两种形式能不能也产生崇高呢?
一、崇高对象与美的对象的关系
首先,崇高和美都是人在审美活动中做出的判断。既然是审美活动就都是超功利的。那么能不能同一个审美对象,既然人产生美感又让人感到崇高呢。当然这里不能把“美感”这一概念的含义扩大化。要是说崇高也是一种美感那么就无法进行讨论了。这里说的美自然是指让人精神愉悦轻松的。如果依照康德所说“美只涉及对象的形式,崇高却涉及对象的无形式,形式总是有限的,无形式则是无限的”。
也就是说康德认为同一个审美对象是不能够让不同的审美主体同时产生美感和崇高的。因为美的对象是要依赖形式的。而崇高的对象则是无形式的无限的。毕达哥拉斯认为美是和谐,美在比例。赫拉克利特认为对于神来说一切都是美的。再美的人在神面前也像一只猴子。智者学派则认为一切都靠人的主观感觉,是通过视听给人以愉悦的感觉。美的内容需要美的形式来表达,形式美是内容美的存在形式。那么当人们超越了形式美看到内容美,或人们直接对内容感到美,没有形式美。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美的对象就可以跳脱出形式的束缚了呢?
大多数美的对象需要依托美的形式,动人的音乐要有美的旋律,美丽的画作需要画面布局各种高深绘画技法,美丽的姑娘要五官端正。但是在这个多元的时代,随着人们接受的开放,会不会听到某个人打喷嚏的声音也像天籁,会不会小孩毫无章法的涂鸦中也有人类最初心底纯真的美,会不会某个哪怕脸重度烧伤的姑娘,也有着惊人的美丽呢?虽说大多数的美需要依托形式。但是美的对象偶尔也会跳脱形式的牢笼,被人捕捉到,并产生美感。
崇高最早是古罗马美学家朗吉弩斯提出来的。生命圣化道德,恐惧是崇高的主要来源。还有一些抽象的形式。博克认为崇高的形式是无限的、巨大的、晦暗的。赫尔德认为崇高的形式是一和多,一的特质强烈就是崇高,康德则认为是数的无限大和力的巨大。也就是知解力无能为力的事物。但是这就出现了矛盾,纵向是科技的发展,导致过去人们知解力无能为力的事物,那些神秘的恐怖的。现在可能一切都在人类的眼中变得不神秘不恐怖。具体来说,比如龙卷风在过去是不可预测的。在人们远观的时候可能觉得恐惧害怕,在确认自己不会被龙卷风卷入其中的时候又会产生崇高。这种崇高从何而来呢?因为人可以置身其外的时候,会感叹龙卷风的壮观恐怖,自己在这伟大的自然当中存活下去,心中有爱眼中有如此广袤的世界。但是现在,龙卷风是可以预测的,已经对人类不再构成威胁,甚至连损失都可以避免,但是它依然可以是崇高的一种形式。
横向的矛盾是,可能存在一种即使人类的知解力无能为力的形式,比如经典的例子海啸。处于海啸中的人会只有恐惧,因为危及到生命,这种情况下不会产生崇高。但是在岸上安全区域观看的人则会产生崇高。那么就这个例子来说,厉害的判断,在审美判断之前。是不是并没有逃出审美活动的超功利性。也不符合审美判断的先验性。
二、崇高与恐惧的关系
博克说:“任何堪称引起恐怖的事物都能作为崇高的基础”。虽然说的是任何引起恐怖的事物,但是博克和康德的论述重点却是自然现象。这就脱离了艺术创作,事实证明艺术创作实践中,崇高并没有缺席。艺术作品中同样可以感受到崇高感,这就是对康德崇高理论不完善的质疑。并且恐怖也不应当仅仅包括自然现象,应该包括社会历史文化等等很多方面。阿多诺主张:“我们能够从艺术作品所展现事物的高大和力量中体验到崇高”。
崇高与恐惧之间的关联既可以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也可以是艺术当中的。除此之外,康德还遗漏了因为信仰民族宇宙观的不同,会出现令一个种族产生恐惧的事物,对另一个种族则没有这种影响。比如汉族人比较畏惧老虎,所以武松打虎是一种英雄的做法。但是纳西族人却不怕老虎,纳西族人把老虎当作自己的祖先。
克服恐惧产生的崇高应该是,人在面对恐怖的对象的时候感受到了自身的强大,从而产生了崇高。在原始社会,当人逐渐有了主体意识,从新认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便开始不是完全臣服于自然。而是借助自然的力量去克服对自然的恐惧。古老的巫术仪式和祭祀仪式中,人们就认为人类可以某种方式获得自然的力量,或是跟自然达成某种协议。比如中国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皇帝在古代被看成是一个自然的象征,一举一动都代表着上苍的旨意。人们把对自然的恐惧转换成了对帝王的尊敬。
三、崇高的现实意义
朗基纳斯在《论崇高》的第七章中说:“我亲爱的朋友,我们应当懂得:在生活中为一切高尚心灵所鄙弃的东西,决不会是真正伟大的。没有一个真有见识的人会认为财富、名誉、光荣、势力或为荣华富贵围绕着的一切是幸福……”现实生活中,崇高是一种对于人的灵魂的完善。人能够不再原地踏步,冲破被世俗限定的桎梏实现灵魂的升华,是需要自我否定的能力,和面对自己的勇气的。崇高像是耶稣那张仁慈而悲伤的面孔,当人们把对自然的崇敬和畏惧转移到耶稣身上的时候,崇高也悄悄的住在每一位基督徒的心理。
崇高似乎总是发生在人对客体的情感当中,无论是远古的太阳神伏羲女娲还是通过奉献生命灵魂得到升华的英雄们,人们总是在客体当中看到崇高的光芒。蒋孔阳在《美学新论》中提出了;“崇高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显现”的观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人们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那么是不是就是说人类从群体回归个体,这就使作为个体的人和崇高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呢?
答案是否定的。每一个灵魂都需要得到升华,只有险隘的人生才是始终在原地踏步。赫尔德认为:对人类的爱,是一种人道的崇高。这就包含人的道德、人对生命的爱重、人的抱负等等。这就对人的自我灵魂的不断完善提出了要求。
无论是那些为了推动历史进步,用自己的生命作为祭奠的人,还是传说中为天下苍生尝遍了百草的神农氏,抑或拯救苍生功德无限的菩萨,还是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个体。崇高是贯穿整个世界整个历史的。崇高离生活并不是遥远的抽象的失去现实意义的。
崇高来自人们追求文明的力量,来自人类道德和理智的光辉。正如复旦大学林新华所说:“因此,在多元的文化时代,我们能够运用这种跨文化美学的分析方法,深入到不同的文化情景当中,有时甚至还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局限,才能获得崇高感。这里实现了崇高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一种互动”。对生命和世界怀揣敬畏之心,崇高就在离我们不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