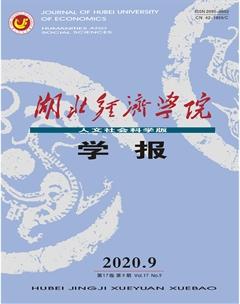新世纪美国沈从文研究述评
刘竺岩 周倩
摘要:新世纪以来,美国沈从文研究总体呈现多视角、新方向的特征。美国学者主要聚焦于沈从文作品的城乡书写研究、跨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作品研究、作品英译的反思批评与翻译史考察,以及社会变革期的沈从文思想研究。与国内研究相比,这些代表性成果大多具有视角新颖、研究方法独特的特征,因而对国内沈从文研究起到结论与方法上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新世纪;美国;沈从文研究
从1925年林宰平的《大学与学生》到当前探讨沈从文的“众声喧哗”,对沈从文的研究总体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的“褒贬不一,毁誉悬殊”,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冷外热,反差较大”,到新时期以来的“反思深化,硕果累累”。其中,美国的沈从文研究滥觞于1960-1970年代。以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金介甫《沈从文传》为代表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传入大陆,为大陆学界沈从文研究的深化起到先导性作用。
进入新世纪,随着美国沈从文研究的不断开拓与深挖,对沈从文的探索逐渐走出初期的基础性研究,总体呈现多视角、新方向的特征。与同时期大陆学界沈从文研究相比,这些成果既呈现不同文化视角所造成的特异性,也因中西学术交流的日益密切而产生相似性。从研究对象看,新世纪美国沈从文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包括沈从文作品的城乡书写研究、跨文化比较视域下的作品研究、作品英译的反思批评与翻译史考察,以及社会变革期的沈从文思想研究等。这些成果一方面为国内研究提供了思路上的借鉴,同时也因地域的限制,存在某些偏颇。本文以新世纪以来的国内研究为参照,对美国沈从文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进行简要述评。
一、城乡书写研究中的沈从文作品
进入新世纪,部分美国学者侧重于以沈从文作品中城市与乡村书写的巨大差异,介入其中的道德问题,以此深入沈从文作品对现代性的反思。
纽约城市大学伍梅芳(Janet Ng)的《道德风景:阅读沈从文的自传和游记》(A Moral Landscape:Reading Shen Cong-wens Autobiography and Travelogues)从《湘行散记》和《从文自传》人手,探究沈从文自传作品中地理位置对作品的意义。作者认为,沈从文的“旅行地点比他所写的实际地点和人物更能体现其主体性”。沈从文描述的地方是其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即一个想象出来的景象,或一个城市知识分子乌托邦梦想的神话场所。在作品中,知识分子对农村和部落群体的写作态度可被描述为“帝国主义的怀旧”,这种态度在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塑造中体现的尤为强烈,“在沈从文的文化语境中,乡村在中国文学中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比喻,而是一个特别政治化的隐喻”。在作者看来,出白军人家庭且亲眼见证过屠杀、镇压、战争,因而沈从文在多方面都与暴力渊源颇深。“通过他的作品,沈从文为读者再现了这种侵入式的体验。”
伍梅芳认为,沈从文在叙述中进行的旅行,并非自我启迪、自我发现的朝圣之旅,而是对该地区的详细标注地图、历史、地形信息的旅行指南,这使得读者能够保持距离,观察他人的悲剧和战争。作为京派作家,沈从文以城市或精英读者为书写对象,其叙事和审美视角不属于湘西原住民,而是反映城市精英的目光。因此沈从文将风景、生活与战争都变为画卷,成为知识分子审美崇高的场所。反之,湘西也得以融入城市意识、知识分子意识和读者意识。此外,作者还指出沈从文作为知识分子、京派作家的身份与他和苗族的母系关系及对自身“乡下人”的定位之间的矛盾,这促成他对乡村的依恋与疏离,且通过对乡村及乡村人民的独特视角,折射出现代城市生活的颓废。
最后,作者在道德层面上探讨沈从文写作中的暴力内容。沈从文将血腥残忍的战争屠杀场面平静文明地如画卷般展示出来,试图通过对边缘群体的暴力认知,反思如何对社会苦难做出贡献:通过种种逆转书写呼吁重审我们的制度化觀念,将美丽的事物同残酷的真理并置。因此作者认为,无论是理性的或是神秘的,沈从文的游记都不单是对人类地域的探索,也是对历史书写方式和人类主体被限制于此书写方式中的挑战。
太平洋大学的陆杰(Jie Lu)在《批判城市,想象乡村:沈从文的都市小说》(Critiquing the City,Envisioning the Coun-try:Shen Congwens Urban Fiction)中侧重沈从文都市小说,试图从乡土小说与海派现代都市小说的文学语境出发,探究沈从文对现代城市的情感及其对现代性的态度。作者指出,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以城市为主题者,可以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占据半数,与其乡土小说大致相同。但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之所以受关注程度不如乡土小说,更多原因是都市小说的诗意与想象与其乡土小说相去甚远,而他的城市小说也明显不具备“湘西那样的迷人与异国情调”。同时,沈从文的都市小说在表现城市世界中的心理扭曲与精神无能时,其氛围“显得陈腐与公式化”。
首先,沈从文的都市小说表现出的反城市倾向,实质上是其湘西乡土小说的另一面。在沈从文的城市书写中,他更加关注城市的内在性,很少描述城市的物理轮廓,“甚至对室内空间也缺乏详细的描绘”。作者将这一现象解读为沈从文对城市以及城市生活的有限视角,这源于城市的扩张等因素使得作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感受到焦虑、恐惧与身份的丧失。作者将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与其乡土小说在内在性的层面上进行比较,认为在其乡土小说中,对乡村的景观、生活以及历史的详尽描述,形成了极为鲜明的时空感。但在其都市小说中,视觉视角的缺失使得作品中对城市环境的描写缺失了,这就导致在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中,原本与其乡土小说密切相关的全景式表现被单一的城市内在性所取代。
接下来,作者通过对沈从文都市小说的文本分析,归纳了这种单一的城市内在性的几个特征。其一是以《绅士的太太》为代表的非现代的室内空间。作者惊异于在这样一个上层家庭的内部空间中,几乎一切现代的用品都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装饰品,而缺乏与现代城市生活相关的“动态氛围”。其二是在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中,主要的空间并非城市空间,而是自然。对此作者提出了沈从文“似乎只能在他的城市小说中描述自然的外在性——非城市空间”的疑问。以《春天》为例,作者敏锐地指出,在沈从文的都市小说中理陛的思考与对话是与自然密切相关的,而非与现代情感相关联。针对沈从文对城市内在性的排他性重视,作者将其与包括左翼文学在内的上海都市文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无论是新感觉派还是左翼文学,都做到了“将城市空间作为影响现代个体现代情感的主导因素”以及将城市景观用于对现代情感的塑造。而在沈从文那里,城市人的活动范围往往局限于室内或自然,是“传统城乡统一体”的产物,于是其小说中的“城市”仅仅成为了一种道德符号,而非一套完整的城市语汇。
接着,作者对沈从文“乡下人”身份的自我认同与其都市小说书写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探析。作者认为,实际上的“城市居民”身份与沈从文自我定位的“乡下人”身份,一方面使得他在与乡村的审美距离中,得以想象与表达整体的湘西:而在城市中的生活使得沈从文难以产生对城市的全面视野,又因其有意识的“乡下人”身份建构,使得其笔下的城市在道德上走入了乡村的对立面。
因此,沈从文对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的书写与其对城市内在性的关注实际上“是通过一种现代情感和对城市的祛魅来实现的”:而他对现代性的态度也是矛盾的,这使他对城市的关注指向道德层面的批判,城市本身仅仅作为背景出现在他的城市小说之中。
较之陆杰的文章,伍梅芳的角度与新世纪的大陆沈从文研究相比,更富创新性。作者并未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探究沈从文作品对城市与乡村的书写差异,而是以沈从文作品中的纪实性文本——自传与游记切入,以地缘思维考察沈从文游记中的地理文化形态,探寻作家活动与其道德观形成的关联性,由此进入作家城市与乡村观念的更深层次。首先,伍梅芳的分析着眼于沈从文的精英立场,亦即作家本人虽怀有对乡村深切的依恋,但在实际上与乡村疏离。那么,沈从文对现代城市道德颓废的猛烈攻击,不仅仅源于他对乡土的绝对肯定,更来自于沈从文的精英知识分子身份与其自认的“乡下人”身份问的复杂纠葛。其次,以“道德景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进行阐释,无论在沈从文研究领域,还是放眼于其他作家作品,都不失为大陆学界的一个崭新角度。整体看,除萧纪薇的文章外,仅美国长滩城市学院张盛泰的中文论文《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地缘道德景观》,从地缘道德景观、地缘传统渊源、作品表现的空间形式、地缘政治意义、现代性等方面,探究沈从文作品中地缘与道德观念形成的复杂关系。这一批评路径在沈从文研究领域中,尚属首次引入大陆学界。此外,则有郑斯扬的《<小鲍庄>中的道德景观》以关键词“仁义”展现王费ll乙作品《小鲍庄》中潜藏的道德观念,从而阐释王费忆“对乡土中国道德秩序和道德精神之时空探索”。总体看,正如李怡所言:“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的话,那么这样的‘二元却又很可能是彼此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有对立,却也存在着交融与结合。”伍梅芳的文章以“道德景观”的崭新批评路径,突破了此前研究对沈从文关于城乡情感的二元对立分析方式,展现了沈从文关于现代的复杂认知。
陆杰的文章在题材上与国内沈从文都市小说研究相一致,侧重探究沈从文城市与乡村书写的对立。早在1990年,吴进即以《论沈从文的都市小说》探析沈从文城乡书写的差异,否定其城市小说对现代都市的片面性指责。此后的大量研究成果,都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沈从文湘西小说优于都市小说的观点,陆杰的文章也在此列。相较于大陆研究,陆杰文章的创新性在于,较早深入沈从文小说的城市空间书写。认为正是沈从文将空间书写局限于都市的室内与自然,才使得都市小说的视野难以在城市中展开,因而难以形成对现代都市的全面观照。这一思路的提出,有力佐证了此前大陆学界对沈从文都市小说内在缺陷的论证。
总体看,对沈从文作品城乡书写差异的探究,在中美学界同为沈从文研究的重要领域。新世纪美国学界的此类成果,虽在题材上与国内成果相近,但由于研究路径的创新,使得结论或佐证上形成独特性得以可能,进而为国内研究提供参照。
二、跨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沈从文作品研究
新世纪以来,美国沈从文比较研究的代表是Zoya Stan-chits的《寻找现代世界的精神自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沈从文<边城>和戴维·马洛夫<一种想象的生活>中的跨界》(In Search 0f spiritual Freedom in a Modem World:Cross-ing Borders in Fyodor Dostoyevsky The Idiot,Shen Cong-wen's The Border Town and David Malouf An ImaginaryWorld)。文章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沈从文《边城》与戴维·马洛夫《一种想象的生活》进行平行研究,涉及屈原与奥维德的流亡文学传统。作者梳理屈原和奥维德对后世流亡文学的深远影响,发现无论是屈原还是奥维德,在遭受流放以后,都在其作品中创造了一个“精神慰藉的家园”。在此传统中,这三部现代作品都可以被划归到“流亡文学”的范畴。作者在这里所谓的流亡,指由于与现代城市的紧张关系所导致的断裂关系,是一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放逐。作者认为这三部作品的可比性在于,同属现代城市流亡文学,且同样表现了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的敌对关系。三部作品同样以两个对立世界之间持续的张力来决定情节,通过跨越隐喻的边境,以追寻精神放逐的释放。作者注意到,《一种想象的生活》与《边城》中的“河流”具有复杂的象征意义,是分割肮脏的现实世界与纯净的想象世界的界线;《白痴》中的巴甫洛夫斯克与圣彼得堡,以及瑞士与俄罗斯,都是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对立,前者象征外界的自由与开放,后者是充斥着压抑的堕落世界。三部小说在人物上存在大量的二元对立,如《白痴》中梅诗金与罗果仁,以及《边城》中老船夫与城市商人,都是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比。对两个世界界线的跨越在三部作品中意味着精神放逐与自由之间的墙被打破了,“这种从精神和肉体死亡的世界中解脱出来的运动,揭示了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文化孤立和孤独。”
作为美国的“沈从文研究第一人”,金介甫(JeffreyKinkley)在1990年代以來,除注重沈从文作品的乡土性外,也侧重于跨文化影响研究,注重沈从文的苗族作家身份及其作品中的异域色彩。他的《沈从文与想象的本土乡村》(ShenCongwen and Imagined Naive Communities),将沈从文定位为“一个非鲁迅、非社会主义者与非现实主义者,走自己反儒家、亲西方、非城市和非政治道路”的乡土作家。在金介甫看来,沈从文的作品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是因为在其作品中,中国是一个前工业时代的道德共同体。这些作品以“舒适的家乡”和“当地多样的风俗习惯”为表征,不只以民族、种族等现代性的概念作为纽带。沈从文的文学语言与中国古代诗人、游记家也存在继承关系,这种富于异域色彩的文学传统继承了屈原与道教,以与屈原相类的楚文化精神创造了中国西南的现代神话。这使得沈从文倾向于“未受破坏的传统文化”,从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关注。如《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以西南原始文化含蓄地谴责了汉族的高等文化。此外,作者也简要提及沈从文作品对韩少功、高行健的深刻影响。这些观点与作者在中国大陆发表的中文论文《屈原、沈从文、高行健比较研究》相一致。
新世纪以前,美国的沈从文比较研究肇始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他将沈从文的田园书写与华兹华斯、叶慈、福克纳相提并论,但并未展开。金介甫的《沈从文传》则认为《边城》“不像《包法利夫人》那样写得富于启发性,却像《项狄传》那样独出心裁,像《追忆似水年华》那样扎实”,他深信对沈从文及其作品的公正评价,将“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呲后,金介甫深入于沈从文的比较研究,将沈从文与泰戈尔、狄更斯、都德等进行影响研究,与夏多布里昂、高尔基、普罗斯特等进行平行研究。此外,聂华苓、王润华等学者也重视沈从文与海明威等作家的对比。
新时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沈从文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于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是沈从文与外国文学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早在1986年,程光炜、王丽丽的《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比较视角》即从故乡、乡村与近代文明的对照,以及普通人书写三个层面提出二者的可比性。此后,对沈从文与福克纳的平行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其中新世纪的代表性成果有杨瑞仁的《沈从文·福克纳·哈代比较论》、李萌羽的《多维视野中的沈从文和福克纳小说》等。前者将三位作家置于“相互关联和彼此照应的‘交互语境”旧中,把并无实际关联的作家进行平行研究,探索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在面对共同社会现象时的相似性与特异性。后者从本土化、后现代性、生态美学、宗教学与原型批评等多个角度,“对沈从文、福克纳小说意蕴比较阐释空间”作出进一步拓展。除福克纳、哈代外,国内学者亦倾向于将沈从文与梅里美、乔治桑、契诃夫、屠格涅夫等进行平行研究,由此形成了一个深入而复杂的比较系统。
总体看,新世紀以来的国内沈从文比较研究,一定程度上受惠于此前的美国学界研究成果,尤以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为最。而影响研究则始终是国内外沈从文比较研究的薄弱环节。注重沈从文的苗族作家身份,以此为基础对沈从文进行跨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金介甫开其先河。这方面的研究自新世纪以来,已成为国内“显学”,产生大量学术成果。但和新世纪以来的美国学界比较研究成果相比,更倾向于探析作品中的苗族文化内涵,与道家、楚文化等的继承关系,对湘西“异域文化”进行总体性探究的成果仍然较少。
三、沈从文作品英译的反思批评与翻译史考察
作为《边城》英译者之一,金介甫(Jeffrey Kinkley)在《沈从文杰作<边城>的英译》(English Translations of Shen Cong-wens Masterwork,Bian Cheng(Border Town))中,对包括作者本人的译本在内的四种《边城》英译本进行比较,讨论可能对翻译和读者接受产生影响的个人、语言、社会、政治、历史和跨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形成了简略的《边城》英译史。首先,作者梳理四个译本中译者与沈从文问复杂的交往关系,即除项美丽(Emily Hahn)之外,包括作者本人在内的另外五位译者都与沈从文本人有直接的交往关系,并对这些译者在翻译《边城》时是否与沈从文进行交流提出了疑问。
作者从译文的角度对四个版本进行比较。项美丽(E milyHahn)与辛墨雷(邵洵美)合译的版本(1936)与其他三个版本相比,一般都遵从汉语原著的词序。作者认为,这源于项美丽以英语为母语,而不甚通汉语,故采用两步翻译而形成的效果。偶尔删去译者认为不可译的词句也是这一原因的产物。因而这一译本不可避免地存在“令人惊讶的失误”。对于金陧(Ching Ti)和白英(Robe~Payne)的合译本(1947),作者认为它是“最优美、最富文学性的”,原因在于这个译本更容易被英语世界的读者接受。如这个译本将“虎耳草”译为“tiger-lilies”(虎百合),虽然未必符合原著,但远较前一译本直译为“tiger-ears”(老虎耳朵)更富于诗性的联想。此外,金、白译本也借鉴了上一译本。戴乃迭(Gladys Yang)译本是以上三种中准确性最高的,对上文提及的“虎耳草”等译法,都进行了准确的翻译。这源于戴乃迭对中国近代史的熟悉,如对清末民初军队编制及其沿革的准确翻译是前两个译本所不能相比的。但由于译者戴乃迭供职于官方出版机构,这个译本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政治正确”,如对涉及“哥老会”词句的删改。在分析前三个译本之后,作者简要介绍其本人译本的背景和翻译风格,认为这是“学者式的翻译”,不忽视文中的文化细节,因此译本显得“冗长”。
接下来,作者考察了四个译本的语境与接受。作者认为项美丽、辛墨雷译本淡化了《边城》的独特性与地域性,将其中与“落后”“粗野”“野蛮”相关的语词删去。作者认为两位译者之所以这样做,似乎是有意让小说代表“中国”,从而将沈从文定位为一个“全球的”作家。作者认为当时的一个文化语境似乎也影响了这一译本,即1930年代赛珍珠(Pearl s,Buck)《大地》(The Good Earth)的成功。从这一语境来看,项、辛译本似乎是针对赛珍珠对中国农村想象的一种更真实的“回应”。而金陧、白英译本也是将《边城》作为世界文学翻译的,这个译本将《边城》题目译为“The Chinese Earth”(《中国大地》)。虽然这个译本比项、辛译本对当地文化、人性、两性关系的概括更为精辟,但他们的翻译依然淡化了地域、民族和军队的主题。戴乃迭译本虽有缺陷,但较准确地延续了沈从文小说传统,“将沈从文的小说描述为一部关于中国民族社会的作品。”作者本人的译本更关注小说的乡土话语,也关注特定地域细节。但作者也提及,他在1990年代以后倾向于反对将沈从文视为狭隘的乡土作家。
对于译本的接受,作者从不同时代的出版情况进行考察。项、辛译本的影响无法考证,但由于其在杂志上连载,可能对一些在欧美大型图书馆工作过的汉学家产生影响。尽管金、白译本并非畅销书,但作者认为它可能对在外国大学就读的华裔学生、以及受夏志清影响的读者们产生巨大影响。戴乃迭译本由于进入《熊猫丛书》,在全球有较广泛的分布,但仍以西方高校图书馆的馆藏为主。作者本人的译本之所以广为人知,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网上销售。此外,由于这一译本在翻译上准确再现沈从文的创作,得以作为教材进入高校的文学翻译课堂。
曾在香港岭南大学、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任教的欧阳桢(Eugene Eoyang)在《湖南的弗洛伊德:译沈从文<萧萧)》fFreud in Hunan:Translating Shen Congwen's“Xiaoxiao”)中,基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探究《萧萧》中“弟弟”这个特殊词汇的英译问题,希望译者在翻译技巧上能够更加关注原文文本的内在逻辑。作者在对《萧萧》进行英译时,关注“童养媳”这一极富中国传统色彩的特殊婚姻形式,即对萧萧来说,这个孩子既是“孩子”的身份,又是“丈夫”的身份,这隐含着一种含蓄的恋母情结。因此作者认为,在这个恋母情结的矛盾中,萧萧对这个孩子的称呼需要准确表达这种微妙关系。作者注意到“弟弟”这样一个既对孩子,又对丈夫所进行的称谓,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难以理解。起初,作者将之翻译为“小弟弟”(little brother),但认为在英语语境下,“little”更多指向“身材矮小”或“年轻”,不是一个正常的称谓语。直接音译为“Didi”又使得英语读者不能理解对话者之间的感情。作者又试图将“弟弟”译为“Junior”,这虽然是一个可以正常使用的称谓,但作者认为,“Junior”一般适用于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对于湖南农村家庭并不合适,且它并不隐含着小说中的恋母情结。最终,作者选用“Sonny”(小家伙;宝贝)这一称谓,认为这个称谓既可以作为呢称来称呼一个小男孩,也可以成为妻子对丈夫的昵称。作者将这一译法与《萧萧》的其他两个英译本进行比较,认为这个译法展现了小说的一个重要意义:萧萧与小丈夫的关系又像母子关系,但这一关系又与乱伦无关,而是原始的、田园诗般的。
国内的沈从文作品英译研究始于1985年华强的《沈从文著作的外文翻译》,文章以概述海外譯文篇名、作者名、书刊名为丰。进入新世纪,逐渐出现聚焦于沈从文作品英译的期刊论文与硕士论文,这些成果多以某一视角切入译文文本,探析其中的翻译策略,如刘汝荣的《金介甫英译<边城>中文化移植的操纵理论考察》、隆涛的《沈从文<边城>中的民俗英译方法论》等。2010年以后,也出现了沈从文作品英译的综述类成果,如汪璧辉的《沈从文海外译介与研究》、徐敏慧的《沈从文小说英译述评》等。在这两类研究中,前者以对译文的探析明显有其侧重,后者则倾向于全面概述沈从文作品的英译状况。与美国学界的研究相比,金介甫与欧阳桢研究的首要特征是凸显译者的主体性,以其翻译实践对本人译本进行探究与反思。其次,两篇文章深入具体文本,尤其是欧阳桢的文章,深入到一个词语的译法,以小见大,准确反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义差异。其三,金介甫的文章在不同译本的对照中,形成了《边城》的英译史,结合时代特征与译者情况,对不同译本的特征与接受进行了详尽的探究。当然,以译者身份进行的译本探究不可避免地存在拘泥之弊,如欧阳桢对萧萧与小丈夫关系的考察,局限于对“恋母情结”的分析,未能深入中国传统民俗视角下的“童养媳”问题等。
四、社会变革期的沈从文思想研究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界对社会变革期沈从文思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罗格斯大学王晓珏(Xiaojue Wang)的《从精神病院到博物馆:沈从文1949年转型中的精神错乱与精神分裂症话语》(From Asylum t0 Museum:The Discourse of Insanityand Schizophrenia in Shen Congwen's 1949 Transition)。文章关注沈从文由作家到学者转换的思想,通过分析1949年前后沈从文的主体性危机,以及他从文学创作到艺术史研究的转换历程,探究沈从文在1949年前的审美视野及其在社会转型中独特的历史意识。作者通过对精神分裂症的分析,认为社会转型期发生的精神分裂症对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知识分子活动的考察有重要意义。对沈从文来说,其精神分裂症是一场个人危机。在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分裂对于个人应对政治与社会转型而言,也是一种“永远不会消失的痛苦”。接下来,作者通过分析沈从文在这场个人危机期间所写的日记等文本,了解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心理状态。从沈从文屡次提及的“自杀”的代名词——“休息”“解放”,作者将沈从文此时的心理状态理解为“卡夫卡式的焦虑异化”,即“内在自我的破裂”。在这一阶段,沈从文一方面坚持艺术自主性与个体能动性,一方面又承受转型时期的排斥和孤立,因而其“疯狂”实际上是他对自身原则的坚持,同时也表现为“疯狂和理智之间的不稳定界限”。接下来,作者分析沈从文在博物馆中工作的深层内涵。从社会层面来看,沈从文进入博物馆工作意味着“与社会和存在不再有重要关系。”从精神病院到博物馆,似乎是从一个密闭空间到另一个密闭空间。但对沈从文来说,博物馆又是一个摆脱意识形态影响、得以实践其美学思想的地方。作者认为沈从文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撰写过程中,对“陈腐”的古代服饰的琐碎研究,建构了一种替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美学。由此,沈从文在从精神病院到博物馆的转变中,克服其心理危机,并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美学概念。
自金介甫《沈从文传》问世以来,对沈从文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思想转变的研究,成为美国沈从文研究的重镇之一。作为沈从文生平的重要转折点,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一阶段引发美国学者的关注。早在1970年代,金介甫就将沈从文由文学创作转入文物研究的选择解读为“他不但没有被‘洗脑筋,而且还像过去那样,用冷静旁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巨大的社会变革,他有处世的战略:韬光养晦,与世无争——‘退居第二线。”与此相似,新世纪初期的国内学界也延续了这一思路。2002年,李扬的《沈从文的最后40年》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沈从文的内心深处“无论是对新政府的领导方式,还是对‘改造思想的方式都有着相当程度的抵触。”因而,即便沈从文尚未放弃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其作品《老同志》仍“很难见到他往日小说的神韵。”
但随着对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生平的深入探究,国内学界逐渐对沈从文文学思想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微妙关系产生更加深刻的解读,并由此重新阐释沈从文从作家到学者的转变。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结合家书,分析沈从文在革命大学学习期间“从具体实践中学习为人民服务”的自觉靠拢,将《老同志》的写作视为“让沈从文产生了恢复用笔的冲动。”同时,此著也重视沈从文在四川参与土改时期“在一种完全新的感情中,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的积极态度。李斌的《<老同志)与沈从文创作转型的努力》则认为,虽然这部小说保留作家大量积习的症候,但“通过对劳动模范的歌颂表达了沈从文靠拢人民文学的真诚努力。”
与同时期国内研究成果,尤其是2010年以后的成果相比,王晓珏的文章从精神疾病的医学原理人手,分析沈从文的主体性危机,而非仅仅通过沈从文的“呓语”式文本进行语义层面的解读。此外,对精神病院与博物馆两个空间象征意义的解读,可以窥见沈从文由作家到学者转型的社会性意义转变。但此文也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很大程度源于作者意识形态的偏见。文章将“精神病院”与“博物馆”进行二元对立的分析,尤其是认为进入博物馆意味着沈从文“与社会和存在不再有重要关系”。事实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博物馆这一工作环境,不可能意味着“与社会相脱节”。在叙述中,作者没有意识到在从精神病院到博物馆之间,沈从文试图重新提笔写作,并在题材上主动向主流意识形态靠拢的真诚努力。正如李斌在《(老同志)与沈从文创作转型的努力》中所言:“沈从文无意去弥补小说文本呈现出的诸多缝隙,这恰好成了他既努力融入新的时代,又保留许多积习的症候。”这样“新旧并存”的文学思想,充分体现沈从文积极靠拢政治形势的倾向。而从“精神病院”到“博物馆”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忽略了沈从文的这一微妙的思想嬗变。归其缘由,除了文化视角的差异与文献资料的不足外,当源于作者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所致。
五、結语
承续夏志清、金介甫等老一辈汉学家,新世纪美国沈从文研究不断发展、深化。在城乡书写研究方面,美国学者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沈从文作品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同时在研究路径上有所创新。在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美国学者拓宽了沈从文平行研究的视角,同时注重沈从文的苗族作家身份,能够对沈从文作品的“异域文化”色彩作出较为总体、全面的探究。在作品英译的反思批评与翻译史考察方面,作为译者本人的美国学者不仅对其本人译本进行再审视,而且通过梳理沈从文作品的翻译史,以接受者身份对沈从文作品英译进行细致分析。在社会变革时期沈从文思想研究方面,美国学者以“他者”视角审视中国社会变革中的沈从文思想突变,虽不乏因意识形态偏见而导致的偏颇结论,但由于异质文化带来的学术互补,仍对国内沈从文思想研究不无裨益。
总体看,新世纪美国学界的沈从文研究与国内研究具有相似性。首先是研究领域的贴合,其次是对于共同话题的重视,最后则是对沈从文保持高度评价的一致性。但同时,美国的沈从文研究也具有较强的特异性。第一,美国学者将沈从文作为表现“异质文化”的代表性作家进行考察,这使得他们对沈从文的研究视角更为新颖。第二,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美国学者往往在相同话题中,采用迥异于国内学界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对沈从文进行审视。第三,由于意识形态环境的差异,美国学者以异于国内学者的立场进行探究,使得某些结论和国内研究大相径庭。尽管与国内研究相似,新世纪美国学界的沈从文研究还存在某些弊端,但不同的研究思路、方法与结论,仍能带给国内研究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