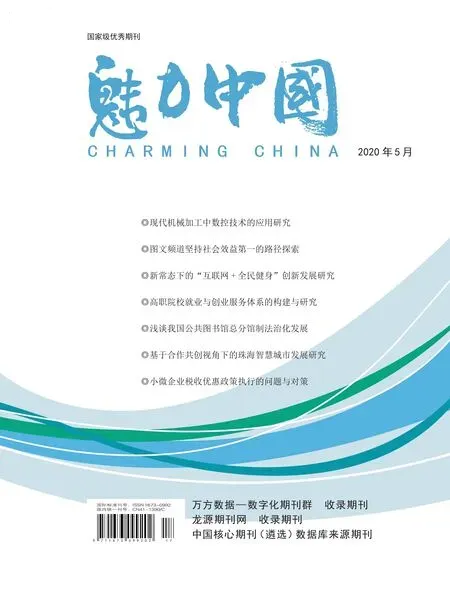去而复返:托尔金作品的旅途主题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J.R.R.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的中洲系列作品肇始于给无法入睡的孩子们讲的睡前故事,从枕边故事《罗佛兰登》(Roverandom)开始,慢慢地有了后来的开山之作:《霍比特人》(The Hobbit)。[1]《霍比特人》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为了适应儿童的阅读体验,而设计的以旅途为叙述载体的故事样式。这其实是西方近代儿童冒险故事的一般范式,既方便于作者借助旅途本身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2]而不断修正人物和情节,也因为旅途的未知性而提供了想象力腾飞的土壤。事实上,《霍比特人》又名《去而复返》(There and Back Again),来源于撰写者也是冒险者的比尔博·巴金斯(Bilbo Baggins)的《西界红皮书》(Red Book of Westmarch)。[3]从这个译名,可以清晰地看出托尔金旅途主题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构建了一种“去而复返”的模式。这种模式同样暗含于之后主题更为宏大的《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和《精灵宝钻》(The Silmarillion)中,但随着作者创作的深入,它的一些特点又有了新的变化。
一、《霍比特人》:双重性和三要素
不论是比尔博还是《魔戒》中的弗罗多(Frodo),他们的旅途都伴随着地理上的和精神上的双重性变化。地理包含时空变化,而精神则更多意味着思想的改变和品质的培养。勒诺·莱特(J.Leonore Wright)就托尔金的旅途主题归纳了三个特点:走出洞穴之旅、通向内心之旅、朝圣者和向导[4],这其实就对应了三个要素:走出去(时空)、走进去(成长)和外力(导师)。在《霍比特人》中,则是比尔博走出夏尔(Shire),在甘道夫(Gandalf)的指导下,前往孤山探险,并战胜恐惧,在勇敢中顺利完成任务的故事。不论是《精灵宝钻》中贝伦(Beren)与露西恩(Lúthien)的故事,还是《未完的传说》(Unfinished Tales)中塔尔-阿勒达瑞安(Tar-Aldarion)的航行,在某些方面上都契合着这种“双重性”的成长元素。但比较这些作品,其实是可以看出一种内在脉络的延伸和拓展的。比如《魔戒》的旅途是以摧毁至尊戒为中心的,它同样具备着三要素以及双重性,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在二重性之中又因为“双塔殊途”即任务的分离而成就了新的叙述形式。
弗罗多一线的旅途,是抱着必死信念的前进。对于他和山姆(Sam)来说,每向前一步,就是在承受着魔戒欲望重压下加倍的精神摧残,这时候,地理上的变化与精神上的成长是一种紧密联系的状态,而不是像比尔博那样,呈现出一种事后“成长”的情貌。二者互为导师,如同朝圣者那般,承受的更多是旅途的摧残而非成长。而其他护戒者一线的旅途则围绕着如何尽可能地吸引索隆(Sauron)的目光,挫败他的计谋,以求遥远地呼应弗罗多,提高完成主任务的可能。这时候他们的旅途则以地理上的变化为主导,在不同的事件中由不同的导师指引而获得成长。比如在树须(Treebeard)的指导下,梅里(Merry)和皮平(Pippin)重新唤醒了守卫绿色家园的本心;在洛汗(Rohan)驰援和米那斯提力斯(Minas Tirith)保卫战中,“带来的正是勇气,还有希望”[5]。
二、《魔戒》:善恶对峙的多线纠葛
《霍比特人》的故事设定在“精灵的黄昏与人类的崛起之间”的时代,而《魔戒》在于“创造人类心灵的镜子”。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托尔金创作思想的深化,这一方面是从童话到哲学、古语言文化等多要素杂糅故事的转变,一方面是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使然。可从根本上说,《魔戒》无非是霍比特人对旅途主题的又一次重复,只是这次的主题更为宏大,牵扯到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种族命运。这虽然在大背景上强化了上文所述的双重性的影响,比如相较之下更凸现出弗罗多“马上就奔出门,再一路奔下小径,帽子也不戴”的果敢的难能可贵,但同时也很自然地因着牵涉到了更多的文学形象而构筑了叙述上的独特之处。
在双重性之中,作为虔诚基督徒的托尔金的传统“善恶观”在不自觉中为旅途埋下了另一端的双重性。通常认为,自波洛米尔(Boromir)战死后,魔戒之旅便被拆分成双线殊途,后文也都依照着这样来分开叙述,一直到魔戒摧毁后才合并了故事线。可实际上,从护戒同盟的视角来看,旅途自然带有着他们的双重性,即使是殊途后也保持着相似性,但这只是“善”的一端。当牵涉到了“最接近于极恶”[9]的索隆以及其他种族时,这种单纯的双线结构是不足以支撑宏大史诗的叙述的。比如,象征着自由种族联盟的埃尔隆德(Elrond)会议的召开之时,艾森加德(Isengard)的萨茹曼(Saruman)和魔多(Mordor)的索隆都各自酝酿着他们的邪恶计划;他们的旅途通过一系列附庸如戒灵和奥克进行延伸,这种旅途并不能带给实际前行者实在的“成长”,但却给予了邪恶头目看清中洲形势的途径。“旅途”本就是中性词,当“善”的一端在成长时,“恶”的一方也通过一种时空上的跨越和精神的操纵压制着一切反抗的强力。所以,在这种多线纠葛中,才能够承载诸如“昏庸”的洛汗王的奋起[10]和“明智”的刚铎(Gondor)宰相的消沉的精彩表演。诚然,托尔金仍然是以护戒同盟的双线为主要结构的,否则他也不会“答应过要写附录”[11]来补足多方视角下仍不够具体的其他故事。可这也是托尔金重建失落已久的如同荷马的《奥德赛》和维吉尔的《埃涅伊德》的秩序与崇高的情怀与艺术自觉。[12]
三、《精灵宝钻》:去而复返的非环形模式
霍比特人去而复返的信念毕竟是出于对家乡“绿树荫下或阳光里闪烁的小溪、小河或泉源”[13]的美好的热爱,而且还蕴含了一种无上的友谊。比如护戒同盟中因着旅途而成就的精灵莱戈拉斯和矮人吉姆利的情谊[14],就很可能是现实中托尔金友谊缺失的文学映射。因为战争而失去了早年T.C.B.S.茶会的几位亲密的朋友,托尔金被语文学冲淡了的对幻想故事的真正喜好“很快又被战争启动了”。但世上还有伊迪斯[15],藉由这份曾经因为监护人不允许的爱情,托尔金在《精灵宝钻》中又创造出了“去而复返”的新形式。三大远古传说,尤其以《贝伦与露西恩》为代表,以爱情而非友谊成为了旅途归家信念的凝聚点。但不仅如此,现实中的哲学思潮也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创作。
这种坚信自己一定能够归乡的信念体现在20 世纪存在主义和基督神学的殊途同归上,哲学家萨特(Sartre)“认为人被抛入荒诞的世界而不得不作出选择时人不可逃避的责任”[16]和托尔金的创作思想“当他回望那命运的深渊时,他必和古代英雄一样感受到不可逆转的毁灭的悲剧,同时由于和那种绝望远隔着时空,他也必能更诗意地体会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可这种“归乡”在《精灵宝钻》中又得到了升华,不单是霍比特人的地理归乡,更是精神上的归乡。比如,贝伦与露西恩以爱情为故乡,定居在欧西瑞安德(Ossiriand)而再未回到地理上的故乡多瑞亚斯(Doriath)。这意味着“去而复返”的“返”又开辟了一条新路,使得该模式并不是一个环形结构,它会因着故事的主题而升华,引导读者前往更深层次的思索。正如我们无法否认流浪的图林·图伦拔终其一生都没有回到他的故乡,但他始终与被诅咒的命运抗争的旅途,正反反复复地通过锤炼他的灵魂指向了悲剧英雄性质的结局。在一生的对手格劳龙的尸体旁死去[19],难道无法充分体现托尔金这种非环形的去而复返模式的艺术冲击和震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