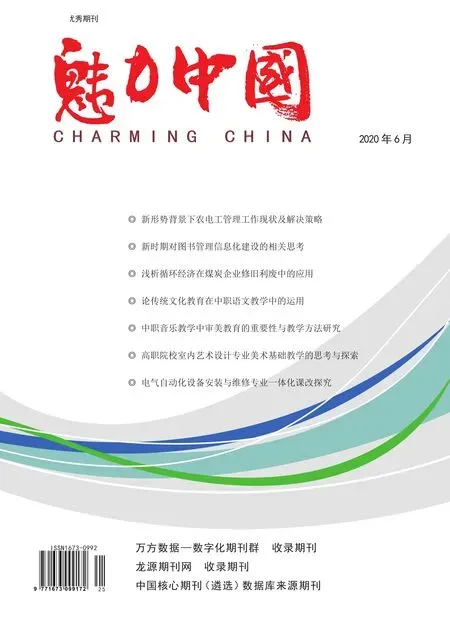在虚实相融的舞台空间再塑情感真实
——观《国家的孩子》有感
(北京舞蹈学院研究生部,北京 100081)
2018年12月12日,由中国文联、中国舞协、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共同主办的“蓝蓝的天空——中国舞协‘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原创内蒙古题材舞蹈作品展演”在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剧场举办。该晚会中佳作频出,从多角度、多题材出发,对蒙古族人民在草原上的生活容貌、精神面貌、情感风貌进行了艺术化表达。
在展演中《国家的孩子》这个作品从国家和个人的角度出发,描写了3000名上海孤儿因自然灾害而寄养在内蒙古人民家中。孤儿们和新父母的感情由开始的“生硬别扭”到后来的“水乳交融”再到分离时的“肝肠寸断”,三个阶段的情感递进和升华十分流畅,不着痕迹。编导吕梓民完整地建构了一个叙事清晰、情感饱满的作品,为现实主义舞蹈作品的创作树立了一个标杆。
《国家的孩子》总时长12分钟,虽然是一个群舞剧目,但是体量与传统群舞相比已是大出了一倍有余。舞蹈故事的发生背景和重大转折是通过旁白念出,让观众清楚剧情的进展,舞蹈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共同参与完成了情节的推进和情感的转换。作品的成功一方面借力于题材的优势,“内蒙古草原牧民抚养内地孤儿”是历史真实事件,该事件作为“一方有难、八方来援”的典型范例牵动着一代国民的爱国情怀,事件内含的民族团结意味也使题材的受众更加地广泛,十分适合舞蹈的编排。另一方面,创作者对题材的选择十分重要,但对于题材的理解和最终选择的编排方式则更加重要。舞蹈创作“重要的不是说了什么,而是怎么去说”是公认的一个道理,一个优秀的题材同样需要独特的角度和灵活运用的创作手段去保证作品最终的成功。笔者认为《国家的孩子》这个作品中至少出现了如下三个令人欣喜的创作现象:
一、蒙太奇式的舞台时空交替
蒙太奇是法文“Montag”的译音,原为建筑学术语,意为构成、装配。1在电影艺术中,这一术语被用来指画面、镜头和声音的组织结构方式。用不同方式连接起来的镜头,会被赋予在原先镜头中没有的全新含义,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爱森斯坦认为,将对列镜头衔接在一起时,其效果“不是两数之和,而是两数之积”。凭借蒙太奇的作用,电影享有时空的极大自由,甚至可以构成与实际生活中的时间空间并不一致的电影时间和电影空间。回到舞蹈上来,《国家的孩子》历史跨度大、人物角色多、心理变化明显,如能较好地运用蒙太奇手法到创作中,会极其加大舞蹈结构的复杂性和可看性。编导吕梓民运用蒙太奇的方式重构了时间和空间,在舞台上通过焦点转移的方式切割出了过去时间和当下时间、现实空间和想象空间两对舞台时空交替发挥叙事作用,引导情感走向。
在舞蹈的第一个画面,画外音交代了故事背景:“上世纪60年代,我国连续三年三年自然灾害,内蒙古人民将上海市的3000名营养不良的孤儿转运到草原牧民的家中,草原牧民们用乳汁养大了这3000名孤儿。“我”刚到草原那年,只有7岁。)文中叙述较简略)这段画外音告知了叙事的三要素,时间是上世纪60年代,地点是内蒙古草原,人物是在一群从上海孤儿院来到内蒙古新家的孤儿中的“我”。清晰的设定为接下来的蒙太奇的时空转换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画外音还点出“我”的年龄是七岁,这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提供了更直接的引子——孩子适应环境的问题。
画外音过后,舞台前区淡黄色灯光亮起,一辆勒勒车和一个中年男人在舞台前区,(有画外音之前的铺垫,观众自然联想到这是故事里的“我”)“我”擦擦眼镜、整理下衣服,微蹙双眼视线飘向远方,而后缓缓坐下。勒勒车向舞台后方驶去,将“我”拉入了过去的时空。从后方涌上来背对的人群将向后隐去的“我”吞没,进行了一次视觉画面的交换,这样的蒙太奇式处理也流畅地完成了一次时空转换,同时也产生了新的语义:回忆的思潮翻涌上来将“我”吞噬。除了节目开始的舞台处理外,过去时间和当下时间的交集在节目中出现了数次。在第二次画外音后(画外音告知,随着一封寻亲信的到来,额吉(蒙语“妈妈”的音译)把“我”从草原又送回了上海),当下的“我”不停在少年的“我”和额吉的身边留恋徘徊,却始终无法插入二者在过去时空中的依依道别。当下的“我”与额吉的共舞动作始终都是追着额吉,额吉却无法感知。在少年的“我”表现出的懵懂无知的反应中,当下的“我”表现得却是动情至深地追忆和呼唤。这表明经过了这么多年,当下的“我”对于从额吉身边的分别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儿时是回上海老家的欣喜,现在是对额吉再难触及的怀念。两种心情交相辉映之中生成了一种全新的语义:时光流逝给“我”带来的心理划痕。《国家的孩子》中这两例成功的时空交替归功于开始时的画外音的交代和蒙太奇手法的运用,这让观众清楚,当下的“我”是这个故事的局外人,当下的“我”始终是一个看客而无法改变过往中的一草一木。
如果说过去时间和当下时间的切换给节目添上了无法触及带来的感伤,那么现实空间和想象空间的交叠则给舞台增加了几分浪漫梦幻的气质。节目开始时“我”坐着勒勒车退入舞台后区的黑暗之中,勒勒车再次扛着当下的“我”出现时是3分30秒左右,在这之表现的是草原牧民对即将到来的孩子们的期盼之情和孩子们初次见到牧民的紧张、恐惧和抵触的情绪,接下来要展现的是孩子逐渐接受牧民成为他们的新父母的情景。当牧民和孩子从定点散开后,舞台灯光第一次缓慢地全场铺亮。勒勒车环绕舞台最外沿走圈,牧民和孩子在偏舞台中间的位置舞蹈。当下的“我”的视线虽然一直没有往舞台里看,但是观众从整体的舞台观感能明显感觉到,当下的“我”望的是在脑海中不断上演的过去的故事。透过剧情,此时的“我”是在故地重游吗,这或许不得而知,但是蒙太奇效应的新语义已经产生:看似表面风平浪静的“我”,仍会对过去的日子心潮澎湃。类似的想象空间和现实空间的对话在节目中不止一处。在4分40秒左右,牧民们抱成一个大圆,将上海孤儿包裹在圈中用爱融化孩子初来的不适。当下的“我”和少年的“我”贴地滑行从圈中溜出,两个“我”做着一样的动作,当下的“我”体会着自己当年的心情,又有一丝看着孩童时自己的惊奇和欣喜。现实空间与心理空间在这里的碰撞十分明显,一方是现实世界中回顾的“我”,一方是想象的记忆空间中体验的“我”。二者的交汇碰撞出的“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作为新的语义赋予作品更高的升华。
从整个作品的舞台时空性质把握,从人物的虚与实的角度来说,只有当下的“我”是真实存在,其他所有的人都只是“我”想象中的画面重现,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它们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无论“我”怎样地改变也终是不能改变。除“我”之外,那辆永不停止的勒勒车也是一个独立于“我”记忆以外的存在,它不仅是当年带我离开草原的那辆手拉车,更是象征着循环往复、从未停止的时间,成为了不停向前的时间的具象表现。
蒙太奇手法被运用在在《国家的孩子》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主义题材舞蹈作品中,舞蹈叙事的多重意味是其效果之一,结合背景的画外音后,效果之二是促成了大历史和小人物的碰撞,历史洪流与个人命运的对话,“宏大叙事”和“私人叙事”的混合。前者和后者体量上的强烈不对等让“我”的故事充满了时代视角下的不可逆性,又回荡着个人视角下的温情。
二、赋予蒙古族语汇叙事意义
在《国家的孩子》中,蒙古族舞蹈语汇是主要的叙事动作语汇,所以蒙古族风格是弥漫在整个作品之中的。草原牧民的动作始终在蒙古族舞蹈语汇的大框架中,只有一个大部分跳的不是蒙古族语汇的是当下的“我”,但这也可以理解为,当“我”身上的草原风韵和情怀不再时,“我”如何来看待这段过往。
舞台上的民族舞作品总会遇到动作语汇的风格性问题,这关系着作品最终能否被市场认为是一个合格的民族舞蹈作品。这里借用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系以许淑媖为首的教员们创立的“元素教学法”的相关理论,每个民族的舞蹈中都有“根元素”的存在,在教材建立之初就以“根元素”为起点衍生新的符合“根元素”运动规律的动作。再往后,这也成为了民族民间舞的创作基本要求之一,因为从既定的动律元素下的再发生新动作,人们会从心理上产生一种熟悉感,会让观众认同作品仍属于民族民间舞的范畴。
我们看到,在剧目中无论是翘首期盼的草原牧民耸动的双肩营造出的拥挤场面,或是草原牧民用博大胸怀温暖内地孤儿,还是孩子们从内心认可新家庭时欢快地在草原上飞驰,运用的都是明显包含“圆韵”、“八字”、“马步”、“揉臂”等元素的蒙古族动作语汇。
起码在四段舞蹈中,蒙古族舞蹈语汇明显得不再只是欢快的风格展示,而是承担了特定的叙事功能。最为精妙的是开头的硬肩运用,通过硬肩动律地不断变化模仿了人与人之间肩膀的交错,生动地表现了站台上人头攒动、翘首企盼的状态。通过重拍、暂停等节奏的运用,高低、位移等空间的变化,让简单的硬肩动作有了特定的叙事意义。最为传神的是8分20秒开始额吉的独舞,运用蒙古舞柔臂、硬腕等元素将挽留、依恋、缠绵的情绪表达出来,这是对即将离去的“我”最放心不下的眷恋。最为意象化表达的是9分30秒开始,额吉将少年的“我”送上归乡的勒勒车,这一刻无论是当下的“我”还是少年的“我”都有着无法言说的悲痛,后方的群舞成飞行的大雁状左右摇荡,大雁又代表一种四处迁移的特质,“我”和额吉如同分飞的大雁,柔臂动作的韧劲将“我”心头难以割舍、如影随形、数十年过去却更深入骨髓的离别之愁物态呈现出来。最为隐秘的是,纵观整个舞蹈,和表现孤儿们初来乍到时的恐慌和紧张运用的一下一顿、收缩紧绷的动作质感相比,6分40秒开始的蒙古族舞蹈动律的大气欢快和洒脱显得和谐美满,蒙族动律拥有了象征孩子们和内蒙父母之间亲密无间、水乳交融关系的能力。
三、群像塑造与个人刻画
在国家的命运、群体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被摆到一起时,个人如同被投向大海的石头一样渺小,只能被时代的巨浪裹挟着前行。这类题材的作品聚焦在大历史背景和小人物之上,突出了矛盾双方的力量悬殊,加强了悲情的效果。不仅是在舞蹈中,在其他的艺术门类中我们也经常看到,在大时代的背景下选取一个最为平凡的普通人作为叙述视角,通过小人物感受到的造化命运的无常和个人力量的渺小来体现个人对于历史洪流的难以抗拒,最后只能留下一声叹息。以小见大也是在舞蹈刻画人物的方法,编导一方面通过群像塑造营造氛围,更重要一方面通过个人心理描写强化感受。在这种双管齐下的模式下,《国家的孩子》成功地塑造了有血有肉的群体和活泼生动的个体。
在刚开始时,当下的“我”坐上勒勒车向后方隐去,是给后面“我”的出现埋下一个伏笔,也是隐约地传递给观众之后的画面皆是回忆的感觉。往后一直到孩子和牧民的关系缓和之前,剧目一直在做群体形象的刻画——一群初来乍到,倍感不适的孩童,一群热情备至,爱娃心切的内蒙牧民。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元素和队形调度交代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且都塑造了较为饱满的人物形象。从4分40秒融合开始,两个“我”从其他人围成的圈中滑出,这时“我”的心中铁门被逐渐打开的心理感受不光是“我自己”的,也是所有孩子的,“我”是所有孩子的一个横截面视角。舞台上其他人和“我”之间一静一动形成对比,表现焦点从丰匀的群体形象切换到细腻的个体形象塑造上来。在内蒙父母用爱打开孩子心中铁门的表现中,没有用大群舞表现双方的交融,而是用更加微观的一对母子来涵盖3000对母子之间的磨合,这样从场面上来说避免了杂和乱的局面,从结构上来说又进一步交代了人物关系以及树立了鲜明的“我”的形象。
第二次群体形象和个体形象的的交叉刻画是在5分40秒,重心在刻画“我”的额吉上。在牧民和孩子合成一圈后,额吉来到圆心,表现焦点从孩子和牧民之间日益融洽的氛围切换到额吉为养活“我”进行辛勤劳作上,额吉轻抚土地、挤着牛奶、提起水桶,在辛苦劳作之余仍给少年的想家的“我”最大的陪伴和温暖。通过这样的编排,展现了“我”的额吉的两个闪光点,一个是她朴实无华地热爱劳动,一个是她对待少年的“我”充满了温情和关怀,丰满了人物的立体程度。
我们发现,在群像的塑造中,舞台表现焦点不失时机地切入到微观的个人视角可以帮助塑造个人形象,推动情感的升华,用群体的情感打动观众,用个体的情感融化观众。
结语:
《国家的孩子》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的舞蹈作品。不同于通常小作品的主要抒情辅带叙事的常态,《国家的孩子》使用外部事件刺激内心情感,再用内心情感去推动外部事件发展,两项并举且做的十分流畅,同时在多重叙述时空的切换中不显混乱。应该说,叙事手段多样、运用媒介大胆、使用技法娴熟,这三点是该作品成功地叙事与宣情的重要原因。能有如此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舞蹈作品出现,也拓宽了舞蹈创作的思路。我们的叙事小作品创作不论是从叙事手段(画外音)、叙事方法(蒙太奇)都可以更加大胆,借鉴其他门类艺术的优秀成果。更重要的是,在舞蹈擅长叙事还是抒情的问题上,不可怀有“长于抒情”刻板印象,不去尝试成功叙事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