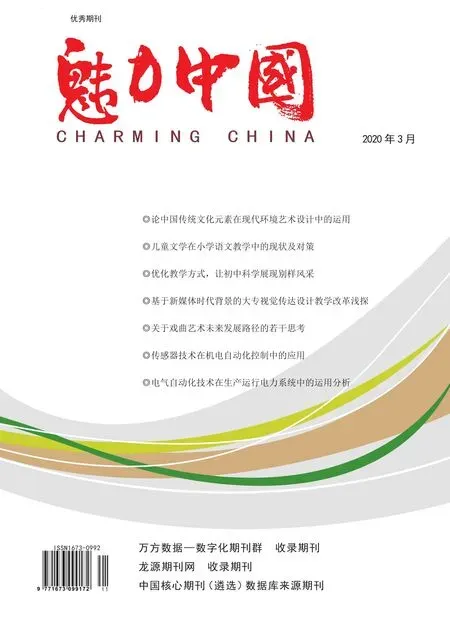杨简“意”论浅析
金天彪
(西北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目前,学术界对杨简“意”概念的研究结果并没有达成共同的认识。崔大华说,意是违背伦理的意念;郑晓红、李承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分辨和区别;陈来先生认为,意是一般的私心杂念,更以指深层的意向状态;张实龙认为,意是一种违逆生命之流的意识;另外,董平认为:“意”是使心灵自体之清明虚灵遭受障蔽的最为根本的非物质力量。以上观点各抒己见,在基于前辈研究的基础之上,本文从本心说和性善论入手,对慈湖先生“意”的理论来源及其独特内涵,做一些拾遗补缺工作。
“意”之理论来源
作为“象山弟子之冠”,杨简继承并发展了陆九渊的“本心说”理论,糅合了儒家的性善论,同时又反对程朱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以“意”动为恶之源,来解释对本心的干扰。因此,“心”与“意”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他提倡“毋意”,以保持“本心之清明、自善、自正”。杨简的“毋意”思想根源来是对孔子“毋意”说的发挥。他的《绝四记》中集中阐述了他对于孔子提出的“毋意”的独特理解,而在《杨氏易传》中,则有对于“毋意”、“不动意”、“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等相关思想的全面阐释。
格去物焉,发明本心
杨简发挥了孟子提出的四端学说,使仁义礼智四德具于心作为基本义理,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规范与本心同体而异名。他说:“此心虚明,光大无际畔,范围天地,发育万物,即道也!”此心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是宇宙本体,万物根源。本心是怎样的状态了?为什么要“格去物焉”呢?杨简认为:“格物之论,论吾心中事耳。吾心本无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则吾心自莹,尘去则鉴自明,滓去则水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之中,十百千万,皆吾心耳,本无物也。”格去心中之物,便使此心自明、自清。事物之纷纷起于虑念之动,所以格物目的就是去除思虑。可以说,格物也是毋意、不起意。这是杨简对其师陆九渊“气有所蒙,物有所蔽,势有所迁,习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于是为愚为不肖”的发展。“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固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仅由与此”,心本是自明自灵、感通无穷的,因“起意”遮蔽了本自光明的心,才变得昏蔽不畅。由此,杨简以“意”蔽我心取代了“物”蔽我心的思想,将人心的昏蔽原因归于“意”。
杨简还说:源泉亦在内之意,谓吾之道心也。道心即意念不动之心也。杨简认为意念不动则为道心,即人之本心;动乎意则为人心,即人欲。由此,意念动与不动,是区别道心与人心的界限所在。“人心自明,人心自灵。意起我立,必固窒塞,始丧其明,始失其灵”,由于“起意”,所以使人心阻塞,丧失了明灵。
“心”、“意”合一
“意”之状态,较为复杂,难以说清,说尽。而心和意又如何辨别?杨简说:“一则为心,二则为意;直则为心,支则为意;通则为心,阻则为意……孟子明心,孔子毋意,毋意则此心明矣。”“至道在心,何必远求。人心自善,自正,自无邪,自广大,自神明,自无所不通。
杨简的“毋意”修养功夫强调无思无为,主张“直心直意,匪合匪离”的修养方法。故《易》曰:“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本心是善的,但常常为“意”所蔽,“心”与“意”的差异在于“直”与“支”。“毋意”就是“直”,起意则“支”。“直心直用”就是依据“本心”顺其而行,便是“毋意”、“不起意”。朱熹解“意”为“心之所发”,王阳明也说“心 之所发便是意”。在杨简那里,“心”是道德伦理原则和宇宙存在的根据,万事万物一切皆从“心”出,“意”也一样。“心”与“意”合一时,由心所发之意便是圆融的,他将此状态称为“直心直用”。因此,杨简反对人们离意求心:“离意求心,未脱乎意。”离开“意”来求“心”是无法做到的,“心”、“意”分离会使得本心受损,此时的“意”便是残缺不美的。
一言以蔽之,心、意合一是其最理想的状态,即直心直用,无思无为。杨简的“不起意”、“无思无为”,并非要人如木石一样,绝对的不为、不思,而是顺应“平常正直之心”而思、而为。因为“人心本清明”,所以顺性而为、而思,就不是动意、起意。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意”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对事物做出评判尺度时的极端之处,是本心的歧出状态; 它会对本心造成误导,但通过“直心直意”和“不起意”的工夫,“意”可以做到与本心合一,回归圆融的状态。欲让本心清明,必须做到“不起意”。后来学者,不断对其阐释,使其内涵更加丰富。如王阳明在杨简的引领下,提出了“四句教”,其中“有善有恶意之动”是认为善恶源自于意;至明末时期,儒学大师蕺山先生对“心”和“意”又给出了全新的解读和诠释,并提出“意为心之所存”的观点。
——兼与朱子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