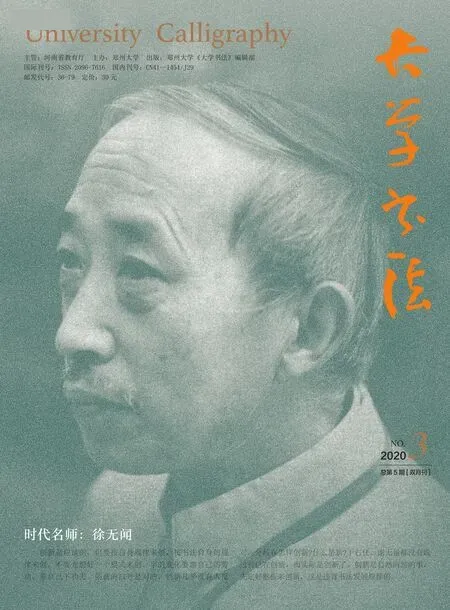浅论馆阁体的是与非——兼论书法艺术的兼容并蓄
⊙ 王永平
馆阁体是清朝官方的指定书体,因其具有用笔丰润饱满、结字平稳匀称、章法整齐均衡、气象雍容华贵等特点,而多用于官方公文、科举考试、牌匾碑额、书籍编撰以及民间墓碑题记等严肃庄重场合,且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时至今日,用该书体书写的各类题记、匾额、碑刻等作品仍然随处可见。然而,近代诸多书法大家却对其否定颇多,认为其“千人一面”“千手雷同”,没有个人风格,甚至是束缚书家个性、阻碍书法艺术自由发展乃至封建礼教压抑人性的罪魁祸首而多予批判和排斥。
为什么一种沿用近三百年的官方指定书体会受到如此极端的评价?为什么诸多书法大家会对一种通用的正体字进行批判否定?尽管近年来不少学者对馆阁体进行研究论述并给予充分肯定[1],但大都侧重于书家或书体艺术特点、历史地位、实用价值或政治作用、书法教育等范畴,对其形成和受到批判的真正原因缺乏深入客观的论述。事物发展从来都具有两面性,书法艺术也不能例外。作为后人,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前人文化遗产的是是非非,妥善处理扬与弃、正与新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当代书法艺术传承的完整性和延续性,更能体现出我们能否摆脱少数书法大家艺术眼光的历史局限性,以一种更为平和、客观、真实的心态看待和把握书法艺术发展规律,从而推动书法艺术走向新的大发展、大繁荣。
一、馆阁体产生的主要原因及异化
作为一种社会通用书体,馆阁体不可能是一天形成的,也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朝廷官府的一纸规定或某个皇帝的个人喜欢就延续下来的。它能延续近三百年,必有其特定历史环境和自然规律。因此,我们讨论馆阁体产生的原因,不能将眼光仅仅局限于馆阁体本身,更应该放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看待。至于其后期出现的一些异化和僵化,则更多地应该从政治干扰和制度体制等方面寻找原因。把书法艺术柔媚内敛、程式化和功利化等问题简单归结到馆阁体对人性或对艺术的约束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客观的。
馆阁体首先是清廷指定的书体,广泛用于官方公文、科举考试、牌匾碑额、书籍编撰等正规严肃场合。官方结合文字发展进程,对书体进行指定或创新的做法可以上溯到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用小篆书写《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作为官方书体来规范文字,“书同文”的做法就一直延续下来。这既是满足官方内部上传下达、维护社会管理秩序的客观需要,更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文化艺术交流的时代要求。篆、隶、楷、行、草五种书体中,楷书因其特有的中和美感和书写特性,逐渐受到官方的高度认可。“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2]因此,自唐楷成熟后,楷书就一直作为官方书体延续下来。唐代“干禄体”、宋代“院体书法”、明代“台阁体”和清代“馆阁体”均指的是这种官方指定或统一沿用的应制书体。
既然是应制书体,其实用功能必然是第一位的,工整规范、易学易辨是最基本和稳定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馆阁体的“千人一面”“千手雷同”,应该是对书写者书法功底的充分肯定。毕竟书家在书写公文布告或参与官方组织的修书编撰时,所代表的不是个人本身,更多的是代表朝廷官方或府衙机构,这个时候要求的“书同文”就不再是同一种文字,而是具体的同一种书体,甚至同一种笔画。特别是几个人联合办公的时候,如果文书里面掺杂过多个人的气息,其行文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就会受到影响,说服力就会大大降低。例如,乾隆皇帝组织编撰的《四库全书》,360多位高官学者参与编撰,3800多人参与抄写,耗时十五年才成书。试想,一部如此巨作,在没有打印机的年代,如果没有严格规范的统一书体,你用颜体,我用柳体,他用赵体,36000余册书籍抄写下来会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编书修史尚且如此,公文奏折、谕旨牌匾等更应如此。
馆阁体也是清朝正体字。“正体代表书法的正统和规范,是明确书法为实用文字之书写艺术的典型式样。”[3]然而,宋朝以后的正体字并不是固定或唯一的,只是在众多官吏日积月累的书写过程中,慢慢形成的一种特点相似、风格相近的书法样式,细微处则随着时代的发展、王朝的更替而出现变化。从宋朝的“了无高韵”“精丽”,到明朝以沈度、沈粲为代表的“端严工整、婉丽遒媚”,再到清朝的“楷法遒美”,即便是在馆阁体盛行的清朝,书体风格也因康熙皇帝崇尚董其昌,乾隆、嘉庆推崇赵孟頫,道光年间多习欧阳修而不同。但总体来说,馆阁体是一种吸收欧体的方正、颜体的丰腴、柳体的匀称、赵体的秀媚而形成的“文备众体”。它点画饱满丰润,结体平稳匀称,章法端严中正,集中体现出了清代众多书家以“中和”为核心的审美趣味和思想。“中也者,无过不及是也。和也者,无乖无戾是也。然中固不可废和,和亦不可离中,如礼节乐和,本然之体也。”[4]由此可见,馆阁体的产生来源于书法大家经典帖学,它的发展凝聚了众多饱学之士的心血努力,它的成熟更是历经历朝历代的实践检验。它不是书法艺术的歪门邪道,不是异域疆土的另类审美,更不可能是扼杀书法艺术繁荣的罪魁祸首。相反,如果说颜、欧、柳赵等书体带有强烈的个人艺术风格,馆阁体则是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和时代审美风格的集体艺术结晶,理应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认可。这一点甚至连尊碑抑帖的标志性代表人物康有为也不得不承认:“其(指清初的馆阁体)配制均停,调和安协,修短合度,轻重中衡。分行布白,纵横合乎阡陌之经,引笔著墨,浓淡灿乎珠玉之彩。缩率更、鲁公于分厘之间,运龙跳虎卧于格式之内,精能工巧,遏越前辈。此一朝之绝诣,先士之化裁。晋、唐以来,无其伦比。”[5]
另一方面,馆阁体不激不厉、平和简精,这种审美风格与其说是“清朝统治者以政治手段介入书法领域,将承载着正宗、正统意识的馆阁体确定为官方正体书法”,[6]不如说是儒家“中庸”思想在正体书法上的具体体现。馆阁体的创造者和引领者本身就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捍卫者,甚至是当代的集大成者,三纲五常、家规道义等儒家伦理在他们身上随处可见。在工作所需、皇帝推崇和主动审美的作用下,要求楷书讲究字形方正、点画丰满、结体匀称、整齐有序更是理所当然。由此来看,在馆阁体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王朝统治者推波助澜的作用固然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以翰林院和文人士子为代表的清代书家群体的审美观念。这也合理地解释了为什么有众多的文人士子在考取功名、公文业务之外投入大量甚至毕生的精力进行馆阁体的研习。如果单纯以功利、统治说,研习者不能从中获得美感和心理满足,则难以自圆其说,清朝宫殿楼宇所留下来的牌匾碑额更不会受到平民大众的热烈欢迎。
尽管近年来,不少有识之士从繁荣书法艺术、推动书法教育大发展等角度为馆阁体进行辩解,但一方面人微言轻,起不了多大作用,另一方面,数量不够,还没有真正形成有效的突破。即便这些关注馆阁体的人,也有不少是人云亦云或多是从封建统治、皇权思想、馆阁体对艺术的压制方面进行论述。其实,早在1996年徐文达先生就在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馆阁体探源》一文,对馆阁体的真正来源进行了说明,但遗憾的是,相关论点并没有引起书法界的真正重视。
关于馆阁体的异化与僵化,诸多文献都有论述,也是诸多批判者否定馆阁体的焦点论据。从功利角度讲,无非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喜欢导致众多学子纷纷效仿;科举考试以字迹书写为判定标准,导致众多士子深受所限;朝廷公文以书写作为赏罚依据,导致一众官员不务正业;官办书院以馆阁体为唯一书学内容和考核标准,导致异化、僵化蔓延流传。归纳起来就是馆阁体承担了不该承担也承担不起的责任。馆阁体原本是一种书写形式,体现的是一种写字规矩,不应该成为其他事由的标准,更不应该成为科举考试、政务处理等事关个人前途命运、国家安定繁荣的唯一标准。至于馆阁体异化、僵化的真正原因:一是制度僵化,二是皇帝懒惰,三是官员推责,四是程式固定。具体表现则无非是技法章法和布局的单调平庸,精致做作,个人的书法灵动美或多或少受到限制。但即便在无意展示个人书写风格的清人写本《四库全书》里,我们仍可以轻松地分辨出不同的书写者来。一方面是因为每个书写者的工整程度不同;更重要的是字如其人,每个人的字迹只能相似,不可能完全一样。共性中蕴含着个性,个性在服从共性的基础上,或似颜、柳,或近欧、赵,使人在阅览典籍之余也能欣赏书法的“筋道”“柔媚”之美,令人心旷神怡。
二、否定馆阁体的原因及人员类别区分
从上文可以看出,馆阁体是清朝乃至明朝、宋朝书家群体或主流阶层的主动选择,也是正体书法的延续和深化。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众多书法家甚至书法大家对馆阁体进行极力否定和批判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从书法艺术的角度发表个人对馆阁体的看法。典型者如洪亮吉和周星莲。洪亮吉曾云:“今楷书之匀圆丰满者,谓之‘馆阁体’,类皆千手雷同。乾隆中叶后,四库馆开,而其风益盛。然此体唐、宋已有之。”[7]周星莲也评论说:“自帖括之习成,字法遂别为一体,土龙木偶,毫无意趣。”[8]这两个评论也多成为后人批判馆阁体的利器。可经认真推敲之后,我们可以发现,洪亮吉的言论是在肯定馆阁体的“匀圆丰满”的同时,从艺术的角度对馆阁体众人雷同、古已有之的现象进行批判。艺术当然讲究开拓创新,讲究独具一格,讲究令人耳目一新,但对实用为主、规矩第一的馆阁体过分强调艺术气息似乎有点强人所难。至于周星莲的“土龙木偶,毫无意趣”则是一家见解。近代书法大家欧阳中石还曾评论馆阁体说:“从‘尚法’这一点来看,立标准、定要求、教有序、学有法,把艺术的要求用比较严格、比较合理的办法规定下来,这是一种建树。”“所以对‘馆阁体’不能轻率地否定。”[9]对同一事物发表不同看法也是学术界值得提倡的事情。
(二)借批判馆阁体表达其他诉求。一是把批判馆阁体作为反抗官方统治的工具。这类主要集中在清初和清末。典型者如傅山和康有为。傅山被人尊为“清初第一写家”。说他是批判馆阁体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提出的“四宁四毋”理论成为后世反对帖学、摆脱馆阁的主要理论依据,对后世的书法实践影响可谓甚远。但综合分析后我们就会发现,他这个说法其实是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和个人动机的。傅山生性清高倔强,以与清政府不合作而著称于世,并对那些投靠清廷的汉人极其厌恶、痛恨。正因如此,在评论前代书法家时,他因为颜真卿的气节而肯定其书法艺术价值,也因为赵孟頫的人格而否定其艺术造诣水平。“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能补。”[10]他贬低一切主流思潮,从赵孟頫到董其昌期间的书法复古潮流更是被他贬得一无是处。因此,当董其昌提出“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的书论后,傅山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四宁四毋”的说法。“四宁四毋”与其说是傅山的一种书论,不如说是他对董其昌的人品和当时书法潮流,乃至朝廷楷模的一种反抗。尽管如此,傅山在晚年时对赵孟頫的书法艺术水平给予了充分肯定:“秉烛起长叹,奇人想断肠。赵厮真足异,管婢亦非常。醉岂酒犹酒,老来狂更狂。斫轮余一笔,何处发文章。”[11]只是这些没有引起后人的重视和反思罢了。康有为是晚清著名的书论家,也是清朝碑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关于馆阁体他不仅没有完全反对,还对馆阁体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见前文),并对如何写好馆阁体提出了看法。说他是批判馆阁体的代表人物,是因为他批判的是包含馆阁体在内的帖学。“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物极必反,天理固然。”[12]且不论《广艺舟双楫》中存在的自身矛盾的地方,但就该书著作的起因及背景就可以理解康有为尊碑抑帖的主要原因。对此,刘恒评论说:“他(康有为)撰写《广艺舟双楫》时,正是向皇帝上书不达、政治抱负遭受挫折的时候,思想极其苦恼,研究书法只是为了排遣郁闷、陶冶心情,因此,不可避免地将其欲革除旧制、变法图新的开宗立派思想寄托于其中。”[13]
二是把批判馆阁体作为排遣仕途失意的途径。这类人主要集中在清朝中末期,也就是馆阁体异化之后的一段时间。“盖有清三百年,名士以不能作楷书湮没终身者,不可胜道也。”[14]典型者如龚自珍。论学问、见识、才情和抱负,龚自珍都能排在众多科举中榜士子的前列,却因“不知馆阁体为何物”,历经六次会试后才中进士。殿试时也因写不好馆阁体仅列三甲,未能入翰林院。压抑悲愤之余龚自珍著《干禄新书》专门讲如何写馆阁体,其中有云:“客有言及某翰林者,定盦必哂曰:‘今日之翰林,犹足道耶?吾家妇人无一不可入翰林者。以其工书法也。’”[15]尽显其对馆阁体的鄙视和痛恨之情。也正因如此,龚自珍喊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著名诗句。文人士子能够高中榜首因而达官显贵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穷其一生而寂寂无名。他们多年努力却迟迟未能中榜,内心难免愤愤不平,便在诗文著作中发发牢骚,骂科举制度,骂八股文,骂馆阁体。特别是那些有志之士,屡次因书写这种“末艺”受挫,以至经世文章无人赏识,满腹才华无处施展,才华抱负远不如自己,甚至有些是自己瞧不起的“小人”却因此步步高升,其内心的郁闷彷徨可想而知。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他们痛苦之余,只好把批判馆阁体作为最重要的发泄途径,馆阁体就承担了更多的指责。
三是把批判馆阁体作为民族振兴的手段。这类人主要集中在近代。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老百姓的冷漠贫困,外加西方殖民者侵略破坏,使得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开始寻找国家救亡图存的途径。经过不断尝试和反思,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国家落后是因为旧的传统文化在作祟。要想图强,就必须把禁锢民众思想的八股文、馆阁体和汉字等封建流毒清理干净。因此,经过数次的文化运动和政治变革,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真正国学从此逐渐走向灭亡,书法艺术也逐步走向了低谷,馆阁体与八股文更是彻底成为带有贬义的特定词汇。
此外,还有一些不懂书法或从没有真正读过书法史的人,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盲目地对馆阁体进行批判。此类人员未提出鲜明的论述,在此不做讨论。
三、我们对待馆阁体应有的态度
馆阁体距今已有一百多年,遗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清朝因其异化对书法艺术发展所带来的约束,更多的是其雍容华贵的艺术内涵和平静典雅的艺术气息。过分地谴责与拒绝,既不能彰显当代书法艺术和艺术家的博大胸怀,更不利于书法艺术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在书法实用性功能几乎丧失的今天,我们对待馆阁体,更应该从丰富书法文化、传承书法精神的角度去正视、去接纳、去借鉴。
正视,就是要正确认识馆阁体的形成原因、艺术价值和历史作用,不要盲目排斥贬低,更不能动辄言封建压迫或皇权统治。只盯弱点而看不到优点,就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书法本身兼具实用与艺术两个方面:实用性强,艺术性就弱;艺术性强,实用性就弱。只有将两者完美结合起来的才能算作上乘之作。行书中的《祭侄文稿》《兰亭序》《黄州寒食诗帖》是如此,楷书中的《宣示表》《荐季直表》《近奉帖》更是如此。作为实用性第一的应制书体,过多地要求馆阁体具备鲜明的个人艺术风格和艺术品位,既不合理,更难承重。正如丛文俊先生所说:“应制之作明确地体现儒家经世致用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有书法之所以成为实用艺术的特质和消极影响,没有理由去苛求古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种种消极的书法现象,其始未必如是,后来的变迁也不能代表初衷,鱼龙混杂,不能一概而论。”[16]
接纳,就是要开展对馆阁体的研究和传承,并将其纳入当代的书法文化当中。艺术根植于大众。全面否定馆阁体既不能保持与普通大众的审美相一致,更不能彰显书家审美趣味的格调高雅。馆阁体能够风靡一时、传承百年,除满足了政令畅通、社会交流的实用需求外,更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主流审美趋向。与其让其束之高阁,不如进行系统的梳理研究,惩恶扬善,去伪存真,将其中的优秀传统部分加以传承延续、发扬光大,糟粕的则弃之不用。对于所谓的馆阁体对书法艺术的限制,我们则更应该正确对待。正体本来讲究法度,“先正书而后行草”的做法更是已延续千年,如果这个约束或限制有众人想象的那么大,那么从“唐人工楷法”开始,宋、元、明、清等朝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书法大家出现。至于说历代正体名家少、建树少,则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自王羲之大统以来,颜、褚、欧、赵、董等大家对楷书则继续完善,后代书家均以此为楷模进行学习,能够在前人法度基础上取得突破的人更是少之又少;二是书写者众,能够在芸芸众生中不受社会风气和统治阶层的审美观影响,长期坚持自己风格的大师本来就少。相反,清朝但凡有所成就的书法大师,绝大多数都有馆阁体的深厚根基,典型者如康有为。因此,将“约束”和“限制”等这样的词汇单单用于描述馆阁体,明显带有不客观色彩。
借鉴,就是要学习馆阁体普及过程中的一些优秀成果和成功做法为时代所用,以此推动书法艺术的大繁荣、大发展。清朝历来重视书法教育,皇帝提倡,书院众多,模式成熟。特别是书法基础教育,“在为数众多的清代书法论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书法教育的内容。其中有些是写给子孙或学生的教材,有些则是书家自己学书经验的记录,还有一些是汇集前人有关书法学习方法的文字,供学书者取法借鉴。”[17]不可否认,清代书院教育是以科举制度和馆阁体为最终目标,在视野和做法上有不少局限性,但因此而对其做法进行全面否定或弃之不用,则有过火之嫌。另一方面,书法不是少数人玩的文字游戏,更不应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经过近百年的低谷后,特别是受当代硬笔书写和电脑打字等因素冲击,书法艺术群众基础较为薄弱,主动拿起毛笔练习写字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针对学习者书法基础薄弱,总结工楷经验、推广规范做法、扩大书法影响,短期内提高书写者用毛笔书写汉字的水平又有何不可?时代发展到今天,传统国学正逐步重新受到大众的欢迎,八股文也已列入部分小学语文教材,我们却仍然只看到缺点而对其大力批判,不免有小肚鸡肠、不合潮流之嫌。
《中国书法史》云:“正体典范的深入人心,不仅是为着实用,还在于它们所具有的通俗性的优美和广泛的社会基础……翻遍历代书史和品书文献,登录能品的书家多与应制书法有关,古人之所以用大量的笔墨去为之评述,其价值取向已不言自明。”[18]艺术是为大众服务的。清代馆阁体的盛行,一方面形成了书法教育的大繁荣,各类官办、私立的书院多如牛毛,大大推动了文字规范化和楷书的普及发展;另一方面,“物以稀为贵”,善工楷书者众,直接导致社会群体出现审美疲劳,工楷自然就成为艺术品中的“庸俗品”。时代在发展,环境也在变化。现如今,毛笔书写的官方正体早已不复存在,馆阁体的约束规范也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善工官楷者更是凤毛麟角。客观评价馆阁体的艺术成就和价值作用,借鉴其优秀成果充实完善书法艺术体系,推动新时期书法教育大发展,特别是高等书法教育的大繁荣,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
注释:
[1]冯广贺.清代馆阁体书法官方实用状况概述[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77-81.
[2]孙过庭.书谱[G]//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24-132.
[3]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6.
[4]项穆.书法雅言·中和[G]//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526.
[5]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干禄第二十六[G]//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861-868.
[6]贺电.清代馆阁体政治功能的再思考[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1):193-201.
[7]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6.
[8]周星莲.临池管见[G]//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725.
[9]张佃新.旧话重提说馆阁——兼及书法的继承与创新[J].书法赏评,2013(06):9-14.
[10]傅山.作字示儿孙[G]//霜红龛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2.
[11]傅山.作字示儿孙[G]//霜红龛集.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2.
[1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干禄第二十六[G]//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861-868.
[13]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254-255.
[14]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M].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165.
[1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268.
[16]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7.
[17]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300.
[18]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254-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