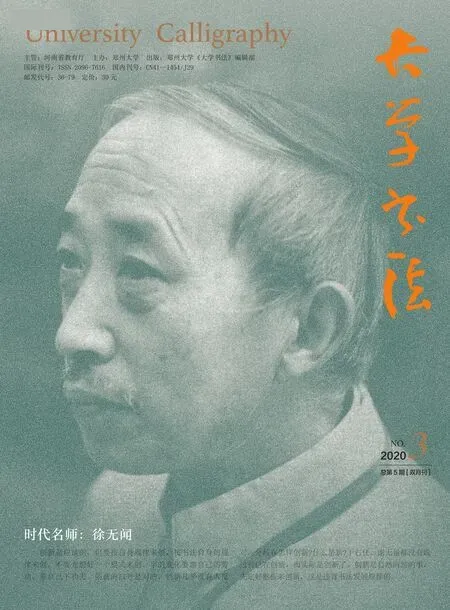论熊秉明的书法“学科”构想[1]——摭谈书法博士教育和书法学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
⊙ 刘镇
当前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目录中,“书法学”属于艺术门类下一级学科“美术学”的下属特设学科(代码130405T)。既称“学科”,显然说明目前书法已经拥有基本独立的知识体系、清晰的研究范围,明确的专业本质、内涵、对象、功能以及意义。
一、由技入道
20世纪60年代,旅法华人熊秉明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中文、中国古代哲学以及“书法课”,之后梳理编撰《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在这之后,国内涌现出阐述书法“学科”构想的成果有《书法美学简论》《书法美学谈》《书法学综论》《书法学》《书法学学科研究》等。自此,书法“学科”意识日益明显,边界逐渐清晰,体系亦趋完善。
20世纪80年代,熊秉明完成博士论文《张旭与狂草》(1984)并提出“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的重要论断(1984,北京),后在国内出版《中国书法理论体系》(1985,20世纪80年代初于香港《书谱》连载),发表《书法领域里的探索》(1985)、《关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的分类》(1986)、《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1995)、《书法和中国文化》(1995)等系列成果。他借鉴西方理论、观点、方法及逻辑体系,立足书法文献及其意蕴,以“学科”意识系统阐述了书法传统。在创造性解读书法内涵及理论构建的同时,又先后在国内开设书技班(1985)、书艺班(1988)、书道班(1992)等,进一步将其理论成果付诸实践,推动书法理论与技法的双向共阐。
书技班:教材为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朱光潜《文艺心理学》(附录部分“形体美”一节)与《谈美》(第七章《情人眼底出西施》);提倡“无须临摹”的书法学习观念,建立“外围点”“内接点”等概念。
书艺班:教材为S·阿瑞提《创造的秘密》,课程安排为第一日写一幅字作自我介绍,第二日超速写法,第三日盲目写法,第四日模拟庸俗,第五日极限情况,第六日“对话”;其间作了题为“书法创作内省心理学探索研究”的讲座。
书道班:教材为《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要求纯模仿的临写、研究性的临写、意趣的临写以及创造性临摹。(宗绪升《熊秉明书学思想研究》)
从内容设计来看,显然带有实验性质,可以说已经预设了书法“学科”体系。这一探索,包含三个层次:“技”,强调静态书法点画形态的分析;“艺”,追寻的是基于点画造型的主观思考与重塑;“道”,是在前二者基础上的嬗变与升华,注重一般规律的抽绎。三者之间,既有严密逻辑的先后顺序,又与其《中国书法理论体系》思考路径保持一致,为书法“学科”制定出一套逻辑清晰、目标明确的教学方案。这种借助西方美学理论重新厘清书法“学科”的构想,潜在地设定了书法是一种可供解剖静态文本,又在跨文化视阈(道)中充分重视了书史背后的思想与观念。由此,这种注重书法内核与精神的持续探索,引起了书法艺术与现代艺术甚至艺术人生(老年书法研究班2002)对话,启发了各种书学流派与现象,推动了书法教育理念的多元化发展。
结合当下来看,熊秉明的“学科”构建与反思精神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譬如,书法学科的定位与培养方案的设置,应当基于何种语境来确定?目前,书法学专业大多游离于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门下,本、硕、博培养点名称更是五花八门,这显然是每所高校对其不同理解所致。实际上,从传统中走来的书法学科理应定位在文史学科之下,其名实早已涵盖了所谓的“文化”,某种程度说与“艺术”“造型”等存在着天然的鸿沟。由此,与其说古代写本、刻本传统中,任何一种学问的诞生都离不开书法,毋宁说书法自古以来就是艺术观念史、思想史的共同载体——“书道”。
二、艺术与科学
从熊秉明的书法“学科”构想中,亦可以清晰感觉到西方美学理论与现代抽象主义的创作原理中理性思维的重要性。这种“数理”逻辑思维,根源于他承袭了父亲(著名数学家熊庆来)的“优美的推导”“洗练的数学语言”,同时,也与早年研究哲学之后的“回归”有关。如他曾在《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择抄》中直言,来源于生活实践的具体技巧是形成风格的唯一来源——后来又选择更为具象的雕塑。他的理论与实践主题中,还从整体上展现出用西方宏观、微观并举重新“观看”东方的辩证性思维。
熊秉明曾努力探寻佛像雕塑艺术形式,称之为“超越生死烦恼的一种终极追求”。这种追溯哲学理性与艺术感性之间的交融,何尝不是一种“理性和信仰的冲突、传统与革命的对立、中西文化的矛盾”呢?(熊秉明《父亲之风》)与其类似,当前“书法学”专业要求同时具有“宽厚的书法学科专业知识”与“较为宽阔的文化视野”,看似错位,实则统一。故而,我们既要强调书法传统所根植的国学基础,也应借鉴西方美学及相关理论观念、方法等去透视书法传统经典的生成与流变。尤其在具体的资料搜集、逻辑推理、体系构建过程中,注重逻辑思维在教学示范、理论推求过程中的重要性。如此,方能拥有严谨、缜密的思考,终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无限接近历史真实。
熊秉明的理论原点与李格尔如出一辙,后者所构想的艺术发展程式,是立体先于平面,触觉先于视觉,“最初的艺术冲动是出自对艺术形态事物的模仿”。由此说来,逻辑理性所标榜的“科学”不仅是书法学科建设的原点,也应是“归宿”。因此,当前丰赡的书教资源,以及传统中感悟性书论、题跋、笔记等看似只言片语,枝蔓丛生,但却内在地隐含着逻辑思维严密的文、史、哲根基与体系。这些文本“空间”的细读,须循依文献考据等“笨功夫”,剔精掘微,剥茧抽丝,进而揭橥“微言”背后之大义。推开来说,学科体系等或可以借鉴无远弗届的哲学、文学理论来统摄与透视,以此拓宽学科视野,提升学术高度,多重维度地完成“原境”意义的追寻。这种寻绎,也是对当代学术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一种探索。
三、“人本论”
熊秉明认为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从抽象思维落实到具体生活的第一境乃是书法。他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中,创造性地使用文评、诗话视角重新建构了书法理论系统:喻物派、纯造型派、缘情派三者以自然为旨归,以造型手段表现书者内心感情;伦理派、天然派、禅意派三者则为以上三类的综合概括与提升,分别对应儒家(善)、道家、佛家。于此构建了一个严密的书法阐释系统。
诚然,早期书论“同自然之妙有”“达其情性,形其哀乐”以及“书之为功,同流天地,翼卫教经者也”,皆尚自然。而从扬雄“心画”、许慎“书者,如也”到刘熙载《艺概》“书也者,心学也”的推导过程,在熊秉明看来是书法重“形”但更重“神”的塑造过程,也即艺术史风格是源自“文化的与形式的”。(沃尔夫林《艺术史原理》)故他认为,书法与诗、文、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此外,熊秉明不仅把书法当作中国美术的核心问题,而且始终把中国书法思想理论置于全世界各种艺术理论的背景之中,不时作东西对照、古今对话,希冀从这种开阔的视野中抽绎出中国书法的理论规律。他在异质文化融合的立场上,突破了以往仅从本土文化内部分析书法的僵局,从“人本”回归角度为当代书法理论研究及书法“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性的学术构架。在其构想中,还触及中国书法认知体系、书法普世价值与审美范式的当代构建、当代中国书法海内外传播的路径抉择、反理性思维与当代书风之关系等,并创造性提出“核心说”“形式论”等新的书法研究方法论,书法界至今仍在普遍采用。
熊秉明的书法“学科”意识,为我们提供了跨文化视野下古今中外对话的多重思考,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但在当前尝试构建书法“一级”学科的过程中依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人学者中国文艺理论及思想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6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