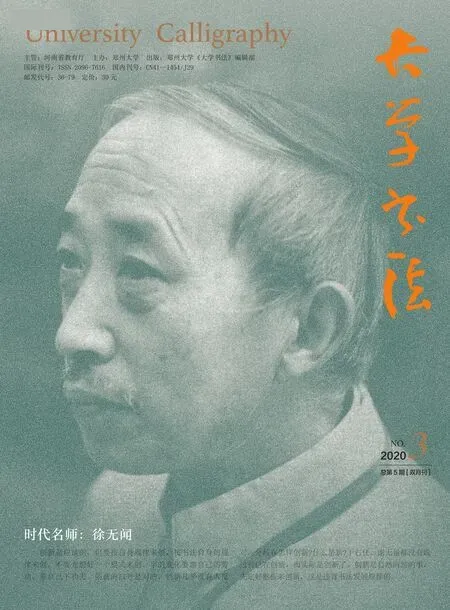苏轼“自然”书法批评观探析
⊙ 李梦媛
苏轼书论散见于其题跋和论书诗中,数量众多且有深入的理论见解,其独特的批评话语既是其自身儒、道、释思想融合的体现,又是北宋后期书学思想的一个直观反映。对于苏轼的书法批评理论,论者大都更聚焦于其“以人论书”的层面,本文认为,“自然”亦是苏轼书法批评观的核心。笔者通过对苏轼书论的爬梳,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援用其文论、画论中的观点,对其“自然”书法批评观进行分析和总结。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明晰苏轼批评观中“自然”的具体内涵和指向,亦能更好地理解苏轼的审美趣向、书法理想等,更期立足此,成为我们今后窥探苏轼所处时期的品鉴风貌和价值取向的一把钥匙。
一、批判“粉饰”,崇尚“萧散简远”——不事雕琢,天然清真
在针对书家作品风格及意蕴的批评论述中,不难发现,苏轼是以魏晋风尚或言锺、王书法大统为审美参照系,其批评语汇更是延续了魏晋书家投射于作品的美学旨趣。苏轼诸多书法批评便是以此展开的,涉及的批评语汇类属于“自然”的相关范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丰富了“自然”的意涵,且共同体现了苏轼的批评观。
对心中圣贤之书,苏轼曾高度赞誉:“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1]“萧散”有风格意义上萧闲疏散、不受拘束之意;“简远”是简练幽远。他亦曾评褚遂良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2],概因其书有王羲之的风貌。可以说,魏晋名士超然物外、萧散简远的风度意蕴,在苏轼看来无疑是饱含自然之姿的。于是,草书“有东晋风味”[3]的秦少游,真书“简远,如晋宋间人”[4]的张旭皆入其欣赏之列。苏轼亦评张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5]“天放”一词源于庄子,有顺应自然、任其自然之意,苏轼谓张旭“颓然天放”,赞其书写状态肆意任情、自然而然,故能臻于“神逸”。按黄惇先生言,“逸”是创作过程中因“初无意”“本不求工”而获得的艺术效果,从这一角度来说,反映的正是张旭在创作中心境的自由。苏轼对张旭的品评,还有一个颇值得关注,其《题王逸少帖》:
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
何曾梦见王与锺,妄自粉饰欺盲聋。
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
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6]
有论者以此认为苏轼言论前后矛盾,其实不然。首先,“颓然天放”的批评语境是将张旭与同时代写草书的人相比,而此诗则是将张、怀与王羲之作比;其次,上述“作字简远”是赞其真书,而这里批评的是二人的草书。细观此诗,张、怀是“追逐世好”的取悦媚世,是有如娼妓涂脂抹粉般的极尽雕琢,而锺、王之书则有如谢道韫一般的淡雅飘逸之姿,其高下显而易见。苏轼对于张、怀的草书并未持否定态度,“张长史、怀素得草书三昧”的评判亦来自于苏轼。但在这种比堪之下,张、怀二人过分注重技巧的表现,而锺、王之书无做作之痕,无疑更符合苏轼“自然”的批评标准。
“清”是苏轼论诗书画时常用的批评语汇,其诗“清句乃绝尘”,即赋予“清”以“高风绝尘”的意涵。李白曾以“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将王羲之高洁质朴、自然洒脱的形象树立起来,苏轼亦有:
青李扶疏禽自来,清真逸少手亲栽。
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7]
时王安石退居金陵,苏轼与之相谈甚欢,便借此诗比之,赞其清真的为人品质。苏轼在诗歌上褒扬“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8],书法上则以王羲之之“清”作为审美风格的典范。这里,逸少之“清”既包含了其超尘绝俗、洒脱旷达的“清人”品格,亦包含了其出自自然真性的书作特征。苏轼《题颜鲁公书画赞》曰:
颜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9]
之所以推重此帖,皆因此帖与王羲之小楷《东方朔画赞》在风格意趣上相统一,是颜真卿承接魏晋之作。“清”作为“自然”这一范畴的另一种陈述方式,还有着其他内涵和具体指向。如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10]“天工”,即浑然天成、不经修饰的自然之美;“清新”则指向清美新颖、不落俗套之美,实可视为诗、书、画共同追求的审美准则。其《跋杜祁公书》亦有:“公书政使不工,犹当传世宝之,况其清闲妙丽,得昔人风气如此耶。”[11]苏轼常用“清”及其范畴群品评书家及书作,这其中的清雅高远、超尘绝俗,饱含了“自然”的意蕴,反映了苏轼向魏晋萧散气质回归、崇尚自然天成的批评观。
二、诟病“苦笔骄”,推重“无意于佳”——抒发真性,自由书写
艺术中的自然,不是客观世界的自然,从其审美内涵来看,也绝非是天然。苏珊·朗格的艺术本质论揭示出,艺术是以各种独特的方式将人类的情感符号化。就书法而言,诚如孙过庭所言:“达其性情,形其哀乐。”[12]苏轼不仅以能否通过书法形式将主体情感和精神表达得自然作为批评标准,也据此提出臻于自然的门径和要领。
(一)“不贱古人”“守骏莫如跛”——破除成法,抒发真性
艺术的形成与演化有其特定的标准和规律,而书法的艺术语言,如用笔、结构、章法等,是构成和表现书法艺术的重要因素,脱离这些,便不能称之为书法。因此,自然并不是任情恣肆、脱离本体的宣泄,在书法作品物化成形的过程中,“法”不可或缺,学法则是必由之路。苏轼曾于《跋鲁直草书》谈及霍去病让士兵在缺粮的情况下踢球,导致体力消耗,认为这是他不学兵法的过失,并借此提出“学即不是,不学亦不可”。[13]苏轼十分强调“法”,他曾言:
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14]
亦曾赞蔡襄“积学深至”以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15]。其句“吾笔法亦稍进耶?”[16]更是他重视法则并以此“三省其身”的写照。对于可学之法,苏轼也做了进一步论述:
王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无法故。[17]
此处并非对王安石的批判,而是告诫世人不要学习他的“无法之法”。所谓“无法之法”,我们或可以“无招胜有招”中的“无招”作比,是看似没有程式,却能任意而出、出神入化,是至上之“法”。但苏轼认为学习阶段需要的是有规律可循、有固定模式的“有招”之法,显然“无法之法”不适宜学习,也学不来。
就艺术而言,当法则不断重复,深入学习的过程中便很容易受制于“法”,从而掉进“法”的泥潭。如果艺术的表达为“法”所囿,那么,作为表情达意的艺术本质又如何能彰显呢?苏轼《跋君谟飞白》云:
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18]
又曰: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
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19]
也就是说,若能通晓其意理,心悟其精神,即便是不学古人也无妨。苏轼此言道出书法的本质并不在于形式技巧的表现,而在于通过这层“法”的面纱,领悟其内在,即言“法”是表现得自然的前提和保障。正如其对智永书的赞誉:“非不能出新意求变态也,然其意已逸于绳墨之外矣。”[20]其间奥义一目了然。
对于死守成法、食古不化的临摹效仿,苏轼的批判是明确的:
客有谓东坡曰:“章子厚日临《兰亭》一本”,东坡笑云:“工摹临者非自得,章七终不高尔。”[21]
蔡卞日临《兰亭》一过,东坡闻之曰:“从是证入,岂能超胜?盖随人脚跟转,终无自展步分也。[22]
苏轼无疑是魏晋传统的推崇者和践行者,对右军的膜拜更不言而喻。然而,艺术的本质既然是情感和精神的一种言说,那么,再精熟的技法、再肖似的临摹,展现的都是为技而技、为法而法,“工摹临者”复刻的是他人的书意。章惇、蔡卞之流是拾人牙慧,如鹦鹉学舌在牺牲创造力的同时,也必然失去己意,背离自然。其《次韵子由论书》曰:
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
世俗笔苦骄,众中强嵬騀。
锺张忽已远,此语与时左。[23]
苏轼批判世俗之人用笔苦于自矜,欲以刻意之工巧而“骄”于世人。“守骏莫如跛”即刻意而为的完备书写不如原本有瑕疵的真实之作,其原因不外乎是故意的创作虽完美无缺,却破坏了出自本真的美感,是主体精神和创造力的双重缺失。因此,苏轼“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24]便有了方法论的意义。既然再怎么学法都无法达到自然,都是“随人脚跟转”,那么以我之法、抒我之意,则是书法表达本性、迹近自然的指路明灯。当然,由于情感本身并不能构成艺术,苏轼对此也有所限定,即所谓:“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25]
(二)“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驾驭规律,自由书写
苏轼的书法批评观中,“法”有着独特的身份。一方面,无“法”则不能实现主体情感的表达,因为脱离规则的书法从本质上不具备成为书法艺术的条件;另一方面,“法”的程式与固定化,易使创作失去自由发挥的潜能,无益于表现得自然。理解了这一层面,再看这一段题跋,其所指便不言而喻。苏轼《书所作字后》:
献之少时学书,逸少从后取其笔而不可,知其长大必能名世。仆以为不然。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然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者,独以其小儿子用意精至,猝然掩之,而意未始不在笔。不然,则是天下有力者莫不能书也。[26]
“用意精至”,不仅是握笔力量的掌控得宜,也是创作时的全神贯注,这些都是献之技法层面的优越条件。但苏轼认为并非握笔有力就能写好字,归根结底是献之创作时能“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换言之,法度是基础,表现得自然不是任笔为体的随意挥洒,而是自如的运用规律,下笔所到处皆不可遏制,而又能不脱离规范。正如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逾矩。”朱熹对此有解:“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27]这其中的辩证关系,与苏轼对于“法”的思考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苏轼《小篆般若心经赞》:
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28]
又其《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
口不能忘声,则语言难于属文,手不能忘笔,则字画难于刻雕。及其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能知也。[29]
当“法”成为书家表情达意的枷锁,演化为刻意和“程式化”的表达,便走向了反面。所谓“忘”,是于创作中忘却技法,摆脱有意识的追求,转化为无意识或者说出自本能的自由书写,这时的创作不再受制于规律,而是主体意识的自由彰显。这种无功利的创作状态,被表述为“纵手天成”“信手自然”:
此数十纸,皆文忠公冲口而出,纵手而成,初不加意者也。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30]
颜鲁公与定襄郡王书草数纸,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31]
“纵手”“信手”有随意放任、不拘束之意,唯有不执着笔法、结构的安排,才能获得“自然绝人之姿”,即合于天造之自然。“瓦注贤于黄金”语出《庄子》:“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所谓“外重者内拙”,不论是游戏抑或书法创作,得失心太重、思虑过多,则极易心绪紊乱,导致发挥失当。因此,苏轼总结到:
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32]
创作过程若是心有挂碍,总在苛求工巧与否的展现,甚至刻意与造作,必然会凝于心而滞于手,成为挥洒自如的绊脚石。因此,冲破藩篱,笔随心至,反而能“举止自若”,苏轼称道的便是这样一种不期而至、不经意的自然。苏轼于此强调书法创作不能存有功利之心,不必冥思苦想,亦不可计较毫端的一笔一画,方能以主体无所用意的自由精神,达到“无意于佳乃佳”[33]的境地。
三、“精能之至,反造疏淡”——返璞归真,技进于道
苏轼曾称扬智永:“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34]以平淡蕴藉的陶渊明作比,苏轼认为智永书有疏淡清远之美。“淡”出于《老子》:“‘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35]即,虽至淡无味,却是味之极。又《庄子》:“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36]可见,“淡”与“道”相通,有着自然素朴之意,暗含了“道”的本源性,在古典美学中,“淡”饱含了不事雕琢、不假矫饰的自然之美。“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斯言道出,获得“疏淡”必然会先经历一个“精能之至”的过程,如同诵读陶渊明的诗歌,初读平淡无奇,经反复诵读,便能察觉其中独特的意趣。“精能”指的是技法上的精深和娴熟,而“疏淡”,并非真的平淡无奇,在美学意义和价值上,“淡”被“道”注入了具有超越性的力量。苏轼对“淡”的审美意蕴赞誉有加:
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37]
可以看出,苏轼论“淡”并非停留于表面,而是发掘其内在的充实之美。正如其所言“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38],表面淡而无味,却囊括了所有的味,有着无所不包的精神内核,是“至味”。
关于“精能”走向“疏淡”,苏轼还有另一个著名论断,兹引出,一并探究。其《与二郎侄》: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39]
就艺术的匠心经营而言,初始的“峥嵘”“绚烂”是规范的深入理解和技法的纯熟修炼,于是求新求变,极尽能事,呈现出技巧的斑斓。随着“渐老渐熟”,便洗尽铅华,获得平淡,这时的平淡并非艺术最初少技巧、缺精熟的阶段,而是涤荡人工造作之后的新生。显然,“平淡”不可力求,是一个由必然到自然的过程,亦蕴含着庄子所言“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思想。
正如苏轼赞陶渊明诗“大匠运斤,无斧凿痕”。“淡”的无斧凿之气不仅是“自然”的彰显,更是近乎于“道”的。“道”需要“技”来展现,而最高超的“技”又是“道”的表现。关于此,苏轼的两段题跋有集中表达:
技进而道不进,则不可,少游乃技道两进也。[40]
有道有艺,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41]
正如苏轼对于“法”的辩证批判,对于“道”“技”,他强调要并重。有关“技道”的庖丁的寓言故事叙述了从依靠技巧到超越技巧,最终游刃有余的过程。如同艺术创作,初期为保证作品的物化成型必然需要匠心,但到了一定阶段,便要破执,从技法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甚至是忘记技巧、摆脱经验,以自由超然的心境书写,这其中对于技巧的泯灭无疑是创作主体得到解放的完美展现。苏轼推重“技道两进”,但“道”是根本,即要求掌握技法语言后,在创作中不断放弃经验和技巧,以获得主体自由,从而使作品合规律性的同时,又不着人工痕迹。这便是臻于自然的不二法门。
小结
苏轼“自然”书法批评观,以魏晋风尚为审美参照系,批判粉饰雕琢,崇尚萧散简远、天然清真;强调创作主体情感的自然流露,诟病对他人艺术语言的套用,认为当以我之法,抒我之意;称赞创作中的“信手自然”,指出应驾驭规律、突破成法,摆脱有意识的追求;追求至味之“淡”,揭示书法创作是由必然走向自然的过程,注重匠心经营之后对技巧的泯灭,技道两进,返璞归真。
注释:
[1]许伟东校.东坡题跋[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52.
[2]苏轼.评书[G]//崔尔平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54.
[3]曾枣庄,舒大刚.三苏全书[M].第14册.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49.
[4]孔凡礼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06.
[5]孔凡礼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06.
[6]苏东坡.题王逸少帖[G]//东坡全集.卷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
[7]苏东坡.次荆公韵四绝[G]//东坡全集.卷十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
[8]孔凡礼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1884.
[9]孔凡礼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177.
[10]孔凡礼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1525.
[11]孔凡礼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184.
[12]孙过庭.书谱[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26.
[13]许伟东校.东坡题跋[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271.
[14]孔凡礼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06.
[15]李福顺.苏轼与书画文献集[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35.
[16]李福顺.苏轼与书画文献集[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31.
[17]苏轼.论书[G]//崔尔平校.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15.
[18]孔凡礼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181.
[19]孔凡礼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0.
[20]顾之川校.苏轼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0:756.
[21]曾敏行.独醒杂志.卷5[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
[22]孙承泽.砚山斋杂记.卷2[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
[23]孔凡礼校.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211.
[24]许伟东校.东坡题跋[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256.
[25]苏东坡.书吴道子画后[G]//东坡全集.卷九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
[26]苏轼.论书[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14.
[27]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7.
[28]孔凡礼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618.
[29]孔凡礼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1980.
[30]许伟东校.东坡题跋[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279.
[31]许伟东校.东坡题跋[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244.
[32]顾之川校.苏轼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0:737.
[33]许伟东校.东坡题跋[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256.
[34]孔凡礼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06.
[35]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M].北京:中华书局,1984:203.
[36]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336.
[37]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13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539.
[38]许伟东校.东坡题跋[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152.
[39]顾之川校.苏轼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2000:710.
[40]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14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1:49.
[41]孔凡礼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