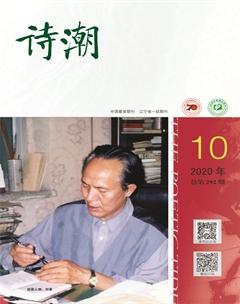这么多嘴唇和月亮
挖掘一座空山,用石刻的嘴唇,
我试图绕过这暂时的黑暗:在石头内部
洗净我食道上的灰,
实际上我吃的是过期的墨水。
思想像营养一样流失,
没有一个追随者,我隔空亲吻过的
不是蝴蝶,就是蝴蝶梦
更多的村民在我的身边低着头
包围我的泪水,要求改变
田野的属性。
“你错了,我们对亲吻不感兴趣”
于是我修的路,从天上掉下来。
向下挖掘的一个圆形的建筑
我将在里面喝暗河的水:改变了习惯
却改变不了命运。
我的汹涌的双手,抱紧童年的皮球。
但是,但是,我还活着
我的海已经漏光,我不得不忍受
月亮從我腰间升起,
照耀我嘴唇上晦涩的语言和无名的耻辱。
[林忠成赏评] 沃·威尔代在《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里认为,“对于今天的世界,决定论、稳定性、有序、均衡性、渐进性和线性关系等范畴愈来愈失去效用,相反,各种各样的不稳定、不确定、非连续性、无序、断裂和突变现象的重要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重视”。李龙炳这首诗,在语言上体现了一股强烈的“后现代征候”,节与节之间,句与句之间,落差大,充满断裂感和不确定性,如果你试图从中梳理出社会通约的公共语言,必徒劳而返。诗人从来不对语言通约性负责,那是社会学、语言学、修辞学的事,诗人只对誊录自身内宇宙负责。
存在决定语言。“在这个时代,一种维系语言结构、社会现实结构和知识结构的统一性的普遍逻辑已不再有效”(《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为什么不再有效?因为人类的生存背景发生了深刻裂变,沃·威尔代指出,“过去的时代创造了三种关于这样的神话:启蒙运动关于人性解放的神话,唯心主义哲学关于精神目的论神话,历史主义关于意义阐释的神话。在后现代时期,这种维系着统一性的纽带已经腐烂,三大原神话的破灭导致了统一的中心丧失。”
对这些破碎无序的词像进行梳理,凭直觉你能发现,诗歌隐隐约约投射出绚丽的幻灭感、命运的无力感、无方向的疏离感。“思想像营养一样流失”“我将在里面喝暗河的水:改变了习惯/却改变不了命运。”个人命运的无力,来自多种社会学小径,“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天运》,庄子),这是一种方向性的荒诞。
无论怎样,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