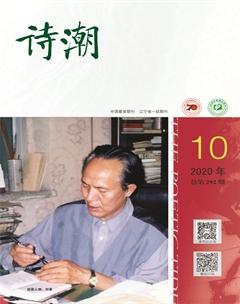真诚的错误及其他 [十四首]
叶延滨
七月七日
用一团愤怒的云
擦拭被雾霾涂抹过的天空
拧出记忆中的泪水
挂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帘
风吹起来了,像嘶哑的号声
雷滚动过我们的头顶
闪电炸开一条路,穿过长空
一次街头的游行
然后都走了,安静了
星子们提着灯陪我等人
等从东北流亡北平的母亲
回到寄居的那家小客店……
真诚的错误
诗人一般爱把月亮当成亲属
情人,不靠谱的情人
家人,远方的家人
写月亮诗人都有孤独症
比方说李白
特别是当他举起酒杯
四顾无人……
诗人有时把太阳也拉进朋友圈
是专门点赞的老友
新上司、大客户、赞助商、名教授
发昏的首长和发烧的恋人
太阳升起来好啊
太阳落下去,那就拉黑它
等明早那个新升起来……
不知为什么 看《诗词大会》
看见一群女孩
争着按抢答器的时候
我腦子里不是唐诗,不是宋词
不是红楼贾宝玉的赛诗会
而像走进了一家电脑店——
这台硬盘大,那台内存小
手上这台有运转最快的芯片……
酒半酣
没开封的酒瓶
像等待公示提拔的公务员
也像等着授勋的军官
衣冠亮堂,正式而体面
有名有号还有度数标明阶级
真有本事,装满了一肚子酒
依旧能不苟言笑
喝干了的酒瓶
堆在墙脚
丢盔卸甲
不讲牌子了
不分度数也没等级了
像退休老头们凑在花园里搓麻将
人堆里,司机比司长更牛:
傻司,司机大爷又和了!
独坐半开的窗前
手上有读了一半的书
桌上还剩半瓶酒
一支燃了一半的香
喝罢半碗的温茶
酒半酣?啥人,半仙……
战争史观
鱼,淡水、咸水,有鳞、无鳞
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鱼
会把河流堵死
会把大海填满
人啊,上帝创造出人
人制造了船和渔网
渔网是大海的清洁工
鸟,所有长着翅膀和羽毛的鸟
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鸟
会把树枝压断
会把天空挤满
人啊,上帝创造了人
人制造了弹弓和箭
弓箭是天空的清洁工
人,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的人
人人人人从从从从众众众众
把鱼捕完的人
把鸟捉完的人
人啊,上帝创造的人
多得把上帝也挤走
战争是谁请的清洁工?
末日最后一叹
梦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哎呀,我终于可能摆脱了
世世代代,没日没夜
无休止地纠缠我的
那些人们!
总有人比我更老
你不叫我叶老师了
叫我老叶了
我笑一笑,回答好
你不叫我老叶了
你叫我老大
我也笑笑,不言语
你不叫我老大了
你叫我叶老
我笑一下,不回声
我想总有人比我老
朝前想太远
地平线总在前方
朝上想太累
上头事情像雾像云
闭上眼回忆往事
事情里那些年轻的脸
冲我笑开了怀:
你是小叶?真老了……
旅 途
在漫长而困乏的列车上
有个人仰着头睡着了
整列车厢的人都看着这个人
睡着了的人,挂着香甜的笑
从嘴角流出一丝涎水
他靠在座位上
座位铆在车厢的地板上
车厢架在列车钢轮上
钢轮驭着他的梦在铁轨上飞跑……
而另一个人躺在鲜花丛中
这个人仰着像睡着了
悼念大厅的人都看着这个人
像睡着的人,两腮搽了红
两片唇像要张开说话
他只是在另一次旅途上
另一拨人在另个站台迎他
他习惯出行习惯告别
习惯人们像今天前呼后拥……
面包会有的三层境界
面包会有的
这曾是一种信仰
在冷风吹过饥饿的操场
像我脸色一样发黄的银幕
有黑白电影晃动着
一个秃顶老头
他说:面包会有的!
我咕咕叫的肚皮
把对他的崇拜
送到全身每个细胞
面包要有的
这常是一种需要
起床挤地铁抢点上班
两片面包,半杯牛奶
一分钟烤箱
一分钟微波炉
在城市拧紧的发条里
面包是最快捷的
上班族专用一分钟
面包还有的
这也是一种习惯
退出上班族,必须有五老
老伴老友老屋老毛病
再加上老习惯——
热杯牛奶烤一片面包
面包说一切会有的
告诉自己又一天开始了
太阳升起,清风拂面……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这架飞机
没有在云海穿过的机翼
没有包裹结实的机舱
飞机的乘客们
一定是驭风而行的神仙
云雾缭绕,衣衫飘飞……
如果没有这列地铁
没有这在地下穿行的隧道
没有自动开闭的车门
地铁的乘客们
一定是穿山入地的精灵
土行孙们,无坚不摧……
如果没有秘书作业发言稿
没有回声宏壮的音响
没有鸟儿般扑腾的掌声
说假話不脸红的这位
真像从疯人院
跑上大街,大喊大叫……
诗 人
他记住了自己犯的第一个错误
也是最后一个——
他冲着一个大肚皮的国王喊
他没有穿衣服……
所以现在他说出的每一句话
都穿着精致的外套
天堂与地狱
一颗露珠
沿着叶片的脉络
晶莹滑动至叶子的顶尖
挂在那里的露珠
牵着一丝阳光
不要多,一丝阳光与一颗露珠
就是最小的天堂
眼前,一根毛发
不知羞耻地占有了
酒店宽大的浴缸
原来地狱并不遥远
原来地狱也不是黑暗无边
一根毛发统治着的浴缸
就是洁白的地狱
割草机
割草机在欢欢地歌唱
像小狗一样贴着地面奔跑
它的歌声是春天的歌声
吵醒了公园里打盹儿的老头
老头闻见了青草的气息
不会歌唱的青草用气息发言
老头眯着眼睛望一眼草坪
草坪是小草聚集的广场
啊,春天到来了,小草在歌唱
老头想起年轻时记得的诗句
剪齐了的小草在开迎春大会
老头想,这是多么温馨的场面啊!
老眼昏花的老头看不清每棵小草
绿色的草坪让他放松地享受安宁
小草不说话小草也不会歌唱
割草机正齐刷刷切断它们的脖子
切断了脖子的小草趴在地上
那些地下的根正悄悄地鼓励它们
记住那个冒充春天的割草机屠夫
记住你们的命运:春风吹又生……
一样的与不一样的和谐
蛋心与蛋壳相伴一生
一生小心地维护和谐相处
因为它们知道
它们天生就不一样
流质的蛋心与脆硬的蛋壳
互相亲密依偎
竭尽努力保持宁静与稳定
知道不同而能共存的共同体
只有毁灭的结果是一样的!
蛋壳破碎之时
蛋心流淌一地
分离竟然瞬间变成毁灭
蛋白与蛋黄在毁灭之时
才显露它们原不一样
蛋壳里浑然一体不分你我
蛋黄与蛋白并不一样
它们一样地躺在煎蛋锅里
谁来告诉它们是不一样的?
童年真实的故事
我想告诉你,童年的日子
后窗斜山坡爬满了玫瑰
那是阳光和露水散步的花丛
门前的湖水罩着晨雾
早起的渔船剪破蓝色丝绸……
我想告诉你,童年的日子
门前的小道喷洒血迹
狂吠的狗还有草丛中的刀
后窗冷月闪动狼的绿眼
黑黢黢的山影搂紧了残星
我只告诉你那个早晨
那是真正温馨的一幅春色
若只讲记忆中的寒夜
那是真实恐怖的一场噩梦
都是童年,童年的一块积木
若是先说早晨然后说黑夜
那是一个凄冷的悲剧
若是先说夜晚再说那早晨
会是一个暖心的喜剧
只想说忘记早晨与夜晚的顺序
好吧,我可以坦然地说
对于我的童年,那个早晨
还有那个夜晚都绝对真实
请允许我保留童年唯一的秘密
早晨和夜晚的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