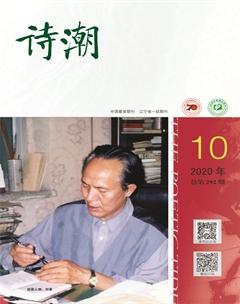生日书 [组诗]
陈衍强
牛街古镇
从镇雄逃亡到盐津的白水江
翻开彝良的高山和峡谷
如同在云南说四川话的大风
翻开雷平阳摘抄过的牛街镇志
江南和江北
头戴青瓦的王冠
身穿岑宫寺和万寿宫的霓裳
用马鞍山的铁索桥拔河
从1936年纠缠到今天仍不松手
天麻和笋子
从盐商拜过的码头顺水推舟
填满现在叫宜宾的叙府
明清的花楼
在飘摇的风雨中
早就春梦无痕
只有四合院里的水井
还在用浪花朗诵民国的事情
只有青石板上的马蹄印
还回响马帮遥远的铃声
从天上看牛街
白天是陈守仁的微雕
夜晚是乌蒙山的小香港
巷子里涌现的一个又一个美女
不仅春暖花开
还弥漫桐子叶粑粑的芳香
她们像吊脚楼一样
把最好的年华伸进江里洗脚
当细鳞鱼从她们的脚背
游到端午节的钵里
哪怕你是过客
都愿与时光一起留下来
把生活的忧愁和欢乐
酿成菜籽沟的玉米酒
灌醉风平浪静的日子
牛街人确实了不起
就连昆明西山的龙门两个字
都是牛街秀才毛以亮古朴的楷书
怪不得到过牛街的人
会使劲喜欢牛街
甚至用余生的竹竿划着竹筏
在白水江上练毛笔字
白水江
白水江的出生地在彝良之外
走出彝良 它就把温婉如玉的名字
改成关河 然后
在金沙江和长江中隐姓埋名
白水江像洛旺和柳溪两姊妹的长裙
牛街古镇 是长裙下的小腿
裸露择水而居的风情
其实 白水江白的是云朵般的浪花
和浪花般的美女 将施特劳斯的圆舞曲
跳成蓝色的天空
白水江有时静若止水
万箭穿心的阳光 也触摸不透它的内心
难怪我面对白水江
只能大胆地爱 但不能拥有
白水江有时放浪形骸
两岸的柑橘和翠竹 都留不住
它匆匆忙忙奔向远方的足音
我即使近水楼台 逆流而上
也来不及追忆逝水年华
甚至无法在它深不可测的怀抱 留下
水性的诗篇和亲热的痕迹
我只好收起英雄的想法和假设
回头是岸 误入摩天轮旋转的月亮湾
一眼就看见苗家姑娘直播的菜花
在芦笙吹醒的春天 灿烂成
彝良以北的黄金时代
小草坝
小草坝是地名 更是山水画
小草坝的人家
不仅在画中劳动 恋爱和生儿育女
还把天麻种满整个小草坝
甚至把外地人当药引子食用的天麻
像吃洋芋一样奢侈
怪不得男的都是坚硬如矿石的英雄
女的都是柔软如炊烟的美人
他们一开门 就看见群山在云朵上
奔驰成鬃毛竖成阳光的朝天马
山俞菜生在山里 岩韭菜长在岩上
杜鹃灿烂成房前的嫁妆
红叶燃烧成屋后的彩霞
小草坝的人家
仿佛居住在陶渊明的散文中
哪怕再苦再累 都能把日子
过成诗和远方
因为他们 每天面对挂在家门口的
一条又一条瀑布
与李白在庐山看见的差不多
清河村
清河村距彝良县60公里
距水浒中的清河县十万八千里
清河村当然有河 并且围着山旋转
村民的房子 多半都建在公路边
从一条岔路口往左走 翻过垭口
就是镇雄县的杉树乡
如果朝右转 可以走到贵州省赫章县
吃8角1斤的米拉洋芋
我是初夏被一辆面包车拉到清河村的
穿過从宜宾到昭通的高速公路建设工地
和集市上的叫卖声
车停在陶家门口的黄昏
小姨夫已经把土生土长的乌骨鸡炖熟
小姨妹正用大声朗诵的自来水
洗她采自房前屋后的折耳根 刺脑包
和一种叫瘦狗还阳的野菜
然后支起火锅 以清热去火的热情
招待我这个口无遮拦的大姐夫
在清河村 当一个村民是幸福的
白天 骑着摩托上山种天麻
夜晚 枕着蛙声和鸟语刷抖音
做乡村振兴的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