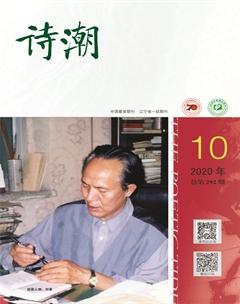魏朝凯的诗 [组诗]
魏朝凯
初 春
万物强忍着残冬的煤烟味
笑容凝固在与世隔绝的橱窗内
祈盼渐渐不知所措地
在夜中搭高云梯寻找着白昼
被乌云摧残了一天的愁绪
只好暂时躲进花样翻新的晚餐
突然,乌云被闪电降服
不得不缩回原形变成黏稠的黑雨
外面的浮尘污秽乱了阵脚
被纷纷吸进伏魔宝袋中,瑟瑟发抖
门缝中传来了瘟神歇斯底里的尖叫
隐约可见一对被憋疯了的小花猫
闪电般蹦高,冲向绿化带
含苞待放的迎春草。顷刻间
所有的街灯都哭了
泪水中宣泄着欣喜若狂的亮光
半个世纪
明明知道不是你,我仍然尾随你
明明知道你早已远离
我仍然每年两次来寻你
明明知道这是我的伤心地
我仍然相信每天有人等自己
春暖花開时,村西老槐树
愿陪我们歇斯底里
大雪封门的日子里,村东麦田
甘做我们高声放歌的自留地
我们从小到大钟爱着这惬意
在没有你在的岁月里,我开始
反省自己,同时也在反省你
硕果累累的时候,不知不觉
已经远离了我们半个世纪
我丢失了自己的影子
音乐喷泉大广场
我在暖阳下摸黑缓行
熙攘嘈杂的人流悉数隐身
我原地打转,转了好多圈
我在陪自己散步
恍惚间却感觉不知身在何处
一只失魂落魄的小麻雀
一个箭步跃过我的鼻尖
我打个冷战,险些
把无人值守的岗亭撞翻
门把手拧了一下入侵者的脸
我惊慌失措地逃向大路边
听到有个声音在呼喊
等等我。说话的工夫已至近前
我急转身,茫然四顾
偌大的广场霞光一片
依然连自己的影子也寻不见
天外有天
一片被距离截屏的天
浓缩着霸气的蓝
俯视中眯着高傲的眼
一朵懒洋洋的白云
哼着自传体的英雄赞
不屑掠过楼宇的方寸宽
一位不会写诗的人
指着白云蓝天,大喝一声
再傲,也逃不过字里行间
一名咿呀学语的孩子
轻轻地,试着叫了声爷爷
思绪便从苍穹回到了人间
刹那间,一切都没有了
天外的天空,大得无岸无边
宅家的日子
错过了早餐、中餐
磨到了傍晚,日子
懒洋洋地归降了晚餐
追完了谍战,再追情感
她说,爱你到永远
窗外,夜雨缠绵,灯下饮酒
他说,你一生都是我的眼
梦
再也感受不到她回眸一笑的心跳
再也无法听到上下学途中
柏树林中的那只夜猫子
头皮发麻却听了还想听的冷笑
那时,拉紧在一起的小汗手
握满一生难以释怀的美好期许
所有的过往已成温馨底片
当初的牵挂经年蔓延
当年的她,还在滋养别人的心
就连那夜猫子,也已隐遁
空留下丝丝缕缕回忆飘散在梦中
少年书屋
伴我熬过不惑之年的土坯房
依然静静端坐在村子的最南边
那棵高大的恋子树
还信守着最初质朴相伴的诺言
如今,我却与那盏彻夜伴读的
罩子灯,一别经年,难以再相见
瘦长的胡同如同想念一样幽深
藏书的大柜失落地呆坐在屋角
一张当年带字的小纸片
就会让我的心海涌起波澜
幼年的梦想还挂在土屋上的弯月里
记忆中的少年,只有温暖的影子
暗 恋
她嫣然一笑
冲我挥了挥手
同样的笑
也挥手送给了他
我感觉
她对我笑时像挥手
对他挥手时像笑
相思树
一只小花猫,躺在树下
晒在暖阳里睡得正香
她的靓影,孑然而立
散发着贝壳油的清香
我压低嗓子,用暗语喊了
一声嫦娥。她端详半天
将头摇得像拨浪鼓,质问
我满脸的沧桑:神经兮兮的
小花猫,喵喵叫着蹿起就逃
一别经年,爱恋依然鲜活
我追了几十年的那个她
却被我一不小心丢在
身后遥远的相思树旁
同桌的你
我有多少次把你气哭
在你新课本署名的上方
夸张地摞上我的名字
你的小拳头捶打在我胸口
那时,在你的文具盒里
每天都有一排削好的铅笔
还有裹着花纸的糖块
那时,我们纯洁得
像两支并排的铅笔
灯光下,当我举棋不定
一部小说的结局时
便想起了你
好想当面对你说出
迟到经年的那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