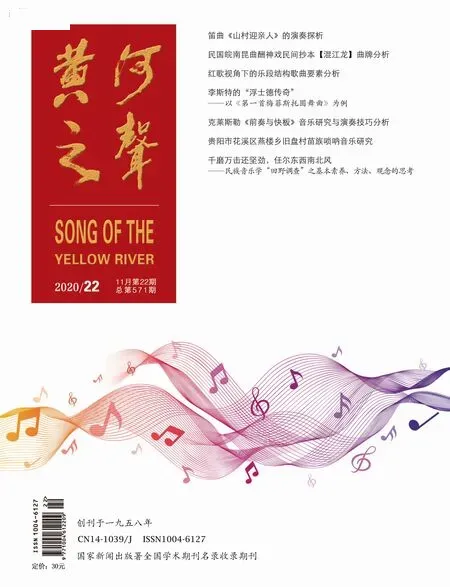大提琴演奏技术前沿问题探讨
◎ 张宇婧 (连云港市艺术学校)
大提琴及其作品经历了根本的改变。尽管过去时代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手法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大体发展成为一种完整的语言,但是当今个性化创作手法的增加不断地向演奏家和观众们提出新的挑战,需要我们迅速而连续不断地理解和吸收新的语言。器乐演奏家们从未面临过这样的困难:需要辨认出每个不同作曲家的新记谱法,掌握每一部新作品的新的技术要求,还得将无法记谱的音响世界令人信服地传达给听众。
一、转折点
变化的第一个象征是1915年左右的两个对比性的作品,科达伊的《无伴奏奏鸣曲奏曲》(作品第8号,1915年)和韦伯恩的《三首小品》(作品第11号,1914年)。科达伊浪漫风格的作品带有宏大的音乐气势,要求卓越的技能,具有“管弦乐配器”效果的大提琴,采用双颤音和自我伴奏的旋律,这首作品开发了扩展的五个八度音域和变格定弦,使其能够表现出独特的泛音,否则受限制的左手是不能演奏的。这首作品建立了一个未来50年都无可匹敌的精湛技艺的新标准。
相反,韦伯恩的作品第11号可能包含了曾经为大提琴创作的三个最短的曲子。这些清晰的结构通过使用靠近马子演奏和靠近指板演奏的对比、大跳、人工与自然的泛音以及从ppp到fff的极端的力度范围赋予丰富的色彩。节奏在当时被认为是复杂的,例如三对四的节奏,即上面是三连音四分音符,下面是四连音四分音符。
二、古典主义者
20世纪40年代及之后的许多作曲家采用传统的演奏技巧,例如马尔蒂努、普罗科菲耶夫、米约和埃利奥特·卡特的奏鸣曲。然而,在卡特的奏鸣曲(大提琴与钢琴,1948年)中采用了“韵律变换”的记谱方法,表示从一种速度到另一种速度的逐渐变化,它是整个作品的主要动机之一,以统一的思想贯穿所有乐章。速度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状态,各种变化的交织贯穿所有乐章。因此,当卡特开发的大提琴技术成为惯例时,智力的新领域已经被扩展,展现出感性认识的新层次。
三、序列主义音乐
随着20世纪40和50年代对序列音乐兴趣的增长,旋律和节奏成为碎片,创作的音乐更加复杂。随着对注重音响探索的增长,对大提琴的技术产生了影响。大提琴领域也得到扩展,与旋律片断相结合,促使演奏者掌握从一个音符跨越遥远的八度跳到另一个音符的大跳技巧。习惯于凭记忆演奏传统作品的演奏者突然发现他们自己需要计算!节拍经常地变化以平衡节奏能量和消除“拍子专制”,速度标记在不断的变动状态,需要掌握更高程度的智力体操。在这种风格中,“精确的速度”记忆和精确的音高不仅对于指挥而且对于大提琴家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四、开放曲式
随着序列音乐变得更加严格,作曲家开始意识到试图去严格控制所有音乐参数(音高、节奏、和声),努力让系统超载,导致混乱的因素出现。这种混乱表现的发现激发了一些作曲家的兴趣,为“开放曲式”的创作打开了大门。20世纪50年代早期采用这种方法创作的作品使演奏家承担一些创作决定。一些作品具有严密的结构,另一些作品则充分信赖演奏家的幻想和审美力。图示记谱法迅速在欧洲流行。彭德雷茨基的《齐格弗里德·帕尔姆随想曲》使用了传统的记谱法和新发明的代表某种演奏说明的符号系统(在开始部分有详细的解释)。这是一部炫技作品,它使用了靠近马子演奏、在琴马的另一边演奏、在拉弦板上演奏、左手敲击、与传统记谱法混合的一些段落。西尔瓦诺·布索蒂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主要体现在用美妙的图形乐谱勾勒外貌,其中有一些作品具有很难理解的风格,还有一些作品更具美感。
纵观历史,大提琴传统的记谱法记录了理想化的声音。然而,赫尔穆特·拉赫曼发明了一种精确的记谱系统,用他的图画指示大提琴家的身体动作。他为大提琴独奏而作的《压力》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审美原则,这里有许多声音是在大提琴琴身和弓子自身上产生的,造成了一个安静、神秘、几乎没有音高的音响世界。在琴马后面奏出混乱的具有摩擦声响的间奏,爆炸性地打破了这个气氛,只是在最后回到这个敏感的世界。这个作品并不是采用随意的方法写成的,相反是一部具有高度逻辑结构的作品,今天看来仍是很激进的作品。
五、噪音
随着嗓音的广泛使用,作曲家要求大提琴家叙述诗文、尖声喊叫,有时甚至是放声大笑,例如杰拉尔德·普莱恩的《浣熊之歌》。迪特尔,施内贝尔采用诗文创作了不同的作品,卡赫尔在其古怪离奇的《齐格弗里德普》中使用了深呼吸、哼唱、尖叫声以及呻吟声,且完全是用泛音写成的。詹姆斯·坦尼使用语言变音作为基础原材料创作其过分华丽的作品《我不是女人吗?》(大提琴、室内管弦乐队)。大提琴家首先朗读了索杰纳·特鲁斯的诗文(带有美国南部的口音),然后演奏旋律化的改编曲,接下去是管弦乐队精选相同内容的一部分,但这次是采用泛音,每一次的变奏逐渐将材料浓縮到精华。
六、新音响
20世纪60年代,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夏季学校聚集着世界上最富音乐思维创造力的音乐家,著名作曲家如施托克豪森、布莱兹、诺诺和贝尔恩德,阿洛伊斯,齐默尔曼等,以及与他们合作的孔塔尔斯基兄弟、齐格弗里德·帕尔姆和其他重要的器乐演奏家,他们的音乐成为音乐史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在他们的作品中,对电子音乐有重大发展的研究以及对音响深度的探讨超越了传统的限制,扩展了音乐的观念。整个乐器产生的声音首次被作曲家用来作为有效的创作材料。大提琴从尾柱到琴头都能演奏;常被作为打击乐器来处理;加入小提琴的音域;重新界定了大提琴在极快的速度和各种音乐表现力方面的能力。大提琴家有责任发展他们的技术和视奏技巧,以适应不同作曲家的个性语言和创作风格。
七、破除传统观念的人
随着风格上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由自由的思想家们创作的极具个性的器乐作品。克塞纳基斯的两个里程碑作品《阿尔法法则》和《科托斯》,是根据古希腊多臂巨人命名的,使他成为最富创造力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以建筑结构为基础,并利用随机变化过程和游戏理论。他是使用计算机的第一个重要的音乐家,在巴黎,他为UPIC计算机编写自己的程序。这些技术很大程度上预示了随后发生的计算机革命以及运用计算机作为创作的工具和助手。克塞纳基斯在《阿尔法法则》中运用大提琴造成静态(通过使用带有精细变化的微分音齐奏)与动态(泛音滑奏、常规滑奏、震音和移动片断的快速垂直运动)相对比。他也在记谱法方面有所创新,诸如微分音、程之间跳动、缓慢而有节奏的泛音滑奏、规定的慢速滑奏与控制精确速度节拍的对比,以及极限音域使得羊肠弦C弦(重新调音贯穿全曲,持续发出低而愉快的声音)的运用成为可能。他还通过在指板的顶端使用人工泛音扩充了较高的音域。最后的两行描绘出两个处于节奏和线条并列的声部,这两个声部互相交叉,只是在指板相反的两端才消失,这种技艺仅仅用左手是不可能完成的,但使用录音带或用非常快的琶音使之成为可能。
《科托斯》比《阿尔法法则》更加激进,开始用一种丰富而密集的声音(充满泛音)在琴马上面强奏,这是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最戏剧性的开场之一,引起“众神的恐惧”。这部作品的其他部分平衡了对比材料的障碍,建立了一种宏伟的结构,其创作技法包含静态的泛音,不同速度的双重滑奏,人工泛音的滑奏,微分音旋律音型片断,单元式重复的、跨越四根弦的、复杂节奏的和弦快速段落以及敲击-摩擦(用垂直的反复下弓不断地撞击和摩擦琴弦)等。这部在大提琴文献中里程碑式的作品,要求演奏家具备体力的和脑力的力量和绝对的耐力。
嘉丽娜·乌斯特沃尔斯卡娅的五乐章《大二重奏》(大提琴、钢琴,1952年)促使演奏者达到强度的极限,在大提琴上采用不断增强的滞韵律发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第三乐章要求使用低音提琴弓子以增加强度。尽管它的和声风格相当传统,但结构既独特又巧妙。在四个不停“加强”的乐章之后,音乐最终转为大提琴歌唱的一条延伸的旋律线,微妙地变化成一种崇高的冥想;钢琴不重要地插入源于第一乐章的材料。凯奇的作品《北之练习曲》表现出如此的难以完成,结果最终被纽约的彼得出版社放弃。这些练习曲要求最大可能地掌握大提琴技术,尤其是能够精确地跳动到指板及指板后任何一点的这种能力,演奏时不用要求揉弦,夸大了跳跃的难度以及不允许修正不准确的错误。这些练习曲控制在每个参数内一一音高、音色、持续时间和力度,并且需要对大提琴有深入地了解。
八、电子和计算机音乐
尽管是在瓦雷兹作品之后的许多年,但电子音乐的重大发展是在20世纪60、70年代。先驱者之一是马利奥,达维多夫斯基,他为大提琴与录好的磁带而作的《同步》第3首是这种风格的里程碑。大提琴经常被用来模仿合成的音响,通过使用拨奏、用弓杆演奏和泛音而实现。在其他作品中,探索大提琴与合成音响关系的是巴里,特劳克斯的《练习曲》和洛夫,盖哈尔的作品。盖哈尔通过使用滑奏、敲击音响、用弓杆演奏和充满泛音的声音给予这部作品更大的价值。乔纳森,哈维为大提琴文献增添了两部作品:其一是为大提琴与录音带而作的十分优美的作品;其二是为大提琴、合成器、计算机写的作品,采用很多四分之一音。费尼霍夫的《时间与运动研究II》实际上也属于这种类型的作品。
结 语
20世纪已经证明了创作语言的变形是与乐器技术和声音自身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大提琴作为独奏乐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表现力上赢得了新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