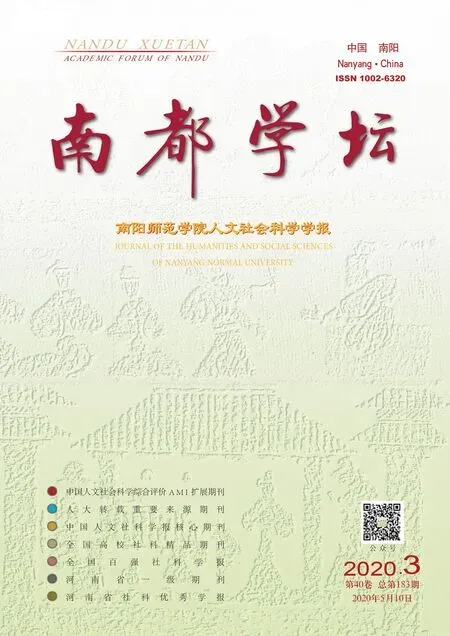乞灵而作,法无定法
——论韩东的诗歌创作思想
郭 海 玉
(南阳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河南 南阳 473061)
任何艺术工作的过程都可以假想地分为三个时期:一是积累素材时期;二是构思或者酝酿时期;三是写作时期[1]71。诗歌的创作过程也是如此,是诗人在审美情感的支配下,对素材进行创造性地改造、组合和传达的过程。韩东有近40年的诗歌创作和阅读经验,这些经验也涉及素材积累、艺术构思、写作传达三个阶段,不过由于他各阶段的观点常常散布各处或交缠在一起,因而这里将其创作思想提炼为灵感来源、诗歌写法和语言形式三个层面。这些层面的创作思想突出体现了韩东坚持思想独立、创作自由、独自创造的可贵品质。
一、灵感来源多样论
关于“写什么”这一诗歌素材、题材问题,韩东的原则一向是依凭兴趣而定。他认为诗歌的思想内容是“因人而异的”,最方便的是写自己“熟悉的”和“感兴趣的”,诗歌题材“没有高下之别,因为人没有高下之别,众生平等”[2]317。他的《只有石头和天空》中也有这样的诗句:“热爱石头和天空的画家/只画石头和天空/我想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没有比它更令人愉快的了。”[3]62明确了写诗要选择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题材还不够,灵感降临才是诗歌创作启动的真正契机。
灵感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本质上就是作家心底油然而生的一种具有“突发性”“无意识性”和“快捷性”的情感,通常被视为“创作不可缺少的机缘”和“天才的标志”[1]97-98。它长期以来也指文学艺术家们这样的创作状态,当创作冲动袭来时,创作者的激情如神魔附体,自动写下炽热的诗句或画下美丽的图画。韩东对灵感的认知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发展过程。起初,他视灵感为创作中的各种意外,认为这些意外重要、敏感而且娇弱,诗人写诗“不仅需要灵感,而且需要对灵感的理解力、控制力,需要对灵感的召唤和诱导的能力。它控制的部分不是灵感的部分,而是灵感的预热、滑翔以及灵感出现的时机。……人为地制造灵感,比如酗酒、吸毒,进入迷离状态。这种对灵感本身进行干预的做法不是长远之计”[4]。既然灵感如此重要和必需,那么它是从何而来的呢?古往今来,诗人、作家、哲学家们众说纷纭。柏拉图的灵感说影响巨大、传之久远。他认为灵感来自“神力的凭附”,当其降临时诗人会像巫师一样“代神说话”,最美的作品都是“诗神的作品”,而非诗人的作品[5]。柏拉图是古希腊时期秘教传统的继承者,因而有将灵感来源神秘化的倾向。韩东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还写过《我的柏拉图》,因而可能对柏拉图学说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灵感来源的理解却极为科学。他认为诗歌创作应该“乞灵于阅读,乞灵于情感抒发”,或者乞灵于“生活”,这里的“生活”特指“身边的、每日如此的、视而不见的、日常的”生活[6]。
所谓乞灵于阅读,是说诗人可以从广泛阅读中汲取创作灵感,比如当代诗歌、翻译作品、古典作品都可以成为自己“灵感的来源”[7],甚至哲学、宗教书籍也要涉猎。韩东就从毛泽东的《寻乌调查》、西蒙娜·薇依的《重负与神恩》《在期待中》以及一些宗教典籍、小说作品中获得过灵感和启发,因而写下了《寻乌的调查》《读薇依》《密勒日巴》《二选一》《食粪者说》《说一个故事》《没爹没妈的孩子》等具有互文意义、意蕴丰富的诗歌。
所谓乞灵于日常生活,是说诗人要重视观察和体验身边的生活,要能不断打破固有的经验框架,发掘出常人难以体味到的不凡诗意。就韩东的日常生活诗创作而言,笔者发现了他发掘生活诗意的四种途径。第一,韩东善于从生命初遇事物的新鲜感觉中来捕捉灵感,通过妙用语言来营造整体情境,以固定生命感官冲动。如《雨夹雪》一诗将雨雪同时降落时诗人瞬间的视觉所见、听觉所闻以及心中所想以感叹的简洁之语固定了下来:“雪珠,多么好听的名字/好听还因为落在车棚上的声音。”[3]141《重新做人》《我因此爱你》等诗则体现出韩东对感官惰性的高度警惕以及日常生活中追求新鲜感觉的自觉,感官化的叙述方式因此成为他这类诗的主要叙述方式。第二,韩东善于从身边事物的特征与相关人物存在状态的共性或关系中捕获灵感,以发现事物与人的意义关联。如《天亮以前》中诗人发现晨光渐亮、黑暗远逝的室外景象与室内入睡者、失眠者凌晨的精神状态之间存在着一致之处,即都处于阴暗和光明各占一半的临界状态,由此韩东领悟到对于事物和生命来说,“脆弱”是清晨的本质属性。韩东很多带有整体象征意味的诗歌都产生于这种诗意发掘方式,如《看不见的风》《风吹树林》《一盘散沙》等。第三,韩东善于从记录生活流变的过程中发现灵感,让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状态在对比中滋生诗意。如《水渠》一诗的灵感来自韩东早年的下放生活,写诗时他正陷入离婚后个人生活混乱的状态,诗歌的静谧意境与他矛盾复杂的内心感受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二者的镜像关系传达了他在现实中再也寻不到简单朴素之美与劳动快感隔绝、无法获得平静的无奈和感伤。而《常见的夜晚》一诗的灵感则来自现实生活中生客初到家中的细腻感受,对此种感受的书写构成了对未来生活中主客关系疏远的预言,这种预言性也是诗意的诞生地。第四,韩东善于从普通人日常的精神状态中发掘灵感,将人物的品行美、精神美等提炼为不平凡的诗意。比如《这家麦当劳》《卖报纸的》两首诗各以侧面描写、特写式手法等来突出表现店主的仁慈善良和卖报人的求知如渴、专心致志。
所谓乞灵于“情感抒发”,是说诗人要善于从遭遇外部刺激后产生的复杂情感中捕捉灵感、为情赋形。如《孩子们的合唱》中就容纳了韩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某种情感,他抓住这种情感力量后将其提拉出来,形成文字后“有一种终于说了出来的畅快”[8]。再如韩东诗歌《明月降临》《黄昏或悲哀》等灵感的产生都源自他调动自己的情感和想象深入到事物内部去体察时感受到的物我交融、主客合一的情感体验。
韩东的诗歌灵感观源自他丰富的创作经验,毫无将灵感神秘化的倾向。而在文艺学中,“灵感”也被定义为“一种由长期的意识工作的成果在无意识心理层面所获得的意外收获”[1]97-98。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韩东的诗歌灵感观是科学的灵感观。近些年,韩东的诗歌创作格言中又出现了“灵感”一词:“一挥而就、立等可取、随笔式才子型听凭灵感充满快感及生理冲动的写作(诗歌)到此为止。既因为不得已,也要自觉如此。艰涩、质朴、幽深、广大、严谨、玄妙之诗我心向往之。”[9]从中可知,韩东已从重视创作机缘或灵感的启动生成向重视创作过程尤其是创作结果转移,这可看作是韩东创作经验不断丰富升华的结果,也可视为他对诗歌更高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的一种自觉追求。
二、诗歌写法多元论
这里的“写法”是指诗歌的创作原则、技巧和手法。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家们习惯将文学的创作原则概括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四大类,对于诗歌创作原则的划分也大体如此。韩东从来不迷信大师系统或文学传统,也特别反感那种企图以一种写法“一统江湖”的做法,他始终强调“任何形式和方法在运用者那里都有变化,最大的不同就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有法无定法”[2]317。也就是说,法无定法是韩东诗歌创作思想的核心内容。近些年他又明确提出“多元”乃“当今诗歌世界的第一大法”[10]373以及诗歌系统“多元”的思想。
韩东诗歌写法多元思想植根于他丰富的读诗写诗的经验中。自1980年至今,韩东一直秉持自行其是的写诗方式,从来不受各种创作原则的拘囿,总是服从诗意传达的需要去寻求适宜的写法。如他早期的诗歌《给初升的太阳》《我是山》《山》《一个黎明》《果实》等,受到了民刊“《今天》诗派”建立在移情说和象征体系之上创作方法的影响;而创作转型期的《山民》《老渔夫》则流露出受小说人物描绘和叙事手法影响的痕迹;再到诗艺成熟期的《两只拖鞋》《雪粒》《黄昏或悲哀》《雨季》《阴郁的天气》《进沟》《风吹树林》等诗歌,则以景象或事件的客观写实为基础追求整体意境的象征性,这类诗中象征性的意象就是心理学意义上的感觉性经验体,在呈现客观事物的真实存在的同时也呈现了自我的心像,因此这类诗歌其实将写实与象征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故而也可称为“整体象征”。除了结合自己的写诗经历来思考诗歌的写法问题,韩东还从当代诗歌丰富的写作历史和现状出发认识到,“非非”的流水账式、伊沙一路的特写镜头式、春树的代言式、乌青的游戏式和他自己的整体象征式[8]都表明诗歌写法的确是自由多元的。
诗歌写法的自由多元必然导致在整体格局层面诗歌系统的多元。韩东诗歌系统多元思想的生成和提出受到了杨黎诗学思想的直接激发,也源于他对自己这代人群体性诗歌行为的反思,也与他的宇宙观、社会观、精神观和艺术观密切相关。近些年,杨黎提到“好诗都是一样的”,诗歌领域多元系统无法并存,韩东表示不能苟同,认为“不一样的才是好诗”,多元系统可以并存,韩东所谓的诗歌系统多元是指当代诗歌可以有许多诗歌品种、观念或系统,多元之间价值平等且无高下之分,但一元之内各作品之间由于有相对一致的传承、准则和规范,因此有高下之分和本系统内的相对价值[11]。韩东的这种认知与他对20世纪“第三代”诗人蔑视官方文艺、反叛“《今天》诗派”的写作方式、对峙“知识分子写作”等诗歌行为的反思分不开。他认为,在中国社会多元化进程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自己这代诗人对艺术多元的追求在成为“带动力量”的同时也被视为“一种危险”,大家在“抵抗作为主流的庞大的一元”并开创了“各自有效的方式和写作路径”的同时,受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成长经验和生理衰老导致的专断倾向的影响,还都心怀“大一统的想象”,“对文艺‘正道’唯一合法的理解演变成了现实层次取而代之的愿望”,并毫无通融地否定“他人的创造”,“对现代文学、艺术整体格局瞻前性的思考”也有所欠缺,因此可谓“成也这代人败也这代人”[11]。如果说,当代诗坛多元化的格局是韩东诗歌系统多元思想产生的诗学语境的话,那么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和他多元的宇宙观、社会观、精神观和艺术观就是其产生的思想基础。在《诗歌多元论》中,韩东强调人类精神不能一次性地掌握宇宙真理,因而只可设想宇宙整体包含诸多宇宙的并存,现代人类社会的构成本身也是多元并存的,因此探索宇宙、社会和生命自身的人类精神必然也是多元并存的。在此情形下,与不稳定的人心和多变的时代精神遥相呼应的艺术也肯定是多元的,因此多元并存、彼此激发才是艺术世界的根本诉求,而一元独霸则意味着艺术之死。
韩东的写无定法和诗歌系统多元思想最早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他与同代诗人也以极富实效的创作实践推进了当代诗歌多元局面的形成。近些年,他的这些思想以诗论的形式出现在当下,因涉及诗歌的创作原则和方法问题、文学艺术的总体格局以及对不同系统的诗歌或文学艺术的公正评价问题,所以其诗论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合理健康的文艺写作和批评生态的形成。韩东之所以能够对自己和同代人的诗歌实践做出历史反思,与他破除我执的多年修行密切相关,因为自我的弃绝也就意味着对源自“文革”时代的对立性思维方式的根本弃绝。在此意义上可以说,韩东的超越自我精神、历史担当意识和实事求是态度值得赞赏。
三、语言形式多样论
关于“怎么写”的问题,仅在理论上明确“写无定法”原则和诗歌系统多元思想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文本层面对以往的诗歌经验进行总结。在诗语的来源和模式方面,韩东主张诗语应该以口语为原生地,汲取各类语言的营养以比较口语化的语言或普通话(而非口头语)来写诗。在诗语的形式层面,韩东提倡发掘自由体诗歌分行术的潜力,主张分行体诗歌形式应该多样化。在诗语与诗的关系方面,韩东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意在否定诗语工具论,强调诗语本体论;新世纪后韩东将诗与真理相连,超越了诗歌语本观,把诗歌语言视为导向绝对、真理或超自然的手段,走出了一条独具个人特色的诗学探索之路。
第一,韩东把口语视为诗语的原生地,主张诗语来源和模式的多样化。20世纪80年代初,针对“《今天》诗派”雕琢唯美的意象语言,韩东率先开始了当代诗歌的语言革命,《山民》《有关大雁塔》《你见过大海》等先锋诗作拉开了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序幕。面对诗歌界将他和“第三代”诗人的先锋诗普遍称为“口语诗”的现实,韩东后来强调充满“生动性、不稳定性、冲突、流动、变动”[12]的口语并不是诗歌语言,而只是其“原生地”,“翻译语言”“外来语”“古代汉语”“方言”等都要进入其中“搅拌、发酵”,如此“诗人们的语言之树才能从此向上茁壮成长起来”[13]。在诗歌持续边缘化的全球时代,韩东还强调当代新诗单走西化或走民族化的路线都不可取,“庞杂、活跃和变动不居”的“现实汉语”才是诗人“创造的前提”[14],诗歌就是用自然的语言方式来做作,是“自然的做作之语”[10]362。近期他又将诗歌自然的语言方式明确地指称为“普通话”,认为“当代诗歌不在于口语与否,而在于普通话与否”,其“在语言层面的分野准确地说就是普通话和所谓文学语言的分野”,他明确反对使用方言来写诗[15]。韩东理解的“文学语言”是指外行比较难以理解的专业语言,普通话则指与当代汉语书面语构成一体关系的标准化口语,这种“毫无特色的‘空的语言’”被他视为诗歌写作的起点,“实”的“语言的诗”是诗歌写作的终点[16]。
由上可知,韩东多年来所说的“口语”其实是指广泛吸收了各类语言的营养经口语化处理后像标准的普通话那样自然、直接、简单、清明的语言,“归真返璞”是这类语言最高的美学追求。这种语言诗学思想使韩东诗歌的语体面貌发生了历史性改变,“由书面语逐渐取代了早期诗歌中的口头语”,且其“书面语同时兼具‘民谣体’的直爽明快和‘翻译体’的弯曲迂回”[17]。
翻开韩东诗集还可以发现,他的诗语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比如爱情诗多使用抒发自我情感的抒情语言,日常生活诗、游记诗则多使用反映事物意义的叙述语言。很多诗歌还运用了带有象征色彩的“梦的语言”和智性语言。韩东曾在《梦的语言》一文中写道:“我的确试图用梦的语言进行写作”,“梦的意义”是梦中事物的组织序列,“梦的逻辑的语言表现”就是“象征”[18]。他还进一步将自己诗中的隐喻概括为随意的隐喻和“展现事物间根本性的象征关系的基本的隐喻”[4]。而一般文学中的“象征”简单说来就是指以事物的具象寄寓作家的深刻思想或领悟的事理的修辞手法,因此这里的“梦的语言”就是展现事物与“我”之间根本性关系的象征语言,即一种“对客观世界与主观感受契合关系的发现和表达”[19]。智性语言,如《人类之诗》《这儿那儿》《重新做人》等诗中表达诗人对生存环境的批评或反讽态度的诗句等。可见,韩东丰富多彩的诗语模式表明,他反对诗语模式的单一,崇尚诗语模式的多样化。
第二,就诗语排列形式而言,韩东自始至终主张诗语分行排列、形式多样。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韩东就积极尝试从译诗、小说、绘画以及影视艺术中汲取营养,创造出了叙述性强、画面感十足、蒙太奇手法和结构方式运用自如的许多诗歌文本新样式。在广泛的创作实践中,韩东也逐渐认识到诗语形式的“不确定”在激发创造潜能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我在不断否定自己的诗,努力想找到一种适当的形式。所以,我各种形式都尝试着写,儿童眼光看世界的,英雄高度看世界的,平淡的,华丽的等等都试着写。并且我不想过早地固定在一种形式上,也许永远不固定在一种形式上。这样,内心就时刻在冲动、不安,不能平静,而且很混乱……我想,这也许是创造的根据所在。”[20]韩东不仅对自己的形式实验持开放的态度,而且对其他当代诗人的各式实验也基本持肯定态度,但是两种极端做法除外:一是“否认传统诗意(抒情、唯美、隐喻、所指)”,认为“诗完全依赖于外在分行”;二是否认诗歌的分行体形式,认为诗“不依赖于任何外在形式或样式”可以独存,如散文式的诗。韩东主张现代诗人应该思考“如何在承认分行术的潜力和全新诗意确有可能的前提下”将“二者结合”[21],这其实就是倡导现代分行体诗歌要以全新诗意为据,力求诗语形式的多样化。
第三,在语言和诗歌的关系方面,韩东反对语言工具论,提出“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为新诗注入语本观念;新世纪后他又将这一口号修正为“诗从语言开始”导向“超自然”,某种程度上虽然否定了诗歌语本观,但仍强调诗人在重视真理的同时也应重视语言。
韩东初入诗坛时,诗歌语言工具论思想很盛行,即把诗歌语言视为表达思想观念或承载意义的工具,担负着指涉现实和承担道义的功能,如“归来”诗人和“《今天》诗派”就持这种观点。韩东等“第三代”诗人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和形式主义文学作品的影响,在彼此的交流中产生了诗歌语言本体思想,韩东率先提出了“诗到语言为止”的口号。该口号流传开来后引起广泛的误读和争议,这促使韩东在1987年后对其内涵做了多次的说明。总体来看,韩东的多次解说意在阐释口号中“语言”和“止”的内涵以及口号的表达“意向”。
他强调,“诗到语言为止”中的“语言”不是指语言学意义上的“与诗人无关的语法、单词和行文特点”,而是特指与诗人的生命体验“高度合一”的语言[22],也可以说是语感——“语言是公共的,生命是个人的,而它们的天然结合就是语感,就是诗”[23]。因此这一口号也可以改为诗到“语感”为止。而口号中的“止”特指“停止”“最终目的”,即是说诗歌不以“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或其他”方面的目的为目的[24],而以语感为最终目的,语感在诗中成为唯一的经验对象。这其实是在强调诗歌语言的审美功能而否定其实用功能,从而否定了以往功利化的语言工具论思想。韩东还指出,这一口号意在强调诗人们要“抽空各种观念”后直接面临事物,并要具有平衡抒情的内容和语言形式的能力[7],“回到诗歌本身”是这一口号的不同提法[24]。可见,韩东此时的诗歌本体观是一种生命和语言一体同构的本体观。“非非”诗人杨黎后来把韩东的口号修正为“诗从语言开始”,韩东表示赞同,但新世纪后又将其修正为“诗从语言开始”导向“绝对、真理、超自然”[25]。在韩东的诗学话语中,超自然是指世界的起源和开端,宇宙万物的根基。他认为诗歌的叙述语言不只要照射事物的意义,在极限处还要照射虚无、绝对、超自然、真理,因此语言自身不是诗歌的最终目的,而只是照射事物的意义和超自然的手段,这就否定了他先前的语言本体思想,突出体现出他将诗与真理挂钩的创作意志。当然,韩东也强调“写作者重视语言,重视生而为人以及超越性的真理并不矛盾,或者,应该将这些矛盾带入写作中解决”[26]。也就是说,韩东既强调以生命体验为本,又强调重视语言,其实是说诗人应力求在具体复杂的实践中做到内心体验与语言形式的高度合一。
曾有不少研究者给韩东诗歌贴上“纯诗”“口语诗”“抒情诗”“哲理诗”“叙述性诗歌”的标签,给韩东附上“口语诗人”“形式主义者”“抒情诗人”“哲学家诗人”的标签,这些都仅仅切中了其诗其人的部分特征,某种意义上遮蔽了其诗语的整体面貌和语言诗学思想的完整内涵。因为“多样”才是其诗歌语言的来源、模式和分行形式的主要特征,也是其多元创作思维的生动反映。总之,韩东的诗歌创作博采众长,突出体现了他锐意打破语言壁垒、文学体裁和艺术门类壁垒、诗歌写法壁垒等的独尊创造的自由精神,韩东诗歌创作之路也启示我们:在跨文化、跨学科、跨艺术和跨文体的交流与合作日渐成为一种流行趋势的时代氛围中,博采众长的诗歌跨界写作,是与诗歌系统内的民族化和西化创作路向、诗歌系统外的“跨界诗歌”(1)“跨界诗歌”是诗人、戏剧家从容在2012年提出的概念,用来指把诗歌与音乐(民谣、摇滚乐)、诗歌与戏剧(比如诗剧)嫁接起来的做法。其共同点在于都致力于将诗歌融入音乐、戏剧等别种艺术形式之中,在拓宽诗歌传播路径和空间的同时,也削弱了诗歌形式的独立性。韩东诗歌的“跨界写作”是在保持诗歌独立形式的前提下,将其他艺术元素引入诗中。创作路向迥然不同的新路向,它预示了一种可以期待的诗歌美学新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