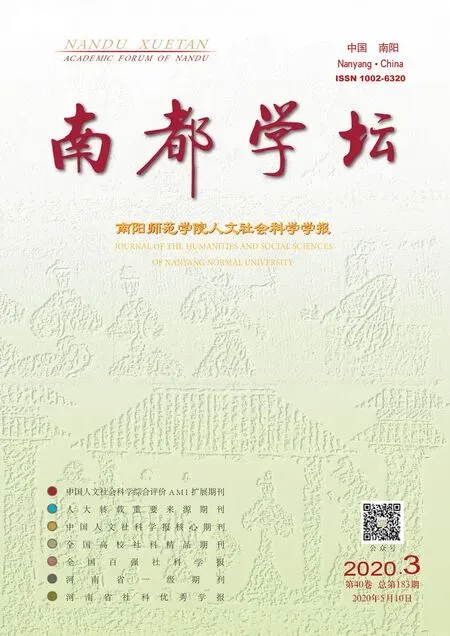欧阳修的易学认知、诠释及其思想
姜 海 军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兵部尚书等职。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经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经学革新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在经学研究上,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开一代风气。正如朱熹所言:
意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欧阳修)、原父 (刘敞)、孙明复(孙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 (李觏) 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意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1]
庆历之际,随着北宋王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加剧,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积极倡导政治变革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之外,也对经学的“墨守”产生了不满,希望改变宋初经学即唐学的现状,倡导阐发《周易》《诗经》《春秋》等经典中的思想义理,以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从而开启了庆历之际的“经学变古”。欧阳修在易学方面多有贡献,并撰有《易童子问》《易或问三首》等书籍,对《周易》作者、解易思路、易学思想等做了一定的阐释,这对于当时的易学、儒学都有积极的影响(1)对于欧阳修的易学,也有学者对此作了探究,比如:张毅《欧阳修的易学与政治》,载《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欧阳修的易学研究与古文文风转变》,载《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罗利《欧阳修易学思想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可以说,了解欧阳修易学对于理解他的经学、政治理念及宋学范式的建立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易传》“皆非圣人之作”
对于《周易》,欧阳修相信《周易》经文、《易传》中的《彖》《象》两传为圣人孔子所作,但他认为《易传·系辞》不是,他在《易童子问》卷三更进一步强调《易传·系辞》以下皆非孔子所作,如其所言:
童子问曰:“《系辞》非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乱,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学《易》者,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其择而不精,至使害经而惑世也。”[2]1119
夫谕未达者,未能及于至理也,必指事据迹以为言。余之所以知《系辞》而下非圣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丛脞而乖戾也。盖略举其易知者尔,其余不可以悉数也。其曰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又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云者,质于夫子平生之语,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观乎彖辞,则思过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圣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数同,而《乾》《坤》无定策,此虽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于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说卦》《杂卦》者,筮人之占书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犹皆迹也,若夫语以圣人之中道而过,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则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2]1123
欧阳修认为,《系辞》以下包括《文言》《说卦》等都不是孔子所作,主要原因是语句“杂取以资其讲说,而说非一家,是以或同或异,或是或非”、思想“繁衍丛脞而乖戾”,为此他举《文言》《说卦》《系辞》《杂卦》里面种种“繁衍丛脞”之说来证明这些都不是“圣人之作”[2]1123。比如他对《易传》中关于八卦起源的认知:
河图之出也,八卦之文已具乎,则伏羲授之而已,复何所为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须人力为之,则不足为河图也。其曰观天地、观鸟兽、取于身、取于物,然后始作八卦,盖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义,其创意造始其劳如此,而后八卦得以成文,则所谓河图者何与于其间哉?若曰已授河图,又须有为而立卦,则观于天地鸟兽,取于人物者皆备言之矣,而独遗其本始所授予天者,不曰取法于河图,此岂近于人情乎?[2]1122
童子曰:“敢问生蓍立卦之说?或谓圣人已画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义可知矣。其(《说卦》)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者,谓始作《易》时也。又曰‘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谓前此未有蓍,圣人之将作《易》也,感于神明而蓍为之生,圣人得之,遂以倚数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尔。故汉儒谓伏羲画八卦由数起者,用此说也。其后学者知幽赞生蓍之怪,其义不安,则曲为之说,曰用生蓍之意者,将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数起之义害于二说,则谓已画卦而用蓍以茎,欲牵合二说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义,岂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显,则大衍之说是已。大抵学《易》者莫不欲尊其书,故务为奇说以神之。至其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2]1123
欧阳修认为,如果八卦是由河图产生,那么伏羲只是传承者,而不是创作者。如果说,八卦是伏羲所做,那么八卦就与河图没有关系。另外,伏羲俯仰取物,画八卦,那就说明八卦、河图没有关系,所以出现了“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就是逻辑上的谬误。此外,欧阳修认为既然伏羲画八卦,那么蓍草则是用来筮占的,并“倚数而立卦”。但是,汉儒认为伏羲画八卦是根据数字而产生,即“卦由数起”,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如其所言“其自相乖戾,则曲为牵合而不能通也”,等等。欧阳修为了说明《易传》中语言堆砌、前后矛盾的状况,举了很多例子,以此来说明《易传》并非孔子所作。
当然,欧阳修对《易传》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驳斥汉唐以来的象数之学、图数之学的诸多谬误,其说自然也遭到了时人的怀疑和反对。不过,欧阳修对《易传》的怀疑有一定的道理,所提出来的《易传》非孔子所作这一说法,近现代以来很多学者也肯定了这一点,如李镜池所说“《易传》之非孔子作,欧阳修在宋初早就怀疑了”[3]。朱伯崑先生在其《易学哲学史》一书中肯定地说道,“近人同样认为十翼非孔子所作,几乎成为定论”,并强调《易传》非孔子所作,“《易传》各篇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乃战国以来陆续形成的解易作品”[4]。
可以说,欧阳修《易童子问》对《易传》的质疑,并非为了反对经典与孔子,而是为了打破汉唐以来所形成的传记系统解经的模式,如他所说“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希望发扬中唐啖赵学派“舍传求经”解经方法,直接从《周易》经文入手,探究圣人之道,从而建立全新的易学体系、儒学思想。的确,欧阳修对经传及汉唐注疏之学的怀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人们对于儒家传记、汉唐注疏之学的迷信,加速了汉学范式的瓦解。反过来讲,欧阳修这种“舍传求经”的思想,推动了宋代义理易学以及新经学的发展。
此外,在欧阳修的影响下,很多学者为了重新理解易学、圣人之道,对汉唐之际所形成经传合一的《周易》文本有所怀疑,并倡导恢复《周易》的古本,亦即经传分立的本来状态,以此来探究《周易》之意、圣人之道。此后宋代诸儒恢复《周易》古本成为当时易学研究的重要现象之一,这一点正如四库馆臣所言:“古《易》上下经及‘十翼’,本十二篇。自费直、郑元以至王弼,递有移掇,孔颖达因弼本作《正义》,行于唐代,古《易》遂不复存。”宋儒对《周易》古本的探究,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阳修等人对经传的质疑,由此引发了人们对原始儒家经典的探究,进而纷纷就自己的理解对《周易》及其思想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而促成了北宋新易学、新经学的兴发,此后晁说之、吕大防、吕祖谦、朱熹等人都推崇古本《周易》,开启了宋代易学研究的新领域。
总之,欧阳修怀疑孔子作《易传》的观点,并非独树一帜,而是对宋初以来疑经惑传思潮的继承与发展。毕竟,从宋代开始就有王昭素、范谔昌等人怀疑《易传》非孔子所作[5]106,欧阳修有可能继承了这一说法,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由于欧阳修在当时的影响力,他质疑孔子作《易传》的观点对孔子权威地位、《易传》以及基于《易传》解释易学的汉唐经学体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这种淡化《易传》义理之学的倾向,对于北宋中期应对佛老之学的挑战极为不利。毕竟,《易传》从汉代之后一般都被视为孔子思想的精髓,更是义理易学的理论基石,如此言论对于儒家化易学无疑产生了消解作用,因此遭到了当时维护孔子易学的王安石、程颐等理学家们的批驳。如王安石曾说:“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6]程颐也说:“圣人文章自深与学为文者不同。如《系辞》之文,后人决学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为之者,或有绘画为之者,看时虽似相类,然终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7]
二、注重义理思想,关注现实“人事”
欧阳修对《周易》经传的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改变唐代初年以来王弼、孔颖达易学占主导地位的经学,也是为了改变汉唐之际流传的经传注疏之学。所以,在易学、经学领域,欧阳修强调义理之学,为此他对倡导义理之学的王弼之学给予高度称赞,如其所言:
《易》之为书无所不备,故为其说者,亦无所不止。盖滞者执于象数以为用,通者流于变化而无穷,语精微者务极于幽深,喜夸诞者不胜其广大,苟非其正,则失而皆入于贼。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而不失其正,则王氏超然远出于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业也。[2]949
呜呼!文王无孔子,《易》其沦为卜筮乎!《易》无王弼,其沦于异端之说乎!因孔子而求文王之用心,因弼而求孔子之意,因预言而求弼之得失,可也。[2]303
欧阳修认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所以他认为那种专注于象数之学的人,既不能真正洞悉易理,而且以其夸大其词,使得易理得不到正确的认知。在他看来,《周易》非义理之学不能明了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的道理,由此他盛赞王弼之学,认为他超越了象数之学,真正把握了《周易》思想的精髓。
尽管欧阳修盛赞王弼易学,但是在解释易学的过程中,他对于王弼易学也多有驳正,对此朱熹就曾说:“欧阳作《易童子问》,正王弼之失数十事。”[5]111这种对王弼易学驳正的做法,也有可能受其好友王洙的影响,王洙曾撰有《周易言象外传》《古易》等著述,就对王弼易学之失多有驳正。《中兴书目》称:“《周易言象外传》十卷,侍讲王洙撰,凡十二篇。《序》云:‘论次旧义,附以新说,以王弼《传》为内,摘其要者,表而正之,故云《外》也。’”叶梦得称王洙《古易》“今本各以《彖》《象》之辞系每卦之下,而取孔氏之《传》谓之《系辞》者,王辅嗣之误也”[5]108。欧阳就对于王弼易学的驳正,主要体现在一些具体卦爻辞的解释之中,
欧阳修对于易学的重视,并非像汉唐之际的学者那样,借助易学诠释宣扬象数之学、天人感应的思想。在欧阳修看来,《周易》乃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人事才是易学、经学的关键所在,如其所言:
自尧、舜、三代以来,莫不称天以举事,孔子删《诗》《书》不去也。盖圣人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绝天于人则天道废,以天参人则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于后世也。然则天果与于人乎?果不与乎?曰:天,吾不知,质诸圣人之言可也。《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此圣人极论天人之际,最详而明者也。其于天地鬼神,以不可知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则昃,盛衰必复。天,吾不知,吾见其亏益于物者矣。草木之成者,变而衰落之;物之下者,进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吾见其变流于物者矣。人之贪满者多祸,其守约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见人之祸福者矣。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则因其著于物者以测之。故据其迹之可见者以为言,曰亏益,曰变流,曰害福。若人,则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恶。其知与不知,异辞也,参而会之,与人无以异也。其果与于人乎,不与人乎,则所不知也。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远之; 以其与人无所异也,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8]
欧阳修认为,从尧、舜、三代以来,人们莫不重视天,即使孔子删定《诗》《书》,也没有删掉关于天的语句。不过,在他看来,尽管天非常重要,圣人也没有摒弃它,但是,在现实中,天道幽远,即使是圣人、《周易》也是存而不谈,只有人事、人道才是最为重要的,“于天地鬼神,以不可知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所以,他认为天地鬼神尽管莫测,但是多体现在人事之上,注重人事,自然也就是注重天意,“人事者,天意也”。欧阳修易学对人事的重视,也是他对佛老之学的态度,他注重人事,尤其注重儒家的人伦道德、纲常名教,所谓“修其本以胜之”,这种做法与韩愈、石介等人极端的做法相比较自然有很大的进步。
可以说,欧阳修的易学,注重义理,更注重人事,罕言“性与天道”,故他多次借助易学诠释来表达对现实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关注,如其所言:
所谓辞者,有君子、小人、进退、动静、刚柔之象,治乱、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学者专其辞于筮占,犹见非于孔子,况遗其辞而执其占法,欲以见文王作《易》之意,不亦远乎!凡欲为君子者,学圣人之言;欲为占者,学大衍之数,惟所择之焉耳。[2]302
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人之际罕言焉,惟《谦》之《彖》略具其说矣。圣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无以异也。然则修吾人事而已,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2]1109
治乱在人而天不与者,《否》《泰》之《彖》详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尽矣。[2]879
童子问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何谓也?”曰:“其传久矣,而世无疑焉,吾独疑之也。盖圣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执于象也,则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阙文多矣。”[2]1107
欧阳修借助易学诠释,认为圣人借助《周易》所表达的主要是对人事的关注,“圣人急于人事者也,天道之际罕言焉”,易理重在人事而不是天道。所以,在他看来,《周易》中的系辞所说的都是关于君子小人出处进退之道、治乱兴衰与得失吉凶之理。即使是具体的卦爻、十翼等所言也都是具体的人事,如《谦》《乾》《泰》《否》等都是如此。比如:
盖君子者养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长,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几乎天下矣,则必使小人受其赐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养小人。《夬》,刚决柔之卦也。五阳而一阴,决之虽易,而圣人不欲其尽决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穷也”。小人盛则决之,衰则养之,使知君子之为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极而必反,不可以不惧。[2]1114
在欧阳修所处的时代,君子小人之争非常激烈,尤其是在范仲淹、欧阳修推动的庆历新政之际更是如此。在欧阳修看来,君子小人的关系并非冰火不容,可以因势利导,利用小人。所以,他借助解释《夬》卦表达了这个想法,他认为《夬》卦有五个阳爻一个阴爻,象征着君子昌盛,小人衰微,但是在这种情形下,欧阳修认为不要消灭阴爻所代表的小人,而是要给小人一定的恩惠,“君子养小人”,这样小人不仅不会坏事,反而感恩君子,由此促成君子事业更加兴盛。这种思考,实际上也是欧阳修变法失败之后的反思。这也是欧阳修易学的重要特色所在,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欧阳易学主张切于人事,而于人事关注的焦点,大体锁定在君子的养成和君子从政的方法、原则上。”[9]实际上,欧阳修的《易童子问》本身就是对自身政治理念与实践的反思,更是对当时思想文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他基于易学诠释,所提出来的一系列的经学、儒学思想,对于之后宋学范式的形成及政治理念都奠定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基础。
总的来看,欧阳修重视义理易学,打破了宋代初年注重章句注疏之学的传统,更是打破了孔颖达《周易正义》所影响的学术范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宋初三先生”、程颐等人对义理之学的重视,更是推动了儒学理论的发展与更新,为宋学范式的确立奠定了学术思想基础。另外,欧阳修的易学解释充满了对人事的关注,尤其是对君子如何执政、出处进退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他通过易学来宣传其变革思想与政治理念,这些不能不说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推动了社会政治的变革。当然,欧阳修对义理易学的重视,实则也是对当时图书易学盛行的一个回应,他曾说:“如《河图》《洛书》,怪妄之尤甚者。”[2]615当时的刘牧、周敦颐、邵雍等都极言象数之学,并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这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人们对人事的关注。欧阳修重视义理易学、重视人事,实际上是为了改变当时的学术风气,进而改变宋初以来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
三、“以史证易”及其思想旨趣
正是由于欧阳修重视人事,所以,他在易学解释的过程中多突出政治治理、明德自修等内容,而几乎不言象数,也不言性与天道。为了阐明其政治理念的客观真实性,欧阳修还在多处采用“以史证易”的方法证明之。如《易童子问》中记载他与童子的问答:
童子问曰:“‘《师》,贞丈人’何谓也?”曰:“师正于丈人也。其《彖》曰‘能以众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问可以王矣,孰能当之?”曰:“汤、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其为毒也甚矣。然以其本于顺民之欲而除其害,犹毒药瞑眩以去疾也。故其《彖》又曰‘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童子曰:“然则汤、武之师正乎?”曰:“凡师必正于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汤、武也。汤、武以应天顺人为心,故孟子曰:‘有汤、武之心则可也。’”童子曰:“‘吉,无咎’何谓也?”曰:“为《易》之说者,谓无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补过也。呜呼!举师之成功,莫大于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仅得补过、无咎,以此见兵非圣王之所务,而汤、武不足贵也。”[2]1108
欧阳修借与童子的设问形式,来解读《周易》中所蕴含的政治哲理。在他看来,《师》卦所讲为出师征伐之意,所以面对童子的问题,即谁可以称王天下这个问题。欧阳修认为只要以民为本,顺天应人自然可以称王天下,为此他援引汤武革命的历史史实,以证明只要顺应民心,征伐也会得到民众的拥护,进而称王天下。换言之,欧阳修强调为政治国、出师征伐都应当以民为本,唯有如此,才能称王天下。当然,他也反对战争,“兵非圣王之所务”。
欧阳修“以史证易”的做法,充满了现实的考量。在欧阳修的易学诠释中,他认为无论是君主,还是君子都应当在社会政治中发挥表率作用,一定要刚健有为,“用晦而明”,如《易童子问》中就如此说道:
童子问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何谓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万物各得其随,则君子向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则君子出而临众,商纣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发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则圣人贵之乎?”曰:“不贵也,圣人非武王而贵文王矣。”[2]1111
欧阳修认为君子、君主的地位都非常重要,不能等闲视之,所以身处不得志之时,也要刚健有为,唯有如此,方能“出而临众”。为此,他举商周之际的社会政治,周文王、周公等人励精图治的精神,以此来暗示为君之人一定要顺势而为。
纵观来看,欧阳修借助历史来解读《周易》,实际上是将易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找到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办法,也为他的儒学思想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历史依据。这种“以史证易”的做法,在郑玄、孔颖达等人的易学中都有所呈现,这对于后来程颐、苏轼、王安石、李光、杨万里等人“以史证易”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启发影响作用。进而言之,欧阳修注重“以史证易”,实际上也是他注重思想义理的一个重要体现。
正因为如此,欧阳修极力宣扬易理与人事,宣扬对现实的关注,极力批判当时流行的佛老之学,而对于儒家“性与天道”的思想则鲜有关注。如其所言:
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与吾子卒其说。修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动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恶是非之实录也。《诗》三百〇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兴衰之美刺也;《书》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尧、舜、三代之治乱也;《礼》《乐》之书虽不完,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然其大要,治国修身之法也。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至于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故虽言而不究。[2]668-669
在欧阳修看来,无论是易学,还是经学都应当以人事为主,重在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故面对当时开始流行的性理之学,欧阳修都是给予反驳,他认为易学及儒家经学所言都不应该强调性理之学。欧阳修针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性理之学颇为反感,认为儒家经典包括《周易》所言都很少谈及人心人性,而主要谈的是人事,亦即有关吉凶善恶、治乱兴衰之事,“六经之所载,皆人事之切于世者,是以言之甚详”。
毕竟,欧阳修作为当时的主要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事务的解决,而不是注重儒学理论的建构,这与同时代的邵雍、张载、二程等人有很大的不同,也与之后的王安石的有所不同。正是因为如此,欧阳修借助易学解释的形式,为当时君子为政、治国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畅言人事,强调人事与社会政治的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在他看来,人事就是天道,“人事修,则与天地鬼神合矣”。在他看来,“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动静得失吉凶之常理也”[2]669。可以说,欧阳修对“性与天道”的思想鲜有谈及,而是积极关注人事与现实,极力突出易学、经学的经世致用之旨,这也是他作为政治家为学的旨趣所在。
总之,欧阳修在解易的过程中极力凸显人事、社会政治的治理,强调为政者当以民为本,注重修德自省,为了说明这些道理,他在解易过程中也注重“以史证易”的方式来证明其思想的正确性、可实践性。与北宋中期所兴起的性理易学诸家相比,欧阳修既没有注重探究易学之中的哲理,也没有就性与天道发表自己太多的看法,而是他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思考,进而使易学解释的义理化、政治化,这虽然在易学、儒学形而上方面没有太多的成就,但是却促成了宋代易学的实践性与社会政治属性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宋代“以史证易”以及事功易学的传承与发展。
总的来说,欧阳修怀疑《易传》及注疏之学,“特别是提出《系辞》等非圣人所作,对河图洛书持否定态度,这在易学史上是第一次提出如此看法,这也是欧阳修的易学最有创见和最为重要的部分”[10]。欧阳修此举,实则是要打破传统传记解经、注疏之学解读经书的汉唐经学旧模式,“舍传求经”,直接从经文中探究圣人之道,从而实现经学范式的转换与儒学理论的重建。欧阳修重视义理易学,尤其对王弼义理易学颇为推崇,这不仅是当时易学的一个重要倾向(如范仲淹、胡瑗、王逢等人都多推崇义理易学),而且也是当时经学“变古”之后的一个重要体现。换言之,庆历之际,随着经学进入义理之学发展的新阶段,包括欧阳修的易学及《诗经》《尚书》《论语》等诸经解释在内都开始强调思想义理,都开始突破汉唐尤其是孔颖达《五经正义》所代表的章句注疏之学的汉学范式,进入注重义理之学的宋学范式。当然,由于欧阳修易学不重视“性与天道”,以至于他与同时代刘牧、周敦颐、胡瑗等人的易学颇有不同之处,同时,由于没有自觉推动新儒学理论的建构,这也是其后来没有被宋人纳入北宋六子的重要原因之一。
欧阳修的义理经学,更多的是其政治哲学的一种外在体现。毕竟,欧阳修与范仲淹、“宋初三先生”一样注重打破旧有的汉学范式,也极力强调在政治理念上推行更加符合宋代大一统、皇权至上的新经学体系与儒学思想。所以,欧阳修的易学解释充满了现实取向性,更加强调纯粹的礼义性、政治性,更加强调易学与当时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建设的内在关联。换言之,欧阳修的易学不仅突出了人事、现实的因素,更是突出了对礼义、制度的关注,而这与其推行的庆历新政颇有内在相通性。他希望继续通过强化礼仪、制度来维护当时以皇帝为核心的政治秩序,只是这种尝试遭到了失败,随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也是如此。实际上,随着佛老之学在当时的盛行,人们更加注重自我的情感、价值的关注,所以如何基于人心来建构新的意识形态以维护社会秩序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所以,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注重礼仪的做法自然遭到了挫败,其礼学化、政治化的易学自然也遭到了摒弃。不过,欧阳修的易学为后来理学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如欧阳修《易童子问》提出来了“‘天地以生物为心’的命题……二程所说的‘天地以生物为心’的思想是来自欧阳修对《周易》的解说”[11]。北宋中后期的胡瑗、张载、周敦颐、程颐等人开始注重易理及“性与天道”的问题,他们推崇道家宇宙论与佛学的心性学说,并结合《四书》学,基于易学、《四书》学建构了全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理学,从而完成了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实现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整合。随着理学化易学及其政治理念得到了统治阶层的认可,欧阳修、王安石等人所推崇的礼义化易学、义理经学以及礼治理念自然也日渐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