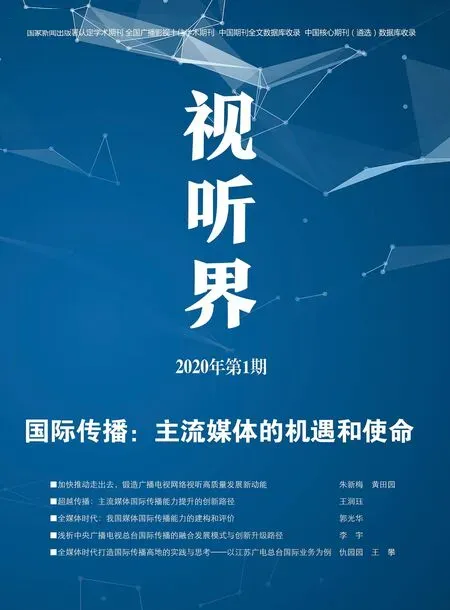分离、游移与重构:恋爱观察类真人秀中的场意识研究
侯 鑫
一、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兴起
近年来,观察类真人秀日渐火爆,成为热门综艺节目的形式之一。这种电视节目形式起源于日本,火爆于韩国,后引进国内综艺市场,进行本土化改造,一经推出便引发收视狂潮。观察类真人秀,就是把节目嘉宾的日常生活和他们在特定情境和规则下的行为处事及状态展现在摄像机之下的真人秀节目。[1]而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就是将恋爱交友日常作为节目观察的主要对象和内容呈现,是观察类节目类别化的产物。时下荧屏中的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大多是以韩国Heart Signal为蓝本。我国恋爱观察类真人秀主要采用以素人男女交友为主线,明星嘉宾观察访谈为辅线,呈现外景纪实拍摄和演播室访谈两种形式,产生明星观察、亲友观察、受众观察等多层观看关系,建构现实的恋爱、婚恋、伦理的社会学讨论空间,进一步拓展电视综艺节目的呈现方式、表现内容、舆论场域和现实意义。
二、微观场下的观察
微观场是传播学场理论的基础理论,指“电视拍摄现场诸要素(包括被摄对象、摄像机/摄像师、记者/主持人等)及其携带的权力关系共同构成的一个客观实在。”[2]微观场又被细致地划分为第一场(被摄对象的自然状态)、第二场(被摄对象的自主状态)、第三场(记者的采访状态)、第四场(记者/主持人的现场播报状态)及第五场(主持人演播室播报状态)。要完成一个电视(视频)节目的拍摄和制作,从场境来看,是需要来自不同场不同状态的音视频素材的排列组合,而要使电视真人秀拍得好看则更为复杂,需要满足人们对于电视真人秀单位信息量真实、充分和价值的多重标准。据分析,在具体的电视实践操作当中,恋爱观察类真人秀,主要包含第二场、第三场以及第四场状态,而这三场状态的有机组合和运用也恰如其分地映射了人们对于真人秀的“真实”“情感”“趣味”的期待和诉求。
(一)真——趋第一场性
“真”是真人秀的生命。人物真实、记录真实、情感真实是真人秀的完美状态。[3]恋爱观察类真人秀节目最大的看点就是“真实”,突出现场感和不可预见性,但这种真实区别于新闻真实和记录真实,更像是一种“虚构的真实”。由于电视节目的“第一场悖论”,摄像机一旦到场,随之背后所涉及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接踵而至,电视真人秀节目通过常规途径几乎没有可能拍摄到第一场自然状态的画面。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恋爱观察类真人秀中的“真实”,并不是客观真实本身,而是导演虚构了第一场,使其某方面属性无限接近被摄对象的自然状态,是一种“虚构的真实”。
微观场理论中的第二场(拍摄对象的自主状态),是指 :“被摄对象可以感知到摄像机/摄像师、记者的存在,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主观上忽视了这些因素的存在的事实。第二场的情形十分复杂。它有可能十分靠近第一场的属性,也可能沦落到第三场(记者的采访状态)的边缘。”[4]很显然恋爱观察类真人秀正是大量运用第二场的画面来靠近趋向第一场性。那从技术应用的角度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恋爱观察类真人秀之中,第二场的镜头是最为常见的。这类节目借鉴了人类学电影的拍摄方法,人类学家与社区居民同吃同住,长时间接触以消弭陌生感,从而获取相对真实性的素材。这类节目将数对男女集中在一个集体空间中,如恋梦小屋、信号小屋、遇见小屋,并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同吃同住共同生活,而摄像头却处于一种相对“隐蔽”的状态之中,摄影师通过在小屋中设置“隐蔽式”摄像机,通过远程操控台来操作,使屋内男女完全沉浸式融入环境之中,摄像头背后的权力关系并没有明显显露出来,这就使得原本年龄相仿、经历各异的单身男女们在长时间的接触和交谈中,荷尔蒙情感的催化下,逐渐卸下心中的防线,呈现出一个个鲜活、真实、可爱的普通人形象。[5]
此外,当被拍摄的事件十分紧急时,被摄对象很容易就会忽视掉摄像机的存在,像这样的第二场的状态在恋爱观察类真人秀中比比皆是。在《遇见你真好》中,被拍摄的对象纪思清和刘适时选择到射箭馆进行一次约会,在运动激烈紧张氛围的营造当中,很明显能看到刘适时作为男生的慌张和局促,特别是在得知纪思清之前是名专业射击运动员之后,更是一改之前塑造的儒雅形象,显露出憨厚老实的一面。因为在紧急状态之下,被摄对象是很难意识到摄像机背后的权力场域的,他们的表现是电视前台化展示中最为真实的状态。
(二)人——语言和动作
在电视娱乐泛化的今天,恋爱观察类真人秀能够突出重围,最重要的就是对于情感的把控、捕捉和流露,我们也可以称其为“人”性,也就是我们在节目参与者、拍摄对象的身上能够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产生一种共情作用。通过人物生动的语言和动作,特别是人物命运的变化可以使故事讲得更为生动,更能引起观众的共鸣。[6]正如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对待感情的各种态度,陈晓雯的执着、奥斯卡的犹豫、陈溥江的坚决、陆文韬的耿直、孙懿琳的勇敢、刘适时的温暖等。同时反观,这些性格鲜明且各异的人设也帮助电视节目形成独特的传播符号,建立其电视节目影响力。
从传播学场理论来看,电视节目都是从第三场作为拍摄的起点,恋爱观察类真人秀也不例外。微观场理论当中的第三场(记者的采访状态):“由记者,被摄对象、摄像机/摄像师三者共同构成的采访状态,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三者都意识到这是一场采访。”[7]第三场的镜头,虽然不如第一场和第二场那么具有现场感和可信度,但是对于人物内心的情感细致刻画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表达手法,在现在的真人秀节目当中应用得十分广泛,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在设置上,为了让观众能跟随人物心境,都会设置每天的心动选择环节,不论是恋梦影像信、“咕咕机”短信、手写书信等形式,并穿插一部分拍摄对象的独采环节,这是非常明显的第三场镜头。
从场的性质来看,第二场和第三场图像的形式特征都是语言性和动作性兼具的,可信度和单位时间信息量都处于中等,第二场以动作为主,第三场以语言为主。语言符号作为主要的叙事信息的传递渠道,而非语言符号则承担起了塑造人物性格、突出细节特征等其他意义的建构功能。在影视创作中,光影、图像、构图、音响、神态与表情、肢体动作等非语言符号在人物形象塑造中作用巨大。[8]电视节目也不例外,要呈现情感,肯定离不开主体就是人,而在电视节目创作中人物的刻画便是通过细节呈现,被称为“人物细节化”。如在《恋梦空间》最后告白时刻,会有一个环节查看之前录制恋梦影像信的权力,决定最终是否告白,每个人进入到这个屋子里面的状态都是各异的,通过他们的语言表述和动作肢体可见一斑,有幸福甜蜜的微笑、有怅然若失的皱眉、有心意互通的手舞足蹈、有郁郁寡欢的不言不语等等。
(三)秀——多场境转换
电视媒介生态中的真人秀节目是21世纪的活跃物种,在信息时代背景下满足受众对信息的多种需求,并使其获得娱乐满足。[9]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对于“趣味”营造的场境较为复杂,从现实时空来看娱乐成分主要集中在演播室空间,但从传播学场理论分析,演播室空间给受众营造的场境却不单一,主要第四场为主、兼具第二、三场,多场境之间还会来回转换甚至是架构之上。恋爱观察真人秀的演播室空间人员配置为:一位主持人搭配若干位明星嘉宾,其中存在一位相关心理专家,如主持人《喜欢你我也是》的张绍刚、《心动的信号》的姜思达、《遇见你真好》的沈涛、《恋梦空间》的梁田。主要的节目内容为解读情节、预测故事、话题拓展,节目的主要形式是采用访谈的形式,类似于常见的电视谈话类节目。
从场理论来看,这类节目主持人的视点是摄像机和嘉宾,而嘉宾的视点是主持人和其他嘉宾,绝不会是摄像机。主持人面向镜头口播时属于第四场,主持人与嘉宾们互动时属于第二、三场,第三场比较好理解就是类似采访的现场,而第二场则需要主持人来带动嘉宾进入自主状态,捕捉一些他们平时并不会表露出来的真实观点和看法。单个场的属性不难辨认,而在电视节目的制作中复杂在于场的游移,不同状态场拍摄的镜头具有不同的属性,场际之间相互配合、转换自如、互为补充,完成整个电视节目的构造。
因此,恋爱观察类真人秀的趣味性主要体现在:一方面,观众观看这类节目首要的兴趣来自于明星效应的加持,特别是流量明星的到来,如明星嘉宾《喜欢你我也是》的娜扎、沙溢、周洁琼,《心动的信号》的朱亚文、张雨绮、杨超越,《遇见你真好》的宁静、王耀庆、吴宣仪,《恋梦空间》的韩雪、于莎莎等。另一方面,“秀”的部分更多来自于分享,主持人和明星在多场境下的游刃有余。明星解读恋爱情节表达个人观点,或观点对立引发争论,或产生认同呈现性格,且适当介入插科打诨、自黑调侃,将整体的访谈氛围引入一种有趣味的状态。
三、宏观场下的观察
宏观场理论将社会传播看作是由文本场、受众场、意义场和文化场相互连接构成的一个复合场域。[10]恋爱观察真人秀拍摄内容观察对象是两性婚恋关系,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观察是满足大众窥视欲望。弗洛伊德在《性欲三论》中,将“窥视”划归为产生性快感的心理机制之一。从社会发展来看,婚恋关系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人对于自我情感的需求。在宏观场景中,电视节目是复合场域,恋爱观察类真人秀节目在拍摄和传播过程中,必然也涉及到了更多的层面问题的探讨,如法律问题、道德问题、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情感与道德的纠葛,如在两性关系中的恋爱动机、传统恋爱道德、男女恋爱中的平等地位以及恋爱观代际问题。
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青少年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对于爱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倾向均可能受到影响。[11]恋爱观察类真人秀不同以往电视荧屏所呈现的婚恋速配节目,过于世俗化、物质化和功利性质,它的主要受众是青年观众,是恋爱发生最美好的年纪,因此节目把重心放在对于恋爱关系中的自然呈现,以及在关系中衍生开来的恋爱观、两性交往、情感和价值观的讨论上。如《心动的信号》中胡金铭和周游的一见钟情、《遇见你真好》中郑晓雯和廖锡荣的求而不得、《恋梦空间》陆文韬在爱情中的摸索实践。我们可以通过节目看到当下所倡导的健康的恋爱观:恋爱对象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恋爱认知不断被强化;传统恋爱道德不断被消解,恋爱关系趋于开放化;恋爱理念平等化,也建立其恋爱代际关系中的良性沟通。
四、对于“观察”的思考
经过传播学场理论的宏观场和微观场意识的分析,对于恋爱观察类真人秀我们必须思考三个问题,一是什么是观察?二是观察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三是谁来观察?首先,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心理学得到答案,观察法在心理学的理论和实践得到广泛运用。观察法是指在自然条件下,有目的、有计划地观察被研究人的行为活动,以分析其内涵的心理现象,研究其心理规律。[12]传播学领域中,经验学派很早就将观察法运用到研究中,进行量化研究分析社会现象和社会行为。
其次,观察的内容,对于恋爱观察类节目而言,最直接的内容就是对于恋爱关系中的行为和语言自然呈现,但也涉及心理层面,包括在关系中衍生开来的恋爱观、两性交往、情感和价值观的讨论。从传播学场理论来看,观察的内容是宏观场和微观场的总合。
最后,谁来观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是背后批判性地思考了传播学经验学派关于传受关系的问题,是关于观察类节目如何建构基于传受双方的复杂观察结构的回答。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应当具备一条亲疏关系的观察链条,当中理应包括来自亲友的观察、明星的观察和观众的观察。从不同视角的认知与剖析,不仅丰富了节目内容,还带来多角度全面的观察视角。
五、小结
恋爱观察类真人秀通过精心挑选的素人恋爱作为主线、性格各异的明星嘉宾观察作为辅线,真实地展现了中国当下两性恋爱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和情感纠葛,节目兼具真实性、情感性和趣味性,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从传播学场理论出发,在宏观场中我们可以看到文本、受众、意义与文化勾连的复合场域;在微观场中,节目向我们呈现的是五种状态场之间的分离、游移和重构。电视节目场意识的研究方法,来自于电视实践之中,又以理论形式指导实践,不仅帮助我们更好认知恋爱观察类真人秀不同场境下的场态属性和具体形式,同时也提供其他电视综艺节目可借鉴和创新的方式方法,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注释:
[1]孙岩.看与被看:观察类真人秀的全新表达空间[J].当代电视,2019(3):60-62.
[2][4][7]程郁儒.传播学场理论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51, 56, 58.
[3]梁波.“全知”、对话与社会面向:观察类真人秀的精品化之道[J].视听界,2019(2):27-30.
[5]童凌潇.恋爱类真人秀摄制手法及其传播特性分析——以Heart Signal为例[J].传播力研究,2019,3(5):33-34.
[6]胡智锋.电视传播艺术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46.
[8]贾宏宝.非语言符号在影视人物形象塑造中的运用[J].声屏世界, 2018(6):38-39.
[9]甄东霞.电视真人秀节目的传播价值与影响[J].青年记者,2017(11):53-54.
[10]程郁儒.电视记录场理论及其应用[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7):84-88.
[11]孙婷.电视婚恋节目对大学生婚恋观的影响及教育引导对策研究[D].西安科技大学,2014.
[12]郭学英.浅谈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J].科技资讯,2009(26):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