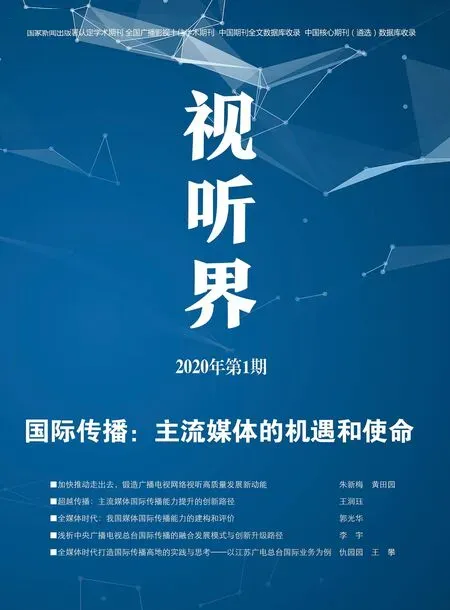“强连接”与“圈层化”:社交媒体人际连接的双螺旋
尤可可 马广军
社交媒体带来的“强连接”,甚至是过度连接,与群体间的“圈层化”构成了当下人际连接的“双螺旋式”的陷阱。从“强连接”视角来看:公共空间压缩了私人空间,如工作领域的信息也由私人社交平台传递,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个人的私人空间;社交平台构成人们沟通交流的舆论场,但同时也是自我监视的“圆形监狱”,“自我”在与他人的社会比较中不断审视与修正,陷入自我的焦虑与心理负担中;社交平台已逐渐被资本消费主义入侵,人与人之间的强互动正在转换成一种无意识的诱劝式广告,在潜行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与此同时,在这种人际连接的“强连接”下还存在着“圈层化”的悖论——“圈层”往往是由个体形成的社会网络,往往以利益、立场、兴趣、价值或情感纽带形成的圈子。在移动社交时代,这种圈层,第一表现在线下生活空间的窄化;第二表现在社交群体的同质化,人与人连接过程的信息传播往往受到生活环境、地理位置、兴趣与注意力的影响,这是导致群体社交圈同质性的动因,在数字空间中,人们更容易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个人或群体;第三,网络“过滤气泡”的产生进一步窄化了个人在虚拟空间中的认知与外部连接,互联网搜索引擎通过大数据了解用户的偏好,进而为用户过滤掉异质信息,形成信息闭塞;第四,人们对社交媒体的依赖往往带来人际连接虚拟化与孤独性心理。
通过理论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的人际连接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有利、健康、广阔,社交媒体的发展已使我们被过度连接,我们的社交关系危机重重,因此,引起人们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并给出建构良性人际连接的方案在当下媒介环境显得极其迫切。此外,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资深教授伊桑·祖克曼从整体上辩证地看待世界的联系,指出从期望路径到有组织的漫步,自我追踪与自我发现,从而重新连接世界,这对网络社会人际连接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本文通过研究基于社交媒体人际连接中“强连接”的表象与现实狭窄的“圈层化”的双重表征(本文将这种悖论称为人际连接的双螺旋),来分析它们分别带来的影响,并给出构建良性网络人际连接的建议。
一、网络强连接的呈现及影响
连接是互联网基本属性与内在法则,在这种连接中互联网逐渐成为一个生命空间,身处其中的群体逐渐回到部落时的状态,这种强连接也带来群体行为的改变,政治权利的消解与工作时间的业余集结。但在媒体社交化和移动化的今天,网络人际连接充满黏性的背后还存在私人空间被挤压,为了强关系而炮制的“人设”,以及消费主义渗透等问题。
(一)网络时代的强连接
1.大连接与群体行为的改变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网络开始渗入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当中。在网络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强连接更易引发社会群体行为的改变。一方面,这种行为模式的改变使人际连接便捷化。“人类连接在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上,我们的相互连接关系不仅仅是我们生命中与生俱来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一种永恒的力量。”[1]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通过研究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对人类的情绪、亲密关系、健康、经济政治的运行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他指出,三度影响力(即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也能影响到你)是社会化网络的强连接原则,决定着社会化网络的功能。1998年,邓肯·瓦茨和史蒂夫·斯特罗加茨提出了“小世界理论”,即小型群体内拥有稠密的联系,大型网络是稀松联结起来的。在社会化媒体的作用下,数人组成的小网络会联结成大网络,这些网络力量的聚合往往会对个体的行为模式带来潜在的深远的影响。
2.无组织力量
被业界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的克莱·舍基不仅看到人类的社交属性,也观察到互联网技术给群体动力学带来的巨大影响。他指出,人类是社会化生物,且人类之间的群体活动对商业、政治、媒体和宗教等领域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电子网络的出现正使得集体行动的各种新奇形式成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大更分散的协作性群体也因此诞生。[2]
移动网络社会中人际连接摆脱了传统社会时空的限制,这种无组织的力量改变了政治竞选的路径。“互联网穿透了社会坚厚的岩层,使所有相邻或相距遥远的层级彼此面对。身份、财富、地域都不再是传播的权力或枷锁,每个人的传播能量已经穿破层级壁垒,开始顶层和底层的直接交流。”[3]
3.大规模业余化
数字网络让分享变得廉价,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了潜在的参与者。[4]互联网为各个群体创造机会,而这些群体协作又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社会生产的创新价值与群体交往中的行为感染。网络的力量在于它使构建群体的努力变成一件简单可笑的事情。[5]再也不存在商业机构一手垄断图像、艺术、信息、舆论等事项的大规模分发出口的情况了。[6]在大规模业余化时代,具备新能力的群体在形成,他们的工作无须遵循管理规则,克服了限制其有效性的传统桎梏。[7]草根阶级借助自媒体登上历史舞台,通过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实现人生价值的转变。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认为:“最成功的网络,就是那些自组织的网络,想一想互联网。互联网的成功之道,并非因为有个一手遮天的组织强迫我们加入互联网的,而是因为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个人都希望能接入互联网。”
(二)网络社交强关系背后的问题
互联网正走向一个过度连接的阶段,从表象上看,这种连接给人们带来诸多便利与施展空间,但这种社交“强连接”已在潜行中侵袭着大众的私域、社会观与消费观。
1.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的消解
微信、微博以及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社交平台产品与形式的丰富性发展,不断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且这种连接往往是并发式的、高频次的,人们可以选择多线程来同时与不同对象进行互动,这种频繁的互动与被互动,连接与被连接往往在潜行中耗费着人们的精力与思想。
另一方面,这种私域中的强连接已被公共空间渗透,人们在私人社交平台发布的信息往往经由其他群体的传播而流向公共空间。工作领域的信息也由私人社交平台传递,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个人的私人空间。
2.社交平台中的“表演”与“攀比”
移动社交平台的丰富性为个体提供了多样的连接,这种连接也形成了天然的“自我表演舞台”与“社会坐标系”。
一方面,社交平台构成人们沟通交流的舆论场,但同时也是自我监视的“圆形监狱”,“自我”在这个监狱中不断审视与修正,这种自我表演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不断进行调整;另一方面,社交平台也在无形中为自我提供了参照物,而根据心理学研究,个体对自我的评价往往来自于周围人提供的社会比较中,这种比较呈现上行比较时,个体往往会降低自我的评价水平,呈现下行比较时,个体会提升自我的评价水平。移动社交平台极大地增加了个体社会比较的广度,这种持续的、高强度的社会比较往往使个体陷入自我的焦虑与心理负担中。
3.“消费主义”对强关系的渗透
英国学者埃里克·克拉克在他的著作《欲望制造家——揭开世界广告制作的奥秘》中指出,“广告对人们产生的影响的原则是:像水滴石穿一样,在不知不觉中进行。”[8]今天,社交平台的强连接已逐渐被资本消费主义入侵,人与人之间的强互动正在转换成一种无意识的诱劝式广告,这种间接广告使消费者形成一种闭环互动关系。“让一个符号参照另一个符号、一件物品参照另一件物品、一个消费者参照另一个消费者。”[9]这种消费总体性与同一性正在潜行中重塑着个体的消费观与消费欲,人们无论是从社交平台内容,还是社交平台中的强关系口碑中获取的信息,都处于一种无意识的被动式的接收状态,这往往对人际连接形成一种入侵。
二、现实“圈层化”的特征及影响
网络人际社交除了呈现出“强连接”的特点外,在个人现实生活中还呈现“圈层化”发展。“圈层”虽然目前在学界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依据传统定义,“圈层”往往是由个体形成的社会网络,往往以利益、立场、兴趣、价值或情感纽带形成的圈子。在这个圈子中,群体往往有着相似的认知、观点与态度。在移动社交时代,这种圈层不仅表现在线下生活空间的窄化,社交群体的同质化,还体现在线上的“算法”信息,人际连接虚拟化与孤独性心理。
(一)现实生活空间窄化
“人们倾向于对生活中的非常规行为给予更多关注,对习以为常的事情往往容易忽视。”[10]与我们想象中自己丰富且不可预知的日常活动不同的是,我们实际生活空间往往呈现狭窄化与固定化。
苏黎世应用科技大学的卡尔·雷杰博士和他的团队通过全球航空线路的数据绘制一个大型的可视化图像,用曲线图来呈现,以国家或个人为横轴单位,以频率和距离为纵轴指标,结果这个旅行线路呈现出“长尾”分布,头部是密集频繁的短途旅行,尾部是偶尔的长途旅行。结果证明,人们往往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离家较近的短途旅行中,每个人的日常行踪显得固定而狭小。
(二)社会群体同质性
“基准类聚”的群体模式是人际连接的重要特征。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通过研究发现同一族群的同性群体之间最容易产生亲密的友谊,并提出“同质性”一词,之后这一词汇也成为社会学家衡量社会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无论是人际中婚姻的亲密关系,还是同事间的信息分享,公共场所的松散连接都具有同质性的特征。教育心理学家贝弗莉·塔特姆在她的著作《为什么餐厅里的黑人孩子都坐在一起?》中提到了种族认同的问题,人们在面对自我隔离时往往会感到不安。尤其当个体在单一的环境中成长,同质性的社交更为明显,人们通常会与参加同一活动的人发展友谊。
在网络空间,社交群体的同质性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社会学家安德里亚斯·维默尔与凯文·刘易斯通过Facebook上搜集的数据发现,经常在Facebook上有合影的学生往往也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来自同一个学校和专业的学生也更容易成为朋友,这说明结构性因素对同质性作用的影响并不亚于个人选择,个体的朋友圈往往受到生活环境、就读学校和个人兴趣爱好等影响。在中国,手机端的各类应用使得“圈子文化”大规模地漫延。微信群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连接,进而强化了群体的边界。
同质性构成社会群体的基本原则,人与人连接过程的信息传播往往受到生活环境、地理位置、兴趣与注意力的影响,这是导致群体社交圈同质性的动因。在数字空间中,人们更容易找到与自己相似的个人或群体。“人们通常会对自己在意的人或事给予更多的关注,即使信息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流通,人们的注意力还是会表现出高度的地方性。”[11]
(三)网络过滤气泡
在互联网未普及之前,人类主要通过专业的信息生产机构来获取信息,这种获取方式较为单一,且参与度极低。网络的介入为个体信息的获取、管理、生产与传播提供了低门槛,大众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更多的信息。然而,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用户难免会被“算法”,导致“过滤气泡”效应的产生。
“过滤气泡”最早由互联网学者伊莱·帕里泽在2011年其著作《过滤气泡:互联网没有告诉你的事》中提出。所谓“过滤气泡”就是人们在网上冲浪所处的个人化的信息世界,这是由一系列个性化的过滤器为网络用户构造出来的独特环境,而这些过滤器盛行于互联网。[12]他通过研究发现不同的人在同一搜索网站上检索同一词语得到的结果完全不同,不同种族或政治立场的人搜索同一新闻事件也会出现不同新闻倾向的结果。由此,互联网搜索引擎通过大数据了解用户的偏好,进而为用户过滤掉异质信息,形成一个充满个性化的信息世界,但同时信息与观念也会形成“茧房”,使用户身处一个单一观点的“网络泡泡”之中。
在人际连接的过程中,除了现实生活狭窄性以及社会群体同质化的问题外,个体信息圈与网络交往也呈现出这种个性化定制,“过滤气泡”的产生进一步窄化了个人在虚拟空间中的认知与外部连接。个性化报纸、算法、社交群体的同质性也促进群体信息圈的同质化。社交媒体逐渐成为人们注意力强大的引导者、专业守门人,个人兴趣已经越来越难以影响人们获取新闻。
此外,社交媒体还能够根据个体的信息与志趣来推送与之相投的朋友。因此,“过滤气泡”的存在不仅将与我们意识形态不符的内容隔离在外,也会将我们不熟悉的人和地点隔离在外。无论是从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来看,人们的关系都会越来越疏远。过滤气泡让人觉得舒适、宽慰、便捷,但它们严重束缚了我们的自由,让我们与惊喜绝缘。
(四)群体性孤独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图克尔在她的著作《群体性孤独》中指出智能手机为主的通信工具使人类进化成“半机器人”,每个人都可以全天候在线,与其他人联系。此外,网络连接技术还给大众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自我身份与认同感的探索。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开始出现模糊化,在社交网络中,我们以真实身份注册登录,但在自我展示的界面中又往往偏离真实的自己。人际在这种真实与虚拟的双重体验中,与网络的连接愈加紧密,“但是我们对彼此的期待却削弱了,这让我们感到彻底的孤独” 。
人际连接在网络社交中逐渐失去了原本平常的充满温度的面对面交流与亲密行为。“通过互联网所形成的连接并没有把我们联系得更加紧密,这些连接却让我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每个人都在用电脑或者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网,我们因为忙碌而使用网络,但是却和技术一起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而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之间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少。”[13]人们被吸引到一个唾手可得的社交平台上,虚拟身份,自我展示,在线聊天,实时表演,在这一系列行为的背后往往是人们为了一时的主观感受而采用分享的方式来排解孤独。
三、超级连接:打破网络人际连接的双螺旋
在移动网络社交的“强连接”与“圈层化”的双螺旋发展中,如何构建良性有效的人际连接?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资深教授伊桑·祖克曼从整体上辩证地看待世界的联系,指出积极寻找弱关系,从期望路径到有组织地漫步,自我追踪与自我发现,从而重新连接世界,这对网络社会人际过度连接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一)寻找弱关系
马克·格兰诺维特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最知名的社会学家之一,主要研究社会网络和经济社会学。他在1983年发表的论文《弱关系的力量》中基于时间跨度、情感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方面的不同组合,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14]个人经验与大规模的社会结构紧密相连,远远超出个人的视野或控制,微观和宏观之间的联结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这样的联结产生悖论:弱关系,经常被认为是一种疏远,但对个人的机遇和他们融入社区都是必不可少的;强连接,培育局部的凝聚力,却导致整体的分散。[15]格兰诺维特认为,主要是弱关系而非强关系才是信息传递的真正桥梁。同时,弱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中发挥的作用远大于强关系。
寻找弱关系是打破禁锢人际连接与产生新的有价值思想的有效方法。好的创意往往也来源于社会结构的作用,当一个个体淡出既有的生活圈,与更多的人建立联系,他就会发现他的思想充斥着丰富的创造力,这种有价值的想法往往来自于这种弱连接的输入。“拥有许多给你提供重复信息和机会的朋友,还不如认识几个真正能拓宽你的圈子,让你接触到新朋友和新思想的人。要是我们想要在社交圈子里与意想不到的群体建立联系,就不能把目光停留在最亲近的朋友身上,而应该主动寻找弱关系。”[16]
(二)有组织“漂移”
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人类社交生活都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与范围。城市规划师提出,任何人居住的地方都存在“期望路径”,即人类对于自己所处的地方与想去的地方之间有一个专属通道,这些通道处处反映出人类的社交痕迹或信息,为设计者提供了符合人类轨迹的设想方案。在互联网中,社交媒体早已为用户定制了信息服务,这使得人类的信息世界也呈定向化。
“城市的危险性在于我们会陷入雄巴德劳维所说的‘个人实际生活的狭窄空间’;而网络空间的危险性则隐藏于帕里泽的过滤气泡理论,即朋友所提供的舒适媒体环境。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要有意识地避开日常路径,给自己创造一些体验陌生事物的机会。”[17]这种随机组织不仅有利于建立群组联系,而且还能帮助大众得到意外收获,打破局限的日常生活。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1967年在他的著作《景观社会》中提出了“漂移理论”,即人们无组织地从某个景观漂移到另一处,包括幽默嬉戏的建构行为和心理地理学的感受意识,以此来克服社会生活中的局限性。在漂移的活动中,个人需要放弃一切娱乐,沉迷于自己所到的景观之中,最大限度地避开常规路线,着眼于自己的心理状态。“今天环境与居住地的不协调并没有被正确地指出,但是却被或多或少扩张的、模糊不清的毗邻地区所包围。漂移体验导致的最普遍的变化是这些毗连边界地区的不断减少,直到达到他们的完全被抑制的程度。”[18]
(三)自我追踪与自我监测
伊桑·祖克曼在他著作的后半部分通过罗伯茨教授的亲身经历来论证自我追踪的重要性,自我检测对打破自身局限行为产生的作用。自我追踪者可以利用智能运动手环等工具来追踪每天的步数、睡眠时间、心跳速率等数据,长此以往找到自己日常活动的规律。人们往往记得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但对日常琐事却充满错觉记忆。
在网络社交的环境下,自我行为的量化最重要的一项指标就是媒介消费。记录个人每天阅读、收听、收看的内容,再用一个时间记录类应用软件来追踪自身网络行为,这种上网痕迹的追踪往往能清楚地显示出个人的个性特点与社交习惯。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人为层面的数据记录,自我监测能够利用信息获得新的发现。通过追踪个人行为,系统就能判断出哪些领域已经没有探索的余地,从而推荐新的路线,避开个人的“期望路径”,从而引领个人走向意外之旅。
四、结语
从媒介技术学派的研究视角来看,媒介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与看法,尤其是个人际遇无法企及的领域。然而,网络社交媒介处处存在着管理者的倾向与政治因素,这是网络媒介给人际连接带来的最大的限制,进而延伸至个体的心理层面。
个体应通过主动寻找弱关系,不定期实行“漂移”活动,运用日记或技术手段来进行自我追踪,自我修正。同时,搜索引擎也应该做出改变,提供更多差异性且有用的信息。此外,信息管理者应引导人们接触陌生社区,从各个方面重构既有的社交圈,形成一个良性的网络人际连接模式。
注释:
[1] [美]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詹姆斯·富勒.大连接:社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对人类现实行为的影响[M].简学,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引言.
[2][5][6][7] [美]克莱·舍基.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M].胡泳,沈满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90.
[3] [英]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4] [美]克莱·舍基.认知盈余[M].胡泳,哈丽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24
[8] [英]埃里克·克拉克.欲望制造家——揭开世界广告制作的奥秘[M].刘国明,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54.
[9] [法]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35.
[10][11][16][17] [美]伊桑·祖克曼.超级连接者[M].林玮,张晨,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
[12] Maria Popova. The Filter Bubble: Algorithm vs. Curator& the Value of Serendipity[EB/OL].Brain Pickings, [2011-05-12].https://www.brainpickings.org/2011/05/12/thefilter-b.
[13] [美]雪莉·图克尔.群体性孤独[M].周逵,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
[14][15] Granovetter M.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78).
[18] [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