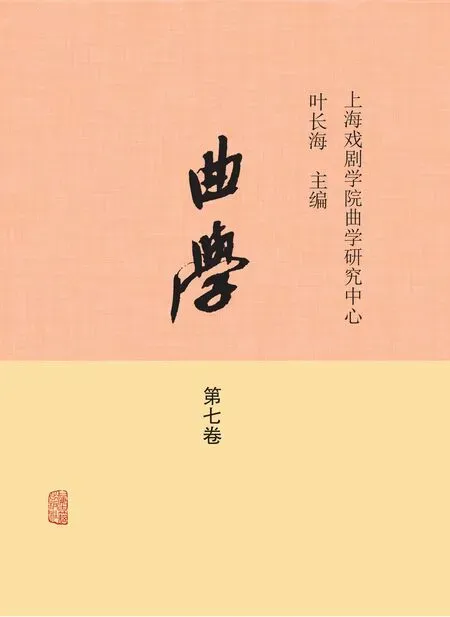戏曲艺术的时间和空间*
陈古虞
戏曲表演艺术的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时间和空间,通常指现实生活。人类无论在生产斗争或是阶级斗争中,对于时间经常讲争分夺秒,对于空间经常讲寸土必争,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时时刻刻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制约,因为人类没法超出在地球上、在宇宙中生活的限制。中国有句谚语“人到七十古来稀”,这是给人的个体规定生存时间了,即使医学进步人类可以活到二百岁,可是二百岁还是局限,和已有亿万年的地球比起来,一个人怎么活也活不到亿万年。所以人的时间还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宇宙的时间、空间是无限的,现实生活是无限的。人的实际生活都受到限制,简单的舞台更受到限制。舞台上的时间和空间是有限的,小小的舞台、短短的两个小时,跟人的生命和人的活动空间相比,人是无限的,现实生活是无限的,舞台上受的限制就很大,这是相对而言。实际上人的时间空间不是无限的,生命也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舞台受的限制就更大。对时间、空间的处理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戏剧表演中的虚拟,无论外国或中国,开始都是以人代物,属于原始状态,演戏时哪能谈得上什么时间、空间的灵活处理?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还有那时候的其他一些剧本,写的都是些古代民间故事,现在某些民间还保持古代演戏的传统,那种戏很有趣,是原始形态的戏剧,舞台很简陋。《仲夏夜之梦》中要表现一堵墙也没有办法,就拿一个人来扮演一堵墙,这个人一上场就向观众自我介绍:“我是墙,因为有两个情人要隔着墙讲话,所以我不得不上来扮做墙。”然后他举手说明以手代替墙的砖缝,回头情人俩通过砖缝来讲话。情人讲完话后“墙人”就说:“情人已经讲完话了,我的任务完成了。”然后下场。这样又占地方又费时间,没法节省。又比如一会儿狮子上场,先说明:“我是一只人扮的狮子,我这个狮子并不可怕,很温和,大家不要跑,不必害怕。”浪费好多时间。中国戏曲也是这样,《张协状元》台上连一张桌子也没有,只好叫店小二来装桌子,小二是捣蛋角色,在台上总是不老实,一边做桌子(充当桌子)一边偷吃,一会儿又要说话,“桌子”讲的话总是笑料,这一切是以滑稽戏的手法来处理的。这就说明它解决不了时间、空间的矛盾,占领了空间,浪费了时间,同时也破坏了戏剧性,使戏剧发展停滞不前;破坏了台上的演出的完整性,甚至节外生枝,把所演的东西移到戏外,变成插科打诨的东西,跑到戏外去了。
古代民间的广场演出,由于设备简陋,时、空的矛盾不好处理。在元代,骑马用竹马上场来表示,如《三战吕布》这个戏中吕布与刘、关、张都绑上竹马在台上打仗,但竹马太占空间,他们互相冲撞就非常麻烦,这样戏是演不好的,不如现在只用马鞭就可以代替来得简单,可见当时还不能很好地解决时、空矛盾。过去毛主席讲过一句话:“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句话非常重要,“必然王国”就是一切都是固定的,一切条件都受自然的制约。我们不能控制自然,不能控制客观世界,一切都受客观世界制约,这是“必然王国”。比如早期演戏用人去装扮墙,就是受到舞台的制约。从现在来看,舞台的发展有个过程,从所受的制约和限制中解脱出来,摆脱这种制约或者说受这种限制更少,就是不断从“必然王国”发展到“自由王国”,这是东、西方各民族戏剧演技艺术共同努力的方法。中西方的戏剧文化传统不一样,走的道路也不一样,所采取的方式也不一样,历史发展也不一样,分道扬镳,各走极端。也就是说无论外国戏剧还是中国戏曲,开始时都差不多,以后由于文化传统不一样而分道扬镳。所以中国戏曲和外国戏剧在舞台时空上存在以下这样的区别。
第一点,中国戏曲舞台上的时间、空间是经过艺术处理的,和生活中的时间、空间不一样,跟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有严格的划分,因而也不要求和生活中的时间、空间有什么统一。舞台上的时间、空间是艺术的时间、空间,不追求生活的真实。而西方戏剧追求生活的真实,所以它要求时间、空间的统一。
第二点,西方戏剧由于要求时间、空间的统一,追求生活真实,采取分场分幕的演出方式,实际上所演的是生活的横断面,一个片段;而戏曲比较起来是流动性的,就像现在工厂里的流水作业,以头到尾,前后连贯。最早的戏曲不分幕不分场,而是分出、分折,如元杂剧分折、南戏传奇分出。这个折和出都是由于以一套曲子为中心的歌唱,有头有尾,实际上与场、幕不相干,这一套曲子可以换好几场,跟外国戏剧的分场分幕完全不相同。
第三点,由于西方戏剧演的是一个生活的横断面,追求生活的真实,同时也追求艺术的真实,所以他把时间、空间在舞台上固定下来。用一定的舞台装置和传统的三一律固定下来,即强调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空间、一定的情节,利用三面墙固定下来。而戏曲舞台的表演是流动性的,前后连贯,所以它的时间、空间就不能固定下来,随时需要转换变化,这一点很重要。时间、空间的转换是以表演艺术为主的,戏曲表演艺术要求跟外国戏剧不同,它要求舞台上的每分每秒都要为我所用,都要使它发挥作用。戏曲舞台的空间不是一个面,而是由每一条线组成的,像几何一样;每一条线又是由很多看不到的点组成的,由无形的点形成看不见的线,这些点和线都要发挥作用,这一点跟外国戏剧不同。外国戏剧表现一个横断面,整个舞台浪费空间,好多布景占地方,演员就用不上这些空间,表演区相对就缩小了。中国戏曲则不同,整个是一个台面,台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不是死角,里边每一个点、每一条线都发挥作用。许多论著都未及谈到这种对戏曲舞台空间的体会,但却是我们中国戏曲中很宝贵的东西,是值得骄傲的。戏曲在舞台上演出没有浪费一点时间,也没有浪费一点空间,而且都为我所用。严格地说,外国戏剧是消极地摆脱时间、空间的限制,而戏曲是积极地运用时间、空间做为艺术创作的手法,这是跟外国戏剧相区分的最重要一点。
第四点,由于以上的原因,外国戏剧为了摆脱时、空的限制,追求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统一,所以它的舞台设置装备就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固定。莎士比亚和十六、十七世纪的戏剧,舞台上能表演室内,同时也能表演室外,还可以表演其他好多地方。到十九、二十世纪,表演都在室内空间了,而且室内装置越来越复杂,演来演去,不但要求三堵墙,甚至还要求第四堵墙,这就成了外国戏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中国戏曲不同,因为戏曲要求首尾连贯、不固定时空,一旦固定东西就多了,就不能首尾连贯,不能转换,舞台上的每一个点、每一条线都定死了。所以戏曲的装置不能多,多了就不能灵活转换,这就使戏曲舞台必然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净化。由于要求简单,要求净化,最后变成过于简单,一桌二椅,空无所有。于是有观点认为戏曲舞台上面就是一个桌子、两把椅子,什么也没有,一穷二白,确实太简单了,这也不好。所以,话剧和戏曲的舞台在发展过程中分道扬镳,各走极端。戏曲舞台上弄成一桌二椅,那个城门也是可以提起来的,外国人看了觉得可笑,中国人则不然,多见不怪。曾经有一个苏联专家看了中国戏曲,说胡子怎么能飘在空中呢?后来老舍先生写文章说他根本不懂中国戏,没有资格来谈中国戏曲。因为二者站的立场不同,苏联专家是搞话剧的,他谈的也对,胡子哪儿会长到空中去?胡子怎么飘起来像秋千呢?老舍先生是中国人,看中国戏看惯了,说长在空中不要紧,不长到空中不好看。可见这是中国戏曲和外国戏剧的不同。
总而言之,这些都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发展过程。中国戏曲和外国戏剧不同,外国戏剧现在发展趋向缓和,也在要求舞台净化;戏曲舞台又太过简单,现在稍微要求有一些装置,不影响表演艺术的必要装置,这是需要的。
戏曲舞台的时间、空间跟生活中的时间、空间毫无关系,是艺术的时间、空间,它究竟怎么样处理?先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梅兰芳主演的《御碑亭》。这折戏演的是一个通宵达旦的时间,但在台上的表演一共只用了十三分钟,包括进出场时间,如果扣除进出场的五分钟,由一更到五更也不过七八分钟,很简短。场上的表演在十几分钟内复杂多变,既在时间上,同时也在空间上有变化,空间动作很多,表情丰富。台上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亭子,因为旦要坐在亭子里头,生要站在屋檐下;亭子虽然很简单,但要具备里面能坐、亭檐能站人的条件;亭子用布做成,要人搬上台,在台上现装,很简陋。用这做例子说明一更到五更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一夜经历了倾盆大雨,这对旦来说是个意外的遭遇,对生来说大雨耽误了他一心一意上京赶考,想进亭子避雨,见里边有一陌生女子而避不成,只好在檐下站一夜。对旦来说更可怕,夜半更深一个女人家突然遇见一个素不相识的男青年。这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如果放在外国戏剧中几乎很难处理,中国戏曲就运用富有变化的歌舞来表现这一事件在一夜里的发展,也表现了外国戏剧里所说的规定情境。《御碑亭》里的一更、二更用散板来唱,鼓点很急,表现心情很急。然后逐渐坐下来,心情平静下来,所以唱流水,甚至让旦唱比较大段的二六,这个地方要用主要唱腔才能吸引观众。中国戏曲的观众不是只看戏剧冲突、戏剧情节、人物刻画,主要的还要艺术享受,他们的要求一方面是戏剧情节发展、戏剧矛盾激化,另一方面还要求充分的艺术享受、艺术欣赏。一开始的锣声就把观众带到规定情境中,引到雨夜中,随着一更、二更的时间推进,跟人物一起处在雨夜里,为旦提心吊胆,为深夜赶考的小生心情焦急。再看旦出来的身段,因为是倾盆大雨,走路不可能是慢条斯理的台步,而是轻轻摔倒在那儿;生一出来就滑得很远,用一个滑步。两人的动作都不同。五更过后又是一个很美的身段,生到底是个男子,匆匆而去,再也没有他的身段;旦则由于五更雨后道路泥泞,她在选择路上可走的地方迈步,这样就做出很美的身段,这样就可以吸引观众。观众不仅看到了剧情的发展,而且还得到了艺术享受。通过这十几分钟的戏,让观众不觉其短地相信是过了一夜,而且就像是跟台上生、旦二人一起过了一夜,说明台上的时间完全摆脱现实的时间。戏曲用的办法完全像变戏法一样变化多端: 利用不同的乐段,不同的歌,不同的舞,发挥歌舞性能,转换时间,一更跟二更不同,二更跟三更不同。《御碑亭》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戏曲里的时间是舞台时间,完全不同现实的时间,这里边听到的更鼓只是一种符号,那个亭子只不过是布做的,由人搬上台,也不拉幕,完全当着观众的面装起来,是一种象征性的布景,一切都是假定的。它告诉观众,我们在演戏,跟上面讲的墙会说话差不多,都是象征的。所以戏曲发挥了歌舞的性能,有戏、有意境,追求艺术的真实,使艺术的真实充实台面的空虚,使人进到艺术的境界当中,不觉其假,这是中国戏曲的本领。当然,这是演员表现艺术决定一切的因素,演得好的就能把观众带到戏的意境中,表演得不好的一切都是假的,不会使人相信。这和演员的本领有关系,一次深刻动人的表演,有动作、有表情,同时要很好的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国戏曲就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另一个例子是《夜奔》,说明戏曲表演中空间的转换。林冲“开了庙门,甩开大步,直奔梁山,走也”。他原在庙里,出了庙门,甩开大步,经过一个过渡,庙门没有了,转换到旷野上,这里只做了一个动作、念了一句台词,就把观众带到另一个空间规定情境中,台上换成了旷野荒郊,夜奔梁山。开庙门的一段戏,通过开门、出门、迈步和一蹦再加一跳等程式性表演,将空间转换的过程交代清楚,表演动作必须做到合理性和准确性。戏曲表演中空间的转换不是无条件的转换,要有交代,要有过渡,这是两个要点。林冲做的开庙门、出庙门身段,如果蹦得不远、跳不出来,马上就甩开大步直奔梁山,那么观众看到的是林冲怎么还在庙里乱蹦乱跳?因此必须看见眼前的庙,必须得躲开庙门,交代清楚,然后再往下唱。这段动作还说明,表示空间、时间的转换,一定要心中有物,一定要条理清楚。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戏曲演出时,舞台上的时间、空间和现实里的时间、空间不是一回事,而且严格分开。时间、空间在戏曲里边都是艺术创作的材料和条件,这一点和外国戏剧不同,不必回避它、摆脱它,而是运用它;要充分运用时间、空间,而不是超越它,事实上也超越不了。舞台上的时间、空间是艺术创作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唱是时间的艺术,动作是空间的艺术。
第二,时间、空间的转换不是自由的。有人说戏曲的特点是时空转换自由,这个说法不完全对,戏曲的时间、空间转换不是自由,必须有交代、有过渡。
第三,时间、空间在戏曲中和虚拟性不可分割。时间、空间在戏曲中都是虚拟的,经过夸张、想象,如《御碑亭》里的二更、三更。由于以虚拟性和程式性为基础,可以把时间、空间的转换包括在虚拟性中。时间、空间的处理是由表演艺术所决定的、是表演艺术决定时间、空间,而不是时间、空间的自由转换决定表演艺术。这一点容易发生混乱,不是时间、空间的自由转换使表演更丰富,而是表演艺术发挥了它的性能,为时间、空间的转换提供了条件,使时间、空间的转换变成可能。
时间、空间在戏曲中表现在程式性、虚拟性的基础上,发挥歌舞的性能,尤其是运用民族艺术写意的和传神的艺术风格,来解决舞台上时间、空间的问题,有时可以达到使人惊异的程度。怎样处理艺术上的时间、舞台上的时间,有时舞台上从一更到二更也可能是一分钟,而又不使人感到跳跃,这主要是艺术的真实发挥了歌舞的性能。《御碑亭》从一更到二更唱四句散板,尽管用了一分钟时间,实际上是象征一个时辰,并不使人感到跳越过来,这就因为有艺术真实的缘故。怎样表现舞台上的空间问题,就比较复杂。
舞台上空间划分很严格,跟生活中不同,一般来讲人物不上场,没有规定情景;人物一上场,通过他的叙述,或者通过他的事件的演变,才能了解他所处的环境。一般来讲规定的情景不一定知道是什么地方,观众也不追问。像《御碑亭》上场时大概知道是在他家里,究竟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反正送他下场就完了;到底是在屋子里边,还是院子里边,都不清楚,观众没有要求;也没有具体唱出来,反正拿着酒杯,他一个妹妹、一个妻子来送别他,给他饯行,送他走就完了。地点不一定规定那样死,总而言之是这个人物上场是在他家里边,拿起酒杯给他饯行,等他下去的时候,这个规定情境也就随着他消失,再一上场,就是其他人物上场,变成了其他地方。场子的变化跟着人物,台上没有具体的布景,不同的场次就是按这样来划分;有时在相同的场子里,也可能有不同的空间关系。如《打渔杀家》,旦在里边唱一句导板“海水滔滔波浪翻”就把情景规定了,上来一个圆场,两人都带着船拨子,有船声、水声,很自然就把情景规定好了。第二句是“江水照的两眼花”,观众就晓得海变成了河,下面是“青山绿水难描画,父女打鱼度生涯”。唱完后桂英讲:“爹呀,这河下生意不做也罢。”萧恩讲:“儿呀,本当不做这河下生意,怎奈囊中无钞,你我父女怎生度日呀。”桂英哭了,萧恩又说:“儿啊,不要啼哭,今日天气炎热,你我把船拨到芦苇之中,凉爽凉爽。”他叫女儿把为父打来的鲜鱼煮好,待他畅饮几杯。他们转到桌边,台上有一张桌子、二把椅子。他到里面喝酒的时候,李俊和倪荣上来了。戏曲的舞台是四方台,就有四个犄角,无论编剧和导演都要得会用这四个角。李俊、倪荣上场,一般上场都到台口,从小边上场,就是右边台角;两人唱四句,一个唱一句,李俊唱“闲来无事江边游”,倪荣唱“波浪滔滔往东流”,李俊唱“手搭凉篷用目瞅”,这一句是指出时间是中午,倪荣接唱“柳荫之下一小舟”,小舟就是小船。这四句说明时间、空间都有了,萧恩他们在船上,李俊他们在岸上,李俊刚才上来走过圆场了,舞台上有些是水面、有些是岸上,他们沿着边上,然后从岸上下船跟萧恩见过礼,一起在船上喝酒。接下来丁郎来了,他是催讨渔税银子来的,萧恩说改日有钱送上府上去就是了,说完两句,萧恩送丁郎上岸,李俊他们还在船里边。倪荣要打丁郎,萧恩劝阻,后来李俊送银十两、倪荣送白米十石,唱:“辞别萧兄到船下,纹银白米送到家。”他们走后桂英问:“啊爹爹,方才这二位叔叔是甚等样人?”萧恩唱:“他本是江湖二豪侠,李俊、倪荣就是他,蟒袍玉带不愿挂,弟兄双双走天涯。”这些词不固定,总而言之唱完四句后,念:“猛抬头见红日坠落西下,儿啊,天时不早,我们回去了吧。”父女两人一个唱一句:“父女打鱼在江下,家贫哪怕人笑咱。看看不觉红日落,一轮明月照芦花。”唱罢,萧恩和桂英同摇船下。整个场子又都是在水里面,没有陆地了。通过他们的唱念,可以说明时间、空间,同时在一个场子上边,也还可以表现河下、岸上。中国戏曲就是这样,上台时可以到处都是水,身段做完了之后他一上岸就可以是岸,这个岸和水的关系是模糊的,并不清楚,谁也没拿尺子去量十分之几是水,十分之几是岸。中国戏曲是有弹性的,如果没有人上场时也可以全部是水,假如在水里的动作少了,它又可以有一部分是岸,观众看了也就晓得他是在岸上,晓得他是在演戏。透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就是同一场子也可以表现出不同的时间、空间关系。《打渔杀家》第一场就完全可以表现出河下、岸上,手搭凉棚是中午,上场时“海水滔滔波浪翻”可以是早晨,完了进场又是“一轮明月照芦花”到了晚上。通过这一场的念白、动作及唱,还有事情的发生和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时间、空间关系。除了这类河下、岸上之外,戏曲还可以表现很多时空,若要表现出门内、门外,只要搬一把椅子在台口一坐,做个关门的虚拟动作,就把门关上了。像《武家坡》《汾河湾》,她在窑门以内,把她的丈夫关在门外;也可以表现楼上、楼下,像《杀惜》《彩楼配》,甚至可以不用椅子,站在桌子上就是楼上,做一个上楼身段,就可以表现在楼上,只要做一个身段就可以了;还可以表现山上、山下,像《长坂坡》《阳平关》这些戏,曹操就在山上,这种动作很多用一个山的景片,表现在山上、山下;在山上还可以表现观战,山下可以表现战斗,或者表现很多其他的戏剧动作。像《水斗》一场,法海在山上,白蛇、青蛇在水里边;《单刀会》也在水里边,以后鲁肃来接他就在岸上;还有像《空城计》《叫关》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中国人本领很大,还可以表现天上、天下。《长生殿》七月七日鹊桥相会,唐明皇、杨贵妃在下面盟誓“夜半无人私语时”,上面就是鹊桥相会。这里很简单,牛郎织女站在桌子上面就完了,在桌子下边各有各的戏剧动作,在桌子上表现在天上,在桌子下边表现在人间。总而言之,必须通过表演把空间规定下来,但又是比较灵活。
时间、空间还可以同时转换,一更可以转到二更,上场时是早晨、下场时可以转到晚上,这是时间的转换。空间也可以转换,比如很多上朝的身段,演员一出来的时候,两边的龙套就是做一个挑帘的空动作,就算上轿了;完了向里走,转出来,然后跪在那里叩头,叩头他也不讲话,他是来奏本的,奏完本也就下朝了,台上没有人,他回头走到台口,然后又是上轿,回到家里就完了。他就是那么来回走几下,就暗示从家里去上朝,然后又回家,走这么几趟。这种变换好像太简单了,台下可能不太看得懂。这是因为把上朝、奏本都省略了,在过去的戏里要用很多时间,现在都省略了。上朝时不管路程多远都没关系,假如我们行路没有多少戏剧情节,我们就一笔带过。元杂剧就是这样,假如台上没什么事,就“去去行行”,“行行去去”。《窦娥冤》就是这样,蔡婆去讨债,她嘴里就念行行去去、去去行行就完了。假如有事情就不能简单了,像《捉放曹》,他们在路上就要唱:“八月中秋桂花香,行人路上马蹄忙”,因为他们在行路,光是讲“行行去去”就不行,他们行路的时候还要有事情发生,他们要碰到那个老丈,所以他们就要唱。有的时候事情发生更多,事情比较复杂就得用扯四门,龙套在四个犄角,先在这里唱一句,站在那里唱一句,然后在当中唱一句,拉开扯四门来唱。事情比较复杂,要做的事情多,动作也比较烦琐,要一句一句在台上交代,所以这时就要扯四门,实际上扯四门就是变,他那么一走就走了很多地方。最典型的例子是《西厢记》,开头第一折张生上来后不久,唱[村里迓鼓]“随喜了上方佛殿”这一句,就把很多事情省了。“早来到下方僧院。行过厨房近西,法堂北钟鼓楼前。游了厢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数了罗汉,参了菩萨,拜了圣贤”,张生这几句唱,走了很多地方: 经过厨房、法堂、钟鼓楼,“游了厢房”,“登了宝塔”,以及“将回廊绕遍”。为什么他唱这几句就行了呢?因为他在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只是走一走、看一看,主要是碰到莺莺“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孽冤”,至于他游了许多地方,数了罗汉,参了菩萨,等等,在戏里一笔带过。那些实际上都是为了交代一下环境。这一段戏里走过很多地方,都是用身段交代,所以时间划分成很多块,同时时间也可以转换。
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时间空间运用方法。比如《打渔杀家》里边,桂英唱“老爹爹到县衙去出首”,后面就是打板子的声音“一十”;她唱完第二句,里面喊“二十”;她唱完第三句,里面喊“三十”;她唱完第四句,里面喊“四十”。这里是用搭架子的办法来解决,很值得注意。中国戏曲舞台上可以表现几十里内的事情,因为萧恩家在渔村,打板子的声音是在衙门,相距几十里地都可以表现出来。电影有特写镜头,戏曲也有特写,就是用搭架子的方法表现出来,不管多远,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发生在后台,神仙也可以说话。用搭架子的方法,并不是在台上让几十里地发生的事情同时存在,如果那样就是活见鬼了,中国戏曲从来没有活见鬼,从来就是合情合理的。搭架子是把里边的事情告诉观众,是这么一种特殊的功能。它并不是要把一个萧桂英在家,一个萧恩在县衙挨板子,同时在台上表现出来,不能这样表现,他俩不是神、不是鬼,不能照面的东西,怎么能照面呢?搭架子就像电影的一个特写、赛球的一个慢动作。
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方法,像《法门寺》中太后从宫里到佛寺去,去的过程中她坐的是辇,由很多太监在前面引路。她从宫里到寺里,中国戏曲的表现方法就是让她“上高台”,这是个术语,“上高台”就是上桌子,桌子上摆张椅子,她在桌子上不动,让大家围着她唱,唱京戏[一官迁]的曲牌子。老旦就坐在桌子上,根本不动,她不动,龙套围着她唱,唱大的曲牌,走大圆场,这样气氛一致。无论观众怎样看她,分明晓得她是坐着,看上去她好像在走,走大圆场,这个台不动,但望上去好像转台,台也在转,人也在走动。在《连环套》《盗御马》中也有这样的场面,曲牌不同,场面是一样的。中国人是很聪明的,是个伟大的民族,虽然是简单的场子,看上去很有趣,当中一个人不动,周围的人一唱一走,气派之大是很惊人的,有流动性,还有舞台的能量,世界其他舞台上没有这么大的能量。从中似乎可以看到科学原理,就像圆规当中那个支点是不动的,不过支点一转就把另一点带动了;又像放射线,像行星绕着太阳转。这种表演法很值得研究,还有很多例子有待整理归纳进行研究。
现在对舞台的时间、空间有很多讲法,归纳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种: 一、 戏曲是用分场(上下场)的表演方法,可以使时间、空间有极大自由。二、 戏曲可以超脱时间、空间的限制。三、 时间空间在戏曲舞台上可以自由转换。这些理论上的时空问题观点是否妥当,需要探讨。
舞台上的时空是不可能超脱的,但可以自由转换,而转换却是没那么自由的。现在有的人把戏曲舞台讲的神乎其神,似乎可以表现宇宙之大,可以把宇宙的什么都表现出来。中国戏曲没这么大的本事,讲它能量大,但都得依靠表演艺术,如除掉表演艺术,只通过一桌二椅来表现宇宙之大是不可能的。戏曲舞台是很简单的,一定要结合实践做深入检讨,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时间、空间的转换和关系,是通过表演来决定的,而不是由上下场来决定。上下场的方法在勾栏时代就有了,在原始时代就有了;上场门、下场门那时变不了,为什么到以后才变?这是表演艺术的进步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什么人也不能超脱时间、空间的限制。现实也受这个制约,舞台也受这个制约,换也不能绝对自由,转换也有一定的规律,主要是虚拟动作,要用表演艺术来加以变换。
时间、空间的关系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和现实生活一样,舞台上也不能超脱时间、空间的限制,自由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
第二点,时间、空间是有艺术真实来决定的,由艺术上的夸张、想象,通过表演艺术的诗情画意来决定的,而一切都要建立在真实性、准确性、合理性这个基础上。所谓准确性,就是一点不能含糊;合理性就是一切都要在情理之中,问一问这样做是否合理,演出时观众是不是能看懂,观众要认为合理才行。如《牡丹亭》中的《惊梦》,杜丽娘先上场,一出来亮相,到台口唱:“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唱完这段转身坐外场椅,春香上来了。演这个戏一定要看实际地方,台上是有房子的,这是情境规定好的,有房子她就不能走过去。中国戏曲是非常合理的、非常准确的,一点不能错。春香上来唱:“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她这里唱的不是自己,“炷尽沉烟”是讲小姐你看,沉香也烧尽了;“抛残绣线”讲的是绣花的线也扔掉了,没有心去刺绣了;“恁今春关情似去年”说的是小姐关心的是去年,好在无限春情跟去年差不多。这时一进门就合理了,一进去房子也就出来了,不能一出来就跑到台当中。演的时候要有个进门身段,没有门就不合理。《西厢记》中的《佳期》,小生一出来情境就规定好了,他唱“彩云何在,月照如水浸楼台”,这是在夜里,他看着月亮;后来他一转身,认为是小姐来了,原来响动的是风动竹声,接着唱“风弄竹声,只道金佩响”,这时他看竹子;“月移花影,疑是玉人来”,他看到了花影,盼着小姐来。这时台上的空间表示的是个书斋,有一个门,因为他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所以他走到门外,站在那里盼望。久等莺莺不来,他回到屋里,刚进去把门关上,莺莺和红娘就上来了,她们上来就不能再往台口走了,因为这是张生刚才站的位置,是个屋子,有一个门。演员要心中有门儿,莺莺羞羞答答先站在那里不动,她拿着汗巾想要进门儿,就是刚才张生进去的那个门儿。红娘望门,见门关着就拉小姐走,因为莺莺是偷偷摸摸来的,所以不能砰砰嘭嘭地敲。后来是红娘轻轻地拍,里面张生一听,马上把门开了,因为他是在里边等着,他晓得莺莺要来,是约好的。这个门儿就在这里固定了的,规定得很严格,所以这个门要非常准确。中国戏曲最重要的一点是虚拟,虚拟出来的房子、虚拟出来的门等等。这些东西虽然在台上没有,动作也是虚拟的,门、窗也没有,可是通过表演又什么都是存在的,都是客观物质事实,只是用虚拟的方法表现出来就是了。然而现在排戏时舞台上的调度,好的传统被破坏了,有些调度让人感到门和房子都没有了,都消失了。所以要在表演艺术中追求真实性、合理性,必须关注到时间、空间相互之间的关系。
第三点,时间、空间不能自由转换,必须有一定的交代、一定的过渡。像《武松打虎》要有个交代才走到景阳冈,林冲要先绕过圆场,然后才能换个地方。《御碑亭》里从一更到二更,必须有更鼓的声音,只有这样交代才行,不能绝对自由、不能跳动。
第四点,中国戏曲以歌舞为主,歌是时间的艺术,舞姿是空间的艺术,所以戏曲有可能积极去把时间和空间作为创作的手段,这一点是跟世界上任何其他戏剧不同的。时间、空间不是消极的,也不能超脱、摆脱,也不是什么自由,而是要去积极地运用。这一点很值得去探索,无论在编剧、导演、表演艺术里边都有很大的学问,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去积极地利用它,使它在表演艺术、表演技术里发挥大的作用。有时在表演艺术里节奏和动作都非常细致,表演能不能引人入胜,能不能到家,都跟划火柴一样,必须争分夺秒,要有寸土必争的精神。韩世昌先生在演《惊梦》的时候,有很多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往往有些很普通的动作,他做起来就像电影特写一样,确是惊人之笔、传神之笔,他唱:“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瑱。”“艳晶晶”就是头上戴的头饰闪闪发光,“艳晶晶花簪八宝瑱”就是很漂亮的头饰。他手指上方,眼一睁,向上一望,这个动作看上去很简单,但韩先生就做得特别好,手随着歌唱渐渐向上,并做出羞涩之态,稍微低一点头,难后一翻,光彩一下就出来了,真可以说是四个字“光焰照人”。这就是充分利用时间、空间来表演,韩先生和梅兰芳先生等许多表演艺术家一样,都在这些小的地方充分利用时间和空间。比如《琴挑》也是一样,一般的表演很平凡,好的演员演就很吸引人。他唱“抱琴弹向月明中”,唱到“抱琴”的时候要看琴,“弹向”时要看月亮,接着唱“月明中”,他要引导着观众。所以好演员一下就能把满场观众的目光都吸引过来,这些动作都是充分利用时间、空间的关系。那个时间就是节奏,空间就是手眼身法步,用时间、空间来做艺术创作的手段和材料,表演才能出色。举一反三,编剧和导演也是一样的道理,怎么更好地利用时间、空间做创作手段和材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中国戏曲与外国戏剧分野的地方。外国戏没有,或很少有这些,他们不懂得利用歌舞,当然这些东西就很少;戏曲懂得利用歌舞,所以时间、空间与表演的关系就很多。
莎士比亚曾说,最好的戏都不过是个影子,他认为舞台很简单,不可能演得十全十美,不可能十全十美地再现生活于舞台。无论怎么讲,舞台都有缺陷,西方戏剧比较真实,可是又比较呆板;戏曲舞台比较灵活,这是因为它有虚拟动作,但是同时又有许多原始演技的东西传留下来,这样就存在互相学习,改进革新的问题,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中国戏曲也有缺点,一张桌子、两个椅子,也太过简单,也可以说是很简陋,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能离开这个时代。但是得看怎么跟上,在舞台上增加布景的前提,一定要认识中国戏曲的特点,要弄清楚布景与时间、空间的关系,这样才是帮助表演而不是妨碍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