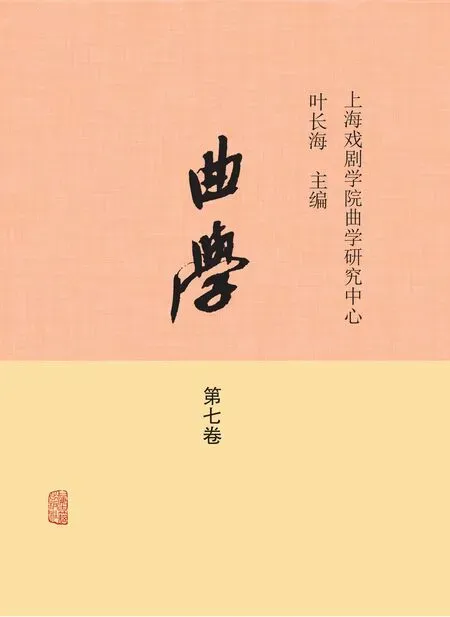王骥德《曲律》论宫调四题
白 宁
缘 起
这是一篇班门弄斧之作。陈多、叶长海两先生1983年注释的《王骥德曲律》(1)(明) 王骥德著,陈多、叶长海注《王骥德曲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是学习研究《曲律》的锁钥之作,在曲学界有着重要影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再版《曲律》时,陈多先生已作古,叶先生单独承担《曲律》的再版修订工作。
笔者就读沈阳音乐学院研究生期间,就细读过该作;继而,笔者撰专著《元明唱论研究》时,再读《曲律》注释,又有新得。后来,笔者考上叶长海先生的博士生,有幸亲耳聆听先生教诲。不久前,先生嘱我对王骥德《曲律》有关宫调部分的论述再作深入考证。
王骥德《曲律》涵盖广泛,堪称明代曲学的集大成之作,对后世有广泛影响。其中有关宫调的内容,多采前人论述,是窥知明代南北曲宫调使用的重要窗口。叶先生为《曲律》论宫调部分所作注释,本已释解通透,为精益求精,嘱我再予考证。现遵先生之命,不揣冒昧,采校雠学方法,对王骥德《曲律》论及宫调的一些问题试作进一步研究,权作拾遗,以就教于先生与各位方家。
一、 四十八调考
王骥德《曲律·论宫调第四》云:“则律之自黄钟以下,凡十二也,声之自宫商角徵羽而外,有半宫半徵凡七也,古有旋相为宫之法,以律为经,复以律为纬,乘之每律得十二调,合十二律,得八十四调,此古法也,然不胜其繁,而后世省之为四十八宫调,四十八宫调者,以律为经,以声为纬,七声之中,去徵声及变宫变徵,仅省为四,以声之四,乘律之十二,于是每律得五调,而合之为四十八调”,“自宋以来,四十八调者,不能具存,而仅存中原音韵所载六宫十一调,其所属曲,声调各自不同”(2)(明) 王骥德《曲律》,明天启四年毛以遂刻本,载《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第23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360—361、365页。。
虽然王骥德(?—1623)提到“自宋以来,四十八调者,不能具存”,遍查中国古代有关宫调的论著,在王骥德之前,论及四十八调者仅见明代的唐顺之(1507—1560),其所撰《稗编》“制管之法”条下,记有四十八调调名,但未用“四十八调”来进行称呼;距王骥德生活年代不远的清初毛奇龄(1623—1716),在所撰的《皇言定声录》、《西河集》、《皇清文颖》、《西河词话》等著述中,都提到了四十八调,清代李(1659—1733)撰《李氏学乐录》也提到了四十八调,《四库全书》在《李氏学乐录》卷首云:“尝学五音七声十二律以器色相配之说于毛奇龄,作宫调图七调全图及十二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合图”(3)(清) 李《李氏学乐录》,四库全书本。,可知,李曾从学毛奇龄。毛奇龄的论述中,几乎每个论述都说明这种理论来源于何处,如论述八十四调时云:“隋唐间多以七律周十二宫为八十四调”,而在论及四十八调时,毛氏没有说明其理论源出。其《皇言定声录》“四十八调、四十九调”条云:“旧以七声乘十二律得八十四调,自子黄钟至亥应钟十二宫各具七声,而宫调备焉。后人以宫商角羽之四声乘十二律而去徵调与二变调得四十八调,自隋唐以后多用之。”(4)(清) 毛奇龄《皇言定声录》卷六,四库全书本。
隋唐以来,涉及宫调的著述、词集、曲集大致二途: 一是演奏宫廷音乐或民间音乐的乐工和唱者实际采用的宫调;二是一些文人、学者研究宫调时所提出的理念。后者推算出的宫调理论,多有未应用于当时的实践。如《隋书·音乐志》记载了郑译“遂因其所捻琵琶,弦柱相饮为均,推演其声,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合八十四调”(5)(唐) 魏徵等《隋书》卷十四,中华书局,1973年,第346页。。其实,所谓八十四调只是一种推演,并未在宫廷音乐中使用,隋代真正所用只有黄钟一宫及十四调,《新唐书·礼乐志》载:“(郑译等人)又以一律为七音,音为一调,凡十二律为八十四调,其说甚详。而终隋之世,所用者黄钟一宫,五夏、二舞、登歌、房中等十四调而已。”(6)(宋)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460页。再如,明代朱载堉最早推算出了“十二平均律”,但他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应用于当时的音乐实践。有清一代,也将朱载堉的推算成果束之高阁。《四库全书》收朱载堉《乐律全书》,前附乾隆皇帝的上谕及大臣的按语:“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奉上谕: 朕披阅朱载堉《乐律全书》,所论音律算法,称引繁赜,但其中较《律吕正义》一书疏漏岐误之处正复不少。”“内廷翰林等考据琴谱指法按语”云:“明朱载堉《乐律全书》,师心非古,喜为臆说,尤以算术自鸣而不知其不可用也。”(7)(明) 朱载堉《乐律全书》,四库全书本。
王骥德并非以精通音律而闻世,《曲律》中有关宫调的记载,多有王骥德引用前代学者或他人的论述。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四十八调并非王骥德首次提出的,而是那个年代一些学者、文人在探讨宫调时的一种理念,反映的不是宫廷和民间实际采用宫调的情况。
观察王骥德《曲律》关于四十八调的推衍方法,可以发现与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论及二十八调的产生方法有相类之处,《乐府杂录》云:“太宗朝,三百般乐器内挑丝、竹为胡部,用宫、商、角、羽,并分平、上、去、入四声。其徵音有其声,无其调。平声羽七调: 第一运中吕调,第二运正平调,第三运高平调,第四运仙吕调,第五运黄钟调,第六运般涉调,第七运高般涉调。(虽去中吕调,六运如车轮转,却去中吕一运声也。)上声角七调: 第一运越角调,第二运大石角调,第三运高大石角调,第四运双角调,第五运小石角调——亦名正角调,第六运歇指角调,第七运林钟角调。去声宫七调: 第一运正宫调,第二运高宫调,第三运中吕宫,第四运道调宫,第五运南吕宫,第六运仙吕宫,第七运黄钟宫。入声商七调: 第一运越调,第二运大石调,第三运高大石调,第四运双调,第五运小石调,第六运歇指调,第七运林钟商调。上平声调,为徵声。商角同用。宫逐羽音。右件二十八调。”(8)(唐) 段安节《乐府杂录》,守山阁丛书本,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一),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62—64页。“徵音有其声,无其调。”这与《曲律》所云“四十八宫调者,以律为经,以声为纬,七声之中,去徵声及变宫变徵,仅省为四,以声之四,乘律之十二,于是每律得五调,而合之为四十八调”相类,二者都是构建于宫、商、角、羽系统之上,只不过《乐府杂录》所论是与七调相乘,而《曲律》所论是与十二律相乘。唐代俗乐二十八调与《曲律》论及的四十八调不同,唐代俗乐二十八调是依五弦乐器排列的音律体系,“五弦五本,共应二十八调本”(9)同上,第64页。,应用于宫廷音乐实践。这与王骥德《曲律》论及的由推衍而产生的四十八调,有着根本的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在《曲律》中王骥德将夹钟商、姑洗商都记为双调,将夹钟羽、姑洗羽都记为中吕调。王骥德此处记载有误。陈多、叶长海两先生在《曲律注释》中对此段的注释为:
黄钟宫俗呼正宫: 由此至“应钟羽、俗呼中管羽调”,所列四十八调“俗呼”,与明唐顺之(一五○七—一五六○)《稗编》所记全同。其中姑洗商与姑洗羽的“俗呼”均误,应加上“中管”二字;分别改为“(姑洗商)俗呼中管双调”与“(姑洗羽)俗呼中管中吕调”。(10)(明) 王骥德著,陈多、叶长海注释《曲律注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4页。
两位先生此处是按照之调进行注释校正的,叶先生曾告诉我,这里的校正是以张炎《词源》为依据的。
明代以前记载八十四调调名的史料,尚有《宋史·乐志》所载《景祐乐髓新经》及宋末元初陈元靓的《事林广记》,可从中找出四十八调的对应调名。查《景祐乐髓新经》可知,“蕤宾商为中管商调”“大吕羽为中管中吕调”(11)(元) 脱脱等《宋史》卷七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604页。,如转换成之调式,即姑洗之商为中管商调,姑洗之羽为中管中吕调。《事林广记》云:“律名姑洗羽俗呼中管中吕调”,“律名姑洗商,俗呼中管双调”(12)(宋) 陈元靓编《增新类聚事林广记》后集12卷,西园精舍刊本。。张炎《词源》与《事林广记》所载,均与两位先生考证相合。
两位先生之所以选《词源》而非《景祐乐髓新经》来校正《曲律》,可能与张炎生活的年代距王骥德更为接近有关;且《景祐乐髓新经》所述为北宋宫廷宫调理论,《词源》与《事林广记》所记则反映了南宋末年民间对八十四调的认知情况。
二、 明代“十三调”之辨
王骥德《曲律》在论及明代所用宫调时云:“何以有宫又复有调。何以宫之为六,调之为十一,既总之有七宫调矣(笔者案: 当脱一“十”字,即“既总之有十七宫调矣”),何以今之用者,北仅十三,南仅十一,又何以别有十三调之名也”。
“自元以来,北又亡其四(道宫,歇指调,角调,宫调),而南又亡其五(商角调,并前北之四),自十七宫调而外,又变为十三调,十三调者,盖尽去宫声不用,其中所列仙吕、黄钟、正宫、中吕、南吕、道宫,但可呼之为调,而不可呼之为宫,(如曰仙吕调、正宫调之类)然惟南曲有之,变之最晚。调有出入,词则略同,而不妨与十七宫调竝用者也。”(13)(明) 王骥德《曲律》,明天启四年毛以遂刻本,载《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第23册,第359、366页。
对于王骥德论及的“十三调”,后世一些学者难有确解。这里,试作考辨分析。
北曲与南曲,有着不同的音乐渊源、发展轨迹、音韵体系与音乐构成。北曲源自中原地区,音乐构成主要是北宋以来的宫廷燕乐,包括当时流行的一些词调音乐,后来又有一些北地少数民族音乐融入,至元代中叶已发展成为成熟的音乐体系。明代徐渭《南词叙录》论及南曲时云:“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郎中’之句。或云: 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夫罕有留意者。”(14)(明) 徐渭《南词叙录》,壶隐居黑格钞本,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三),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39页。
徐渭所说的“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是就南曲的音乐而言。“则宋人词”应指南曲音乐中有宋代词调音乐的要素。“益以里巷歌谣”,是指南曲也吸收了大量南方的民间音乐。“不叶宫调”,是指南曲音乐的构成中,不需像北曲那样必须归入某一宫调。
造成南北曲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北政权的对峙,北方政权先后为金、元,南方则为南宋。政权的对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音乐文化的隔绝。元统一中国后,南北音乐始有交流。燕南芝庵《唱论》所云“南人不曲,北人不歌”,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北音乐的差异。元代后期出现的“南北合套”,是将南北曲合于一炉的早期尝试。元代锺嗣成《录鬼簿》记载:“沈和,和字和甫。……以南北调合腔,自和甫始,如《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等曲,极为工巧。”(15)(元) 锺嗣成《录鬼簿》,楝亭藏书十二种本,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121页。南北合套多依北曲曲牌确定宫调,采用一北一南的曲牌排列方式。
从音乐学角度看,音乐的使用有着调式调性、音高等方面的要求。由于南曲“不叶宫调”,没有固定音高,在演唱实践中,就会影响演唱者与乐队的配合。明代蒋孝《旧编南九宫谱·自序》云:“宫徵乖误,不能比诸管弦。”(16)(明) 蒋孝撰《旧编南九宫谱》,明嘉靖己酉三径草堂刻本,载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三辑,(台湾) 学生书局,1984年,自序页。这是音乐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明中叶南曲兴起后,一些文人、乐工对于南曲采用宫调做了很多尝试和努力。王骥德论及南曲宫调,就建立在这个时代背景之上。
《曲律》论及明代宫调,是以南北曲为前提的,有时讲的是北曲的情况,有时讲的是南曲的情况,有时合而论之。搞清了这个论述前提,就不难理解王骥德所论南北曲宫调的真正的含义。
王氏云:“何以宫之为六,调之为十一,既总之有十七宫调矣。”(17)(明) 王骥德《曲律》,明天启四年毛以遂刻本,载《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第23册,第359页。这里讲的是北曲的“六宫十一调”。元代燕南芝庵《唱论》、周德清《中原音韵》均论及“六宫十一调”。在明人眼里,这应该是北曲所用宫调情况。
王氏又云:“何以今之用者,北仅十三,南仅十一,又何以别有十三调之名也。”(18)同上。案: 结合《曲律》后面论述,“北仅十三”,是指“十七宫调”“自元以来,北又亡其四”后而成的“北仅十三”。“南仅十一”,非指在十七宫调基础上“而南又亡其五”后所剩宫调数量。王骥德表述的含义是: 南曲宫调使用中的所用之“调”而非所用之“宫”,在“宫之为六,调之为十一”基础上,“盖尽去宫声不用”,由于无“宫之为六”,那么本该使用的则是“调之为十一”。“又何以别有十三调之名也”,这里的“十三调”,并非论述的是前文所释“十七宫调”基础上“自元以来,北又亡其四”的十三调,因为此十三调是北曲用宫调情况。王骥德所要表述的,是蒋孝、沈璟编曲集为南曲所采的《十三调》。
王氏又云:“十三调者,盖尽去宫声不用,其中所列仙吕、黄钟、正宫、中吕、南吕、道宫,但可呼之为调,而不可呼之为宫。(如曰仙吕调、正宫调之类)然惟南曲有之,变之最晚,调有出入,词则略同,而不妨与十七宫调竝用者也。”(19)同上,第366页。
王骥德所云“十三调”,不是指十三个宫调,而是专指蒋孝的《十三调》,即蒋孝编《南九宫谱》所附的《十三调南曲音节谱》。《十三调南曲音节谱》只收曲牌名,但调下无曲,亦无文词。查蒋孝《十三调南曲音节谱》所记宫调,其实不是十三种,而是十五种: 仙吕、羽调、黄钟、商调、商黄调、正宫、大石调、中吕调、般涉调、道宫调、南吕调、高平调、越调、小石调、双调。其中,商黄调、高平调下不记曲牌。(20)(明) 蒋孝《旧编南九宫谱》,明嘉靖己酉三径草堂刻本,载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三辑,(台湾) 学生书局,1984年。
后来沈璟编《增定南九宫曲谱》(又名《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
从《曲律》所云:“十三调者,盖尽去宫声不用,其中所列仙吕、黄钟、正宫、中吕、南吕、道宫,但可呼之为调,而不可呼之为宫。”可知,王骥德这里论述的是蒋孝的《十三调南曲音节谱》而非沈璟的《增定查补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因蒋孝的《十三调南曲音节谱》有“仙吕、黄钟、正宫、中吕、南吕、道宫”这些宫调,而沈璟《增定南九宫曲谱》中无道宫。
王骥德《曲律》为什么专提“仙吕、黄钟、正宫、中吕、南吕、道宫”这些是“调”而不是“宫”呢?这是针对《中原音韵》而言。《曲律》云:“《中原音韵》所载六宫十一调……仙吕宫清新绵邈,南吕宫感叹伤悲,中吕宫高下闪赚,黄钟宫富贵缠绵,正宫惆怅雄壮,道宫飘逸清幽(以上皆属宫)。”(21)(明) 王骥德《曲律》,明天启四年毛以遂刻本,载《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第23册,第365页。《中原音韵》所收“六宫十一调”皆为北曲,而蒋孝的《十三调南曲音节谱》所收多为南曲,王骥德解释蒋孝《十三调南曲音节谱》所收的“仙吕、黄钟、正宫、中吕、南吕、道宫”均为“十三调”中的“调”而非“宫”,是有缘由的。
王骥德所云:“十三调者,盖尽去宫声不用。”这不是就调名、谱字而言,而是就调式而言,这种情况与北曲大有不同,“惟南曲有之”。
另,王骥德《曲律》云:“六宫十一调”“自元以来,北又亡其四(道宫、歇指调、角调、宫调)”。其中,角调、宫调并非具体的某一宫调,而是指角声系统、宫声系统;道宫在元代的音乐实践中没有使用,歇指调,俗呼林钟商,现存元代曲集未见作为宫调使用者,但有[离亭宴带歇指煞][鸳鸯歇指煞][歇指煞]三种曲牌(皆属双调)。歇指调有曲牌形态无宫调使用形态。
笔者曾在拙作《宋元宫调筋节考》中对今之可见元代史料中宫调使用情况进行过考证,得出结论:“《中原音韵》‘乐府共三百三十五章’中所记十二种宫调是元代北曲实际使用情况。”“元代的‘十七宫调’、‘一十七调’之说应该是源于宋代‘教坊十七调’或‘一十七调’,是作为一种理念在元代的延续。”(22)白宁《宋元宫调筋节考》,载《曲学》第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76页。《中原音韵》记曲牌335章,其使用宫调共12种: 黄钟、正宫、大石调、小石调、仙吕、中吕、南吕、双调、越调、商调、商角调、般涉调。与王骥德《曲律》相比,《曲律》记载北曲十三调中尚有高平调,《补笔谈》载“南吕调(又名高平调)”(23)(宋) 沈括《补笔谈》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页。,在音乐实践中,南吕宫、南吕调二者演奏演唱时所用谱字相同。
三、 关于宫调“声情”
王骥德《曲律·论宫调第四》云:
《中原音韵》所载六宫十一调,其所属曲,声调各自不同:
仙吕宫清新绵邈 南吕宫感叹伤悲
中吕宫高下闪赚 黄钟宫富贵缠绵
正宫惆怅雄壮 道宫飘逸清幽(以上皆属宫)
大石调风流蕴藉 小石调旖旎妩媚
高平调條拗滉漾(拗旧作拘,误) 般涉调拾掇坑堑
歇指调急併虚歇 商角调悲伤宛转
双调健捷激袅 商调凄怆怨慕
角调呜咽悠扬 宫调典雅沉重
越调陶写冷笑(以上皆属调)(24)(明) 王骥德《曲律》,明天启四年毛以遂刻本,载《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第23册,第365—366页。
在《曲律·杂论第三十九》又云:
《中原音韵》十七宫调,所谓“仙吕宫清新绵邈”等类,盖谓仙吕之调,其声大都清新绵邈云尔。其云“十七宫调,各应于律吕”,“于”字以不闲文理之故。《太和正音谱》,于仙吕等各宫调字下加一“唱”字,系是赘字,然犹可以“唱”代“曲”字,谓某宫之曲,其声云云也,至弇州加一“宜”字,则大拂理矣,岂作仙吕宫曲,与唱仙吕宫曲者,独宜清新绵邈,而他宫调不必然,以是知蛇足之多为本文累也。(25)同上,第472—473页。
《曲律》前段所引内容,王骥德云其出处是《中原音韵》,其实,这段文字最早刊于元初燕南芝庵《唱论》,表述不同宫调有着不同的音乐表现倾向,所论是为元代教坊制曲和演唱的格范。
《唱论》此段原文如下(笔者句读):
大凡声音各应于律吕,分于六宫十一调。共计十七调宫。仙吕调唱清新绵邈,南吕宫唱感叹伤悲,中吕宫唱高下闪赚,黄钟宫唱富贵缠绵,正宫唱惆怅雄壮,道宫唱飘逸清幽,大石唱风流醖藉,小石唱旖旎妩媚,高平唱條物滉漾,般涉唱拾掇坑堑,歇指唱急併虚歇,商角唱悲伤宛转,双调唱健捷激袅,商调唱凄怆怨慕,角调唱呜咽悠扬,宫调唱典雅沉重,越调唱陶写冷笑。(26)(元) 燕南芝庵撰《唱论》,载《历代散曲汇纂》元刻十卷《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卷首,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98年。
元代中叶的《中原音韵》和明初《太和正音谱》都载此段文字。由于《中原音韵》流传较广,因此后世一些曲论者、制曲者多有了解这种格范,王骥德似未全览以上著作,将其记在《中原音韵》之下。
笔者曾在拙作《燕南芝庵〈唱论〉研究》中,通过考证推论出:
这段记述很可能也不是元人所作,而是前代教坊一代代传承的有关制词与演唱的一种格范。宋代释明辩(1085—1157)作《偈》八首,其六有句“吹尽风流大石调,唱出富贵黄钟宫”。这与《唱论》中“黄钟宫唱富贵缠绵”、“大石唱风流醖藉”是一致的。(27)白宁《燕南芝庵〈唱论〉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年,第221页。
元代乐工有户籍,多强调自己的教坊身份,以示传承正宗。明初的乐工,也常在演出时强调传自于前代的“梨园格范”和宫调音乐赋义。《永乐大典残存戏文三种》中的《宦门子弟错立身》中,讲述了金代院本艺人的故事,其中[紫苏丸]有“老身幼习伶伦,生居散乐。曲按宫商知格调,词通大道入禅机”句(28)钱南扬《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227页。;《小孙屠》中[满庭芳]有“想像梨园格范,编撰出乐府新声”句(29)同上,第257页。。
《曲律》对这种观点持否定态度,与时代背景相关,也与作者身份有关。王骥德论述系观察明代南北曲实践总结而成。明人早期以北曲格式所制之曲,便已多有不合于教坊格范者;明中叶后兴起的南曲与北曲更系两途。王骥德是明末人,其时无论是北曲还是南曲,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都不再遵从传自于前代的教坊格范,因此王氏对前人宫调的理论赋予产生质疑并不奇怪。
其实,元代北曲也非严守教坊格范。元代曲集《朝野新声太平乐府》载任则明[南吕·一枝花](题东湖)散套是游兴之作,全曲充满兴致,其首曲:“纤云曳晓红,远树团晴翠。好山如凤凰,新水似琉璃,巧画屏帏。壮观蓬莱地,东湖景最奇。两三行鸥鹭清闲,七十二峰峦秀美。”(以下[梁州][尾]内容相近,略。)(30)(元) 杨朝英选《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四部丛刊影元刻细字本,载《历代散曲汇纂》,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1998年,第61页。文词与《唱论》中“南吕宫唱感叹伤悲”相去甚远,唱工是无法借演唱传递出伤悲之情的。
从音乐自身看,宫调具有规范音高及音与音之间关系的功能。随着音乐实践的不断发展,曲牌体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对音乐旋律的固化,演唱与伴奏乐器之间的协适调整,以及基于音乐实践所造成的调式使用的筛选,使得宫调的很多功能,包括礼乐方面的赋义逐渐回归到音乐本体之中。这样就逐渐强化了音乐的本体性,弱化了对宫调的赋义和规范。这符合音乐发展的自身规律。明代南曲“不叶宫调”,并不意味着南曲没有调式调性。南曲宫调格范虽不严谨,但这恰恰是南曲具有鲜活生命力、能够得以更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今之一些学者将《唱论》这段论述称为“宫调声情论”或“宫调声情说”。其实,元代并没有“宫调声情”的提法,把宫调与“声情”联系在一起始于清代,清初《御定曲谱》卷首引《九宫谱定论说》(未署撰者)与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是有关宫调与“声情”的两则较早阐述,是所谓“宫调声情”在清代的最早记载。
明代曲集所收作品,亦有不合于教坊格范者。如沈璟《增定南九宫曲谱》“仙吕过曲”下收明初陈大声《安乐神犯(犯排歌)》,文词哀伤幽怨,而非《曲律》所引“仙吕宫清新绵邈”,其文词是:
愁人厌听。西风一片捣练砧声。试将郎意比浮萍。萍踪稳似郎心性。欲把寒衣寄。无限别离情。远道谁堪倩。 风和雨。不堪晴。纷纷落叶满江城。萧条意。迟暮景。这般幽怨几曾经。(31)(明) 沈璟编《增定南九宫曲谱》卷一,明末永新龙骧刻本,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第三辑,(台湾) 学生书局,1984年,第146—147页。
四、 明代视野下的律吕与宫调
王骥德《曲律》云:“古有旋相为宫之法,以律为经,复以律为纬,乘之每律得十二调,合十二律,得八十四调。”又云:“又古调声之法,黄钟之管最长,长则极浊,无射之管最短,(应钟又短于无射,以无调,故不论)短则极清……此其法本之古歌诗者,而今不得悖也”。(32)(明) 王骥德《曲律》,明天启四年毛以遂刻本,载《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第23册,第360、367页。
王骥德所云“旋相为宫之法”、音律之管,其实是关于律吕的论述,其论述应来源古代记载,而非明代南北曲实践。
古时常用“律吕”代指雅乐。律吕中宫居首位,用“三分损益法”生其他音律,有左旋之法与右旋之法。中国古代典籍有关乐律的部分常见这类记载,宋代陈旸《乐书》中讲述较清楚,这里引用《乐书》卷一百一进行观察(笔者句读):
律吕子声
先儒之论律吕,正声倍,子而为母,子声半,正而为子,若黄钟之管,正声九寸为均,其子声则四寸半,三分损一,下生林钟之子,又三分益一,上生太蔟之子,由是第之终于中吕,以从十二母相生之法。故黄钟为宫而下生林钟为徵,林钟上生太蔟为商,太蔟下生南吕为羽,南吕上生姑洗为角,此黄钟之调皆得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声。……凡此蔽于十二律均旋为宫之说,失周礼三宫之意也。三宫旋相而唱和有应,曷尝有子声耶?若以为十二律皆有子声,然则黄钟、大吕、太蔟三律何独止用正声耶?(33)(宋) 陈旸《乐书》,四库全书本。
此即王骥德《曲律》所云:“则律之自黄钟以下,凡十二也,声之自宫商角徵羽而外,有半宫半徵凡七也,古有旋相为宫之法。”(34)(明) 王骥德《曲律》,明天启四年毛以遂刻本,载《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第23册,第360页。
古人为确定律吕音高,制作律管以定音。律管并非演奏乐器,通常仅承担校正乐律之功用。其长度与音高相关。《史记·律书》载:“律数,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徵……黄钟长八寸十分一宫。大吕长七寸五分三分一。太蔟长七寸七分二角。夹钟长六寸一分三分一。姑洗长六寸七分四羽。仲吕长五寸九分三分二徵。蕤宾长五寸六分三分一。林钟长五寸七分四角。夷则长五寸四分三分二商。南吕长四寸七分八徵。无射长四寸四分三分二。应钟长四寸二分三分二羽。”(35)(汉) 司马迁《史记》,四库全书本。
汉代郑玄注、唐代孔颖达等正义的《礼记正义》载:“律中黄钟之宫。黄钟之宫最长也。”(36)(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疏《礼记正义》,阮元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16页。与王骥德云“黄钟之管最长”“无射之管最短(应钟又短于无射……)”相合。
依今天乐器制作工艺看,长律管发出的音律低于短律管发出的音律。由此,“黄钟之宫”应是十二律吕中音律最低的那个律管。
律管能够规范音与音之间的音律关系,但历代乐律的音高并不相同,因此虽然“黄钟之宫”始终是十二律吕中音律最低的律管,但不是所有朝代的“黄钟之宫”音律的音分都是相同的。《史记·律书》、《汉书·律历志》提出以黍度尺来确定黄钟律,称为“黍律”。“黍律”并不精确。《隋书·律历志》记载南北朝北周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律的一段话:“今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正以时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异,取黍大小,未必得中。”(37)(唐) 魏徵等《隋书》卷十六,中华书局,1973年,第407页。
用多少黍粒装入容器之办法来确定黄钟律,并不科学,加上“时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异”,造成黍粒大小不同、重量相异,其结果只能是“未必得中”。(38)同上。
北宋徽宗听信蔡京主张,不再用“黍律”,而“以帝指为律度”,《宋史·乐志》记载:“徽宗锐意制作,以文太平,于是蔡京主魏汉津之说,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为度之文,以帝指为律度,铸帝鼐、景钟。乐成,赐名《大晟》,谓之雅乐,颁之天下。”故《宋志》云:“故宋之乐屡变,而卒无一定不易之论。”(39)(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85年,第2938页。
明代宫廷雅乐具有封闭性,文人、民间乐工多接触不到。明代文人所云律吕,多传自前代论述,对其律度已不甚明晰。《曲律》云:“今正宫曰惆怅雄壮,近浊;越调曰陶写冷笑,近清。”(40)(明) 王骥德《曲律》,明天启四年毛以遂刻本,载《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第23册,第367页。王骥德认为,因为“正宫曰惆怅雄壮”所以其律管最长,长则“近浊”,因为“越调曰陶写冷笑”所以其律管短,短则“近清”,将雅乐定律吕之律管音高与宫调所反映的教坊格范置于同等地位论述,这与中国传统礼乐观念不合。
律吕与宫调有着密切关系: 宫调生成之法,依律吕而成;宫调各调相互间的调式关系,需通过十二律予以固定;燕乐各调之音高,也应与律吕相对应,即王骥德《曲律》所引“十七宫调各应于律吕”。北宋、元代民间音乐所用宫调均应于律吕。笔者曾在拙作《燕南芝庵〈唱论〉研究》中说:“《唱论》中‘各应于律吕’,用的是‘应’字而不是‘合’,用字非常准确,‘应’是一种主从关系,燕乐宫调的音准音高要服从于律吕,根据雅乐来推定。这不是音乐学的问题,而是因为雅乐是宫廷礼乐的主体音乐。如果用‘合’,则成为并列关系,显然不符合礼乐制度。”(41)白宁《燕南芝庵〈唱论〉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年,第192页。
在音高标准上,雅乐律吕与燕乐宫调存在相对应关系,律吕的音高若有变动,处在从属地位的燕乐,也需变动宫调的音高。《宋志》之“乐十七”记载了神宗朝时宫廷音高的改动,熙宁九年时:“教坊副使花日新言:‘乐声高,歌者难继。方响部器不中度,丝竹从之。宜去噍杀之急,归啴缓之易,请下一律,改造方响,以为乐准。丝竹悉从其声,则音律谐协,以导中和之气。’诏从之。”(42)(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四十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3358页。燕乐“乐声高,歌者难继”,需先通过律吕“下一律”,而后依律吕校正宫调音高。这就是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都记述“今乐高于古乐二律以下”,但《笔谈》云“只以合字当太吕,犹差高,当在太吕、太蔟之间”(43)(宋) 沈括《元刊梦溪笔谈》卷六,古迂陈氏家藏本,文物出版社,1975年,第4页。,《补笔谈》却说“今燕乐只以合字配黄钟”(44)(宋) 沈括《补笔谈》卷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4页。,二者记载的音高相差一律多,其他各声用字亦相差一律多原因的由来。笔者曾撰《宋元宫调筋节考》,有过考证推论:“熙宁九年(1076),该年沈括‘以集贤院学士知宣州’,后又改知延州、谪均州团练副使、徙秀州,最后‘居润八年卒’(见《宋史·沈遘传》所附沈括事迹)。由于沈括多年在外,缺少与宫廷燕乐的接触。《梦溪笔谈》所记,应是花日新乞改教坊音高之前的情况,沈括作《补笔谈》时,记载的是后来所知。因此沈氏只补不改,其前后所记均为实情。”(45)白宁《宋元宫调筋节考》,载《曲学》第四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50页。
《曲律》记述:“其宫调之中,有从古所不能解者,宫声于黄钟起宫,不曰黄钟宫而曰正宫,于林钟起宫,不曰林钟宫而曰南吕宫,于无射起宫,不曰无射宫而曰黄钟宫,其余诸宫,又各立名色,盖今正宫实黄钟也,而黄钟实无射也。”(46)(明) 王骥德《曲律》,明天启四年毛以遂刻本,载《中国古代音乐文献集成》第三辑第23册,第366—367页。“有从古不能解者”,反映了王骥德发现宫调的调名与起音存在矛盾。其实,这段话既讲宫调又涉及律吕。在律吕体系中,黄钟起宫者即为黄钟宫,林钟起宫者即为林钟宫,无射起宫者即为无射宫。而在宫调体系中,黄钟起宫者称正宫,林钟起宫者称南吕宫,无射起宫者称黄钟宫。
为什么律吕名与宫调名多有不同?为何同样从黄钟起音的调名却有不同?为何律吕称为“黄钟宫”而宫调称为“正宫”?或可从《宋史·乐志》有关鼓吹乐的记载中找到原因。“元丰中,言者以鼓吹害雅乐,欲调治之,令与正声相得。杨杰言:‘……国初以来,奏大乐则鼓吹备而不作,同名为乐,而用实异。虽其音声间有符合,而宫调称谓不可淆混。故大乐以十二律吕名之,鼓吹之乐则曰正宫之类而已。……若以律吕变易夷部宫调,则名混同而乐相紊乱矣。’遂不复行。”(47)(元) 脱脱等《宋史》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1977年,第3303—3304页。
不将燕乐宫调中以黄钟为宫音的宫调式称为黄钟宫,是因雅乐与燕乐不同,因此名不能相同以示区别。前引杨杰所言:“大乐以十二律吕名之,鼓吹之乐则曰正宫之类而已”,“而宫调称谓不可淆混”。在封建统治者看来,雅乐关乎国运天命,其音乐政治功能、社会功能较强,在诸乐中居统领地位。燕乐虽为宫廷音乐,音乐娱乐性较强,不可与雅乐置于同等地位。虽同属宫廷音乐,但雅乐与燕乐、鼓吹乐、钧容直等其他宫廷音乐的尊卑不同。
王骥德《曲律》对律吕与宫调的关系认识混淆,反映的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明代文人、民间乐工对律吕认识的模糊。很多明代文人的记述中,有时用“律吕”代指乐音、音律。如,沈宠绥《度曲须知·中秋品曲》云:“从来词家只管得上半字面,而下半字面,须关唱家收拾得好。盖以骚人墨士,虽甚娴律吕,不过谱厘平仄,调析宫商,俾徵歌度曲者,抑扬谐节,无至沾唇拗嗓,此上半字面,填词者所得纠正者也。”(48)(明) 沈宠绥《度曲须知》,明崇祯原刻初印本,载《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五),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03页。这里所说的“律吕”,已距本义相去甚远。
在明代的曲学实践中,既存在着南曲“不叶宫调”,在曲学著作中,也存在着大多数学者搞不清律吕与宫调之间的关系问题。王骥德《曲律》论宫调中有“有从古不能解者”,就反映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