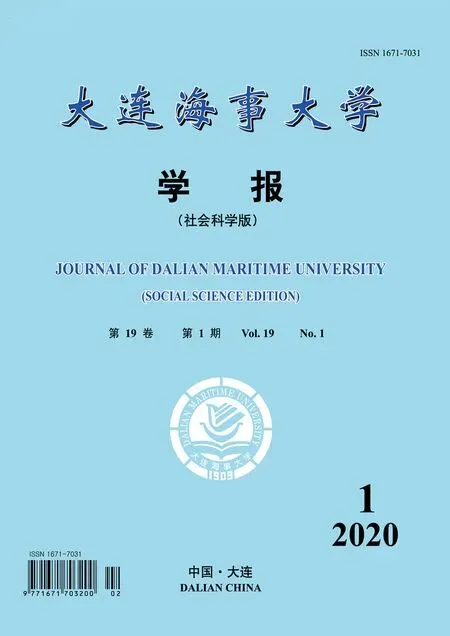“责任”视域下的“心”与“物”
——王阳明“心外无物”新解
黄 瑶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 210046)
“心外无物”学说在阳明哲学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学界对“心外无物”的讨论层见叠出。李瑞全教授等认为,“阳明之提出心外无物,是良知教的理论上所蕴含的一个论题,但它的证成也可以说是阳明学,以至正统儒学,是否合理或有违常识的一块试金石”[1]。可见“心外无物”命题的重要性。但是就目前学界来说,对“心外无物”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心外无物”为依据批判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倾向;二是将这一命题与现象学的意向性构造相提并论。这样的做法未免陷入简单化流弊,造成对“心外无物”命题的误读。事实上,阳明的“心外无物”说较之其他宋明儒学的进展,正在于将心物交融贯注于自我对他者的责任之中。本文力求回归“心外无物”的原初内涵,深挖阳明思想中以仁爱关怀为主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意识。
一、心:自觉承担
要想全面地把握“心外无物”命题,首先需要对“心”的内涵做出准确的界定。《说文解字》里对“心”是这样描述的,“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凡心之属皆从心”。“心”的本意虽是心脏,但由于其处于身躯的中央位置,古人多将“心”引申为思维的器官,把思想、感情、意念、性情、谋划、思虑等都说成“心”。儒家哲学沿用了“心”的这种引申含义,其对“心”的考察可以追溯到孟子的“四端说”。孟子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2]68在这里,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都是由“心”生发构成的,“心”被赋予了本体论意义,成为德性生发的源泉。同时,孟子进一步指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2]261所谓“放心”就是要把丢失的善心找回来。在孟子看来,人们在现实世界往往会迷失自己的道德本心,“求放心”的过程就好比是将蒙尘的玻璃擦拭干净,是一种修心的工夫。
这种修心的工夫发展到陆九渊那里就是“悟”。陆九渊曾自述其学术渊源,称“因读《孟子》而自得之”[3]471。“心即理”的命题最早就是由陆九渊提出来的,陆九渊说:“盖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始不容有耳。故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己矣。’又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如是则仁,反是则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陆九渊还说:“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3]4-5显然,陆九渊的“心即理”,从根本上就是把一切道德原则与价值建立在道德本心之上,“心”是“理”的本体。他认为人们只要“切己自反”就可以获得先天的道德本心。他说:“女耳自聪,目自明,事父自能知孝,事兄自能知弟,本无欠阙,不必他求,在自立而已。”[3]399在陆象山看来,人人皆有与理同一之心,即所谓“本心”,只要秉持本心,就自然能够分辨是非善恶。当“本心”被遮蔽时,象山主张采取类似于禅宗“顿悟”的方式回归“本心”。正如《宋元学案》所记载的那样:陆象山至富阳,夜集双明阁,象山数提“本心”二字。先生问:“何谓本心?”象山曰:“君今日所听扇讼,彼讼扇者,必有一是,有一非。若见得孰是孰非,即决定为某甲是,某乙非,非本心而何?”先生闻之,忽觉此心澄然清明,亟问曰:“止如斯耶?”象山厉声答曰:“更何有也?”先生退,拱坐达旦,质明纳拜,遂称弟子。[4]在拱坐达旦之间,陆象山完成了领悟本心的过程。这种极简的“顿悟”方式是朱子极力反对的。
与陆九渊“切己自反”的内寻路径不同,朱熹主张通过读书等穷理的工夫来实现“心”的回归。朱子说,“人之一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5]1419,“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应事物者也”[5]3108。在这里,朱子将“心”与“知觉”等同起来,使“心”在朱子哲学中丧失了本体上的意义,成为形而下的经验范畴。正因如此,陈来才会认为,朱子对“心”的论述“全面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荀子关于心的见解”[6]。荀子是这样描述“心”的:“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拙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情之至也,不贰’。”[7]可见,荀子的“心”被赋予了认识论的功能,“心”就是“认知心”,它可以认识一切事物,并且对所认识的事物进行“自夺”与“自取”,这与朱子所主张的“心”是不谋而合的。这样的诠释虽然能够避免像陆九渊一样将道德本心简单化,但是却容易将“心”引入片面寻求认知工夫的漩涡,对外在穷理的强调让富含认知意义的“心”脱离了主体意志的自主选择,外在的知识与规范变成了“心”的桎梏,“心”不再能自发地选择道德行为,而只能头戴“知识”的紧箍咒模仿自认为正当的道德行为。当一种行为不是源于内心的选择,那么它就仅仅是一种伪装和假面,行为本身也就丧失了真正的道德价值。事实上,朱子对“心”的这种解释,也正是导致朱子后学中产生以认知工夫代替道德修养倾向的原因。
如果说陆九渊以“悟”归“心”的方式过于简单,朱熹以“认知”释“心”的理解流于片面,那么王阳明对“心”的诠释恰恰是博采众长,择善而从。阳明心学的形成,是在王阳明经历了“读书学圣贤”、“庭前格竹”、“龙场悟道”等百死千难之后的有感而发。当时朱子学定于一尊,象山心学日渐式微,由于对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的失望,“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提出:“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8]1228至此,奠定了王阳明“心即理”的心学宗旨。正如《传习录》里所记载,“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8]17-18由此看出,在王阳明眼里,“心”指的是先天的道德本心,德性的散发是自然而为的,所谓“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正是这个道理。这与朱子的“认知心”完全不同,可以说“心即理”的提出有力地冲击了程朱理学“析心与理为二”的观点,标志着王阳明与程朱理学的分道扬镳。正因如此,当阳明将“圣人之学,心学也”作为对儒家道统的本质理解时,才会将陆九渊置入其中,而将朱子排除在外。
虽然阳明与象山都主张“心即理”,认同“心”的本体论意义,坚持人人具有先天的道德本心,但是由于对修心工夫的认知不同,阳明之“心”与象山之“心”最终也大相径庭。象山认同以“静悟”的方式实现心理合一,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逐外寻理的弊端,但是终会“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为了避免陷入释老之学,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所谓“良知”便是道德本心,而“致”与陆九渊的“顿悟”不同,它是一种渐进扩充的修养工夫。王阳明指出,“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8]69,只是“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8]6。可见,阳明认为人人皆有良知,但是常人的良知总是被私意所蒙蔽,所以必须运用“致”的工夫追寻良知。他认为,“致良知”的工夫“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8]96“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当“良知”充盈圆满之时,那么便能够使得“事事物物各得其理”[8]45,这便是“致知格物”。可见,阳明所主张的“致”是向内追寻本有之良知,这与朱熹的“格物致知”主张“求理于外”有本质的不同。
综上所述,王阳明完成了“心”的本体论转向,“心”的内涵在阳明哲学里摆脱了外寻认识的偶发性,扩充进了丰富的责任意蕴。在王阳明眼里,“心”既不是朱熹的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心,也不再是陆九渊哲学里单纯靠“悟”就可以获得的先天自得。一方面,王阳明肯定了作为道德本心的“心”的本体论意义,认为人人皆有良知,这就为德性的生发提供了可能。正是因为人们先天具有道德本心,才能为道德行为提供有力抓手,才能让主体责任拥有萌芽的温床,最终实现德性的回归。另一方面,王阳明改变了以往以外物寻理的实践方式,主张人们把道德实践用功的地方从“外”转向“内”,在自我的身心上用功。这样的做法能够有效地树立人们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与自觉性,从而为主动担当提供理论保障。可以说,王阳明在前人的基础上完成了“心”的重构,“心”成为责任的发源地,自觉承担的责任观在“心”的加持下成为可能。
二、物:连接他者
如果说对“心”的内涵的重构为阳明哲学里的责任伦理生发提供了必要条件,那么对“心外无物”的进一步阐释便为阳明责任观的树立提供了充分条件。上文已对“心”的含义进行了全面的把握,所以若要进一步理解“心外无物”,就要准确理解阳明所述之“物”。
阳明最初提出“心外无物”的命题是在他与徐爱的一段对话中——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用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8]6-7
从中可以看到,王阳明认为“物”就是“事”,那么何谓“事”?在《答顾东桥书》中阳明曾将“事”与“意”联系起来,阳明云:“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其虚灵明觉之良知,应感而动者谓之意。有知而后有意,无知则无意矣。知非意之体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意用于听讼,即听讼为一物:凡意之所用无有无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矣。”[8]53-54可见阳明认为体现“意”的地方就是“事”,在这里“意”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阳明看来,只有包含“意”的“事”才能被称为“物”,因此,要想知道“事”的含义就必须对“意”进行把握。在这里,阳明认为“心之所发便是意”,那么“意”必然是一个已发的范畴,是在先天道德本心的发端下的经验之“意”。它生发于德心善性,又体现着德性的光辉。正如阳明所说:“《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8]7由此看出,阳明所阐发的“意”便是正心诚意,这与《大学》里“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9]是相互契合的。
既然“意”指的是“诚意”,那么在阳明看来,体现诚意之事便是物。“事亲”、“事君”、“仁民爱物”、“视听言动”都指的是道德行为,所以“事”必然具有“道德行为”这一内涵。如上文所述,阳明认为“物”等同于“事”,所以,阳明眼中的“物”便是指真心诚意、毫无矫饰的“道德行为”。这种饱含“诚意”的道德行为当然不是信手拈来、随意生发的,这样的道德行为在阳明看来必然是萌芽产生于良心善性之上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心外无物”从根本来说就是强调“心”在道德实践中的自觉,任何具体的道德实践都不能脱离道德主体的道德本心而单独存在。这也就明确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性,人们必须为自己所发动的道德行为负责。
由此可知,“心外无物”之“物”在阳明眼里包含着“意”和“事”这两层意蕴。这样的“物”既不是通常所说的自在之物,也不是作为道德行为的对象之物,而是指由道德本心发动而来的,诸如“事父”、“事君”、“治民”等道德实践的行为之“物”。在现实世界中,自我与他者构成意义的主体,但是如果这里的自我与他者是相互孤立的,仅仅构成一幅“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图景,那么这样的世界一定是死气沉沉、没有活力的。意义的进入必定是在自我与他者发生关系之后才会发生的。正如杨国荣教授所说,“意之在物既是一个意向(意指向对象)的过程,又是主体赋予对象以意义的过程”[10]72。林丹教授也认为,“‘心外无物’之说,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它并不是要论述到底有无‘客观存在’的‘外物’、‘对象’,它的思想意义首先在于要求我们不执著于没有真切意义的‘外物’;而一个真正的‘意义世界’必是与吾心切己相关的、相互交融、相生互构之中的世界”[11]。在这样的“意义世界”里,当人们感悟自我的道德本心时,自然能够触动悲天悯人的情怀,从而主动为他者承担道德责任,最终建立起自我与他者紧密的道德关系。正因为如此,“心外无物”之“物”便构成了连接自我与他者的黏合剂,在道德践履之中实现责任的担当。
在这里,可以看到,“物”的含义被进一步扩充,当自我以道德行为的方式作用于对象之物时,自我与对象之物的道德关系也随即确立,“物”被赋予了第二层含义——“关系之物”。杨国荣教授就曾指出,“王阳明在构造其宇宙图景时是以“人与对象的关系为出发点”[10]71的,因此,就阳明“心外无物”命题的宗旨而言,反映的就是在道德实践中作为主体的自我与对象之间的道德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之中,阳明所关注的不是道德对象的自然存在,而是道德对象之于道德主体的道德关系的存在。就道德意义上来说,阳明通过“心外无物”告诉人们,自我与对象之间是“关联性”的存在,脱离了这种道德之“事”的关联性,自我与对象在意义上就成为“不存在”之物。“物”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是行为的过程,更是主体赋予道德对象以意义的过程。正如当我们无作为地面对“亲(父母)”、“君”、“民”时,“亲”、“君”、“民”仅仅是有别于自我的无差别的他者,只有当心体指向这些对象时,他们才能作为伦理关系上的道德对象呈现于主体面前。亦即对主体来说,这些对象才能真正获得“亲”、“君”、“民”的意义。当然,就以事父、事君、治民来讨论“心外无物”来说,阳明的对象之物是与自我同类的“他者”,架构的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道德关系,这样的道德关系的建立彰显了阳明强烈的道德意识和责任担当,成为联结自我与他者的桥梁。
三、心与物一:为他者负责
通过对“心外无物”里的“心”与“物”进行分析,可以看到,王阳明一方面赋予了“心”以本体论意义,肯定了“心”的主体性与自觉性;另一方面,阳明认为“物”是由“心”所自然发动的,这个“物”不是独立于“心”之外的自然之物,而是在道德本心的规范指导下生发的道德实践与道德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具有自觉意识之“心”与主动承担之“物”是合二为一的,正如《传习录》所载:“良知头脑,是当去朴实用功,自会透彻。到此便是内外两忘,又何心事不合一?”[8]105可见,阳明主张破除内外之分,物我之别,达到心体与外物的融合,那么这种融合何以实现呢?
杨国荣教授认为,“心”与“物”的融合是在意向中实现的,他说:“王阳明以意向活动联结心与物,从存在的超越考察转向了意义世界的构造,其思路在某些方面与胡塞尔有相近之处。”[10]76所谓意向性是指“意识对被意指对象的自身给予或自身拥有(明见性)的目的指向性”[12]。简而言之,意向活动就是将外物化为意识的过程。胡塞尔曾指出“任何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13],这句话奠定了胡塞尔意向性现象学的基础。在胡塞尔看来,意识的本质就是用意识活动去消融外在之物,从而使整个外在对象都变成了意识世界的存在。
如果仅仅从字面意思去理解,很容易将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与意向活动等同起来。正如很多学者在提起“心外无物”时必然想起著名的“南镇看花”——先生(王阳明)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8]107-108
这段文字被看作是证明“心外无物”为意向活动的有力证据,但是仔细分析就能窥见其中端倪。山中自开自落之花是独立于主体的自在之物,就自在之物而言,山中花树自然与心体无关,但是花的颜色是否明白是相对于观花主体来说的,也就是说一旦涉及此花的颜色,那么必然与心体的审美相关。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14]。因此,只有当自在之物与具有审美能力的主体相遇时,自在之物才能被赋予意义。“南镇看花”是王阳明为了说明“心外无物”而引述的例子,人们很容易简单地认为其意义就在于证明阳明是所谓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但是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阳明为了让“心外无物”更加浅显易懂,在这里对“心外无物”的本意进行了隐喻,“心外无物”在这个故事里构筑的是一个具有审美意义的世界,“心”与“物”建立起来的是审美关系,“物”并不是单纯的自在之物,也不是由自在之物幻化的意识,而是一种审美活动,这与阳明的“知行合一”也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仅仅将阳明的“心外无物”看成是意向活动,显然是不恰当的,这不仅背离了阳明一贯强调的“事上练”的主张,也容易流入虚禅的境地。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情况下,有学者进一步提出,王阳明的“心”与“物”最终交融于道德关系之中。比如南开大学的单虹泽博士就认为,“阳明思想的核心就是建立在主体间交往基础上的万物一体之学”[15]。这种交往包含着推己及人的“移情”意蕴,具有普遍的良心善性。经由上文分析可知,阳明赋予了“心”以本体论意义,主张通过内寻的路径去求得先天的道德本心,在道德本心的发端之下,主体必然会主动践履道德行为,从而构建起自我与他者和谐的道德关系。似乎“心外无物”最终的落脚点便是建立起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道德关系,但是如果隐去其他分析,仅仅认为“心外无物”最终体现的就是一种道德关系,这难免会落入以偏概全的窠臼,从而忽略了“心外无物”之中所体现的“心”的自觉性与“物”的实践性。
综上所述,“心”与“物”的交融必定包括两个方面的意蕴:一是体现作为道德本体之“心”的主体性和自觉性;二是蕴含作为行为之“物”的实践性和交往性。在笔者看来,同时具有这两方面含义的便是责任,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担当情怀。
按照《说文解字》所载,“责,求也,从貝朿聲”,“任,符也。从人壬聲”。也就是说,“责”意为要求,“任”意为委任、担当。据此,吴先伍教授认为,责任即“将他人的要求担当起来”[16]。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弗洛姆(Erich Fromm)所说,“责任并不是外在强加的义务,而是一件完全自觉的行动,是我另一个关心的生命愿望的答复”[17]。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也认为,“回应他者就是对他者负责”[16]。在王阳明“心外无物”的阐释中,人们看到的正是自我对他者的主动回应。这种回应也就是自我作用于他者的“道德行为”,是“用在于事亲”、“用在于事君”、“用在于仁民爱物”的积极担当。
对于这种责任担当,王阳明是具有自觉意识的。综观阳明的一生,无论是“读书学圣贤”还是“庭前格竹”,无论是“谪官龙场”还是“龙场悟道”,无论是“教化讲学”还是“天泉证道”,无论是“破除贼寇”还是“平定靖乱”,阳明用自己的道德践履为责任担当做了最好的注脚。在《答聂文蔚书》中,阳明写道:“古之人所以能见善不啻若己出,见恶不啻若己入,视民之饥溺犹己之饥溺,而一夫不获,若己推而纳诸沟中者……仆诚赖天之灵,偶有见于良知之学,以为必由此而后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则为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见其若是,遂相与非笑而诋斥之,以为是病狂丧心之人耳。呜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体,而暇计人之非笑乎!”[8]90此番肺腑之言,字字珠玑,无不展示着阳明对于百姓疾苦的关切与担忧。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道德本心的主动生发,是道德践履的自觉担当,也让人们看到,在“责任”的视域之下,“心”与“物”完美交融、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