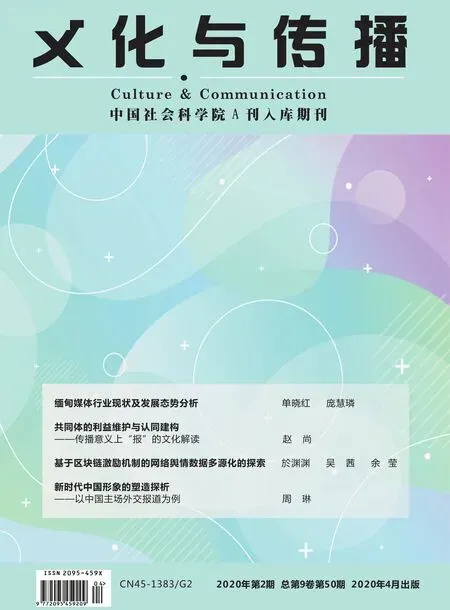新媒体环境下暴恐事件网络舆情传播路径探析
暴恐事件是非常规性的突发事件,较一般事件而言具有敏感性、残忍性和极大的危害性。暴恐事件的特殊性决定了暴恐事件网络舆情具有特殊性、片面性和情绪化等特点,暴恐事件在社交媒体上的扩大化和扭曲化传播易引发恐慌[1],其舆论风向如果引导不力,引发的带有负面社会情绪可能对社会安定和谐、社会公共秩序、社会信任体系甚至民族之间的关系造成威胁。因此,应该有针对性地分析暴恐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并探索有效应对机制,防止暴恐事件网络舆情产生二次危害。
一、传播路径
通过相关文献分析,新媒体环境下暴恐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可以分为单一型、单向型和多向型等三种传播路径。
单一型是指各受众直接从信息源接收信息,受众相互之间基本不受影响,传播路径比较短。在这种路径中,各受众直接从信息源接收信息,整个信息传播过程基本不存在两级传播现象,但可能包含碎片化信息传播。不论是传统媒体时代还是新媒体时代,单一型传播路径都是暴恐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类型。
单向型是指受众A从信息源接收信息,传播至受众B,受众B从受众A处接收信息,再传播至受众C,以此类推。在单向型传播路径中,很有可能存在着多个意见领袖,各个意见领袖作为两级传播的中心媒介,传播至其下一级受众的信息可能与其接收到的信息出现无意甚至有意的偏差,再加上碎片化信息传播等现象的存在,单向型传播路径中可能存在舆论发酵、催化等现象,甚至出现关于暴恐事件的网络谣言和煽动性言论。单向型传播路径中受众数量基本不受限制,但传播效率较慢。
多向型是指多条单一的路径通过受众相互之间不定性的多向联系发生了交叉重合,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传播网络,可以说是单一型路径和单向型路径的结合。在多向型传播路径中,碎片化传播、两级传播等现象频繁出现,加之某些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掺杂其中,网络舆论常常通过多向型传播路径发酵、催化,向着不乐观的方向发展。
二、传播过程
新媒体环境下暴恐事件网络舆论的形成往往形成一个生命周期,这个周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潜伏酝酿阶段
暴恐事件发生之后,网上开始有关于该事件的消息流出,网络媒体、“大V”开始转载报道,社会网民开始评论关注。暴恐事件的网络舆论形成的一大原因是其具有敏感性和社会安全相关性,暴恐事件往往受到社会公众的明显关注且容易引发广大网友的共情心理,暴恐事件对自身和家园安全性的威胁使得社会公众缺乏安全感甚至对社会秩序产生怀疑,从而引发暴恐事件舆论开始酝酿。
(二)初步发展阶段
社会网民针对暴恐事件开始在各大互联网站、论坛、新媒体平台展开激烈的讨论,转发评论急速增加,并对暴恐事件相关动态保持持续的关注。当暴恐事件开始出现网络舆论的苗头时,部分官方媒体也已经对暴恐事件进行了一定的事实报道。权威媒体对暴恐事件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网络上其他网络媒体,这些网络媒体随即参与其中。社会网民在网络上看到自己所关注的事件开始大规模的出现并得到众多网络媒体的提及,更加刺激他们在网络上参与讨论,并且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认识对网络上出现的信息进行评论、发表意见。越来越多的网友参与进该暴恐事件的讨论中,使得主流媒体开始对暴恐事件进行深度报道,并可能提及其它暴恐事件作为对比,在此过程中,有关于该暴恐事件的网络讨论逐渐增加,社会网民的发声也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涟漪效应。
(三)高涨形成阶段
社会网友和众多网络媒体针对暴恐事件进行着激烈的讨论,并在不同的社交网络媒体上进行转发散播,不同甚至相反的意见观点进行融合或碰撞,各种官方权威媒体也参与其中,逐渐在网络上形成了基本一致的一种观点或者完全相反的不同观点,网络舆论基本形成。随着网络舆论的升级,暴恐事件的相关信息在线上线下均得到了众多的关注,并可能形成“线上传播、线下实施;线上煽动、线下轰动”的风险效应,甚至开始显现出各种负面社会情绪。
(四)衰减消退阶段
随着官方权威媒体对暴恐事件的真实情况进行公开报道和对暴恐事件引发的各种问题进行回应,社会网民的负面情绪得到疏通和缓解,渐渐从不理智的恐慌焦虑状态回归理智。并且暴恐事件发生后网络上的讨论热烈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渐渐下降,整体的网络舆论开始随着官方政府的引导和控制往积极的方向发展。社会网民渐渐开始关注其它新的网络事件、对暴恐事件的关注度逐渐下降,暴恐事件网络舆论逐渐衰减消退。
三、传播机理
在这样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中,新媒体环境下暴恐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演进,呈现以下特点:
(一)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动增强,网络舆论呈现“倒流”趋势。
在传统媒体时代,网络上舆论形成的讨论载体主要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但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舆论形成的载体主要转变成了各大互联网客户端和自媒体平台,比较典型的是“两微一端”:微信、微博、手机客户端。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虽然仍参与其中,但其作用逐渐在下降,并且许多传统权威媒体都在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开通了自己的媒体号。在越来越多网络舆论形成的过程中,这些传统媒体反而要从许多普通网民处获得第一手信息,例如“乌鲁木齐5·22”暴恐事件最早的信息源就来自新浪微博,网民关注转发之后才迅速进入主流媒体的视野,得到更多网民的关注和众多门户网站的报道。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互动增强显著推动着网络舆情的演变和发展,网络舆论“倒流”至传统媒体的现象明显在增加。
(二)网络舆论形成的讨论载体逐渐多样化,新媒体平台的影响力逐步增强。
在传统媒体时代,网络舆论的走向往往受到传统权威媒体的议程设置影响。而新媒体时代,新闻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增强、互联网中的匿名性和交互性使得自媒体的发展迅猛。网络舆论形成的载体不再仅仅局限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微博、微信、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也逐渐成为形成网络舆论的主要载体。微博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官方媒体传,受众接收”的单向传播模式,社会网民在该平台上参与度高,且新媒体平台传播具有碎片化传播、方便快捷等特点,使得微博在网络舆论形成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大增加,成为形成网络舆论的主要阵地。
(三)“线上传播、线下实施;线上煽动、线下轰动”趋势明显。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网民对社会公共事件的网络舆论的参与度较之传统媒体时代大大增加,公众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可以方便快捷的参与到暴恐事件相关信息的转发和讨论中。并且,随着这种现象的高涨,社会公众渐渐不满足于在网络上直抒胸臆,许多暴恐事件的传播过程中都出现了“线上传播、线下实施;线上煽动、线下轰动”的现象。最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往往是负面的。例如“3·1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发生后,很多网民在网络上怒骂新疆人;网络上网民的负面情绪使得某些地方的个别公众对新疆人态度不友善,这样的现象很容易引发民族矛盾。
(四)网络审判与线下审判逐渐融合。
传统媒体时代,尽管暴恐事件会通过各大权威传统媒体向社会公众报道,也会形成一定的舆论,但具体对暴恐事件的最终审判是由线下官方部门完成的。新媒体时代,暴恐事件的网络舆情归根结底是社会公众针对暴恐事件态度、情绪和意见的总和,如今的网络舆情中甚至包含着社会公众的行为倾向。因此,在暴恐事件网络舆论的形成过程中,许多社会公众在网络上已经直接或间接的对暴恐事件进行了相关“审判”。并且这种审判在一定程度上对线下官方部门的审判是具有影响力的。但是,暴恐事件的网络舆论不一定都是利于社会公共安全的,某些情况下,公众的情绪受到某些别有用心的煽动,使得暴恐事件的网络舆情甚至“绑架”了线下官方部门,使得正常的社会工作受到负面影响。
四、诱发机制
暴恐事件发生后,舆论主体(社会网友、意见领袖、网络“大V”等)通过三种传播路径接收到关于暴恐事件的相关信息,然后整个舆论主体内部进行复杂的信息传播与反馈过程,最终大致形成网络舆论。舆论主体通过讨论形成网络舆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受到暴恐事件的敏感性、网络中的匿名性、互联网的交互性以及网民自身的不理智性等因素的影响,舆论可能进一步受到催化进行发酵,正常的针对暴恐事件的新闻报道可能引发不利于社会公共安全的舆论狂潮,掀起社会负面情绪,引发负面舆情的因素大致可分为三个。
(一)暴恐事件因素
暴恐事件本身具有强烈的危害性、刺激性和不确定性,事件中的受害对象、发生时间、发生地点甚至发生原因都和社会公众自身的安全密切相关,暴恐分子有意避开政府机关、机场等关键设施的严密防御范围,城市成为暴恐分子制造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2],还有的选择早市、火车站卖票口等尚未得到有效防御的人群密集场所发动袭击[3]。由于暴恐事件的突发性,社会公众极易受到暴恐事件的伤害或影响,其残忍性极易引发公众的恐惧、焦虑等情绪,加之暴恐事件的受害者是弱势群体的社会公众,这些原因叠加致使整个社会对暴恐事件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和关注。
(二)网民自身因素
公众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或灾难性事件时本身具有不理智性和恐慌性,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容易引起公众自身的主观猜测甚至臆想。新媒体环境下,暴恐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出现的信息源头常常是目击群众而非官方媒体,在普通网民发布信息到官方了解事件真相并作出回应、发布官方新闻信息这一段时间内,极易发生风险舆情的发酵,普通网民发布信息(信息很有可能不完整甚至片面),网络“大V”参与评论和转发,而官方尚未能做出回应,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公众极易产生恐慌心理,引起焦虑等负面情绪并通过互联网将这种负面情绪向周围无限扩散,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社会公众往往在获取暴恐事件相关信息后结合自己的理解和认知从而形成一种对暴恐事件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是自我的,是带有浓厚的个人主观情绪色彩的,大量的个人自我认识在网络上进行交流整合,形成了一种网络整体认识,这种网络整体认识非常容易因为缺乏理性而受到负面情绪的影响。
(三)网络媒体报道方式
网络媒体在互联网上的报道是社会公众获取新闻信息的一大途径,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信息传播的时效性大大提升,新闻信息发布的途径和方式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也更加的丰富多样。而且,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媒体分众化已经越来越明显,某些网络媒体的信息发布侧重点往往比较片面;加上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的“营销号”,这些营销号的目标通常是通过标新立异来吸引网民的注意力达到聚焦效果,因此在发布消息时因为自身的利益因素往往带有主观意识,发布的信息具有较强的煽动性和较低的真实性。这些网络媒体的综合因素常常会导致暴恐事件信息的传播变得碎片化,社会公众非常容易接收到碎片化信息甚至是虚假信息。
在以上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情况下,网络舆论在形成的过程中非常容易向着不利于社会公共安全的方向发展。例如在2016年12月28日的墨玉县暴恐事件发生后,库尔勒一网民在微信群中发布消息“12月28日墨玉县暴乱,库尔勒也出事了!”这一条讯息在短时间内被许多网民转发传播,引起了不少关注。但当天不久,库尔勒公安局网安民警在网上巡查时就发现了这一谣言并做出了澄清。虽然官方媒体进行了辟谣,但由于之前的不实消息在短时间内传播广泛,仍然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影响。
五、应对机制
从信息扩散机制的角度来看,暴恐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受到传播路径的影响;从碎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暴恐事件的网络舆情传播受到新媒体平台的影响。因此,应该抓住整个网络舆情的生命周期演进规律,建立暴恐事件网络舆情传播风险应对机制。
(一)加强有关暴恐事件敏感信息的互联网监控,将风险扼杀于萌芽(舆情风向恶化前)。
新媒体环境下暴恐事件网络舆情的风险效应至少要在舆论初步发展阶段甚至高涨形成阶段才能够体现出来,所以暴恐事件发生之后网络舆论的潜伏酝酿阶段是一个可以采取主动防范措施的绝佳时期。各种导致风险舆论出现的信息源头基本出现在这个阶段。因此,在这个阶段,官方政府可以建立一个专业高效的互联网监控机制,专门针对各种有关暴恐事件的敏感信息,发现敏感信息源头后,及时准确的进行处理,将风险扼杀于萌芽的状态之中。
(二)积极观察社会公众的心理、情绪变化,准确把握风险信息源的切入点及突破口(舆情风向恶化期)。
暴恐事件网络舆情出现风险效应,往往是因为网络空间中出现了不利于社会安全的煽动性言论。这个阶段部分社会网民已经受到了煽动性言论的影响,极其容易产生恐慌、焦虑等情绪,失去独立的理智思考能力,转向一种不理智的盲目从众状态。这种情况下,官方政府应该对社会公众的心理及情绪变化保持持续的关注和分析,同时应该结合之前的互联网监控机制,迅速准确的找到导致暴恐事件网络舆论出现风险的信息源,并对其进行详细的分析和准确的判断,及时针对风险信息源做出澄清和回应,以保证社会公众的负面情绪能够得到疏通或缓解。
(三)建立健全的发言机制,充分发挥新媒体平台的影响力,有效引导网络舆论(舆情有效疏导期)。
这个措施在暴恐事件发生至网络舆论完全衰减消退整个期间都适用。官方部门的权威信息往往是暴恐事件网络舆论(特别是风险舆论)高涨期社会公众的“定心剂”,这些权威信息基本代表着暴恐事件的事实、官方的态度和处理方式,能够使处于安全感薄弱状态的社会公众的负面情绪得到回应和疏解。因此,暴恐事件发生后,官方部门应该第一时间发布正确的权威消息,并转变以往“报喜不报忧”的错误观念,主动表示出负责且真挚坦诚的态度,这样才容易获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引导网民正确认识暴恐事件的实质。
同时,应该善于利用新媒体平台的影响力,不能只在传统媒体发言,新媒体环境下,新媒体平台能够更“广、准、快”地将新闻信息传播至广大社会网民。政府部门应该在各类新媒体平台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发言机制,在暴恐事件发生之后,及时线上线下同步发布权威信息。甚至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建立咨询、回复机制,在网络上与社会网民互动。此外,政府应该善于组织网络上的各种“大V”、其他网络媒体等在网络上具有影响力的意见领袖,争取组织各领域密切合作,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引导暴恐事件的网络舆论。
结语
本文以传播学中的信息扩散机制、碎片化传播理论作为视角,通过对“12·28墨玉县恐怖事件”等案例分析,提出了“单一型”、“单向型”、“多向型”三种新媒体环境下暴恐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路径;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暴恐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讨论了新媒体环境下暴恐事件网络舆情的传播及演进呈现出的特点;探索了应对新媒体环境下暴恐事件网络舆情的风险效应的措施,为预防、应对、处置、反思此类事件提供借鉴,规避其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