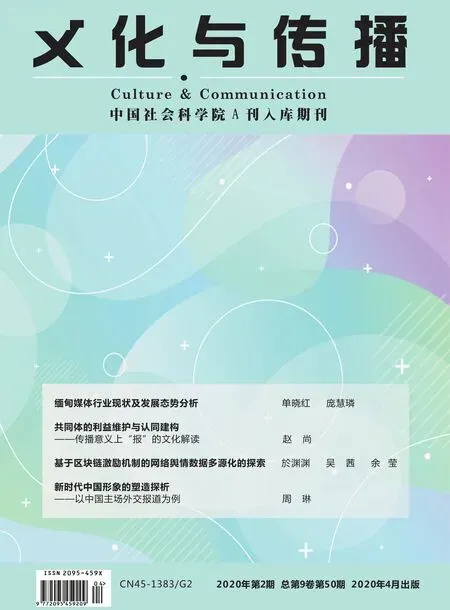共同体的利益维护与认同建构
——传播意义上“报”的文化解读
“报”是中国自古至今表示新闻传播非常重要的概念,比如进奏院状报、邸报、朝报、小报以及京报等,近代以后刊登新闻的纸质媒介叫报纸,专业媒介刊发新闻叫报道。那么,“报”字究意从何而来,又为什么叫“报”呢?这是一个事关中国古代报纸起源以及新闻传播活动规律性的问题。陈寅恪先生曾云:“凡解释一字即为一部文化史”,关于社会学、伦理学意义上的“报”,学界已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但关于传播学意义上“报”的研究还很少,为此,笔者不揣浅陋,置喙其中,以求教于方家。
一、汉代的“通奏报”之“报”:对等、回应意义上的“报”
根据王国维先生的观点,商代甲骨文中的“匚”等字即为“报”(该观点得到了学界比较一致的认同),其原义为“郊宗石室”[1],是商代的祭名之一,其意为对于神祖的报谢:“报,答也,酬也。”(《集韵·号韵》)“报,报德谓祭也。”(《国语韦氏解·卷四》)“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礼记·郊特牲》)例如:“贞,其匚于上甲家。”(《甲骨文合集》13581)意为商王等对于先王神上甲(保佑)的报谢。而在西周金文中才开始出现的、作为繁体的“報”,则表示报怨意义上的“报”:“報”的左半部分表示用来夹犯人双手的刑具,右半部分是用手捕人之形(即降服之“服”的前身),合起来的意思是“当罪人也。”(《说文解字》)如:“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报虐以威。”(《尚书·周书·吕刑》)“壬戌,大败宋师,以报其入郑也。”(《左传·隐公十一年》)
直至今天,报谢与报怨意义上的“报”,一直都是“报”非常常用的涵义与用法,而这也衍生出了传播意义上“报”的第一个涵义与用法——表示当事双方之间在信息层面上的回应。报谢与报怨意义上的“报”一般表示物质(或物质兼信息)层面上的回应,而我们这里讲的当事双方之间的回应,主要指信息层面上的,而且大多是非谢非怨、中性的,例如战国时期的《报燕王书》是乐毅对于燕王(派人责备自己)的一种回应,西汉的《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对于其友人任安来信的回信,“将已受命,拜而报君曰:‘臣闻国不可从外治……’”(《六韬·龙韬》)是将军对于君王(派遣自己出征)的一种回应。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这条史料:“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西汉会要·卷六十七》)这条史料曾经被不少人认为是汉代存在邸报的证明,但实际上这里的“报”,指的是朝廷对于臣下之“奏”的批复(回应的一种形式)。《唐六典》曰:
臣下章奏皆上书尚书,尚书上于天子。凡群臣上书通天子者,凡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章者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奏者上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有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校,送谒者台通者也;表者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以诣尚书通者也。公与校尉诸将不言姓,大夫以下皆言姓。报章曰闻,报奏曰可。其表文尚书报所上,云已奏……(《唐六典·卷八》)
从这段史料可以看出,汉代臣下上奏皇帝的公文,一般都需经过尚书这个环节,而朝廷(皇帝、尚书等)对于臣下的上奏进行批复,就被称作“报”:“报奏曰可。”(意为:批复臣下的上奏用“可行”)所以“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的意思就是:各个郡国在京师里都有邸,其作用就是为了让郡国长官或其派遣的使者在京城时临时居住,以向朝廷上奏言事,以及等待朝廷的批复;或是供郡国长官或其使者在等待皇帝上朝接见之前的住宿之用。
二、传报、禀报意义上的“报”:维护共同体利益的偏私性传播
除了对等、回应意义上的“报”以外,在春秋战国之际,还产生了主动传报、禀报意义上的“报”,这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出现了大变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各种利益群体的分化与组合,这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共同体,这在当时一般被称之为“党”。据刘泽华教授的分类,主要包括地缘性的党、血缘性的党、有一定隶属关系的党、政治性的党、利合志同相结的党以及结盟的党等[2]。这其中,除地缘性的乡党以及部分血缘性的党以外,大多数的党都以向外争取利益作为主要目标,也即是具有利益等方面的偏私(与“公正”相对)性:“吾闻事君者比而不党,夫周以举义,比也。举以其私,党也。”(《国语·晋语五》)“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朋党比周,以立其私。”(《管子·任法》)“治国无法,则民朋党而下比,饰巧以成其私。”(《管子·君臣上》)而“公”、“正”、“义”等则往往意味着对于偏私性“党”的否定:“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尚书·洪范》)“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誉民,不恤公道通义,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荀子·臣道》)“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荀子·强国》)“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公心不偏党也。”(《韩非子·解老》)“阿党不公。”(《吕氏春秋·审应》)“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韩非子·饰邪》)所以,这一时期被称之为“党”的共同体,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利益的偏私性。
春秋以前,正面、报德意义上的“报”,大多还具有对等性的特征,即“施”与“报”的分量在大体上是相当的,但到了春秋战国以后,随着君主专制政体的逐步建立,这种正面、报德意义上的“报”越来越具有了不对等性:“报机制的对应性法则只对等级内有效,是横向作用的;在纵向上,上对下即使做份内之事也是‘恩惠’,下对上则只有感恩戴德、以死相报。因为事实上巨大的不平等,报机制中封建的、迷信的异化内容也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的强大逐渐增多。”[3]也即是说,带有非平等、依附性的“报”越来越多,如“必行其私,信于朋友,不可为赏劝,不可为罚沮,人臣之私义也。”(《韩非子·饰邪》)“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韩非子·入奸》)“岩穴之徒皆私门之舍人。”(《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这些“必死之士”、“舍人”等恰恰是因受到主子的私恩,而反过来维护他们主子所代表的共同体利益的,这也被法家称之为“私义”:“民多私义”(《商君书·画策》),“破公家而成私门”(《战国策·魏策一》),“士为知己者死”(《战国策·赵策一》)。而带有依附性、向心力的“报”往往就是这种私义的表征:“死士,欲以死报恩者也。”(《战国策补释·卷六》)“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众人遇臣,臣故众人报之;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战国策·赵策一》)“国士报之”指的就是战国时豫让以死来报答礼遇自己的智伯的故事。从这一时期开始,不唯物质性的“报”,就连信息性的“报”,也同样具有了属于“私义”范畴的、维护以主子为代表的共同体利益的偏私性,如“渔父……招子贡子路,二人俱对……子贡还,报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圣人与!’乃下求之……”(《庄子·渔父》)“生间者,反报也。”(意为活的间谋,是赶回来报送信息的)(《孙子兵法·用间篇》)“公子(魏国的信陵君)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史记·魏公子列传》)
带有依附性、向心力的“报”是把外部信息传达到共同体内部的一种偏私性传播,但在中央集权的古代社会里,因自然经济长期占据主体地位,关于商品经济的信息不可能被持续不断地传递,而最有可能被持续传递的(持续传递是报纸出现的必要条件)是帝国官僚体系内部官吏们所关注的政治、军事信息。由于朝廷是每天都会更新的政治、军事信息的总汇,所以,只有当朝廷成为某个共同体的外部时,这种“报”才有可能会是持续的。在唐代的进奏院状报产生之前,把朝廷信息持续传播到某一共同体内部的情况实际上已经存在了,这种传播自然是偏私性的、为了共同体自身利益的,因此与君主代表的“公”的利益是相违背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对此已有论述:“朋党比周,以环主图私为务,是篡臣也。”(《荀子·臣道》)“大臣比周,蔽上为一,阴相善而阳相恶, 以示无私,相为耳目,以侯主隙,人主掩蔽, 无道得闻,有主名而无实。”(《韩非子·备内第十七》)所谓“环主图私”、“相为耳目,以候主隙”实际上就包括不断地把以君主为中心的朝廷信息传递到共同体(所谓“比周”)内部,这一常常被称之为“报”的过程。这里试举几例:
桀等因谋共杀光,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旦置驿书,往来相报。《汉书·燕剌王刘旦传》
这条史料说的是汉武帝时燕王旦意图谋反,与在朝廷中的上官桀等(彼此为利益共同体)互通信息(即“往来相报”),这其中就包括上官桀把朝廷信息传递给燕王旦。
时晋王在扬州,每令人密觇京师消息,遣张衡于路次往往置马坊,以畜牧为辞,实给私人也。《隋书·荣毗传》
隋朝时的晋王秘密地派人从京师往扬州传递朝廷消息,这里虽然没有使用“报”,但“实给私人也”与“报”的涵义一样,表征着信息传播的偏私化性质。
禄山……常令其将刘骆谷留京师诇朝廷指趣,动静皆报之。(《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
安史之乱之前、进奏院设立之前,安禄山就已经派将领常驻京师,打探朝廷的一举一动,然后传报给自己。
但总体来说,这种共同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偏私性传播,一般都因与朝廷所代表的“公”的利益相背,而被朝廷所禁止,如汉代统治者就认为“泄露省中及尚书事者,机事不密,则贼害成也。”(《汉书·卷一百》)为此还专门设有“探知秘事”、“探知尚书”等罪[4],此后的朝代也大都设有“泄露禁中语”等罪。虽然有像上面几例那样的秘密新闻信的情况,但因朝廷的禁令,这种新闻信的传播在空间上非常有限,在时间上也很难持续太久,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报纸在唐代安史之乱之前一直难以出现。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唐代中央政府统治力的下降等原因,各藩镇的进奏官可以明目张胆地向他们的藩帅进行偏私性的朝政新闻传播,这种新闻传播从载体上说是进奏院状,但由于其带有非常明显的维护藩镇这个共同体利益的偏私化性质,因而也被称之为进奏院报状、进奏院状报等,乃至于直接被称为“报”[5],这个“报”就表示维护共同体利益的偏私性传播。
三、宋代以后的官方邸报之“报”:帝国官僚体系共同体的认同建构
个体对于共同体具有依附性、向心力,共同体对于个体也同样具有凝聚力、粘合性,与此相关的新闻传播也叫做“报”,这种“报”在宋代的官方邸报之前虽然很少见,但也并非没有,比如:“义康左右爱念者,并听随从;资奉优厚,信赐相系,朝廷大事,皆报示之。”(《宋书·卷六十八》)讲的是南朝宋的大臣刘义康被从中央派到地方担任太守,朝廷对其的赏赐以及与其的书信不间断,且在信中把朝廷大事都通报给他,这种新闻信显然很接近于宋代以后的官方邸报,其目的也是为了维系他对于自己与朝廷之间这个共同体的认同。
宋代以后经过官方审定发布的邸报,与之前的唐代进奏院状报以及其他维护共同体利益的、偏私性传播的“报”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过滤掉了可能会使各个君主以外的共同体“环主图私”、“相为耳目,以侯主隙”的内容,比如宫廷内斗、朝廷党争以及对外战争失败等的消息:“进奏院逐旬发外州军报状……将灾异之事悉报天下……京东逆党未必不由此而起狂妄之谋……灾祥之事,不得辄以单状伪题亲识名衔以报天下。”(《宋会要辑稿·刑法二》)“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四十五》)而尽可能地使地方共同体的利益与中央政府的利益相一致,也即是努力达到“共赢”、“共享”的局面。“如果说,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信息;那么仪式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传播的仪式观认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传播往往与‘分享’、‘参与’、‘团体’以及‘拥有共同信仰’这一类词有关”,“反映了‘共性’、‘共有’、‘共享’与‘沟通’(即‘传播’)在古代有着同一性和共同的词根。”[6]在一定意义上,宋代官方邸报是以中央与地方“共有”、“共享”帝国政治性为主的新闻信息,建构“拥有共同信仰”的共同体认同为目的的。这个“共同信仰”概括起来,就是帝国官僚体系的整体、共同利益至上。皇帝的权威固然要维护——邸报中排在首位的皇帝诏旨与皇帝起居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庶几朝廷命令之出,天下通知。”(《宋会要辑稿·职官二》)但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当皇帝犯错而损害共同体利益时,皇帝甚至也要通过下“罪己诏”等途径来自我批评,如“前日忽传邸报,六月十四日陛下降罪己之诏,臣伏读流涕……”(《郧峰真隐漫录·卷八》)至于邸报中的官吏任免与刑罚,则更是从共同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而对于官员进行的调度、赏罚:“进奏院逐旬发外州军报状,盖朝廷之意欲以迁授降黜示赏功罚罪,勉励天下为吏者。”(《宋会要辑稿·刑法二》)所以,宋代以后的官方邸报之“报”,依然具有偏私性传播的涵义——相对于所有社会阶层来说,邸报所传播的主要是与帝国官僚系统内部官员利益相关的信息,而与普通百姓即“民”的利益最为密切的水灾、旱灾等灾难性、民生性信息,则较少能在邸报上传播:“将灾异之事悉报天下,奸人赃吏、游手凶徒喜有所闻,转相煽惑,遂生观望……”(《宋会要辑稿·刑法二》)这与宋代统治者“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的理念完全吻合。所以,宋代的邸报也被称之为“朝报”,就是因为它可以被看作由朝廷发出的、为了建构对于帝国官僚体系这个共同体认同的偏私性传播。
从邸报的实际传播效果来看,宋代大量的邸报诗等,大多反映了士大夫们对于帝国官僚体系内部事务、官员的认知以及情感、评价等,虽然也有与普通民众以及国家有关的内容,但大多是间接的、第二位的。首先是与皇帝及丞相等中央政府官员有关的,如郑獬《读邸报》:“天子朝坐朝明光,丞相叩头三拜章。乞还相印避贤路,愿为天子专城隍。上恩深厚未闻可,丞相退让闻四方。浓书大纸批圣语,鸣驺却入中书堂。”(《郧溪集·卷二十六》)陆佃《依韵和门下吕相公从驾视学》:“纁帛升龙日月章,平明鸾辂幸胶庠。侍臣独恨身千里,邸报空看字数行。故事一遵皇考庙,余波仍及武成王。谁知玉尺横经处,犹是当时旧讲堂。”(《陶山集·卷二》)士大夫读者们通过阅读邸报里的内容,对于皇帝及丞相(第二例中的吕相公指的是宰相吕大防)等充满了正向的情感与评价。其次是关于一般官员的,如“是日坐中观邸报,云迂叟已押入门下省。”(《苏文忠公全集·东坡续集卷二》)讲的是从邸报中得知朝廷人事变动;洪适《八月下旬观邸报二绝句其二》:“琴堂少值烹鲜手,壮县空遭沸鼑名。止火艳薪俱下口,风移全在长官清。”(《盘洲集·卷七》)是对于优秀官员的赞扬。再次是与帝国官僚体系整体利益(这一点与百姓、国家利益有重合之处)有关的事情,其中有为之喜的,主要是对外战争取得胜利的消息,如薛继轩《读邸报两首》:“大漠烟尘静……捷奏腾千里。”(《浪语集·卷五》)“邸报韩侯淮阳之捷,为之喜而不寐。”(《梁溪集·卷一百二十五》)也有为之忧的,如王迈《二月阅邸报》:“书生忧愤空头白,自有经纶社稷臣。”(《臞轩集·卷十四》)表达了对于贤臣的渴望。此外还有些反映了想融入帝国官僚体系这个共同体的一些士人的心声,如郭祥正《邸报》:“边塞疮痍后,朝廷气槩中。不才思献赋,天路恐难通。”(《青山集·卷二十》)
当然,由于现实以及人的思想的复杂性,邸报并不总是能在帝国官僚体系内部发挥正面的认同建构作用。士大夫们在阅读邸报时,有时也会对之作出霍尔所说的协商式乃至对抗式的解读,如“直史馆孙公冕……每得邸吏报状则纳怀中,不复省视。或诘其意,曰:‘某人贤而反沉下位,某人不才而骤居显官,见之令人不快耳。’”(《渑水燕谈录·卷第九》)但总体上讲,宋代及以后的官方邸报(明清的官方邸报与宋代的相比,并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帝国官僚体系内部的皇帝与士大夫知识分子之间,建构起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对于维护这个以皇帝为主导的共同体的整体利益,建构士人们对于这个共同体的认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近复关原旧,频看邸报新。”(《涉斋集·卷六》)“边事廷伸奏,朝除邸报驰。”(《阆风集·卷四》)说明士大夫读者无论身在何处,都有可能通过邸报来想象这个共同体。唐庚《读邸报》:“当今求多闻取士到蓬荜。时时得新语,谁谓山县僻?昨日拜御史,今日除谏官,立朝无负汉恩厚,论事不妨晁氏安。台省诸公登衮衮,闭门熟睡黄紬稳。”(《宋诗钞·卷四十六》)以及下面这条史料:“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团练副使之日,故团练使翟守素两曾夏州驻泊,守素与臣同看报状,见李继迁进奏事,因谓臣曰,此贼未是由衷,必恐终怀反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说明士大夫读者不仅能通过邸报来想象这个共同体,而且能为了这个共同体或喜或忧,甚至建言献策,表现出了对于共同体的认同感。
结语
对于共同体而言,表示偏私性传播的“报”,往往是利益维护与认同建构兼具,只不过有时会有所侧重:宋代之前的“报”,虽然大多偏重于共同体利益的维护,但把外部信息传报到共同体内部,也强化了“我们”与“他者”的区分,实际上也强化了对于共同体的认同;宋代以后的官方邸报之“报”,虽然偏重于共同体的认同建构,但建构共同体认同本身,就是对于共同体利益的维护——只有成员的认同度高,共同体才有凝聚力,才能取得更大的利益。
近代以后,为区别于中国本土原有的邸报、京报,纸质的新闻媒介一开始被称为“新闻纸”,但后来“报纸”却逐渐取代了“新闻纸”(中间有个“新报”称呼的过渡)而为世人所接受,个中原因,表面上看,是为了符合中国人一直以来把刊载新闻的纸质媒介叫做“报”(邸报、京报等)的习惯,而从深层次讲,笔者认为是人们出于对“报”固有的、服务于共同体利益维护与认同建构这个内涵的“集体无意识”。但凡新闻传播,都有所偏私,除去一些低俗化的媒介以外,大多都以维护本媒介所服务的共同体利益、建构对于该共同体的认同作为鹄的,比如分众化、贴近性、阶级性、新闻自由、新闻选择、新闻价值、新闻立场、报道框架、编辑方针等,都是新闻传播偏私性的不同表现形式,所谓纯客观、超阶级、超党派、绝对自由的新闻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理想而已。当然,根据福柯的权力理论,在许多情况下,所谓的共同体利益可能实际上主要是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但至少在共同体与外部之间还是存在着比较明显界限的。因为这种偏私,因为这种实际上或想象中的某一个共同体的利益,报纸等新闻媒体实际上体现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使得新闻媒体的所谓“公正”只是有限的、相对的,它可能更多地是在建构偏私性的内容:“媒介拥有设定议题的权力,毁坏议题的权力,影响和改变政治进程的权力;帮助的权力、告知的权力、欺骗的权力;打破政府与公民、国与国、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权力平衡的权力;被政府、市场,或者抵抗的受众/公民/消费者否决的权力……制造和保持意义的权力;劝说、认同和强化的权力;使削弱和使安心的权力……”[7]国外学者费希曼通过田野调查较为详尽地显示了,新闻的逻辑就是官僚机构的逻辑[8],这可以说从实证的角度证明了,但凡新闻传播,都具有“报”那样的偏私性特征。比如我们今天所说的“警报”往往是在维护某个共同体的利益,“公报”往往是在建构对某个真实或想象共同体的认同,而“警告”与“公告”则更多地具有法律意义上交涉等意味。正因为“报”与共同体的这种关联,所以直到今天,传播意义上“报”的生命力依然长盛不衰,即使纸媒当前在大批地关停,但“死的是纸,活的是报”,只要有共同体存在,就有偏私性传播意义上“报”的存在,因为人们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共同体,也同样需要维护共同体的利益,以及共享对于共同体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