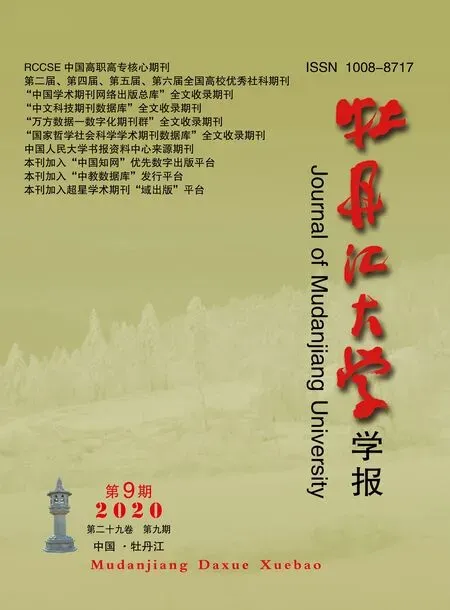从受害者到加害者
——电影《小丑》中“小丑”的创伤解读
代兆凤 王振平
(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222)
一、引言
《小丑》(Joker)是托德·菲利普斯(Todd Phillips)导演,杰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主演的DC犯罪剧情片,也是2019年最具热议的电影之一,自10月发行以来在多个电影节获得大奖。2020年2月10日,“小丑”的扮演者菲尼克斯更是凭借此电影获得第92届奥斯卡最佳男演员殊荣。电影以DC漫画公司的蝙蝠侠系列电影中经典反派“小丑”(The Joker)为主角,讲述了现实社会中一个演员小丑成为暴徒“小丑”的故事。电影叙事虚实结合,表现了主人公亚瑟(Arthur)如何在童年与现实的双重创伤下,尝试自我救赎失败,最终成为被称为“小丑”的社会暴乱分子——DC漫画英雄蝙蝠侠的头号对手。电影既有对人性和社会的探索,也有对暴力的思考。有人认为它鼓吹暴力和民粹,在为犯罪行为作道德辩护,也有人认为亚瑟是受害者,对他的遭遇表示同情。不同的观众反应使得电影更具争议性。导演究竟试图塑造一个怎样的角色?想表达怎样的情感?想进行怎样的道德或社会批判?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小丑”的历史,然后再从亚瑟的经历去看人生,看社会,看电影的主题。
二、符号化的“小丑”
超级反派“小丑”在《蝙蝠侠》(Batman)第1卷第1期(1940年6月)初次面世。漫画家杰瑞·罗宾逊(Jerry Robinson)创造了一个不断为蝙蝠侠制造麻烦的恶魔形象,滑稽可笑,取名“小丑”。初期的“小丑”是一个绿头发,白皮肤,涂口红,咧着嘴,身穿紫色衣服的怪人。1966年在蝙蝠侠连续剧《啼笑泪痕》(The Joker Is Wild)中,真人版“小丑”首次登场,这一版“小丑”更像是造型滑稽、只喜欢恶作剧的小丑。1989年电影《蝙蝠侠》中的“小丑”是一个被蝙蝠侠打入化学药池导致面部神经受损、永远咧着嘴的笑面人,一个更加现实的反派角色,电影的哥特风格将“小丑”的疯魔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愈加深入人心,为后继版本提供了模板。2008年,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The Dark Knight)演绎的“小丑”邪恶狡猾,行事癫狂,挑战秩序和人性,被称为最邪恶的“小丑”。在人们心目中,“小丑”就是一个制造混乱的恐怖分子,“在2008年,他是美国面临的9.11后恐怖主义威胁的强有力隐喻。”[1]不过有人并不把他看作国家的威胁,甚至在经济危机时期提倡“小丑”的无政府主义。此后的电影里,“小丑”成为具有独立象征意义的典型形象,不再依附于蝙蝠侠而存在。
在成为一个艺术形象后的60多年中,“小丑”早已超越了电影形象本身,成了一个特别文化符号,也早已形成了其特有的象征意义。该角色尤其受到无政府主义者、游戏玩家、男权主义者的追捧,他“让世界燃烧”的啸叫鼓舞着社交媒体上的狂热分子。“在这些越轨行为和他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总体倾向之间,‘小丑’已经符号化,成为许多感到与社会隔绝或对社会愤怒的人在互联网上的有力象征。”[1]“小丑”其实是尼采超人哲学(Overman Philosophy)的一个极端的体现,他不遵守社会固有的逻辑和秩序,相较于超人和蝙蝠侠等充满正能量的形象,他代表的是另一种力量,思维怪异,行事独立,在他的世界中,没有什么是无法实现和不可能完成的。如果说蝙蝠侠代表的是正义与秩序,那么“小丑”则象征着邪恶与混乱。
在电影《小丑》中,“小丑”的画风大变,他不再是一个纯粹的邪恶符号,尽管依然怪异,但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已经实实在在地落到了人的身上。亚瑟是一名靠扮演小丑勉强糊口的普通人,患有精神疾病,和母亲住在一起。他工作努力,幻想成为像大明星莫瑞一样的优秀脱口秀演员。但童年经历和现实遭遇却使他一步步走向歧路。在幻觉和现实的表现中,“小丑”不再神秘,不再迷人,他是孤儿,他受尽虐待,他没有高智商,他病态,他内心扭曲。这一角色能激发观众的情绪,正在于他不再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恶人,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一个可怜虫。
创伤是由创伤情景作用于创伤主体,经由条件过滤选择而形成的一种持久的痛苦反映。[2]207从创伤形成的深层原因看,“小丑”自我身份建构失败后走上暴徒之路,暴露的不仅仅是“人性之恶”,更有“人世之厄”,也由此说明,亚瑟从演员的小丑变为现实的“小丑”,言说的不只是个人身上发生的悲剧,更是当今社会的现实寓言。在冰冷的画面和沉重的情节中,“小丑”充满了对身处绝境的底层人物的同情和对韦恩集团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漠和和贫富分化的绝望。
三、创伤累累的“小丑”
创伤是“对于突如其来或灾难性事件所带来的一种无法回避的经历,其中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侵入的方式反复出现。”[3]11从表征看,创伤会破坏人类的意识和记忆机制,受害者的创伤经历多表现为以幻觉或潜意识等形式出现。亚瑟便是如此。在幻觉和现实的转换中,观众看到他在现实中屡受伤害,也能感受到他没有言说或无法言说的童年创伤。不管是现实中还是在童年时期,给他带来致命打击的创伤都不是来自身体,而是来自心灵。电影在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表现了亚瑟内心的苦痛。面容憔悴的亚瑟坐在梳妆台前,把双手放进嘴巴,扯出夸张狰狞的笑脸,眼泪交织着眼妆溢了出来。那是冷笑,也是苦笑,或者说,是笑也是哭。哭自己,不被认可,没有做人的尊严,笑自己,还在努力,希望有美好的未来。
(一)童年创伤
童年虐待,如暴力或情感疏离导致的创伤会使受害者的人格扭曲变形。[4]92由于创伤的无法言说性,很多在童年经历过创伤的人会出现记忆空白,“童年创伤经历所带来的不仅只是梦魇,它同时也给童年记忆带来了断裂,蒙上了薄雾,使得受创者成年后无法回溯、理解和记忆自己的童年,从而成为没有童年的人。”[5]53亚瑟就是没有童年回忆或没有童年的人。偷看母亲信件后,发现自己的父亲很可能是托马斯·韦恩——哥谭市最富有、有权力的男人。但精神疗养院的病历记录却披露了真相:他是被母亲领养的,母亲患有妄想症,并在男友虐待儿子时冷眼旁观。受过创伤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寻找能为他“提供特别照顾关系的权势人物”,并倾向于“理想化他所依附的人”。[4]104亚瑟时常遭受陌生人和同事的戏弄和排挤,唯一能使他感到宁静和放松的,就是看喜剧脱口秀。他对脱口秀表演的喜爱源自对喜剧脱口秀主持人莫瑞的崇拜,他渴望成为莫瑞那样的人。由于童年遭遇,他在潜意识中渴望父爱,莫瑞的形象弥补了父亲的空缺。童年作为人生起点,是世界观、人生观等形成的重要阶段,失去童年或童年记忆的破碎,意味着身份的断裂和方向的迷失。亚瑟所说“我这辈子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真实存在”正是他对自己毫无存在感的哭诉。
(二)现实遭遇
在《蝙蝠侠》里被扔进化学池的“小丑”是个想象中的童话人物,而电影《小丑》中的“小丑”却是现实的,更加具有社会批判性。几十年前,创造一个“小丑”需要把人推入化学池,而现在,只要把人推向社会,就可能创造出一个“小丑”。带着童年创伤阴影的亚瑟,曾经试图在现实中做一个愉悦他人的人。但是,无情的现实把他推向了暴力舞台,他从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
亚瑟创伤体验的加重来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影片一开始的广播显示,他所居住的城市正处在混乱的边缘,街道上涂鸦遍地,地铁上冷冷清清,一片萧条。出于自我保护,人们变得冷漠,过度冷漠导致相互排斥。在公交车上,亚瑟扮鬼脸逗小孩玩,却被当成骚扰者,想要解释却颠笑症发作,结果招致更多的反感与排斥。他对邻居苏菲充满爱情幻想,苏菲却对他不理不睬。被小混混戏弄殴打却无人相助,又遭同事陷害丢掉了工作。他在日记中写道:“患上精神疾病最糟糕的……莫过于人们想让你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也就是说,最让精神疾病患者痛苦的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不被理解,得不到温暖,被社会排斥。
三个调戏女性的金融精英在地铁被小丑杀害,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媒体对小丑大加鞭挞。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本来是一场血腥的谋杀,却受到了市民的拥护,杀人者反而被视为反抗社会的偶像。因为亚瑟杀人时是小丑的装扮,小丑这一形象遂成了反抗社会的象征,游行示威者都画上了小丑妆。还有,当抗议声此起彼伏,民怨沸腾时,大佬们却在欢快地欣赏着卓别林的《摩登时代》。《摩登时代》最显而易见的主题,就是对底层工人的同情,对资本家和工业社会的批判。现代化在带来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的异化,《摩登时代》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现象提出质疑和批判的电影。显然,在这样的情形下,让以亚瑟臆想中的父亲韦恩为代表的那些上等人看这样一部影片,作者的用意不言自明:人们所经历的,正是另一个摩登时代,只不过社会变化情形和人的变异方式有所不同。这样的场景既荒诞又讽刺,表达的却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那些上等人眼中,社会依然歌舞升平,生活依然美好快乐,他们看不到,也不想看到别人的悲苦,示威的市民不过是一群小丑在胡闹而已。
(三)自我救赎与创伤修复
根据创伤理论,人一旦遭受严重创伤,将无法完全摆脱内心的痛苦和扭曲,最终对世界缺乏客观或积极的认识而导致生活的失败和信念的瓦解[6]78。要想修复创伤,受创者首先要建立安全感,并尝试个人目标的实现。“建立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创伤复原的基础。”[7]57在童年与现实的双重创伤下,亚瑟试图寻找出口,修复创伤,但是,身处冷漠的社会,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何以建立安全感?在自我救赎之路上他不但寸步难行,而且渐行渐远,最终信念瓦解,不再相信自己,也不再相信他人,终于走上极端的暴力之路。
首先,面对无法言说的创伤,亚瑟曾尝试 “谈话治疗”,诉说痛苦与挣扎。但却被告知由于政府削减预算,心理咨询所将被迫关闭。“谈话治疗”是他倾诉的出口,走向积极生活的一条出路,最终这条路被不作为的政府封闭,他失去了倾诉内心苦恼与伤痛的正当出口。
然后,亚瑟尝试通过建立关系进行创伤复原。母亲本来是这个冰冷世界上唯一能带给他温暖的人,可他却最终获知,母亲所说不过是疯人疯话,不足为信。于是,他发现,不但自己现在不被认可,就连自己是谁,从哪里来都成了问题。与其说这一记重锤来自医院或母亲,不如说来自他自己,他没有成为他认为他应该是的那个人。这样的事实也让他从根本上否定了自己,使他对人生仅存的一点点星火,瞬间灰飞烟灭,终致彻底崩溃,亲手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他可以承受世间所有的冷漠和不公,谎言和排斥,但面对母亲编织的谎言,他再也无法忍受。母亲的谎言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终于明白,他一生都生活在谎言与虚妄中,没有快乐的童年,受尽虐待,幻想中的父亲也根本不存在。母亲对他的昵称是Happy,在这样的时刻,Happy这个称呼,对于他,对于观众,都成了一种讽刺。
自我创伤复原的结果,是彻底的疯癫和疯狂的复仇。亚瑟在弑母前说道:“我原以为我的人生是一出悲剧,但其实它是一出喜剧”。杀人给他带来复仇的快感,杀人成了他一生的高光时刻。母亲令他绝望,社会令他绝望,自己也令自己绝望,杀人成了让自己的悲剧人生变成一出小丑式荒诞喜剧的唯一路径。亚瑟幻想着冷漠的哥谭市会有人对他报以好感,比如邻居、同事、莫瑞等等。他幻想和女邻居相恋,幻想自己的脱口秀表演大获成功。但是,幻想中的光明并不是他走向美好人生的灯塔。现实中,他不但没有获得爱情,颠笑病发作也导致表演失败,最终因在地铁上遭遇无端殴打而开枪杀人,走上了暴力之路。影片中多次穿插的幻想镜头既表现出亚瑟也有美好的追求,也表现出他在现实中的无能为力。他有“角色自期”,却没有或无法“行为自律”。唯有在幻想中,他才可以摆脱束缚,自由追求自己的理想和表露真实的内心。可是,美好的幻想终归是虚幻的,他需要面对的是真真切切的身心创伤。所以,结束了母亲的生命,他就彻底斩断了和这个世界最紧密的联系,也不再对世界报以任何幻想和希望。这时,他心底的创伤已经转化为把他推向暴力“小丑”的恶魔。
成为像莫瑞一样的脱口秀主持人是亚瑟努力的方向,莫瑞是他走出创伤的动力源泉,可莫瑞在他滴血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当发现莫瑞对自己的脱口秀表演大加嘲讽后,他的美好形象崩塌了,亚瑟信仰的大厦也就此崩塌。被莫瑞请上节目后,他再也无所顾忌,对着直播的摄像机,尽情发泄自己的不满。最后,他枪杀了他的偶像,彻底放弃了信仰,放弃了世界。被警察逮捕的亚瑟在暴乱中遭遇车祸,从昏迷中醒来后,他在小丑们的欢呼声中站上车顶,用血迹在自己的脸上画了一张小丑脸。那个童年不幸,成年后也不被社会所容纳的亚瑟,已经在车祸中死了,车顶的亚瑟实现了浴火重生,他终于成就了自己,成了真正的“小丑”,成了小丑们崇拜的神。
就像他在笔记本上写下的那样,“我的死一定比我的生更有价值”。他终于以“小丑”的身份证明了自己的存在,以死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我们看到,卑微的小丑也可能变成杀人不眨眼的“小丑”。当小丑只能如亚瑟般诉诸暴力的时候,就是社会文明面临危机的时候。
四、结语
《小丑》讲诉了一个“摩登时代”的底层人物如何在童年与现实的双重创伤下挣扎,一步步从受害者成为迫害者,最后沦为反社会暴徒的经历。表面上看,是亚瑟制造了诸多社会混乱,但社会混乱的根源是社会本身,即使没有亚瑟,还会有某个汤姆或亨利出来制造混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贫富悬殊,固化了阶层,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看不到希望,只能成为卑微的小丑,甚至变异为邪恶的“小丑”。没有社会制度的根本改变,再多的蝙蝠侠也无济于事。“小丑”是暴力、贫穷、歧视等创伤孕育而成的怪胎,他有寻求复原的企望,他也需要社会的认可和帮助。一旦努力落空,创伤个体往往会走向极端,或自残,或残害社会。如何对待这样的创伤个体,是任何人和任何社会都需要严肃对待和认真解决的问题。这或许正是《小丑》带来的警示。对于主人公亚瑟而言,他的表演,是笑还是哭;他的大脑,是痴还是不痴;他的行为,是丑还是不丑;他的人生,是喜剧还是悲剧。这,也是电影给我们留下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