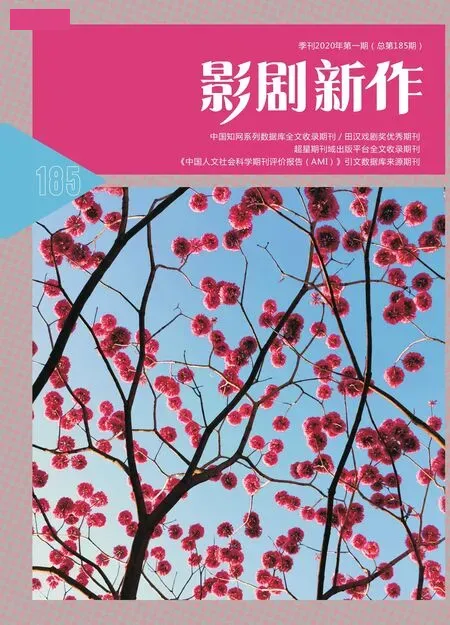戏剧冲突中的历史人物
——由话剧《望故乡》谈起
沈 梅
伟大的历史人物往往是由其所处的时代孕育出的。于右任先生出生于清末,时值新旧交替的巨大变革时期,作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在少年时代即显示了出众的才华和对国家、人民的深切关怀。从写诗抨击晚清政府到沪上办报宣传革命、为民疾呼,从统领靖国军、驰骋沙场到办校兴学、创立标准草书文化救国……于右任先生为国家、为人民矢志不渝,在文化、艺术、教育等诸多领域均有深厚造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1],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从戏剧创作的角度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写作题材:在风雨如磐的时代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突破重重阻力,上下求索,探寻救亡图存之路。马蹄先生的《望故乡》就是以于右任先生的一生为刻画对象的一部戏剧作品,通过五幕话剧,艺术地表现 了于右任先生忧国忧民的一生:从关中求学到沪上办报,从统领靖国军到任监察院院长,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于右任先生身居海岛、心系大陆,希望身后能在高山大树之巅,遥望故土……
通过剧本,我们不难发现,作者查阅并掌握了很多历史资料,深入了解了于右任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事迹、所立事功、所作诗文,并且对这些资料做了加工剪辑和艺术处理,不少场景之间的转换衔接以及诗词穿插都能看出作者的努力和匠心。不过,历史人物的戏剧创作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历史人物特别是知名历史人物,其事迹广为人知,形象深入人心,如果选材得当,立意深远,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另一方面,戏剧不是历史,戏剧人物不等同于历史人物,他(她)必须是满足戏剧创作要求的人物:剧作家要使这个人物的行动有明确动机,并且这些行动又推动戏剧冲突持续前进并最终达到高潮,最终完成作者的立意。如果这个人物只是在舞台上展现了他一生中的某些轨迹,而这些轨迹之间缺少内在有机的联系,体现不了深刻动机和作者立意,这个戏可能就会如七宝楼台,虽然不乏精彩的片段、机智的对话,但从整体上看,它至少不是一个完整自洽的整体。这里,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己对历史剧创作的一些理解,谈一下对《望故乡》一剧的看法,不当之处,还请马蹄先生见谅。
一、关于立意
一部好戏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立意(或曰主题,也有论者称之为前提),历史剧创作也是如此。著名剧作家郭启宏先生在谈及自己的历史剧创作就曾说:“历史剧贵在立意”[2](P94)。立意的获得是不断思索感悟的结果,剧作家往往会花上数月甚至更长时间去处理一个题材,寻求独特深刻的立意,从而指引创作达到更加理想的目标。“虽然你不应在你剧本中的对话里提到你的前提,但你必须让观众心领神会。不管它是什么,你必须证明它。”[3](P6)缺少清晰明确的立意,任何想法和情境都不足以将写作带向一个逻辑上的结论;没有清晰且有效的立意,剧中的人物往往会缺少深刻的动机,显得虚弱而飘浮——彷佛在一个又一个事件里,他们只是被动应对,不知自己何以如此。
在《望故乡》中,作者塑造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于右任,从晚清到民国,他对时局的不满以及自己救亡图存的努力从未停止。这样一个于右任,展现了作为历史人物的他的大部分事迹,其中不乏生动精彩之处。但笔者觉得剧本的立意还可以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于右任的事迹既是他个人的,也是属于那个特定时代的,做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他不断尝试救国之道,但最终并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在沧海横流的时代中,这样的人不止一个,为什么会这样?是个人原因还是历史原因?历史上,像于右任这样上下求索的仁人志士代不乏人,屈原、陆游、辛弃疾、文天祥……属于“这一个”的于右任,有什么属于自己的独特性?……如果沿着这种思路追问,也许剧本的立意和人物的深度会有所加强。《望故乡》中,由于立意不够清晰明确,主人公于右任的目标虽然是共知的,但缺少作为个体独特而深刻的动机,导致事件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凑自然,各场次之间缺少一种不断递进、逐步加强的节奏感。
郭启宏先生在谈历史剧创作时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坚持主观的“道”与应对客观的“势”的冲突里,大致有四种选择:殉道抗势、泯道媚势、存道避势和徘徊于道势之间。“进不能,退不甘”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思想,又是一种意象,还是一种象征,可以任由作家的生花妙笔,做出艺术的表述。[2](P94-95)这些可能都会给创作历史剧的编剧以启示。
另外,剧名《望故乡》,顾名思义,是身处异地的于右任难忘故土,心系祖国和家乡,但五幕剧中,表现这一意思的篇幅并不多:除第五幕外,只有第二幕的结尾部分,于右任惊闻父亲病危却不能返回陕西这一处,其它地方虽偶有提及,但未见着力,所以通篇看来,剧名与剧本表现内容有一定出入。
二、关于人物
每个人都有三个维度:生理、社会、心理。缺少这三个维度, 我们就不能对一个人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同理,塑造一个戏剧人物,仅表现他是清高孤傲还是随波逐流、是忧国忧民还是独善其身也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写出他(她)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清楚什么造就了他,其性格持续变化的原因,以及无论他愿意与否、其性格变化的必然原因。例如哈姆莱特,我们不仅知道他的年龄、外貌、健康状况,还能推出他的脾气。他生活的背景和时代也赋予他行动的动力。我们知道过去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其身处的社会环境、他父母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对他的影响。我们了解他的心理,并能清晰地看出它是如何发端于他的生理和社会特征的。总之,一个人物是他生理特征和环境加诸于他的影响总和,缺少必要的维度,这个人物就不够鲜明立体。
如果不能有一个清晰连贯且不断深入的动机,人物的行动就缺少关联性。在《望故乡》中,少年时期的于右任即对晚清统治极其不满,他写诗言志、希望自造前程,逃亡上海的他先后创办几份报纸,呼吁革命,随后又在关中统领靖国军,对抗各省军阀……事迹不可谓不多,功绩不可谓不伟。但这些事件的内在联系是什么?最初触动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写诗、办报、统军、慰劳后方军民的个人动机又是什么?他不满腐败的晚清政府、军阀割据的时局和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那他理想的国家是怎样的?他希望民众过上怎样的生活?他为什么要宴请陈军长?他留胡子的原因是什么?……在遭遇重重危机和多次变故之后,于右任的动机有何变化?是不断强化、愈挫愈勇还是让他感时伤世、莫可奈何?……在第二幕中,加入同盟会的于右任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应该是他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但这一目标不够具体和个人化,在剧中也缺少足够的呼应。在第三幕里于右任做了靖国军总司令,他这样做的动机和目的又是什么?在胡景翼传达冯玉祥收编靖国军的意图之后,于右任的拒绝体现了个人气节,这样做还显得不够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拒绝理由必须是站在民族利益的前提下的。
生活在变动,每个人都处于永恒的波动、变化状态之中,没有人能在经历过一个影响其生活方式的冲突之后仍保持原样,他(她)会从一个心理状态走向另一个,并被迫去转变、去成长、去发展。哈姆莱特在戏剧的开始和结尾判若两人。事实上,他几乎在每页纸里都有变化。他的变化合乎逻辑,沿着一条稳定的发展线路前进。同样,我们每一个人,也在不同阶段、不同事件里不断变化,关键在于,编剧要找一个对人物的处理最为有利的时刻。在内忧外患的情境里,于右任由写诗到办报再到统军,他的行动变化巨大,他的情感和内心有着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又怎样推动他的行动,去实现新的变化?这些可能也是作者在叙述事件的同时,需要注意的。
另外,剧中次要人物的行动应服从主要人物,他们一起推动矛盾发生、发展直至高潮,剧中楞女作为于右任的女儿,戏份不少,她给父亲量胡子、端午节与父亲对话等场景的设置,体现了于右任生活的另一方面,也活跃了舞台气氛。但总体感觉,这条线与于右任的行动结合得还不够充分,有些时候有偏离之感。此外如高仲林、邵力子、王陆一等人物,也可以适当地“删头绪”、“密针线”[4],从而更好地衬托主要人物,凸显主题。
三、关于冲突
没有冲突便没有戏剧。剧作家不仅需要让人物愿意为其信念而斗争,而且需要让他具有足够的能力和毅力将其斗争进行到底,直达逻辑的结论。冲突以矛盾为基础,包含势均力敌的两股力量。对手力量的强弱,不仅会直接影响主人公的性格塑造,而且会直接左右戏剧冲突的张力,并且影响剧本立意的阐发。没有对手,不足以见主要人物的力量,孱弱的对手也不足展示人物的强大,只有旗鼓相当的两股力量不断交锋,才能展现戏剧张力,实现戏剧冲突。
在《望故乡》中,阻碍于右任实现目标的阻力是什么?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贪腐滋生、内斗频出的国民党政府?人和环境的冲突固然可以,不过在《望故乡》的一、二两幕,作者将这个对手设置成代表晚清政府的陕甘总督升允,他缉拿于右任,并在拉拢不成后又设计陷害。但这二人的冲突还不够紧凑、尖锐,并且未能支撑全剧。在第三、四、五幕中,均没有一个与于右任形成对手的人物,如果说这个对手是其他军阀和国民党高层中的某些力量,它们也没有对于右任的行动构成一种如影随形、步步紧逼的压迫。所以整体上感觉于右任缺少一个强大的对手,整个戏缺少一个逻辑高潮——在这个高潮里,对立双方的矛盾得到升级并最终爆发,作为主要人物的于右任在感情和心理上也能有质的变化与升华。
总之,一部历史题材的话剧,不可能仅以“再现历史”为终极目的,剧作家“要进入人们的脑中,要站在他们曾经站立的地方并看到他们曾经看到的世界,要对他们的动机和意向做出合理的估量——而这恰恰是已有记载和将有记载的历史所不能企及的。即使当所有外在的实据已被掌握,进入角色们头脑之中的唯一途径仍然是想像。这确实属于戏剧的本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