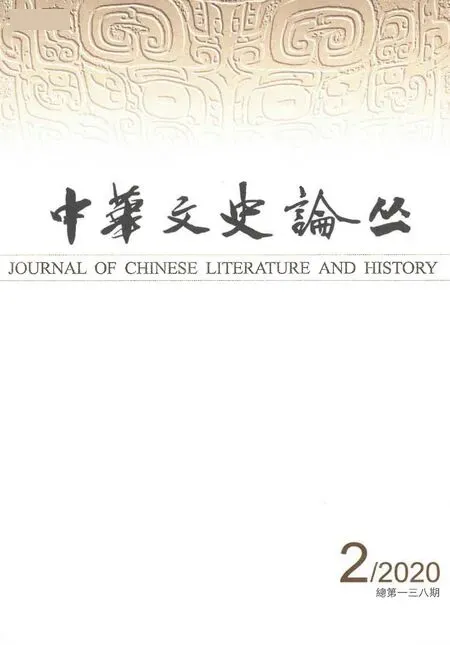何處是洞庭:《洞庭靈姻傳》的小説史語境及道教洞天觀念
李小龍
提要: 《洞庭靈姻傳》的故事發生於洞庭,然此“洞庭”究屬何地卻頗有參差。正文既云“湘濱”“生於楚”,當屬楚地;又云“聞君將還吴”,則又屬吴。這一矛盾僅通過校勘無法解决,因爲有些衝突並非來自字詞,而來自故事構架。事實上,這種矛盾當與古人地理觀念有關,即認爲此二處本即相通,這在傳文中亦多有體現。將此傳放入《梁四公記·震澤洞》《靈應傳》等小説史語境之中會發現,這種模式在小説史世界裏也已秘響旁通。若進一步切入其文化語境,可知這些小説的洞天想象與互通設定均來自道教的洞天觀念。
關鍵詞: 洞庭靈姻傳 柳毅 洞庭 太湖 梁四公記 道教 洞天
《柳毅傳》是唐傳奇中膾炙人口的篇目,此傳原名當作《洞庭靈姻傳》。(1)參見李小龍《〈柳毅傳〉原名考》,《文史知識》2019年第5期,頁68—72。“洞庭”是這一傳奇故事發生的背景,同時也爲故事附着了神奇色彩,因此作者特意將此揭於標題之中。然細繹文本會發現,這個關鍵的地點在作品中有着貌似不可調和的地理錯位。北宋范致明在其《岳陽風土記》中便指出了這個問題,他説:“君山崇勝寺,舊楚興寺也。有井曰‘柳毅井’。按: 《靈姻傳》始言‘還湘濱’,中言‘將歸吴國’,固無定處。”不過他的解答卻是“前人因事闕文,後人遂以爲實,此亦好事者之過也”。(2)范致明《岳陽風土記》,《全宋筆記》(2編7),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年,頁84。我們自然也可以與范致明一樣,用敍事作品隨意虚構而不甚嚴謹的技術性原因來規避這一矛盾,但這種解釋卻忽略了作品形成地理錯位更複雜的深層邏輯,錯失了更爲豐富的解讀可能。
一 “湘濱”洞庭
言及洞庭,大多數人會自然而然地認爲是湖南的洞庭湖,作品對此也有支持。傳文開篇即云柳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3)陳翰編,李小龍校證《異聞集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9年,頁85。以下引用《洞庭靈姻傳》文字皆據此,不另注。有“湘”字,自然指其欲歸湖南。此後柳毅在向洞庭君自我介紹時也説“毅,大王之鄉人也。長於楚,游學於秦”,他是洞庭君的同鄉,又説“長於楚”,則爲楚地洞庭已然無疑,似乎不必再論。
不過,這兩處清楚明白的證據也會遭遇挑戰。龍女在托付柳毅時説“聞君將還吴”,又清清楚楚地説柳毅要回的是吴地,這與前引“將還湘濱”及“長於楚”是矛盾的。面對這一參差,研究者只好盡力彌補。張友鶴先生《唐宋傳奇選》注云:“吴: 通常是指現在江蘇一帶地方,這裏卻指湖南。三國時吴國的疆界包括湖南在内,所以湖南也可以稱做‘吴’。”(4)張友鶴選注《唐宋傳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頁40。周紹良先生《唐傳奇箋證》也持同樣的意見。(5)周紹良《唐傳奇箋證》,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頁140。不過這一解釋容或牽强,因爲三國時的吴地包括湖南,並非“行政區劃”,而是割據疆界,後人除非有特殊政治態度,否則全無遵依之可能。李時人先生注本即云:“江南一帶本春秋時吴國故地……湘濱、洞庭湖均應爲春秋時楚地……未詳此處何以言‘將還吴’。”(6)李時人、曾志松評注《唐人小説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19—120。也有學者説“吴: 本指江蘇一帶,此處借指南方”,(7)《古代小説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年,頁328。仍屬暗换概念。這兩種解釋思路均盡力證明吴同於楚,以便使傳文不致矛盾,然李復言《定婚店》云:“雖仇敵之家,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吴楚異鄉,此繩一系,終不可逭。”(8)李復言撰,程毅中點校《續玄怪録》,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87。可見古人多將“吴楚”理解爲異域,則於此用力,或恐徒勞。
欲爲楚地洞庭提供支持,若不考慮複雜因素,僅從校勘層面討論反倒更易解决: 《類説》所收節本此處作“聞君將還,托寄尺書”,(9)曾慥輯《類説》,《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62),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頁470。而《醉翁談録》所收《柳毅傳書遇洞庭水仙女》作“聞君還鄉,甚近洞庭”,(10)羅燁《醉翁談録》,《續修四庫全書》(126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443。均將原來引起矛盾之“吴”字規避了。李劍國先生《唐五代傳奇集》便將此句校訂爲“聞君將還鄉”,並校云:“原作‘將還吴’,與開頭‘將還湘濱’及下文‘長於楚’抵牾。《類説》、南宋皇都風月主人《緑窗新話》卷上《柳毅娶洞庭龍女》……作‘聞君將還’,《醉翁談録》作‘聞君還鄉’,今據《醉翁談録》改‘吴’爲‘鄉’。”(11)李劍國輯校《唐五代傳奇集》,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649,659。但這一校勘也不能定讞,因《類説》尤其是《醉翁談録》的句式與原文並不盡相同,則其無“吴”字究屬將原文删節所至還是原本如此,尚有討論空間,據之校改的邏輯認定在於後者,但我們無法排除前者。
事實上,“吴”字雖與“將還湘濱”抵牾,但也有資料似可證明錯誤的是“湘”而非“吴”。蒲松齡《聊齋志異》有《織成》一篇,其中引用此傳故實云“洞庭得遇龍女而仙”,清人吕湛恩注節引此傳内容,開端即云“柳毅下第,將還於湖濱”,(12)蒲松齡著,任篤行輯校《全校會注輯評聊齋志異》(修訂本),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頁2088。因其後未引柳毅之自我介紹,故此處將“湘濱”改爲“湖濱”,即抹去湖南洞庭的唯一線索,也抹去其所引證之《柳毅傳》情節參差之處。當然,這一資料也同樣不可靠,至少,這一改動與蒲氏原文扞格: 蒲氏文中稱柳生爲“襄陽名士”,其後又云其“至武昌”而得娶織成,都在兩湖之地,知蒲氏之認定與吕氏不同。
傳文中有一易爲人忽略之細節,似可證明柳毅確實是“還吴”,而他所去之洞庭卻在楚地。柳毅初見洞庭君時,洞庭君客套寒暄云“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遠千里,將有爲乎”,若柳毅“還吴”,洞庭君亦在太湖,“不遠千里”四字則全不合情理。此種敍述透露出來的邏輯信息一般來説是校勘問題無法解决的,只能放在故事敍述的脈絡中去解釋。也就是説,從洞庭君的話中可以看出,作者在敍述框架的設定中,柳毅從所還之處至此龍宫需歷“千里”之遥。
李劍國先生《唐五代志怪傳奇敍録》也認爲此當即楚之洞庭,不過,其理由中有“傳文稱‘洞庭含納大直’,含納百川唯湘岳之洞庭湖才可當之”的意思,(13)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敍録》(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304。這或可商榷: 一是古稱震澤之太湖(參下文),是否亦可稱爲“含納大直”;二是這四個字主要形容洞庭君,指其有涵養,這一點通過傳文亦可感知,雖然不無影射洞庭之意,但主要還當在人物形象上去解釋。
二 “吴”之洞庭
以上所述,似乎大多數觀點都認爲“洞庭”即楚之洞庭。實亦未必,因爲傳文中還存在着大量反證。
傳文述柳毅因“念鄉人有客於涇陽者,遂往告别”,而龍女又“嫁涇川次子”,則二人相遇之處當在涇陽附近無疑。龍女將書信交給柳毅後“東望愁泣,若不自勝”,其所望必爲家鄉。涇陽地處北緯34度、東經108度左右;湖南洞庭湖約爲北緯27至29度之間,東經111至113度之間: 二地經度相近,緯度差别較大,則若其所望爲楚之洞庭,當作“南望”爲是。吴地太湖北緯約30至32度之間,東經119至120度之間,其緯度與涇陽相差不如前者之甚,則云“東望”較合。可見,其“東望”的其實應是也被稱爲洞庭的吴地太湖。
太湖被稱爲“洞庭”由來已久。《文選》録左思《吴都賦》云:“指包山而爲期,集洞庭而淹留。”劉逵注引王逸云:“太湖在秣陵東,湖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謂洞庭。”(14)蕭統編,李善注《文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230。與《洞庭靈姻傳》大抵同時而稍後的《古岳瀆經》中又有“公佐訪古東吴,從太守元公錫泛洞庭,登包山”的文字,可知當時人將太湖稱爲洞庭亦爲常例。
而且,不只當時人習慣將太湖稱爲洞庭,後人似乎也有類似的看法。如蘇軾《洞庭春色賦》,其題有“洞庭”,文中卻云“卷震澤而與俱還”、“鼓包山之桂棹”、“追范蠡於渺茫,吊夫差之惸鰥。屬此觴於西子,洗亡國之愁顔”,不但提及范蠡、西子,而且有“震澤”、“包山”,這都表明其所詠之洞庭爲太湖無疑。另外,賦中還有“携佳人而往游,勒霧鬢與風鬟”之句,(15)《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1。“霧鬢風鬟”即用《洞庭靈姻傳》之典,知蘇軾所寫此之“洞庭”非但爲太湖,而且恰用柳毅所往之洞庭比之。
作品中也有一些隱蔽的内證,如傳文中提及的“橘”。范成大《吴郡志》卷九云:“柳毅井,在洞庭東山道側。按: 小説載柳毅傳書事,或以謂是岳之洞庭湖。以其説有橘社,故議者又以爲即此洞庭山。”(16)范成大《吴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16。看來,范成大也認爲,“橘社”是一個關鍵證據。當然,湘之洞庭亦産橘,《山海經·中山經》曾載:“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蘪蕪、芍藥、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17)郝懿行《山海經箋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184—186。然唐代言“洞庭橘”者,卻多指太湖。如與本傳作者李朝威大抵同時的白居易,其《輕肥》云“果擘洞庭橘,膾切天池鱗”、《有木詩》云“謂爲洞庭橘,美人自移植”、《揀貢橘書情》云“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18)謝思煒《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74,251,1894。所指均爲太湖之橘;晚唐康駢《劇談録》卷上有《潘將軍失珠》條(《太平廣記》卷一九六亦録)云“吴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19)康駢《劇談録》,《唐五代筆記小説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1464。亦甚清楚。
其實,作品的故事建構中,還隱含了一些無法迴避的邏輯證據。張偉然先生《柳毅傳書之“洞庭”考》即提出: 洞庭君之弟爲錢塘君,錢塘與湖南的洞庭地域懸隔;柳毅得財寶後“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後又“徙家金陵”娶龍女,而後“相與歸洞庭”,這些地方都距太湖較近;最關鍵的是開元末年柳毅表弟薛嘏“爲京畿令,謫官東南,經洞庭”,“由京師到‘東南’是不必經過”湖南洞庭的。(20)張偉然《柳毅傳書之“洞庭”考》,《中國地名》1998年第5期,頁10。這些證據雖然都不是確證——因爲還都有模糊的空間,不過,若不吹毛求疵的話,應該承認,每一項都有一定程度的説服力,更何況這幾處證據一起出現,有一些還可互爲援證,如此云“謫官東南”,前則云“東望愁泣”,自然不可能都是作者筆誤。
此外,我們還可以補充一個比較有趣的證據,傳文中多次提及洞庭君之龍宫中有“靈虚殿”,并言及“坐於靈虚之下”、“辰發靈虚”,此殿之設,當從古道書《靈寶略紀》而來,其書有云“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21)張君房《雲笈七籤》,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40。此書也是道教洞天觀念的關鍵文獻,與《洞庭靈姻傳》關係密切(參下文),入靈墟(靈虚)須上包山,雖然此處之“靈墟”或虚指,然二者有密切之關係則亦是事實,其屬吴地亦當無疑。再加上前文提及橘社意象的安排及“東望愁泣”的表述,可知其共同指向就是吴地太湖。
三 “密通”洞庭
分析至此,似乎矛盾無法調和。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解釋: 作者或許正因吴、楚二地皆有洞庭之稱,從而故意在作品中將其並置。元人尚仲賢在其雜劇《柳毅傳書》中之設定似即如此: 柳毅自稱“淮陰人氏”,則當隸於吴;但寫龍女則云“儂家鸚鵡洲邊住”,柳毅一聽便知“你家在洞庭湖水中”,(22)寧希元、寧恢選注《中國古代戲劇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頁502,498。又表明洞庭湖在湖南。也就是説,尚仲賢很可能把握住了此類故事以洞庭之名聯結吴地太湖與楚地洞庭湖的關目。
這一推測應該是符合《洞庭靈姻傳》作者原意的,關鍵在於傳文中“密通洞庭”四字。“密通”一詞《漢語大詞典》收録,釋云“猶近達”,(23)《漢語大詞典》第三卷,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9年,頁1536。所舉語例即此傳之文。然此釋實誤,遍稽文獻,“密通”二字用例甚多,如《宋書》云“乃密通音譯,潛送器杖”,(24)《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2124。《魏書》云“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泄”,(25)《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533。《南齊書》云“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驛,密通彼此”,(26)《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年,頁488。《梁書》云“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27)《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641。均爲暗中相通之義。此以“近達”爲釋,不過是望文生義罷了。此後學者頗受影響,如周先慎先生即釋此“密”字爲“近”。(28)《古代小説鑑賞辭典》,頁328。李劍國先生或許同意“近達”之義,然亦知以“密”爲“近”之不妥,遂據《四庫全書》本《太平廣記》將“通”字校改爲“邇”,(29)《唐五代傳奇集》,頁659—660。這樣,“近”的意義即由“邇”字承擔。但這仍可商榷,從文字角度看,“邇,近也。柳毅歸湘濱,與洞庭湖相近也”,然若云“近”,爲何前有“密”字,實不能通。若要解决這一細微的校勘問題,需要瞭解古人有關洞庭的地理觀念。
《山海經·海内東經》“入洞庭下”一句郭璞注云:“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吴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爲‘地脈’。”(30)《山海經箋疏》,頁253。郭注當有來歷,因早於郭氏的周處在《風土記》中便有類似的説法(31)虞世南輯《北堂書鈔》,《續修四庫全書》(121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30。;郭璞《江賦》又云:“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潛逵傍通,幽岫窈窕。”(32)聶恩彦《郭弘農集校注》,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7。亦可相證;張華《博物志》卷八又云:“君山有道,與吴包山潛通。”(33)張華撰,范寧《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97。可見在中國古人的地理想象中,洞庭湖是地穴,太湖與之有地脈相通。《洞庭靈姻傳》的作者顯然非常清楚這種關係,作品中龍女在説“聞君將還吴”之後,緊接着便説“密通洞庭”,這裏的“通”字與前引《山海經》、《江賦》、《博物志》所用之字同——不但如此,這三種文獻還不約而同用了“潛”字,此之“潛”,即“密”字,“潛通”即“密通”也。郭璞《江賦》所云“潛逵傍通”,其“逵”字據郭氏在《山海經》中的注説是“水中之穴道交通者”,(34)《山海經箋疏》,頁150。與此傳“密通洞庭”可以互證。由此可知“密通”爲此傳原文,可以理解爲龍女知道柳毅要回吴地,但她的意思是説吴之包山與楚之洞庭有密道相通,可用通過此密道來送信。
若如此理解,再回到原文,發現只需要改一個字,全文就文通義順了,即如吕湛恩所引,將“湘”改爲“湖”。柳毅雖爲楚人,然其所居之地爲吴地,故前云“將還湖濱”,龍女亦知其將歸吴地。但是,洞庭君卻在楚地,只是柳毅可從太湖之密道直通楚地而已。所以,柳毅見洞庭君之神奇不只是凡人入水,而是瞬息千里——“瞬息”一詞傳文亦可相證,即武夫出迎柳毅,讓他閉目後云“數息可達”,根據下文洞庭君的寒暄我們知道,這個“數息”當行過了“千里”;而“千里”雖爲約數,但揆其實,由太湖至洞庭湖現在測量約八百餘公里,合唐制一千五百里左右,亦相仿佛。然後柳毅自稱爲“大王之鄉人”及“長於楚”也就了無參差。此外,錢塘雖爲洞庭君之弟,但其“昔爲錢塘長,今則致政矣”、“縻繫於此”,知其已不在錢塘任職,且被上帝軟禁於洞庭——這一點看後文寫其“項掣金鎖,鎖牽玉柱”以及柳毅“斷金鎖,掣玉柱”的形容便可知道;更重要的是,作品特意强調了“故錢塘之人,日日候焉”,這當然是爲了與錢塘潮的特色建立聯繫,但也未嘗不是告訴讀者,錢塘君已遠離錢塘了。如此一來,文中圍繞柳毅之事多在吴中亦合於情理。吕湛恩注引異文雖然很可能並無版本依據——吕氏注成書於道光五年(1825),得睹秘本的可能不大——但這個異文還是值得注意,因爲“湖”與“湘”字形相近,頗易混淆;加之後世傳抄、刻印者並不了解作者“雙洞庭”並置的複雜設定,確實容易將原本之“湖濱”誤爲“湘濱”。事實上,“湘濱”一詞頗爲奇怪,若想指柳毅欲回楚之洞庭,有很多更合理的表述可供選擇,如“江濱”、“洞庭之濱”以及“湖濱”,這裏卻選用“湘濱”這一古代文獻用例甚少的詞,至少是頗啓人疑竇的。加上“湖”、“湘”二字字形相近,不排除抄寫者因後文“生於楚”的表述而將此字改動之可能,因此,或可用理校之法將此字改回。
四 震澤洞庭——小説史語境的旁通
其實,《洞庭靈姻傳》不只是在自己的文本世界中設定了兩處洞庭的“密通”,當我們把目光投向小説史,會發現它的設定已經逸出自己的疆界,與前後的其他小説文本建立了秘響旁通的互文關係。
初唐張説有傳奇《梁四公記》一篇,其中一部分曾被《太平廣記》擇出,以《震澤洞》爲名,收入卷四一八“龍一”中。在其文中杰公説“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後,梁武帝欲遣使者通信,於是募得羅子春兄弟“入洞穴,至龍宫”,見到龍女並獲寶珠。(35)《唐五代傳奇集》,頁271—272。下引《震澤洞》文皆出於此。這一情節構架與《洞庭靈姻傳》頗爲相似,所以《太平廣記》在卷四一八選録《震澤洞》入“龍一”之後,在次卷便選入了《柳毅》一篇入“龍二”,而後世稗編更多將二者並列,如《唐人百家小説》便爲其取了與《洞庭靈姻傳》相類的名字《龍女傳》,並將二傳前後並置。(36)《唐人百家小説》,日本公文書館藏明刊本,第一一三、一一四帙。據此來看,李朝威在作此傳時,很可能受到《梁四公記·震澤洞》的影響。在這種背景下,我們再來看兩部作品有關洞庭的設定,《震澤洞》云:“震澤中,洞庭山南有洞穴,深百餘尺……(杰公)曰:‘此洞穴有四枝: 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岸。’”此云“震澤”,即爲太湖,其“洞庭山南”之洞穴所通“蜀道”、“羅浮”均遠在千里之外,則所云“洞庭湖西岸”必指楚之洞庭湖。也就是説,此“震澤中洞庭”與楚之“洞庭湖西岸”是相通的。由於二傳之間的影響關係,我們可以認爲李朝威對“洞庭”的設計可能瓣香於張説。
此外,另一篇被收録於《太平廣記》卷四九二的傳奇《靈應傳》又再次把前文所及的兩部作品聯繫在一起。這篇作品當受《洞庭靈姻傳》的影響,僅從其命名即可看出。(37)參見李小龍《〈柳毅傳〉原名考》,《文史知識》2019年第5期,頁68—72。更確鑿的證據是,《靈應傳》已將《洞庭靈姻傳》當作“史傳”而引爲“口實”。(38)錢鍾書《管錐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頁1302。程毅中先生即認爲此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柳毅傳》的翻案文章”,甚至其中周寶見九娘子一段“和柳毅在洞庭君宫中第二次見到龍女的情景十分相似,但和《靈應傳》全篇的風格並不相稱”,(39)程毅中《唐代小説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頁235—236。則其襲用《洞庭靈姻傳》之迹甚明。有趣的是,這篇作品在襲用李朝威的同時,也襲用了張説《梁四公記》中《震澤洞》一節。文中九娘子自述家世時説:
妾家世會稽之鄮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室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絶,不忍戴天,潛遁幽巖,沉冤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宫,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仇庾毗羅自鄮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宫,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杰公敏鑑,知渠挾私請行,欲肆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於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40)《唐五代傳奇集》,頁2612。
《靈應傳》此段完全是作者參照《震澤洞》的相關文字而形成的互文,我們可參看《震澤洞》的相關文字:
有會稽郡鄮縣白水鄉郎庾毗羅請行,杰公曰:“汝五世祖燒殺鄮縣東海潭之龍百餘頭,還,爲龍所害。汝龍門之仇也,可行乎?”毗羅伏實,乃止。於是合浦郡洛黎縣甌越羅子春兄弟三人上書自言:“家代與陵水、羅水龍爲婚。”
除此之外,還有幾處也有意照應: 比如作者讓九娘子嫁給了“象郡石龍之少子”,她的丈夫“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期年,果貽天譴”,其實是以《震澤洞》中“象郡石龍,剛猛難化”一句爲藍本的;再如她説梁武帝“召人通龍宫,入枯桑島”,其實張説之作並没有明説所探之龍洞在哪裏,但杰公説此震澤之洞穴通四處,前已言及三處,唯最後的“枯桑島東岸”不知所在,歷來文獻中並無“枯桑島”之名,當爲作者虚構(參下文),《靈應傳》便據此將九娘子之宗族置於枯桑島了。
更重要的是,《靈應傳》在繼承《震澤洞》故事框架之後,同樣把故事的發生地劃定在了吴地。當周寶質疑其“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的時候,她回答説:“妾家望族,海内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内外季昆,百有餘人,散居吴越之間,各分地土。”這裏的“陵水、羅水”即指《震澤洞》云羅子春“代與陵水、羅水龍爲婚”,所以説“皆中表也”;而“洞庭”,則指《洞庭靈姻傳》中的洞庭君,又虚陪了一個“彭蠡”,之所以如此,或許與《尚書·禹貢》有關,其云“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厎定”,(41)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624。將二水之龍皆屬外祖,而其後説“散居吴越之間”,則已承認此處之“洞庭”爲吴之洞庭了。也就是説,無論最早的《震澤洞》,還是我們討論的《洞庭靈姻傳》,以及接受此二傳影響的《靈應傳》,故事表面上的發生地都是吴地太湖。
但這只是故事的表層,細讀文本,會發現這兩篇作品中的龍宫卻可能都在距離太湖千里之外的楚地。
我們先來看一下張説之作。《震澤洞》在提及龍宫時先説“有長城乃仰公馳誤墮洞中,旁行升降五十餘里,至一龍宫”,然後出洞後“爲吴郡守具言其事”,似乎是説此龍宫距離震澤不過“五十餘里”。但杰公説此洞穴有四枝,如前所言,除枯桑島不詳外,餘皆有千里之遥,若果如此之近,杰公之言似無意義。此疑亦有後文可證。羅子春在龍宫得到寶珠後,龍女“命子春等乘龍,載珠還國,食頃之間,便至江岸”,如果確實僅五十餘里,似不必有此一節,還特意點出“食頃”,聯繫《洞庭靈姻傳》的“不遠千里”之途,卻也不過“數息可達”,便知這裏絶不是爲了形容相隔之近,而是相隔甚遠但又極快的意思。也就是説,在《震澤洞》的設計裏,入洞是在震澤之洞庭山,但取寶卻當在千里之外了。
其實,《震澤洞》此段標點尚可斟酌,當代學者均標爲“此洞穴有四枝: 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岸。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42)張國風《太平廣記會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年,頁7450;《唐五代傳奇集》,頁271。筆者認爲,或許當標爲“此洞穴有四枝: 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谿;一通枯桑島東岸,蓋東海龍王第七女掌龍王珠藏”,如果“四枝”之後是句號,則“蓋東海龍王”云云便是籠括“四枝”而言,但前之四枝,有意分在西、北、南、東四方,而“東海龍王”自然只能在東,顯然不可能可蓋言四枝。所以,“東海龍王”的説法只能是僅就“枯桑島東岸”而設——二者均有“東”字亦可爲證。也就是説,作者並未將龍宫設在震澤洞庭山下附近,而是設在千里之遠的枯桑島。這樣標點,便與羅子春乘龍而還的情節合拍了。
這種解釋還有《靈應傳》的支持。其云:“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宫,入枯桑島,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以求異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靈應傳》的作者認爲《震澤洞》所載藏寶之龍宫即在枯桑島。事實上,“結好於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這句引文還有更重要的信息: 在《震澤洞》中,龍女是“東海龍王第七女”,而在《靈應傳》中則變成了“洞庭君寶藏主第七女”,可見在後者的情節設計中,龍宫又當在洞庭,而且是震澤洞穴所通四枝中的“洞庭湖西岸”的那個千里之外的楚地洞庭;同時,作品又將《洞庭靈姻傳》中的洞庭君認爲外祖。即此可知,《靈應傳》作者認爲《洞庭靈姻傳》中的洞庭君就是楚地洞庭湖之龍王。
從以上論述可見,這幾部作品在故事發生地上都設定了顯、隱二處: 故事的開端起於某處,核心情節卻在暗中移置於他處。這樣的設定會讓情節脱離現實的束縛,從而既允許作者肆意鋪敍,又令讀者易於接納。此種故事发生地點的密通與暗换,既讓作品的情節進展上體現出“别有洞天”的勝境,也爲作品藝術生發開啓了法門。但此設定其實並非張説與李朝威的創造,而是有着道教洞天觀念的文化淵源。
五 第九洞天與第十一福地——基於道教“洞天”的聯通
學界對道教洞天福地的觀念已有深入研究。在道教早期文獻中,“洞天”譜系不斷完善,最終形成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的龐大體系。如《藝文類聚》卷七引《茅君内傳》載:“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羅浮山之洞,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曜真之天。”(43)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39。已有“洞天十三六所”的説法。《真誥》正文亦云“大天之内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並有“其第八是句曲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的具體内容,陶弘景注又云:“《傳》中所載,至第十天,並及酆都、五嶽、八海神仙。”此前還有注云“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清虚是王屋洞天名。”(44)陶弘景《真誥》,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195,191。知此時已有成熟的十大洞天排序。完整名單則就目前所見,最早爲唐代道士司馬承禎的《天地宫府圖》,但這一體系的形成一定在此之前,因爲《天地宫府圖》的序説:“真經所載者,此之略備;仙官不言者,蓋闕而未詳。”知其名單當來自所謂之“真經”,因此,還有兩處明云“未詳”或“莫知”,(45)《雲笈七籤》,頁608,611。這也可見他態度的嚴謹。
道教十大洞天中,“第九林屋山洞,周回四百里,號曰尤神幽居之洞天。在洞庭湖口,屬北嶽真人治之”。陶弘景在《真誥》的注中更詳細地説:“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太湖苞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靈寶五符》處也。”則知這第九洞天即吴地洞庭無疑。而楚地洞庭湖中的君山又是“洞天福地”中的第十一福地:“第十一君山,在洞庭青草湖中,屬地仙侯生所治。”(46)《雲笈七籤》,頁620。
知道了這兩處洞庭均名列洞天福地之中後,我們即須説明,道教洞天觀念有一個重要特點,即所有洞天福地都相互連通。
《太平御覽》卷六六三引《五符》(即早期道書《太上洞玄靈寶五符經》)的記載與《真誥》相近,云:“林屋山,周四百里,一名苞山。在太湖中,下有洞潛通五嶽,號天后别宫。”(47)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2959。然多出“下有洞潛通五嶽”之語。此與前文所引《山海經》郭璞注亦相合,這也就能明白前引郭璞《江賦》之語云“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道”之語了,因在道教的設定中,它們本來就相通的。事實上,《真誥》原文中也有類似表述:“此山洞虚内觀,内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古人謂爲金壇之虚臺、天后之便闕、清虚之東窗、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真洞仙府也。”所以,在道教的洞天想象中,此二處洞庭的“密通”是無須置疑的。
有趣的是,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洞庭靈姻傳》中兩處洞庭的互通,還可進一步了解《震澤洞》中更複雜的互通關係。
《真誥》云:“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間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48)《真誥》,頁190,196。與《震澤洞》“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穴溪;一通枯桑島東岸”極爲接近,仔細對勘,會發現後者實據道教洞天敷衍而成。據司馬承禎載:
第五青城山洞: 周回二千里,名曰寶仙九室之洞天。在蜀州青城縣,屬青城丈人治之。
第七羅浮山洞: 周回五百里,名曰朱明輝真之洞天。在循州博羅縣,屬青精先生治之。
第九林屋山洞,周回四百里,號曰尤神幽虚之洞天。在洞庭湖口,屬北嶽真人治之。(49)《雲笈七籤》,頁610—611。
則《震澤洞》虚設之“通洞庭湖西岸”者,即林屋山洞;“通蜀道青衣浦北岸”者,即青城山洞;“通羅浮兩山間穴溪”者,即羅浮山洞。唯一找不到出處的是最後的“枯桑島東岸”,是否爲作者據此處“第十括蒼山洞: 周回三百里,號曰成德隱玄之洞天。在處州安樂縣,屬北海公涓子治之”仿擬而出呢?“括蒼”二字與“枯桑”音近,且有“北海公”云云。另據《雲笈七籤》卷三《靈寶略紀》云:“太上大道君……坐於枯桑之下,精思百日,而元始天尊下降,授道君靈寶大乘之法十部妙經。”中有“枯桑”二字,未知有關係否?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道教與洞天福地相配而行的“十洲三島”中之“扶桑”,《雲笈七籤》載:“扶桑在東海之東岸……地多林木,葉皆如桑……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50)《雲笈七籤》,頁39,603。不但“扶桑”二字音近,且爲神仙所居之“島”,又云“東海之東岸”,重合之處更多。總之,最後一處或許是據太上大道君悟道之處與道教之神仙想象捏合而成。另外,由於司馬承禎與張説大致同時,亦不可完全排除張説所見“洞天福地”譜中有“枯桑島”之可能,比如唐末道士杜光庭爲道教洞天觀念的又一個整理者,在他的設定中,就突然多出一個“滄海島在大海中,高五萬里”的條目,(51)羅爭鳴《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頁386。初看似乎與“枯桑島”亦相仿佛,但在司馬承禎的譜系中卻全無蹤影。
總之,對這一問題的討論,在加入道教洞天福地觀念後方豁然開朗。正如程毅中先生指出的:“儘管在社會生活中佛教戰勝了道教,而在小説領域裏,道教的影響卻比佛教大。”(52)《唐代小説史》,頁351。若不審視道教之文化語境,在小説解讀中便難睹“洞天”之勝。
六 洞庭之寶、龍——道教“洞天”的淵源
作爲道教神仙世界想象的基礎,洞天之中還當有無數寶物。《真誥》即載句曲洞天之内多有黄金、白玉、寶鼎等物(53)《真誥》,頁193,200,203,204。。而被認爲開啓“洞天”建構的道書《抱朴子》更云吴王“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即《靈寶經》之事。(54)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08。再看《靈寶略紀》述《靈寶經》之起源,從梵氣天尊到元始天尊,傳到帝嚳,再傳至禹,“禹未仙之前,乃復封之,鎮乎北嶽及包山洞庭之室。距吴王闔閭時,王出游包山”,見一人名山隱居,“隱居諾,乃入洞庭,訪游乎地天一千五百里,乃至焉。見一石城”,(55)《雲笈七籤》,頁38—40。終取得《靈寶經》。這裏提及“包山洞庭之室”以及山隱居“入洞庭,訪游乎地天一千五百里”很值得注意。似乎其從包山入,卻走到一千五百里之外了,根據前文推算,這個距離恰恰可以走到楚地洞庭。這一尋寶的過程是否會對前述《震澤洞》及《洞庭靈姻傳》産生影響呢?這是很有可能的。那麽,楚地洞庭也有寶物嗎?王嘉《拾遺記》所載“洞庭山”云:“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其山又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宫觀異常。乃見衆女,霓裳冰顔,艶質與世人殊别”,(56)王嘉《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235。此文前云“楚懷王”、“瀟湘”乃至“屈原”云云,顯爲楚地洞庭。而其靈洞中不僅有寶藏,還有仙女——這就又回到《洞庭靈姻傳》的故事框架中來了。
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是司馬承禎《天地宫府圖》之後重新梳理道教洞天的文獻,對後者闕疑者有所補充,同時又有改動。比如把林屋山洞的主神從“北嶽真君”改爲“龍威丈人”。(57)《杜光庭記傳十種輯校》,頁388。這個龍威丈人是誰呢?前文引陶弘景《真誥》注中説:“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太湖苞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靈寶五符》處也。”《靈寶略紀》亦云:“孔子愀然不答,良久乃言曰: 丘聞童謡云:‘吴王出游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則龍威丈人即入洞得書的山隱居。於是,在道教早期文獻中,林屋洞天主神或云天后、或云北嶽真君,龍威丈人只是偶入仙洞得書之人。而到了杜氏這裏,則將其作了置换。不得不説,這一改立讓林屋洞天即包山洞庭與紫文金簡之寶書産生了關聯,甚至關鍵性人物名爲“龍威丈人”似乎也是《洞庭靈姻傳》以“龍”爲故事核心要素之觸媒之一。
另外,林屋山洞的稱號也值得一提。司馬承禎云其“號曰尤神幽虚之洞天”,杜光庭或許認爲此名不好理解,以其有誤字而將“尤神”改爲“左神”。然而,“左神”與“尤神”其實一樣不可解,又無文獻援證。私以爲,或許原文爲“龍神幽居”,早期道經的抄寫較爲紛雜(參考《真誥》一書之流傳即可知),或許抄寫者將“龍”字寫爲草體,頗類簡化之龍(“龙”),抄録者不識,遂依字形定爲“尤”,而杜光庭又因其不可解而據字形臆爲“左”,卻可能都是錯誤的。若果如此,則此洞天在更早的時代便與“龍”産生了聯繫,(58)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敍録》(增訂本)論此“龍女報恩及龍女與世人婚戀,均爲佛經母題”(頁306—307),重點在故事而非要素。從而成爲《洞庭靈姻傳》故事的秘密基因。
這裏的寶物雖然仍是道教洞天觀念中的應有之義,但在《洞庭靈姻傳》卻呈現出不同的意義。我們可將此傳與《桃花源記》作比,二者的敍事世界建構均受道教洞天觀念之影響,然同中有異。《桃花源記》將此洞天描畫爲躲避戰亂之世外桃源,有非常鮮明的道教洞天色彩,(59)參見張松輝《“桃花源”的原型是道教茅山洞天》,《宗教學研究》1994年第Z1期,頁47—52。陶淵明對洞天觀念的接受也更合於道教的設定: 重點不在於寶物,而在仙境。所以,作者對失去的桃源無比痛惜,最終也清醒地讓誤入洞天之人不帶走一片雲彩而重回濁世。《洞庭靈姻傳》的作者則只是借用道教觀念,既無道士架空幻設之必要;又無陶淵明身處亂世之痛切。故寫柳毅雖有緣得入洞天,卻並未淹留,作者之歡樂仍全神貫注於塵世,入龍宫便大肆得寶,然後便去洞天而回人世;甚至於龍女追隨配嫁之後,寫其“相與覲洞庭”,也不過“既至而賓主盛禮,不可具紀”一筆抹過,又立刻“徙居南海”,再入紅塵。不過,有趣的是,柳毅與龍女最後仍“相與歸洞庭”,即重歸於洞天之中,原因卻是“洎開元中,上方屬意於神仙之事,精索道術,毅不得安”,則其敍述脈絡,仍重回道教洞天設定之内,《真誥》反覆引及“兵病不往,洪波不登”的世外洞天仍是逃避現世紛擾的“桃源”。(60)《真誥》,頁191,197。前引《聊齋志異·織成》末云:“相傳唐時柳毅遇龍女,洞庭君以爲婿。後巽位於毅。又以毅貌文,不能攝服水怪,付以鬼面,晝戴夜除;久之漸習,忘除,遂與面合爲一,毅覽鏡自慚。”(61)《全校會注集評聊齋志異》(修訂本),頁2087。從《洞庭靈姻傳》角度來看,實是續貂之惡札,因爲柳毅重返的並非地理意義上的楚地或吴地洞庭,而是神仙所居之洞天福地、世外桃源。